107岁马识途,“子弹”还在飞
许晓迪
2010年,电影《让子弹飞》上映,改编自《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首映式上,姜文笑言:“马老是我的保护神。古人有言:‘信马由缰(姜)’嘛。”
这一年,马识途95岁,坐着姜文的“子弹”再度飞入大众视野,尘封多年的《夜谭十记》也被发掘出来,成千累万册地赶印。一些年轻人找他签名,亲热地自称“粉丝”。
11年后,2021年1月22日,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蔡林君随社长黄立新拜访马识途后,抱回了三大卷甲骨文研究笔记。
刚过完107岁生日的马识途,那天兴致勃勃地说了好多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事儿,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感觉他还是当年那个学生,充满学习的激情。”蔡林君对记者说。
当年,意欲在文字学中深耕的马识途,因革命需要离开昆明,所有笔记文稿付之一炬。此后,他冒险犯难,九死一生,战斗到1949年,又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如此70余年,与甲骨文绝缘。
大师们的谆谆教诲,马识途念念不忘。2017年,写完《夜谭续记》后,他开始投入古文字研究,历时3年多,即使中途生病住院,也记挂着书稿,一出院又立马进入工作状态,废寝忘食。
编辑书稿的过程中,蔡林君震惊于马识途的高效。3月23日,她把排好的大字版校样带给马识途,5天后收到微信,让她取回。“马老看着那一摞纸,很得意、很自豪的样子,像是说,‘我都看完了啊。’”他的女儿马万梅告诉她,马识途这些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拿着放大镜一页页地核查书稿,几乎一动不动。

书中的甲骨文,蔡林君请了书法家重新撰写,为此要借马识途的原稿一看。“听我说要借走原稿复印,马老手按在稿子上,恋恋不舍的,直到我说出‘明天一早就还给您’,才松了手。”
这是一份弃学70余年的学生迟交的作业。如果回到1941年的昆明,让那个26岁的青年再做选择,他会何去何从?是走向象牙塔,还是置身十字街头?
107岁的马识途说,不会做第二个选择:“我入党就宣誓:终身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80年前的秋天,马识途来到春城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后转入中文系。
这一年,他26岁,作为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家伙”,和少男少女们一起参加食堂的“抢饭战斗”,泡在茶馆里读闲杂书、论天下事。教室是土坯房,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叮叮咚咚地淹没了讲课的声音;先生们穿着寒碜、面有菜色,却是八仙过海、百家争鸣。马识途见过南北两个大教室的对垒,南边的教授听到北边的教授批评自己,跑过去当面对峙,两人吵得面红耳赤,然后互相握手,一同有说有笑地回家去。
“教授天团”众星璀璨,有的课程火爆,窗口挤满旁听的人;有的则出名的冷门,如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专修的只有五六人,马识途是其中之一。在新书中,他凭记忆复现了当年的课堂。
第一堂课,唐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副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又画上两个奇特的字符。这副对联讥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唐先生指着黑板上“东”“西”两个古文字:“骂得就是他们——不是东西。”
最后一堂课上,唐兰的“送行谈话”更是真切动人:“古文字学知识浩如烟海,涉足其间的人不多。有的人在海边才湿了鞋,眼看波涛汹涌,就知难而退了;有的人下海游了去,也有半途而废的,还有被水给淹没的。只有很少的人有坚强的意志,会锲而不舍、乘风破浪,向隐约渺茫的彼岸奋勇前进,虽不免载沉载浮,吃不少苦水,终会到达彼岸……相信学术的道路虽然崎岖,但总有中国人不断探索,哪怕不过识破一字,也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山河沦陷、硝烟炮火中,唐兰、罗常培、闻一多、王力、陈梦家等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家,笳吹弦诵在山城,致力于中国文明密码的破译与传承。而对马识途来说,闯入文字学的大门,却是一场“别有用心”的计划。
“当年,国民党特務四处追捕我,南方局领导令我走避昆明,长期埋伏。为了更好地隐蔽身份,我化名考入西南联大,成为学生。”马识途对记者说,“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革命工作,正为此,我必须学好学术课程,当然吃力,但有兴趣。”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以一本方言记作为毕业论文的“高龄学生”马千禾,是中共西南联大的支部书记。而这样的“改头换面”,马识途已经历过多次。“马千禾”这个名字,就是他再三试验墨色和字体后,在高中毕业证的名字上添了那“天衣无缝”的一撇。而那个本来的名字“马千木”,对他已十分陌生。
1931年,少年马千木走出兵匪猖獗的四川,远赴北平,报考高中。此后7年,他浪迹京沪,随逃难的人群爬上火车车顶,一路拉扯照应;和参与“一二·九”游行的学生踏平铁丝网,勇往直前。因怀揣“工业救国”梦,他考入中央大学化工系,抗战爆发后,一度想去大茅山打游击。
1938年,马识途对着两本书中的党旗图案和马克思照片,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决定改名“马识途”,意为找到道路,老马识途。这一年,马识途23岁,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他奔走于湖北农村,有时扮成收山货的商人,混入土匪窝;有时扮成小贩,挑起担子游乡串院;有时则“本色演出”,扮作寒酸的知识分子。路上吃粗劣的苞米加红苕饭,就着辣椒萝卜青菜;晚上住在鸡毛野店,被臭虫、虱子咬出一身疥疮。有一次,他披上国民党军官的“老虎皮”,做了一个军粮督导员,因为记账时太规矩,被老会计指点敲打,只能随着他们假装“贪污腐化”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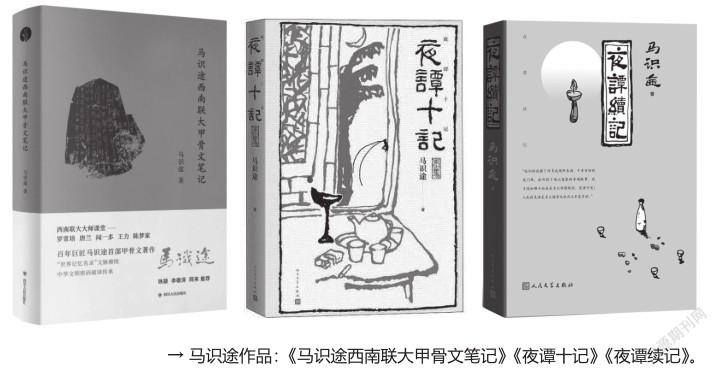
1939年底,经组织批准,马识途与刘惠馨结婚。他们的家在湖北恩施一处柑橘园中,那里也是鄂西特委的交通站。两个年轻人快乐地做起了诗:
我们结婚了/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我們也找到了证婚人/可不是亲戚或社会名人/而是我们遭遇的艰辛/我们也找到了介绍人/可不是说得天花乱坠的媒人/而是我们矢志不渝的革命/……我们永远不会分离/直到我们该永远分离的时候。
“分离的时候”来得如此快。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鄂西陷入白色恐怖中。因叛徒出卖,特委书记何功伟、妇女部长刘惠馨被捕,1个月大的女儿也随母亲关进监狱。马识途强忍悲痛,疏散组织,转移同志,只身赴重庆,夜上红岩村,按照“长期埋伏,继续力量”的指示,奔赴昆明。
这一年11月17日,刘惠馨、何功伟壮烈牺牲。此前,马识途的三哥马士弘曾到狱中探望这位共产党弟媳。4月的天气,她穿着空心棉袄,内衣撕了做尿布;没有奶,就把馊饭嚼烂,一点点喂给孩子。看到兄长难忍心酸,刘惠馨从容一笑:“三哥,你婆婆妈妈的干吗。”
一年后,马识途为战友和妻子写下《遥祭》:“你用鲜血把人民的红旗,染得更为鲜艳而美丽。我将举起它,永远向前,再不流辛酸痛苦的眼泪。”
此后的生活,是虎口脱险、九死一生。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叛变,马识途坚持留在成都,指挥组织疏散。他将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改了发型,刮掉八字胡,黑框眼镜换成假金架子眼镜。平常戴的罗宋帽、穿的风雨衣,翻个面就成为另一套行头。他想了一个假名“张司光”,亲手制作假身份证,危急时“司”字左边加一竖,“光”字头上改一笔,就能以“张同先”金蝉脱壳。为去香港汇报工作,他打扮成一个猪鬃出口商,搭着“三青团”包的商车逃出成都;绕道贵阳、柳州,混在商人堆里去妓馆吃“花茶”,混过宪兵的检查;到达广州后,又西装革履打扮一番,大模大样地登上头等车厢,终于平安到达香港。

这一年12月,当马识途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随解放大军进成都时,他想起几个月前那场险象环生的逃亡。此刻的成都,锣鼓鞭炮齐鸣,群众载歌载舞,花束漫天抛撒。第二天,全体地下党召开第一次集体大会,当马识途响亮地说出“同志们”三个字时,全场鸦雀无声,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他们有的从大雪山区的游击队赶来,脸上还见风霜;有的刚刚走出监狱,脸色苍白,铐痕犹新;有的刚做完策反工作,还穿着国民党的黄军服;还有更多的同志,没能走进欢乐的会场,永远地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为拍摄纪录片《百年巨匠——马识途》,导演梁碧波带领团队,沿着马识途的生命轨迹实地走访了一遍。他们找到当年马识途和刘惠馨生活、战斗过的鄂西特委交通站。“资料上说,那里有一片红色的山岩,当时根本不信。到当地一看,真有一大片山岩,像一面红旗,特别震撼。”梁碧波对记者说。
刘惠馨牺牲19年后,马识途在北京找到了他们的女儿。1960年“五一”节那天,父女二人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百感交集,热泪横流。“一种负疚的感觉猛袭心头,我是应该写一点纪念他们的文字了。”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因为偶然写了一篇小说《老三姐》,被作协书记处的领导发现了“富矿”,于是半推半就地写起小说,不为出名图利、在艺术殿堂占一席之地;只为服务革命、教育青年。一个个短篇,都是他加班开夜车,抓开会时的会前会尾,一点点写成的。
1960年夏天,马识途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一连开了180多个夜车,回家面对桌上的稿纸就开始头疼。主人公柳一清、贺国威的原型,即是刘惠馨、何功伟两位烈士,马识途写出了他们的钢铁意志,也不回避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夫妻爱、骨肉情、父子恩。彼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说杀气腾腾,小说几经删改,“所有流泪的地方都把眼泪抹去”。
1966年,《清江壮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个月后,成为60部“大毒草”作品之一。“文革”中,作家阿来读到了这部“禁书”。他告诉记者:“那时的革命叙事都是‘样板戏’那一套,看似光辉无比,实则假大空。《清江壮歌》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我们这些中学生享受了读‘禁书’的快感,也看到了革命更艰难、更曲折、更真实的一面。”

“禁书”的作者马识途,此时已斯文扫地、家散人亡。这个“老革命”被“造反派”押上卡车,戴着高帽游街,“当众演猴戏”;还被安排劳改,每天打扫厕所。他把那个臭气熏天、尿水横流的厕所收拾得干干净净,并写了两张告示,让大家遵守公德,“小便向前一步”“屁股对端,大便入坑”,下面署上“本所所长白”。三天两头,他被各大单位“订购”去批斗,渐渐习以为常,索性低头默想几句打油诗:“今天革命叮当响,明天枷锁锁革命。造人反者人恒造,有理无理何能分。满街吹打谁上台,喇叭声里又一年。谁上谁下我何干,拉上窗帘袒腹眠。”
在昭觉寺的“文明监狱”,马识途被“监管”了6年。在这里,他除荒草,整道路,垒洗衣台,修洗澡间,还把西园空地开垦出来,种菜栽花。因为总要写交代材料,墨水稿纸供应充足,利用这个“优势”,马识途重操旧业,将记忆底层的人和事重新翻腾出来,偷偷写下50多万字的作品和文章。
当文艺的春天到来,这些“地下写作”破土而出,马识途迎来了文学生涯的新生。
“上世纪80年代,《青年作家》杂志每期刊登马老的讽刺小说,我們追着看。它有针砭时弊的一面,又有四川人特有的那种善意、幽默的批评。”阿来说。
1993年,刘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后被分配去编辑《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稿子是马老从成都寄来的,还附上了他画的一串红辣椒,我们拿来做了封面。”后来,马识途来北京看望住院的人文社老总编韦君宜,刘稚第一次见到了80多岁的老作家,“强壮高大,中气十足,精神头很足”。
韦君宜和马识途是老朋友,一同在白区做过地下工作。1982年,正是她向马识途邀约创作,促成了《夜谭十记》的出版,创下20万册的轰动销量。这部被作者自称“乱谭”的书,以旧中国衙门里的10位穷科员为主人公,他们结成“冷板凳会”,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吹野狐禅。10个故事,上至浮华官场的钩心斗角,下到市井小民的悲欢离合,俨然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明上河图”。
这些故事和素材,都来自马识途的“职业革命家”生涯。韦君宜约他写续篇,马识途欣然应允,开始动笔写提纲。后来,韦君宜突然中风,加之马识途公务繁忙,写作计划就此搁下。
20多年后,95岁的马识途因《让子弹飞》一朝“走红”。他的头脑“又开始发热”,想把搁置许久的续篇写完,其间动笔又停笔,战线越拉越长。后来,癌症两度来袭。马识途抱着当年搞地下革命不畏死的态度,奋力写作。初稿完成之际,医生告诉他,肺上的肿瘤阴影不见了,血液指标也完全正常。他戏说道:“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吗?”
2017年,刘稚来到马识途家,看到了摊在桌上的《夜谭续记》手稿。“马老说现在不能给我看,还得再整理、润色一下。”一年后,马识途来北京参加活动,将定稿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天下午,刘稚听他讲了一个爱情故事:抗战时期,一位少数民族的女族长,爱上一位归国华侨。日本人把滇缅公路炸毁,女族长带领全族修路,盼着爱人开着车子来相见。“他说,我脑中的故事太多了,但是我老了,写不出来了。”
2020年,《夜谭续记》问世,旧时代的“冷板凳会”变为新中国的“龙门阵茶会”,不变的是四川人以四川话讲四川故事的“乱谭”本色。与新书一同到来的,是马识途一封深情的“封笔告白”,后面附上5首旧体诗。“‘报到通知’或上路,悠然自适候召书。”他期待着“天能假岁”,见证党的百岁生日,到那时向马克思报到,也能悠然上路,死而后已。
“我看他感叹老之将至,恋恋不舍的,赶紧去探望。我告诉马老,写完书有点惆怅,这是正常的;但要说封笔,我绝对不信。”阿来说,“他说过,100岁之后,要像小孩一样,一岁一岁地活。101岁是1岁,102岁是2岁,107岁就是7岁。”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快推出时,阿来去探望马识途:“怎么样,没封笔吧?”
笔没封,另一个愿望倒是实现了。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马识途端坐于电视机前,看到空中护旗梯队从天安门掠过、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动得一直小声哼唱国歌的调子。
这位107岁的老人,始终关心着中国与世界。“还有哪些故事,是想继续写给、讲给大家听的呢?”“一言难尽,文缘未了,终身遗憾。”他如此回答。
“子弹”还在飞,马识途的“枪”里还藏着许多传奇。
(摘自《环球人物》2021年第2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