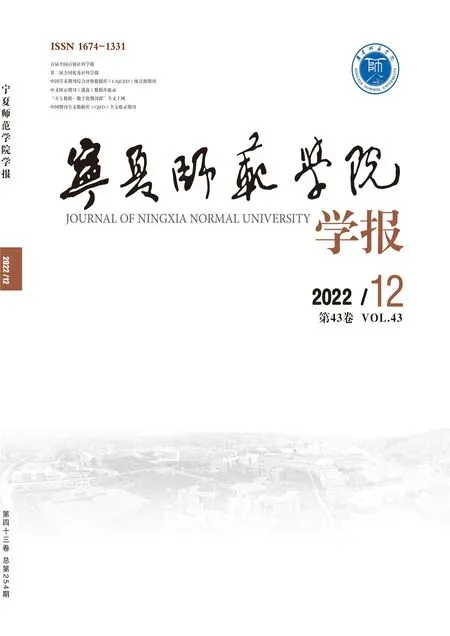梁启超社团思想述论
马 艾
(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维持官、民二分格局,官府之外,除了以血缘姓氏为纽带的家族,基本上不存在合法的组织结构。而社会各领域一旦产生自发的组织——如白莲教、天地会等秘密社会组织,往往会被官府予以镇压,这是中国古代官僚制集权政治的狭隘性使然。
近代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侵入,传统社会结构逐步瓦解,一批依托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型社会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与新的经济关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他们有能力突破旧的社会藩篱,创造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戊戌变法运动期间,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在北京、天津、长沙、广州等地创办报纸、举办学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戊戌变法虽很快被顽固派所镇压,但办报、办学会经此滥觞,辛丑之后再度勃发,遂成一代之风气。而近代中国社团的兴起,直接推动了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在旧中国土壤中的生根发芽,这一切都离不开梁启超先生的不懈努力。因此,梁启超的社团思想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潮的重要内容,对于开启民智作用斐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梁启超社团思想的渊源
(一)西方社团观念传入中国
近代以降,西方传教士不断东来,他们在中国以“社团”的形式开展传教、设会、办学、行医、译书等活动,创办了学堂与学会结合的教育类社团、“广学会”与《万国公报》为代表的传媒类社团、中华博医学会为代表的医疗慈善救济社团等,对近代中国社团组织的兴起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如梁启超先生就认为:“欧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学校振之于上,学会成之于下,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自百年以来也”[1]。此外,梁启超与广学会负责人李提摩太关系紧密,甚至担任李提摩太的秘书。强学会建立后,包括李提摩太在内的多位传教士入会,亦因此,梁启超明辨了西方学会与中国传统会社的区别所在。教会与传教士以及西方学会对中国学会的影响,李提摩太记忆犹新,康、梁等志士常与之畅谈:“并发表关于改革中国的演说,并且进行讨论”,“会员们感到了深刻的兴趣,他们请我留在北京几个月,以便向他们建议如何进行工作。”[2]戊戌维新运动期间,若干上海青年建立青年维新会(Tunior Reform Society),并在杭州、南京、武昌、天津设分会,他们纷纷找李提摩太,请他帮助修改维新会章程,讨论如何才能启迪国家[3]。
(二)开始关注西方社团
对于西方国家的议会、政党等,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就引起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关注,不过当时还只是停留在中国古代的朋党观念上,如马建忠就认为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凡所官者,皆其党羽”[4]。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现代西方社会组织,学会、政党等名词才渐为世人所熟知。例如,梁启超就认为,学会“唯强吾国之知”“舍学会其曷从与于斯”,足见其对学会的重视程度,认为救国的当务之急是建学会,成团体,开民智。另外,康有为也数次提到创立学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各直省设立商会……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泰西国势之强,皆借民会之故”,并致力于创立诸如强学会、保国会、湘学会、农学会等新式社会团体。
二、梁启超社团思想的内容
(一)主张“合群”
梁启超认为:“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数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亿万人群而成国,兆京陔秭壤人群而成天下。无群焉,曰鳏寡孤独,是谓无告之民。……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色人,美洲、南洋、澳岛之红人,所占之地,居地球十六七,欧人剖之钤之,……亦曰唯不能群之故。”[5]可见,梁先生断定,近代以来,西欧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典范,能够在世界各大洲实现殖民统治,其根源就在于能“合群”。
对于合群的重要性,梁先生认为:“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自然淘汰之结果,劣者不得不败,而让优者以独胜云尔。优劣之道不一端,而能群与不能群,实为其总原。”[6]不仅是飞禽走兽,世间万物生存的基石都是“群”,符合这一规则的便是符合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人类更是如此,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如民族、国家等,如若想要生存发展,不被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所淘汰,合群是根本法则。
(二)推原不群之故
对于中国人不能合群的原因,梁启超提出以下四个根源:
第一,“公共观念之缺乏”[7]。人们一般合群是因为“不得不群”。因为“以一身之所需求所欲望,非独力所能给也……于是乎必相引相倚,然后可以自存”。并且认为如此这般便是“公共观念”,实乃大错特错。“若此者谓之公共观念。公共观念者,不学而知……”也就是说,凡事的出发点是利己,包括合群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谋取个人私利,根本算不得合群,并无半点公共观念。“故真有公共观念者……牺牲其现在私益之全部分,以拥护未来公益,非拂性也,盖深知夫处此物竞天择界,欲以人治胜天行,舍此术末由也。”[8]换言之,真正的公共观念是与国人的“合群”思想之初衷完全相反,也就是合群是为群之利益而非个人利益。
第二,“对外之界说不分明”[9]。这是梁先生提出的国人不群的原因之二。在先生看来,内外分明是成团之要务,意即“凡结集一群者,必当先明其对外之界说,即与吾群竞争之公敌何在是也”[10]。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抵御外侮、自强救国奋勇争先,所以应首先明确国家意识,才能爱国救国。为了说明国家为最重要的群体,先生分别以希腊、英国、日本的历史为例,阐明内外之别。“昔希腊列邦,干戈相寻,一遇波斯之来袭,则忽释甲而相与歃血焉,对外之我见使然也。昔英国保守、自由两党,倾轧冲突,曾无宁岁。及格里迷亚战争起,虽反对党亦以全力助政府焉,对外之我见使然也。昔日本自由、进步两党,政纲各异,角立对峙。遇藩阀内阁之解散议会,则忽相提携结为一宪政党以抗之,对外之我见使然也。”[11]
第三,“无规则”[12]。虽然中国有“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俗语,似乎人人都以为所谓“国法”“家规”就是社会规则,即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实则不然。时至今日,中国人对法律的理解都是非常落后的。在梁启超先生看来,“法律凡一群之立也……莫不赖有法律以维持之。其法律或起于命令,或生于契约”[13]。而西方诸国之所以文明,是因为个人与群体都“善为群”,并遵循一定的法律法规,“小而一地一事之法团,大而一国之议会,莫不行少数服从多数之律,而百事资以取决”[14]。相比之下,中国所谓的“善为群”,只是对独裁专制的“予一人”之唯命是从,正所谓“以一二人之意见武断焉梗议焉”,这也是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无规则”表现之一。西方诸国的社会组织进步的原因就是都会“委立一首长,使之代表全群,执行事务,授以全权,听其指挥”。即使是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进步人士,也认为“以少数服从于多数,是为多数之奴隶也;以党员服从于代表人,是为代表人之奴隶也”[15]。梁启超先生反驳道:“嘻!是岂奴隶之云乎?人不可以奴隶于人,顾不可以不奴隶于群。不奴隶于本群,势必至奴隶于他群。”[16]认为合群不是奴隶思想,不是个人被群体所奴役,个人“服从多数,服从职权。即代表人正所以保护其群而勿使坠也。而不然者,人人对抗,不肯相下;人人孤立,无所统一”[17]。这一思想极其符合社会进化论,也就是人类社会所以脱离动物界,其要害就是创制组织,而且发展进化社会组织,梁先生的“合群”说就是号召人们将中国落后守旧的组织解体摧垮,向西方学习,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形成新的社会规则。
第四,“忌嫉”[18]。梁启超认为无论是中国古训,还是以往被误解的边沁学说,所阐扬的都是一个正理,即“毋狃小乐而陷大苦,毋见小利而致大害,则其于世运之进化”[19]。为此,梁启超先生专作《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正本清源,说明边沁乐利主义与合群思想的契合而非背离。“汉宋以后,学者讳言乐,讳言利:乐利果为道德之累乎?……毋亦以人人谋独乐,人人谋私利,而群治将混乱而不成立也。”[20]这是迄今国人纠结的问题之一,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矛盾,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精神从来都是抹杀个人的一己私利,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如此。梁先生并不认为西方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对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只有负面,恰恰相反,他认为,只有个人的要求得以满足了,才是群体目标实现的基础。“夫人群者,无形之一体也。而其所赖以成立者,实自群内各各特别之个人,团聚而结构之。然则所谓人群之利益,舍群内各个人之利益,更无所存。”[21]可见,梁启超先生认为乐利主义与合群思想是辩证统一的,这一观点的提出,无疑对于传统的旧式思想是一种纠正,也让人们更加明确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总之,成群是梁启超先生的主张,在先生看来,阻碍合群的因素有很多,“如傲慢,如执拗,如放荡,如迂愚,如嗜利,如寡情,皆足为合群之大蠹,有一于此,群终不成”[22]。当然,最重要的阻碍因素是封建专制主义,在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对比后,认为古代中国的所谓“群”是“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其所以为群者,在强制而不在公意。则虽稍腐败,稍涣散,而犹足以存其鞟以迄今日”[23]。而真正近代的群的形成也是任重道远,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当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所谓有新思想、新知识、新学术之人,如是如是。亡中国之罪,皆在彼辈焉。呜呼!呜呼!则吾侪虽万死其何能赎也!”[24]
(三)提出合群之道
对于合群之道,梁启超先生有如下思考。
首先,倡公德。
梁启超先生在《论公德》一文中提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若此者谓之公德。”[25]何为公德?所谓“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26]。无公德不能成国,无公德不能成团,无公德亦不能成群,公德是现代国家的基础,现代社会的基石,中国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中国传统文化并未太多涉及公德,倡导的更多则是私德,“虽有无量数……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27]。梁启超先生以《论语》《孟子》等传统典籍为例,说明其中所阐扬的道德主要是私德,“吾国民之本铎,而道德所以出者也……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谟》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论语》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知命知言’,《大学》所谓‘知止,慎独,戒欺,求慊’,《中庸》所谓‘好学,力行,知耻’……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之资格,庶乎备矣”[28]。所谓德行,更多指的是个人的修行,而非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与贡献。
其次,兴学会。
兴学会是戊戌维新思想家们创办社团的肇始。在梁启超先生看来,西方国家日趋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会遍及各个领域,对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都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彼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工学会,有法学会,有天学会,有地学会,有算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有光学会,有重学会,有力学会,有水学会,有热学会,有医学会……莫不有会。”可见,学会于泰西诸国之重要,覆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系统有序的学会网络。不仅如此,对于这些学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人才日众,以为国干,用能富强甲于五洲,文治轶于三古。”[29]因此,梁启超先生极力主张广建学会,而且中国当时的社会已非古代“疾党如仇,视会为贼。是以佥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30]的状态。“今天下之变亟矣。稍达时局者,必曰兴矿利,筑铁路,整商务,练海军。”洋务运动迈开了中国近代化一小步,前所未有的将“西学”与“中学”相提并论,“自强求富”不仅是口号,也是迫在眉睫的救国之法。无论是整商务,练海军,还是兴矿利,筑铁路,都是自强求富最重要的途径,这一点可以说清廷上下众人皆知,但是最棘手的是人才缺乏,学会更无从谈起。所有“西学”的学科与领域,对于中国而言,可谓白纸一张,都需要从头学起,所以,梁先生提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31]。
除了分析学会的重要性,梁启超先生还提出了:“一曰胪陈学会利益……十六曰公派学成会友,游历中外,以资著述。”[32]以及建立学会的具体十六种举措。该套举措,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不可谓不完备,不可谓不高明,“遵此行之,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33]在梁启超等诸位先生的带领与倡导下,新知识分子以学会的建立为先导,广泛建立各类社会团体,也为科举制度废除后仕子表达政治见地和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机遇与舞台。
再次,改科举。
梁启超先生疾呼:“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唯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34]毋庸置疑,只有选拔人才的方式与内容发生质的改变,中国知识分子才会摆脱“饱学的无知”,近代意义的社团才能真正兴起,也才能从方方面面真正推动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化的轨道。新知识群体有着旧式知识分子难以具有的新的知识结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以梁启超先生为先锋的新知识群体,在短短几年内所建立的社团组织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在国难当头亟须其救亡图存之际,新的使命又促使他们有了新的追求,于传统经籍之外寻求社会进化之道,以图富国强民。然而历史终归是现实的,新、旧知识分子的交替过程并非朝夕之间,更非今人所能料想之事。不难想象,千余年居于四民之首的旧士人,在科举废除之后,昔日诗书墨卷之路断绝殆尽,陷入不得不另谋出路之窘态。无论是投笔从戎,还是“出于商与士之间”,抑或“出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的尴尬,都未曾阻挡新士人成为时代骄子的探索之路。毫无疑问,新式学校乃当务之急,西学亦必与之齐头并进。
其一,兴学校。梁启超先生在《论科举》一文中,提出了改科举的“三策”,上策即兴学校,也就是改革科举制度,变革选拔人才之法。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起于隋代的科举,是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的否定物,对隋唐以后的中国社会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自明代以后,八股大盛,使得本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读书人变成“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科举取士之弊端已暴露无遗,遭到先进知识者的批判。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数篇文章,如《论科举》《西学书目表》《学校总论》等,希望能自上而下的改革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其中反映的思想在当时实在可谓振聋发聩,如“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35]。梁启超对明清时期科举选拔的所谓“士人”已是绝望至极,道:“以国事民事托于此辈之手,欲其不亡,岂可得乎?况士也者,又农工商贾妇孺之所瞻仰而则效者也。士既如是,则举国之民从而化之。民之愚,国之弱,则由于此。”[36]1901年,清政府开始对科举制度的考试科目进行改革,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作为乡会试的命题,并且不准再用八股文程式。之后,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张百熙等先后上书递减科举,清廷也相应地采取了改革措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终于走到了末路尽头,代之而起的是新式学堂的兴起。同时,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也已不再是科举考试的结果,而是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了解的程度。
其二,学西书。“开智”与“新民”是启蒙的钥匙,也是梁启超先生力主的救国救民之途,亦因此,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受西方近代文明启蒙后,或把自己所见的西书开列成表,或把自己的观感和其他真切的认识记录在案,或译介西方近代文化,去启他人之蒙。汤因比说:当两种文明发生碰撞交黔之时,知识分子便作为一种‘变压器’而出现了。他们承担着双重使命:一是学习先进的文明并把其精华传播到全社会中去,二是慎重地用全新的眼光‘重构’固有的文明,使之获得新生而生存下去”[37]。陈旭麓先生提出,近代中国人“接受启蒙的途径大致有三:一是沉潜于‘西人公理公法之书’”[38]。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来使国人树立崭新的人生理想、价值信仰系统和行为规范,“没有崭新的人生理想、价值信仰系统、行为规范的确立,社会近代化其路无由”[39]。合群是一个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基础,也是被启蒙的基本表现。饱受中国古代传统“君子群而不党”思想影响下的读书人,对现代合群思想是戴有色眼镜看待的。要想摘掉眼镜,改变旧思想与旧观念,读西书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40]
最后,办报刊。报刊与团体作为新事物,几乎是同步出现于大江南北,成为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标志之一。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鼓吹变法,并组织强学会,奠定了此后学会团体发展的模式。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更加刺激了先知先觉者的觉醒,民主革命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在这一背景下,民间团体不但数量增多,类型也由单一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多种功能的团体,据《苏报》《大公报》等报刊的报道记载,1901—1904年,江苏(含江宁)、浙江、广东等地,先后建立新式社团271个(不含分会)[41]。其他如商会、教育会、农会等学会也相继建立。
三、结语
各类新式社团的出现,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关系正在重新分化组合。中国国内社会分工细化,社会群体分层日益明确是历史的必然。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有所不同,必定希望有渠道表达和维护其共同意愿,社团便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不同群体进化出来的新式组织按照新的社会要求进一步走向聚合,不断扩大社会地位与影响,逐渐置喙于地方和国家事务。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社会联系的纽带已不再是古典式的血缘、宗法和地缘,近代新式社团已经逐渐取而代之。而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先生的社团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