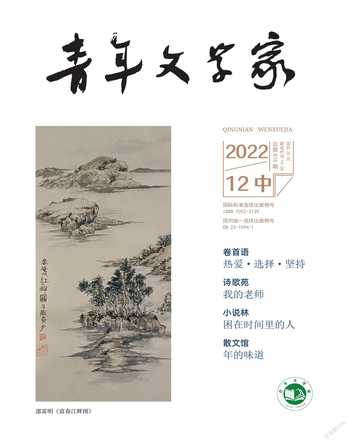试论杜甫诗歌中的儒家伦理观
董瑜婧

杜甫的诗歌和思想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广为流传,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孔孟等儒家思想作为杜甫诗歌中不可忽视的思想传统存在,也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体现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笔者将浅析在杜甫诗中体现孟子提出的“亲亲、仁民、爱物”观点,通过孔孟儒学的角度分析杜甫诗歌的伦理观。
杜甫出生于百年望族的封建官僚家庭,有着极厚的家学渊源。杜甫在为其祖母所作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中提到家族祖先说:“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在《进雕赋表》中,杜甫又称:“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可见杜甫为自己的家族传统而自豪。而杜甫的一生也遵循孔孟之道,把“奉儒”与写诗当作自己事业的追求,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进雕赋表》引《杜甫全集校注》)。杜甫历经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数次入长安,又遭逢乱世,战争四起,在长安蹉跎十年后亲历安史之乱,陷贼长安,后又被贬华州,最终向西南漂泊,一生颠沛流离。故杜甫诗歌题材丰富,其中一以贯之的儒家思想也流露于作品之中。杜甫在政治抱负上,始终秉承直言进谏、忠君报国的精神,渴望实现政治清明、太平盛世的理想。流浪漂泊不定、陷落战争逃亡时,心系百姓、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身上隐现的儒家传统思想与先秦时期孔孟之思想相互照应,无形中形成了对过去儒家思想的一种复现。
《孟子·尽心上》中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语,这句话与早期儒家思想最为贴近。儒家按照孟子之言对人伦之序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亲亲”“仁民”“爱物”。本文将尝试从“亲亲”“仁民”“爱物”三个层面,对杜甫诗歌中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进行探讨,以明晰杜甫诗歌中的儒家伦理思想。
一、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亲亲”观
“亲亲”观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
首先,是亲君王。儒家特别重视尊王,孔子在《春秋》中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又重视夷夏之别,“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还赞扬在维护“诸夏”、抵拒“夷狄”的斗争中作出贡献的管仲,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尊王传统一直以来是延续在儒家精神中的重要部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杜甫既是小家中的中流砥柱,又是国家中参与政治生活的一分子,以一个臣子的身份迫切期待皇帝的赏识。在这个角度上看,他既有继承了儒家传统文士直言不讳,对君主不留情面“拾遗”的决心,又有一种维护君主权威的自觉,就像亲人之间护短一样,因此时时展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例如,《北征》中的“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明确表达了其身为大唐臣子内心的忧愤不平,隐含对尚未太平的政局的担忧。同时,“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北征》引《杜诗详注》)又展现出一种希望与赞美。整个黑暗势力全部被消除,杜甫认为国家将要中兴,以历史上周王朝与汉王朝的历史经验在诉说一种期盼,一度衰落一定会再次兴起,这对于唐玄宗来说更是有一种维护。唐玄宗授意将乱臣贼子、红颜祸水一并消灭,而“马嵬事变”成了一个朝代中兴的转折点。杜甫对此予以了赞扬,又引历史上的伟人周宣王、汉光帝这些明哲之君,将唐肃宗也囊括其中,自觉地维护了统治者的正统权威地位。
其次,不仅是君父的思想使他如此,还有民族认同感的“亲亲”。亲同民族的人民百姓,排斥异族势力并将其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认为属于正统的汉民族的血脉是不同于被发左衽的蛮族的,儒家思想正统观念中对汉民族同胞的概念也含于“亲亲”之中。
然而,唐朝对民族问题始终没有作为主要问题处理。唐朝民族问题愈加凸显,使得诗人无法不正视这个问题。唐王朝的前半期,武后、韦后等女性插足政治,恰恰说明唐王朝具有异民族性质,而这一性质在唐玄宗以后消失,代之出现的是源于汉族式社会弱点的种种特征,这很容易造成其他民族的进犯。在唐安史之乱后,本是援助唐朝击败叛军的回鹘军队却留在了大唐的土地上。对此,杜甫在《北征》中便有表达对此的忧虑与不满,他对军队的描写中“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一方面有意突出了少数民族军队骁勇善战、无所畏惧的军事战斗实力,另一方面对唐肃宗“圣心”寄托于回鹘军队上的不安与担忧,即当时朝廷上的议论,借兵实际上是没有人敢提出反对意见的。更加突出其态度的是两年后唐肃宗乾元二年秋他写的《留花门》:“北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杜甫最终没能忍受君主一味依赖借兵政策,以委婉的语气表达了对皇帝无能的哀叹,仍旧希望恢复过去的羁縻政策。
再次,“亲亲”在回归于家庭时,意味着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与担当,在乱世之中顶天立地的家庭脊梁。儒家伦理精神中家庭内部关系是遵循一定顺序和规矩的,杜甫身处乱世更加凸显出这种伦理观中展现出的人文精神。《孟子·滕文公下》有言“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意味着大概可以将亲属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即父子、兄弟和夫妇。父子通过“孝”维持, 兄弟通过“悌”维持,而夫妇之间应“忍”。“忍”在家庭内部表现为彼此有一颗包容之心,而在战乱年代实际上是一种共苦的感情与相伴不弃的精神,杜甫与妻子正是如此实践的良好典范。杜甫一生只有一位妻子,在当时歌妓盛行的情况下还曾写下“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引《杜诗详注》)来讽刺这一时风。杜甫在多首诗歌里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以及对妻子在战乱中相伴的感恩,如“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述怀》引《杜诗详注》)和“何日干戈盡,飘飘愧老妻”(《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引《杜诗详注》)。在战乱年代,妻子不仅要忍受战乱的流离之苦,还要承受家庭贫苦、儿女尚幼的衣食之困。面对妻子毫无怨言的无私付出,杜甫看在眼里无限感慨,因此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北征》中,杜甫写道:“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北征》的创作时间是杜甫升官之后的第一次探亲,他内心焦急赶忙去看望妻儿,见到之后“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杜甫对亲人的爱是不容置疑的,贫寒的家境使诗人心疼自己的孩子与妻子,妻子不施胭脂,孩子衣不蔽体,又因战乱无法相见,在此之前诗人甚至不知亲人是否还健在,杜甫必然担忧亲人。又如《羌村三首》其一:“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种战乱中团圆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心酸却温暖无比,在杜甫身上“亲亲”是内在而生的感情,是患难与共的真情。
后来,杜甫在一家人入蜀后过得稍有安逸,便创作了“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诗篇纪念,这也是杜甫妻子少有的与夫君琴瑟和鸣的悠游时光。除了对爱情的真挚外,杜甫也曾多次表达他对家人真切的亲情之爱,有对他姑母的感激,“是以举兹一隅,昭彼百行,铭而不韵,盖情至无文”(《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引《杜诗详注》);有对兄弟姐妹的思念,“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月夜忆舍弟》引《杜诗详注》),分别又有“孝”与“悌”的温情。
二、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仁民”观
孟子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恻隐之心为仁的思想。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又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杜甫是实践孟子“恻隐之心为仁”的典型,在乱世之中始终秉持着一颗仁民爱民的心。
对儒家理想中的天下局面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杜甫毫不隐讳,直面现实表达自己的不满。孟子提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杜甫就有诗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引《杜诗详注》)。儒家主张让人民“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齐桓晋文之事》),杜甫则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引《杜诗详注》)。儒家反对不义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杜甫则讽刺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引《杜诗详注》)儒家谴责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杜甫则控诉那个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引《杜诗详注》)。
弱者形象在他的“三吏”“三别”中也均有生动传神的刻画。《新安吏》中的“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描写了中男中的另一类值得关注的瘦小中男,他们父母在乱世中去世,幼而无父,本该作为国家希望保留下来,却被迫逼上战场。杜甫对那些依照律令本不必服役的孩子们抱有深切的同情,他质疑了官吏的征兵政策,却最终无法改变他们悲苦的结局。除此之外,《石壕吏》中的老妪老而丧子、无依无靠,最终被强行拉去充人数。《新婚别》全诗是一个女子大声地诉说生活中无尽的苦难,丈夫在新婚之夜床还未睡暖就已经被拉上战场,战场又是九死一生,渴望白头偕老对爱情充满幻想的新婚女子被迫独守空房,君今往死地,岂不是一辈子难以再见?这不只是老而无夫,这是人祸,年纪轻轻却只能像寡居一样生活下去,更增加了新婚妇人的悲剧色彩,突出了战争的无情,引人同情。《垂老别》更是催人泪下,老而无子,“子孙阵亡尽”,老妻睡在路上声声哀啼,在腊月却只能穿薄衣裳,最终老人仍旧从军而去,又会生新寡之人无尽的苦痛。《无家别》中主人公踏上征程却无人与他送别,家园里只有蒿藜、几个寡妇、野鼠和狐狸。凋败之象尽在眼前,百姓疾苦的悲叹呼之欲出。杜甫以亲身经历的感官去展现民不聊生的苦难图景,大量弱者形象皆出于杜甫笔下,男女老少,各自不同。正是如此,这种恻隐之心不仅是杜甫自己有,他还将这样的感受传递给读者,引起情感的共鸣,表达仁和慈悲。
不仅仅如“三吏”“三别”那样描述人的苦难,杜甫还进一步将自身的安危福祉自觉地联系到普天之下的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通过一场秋风吹走三重茅草想到天下寒士,甚至愿意独受冻死也要大庇天下寒士。这场大风吹醒了杜甫,让他从以前那个在逃难途中能共情但无能的旁观者,变为了一个实实在在迫切想要奉献的人。杜甫推己及人又舍己为人,天下寒士,黎民百姓,杜甫将他们装在心中,仁民以百姓的安危福祉为要义,这便有了儒家的济世精神,恻隐之心与仁爱精神。
三、儒家伦理道德中的“爱物”观
“爱物”可以说是最高境界了,可是在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赞颂万物几乎不可能。杜甫对祖国山川被无情践踏的苦楚,对家河破碎的无奈无不流露在诗行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杜甫将这种仁爱思想融入祖国的山川之中,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杜甫终其一生无论是顺境,還是逆境,都在用他的拳拳之心体现着一种天地大爱大仁的思想。
“爱物”突出的应是万物自然,从自然审美出发却不一定是赞美的昂扬激情,以景观物、以景感物,有识万物之美的能力也有抒自我之情的感悟。在《秋兴八首》其一中有“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两句。钱谦益看到第一句里的枫树,马上联想到宋玉的《招魂》。钱谦益说:“宋玉以枫树之茂盛伤心,此以枫叶之凋丧起兴也。”又有杜诗《滕王亭子》中的“清江锦石伤心丽”,“伤心丽”,美丽得令人伤心。以情感人,以情感物,杜甫爱物重在情,又以景造情,以审美价值与审美感受推及万物。杜甫在孟子设想的人伦之序框架下展现了儒家的伦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