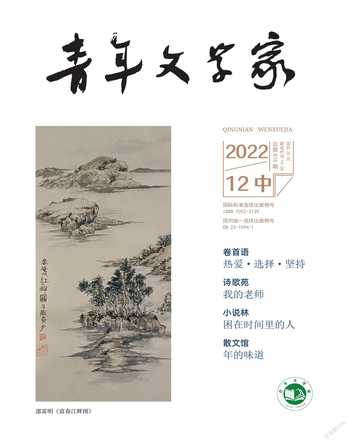小院中秋
李佳玮

记得小时候供电还很不稳定,尽管白天电视机还能打开,但是到了天黑时,“吧嗒”一下子,灯泡灭掉。灯泡灭了不要紧,蜡烛常年插在酒瓶子上,拿过来点上就是。蜡烛一点,整个屋里敞亮了许多。哪怕一点儿东西,影儿都拉得那么长,一粒瓜子仁,像头熊一样伏在墙上。蜡烛插在酒瓶子上,方便拿着到处移动,而且还不会被滴下来的蜡烫着手。每天晚上,我都举着个酒瓶子,到处闲逛。
八月十五那天,照例还是停了电,不消别人作声,我从抽屉里摸出火柴,划着白磷,点上蜡烛,像展开一场神圣的仪式。中秋的夜晚不同于平时,蜡烛也要多点几支,屋门口放一支,屋当中放一支,靠北墙根再放一支。蠟烛点得多,屋内也更加明亮,风过焰动,从屋外头看,好似屋里飘飞着几只赤色的萤火虫。
望夜气爽,屋中并不宜长待。屋里比外边要闷,待久了,只会叫人平添惆怅,于是搬小桌到天井—还是天井里叫人好受。天井不大,影壁前卧一盆荆疙瘩,我们就在荆疙瘩旁支上小桌,月饼、小食杂陈其上:月饼被均匀切成八块,那时节没有千奇百怪的馅儿,总共算来,只有五仁、枣泥、豆沙、芝麻、莲蓉、玫瑰几种而已;葡萄干、杏仁、核桃仁、圆铃枣、石榴,还有些山果木儿,一把一把的在那里。屋里坐着开水,不时要进屋冲满茶壶。顺老人的意,家中喝铁观音、碧螺春、毛峰、毛尖之类的绿茶,都要掰上一小段苦丁。我那时候怕苦,都是要敲一块老冰糖放进去。苦丁的苦和老冰糖的甜很难融合,两种味道拧在一起,有点儿奇怪,但是别有趣味。绿茶性凉,苦丁性寒,二者相合,其效倍之,故不宜多饮。秋夜团座,说讲究也讲究,说不讲究也不讲究,碗底的茶叶末子,往院子一角一泼就是。
小院的一角,有几棵桂树。桂子开时有早有晚,齐地的天气,毕竟与南方相异,因而育出来的桂树,也总是有些不同。白露时节,江宁便已是桂子满枝的盛况,而此院中的桂树,不过才是佳蕊初绽,而就是这初绽的木樨,也卓然有一番境界。淡淡的藤黄色,藏在叶子后头,欲现还休,香味并不十分冲鼻,若不是凑近附身于其上,很难真正闻到它的味道。这些桂囝,到了夜半,便一跃变成星星,望得到身影,却又寻不到踪迹。盆里的桂花,一碰枝子,便一闪一闪的,栩栩然如梦,到底是叫人迷醉了,分不清是桂花还是星星。遥知不是星,为有暗香来,若是去到天上,不知此话还能否讲得通。
十五夜最要紧的还是月亮,但此时的月亮偏偏最容易叫云彩遮住,所谓“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是也。一抬头,发现天上只有浓云千里,月影几缕,顿时没了先前的兴致,难怪司空图觉着“此夜若无月,一年虚度秋”—整个秋天都没有过头了。司空图这里有些小家子气,但没有月亮的中秋,确实叫人遗憾。我过过好几个没有月亮的中秋,坐在院子里,甚是煎熬。说一点儿没有,也不完全正确,有那么丝丝缕缕纱幔般的月影,从云层后轻散开来,柔柔弱弱,影影绰绰,淌着淌着,一阵风儿过,又变成了一团青縠,弥散在鹑尾之野。月光滴在桂花上,花瓣又增加了几分秀润,有时候也会增加几分寒意。桂与月总是密不可分,“桂子月中落”“玉颗珊珊下月轮”“不辞散落人间去”,桂花乃是自圆魄而来的仙客,“天香云外飘”“是天上、余香剩馥”则花香又悄然散到天上去了,滋润着蟾宫玉苑。
院子里也有一座小小的宫殿—山墙一角的狗窝。狗窝自破瓮改造而来,抠了个两尺见方的“小门”,倒扣在地上,里边铺上旧垫子和蒲团。这样清凉静谧的夜,小狗也感受到了,不吠,蜷卧在蒲团上,大概早已睡着。家人们还在那里坐着,而我困了,再斟一碗儿月光,便睡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