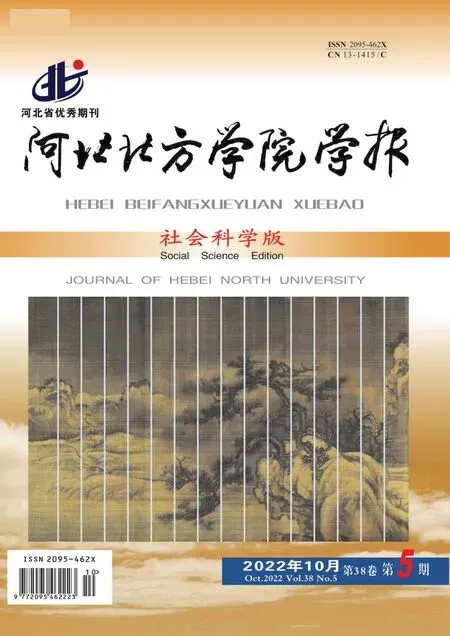论孙奇逢人格气象及其理学思想
魏 弋 贺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孙奇逢是明清时期北方理学奠基人物,也被称为清初三大儒。他常被视为明清交替时期特殊思想背景下的“侠儒”代表,其理学思想展现了这一时期理学家们的时代特色:即人格魅力与思想创造的高度统一以及学术性格影响下哲学体系得以定型。
一、仗剑天下与践履躬行
明末,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一部分平日坐而论道的理学家们放弃了道德理想,亦有部分腐儒消极面对,或归隐或自尽。刘宗周的弟子施邦曜临死之时作诗道:“惭无半策匡时艰,惟有一死报君恩”,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1]。这些人没有深刻认识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未能恪守自己的理想信念。孙奇逢遭逢乱世,但他在危机面前没有表现出颓然逃避的态度,反而积极地应对磨难。罗国杰认为:“气节是指一个人在政治上、道德上的坚定性……气节这一德目要求人们不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始终保持自己的操守。”[2]孙奇逢这种对道德追寻的坚定性也是所谓“立根之志”,是将人格价值置于生命价值之上的体现。这种豪侠气象促使他在理学实践上重视践履躬行,积极主动地寻求理想人格的实现。
孙奇逢原籍直隶容城,即今河北省容城县。燕赵之地历来多慷慨悲歌之士。他“少倜傥,好奇节……欲以功业自着”[3],少年之时便英姿飒爽,志向高远。天启之时,魏忠贤执掌大权,左光斗和杨涟等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关进大牢。孙奇逢与鹿善继因与这两人有故交,所以尽力营救。据记载:“先生及门人张果中,拮据调护,供其橐鳝……音气浩然,旁若无人,其子弟仆从,厂卫严缉,莫敢舍者。先生与鹿太公为之寄顿。”[4]457此时,魏忠贤权势熏天,朝中大臣皆惧祸引避,但孙奇逢不畏艰险,展现出了迎难而上的豪迈气魄。左光斗等人在狱中惨死,孙奇逢与其他义士又为他合力偿还所谓“赃款”,收敛尸首,此事不仅在孙奇逢传中有所提及,在左光斗传中也有记载:“容城孙奇逢者,节侠士也,与定兴鹿正以光斗有德于畿辅,倡议醵金,诸生争应之。”[5]
明代后期社会动乱,遭逢乱世的孙奇逢并不像其他腐儒那样只会临事一死报君王,而是积极地用实际行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崇祯丙子年间容城被围,当时孙奇逢“土垣将圮,穷书夜拮据修筑,先生指授方略,士民协力捍御,城赖以全。事定,巡抚都御史强其平、南刑部郎胡向化,交章闻于朝,特诏褒嘉”[4]457。孙奇逢组织民团所作规章制度至今依然保存着,据《山居约》记载,当时孙奇逢提出了“严同心”“戒胜气”“备器具”“严行止”和“储米豆”[6]1150等实用举措以保障民团的战斗力。孙奇逢少年之时,杨补庭曾问他:“设在围城中,内无粮刍,外无救援,当如之何?”他答道:“效死勿去。”[6]1379纵观孙奇逢一生,他都在践行着自己的这个志向。
女真定鼎中原,建立了少数民族王朝。此后,孙奇逢常年在夏峰山讲学,不再过多过问时政。康熙三年(1664),孙奇逢友人因私修史书被朝廷逮捕,此时已81岁的孙奇逢再次展现了他雷厉风行的个性,他在听闻此事之后随即说道:“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八十一岁老人得此已足矣”[6]1421,亲身赶往京师陈述详情。行车途中他仍就此事教导子弟们:“忧患恐惧最怕有所,一有所则我心无主,古来忠臣义士孝子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张,无事不宜生事,有事不宜避世,学者正在此着力”[6]1421,其气魄可见一斑。
考察孙奇逢经历的诸多事件,可以明显感受到他有一种执剑行天下的豪迈气象。袁贵仁提到儒家要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有复礼重行和反求诸己两种途径[7],而复礼重行的“重行”观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的工夫论中,被许多理学家所重视。不论是朱熹“知先行后”还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在对“行”的重视程度上两者可谓一致。这种践行的稳定实现既需要有对理想境界的笃信,亦需要有迎难而上的魄力与深度的体悟反思,孙奇逢的这种气魄促使他不遗余力地强调践履实践工夫。孙奇逢经历过乱世,因此他深切体会到人的修行无法完全摆脱客观环境与具体事物的羁绊。他讲道:“所谓善、不善皆吾师,只在此心有实受益处”[8]54,即人生在世总要经历顺境逆境,修行不能完全规避这些事情,所能做的就是要在不断地待人接物和处事立足中寻求体悟启发。为此,孙奇逢在阐释“道”的概念时特别强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八字要体得亲切”[8]545,即“理”不离实际事物而存在,为学修行之人倘若离了具体的事物而空求一个“理”,最终不过是一场空而已。
孙奇逢为后世学者梳理出了自身修行路径,“我辈今日谈学,不必极深研几,拔新领异,但求知过而改,便是孔、颜真血脉”[8]33。“不知顿从渐来,无渐何顿可言”[8]51,指求学路上必须要在每件事上求得体悟,积累后方能通达。孙奇逢这种观点是对朱熹修行观的继承发展,同时也是对当时只知空谈而不知实务风气的一种批判。结合这种对实际践履的强调,孙奇逢提出了他对于“心”作为本体的一种理解:“心无体,以事物为体。心无用,以好恶为用。离事物间无知可致。离好恶别无致知之功。一部大学,须于此领悟。”[9]554孙奇逢的这种心本体的认识看似与王阳明一致,但事实上他的“心”已经依托于事物而存在,变成了一种“实心”。他所谓的“行”是实实在在的躬行实践,“行”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是判断“知”是否实在的必要条件。摒弃对玄而上本体的直接体悟与架构,而沿着体用合一的路径在践履发用中慢慢领会原初的天人统一关系,孙奇逢着力于强调“知与物不离”[10]278便是一个佐证。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认识“自我”的路径,是在实际践行中克己去私以求实现个体自觉的过程。
二、乐观豁达与理在实处
通过道德主体意识的培养,达到天人合一以及理想人格的境界,以此实现对“天命”的统一,这是宋明理学心性修养的最高境界,并为理学家对“乐”的观念的架构奠定了基础。孙奇逢在现实境遇中看到理想彼岸仁善的存在,超越了儒家所谓最难破的“死生观”。
孙奇逢身处明清朝代更替的动乱时期,是这一个特殊时段的受害者。据孙奇逢记述:“甲申以后,畿南地多为从龙诸贵人采地。”[9]1308尽管表达比较含蓄,但还是可以看出祖产因圈地被占,他只得带着一家老小南迁,开始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顺治七年(1650),他才得以在辉县苏门山安定下来。但由于长期的劳顿,孙奇逢身患重病,整日忍受病痛折磨,之后他的继室杨氏又因病去世,孙奇逢连番遭受打击。但看孙奇逢个人记述,他在抒发自己悲凉心情之时从来没有放弃过鼓励自己,没有停止过自我开导。南渡的道路艰难坎坷,孙奇逢说道:“人生患不得意耳,不知得意时,却要防失意;失意时,未尝非得意也。”[9]683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孙奇逢对人生的顺逆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当下的失意未尝不是为以后的得意作了准备。经历过如此坎坷,不仅没有意志萧沉,反而还能燃起对新生活的憧憬,可见孙奇逢有着豁达的心胸。南渡的劳累使孙奇逢长期遭受病痛折磨,他多次提到了自己的病情,“平生常与病相随”[9]71,“薪绝停朝药,粮赊减夜餐”[9]75。身患疾病却因为生活贫困无钱医治,只能靠意志来克服痛苦,其艰辛可想而知。但即便在这种绝境下孙奇逢仍能苦中作乐,在黑暗中寻求一丝光明。“人知病之苦,不知乐之苦。乐者苦之困,乐极则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乐。苦者乐之困,苦极则乐生矣。”[8]34孙奇逢将病痛苦楚升华为人生在世会经历的挫折苦难,将人生得意升华为人生之乐。绝境中挣扎的他一方面没有熄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方面又能更进一步看到苦乐顺逆之中的矛盾转换关系,“盖荣辱得丧,最易挠败天真,既荣不堪辱,既得不堪丧。无荣恶乎辱,无得恶乎丧,是为达者自得之”[9]683,他认为荣辱得失是一种互为前提的存在。
基督教与佛教将“苦”视为人生存在的必然与真谛,认为“苦”是超脱的基石,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是将脱离现实存在的理想世界作为精神解脱的臆想。胡伟希认为这种思想源自于人们对宗教性形而上学的冲动[11]。与此相较,孙奇逢在对人生境遇的把握中看到了实然存在的规律。福祸相依,苦乐互因,不可执意追求,孙奇逢的这种人生辩证态度升格成了一种辩证的哲学思想,这也是孙奇逢辩证的宇宙观的重要来源。在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矛盾辩证的思想火花一直存在,在此基础上,孙奇逢结合个人的经历以及人生态度,继承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了矛盾普遍存在的宇宙观:
一不独立,二则为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阴必有阳,有动必有静,有虚必有实,有本必有末,有始必有终,有内必有外,有寒必有暑,有往必有来,有进必有退,有消必有息,有常必有变,有经必有权,有同必有异。类而推之,事事皆然[9]376。
世界处处存在着对立矛盾,它们交相运动,构成世间万事万物。孙奇逢虽然也是在现实中实现了思想的超越,但他并没有完全脱离于现实存在而悬空架构,他的这种辩证思想恰恰是在规律的把握中完成了道德人格的升华。李泽厚曾言:“中国哲学正是这样在感性世界、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去寻求道德的本体、理性的把握和精神的超越。”[12]基于这样一种全面的认识,孙奇逢的理学思想比同时代学者更加灵活和实际。
孙奇逢以“理”为其思想的最高范畴,他提到:“何谓性学?天理而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非人之所能为,欲须臾离之而不得者也。”[9]336但在这种宇宙论的基础上,孙奇逢思想中“理”的概念更加具体,而非一种玄妙的空谈与虚无。他提出:“学者要识得一定之理,又要识不定之理。一定之理易有执滞,不能免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不定之理最善解脱,所谓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而勿正。”[8]77其理学思想与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态度密不可分,因此他一方面谈到对人而言“理”不离礼义而存在,是具体的道德秩序;另一方面认为日用动静皆有“理”,既然世界是阴阳变换和矛盾交融的,那么作为本体的“理”同样也是散落于其中的,这种矛盾变化也是“理”的重要特点,“天下之道,莫善于相反而相交,以为用交则通,不交则携,天地且然”[10]32,这本身就是天理的作用使然。孙奇逢强调这种联系,一方面是要强调“理”无处不在而又主宰万物,另一方面告诫学者不要悬于自然人伦之上去空求一个“理”,要看到“理”的实际发用处。同时也要做到“见其确然不可拟议,当下承当”[8]85,就是要在认识中自觉把握这些规律,效仿天地运转打磨自己的心性。
三、务实开放与兼容并包
孙奇逢门下弟子众多,如汤斌、耿介和魏莲翁等人。作为老师,他从来不限制弟子的出路,其门人不论是入仕事清,还是归隐山林不问世事皆可。如“王余佑喜兵法,兼文武经世之才;汤斌则出仕为官,身居高位;李来章、窦克勤等人则讲学书院,开一时之风”[6]1168。学者们常评价程颢教授弟子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门下不论贤愚都可获益,这与程颢从容洒脱的外倾性格是紧密相关的[13]。孙奇逢亦是如此。在学术讨论中,孙奇逢的这种性格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面对魏裔介抑王扬朱的过激态度时,他仍能看到魏裔介学术的可取之处,并对其学术态度予以肯定,由此可见他人格气象中所具有的务实开放的突出特点。随着年龄增长,孙奇逢为人愈加谦和,“七十较六十而加毖,八十视七十而更殷。秉烛之光不熄,日月之明何分”[8]359。李留文认为,孙奇逢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清初北方思想文化的冲突调试得以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14]。
明清时期,理学已处于主宰地位。孙奇逢的任务是要理顺数百年的理学发展轨迹,同时跳脱出传统思想分化的束缚,探寻儒学哲学体系中真正的精神内核。孙奇逢面对的是各学派皆按自己所需随意定义“道统”之传,门户之争愈演愈烈的现状。因此,他当仁不让地接下了梳理学脉和承续道统的重任。而孙奇逢学术旨趣的具体体现也受到了这种包容开放的人格气象影响。
在明亡反思背景下,王学在清初成为诸人批判的对象,但孙奇逢选择做时代的逆行者,他坚持辩证看待阳明心学的合理成份,反对过度贬低阳明心学。潘志锋认为孙奇逢的这种学术判断只是为王阳明之学正名[15],事实上,孙奇逢的学术观并未止步于此,这得益于他执着的精神气象以及豁达的胸怀气象。孙奇逢并没有止步于和会朱陆的思想潮流,没有局限于在狭隘的理学发展脉络中探索,而是追溯到了整个大儒学的思想体系:“道原于天,故圣学本天。本天者愈异而愈同,不本天者愈同而愈异……汤、武自不能为尧、舜之事,孔、孟自不能为汤、武之事,而谓朱必与陆同,王必与朱同耶?”[8]137道学本出于天,正因如此,道学孜孜追求的目的应是如何认识体悟天道,而非构建固定狭隘的学说体系。孙奇逢进一步说道:
天下有治有乱,圣学有晦有明,皆天以聪明有之,人力不得而与也。我辈今日亦只定我辈今日之议论,使前人言之而后人再不敢言,则愤、典者乃伏羲、神农、黄帝、颛顼、高辛之书,孔子不敢删矣;春秋乃列国侯王之史,孔子不必修矣;传注有左丘明、郑康成、王辅嗣、孔安国诸公,程朱不可出一言矣,有是理耶[8]138?
孙奇逢将学术的发展与宇宙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相结合,指出学术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对应的话语诠释,但语言阐释只是辅助人们认识何为“理”的工具而已,局限于固有的话语表达就会陷入狭隘的学术观中。依照孙奇逢的认识,朱陆之说的出现都是儒学体系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是儒学内部的争论,而非正伪对立。这种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后世门派意气之争不过是“朱子不自讳。后人何必代为之讳”[9]1286。对佛老思想,孙奇逢也能够客观看待,认为可以吸收其精华:
问:阳明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此非兼而取之乎?曰:皆吾之用,谓吾儒之道大,其佛老庄与吾儒之不相谬者,皆吾之道,故皆吾之用。如云兼取佛老而所用者,佛老之说也则杂矣[9]559。
针对具体如何区分圣学与伪学的问题,孙奇逢在提出了自己的大儒学观之后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只要承认伦理秩序的学说皆可以括入儒学的范畴,即“儒释之辨不明,正在强不同以为同。一在人伦上做工夫,有不得则反求。一在蔑弃人伦上做工夫,有不得则勿求。分明两条路,必欲强而一之,彼此两失之矣”[9]675。
对于泯灭儒家伦理道德之说,孙奇逢的态度仍是非常强硬的,可见儒家所宣扬的人伦秩序是他的底线,同时也是儒家思想区别于其他学说最根本的标准。孙奇逢的这种吸收并不是简单的调和,而是一种更加宏大的学术观点。一定程度上来讲,圣学作为对天理的诠释,其正确性并非来自于与异学的辩驳,而是得自于将自己的话语体系更加贴近天理的本来面目,能够给人的修行带来实实在在的指引。
孙奇逢的这种学术认识将自己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应用到了儒家学术观的构建中,极大地提高了儒学本身的可塑性。甘祥满在对先秦儒家的“道统”观念进行评价时,认为先秦时期的“道统”观念与其说是对“道”的脉络梳理,不如说是“统”或者“治统”的一种实践观念的展开,因为他们并未明确“道”的确切含义[16]。孙奇逢同样如此。在他心中,儒家思想就等同于真理,而非一系列繁琐的具体的体系。李二曲曾高度评价孙奇逢的这种学术观:“卓哉!钟元可谓独具只眼,超出门户拘曲之间万万矣。”[17]桂涛在论述孙奇逢对“隐”的认识时提到,孙奇逢所要保证的是儒生能成万世之师,儒家所推崇的道能够永久运行于天地之间[18]。因此,在这样一种大气魄面前,他必然不会拘泥于所谓内部的门户之分。王坚曾认为,孙奇逢这种将儒学理想与现实、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等知行合一的取向也影响到颜元和费密等人,重构了“道统”,重视追寻周孔之道躬行实践的学术旨趣[19]。
理学家们在理学话语体系下的思想构建虽然大体不超出理学原有的范畴体系,却深刻展现出他们对万事万物运行发展的思考。理学家们各自的性格气象也是推动他们形成自己哲学体系的重要力量。孙奇逢豪放率直、乐观豁达以及包容天下的性格既是他面对所处时代的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他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动因。正如阿多诺一直呼吁的,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更要看到思想者所呈递出来的思想与现实逻辑的交织,看到思想产生的动态历史。申涵光亦评价孙奇逢道:“始以豪杰,终以圣贤。”[20]因此,剖析孙奇逢个人的气象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他的理学思想,也对理解他的思想形成历程是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