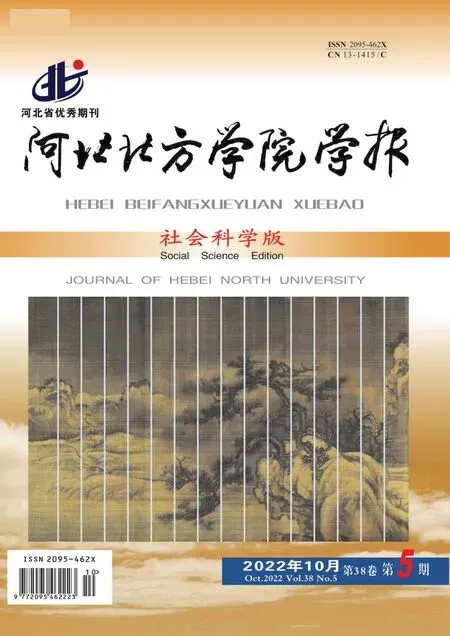论《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宋代讼师的负面作为
王 泽 青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讼师”作为正式职业最早出现于南宋,但早在北宋中叶,“健讼”现象就已蔚然成风,甚至出现了讼学经典《邓思贤》[1]。有关宋代讼师的研究成果颇丰①,然而“讼师”在宋代却是一个污名化严重的职业。刘昕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讼师来源复杂,素质低下,时常扰乱地方秩序[2];陈景良认为士大夫反感讼师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儒家义利观[3]。目前,尚缺乏探讨污名化与讼师自身行为间内在联系的研究。《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中有不少案件涉及“讼师”,他们几乎均以负面形象出现。换言之,出身士大夫的名公与“讼师”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对立的。长期掌握书写话语权的士大夫们究竟为什么厌恶“讼师”?《清明集》中的判词为人们提供了思考的新角。下文以《清明集》为中心,研究其中记载的“讼师”负面作为,以补充对讼师污名化和负面书写的原因。
一、讼师的合法性与非法性
宋代虽然出现了“讼师”一职,但这一名称的广泛流传却是在明清。部分研究认为讼师在宋代是一个非法群体②。在明确宋代“讼师”合法性之前,首先要厘清宋人在文献中用何种称谓记载讼师以及这些称谓之间的区别。
(一)对“讼师”的定义
《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讼”:“讼,争也。”[4]51“师”的含义为:“师,二千五百人为师。”[4]123故“讼师”指“好争执的一类人”。戴建国认为:“凡是收徒讲授讼学、教唆诉讼、协助诉讼以及起司法调解作用的第三方人士,都可归为讼师之列。”[5]笔者沿用此种说法。关于“讼师”的名词称谓,大致有以下3类:
1.《清明集》中有以下特指“讼师”的称谓:茶食人[6]476、讼师官鬼[6]473、把持人[6]474、安停人[6]462、哗鬼/哗魁讼师[6]481-482以及珥笔(之民)[6]280。
2.《清明集》中除了指代“讼师”还存在其他含义的称谓有假儒衣冠[6]475、哗徒[6]484以及健讼(之人)[6]123。
3.在其他宋史史料中指代“讼师”的称谓有:囚牙讼师[7]、代笔人[8]8399、佣笔之人[8]8415、写状钞书铺户[9]19、健讼之民[9]114以及代写状人[8]8398。
上述称谓中,“茶食人”与“写状钞书铺户”指在书铺里刊刻诉状并为诉讼人所述内容真实性做担保的合法性职业讼师[6]641;健讼之人、安停人、珥笔(之民)和健讼之民是来自民间非官方认可的讼师;讼师官鬼、把持人、哗鬼/哗魁讼师、假儒衣冠、哗徒和囚牙讼师是极具负面色彩的讼棍,他们既可能来自官方,也可能来自非官方。
(二)官府与非法讼师的博弈
为了防范讼师违法乱纪,官府对“讼师”行业的管控非常严格。首先,对“写状钞书铺户”出身资格要求较高:每名“写状钞书铺户”需要有“土著人三名保识……不曾犯徒刑,即不是吏人、勒停、配军、拣放、老疾不任科决及有荫赎之人,与本县典史不是亲戚”[9]19。若符合资格标准,则“置簿井保人姓名籍定,各用木牌书状式,并约束事件挂门首,仍给小木印印于所写状钞诸般文字年月前”[9]19。官府可以给“写状钞书铺户”颁发营业执照,也有撤销“写状钞书铺户”营业权的权力——“如违县司约束,指挥断讫毁劈木牌印子,更不得开张,书铺内有改业者,仰赍木牌印子赴官送纳亦行毁弃,他人不得冒名行使,身死者妻男限十日送纳”[9]19。民间讼师则相对自由,他们比普通百姓略通文法,且无需得到官府的资格认定。因此,他们既可以代写诉状,也可以协助百姓打官司。其次,官府对诉状写作亦有严格规定:“不经书铺不受,状无保识不受,状过二百字不受,一状诉两事不受,事不干己不受,告讦不受,经县未及月不受,年月姓名不的实不受,披纸枷布枷、自毁咆哮、故为张皇不受,非单独无子孙孤孀、辄以妇女出名不受。”[6]638这也正好点明业余“讼师”不被认可的原因,即他们仅以营利为目的,无法向官府承诺诉状的真实性。而许多宵小之徒的法律陈述真假参半:“奸民无知,动以撰造公事,欺骗善良为生。见人家烹犬,则曰本家失犬。见人家牵牛,则曰本家失牛。见人家女使病死,则曰原系本家转顾,恐有连累。见人家仆死,则曰系是本家亲族,不曾走报。凿空入词,文引纔出,则计会公吏、耆长之类,追扰执缚,殆同重囚。又使一等游手之人,从旁打合,需求酒食,乞取钱物,饱其所欲,而后和对。”[6]517-518普通百姓不通文法,嚣讼之徒常利用他们贪图小利的特性暗中教唆百姓争夺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官府对民众提出虚妄诉词的心理并非不理解,但官府也深知“大凡词讼之兴,固不能事事皆实,然必须依并道理,略略增加,三分之中,二分真而一分伪,则犹为近人情也”[6]497。故而官府反对的是嚣讼者在事不关己的案子里“澜翻其词,自假毁伤,撼动一时之听”[6]503的行为,毕竟乌龙案件耗费人力物力,徒增地方政务成本,良民亦深受烦扰。裴汝诚认为,在两宋之际,撰写诉状经历了允许百姓自己撰写到必须由官府认证的正规书铺撰写的变化,体现了诉讼程序的正规化过程[10]。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诉状撰写存在两宋公认的两条原则:一是必须符合实际情况,不得增加虚词,并由“当地土著”3人或者“茶食人”担保。换言之,担保人与委托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6]641;二是诉状须与己相关[9]19。
通过这些规定,民间诉讼更加规范化与合法化,官府亦可牢牢掌控民间诉讼。官府认可合乎规范的代书业务,也认可在书铺供职的代书人,反对的是非法诉讼业务以及私下非法进行诉讼业务的“代书人”和“非官方讼师”。为了攫取利润,非官方讼师所撰写的诉状虚实难辨,常常出现信口雌黄甚至颠倒黑白的讼词。同时,非法讼师中又存在不少讼棍,如“假儒衣冠”和“哗徒”。非官方讼师侵蚀了政府对民间诉讼的管辖权力,在这场争夺“代书诉状”权的竞争中,两者必然相互对立。
要之,宋代“讼师”一职既包括代书人,也包括为民间提供诉讼咨询并协助百姓诉讼的“健讼之人”。由于“代书人”中存在游走于官民之间私下提供非法咨询的不法人员,因此实际上官府反对的是讼师中扰乱法律秩序的一类人,这些人中有的是合法讼师,有的不是合法讼师。诉状中严禁虚假之辞是古今中外诉讼行业公认的准则,官府该条要求并无不妥之处。因此,不能因为官府反对不法讼师就笼统地认定讼师群体在宋代是非法群体。既然灰色业务广泛存在于讼师之中,那么即便是有合法讼师的存在,官府对“讼”的观念也始终以“负面”为主。因此官府严格约束“写状钞书铺户”,这不仅是为展现威慑力,同时也具有与民间健讼之徒相抗衡的意味。
二、《清明集》中讼师的负面作为
《清明集》中记载了不少讼师参与民间诉讼的案例,他们大多以负面形象出现,即使是茶食人也遭到批评。《清明集》中对讼师的负面记载并非恶意为之,反而正是这些记载让人们了解到讼师为何在当时遭受唾弃。
(一)教讼
“健讼”之风的兴起常给后人一种宋人懂得运用法律维权的历史错觉,其实不少发起官司的百姓只是被“嚣讼之徒”所利用。“浙右之俗,嚣讼成风,非民之果好讼也,中有一等无藉哗徒,别无艺业,以此资身,逐臭闻腥,索瘢寻垢,事一到手,倒横直竖,一惟其意,利归于此辈,祸移于齐民。”[6]484不法讼师教唆民众大兴诉讼,借机勒索百姓。韩应之和韩闳皆是许氏之子,但许氏过分偏爱幼子韩闳,导致3人闹上官府,官府将韩应之以“不孝诬告”的罪名关押起来。讼棍活动于许氏与韩闳之间,挑拨离间三者关系。最终官府传唤3人至一处,使彼此坦诚沟通,很快便化解了矛盾[6]361。在这一案件中,讼师的协调方式是通过欺骗和勒索等不正当手段为己牟利。讼师在诉讼中代表的不是当事人利益而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官府规定“如告论不干己事,写状书铺与民户一等科罪”[6]641,正是为防范讼师无中生有和颠倒是非。
教讼之人常常为了制造官司而违背官府的规定。如《惩教讼》中就有教讼之人替小孩子写状的记载,这种作法违反了年幼不当为状首的规定。不仅如此,教讼之人还替后夫陈念三写状干涉其妻前夫的财产分配,按宋律,此举违反了后夫不得干涉前夫财产分配的规定[6]479-480。
在士大夫眼中,讼师作为与案子无关之人,在背后挑拨诸多利益关系,使原本的矛盾不断被复杂化和放大化,破坏了淳朴的民风,百姓被有心人利用,无端增加了官府事务:“大凡市井小民,乡村百姓,本无好讼之心。皆是奸猾之徒教唆所至,幸而胜,则利归己,不幸而负,则害归他人。故兴讼者胜亦负,负亦负;故教唆者胜固胜,负亦胜。此愚民之所重困,官府之所以多事,而教唆公事之人,所以常得志也。”[6]476儒家文化本就对事不关己却好打抱不平的游侠文化感到厌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矣,虽闭户可也”[11]。
官府虽知晓普通百姓是因不通文法而被讼师利用,但仍拒绝将法律的知情权交予百姓,这便难以根除哗徒利用百姓的现象。鉴于此,百姓打官司的目的十分错综复杂。因此,这种兴讼和教讼之风都不能等同于近代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
(二)勾结官吏
由于非法讼师不被官方与社会所认可,因此他们的收入大多来自灰色交易,即通过教讼与贿赂获得。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讼棍与地方吏员勾结进行钱权交易的现象——“龙断小人,嚣讼成风。始则以钱借公吏,为把持公事之计”[6]473。这其中也包括被官府所认可的茶食人,“李三六系茶食人,行赇公事,受钱五十贯,欲决脊杖十三”[6]464,“成百四,特闾巷小夫耳。始充茶食人,接受词讼,乃敢兜揽教唆,出入官府,与吏为市,专一打话公事,过度赃贿”[6]476。收受贿赂养活了一群不事生产之徒,可以想象,在不少案件中金钱决定了案件审理结果,无辜之人遭受牢狱之灾的现象比比皆是。郑臻、金彬和吴恭3人是地方的配吏,他们与讼棍结党营私,把持公事。地方官蔡久轩在任时,欲替一方百姓剔除此等毒瘤,奈何此3人提前联系好讼棍,贿赂匣司胥吏,将原本批捕3人的公文搁置遗漏,以待蔡久轩期满离任。为了脱罪,他们甚至私拆文案,藏匿县丞呈报的案卷,伪造相关文书[6]421。在这起案件中,讼棍不仅行贿,还勾结胥吏,这种权钱交易严重腐蚀了基层官僚系统。赵若陋则更加过分,他“专置哗局,把持饶州一州公事,与胥吏为党伍,以恶少为爪牙,以至开柜坊,霸娼妓,骗胁欺诈,无所不有”[6]398,甚至诬陷百姓鲁海,致其死于非命。即便背负了这样的命案,赵若陋也只是被判竹篦责打30下。此后,赵若陋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殴打学子,甚至在除夕夜因赌博施暴他人,但官府却难以将其绳之以法[6]398-399。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赵若陋与地方官府中的吏员相互勾结,“若陋罪如山积,郡狱刻木,皆其党与”[6]399。最典型的讼师勾结官吏的案例莫过于郑应龙一案。郑应龙的行贿已然公开化,他常在县衙附近打听公事,一旦官府下达追捕令,他便收买承办吏人,收藏追捕公文。又或者打听案子的判决结果,然后向被追捕人提前通风报信,借此牟利。一次,县衙追传缪元七等人,以对证其与陈元亨之间的产业纠纷案,郑应龙竟公然收留陈元亨,允许他在自家饮食,同时将缪元七藏匿起来,不准他前往官府对峙。等到承办吏人上门逮捕,郑应龙又将人犯偷偷放走并殴打了承办吏员[6]474。长此以往,官府不仅难以有效行使自身职权,就连处理公务也需要仰讼棍鼻息。多数地方官只能对此熟视无睹,以求平稳度过任期。
讼师不仅勾结吏员,甚至与一些官员狼狈为奸。陈瑛在赵知县接任时成为讼师,却与赵知县共同欺压百姓。赵知县无端科罚百姓钱财1 000贯,却美其名曰为“暂借”,陈瑛则趁机骗取他人产业,金额高达7 000缗[6]462。宋自牧决心要铲除此等毒瘤,随着案件的进一步调查,陈瑛放债追息和谋夺他人产业的犯罪真相也浮出水面。其中所涉及的受害人众多,如罗喆曾借陈瑛现钱600贯,却被借款产生的高利息逼得变卖田产。陈瑛甚至教唆张云龙发起诉讼,诬告罗喆拖欠欠款不还,等此事闹到官府后,陈瑛又去收买官吏,让罗喆向县衙缴纳千缗寄库钱作为和解条件,就这样陈瑛白白夺取罗喆4 400贯家产[6]463。
讼棍与吏勾结,层层贿赂官与吏,导致案件审理工作被反复拖延,甚至常常不了了之。朝廷命官在地方势单力薄,同流合污、姑息养奸或对抗到底成为官员与这些讼棍相处的常见模式,但对抗到底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当讼棍与官吏勾结时,原本为民伸冤的地方官沦落为压迫一方百姓的帮凶。法理被讼棍和贪官污吏所把持,百姓通过诉讼渠道成功伸冤且能全身而退的几率不高。
(三)抗衡官府
由于讼师总能找到“商机”攫取财富,并且四处贿赂打点人事,因此易凭借雄厚的财力和人脉扩大自己的势力网,成为威胁地方政府和社会治安的毒瘤。
《先治依凭声势人以为把持县道者之警》一文中就记载了普通人在惹上官司后,不是将希望和信任寄托于地方府衙,而是仰仗讼师庇佑的现象——“今三僧监系于县,不求于他人,而皆指添监(讼师)以为归,则其平时城狐社鼠,已可想见”[6]475。这不仅使官府在百姓中的威信降低,也使财力雄厚却犯法的权势之人可以逃脱官府的制裁,甚至存在地方官吏不敢不从讼师意愿的现象。如讼师刘涛便将府衙风气变成“涛之所右,官吏右之,所左,官吏左之。少咈其意,则浮言胥动,谤语沸腾,嚣嚣嗷嗷,不中伤其人不已”[6]478。他时常将自己替人打官司的行为解读为行侠仗义,但百姓却无人认可他的自夸之词。
婺州的金千二和钟炎出身显贵,金千二是势家干仆之子,钟炎是州吏钟晔之子。这两人“敢于出入州县,敢于欺压善良,敢于干预刑名,敢于教唆胁取,敢于行赇计嘱”[6]481。受贿所得不义之财装满了两人荷包,金千二甚至逾制营建楼宇,奢华程度甚于官府。更过分的是,这两人逐渐在地方经营出了自己的势力网:“金千二或姓金,或姓刘,或名培,或名埴之,变诈反复,无非预为奸狼败获之地。是二人者,同恶相济,互为羽翼,一郡哗徒之师……其威力过于官府。”[6]481地方顽固势力一旦姑息养成,就难以铲除,人际利益的盘根错节更加剧了吏治的恶化。《撰造公事》一案生动地记录了官府难以裁制“哗徒”的现象。“哗徒张梦高,乃吏人金眉之子,冒姓张氏,承吏奸之故习,专以哗讦欺诈为生。始则招诱诸县投词人户,停泊在家,撰造公事。中则行赇公吏,请嘱官员,或打话倡楼,或过度茶肆,一鏬可入,百计经营,白昼攫金,略无忌惮。”[6]482张梦高在积累了一定财富后,“出入州郡,颐指胥徒,少不如意,即唆使无赖,上经台部,威成势立,莫敢谁何。乘时邀求,吞并产业,无辜破家,不可胜数”[6]482。甚至地方政府传召赵时消的通牒都被张梦高和赵时消暗自私藏,以至通牒逾期[6]483。
处在“官”这一位置的士大夫常常被困在地痞流氓构建的利益网中,纵有为民除害之心,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地方吏员或出于平息事端之考量,或出于贪财之心,常默许讼师的不法行径。可以看到,多数讼师并不是通过法律条文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人情关系、利益往来甚至是威逼利诱等不正当手段来解决矛盾。
三、再谈讼师负面书写之原因
梳理宋代“讼师”相关记载,很难不被史料中贬低讼师的主流意识所震惊。有学者认为“讼师乃古代律师”[12]。细细分析,“律师”与“讼师”其实存在根本性差异,不能因为替人打官司这一共性而将两者混同。首先,在法律观念还未普及时,许多百姓并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中国古代的基层社会习惯用人情伦理去协调诸方矛盾,因而由百姓发起的诉讼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其次,除了官方认可的写状钞书铺户外,大部分讼师的收入来源都是非法的。他们耳听八方主动出击找寻发起诉讼的契机,刻意挑拨矛盾,根据当事人富裕程度进行勒索。这与近代律师收取雇佣金有天壤之别。最后,讼棍平息法律案件的方式并非依靠法条和自己的专业水平,而是“未得钱,则嗾之使论,既得,则尼之使止”[6]483。因此,他们与近代律师是两个看似相近实则相去甚远的职业。不能因为士大夫和官府针对其负面作为进行合理打压便断言“严重阻滞了宋代民间法律服务行业的正常发展,法官与讼师难以走向现代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道路”[2]。《清明集》中的断案人主要是士大夫,从以上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士大夫厌恶讼师的原因:
第一,讼师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存在为普通百姓的私欲打开了一扇窗。在嚣讼之徒的教唆下,原本安分守己之人选择借助官府公权力去诬陷良善——“讼乃破家灭身之本,骨肉变为冤仇,邻里化为仇敌,贻祸无穷,虽胜亦负,不祥莫大焉”[6]637。
第二,许多原本安分守己之民被“讼师”宣传的蝇头小利所误导,将精力放在打官司上,严重占用务农时间,财产也在讼师的操控下散去,以至于普通自耕农不得不变卖田产,沦为佃农,许多人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长此以往,国家的税收便会受到影响。
第三,讼师的负面作为严重损害了地方政治生态,官吏与讼棍沆瀣一气,形成利益共同体,他们共同从案件中获利。受牵连的百姓犹如跌进苦海,难以自拔。普通百姓如不幸得罪讼师,那么即便是清白之躯也难以伸冤。纵使幸运地遇上开明官员,也很难等到公正的审判结果。在实际运作中,官员为求仕途平坦也不得不姑息养奸或与讼师合作共谋,偶有清廉官员欲剔除讼师中的毒瘤,但很难将其连根拔起。
第四,非法讼师来源复杂,他们凭借金钱、人脉和家世背景建立起影响地方社会治安的势力。他们轻视官府,严重侵蚀了政府权力的施展空间。百姓在遇到官司时,不会将希望寄托于原本应当保护他们的父母官,而是选择依赖讼师。这为官府带来了许多困扰,尤其当吏欺瞒县官勾结讼棍,或者讼棍与吏本就是血亲关系时,地方官就不得不仰其鼻息才能继续生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吏治的腐败。
由上可见,士大夫对讼师的负面书写并不单纯是由于彼此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对讼师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其作恶的现实为依据的,这一系列行为反过来强化了士大夫对“讼”和“讼师”的偏见。因此,宋代史料中鲜有讼师的正面事迹。许多讼棍通过教讼、勾结官吏和抗衡官府等行为徒增府衙政务,侵蚀公权力,严重破坏了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态。士大夫对讼师的书写偏见正是基于这些负面现象而生的。虽然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责任不应由所有讼师承担,但讼师一职的污名化必与这些负面行为息息相关。
注 释:
① 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郭东旭《宋代的诉讼之学》(《河北学刊》1988年第二期);裴汝诚《宋代“代写状人”和“写状钞书铺”——读〈名公书判清明集〉劄记》,(《半粟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6-315页);陈智超《宋代的书铺与讼师》(《陈智超自选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5-357页);朴永哲《从讼师的出现看宋代中国的法与社会》(《宋史研究论丛》2008年第一期);刘馨珺《南宋狱讼判决文书中的“健讼之徒”》(《中西法律传统》2008年第六期);戴建国《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人——以私名贴书、讼师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4年第二期)等。
② 在王浩然《中国古代讼师的社会功能——以宋代讼师为基础兼与英国中世纪律师比较》和刘昕《宋代讼师对宋代州县审判的冲击探析》中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