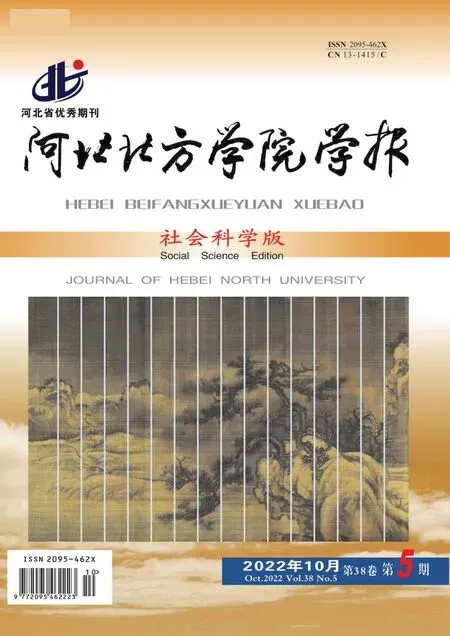辽太宗“造神”与辽初宗教政策的转变
燕 志 磊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造神”指为达成某些目的人为地将自己或其它偶像塑造为最高精神信仰的神化活动,以实现对一定时期或具体范围内政治经济局面及人类群体精神的全面控制[1]。关于辽初耶律阿保机与其皇后述律平所进行的神化活动已有学者进行研究。任爱君在《神速姑暨原始宗教对契丹建国的影响》中探讨了太祖和太宗时期如何利用原始宗教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问题。孟凡云《耶律阿保机的神化活动及特点》和《辽述律后“人神合一”活动及其采取的宗教形式》分别对辽太祖和述律后所进行的宗教实践进行分析。辽太宗即位后因循太祖既定轨辙,在多重压力下对神祇进行构造与改造,从宗教出发推进非汉族政权汉化。
一、辽太宗“造神”原因发覆
宗教自古以来便反映着人类的哲学思维能力,古代人类的社会行为和思维规范被束缚在宗教的枷锁中,宗教甚至可能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2]。阿保机深知此道理,为了巩固皇权,他首选宗教作为思想控制工具。宗教领袖神速姑导演了“龙锡金佩”事件,帮助耶律阿保机顺利夺取可汗之位。即位后,阿保机为平息诸弟叛乱,处置了神速姑,更在916年举行柴册礼,“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3]10。辽初政权的“君权神授”色彩浓重,政权与神权的合一发展成为阿保机执政时期的特色。宗教神权贯穿于太祖整个统治生涯,甚至其去世也被演绎成神话传说,大星陨落、黄龙缭绕和黑气蔽天皆成为太祖去世之兆[3]23。辽太祖的突然去世至少为耶律德光留下3个未解之题,使他不得不开始思考神化活动的重要性。
(一)辽太宗即位的非合理性
耶律德光并非以太子身份即皇帝位,其继位一事与辽俗不和。天显二年冬十一月,太子耶律倍率群臣向当时统摄军国大事的述律后求立天下兵马大元帅德光为帝,赞扬其“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3]28。此是以《辽史》为代表的辽朝文献中关于耶律倍“让国”于耶律德光的记载,而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中土文献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其记载太宗即位得益于述律后“推举”,继位失败的耶律倍更是作出“出逃后唐”的过激举动[4]。虽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帝位,但德光一直对自己嗣立的非正统性心有芥蒂。为此,他赋予天下兵马大元帅“储君”的意义,先以契丹旧制柴册礼即位,上尊号曰“天皇王”,后又以汉制即皇帝位,自称为“嗣圣皇帝”[5]。为了巩固政权,德光采取了诸多措施,却依旧未能在政权之外获得神权的加持。神权的重要性正是在于其能对普罗大众施加思想约束,助力政权巩固[6]283。鉴于此,太宗急于寻求宗教神化活动的帮助。
(二)定州之战失败带来的教训
太宗继位之后,不仅面临与述律后争权的内部问题,而且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从一定程度上讲,辽太祖阿保机在建国初期所设定的政治蓝图便是建立一个汉式王朝,因此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南方[7]。阿保机突然去世,次子德光即皇帝位。此时,中原王朝藩镇割据,战乱频仍,这种局面不免波及刚经历政权更迭且统治并不稳定的契丹。唐义军节度使王都以定州归降为报酬,遣使向契丹求助,即位不久的德光“命奚秃里铁剌往救之”[3]28,但结果是铁剌战败,士气大伤。后“唐将王宴球于定州,唐兵大集,铁剌请益师。辛丑,命惕隐涅里哀都统查剌赴之……壬子,王都奏唐兵破定州,铁剌死之,涅里哀查剌等数十人被执。上以出师非时,甚悔之”[3]29。这两次出兵的失败给辽太宗带来沉重打击,以至“数年不敢窥边”[8]4286。太宗贸然出兵不仅造成了军事上的失败,更削弱了其在政治上的公信力。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此次出兵失败后,“述律尤思念突欲”[9]892。即使暂不论中原文献记载真实性问题,也足可见辽朝内部对德光几次军事行动的不满。军事与政治上的双重教训使得德光不敢再鲁莽行事,因此他需要“上天的旨意”为自己正名,更甚之,为自己承担失败的后果。
(三)辽太祖去世后契丹精神信仰的缺失
被视为契丹之神的辽太祖去世之后,辽朝军政大权由述律后掌控。这个突变使得契丹社会的神权色彩被打破,偶像的逝去导致民众信仰缺失,急需新的精神寄托。在这一精神信仰的空白期,述律后也在积极进行神化活动,这一举动给辽太宗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倘若述律后的“造神”活动成功,则意味着其将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自神册元年阿保机以中原之礼登上帝位起,辽朝便确定了以皇权为核心的单核心权力结构模式。在皇权这一内核之外,是紧密围绕的帝族与后族共同组成的权力外壳。在血缘伪饰下,帝族和后族为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必然会产生激烈的权力斗争,威胁皇权统治。本就处于述律后联合执政阴影之下的太宗自然不希望自己前期的政治谋划付诸东流。因此,太宗迫切需要争夺神权,将自己与神灵比肩,借此与以述律后为首的后族势力相抗衡。从契丹建国伊始,统治者便一直利用宗教神化政权,以达到巩固皇权核心的政治目的。太宗亦深谙此理,因而积极准备并进行“造神”活动成为其为政时期的重要实践活动。
二、辽太宗“造神”步骤索隐
辽太宗的“造神”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其神化的对象并不统一。前期,辽太宗将太祖阿保机作为最高精神信仰偶像,试图赋予其至高无上的神权;后期,辽太宗开始借力佛教努力将以白衣观音为代表的佛教塑造为普遍信仰。
(一)神化活动的尝试期——辽太祖地位的再抬升
耶律德光神化活动的第一阶段,从天显元年(926)即位开始,至天显十一年(936)出兵援立石敬瑭成功结束。在这10年间,太宗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自己的宗教实践活动,一是表明自己“受权于天”,二是证明自己“受权于君”。在通过两次柴册礼完成“君权神授”仪式的同时,太宗努力抬高辽太祖的地位。他继承了太祖时期的“天显”年号,“有司请改元,不许”[3]28,且沿用13年之久。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己是承太祖之位,继太祖之志。为实现对最高权力的继承以及维护现实统治,辽太宗将太祖庙塑造为具有契丹传统信仰和中原礼制精神双重属性的祭祀场所。宗庙是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中原贵族认为宗庙与国家社稷同等重要[10],辽太宗在阿保机引入的中原王朝宗庙观念基础上逐步完善辽朝国家宗庙制度,并将拜谒太祖庙视为头等重要之事。仅据《辽史》记载,在太宗尝试“造神”活动的第一阶段,“谒太祖庙”便进行了12次,还不包括“告太祖庙”与“祭太祖庙”。为宣扬太祖功德,太宗还“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3]32,并“御制太祖建国碑”[3]34。至此,太宗达到了其“造神”的第一个目的——太祖成为契丹公认的神主,成为契丹社会的精神信仰。接下来,太宗试图赋予太祖这一新晋契丹之神和自然之神同等的地位。从原始社会开始,契丹人便将太阳和月亮等自然神灵作为祭祀对象,对太阳的崇拜尤甚,《辽史》载:“皇帝升露台,设褥,向日再拜,上香”[3]836,“八月丁酉,以大圣皇帝、皇后宴寝之所号日月宫,因建日月碑”[3]32。太宗的这一举措有意使太阳成为辽太祖的象征,使阿保机的地位无人可及。但此举也留下一个隐患,那便是无形中抬高了阿保机皇后述律后的地位。
辽太宗“造神”的第一个10年,其母述律后并未阻拦其“造神”举措,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其作法的。究其原因在于述律后也想利用太祖提高自己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契丹国志》曾记载太宗白日梦境一则:“契丹主德光尝昼寝,梦一神人……神人语德光曰:‘石郎使人唤汝,汝须去。’觉,告其母,忽之不以为异。后复梦,即前神人也,衣冠仪貌,宛然如故……乃诏胡巫筮,言:‘太祖从西楼来,言中国将立天王,要你为助,你须去。’”[11]18此事件真伪性有待考查,但太宗及其母的确都不约而同地将神化太祖作为自己争夺权力的筹码,借太祖之名,行政治斗争之实。从中渔利的述律后支持这一阶段德光“造神”的相关政治举措,并非“母子情深”所致,而是个人利益作祟。
(二)神化活动的关键期——白衣观音入主木叶山
太宗“造神”计划的第二阶段,也是整个神化活动中最关键的时期,从天显十一年(936)援立石敬瑭成功开始,至会同元年(938)幽云十六州划归辽境结束。幽云十六州地处华北平原,自古以来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农业耕作区,与契丹腹地的经济模式完全不同。若其归入辽朝统治区域,不仅使辽朝疆域版图扩大,还使得辽统治者面临如何管辖境内的契丹、奚人与汉人的问题。从南北朝以来,“河北及其附近的山西、河南与山东是法华经信仰及观音信仰的中心”[12]。面对此局面,若仍旧将太祖作为最高偶像信仰并不现实,故太宗将视线转向了幽云地区最为兴盛的佛教。前有假借托梦一事为铺垫,太宗索性继续利用梦中“神人”,指幽州大悲阁兴王寺之白衣观音像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于诸部。”[3]446清人段玉裁曾为《说文解字》“庙”字作注:“古者庙以祀先祖,凡神不为庙也。为神立庙者,始三代以后。”[13]779太宗不仅为白衣观音神像立庙,更将其供奉在辽朝的神山——木叶山。木叶山在契丹人心中拥有无法超越的精神地位,是契丹人心中的“神山”。辽之祖神与始祖可汗之魂灵栖息在此,阿保机时期将其视为国家大宗之所在[14]。从此,白衣观音获得了与祖神同等的地位,菩萨信仰也迅速流传开来。为进一步提升白衣观音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太宗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3]835。菩萨堂仪非胡剌可汗时期旧俗,却一跃跻身为与柴册仪和再生仪等辽朝重大礼仪制度平级的仪式,这足以体现太宗对其的重视程度,他也成为此仪式的首位践行者:会同五年六月,述律后身体不适,太宗“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七月乃愈”[3]52。
太宗在这一阶段的“造神”活动是准确且迅速的。他放弃了原始宗教转而向发展中的佛教求援,选定白衣观音作为自己神化的偶像符号,赋予其本土宗教的含义。太宗的政治目的与佛教的发展相辅相成,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佛教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迅速传播的佛教又成为太宗约束人民思想的新工具。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辽太宗的专制皇权发展到顶峰,白衣观音的传入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述律后妄图借萨满教抬高自身政治地位的活动失败,后权发展的势头得到抑制。自此之后,辽朝佛教发展愈加兴盛,世家大族以一己之力修建佛教寺院的风气十分盛行,他们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积极进行寺院和佛塔等的修建,成为辽代佛教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的参与群体。
三、太宗“造神”的特点及辽初宗教政策的转变
在政治与军事的双重压力之下,辽太宗选择借助神灵“旨意”冲淡自己承受的非议,以神权作为皇权的“辅助工具”,加强皇权核心统治力。由于处于契丹社会转型期,为适应统治需要“因俗而治”,因此其神化活动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并影响了辽初及后来契丹宗教政策的制定。
(一)辽太宗神化活动的特点
辽太宗神化活动的特点包括:借助其他偶像符号进行神化活动、尝试走出原始宗教的桎梏以及对“女神”形象的有意塑造。
1.借助其他偶像符号进行神化活动
与辽太祖和述律后将自己作为神化的对象不同,辽太宗在“造神”过程中从未打算将自己塑造为神灵,而都是借助其他偶像符号,这主要是政治背景使然。在太宗神化活动的第一阶段,他选择继续神化太祖。这一决定有两个好处:首先,缓解了来自述律后的压力,也更容易为民众信服,在太宗政权并不稳定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其次,太宗执政时期正处于辽朝历史叙述的生成阶段,这一时期德光承太祖之志有意将家族始祖塑造为契丹共祖,以家族统治史作为整个契丹统治集团的历史[15]。因此,对太祖与奇首可汗的神化很有必要,这抬升了阿保机家族在契丹发展史上的地位。在神化活动的第二阶段,辽太宗选择白衣观音作为神祇,这不仅有利于对不同地区民众的统治,更成为其摆脱原始宗教束缚进而构建封建皇权统治的关键一步。
2.尝试走出原始宗教的桎梏
辽太宗放弃原始宗教,以佛教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新工具。原始宗教产生于人类最初认识自然界的有限能力基础上[16],在契丹建国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却导致巫的权力膨胀,严重破坏了辽朝统治者在军国大事方面的绝对决定权。太宗另辟蹊径,树立起白衣观音的“家神”地位。另外,有必要对“家神”一词进行检视。“家神”,顾名思义指一个家族的保护神。众所周知,皇族和后族是辽朝地位最为崇高的两大权力集团,对“家神”中的“家”是否特指皇族耶律氏的探索很有必要。若是特指,则表明太宗已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以述律后为代表的后族势力的掣肘。
3.对“女神”形象的有意塑造
太宗在“造神”过程中有意树立“女神”形象,这一点明显体现在第二阶段。辽人历来对女性始祖十分重视并形成了契丹特有的女神信仰体系,这主要根植于契丹“白马青牛”族源说。据《辽史·地理志》所载,乘白马的神人与驾青牛的天女相遇于木叶山,二人结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3]445-446。《契丹国志·初兴始末》认为“始祖诞生”的契机是“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11]1。相比《辽史》传说中强调天女与神人两个人物形象,《契丹国志》则更为注重塑造“妇人”的角色,且在描述中少了些许神化传说色彩,更为平易近人。由“神”到“人”的转变更加说明了此传说流传的广泛性,这一族源说深刻烙印在契丹普罗大众心中。可见,从契丹原始社会末期始,女性始祖的形象便深入人心。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原以来,观音普遍被认为是女性形象,从太宗对这一神人梦中之姿的描述来看,其也偏向于女性形象。《契丹国志·太宗嗣圣皇帝》载:“梦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辎軿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带,执骨朵,有异兽十二随其后。”[11]18文中神人乘的“辎軿”,一般被认为是贵族妇女的出行工具[17]。还有一点可以佐证,王鼎《焚椒录》记载宣懿皇后容貌秀丽,堪称萧氏之首,“皆以观音目之”,因以观音为小字。可见,在契丹人心目中,观音是“美”的象征[18],并常将女子比拟为观音。为何太宗在此阶段有意巩固女性神灵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述律后此时也在积极促成“人神合一”活动,欲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将自己塑造为新的女神,因而有意贬低“天女”。太宗此举或在无形中压制述律后的僭越行为。
(二)辽初宗教政策的倾斜与变化
在契丹的发展进程中,宗教始终贯穿于契丹人的精神世界乃至日常生活,并深刻影响了契丹历史的运行轨迹。辽朝文化发展有其特殊性,多元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不断融合,也造就了多元化的宗教信仰。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为适应统治阶级需要,宗教信仰开始发生变化。契丹社会早期至辽朝建国初,巫教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原始宗教制约了统治者最高权力的行使,阿保机为巩固政权开始有意发展其他宗教,其中以儒教为盛。太祖时期以儒学为尊,孔子更是被神化为宗教偶像。据《辽史》载:“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3]1209由上可见,儒教不仅是阿保机用来对抗原始宗教的有力工具,更是保障皇权核心统治力的思想武器。而巫则从契丹社会早期的统治者转变为契丹皇族的服务者,原始宗教活动逐渐成为一种纯粹的仪式[19]。与其父不同,德光即位的非正统性使他对主张长幼有序的儒学讳莫如深。为强调自己嗣立的合法性,缓解民众心理落差,辽太宗另辟蹊径,改变“祖宗之法”,树立起“白衣观音”的家神地位。天显十二年,太宗将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迁往契丹族的神圣之山——木叶山建庙供奉,“尊为家神”,即所谓的“菩萨堂”,并于拜山仪后制定“菩萨堂仪”。自此,佛教在契丹更为广泛地流行,契丹上层宗教政策也开始大幅向佛教倾斜,一时间崇尚佛法和营建佛寺成为主流。据《辽史》载,太宗会同五年拜谒太祖庙后“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3]52。燕京地区更是“僧居佛寺,冠于北方”[11]217。由此足可见统治者对佛教的提倡使佛教得以迅速传播。
辽太宗时期的“造神”活动是太宗从宗教出发对非汉族政权汉化命题的有益探索。辽太宗在“造神”活动前期极力提高辽太祖的地位,这一决策的制定是出于与述律后政治博弈及巩固皇权的需要。而太宗在“造神”活动后期选择白衣观音这一佛教成员也并非偶然。辽太祖时期对三教并蓄发展的包容为太宗提供了有利条件。辽朝建国后,虽原始宗教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但诸如佛教、儒教和道教等并没有被勒令禁止,这使得太宗后期利用佛教获得神权辅助成为可能。出于治理幽云地区与巩固皇权统治的需要,太宗选择白衣观音这一形象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另外,林鹄曾分析,至少在太宗和世宗朝,辽曾有过短暂的入主中原计划,其统治者恐怕并非没有考虑过将辽朝转变为汉式王朝的问题[7],只是后来各种原因导致这一计划只能以空想告终。因此,树立起中原王朝普遍存在的佛教信仰,也许是太宗的另一重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