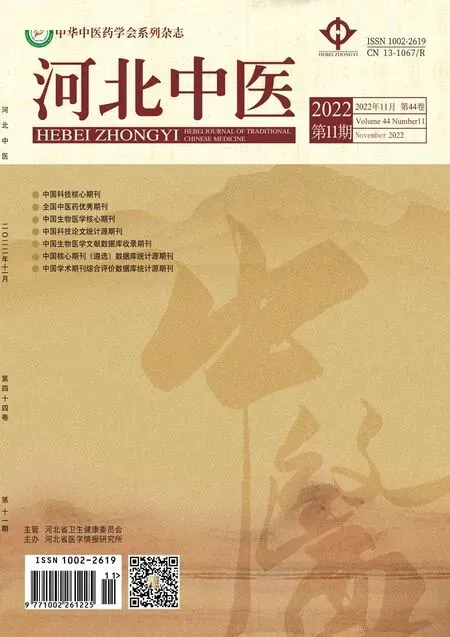王沛教授平衡阴阳、化浊解毒法治疗膀胱癌经验探析※
李佳萌 商建伟 宋连英 司红梅 张耀圣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 100700)
膀胱癌是指起源于膀胱的恶性肿瘤,一般特指膀胱尿路上皮癌,是泌尿系统常见肿瘤,典型表现为无痛性全程肉眼血尿。目前在世界上最常见肿瘤中排名第10位[1],按照模型统计推算,膀胱癌在我国全部恶性肿瘤发病谱排第13位,居男性恶性肿瘤发病谱第8位,45岁以后,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出现快速上升趋势[2]。受制于诊察工具的缺乏,古医籍中对膀胱癌并无对应病名。但依其症状,概括纳入“癃闭”“尿血”“淋证”等范畴。目前,各家学者对膀胱癌的病因病机认识意见不一。
王沛教授为著名中医外科学家、肿瘤学家,我国培养的第一批中医高等人才,为北京市第二届“首都国医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膀胱癌治疗中善用中医外科思维。王教授认为,在膀胱癌的治疗中,应突破邪在膀胱,攻邪为主的局限,回归到治本之上,辨局部症状推求整体,力在平衡阴阳,治疗确有特色。现将王教授治疗膀胱癌经验总结如下。
1 辨治特色
1.1 阴阳失衡为本,毒浊内结为标 《内经》将阴阳平衡作为生命活动之基,《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曰:“生之本,本于阴阳……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解散。”阴阳平衡指阴阳消长转化保持协调,无偏盛与偏衰的状态。生理活动的基础在于阴精与阳气的运动,气化运动亦依赖阴阳的升降出入。脏腑、气血为维持正常的功能同样需要平衡。阴阳协调,则正气足,邪不可干。阴阳一旦失衡,则正常生理活动被破坏,成为疾病发生的基础,是导致癌病发生的根本原因。《素问·评热病论》有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外证医案》概括为:“正气虚则成岩。”《医宗必读·积聚》云:“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均概括了癌病的发生基础在于正气的亏虚。中医学认为,局部的表现必有内在机体的失衡,疾病必先有虚,阴阳失衡是其总的概括。王教授认为,肿瘤的发生首先是人的整体阴阳失衡,治疗时虽要对局部症状进行治疗,但其本应从全身状态入手,扶正补虚,平衡阴阳。发病既然首推阴阳失衡,凡有肿瘤,必先探明患者的阴阳盛衰、失衡状态。其次是毒浊的发生。中医外科学认为,人体发病是由于各种邪气停滞,导致局部经络阻塞、气血凝滞等,故于体表、窍道产生局部症状、体征,从而形成外科疾病。肿瘤即是邪气停滞产生的毒浊产物。浊者,不清也,为害清之邪气。《丹溪心法》认为“浊主湿热,有痰,有虚”。《金匮要略心典》认为毒是邪气蕴结不解所致。邪盛亦谓毒。膀胱癌预后不同于普通六淫所致疾病,故谓之毒。中医病因学认为,致病邪气,或来于外感浊毒,或源于气血紊乱、脏腑失调产生的内生浊毒。浊质重黏着,易胶于阴血,可化热酿毒;毒性烈峻猛,大伤正气,则浊邪易滞。两者性近且可相互导致,故并称。毒浊既可因阴阳失衡,外邪趁虚而入所致,又可因脏腑功能紊乱,运行失常,代谢不得排出,积久蕴成。毒浊的产生不离阴阳的失衡紊乱。且毒浊猛烈胶着,深伏于内,病情进展迅速且缠绵难愈,耗伤脏腑经络气血。再加重阴阳的紊乱,正气愈损,由此循环,病患日渐虚弱,难敌毒浊,正邪相对难抵颓势。
阴阳平衡,正气充足,机体平和时,人体可自行抵抗、消除邪气,清理代谢浊物,使邪气难以留滞。当阴阳失衡,机体紊乱时,邪气易于侵入停留,代谢排毒不畅,毒浊积蕴成瘤筑癌。若人体正气约束不及时,肿瘤势必增长迅速,甚至输布为害,导致肿瘤发生转移。膀胱癌发病本基于此,且膀胱居下焦,湿浊趋下,尤以毒浊为害。无痛性全程肉眼尿血是膀胱癌的主症,尿血或因热或因虚,均归于阴络损伤。阳络居上,阴络在下。阴络损伤,为“清邪在上,浊邪在下”之浊邪所伤。《景岳全书》谈及:“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此处外溢为从上而出,吐血衄血;内溢为从下而出,溺血便血等。故尿血为阴络损伤所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云:“形伤则肿,气伤则痛。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因此,膀胱癌的特点是浊毒损伤膀胱阴络之形,产生无痛性血尿。浊毒阴邪损伤阴分血络,是膀胱癌的主要病理机制。膀胱癌患者出现排尿异常的症状,首推气化失常。尿液正常排泄与脏腑功能正常、阴阳平衡密切相关,尤以阳气为要,阳旺则气化。排尿异常多责之阳气虚,多为湿邪所致。毒浊壅滞下焦,阻碍气机,通调紊乱。或见尿频、尿急,或见尿少、尿闭。从阴阳角度看,排尿异常多责之阳气虚,病在气分。张景岳云:“凡下焦阳虚则阳气不行,阳气不行则不能传送而阴凝于下,此阳虚而阴结也。”故阳虚使患者排尿异常的同时,加重毒浊的积聚。
故王教授认为,膀胱癌为整体阴阳失衡,感受邪气,瘀血痰浊湿毒等产物搏结于虚弱脏腑膀胱而成。病性以阴阳失衡为本,毒浊内结为标。提出“平衡阴阳,化浊解毒”的治疗原则,治疗时必须以恢复正常阴阳平衡状态为宜。
1.2 重在调补脾肾,依症辨证论治 《素问·评热病论》曰:“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地。”病发于膀胱,必因膀胱虚弱,病位在膀胱。目前各家对于膀胱癌的病因病机认识不一。花宝金教授认为膀胱癌因肾精亏虚、肝气郁结所致[3]。孙桂芝教授认为脾胃积湿生热,蕴积膀胱,加之肾气亏虚,积毒成瘀致膀胱癌[4]。蒋士卿教授则认为肾气亏虚、膀胱湿热为膀胱癌发病关键[5]。王晞星教授认为膀胱癌主要病机为湿热[6]。然膀胱属六腑,为空囊器官,与肾相表里,虽主司开阖,实则赖于肾气,膀胱失司,责之在肾。肾为先天之本,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肾虚则五脏六腑之精不足,阴阳失衡。肾主津液,津液在肾的气化作用下输布,浊者化为尿液归于膀胱,肾阳虚,肾气不固,则膀胱失约。“浊阴归六腑”,邪浊及病理产物遂流入膀胱,酿成癌毒。因此,王教授认为膀胱癌病症与肾密切相关,病位当在肾与膀胱。脾胃作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承担着补充正气的职责。李东垣曰“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水液的代谢亦依靠脾之转输,方能排泄。脾胃所生正气不足,可使疾病产生。脾胃代谢水液失常,又会加重膀胱癌的血尿与排尿异常。脾与肾关系上讲,脾肾在先后天互相资生滋养和水液代谢方面联系紧密,《辨证录》谓“胃为肾之关,胃土能消,而肾水始足”,可见肾之强弱,有赖于脾胃的滋养。又云“肾水旺而胃中之津液自润,故肾气足而胃气亦足”,肾精对脾胃的运化亦有重要作用。故脾肾与膀胱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膀胱癌通常发病于中老年人,中位诊断时间男性为69岁,女性为71岁[7]。是男女中年以上,脾肾脏腑功能本就减弱,多有亏虚,使正气渐弱,阴阳常难守衡。因此王教授在辨证论治时尤重脾肾,健补脾肾,可鼓动正气抗邪,制约肿瘤。亦可改善具体症状,减轻患者的尿血与排尿异常等。疾病已成时,补益可使正气有力抗邪,重振颓势,又可支持手术及放化疗过程,改善术后情况。肿瘤生长耗损气血,病程久,愈加虚弱,且癌病患者往往伴有其他疾病,有时甚至无法支持及时手术。待施手术及放化疗等峻烈之法时,亦会损伤正气。中医外科有“护场”理论,认为正气对局部肿瘤形成围困,可抑制肿瘤增长,避免肿瘤转移扩散,更能使药物攻邪减少耗损,增加疗效。健补脾肾即是建立“护场”。结合药物归经、功效与症状表现,在膀胱癌治疗中常用生、炙黄芪补虚升气,茯苓健脾,杜仲、何首乌、女贞子等补肾,在健补的同时平衡阴阳、气血,改善具体症状。
王教授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将膀胱癌辨证分4类:湿热下注证、瘀毒蕴结证、脾肾两虚证、阴虚内热证。再分别予清利湿热,凉血止血;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健脾益肾,软坚散结;滋阴清热,化瘀止痛[8]等不同治法。根据患者症状的不同,推及阳气与阴络阴精的状况,结合临床的不同表现,临证化裁组方,意在平衡阴阳。
分析其阳气与阴精的失衡状态,调治尿血时,当从阴论治,从血考虑。排尿异常多责之阳气虚,当从阳论治,从气考虑。膀胱癌虽发于膀胱,实则在于脾胃失调。尿血及排尿异常等症状也提示脾肾的失职。治疗时需从症状出发,分析阴阳状况,重在调治脾肾。
1.3 引经用药达病所,专科用药有专功 引经药是指某些药物可引导其他药物到达疾病所在部位,能够增强方剂疗效[9]。《医学管见》有云:“引经即引治病之使,致谓病之所在,各须有引导之药,使药力与病遇始得有功。”在肿瘤治疗中亦需引经药。王教授在多年的经验中发现龙葵、萆薢可作为膀胱癌的引经药。龙葵性苦、寒,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发现龙葵在肿瘤治疗上有抗细胞凋亡、调控细胞周期、抗侵袭转移、增强免疫力等功效[10],且龙葵可以利水消肿,其清热解毒、利水消肿之功效利于攻毒散结,通利小便,在膀胱癌的治疗中十分重要。萆薢性平,味苦,入肝经、胃经、膀胱经,具有利湿去浊、祛风通痹的功效,临床上用于治疗风湿痹痛,腰膝疼痛等证。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萆薢有效成分在泌尿系统、免疫系统等方面均具有一些药理活性,亦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11]。王教授以龙葵、萆薢为治疗膀胱癌的引经药,既引诸药直达病所,同时发挥其清热解毒去浊之功效,可谓精妙。
专科药是指主要用于某种疾病的药物。王教授治疗膀胱癌常选用土茯苓、猪苓、茯苓、泽泻、杜仲等作为专科药使用,确有疗效。土茯苓除湿解毒,对湿热淋证有独特功效,亦可除痈肿。猪苓、茯苓、泽泻均为利水渗湿之药,对膀胱的利水通达有所助益。且茯苓能补能利,兼能补益,亦可利湿以助除痰,用以化解痰饮毒浊。猪苓利水渗湿,入肾与膀胱经,通淋消肿满,除湿利小便,功专于行水,可助阳利窍。凡水湿在肠胃、膀胱者,必须猪苓利之。泽泻通利小便,泄邪于下。杜仲补肝肾,强筋骨,可温补肾阳,强健腰肾。补肾而性偏燥,治肾中有湿气为宜,以其动而能散湿之功。诸药合用,使泄中有补,真阴不竭。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土茯苓在抗炎性反应、抑制肿瘤的发生发展、提高机体的自我保护和调节能力等方面作用显著,在肿瘤、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等相关疾病治疗中作用显著[12];茯苓中含的茯苓多糖、三萜类等成分,具有利尿、镇静、提高免疫力、抗炎、抗肿瘤等多种药理作用[13];猪苓多糖有抗肿瘤、抗炎、护肝和抗纤维化等作用,可改善微循环、扩张血管等[14]。针对尿血等症状,王教授亦有调整。用当归补气活血补血,《本草新编》认为其对疮痈未溃者可去毒而除秽,已溃者活血而生肌;阿胶尤善补脾虚劳倦之血,滋阴止血;栀子善清热利尿,凉血解毒止血;白茅根凉血止血,清热利尿;仙鹤草补虚解毒,收敛止血。以上均为治血尿之药。
王教授在治疗膀胱癌中,常以龙葵、萆薢引经,既引诸药直达,又可施展自身疗效,同时佐以土茯苓、杜仲、猪苓、茯苓、泽泻等专科用药,对症治疗,随症加减,健补脾肾同时改善症状,用药精当,疗效显著。
1.4 以毒攻毒专注局部,调补气血顾及全身 王教授治疗膀胱癌常用生药、虫药,不避毒药,以毒攻毒是一大特色,意在专攻局部,使用具有攻邪抗癌作用的药物抗击毒浊。常用化痰祛湿、软坚散结、通经活血、清热解毒之品。而生药、虫药、毒药正有此功。生药是未加工或只经简单加工的中药。虫类药是生物界中的虫类生物入药。毒药指有毒性的药物。炮制虽能纠正其偏性,减轻药物的毒性,但治疗肿瘤有时恰恰需要取其毒性、偏性,不减其本效[15]。肿瘤虽本虚标实,但一味补益不免助癌发展。肿瘤生长迅速、压迫局部,可出现发展、转移等。且癌毒炽盛,深居脏腑,非攻不克,只有投以性峻力猛的有毒之品才能及时有效的治疗。癌毒邪深居膀胱,治疗时可用生药、虫类药、小毒药及时攻邪。取此类药物性峻力猛,有攻毒散结、化癥消肿、通络止痛之效,若攻伐之力不足,难免发生扩散转移复发,故应大胆用药。选药务必精准,针对不同毒浊辨证用药。椿根皮清热燥湿、止血;苦参燥湿利尿;藤梨根清热解毒,利尿止血,此三药可利湿化浊。生半夏有毒,善燥湿化痰;胆南星清火化痰;山慈菇有小毒,善化痰散结;夏枯草清肝解郁,清燥湿热,此四药可化痰祛浊。瓦楞子为动物壳,可消痰化瘀,软坚散结,可治瘿瘤痞块;半枝莲清热解毒,散瘀化浊;马齿苋清热利湿,凉血解毒;白花蛇舌草解毒泄浊,此四药可解毒泄浊。对于癌痛明显的患者,可用马钱子、闹羊花镇痛。马钱子有大毒,可通络止痛,散结消肿;闹羊花有大毒,可散瘀定痛。中医学认为虫类药为血肉有形之品,多属咸、辛,性温或平,大部分有小毒。由于辛味能散、能行,走窜温通,可荡涤积滞;咸味入肾入血,软坚散结,以咸味药引经报使,亦有引经入药之效[16]。王教授常用虫类药治疗瘀血、癌性疼痛,如僵蚕、干蟾皮(蟾蜍)、穿山甲、水蛭、全蝎、蜈蚣、土鳖虫等。既能引药入肾,又可破瘀显效。此法虽功效显著,但王教授强调,必须把握用药剂量剂型,为求安全,可配伍少量生姜解毒等;其次,务必向患者交待好煎熬方法,特别是有毒药物的先煎和煎煮时间,如患者服药后明显不适,及时停药就诊。若煎煮后气味难闻,难以下咽,可在处方中佐以焦三仙(焦麦芽、焦山楂、焦神曲)、肉桂、肉豆蔻等调整气味。
使用生药、虫类药、毒药,意在专攻局部,其本仍落在补益气血,扶助正气,平衡阴阳之上。故不能妄投,使用时需慎重,适量应用,不宜量大久用,打击癌毒以衰其大半即止,避免损伤正气,加速溃败。膀胱癌为慢性消耗性疾病,多为虚证,用药时首先要保护好正气,从根本上改变患者虚弱状态。其次攻法猛烈,正气虚衰使不可承受,攻邪当在补益基础上施方。术后及放化疗患者,毒浊已然大去,正气正弱,宜修养补益,不应大加攻伐。调补全身气血,健运脾肾,意在扶助人体正气,补益虚弱,协调机体阴阳偏盛偏衰情况,可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增强抗邪能力,抑制膀胱癌的生长、转移、复发,正所谓“养正积自除”。补益气血,顾及全身,正合平衡阴阳、改善症状、调治脾肾的治疗理念。在此理念指导下,扶正健脾益肾治本,攻毒散结解郁治标,攻毒浊之时注意补益正气,不求急功,缓缓图之,顾及全身状态。意在调整正邪局势,恢复正常的阴阳平衡状态。
王教授用药精准有特色,用药虽用生药、虫药、毒药,实则针对毒浊及时攻伐。只为攻邪助正,强调必须结合膀胱癌病情及患者体质,严格把握药物选用与剂量,调补气血顾及全身,攻毒适可而止,时时考虑顾护人体正气。
2 典型病例
王某,女,68岁。2002-11-11初诊。2002-10-15确诊为膀胱癌,经电灼及局灶切除,病理为膀胱移行细胞癌Ⅱ级,术后用灌注及介入1次。现症见尿多尿频,量少,有血尿,时有腰痛,下坠感,舌淡黯,舌底动脉黯,苔白,脉沉。诊断:膀胱癌(脾肾亏虚兼湿热证)。处方:生黄芪15 g,炙黄芪15 g,补骨脂15 g,土茯苓15 g,生首乌15 g,龙葵15 g,仙鹤草15 g,白茅根15 g,猪苓15 g,茯苓15 g,车前子10 g,白花蛇舌草15 g,鸡血藤15 g,阿胶10 g,生甘草10 g。日1剂,水煎2次取汁300 mL,分早、晚2次口服。2002-11-25二诊,尿频好转,下坠感好转,血尿减少,面黄,舌稍淡,苔白,脉沉。处方:当归12 g,鸡血藤30 g,补骨脂15 g,生首乌15 g,土茯苓15 g,仙鹤草15 g,龙葵15 g,生黄芪15 g,夏枯草15 g,白茅根15 g,阿胶10 g,女贞子15 g,生甘草10 g。2002-12-08三诊,尿清,憋尿时痛,面色渐润,舌淡,苔白,脉沉。处方:生黄芪15 g,生首乌15 g,土茯苓15 g,当归10 g,鸡血藤15 g,阿胶10 g,女贞子15 g,白茅根15 g,补骨脂15 g,仙鹤草15 g,生地黄15 g,熟地黄15 g,泽兰15 g,白芍15 g。患者症状好转,未再复诊。
按:患者老年女性,阴阳失衡,脾肾渐弱,正气无力抗邪,使邪气停滞,代谢不得清,毒浊蕴结。经手术并行介入治疗后,肿瘤既除,不必妄加猛药。然正气已虚,阴阳失衡未改善,观其尿频尿多,时有腰痛及下坠感,考虑肾气虚衰,无力制约膀胱,开阖失司。肿瘤虽除,湿热之邪未净,伤及阴气,蕴则化火,伤络血破,发为血尿。阴阳失调、脾肾不足为本,湿热为标,治以补虚扶正调补脾肾为本,清利湿热除标。用药以健补脾肾之品为基,龙葵引经,清利湿热,施淡渗利湿专科之药,改善尿频症状,佐之活血止血,稍用解毒化浊之白花蛇舌草,清解浊气。用药后果见效,尿频症状改善,可见气化得行,故思路不变,但仍有尿血,为阴分不足,故加用补阴之女贞子及补血活血之品。三诊时未再尿血,此时阴阳渐平衡,症状改善,面色渐润,多加补益,使正气得复,脾肾渐益。补益之余稍加解毒化浊之品,以消除邪气。辨证精准,治疗得当,患者症状明显改善。
3 结语
王教授认为,膀胱癌发病以阴阳失衡为本,毒浊内结为标,浊毒阴邪损伤阴分血络是膀胱癌的主要病理机制。治疗时当依症辨证论治,明晰阴阳失衡情况,重在调补脾肾。当以扶正补虚,化浊解毒为原则,立法扶正健脾益肾治本,攻毒散结解郁治标,使阴阳平衡,正气足以抗邪,改变正邪交争局势。在此理念上,以龙葵、萆薢引经直达病所,佐以土茯苓、猪苓、茯苓、杜仲等专药,在扶正同时适量运用生药、虫类药、毒药,重抗邪气,使正气渐复,邪气渐消,病邪得抑,症状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