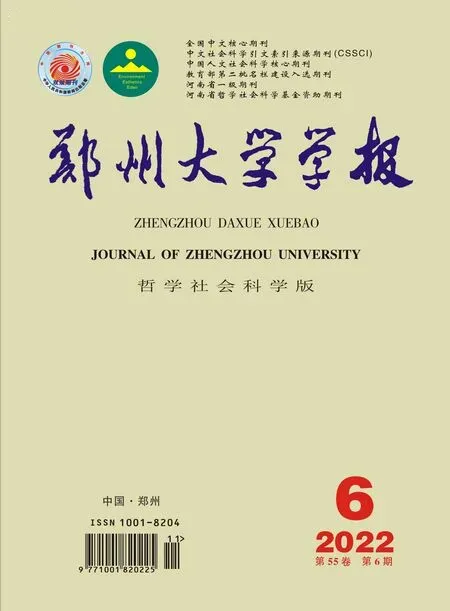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黄色新闻的社会控制
——以上海“黄陆案”为例
张振亭 张桂杰
(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美式新闻的影响,中国报刊界“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性,诸如追求轰动效应和鼓动感伤主义以迎合大众”[1](P27)。“黄色”罡风吹遍上海望平街,“连《新闻报》《申报》这两位老大哥都站不住脚,非靡然从风不可”[2](P127)。黄伯惠接办《时报》后,更是模仿美国“黄色新闻大王”赫斯特上演黄色新闻的“拿手戏”[3]。在“刘海粟人体写生”“石女离婚”“马振华自杀”“太保阿书伏法”等系列事件推动下,黄色新闻渐成风潮,遂演化为报界的一种病态。1928年6月至1930年6月,围绕上海公馆大家小姐黄慧如与已有妻室的包车夫陆根荣由私奔到陆被审判再到黄猝死一案(简称“黄陆案”),《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大报以及《福尔摩斯》《罗宾汉》等小报进行长篇累牍、不厌其详的报道,引得人们“争相购读”,“每天清晨还是曙光初透,而望平街上早已万头簇动,人山人海,等不及报贩的分派,群以先睹为快”[4](P139),轰动性可见一斑。黄陆案无疑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持续时间长、报道多、影响大、社会反应激烈的一起新闻事件,堪称中国新闻史上黄色新闻的典型。黄色新闻猛烈冲击着社会伦理道德、风尚习俗和规范秩序,引发了消费女性、造谣诽谤等诸多社会问题,造成不良的影响,文化知识精英甚至普通读者纷纷加入到抵制黄色新闻队伍之列。同时,当时的政府在行政司法层面也有所行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予以约束。这表明,当时社会各界对于黄色新闻确乎有所控制。但总体上看,司法和行政控制在具体执行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成效甚微。因此,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黄色新闻的社会控制方式与效果,有必要进行分析研究。
社会控制广义上是指“对人们的行动实行制约和限制,使之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的任何社会过程”[5](P481)。由于新闻事关公共利益,又具有建构社会规范的功能,因此,新闻的社会控制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议题之一。舒德森曾总结了四种新闻社会学研究路径,即政治的、经济的、组织的和文化的控制[6](P172-197)。在我国新闻研究史上,对越轨新闻的社会控制论述也早已有之,如邵飘萍提出如果新闻纸“滥用威权流于专制,或颠倒是非,捏造谣言,则社会方面应加以制裁”。如果有“不德”记者滥用权力,则“同业可加以制裁”[7](P224)。任白涛认为可以从国家、社会、新闻社或全新闻界、记者个人等层面,对报界失范行为予以制裁[8](P114)。关于该问题的探讨一直延续至当代,相关学者对新闻的社会控制进一步总结概括,指出新闻业受信源、商业、政治和同伴压力[9](P200-206),或认为受司法、行政和资本控制,以及媒体自律和公众震慑等方面的影响[10](P239-240)。参考上述研究,本文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黄色新闻的社会控制分为政策法规控制、同业控制和公众控制三个方面。
二、南京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对黄色新闻的政策法规控制
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实践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新闻报道多以具体越轨行为(如揭人隐私、毁人名誉、淫秽色情、捏造事实、描写失当等)作为查处的依据。1927年10月,《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小报审查条例》核准施行,规定“诡辞诲盗,有妨治安者”“迹涉淫亵,足以诱惑青年者”“摘人隐私,毁人名誉,专事嘲讪谩骂者”以及“专载妄诞,以淆惑观听者”,将禁止发行或销行,并惩戒发行人或编辑人[11](P575)。1928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第251条“妨害风化罪”规定,“散布或贩卖猥亵之文字图画及其他物品,或公然陈列者”,或者“意图贩卖,而制造持有前项之文字图画及其他物品者”,均处一千元以下罚金[12](P61)。1929年8月,因所载《西歪女士之描写文》一文被认为文字污亵有碍风化,《金钢钻》主编遭起诉,所依据的即上述规定[13]。1928年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及警备司令部开始对过度渲染、题目猎奇和描写过当的新闻采取行动,严加查禁,此后各报中“关于自杀之详细记载已不多见”,但“其他奇怪之题目,则固无日不有”。同年10月,警备司令部召集新闻界谈话,要求各报对于此种新闻“勿作铺张扬厉之记载”[14]。
由于早期的政策法规不够具体,管理工作成效不佳。比如当时对一些大报的行为,政府当局往往不予深究。政府严禁报纸有伤风化,上海《时报》首当其冲,曾有人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提出《时报》以巨大篇幅刊载社会新闻,“实有诲淫诲盗之嫌,应从严惩处,勒令停刊”。但大会讨论时却认为该报是一张有历史的报纸,“如在此时处分过严,将被认为压迫舆论,而招致国际上的不良观瞻,因此决议交中央宣传部饬传该报最高负责人来部面加申诫,从轻发落”。“饬传”时,作为最高负责人的老板黄伯惠却没有去,已从《时报》离职但被认为是该报黄色新闻“始作俑者”的金雄白被安排前往南京听训。面对官员“声色俱厉地大肆诟责”,金以欧美报纸均“连篇累牍、绘影绘声地大登其社会新闻”为由据理力争,最终风波竟得以平息[4](P140-141)。当然,在政府的高压下,《时报》在当时也不免要有所收敛[15](P144)。基于政治及社会舆论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政府当局对黄色新闻的管理多为选择性执法,大报凭借其地位和影响力与政府间存在着一定的周旋与抗衡余地,往往可以轻松逃脱。小报在政治格局中无足轻重,向被认为报道有碍风化,一旦越轨就难逃制裁,但很多小报对此显然早已习惯,往往会淡然视之,“不怕坐牢监”,也“不怕罚金钱”[16]。这些表明,当时关于黄色新闻的惩处虽有明文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上当局往往难以落到实处,政策法规的控制效力大受影响。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强化了对黄色新闻的控制。1930年1月,政府核准了《南京特别市教育局民众读物审查规则》,规定民众读物中含有“词句淫亵”“捏造事实,煽感舆论”以及“其他流毒社会,贻害青年”等内容的,一律不准发行[11](P577)。同年12月颁布的《出版法》规定“妨害善良风俗”的内容不得刊载,否则禁止出售及散布,并在必要时进行扣押,同时处以发行人、编辑人、著作人及印刷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之罚金”[11](P107-108)。此外,针对各大报“刊载社会新闻,流毒无穷”的问题,社会局“特地函劝各报慎重登载”。但评论认为,仅纸上空谈而不明令禁止,“只怕无济于事”[17]。
上海报刊多在租界出版,直接受租界当局的控制。1919年6月,《上海法租界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颁布,规定刊行有违反公众安宁或道德内容的,“经理人、著作人,如有印刷人一并送会审公堂追究,按法惩罚”[18]。1926年5月,《法租界公董局印刷业管理办法》出台,其中亦有类似条款。公共租界工部局1919年7月曾拟定“印刷附律”提案,规定不能印刷或转载“任何暧昧性质或卑鄙之事件”,以及“含有扰乱或毁渎性质以至破坏治安之事件”等[19]。该提案最终未获批准,但其基本内容对租界内的出版活动却产生了重大影响。1928年1月,《福尔摩斯》因刊载“秽亵文字,有伤风化”,被工部局刑事检查科起诉,最终被判“处罚金三十元”[20]。1928年6月,《罗宾汉》刊载的文章被认为文字污秽并诉至临时法院,但经审理判其无罪[21]。1930年,《礼拜六》因载有“猥亵图画及不规文字”被查悉,编辑和经理被各处罚金一百元,“如无力完纳,准以二元折易监禁一日,报纸没收”[22]。一百元约是当时普通外勤记者两三个月的工资,因此上述惩罚总体上属于“薄惩”。事实上,此间的新闻报道“只要不对租界当局的殖民统治构成威胁,不触犯法律,任何新闻报道,租界当局都是允许的”[23](P183)。当时的多元统治格局以及租界文化的商业性,为黄色新闻的野蛮生长提供了温床。
由上可见,针对1930年前后的黄色新闻潮,特别是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后,政府和租界当局也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对违反者追究责任,施以惩罚,予以强制控制。但遗憾的是,在黄陆案中涉及这种硬性控制很是少见。从事件发展及结果看,政策法规控制近乎失灵。1929年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社会月刊》发文称,黄慧如事件“报纸上闹得乌烟瘴气,在理她已经死了,终可告一段落。可是一般吃黄陆饭的朋友和捕风捉影的记者先生,还不肯轻轻放过她,真死假死闹得一团糟”。文章还称报纸对女性的关注点令人迷惑,一遇稍有名气的女子就随便给人作起居注,是“社会的病态”[24]。该文对黄色新闻的分析不可谓不透彻,批判不可谓不严厉,但却未见其有对社会局具体控制行动的报道。1929年1月,镇江市一市民呈请民政厅禁演黄陆故事戏,理由是该戏“旨趣卑劣”“只知投机牟利,不顾其他”,遗毒社会,诲淫伤俗。民政厅做出批示,通令各地严行禁止,依令查办[25]。但5月份“通运路聚乐第一台”却仍在张贴海报,“定期开演黄慧如与陆根荣”[26]。这表明,民政厅的查办缺乏震慑作用,演出活动并未停办。在上海,社会局鉴于演出黄陆的戏剧内容复杂,特地通告游艺界,对于排演的脚本,“须要纯正,切勿画蛇添足,无中生有,一味的只顾营业,不顾到社会上的利害”[27]。以黄陆案为题材拍摄的电影《血泪黄花》曾因内容渲染失当,“且足以引起社会间不良之观感”而被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禁映,但之后仍有戏院开映此片,电影检查委员会只打算处“少数之罚金以资惩戒”[28]。这些足以表明政府对黄色新闻的基本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告官不究。
三、新闻同业对黄色新闻的控制
伴随着黄色新闻之风肆虐,新闻界声誉受损,一度陷入社会认同危机,新闻记者甚至被视为“报痞”“报商”。这种状况激发了业内一些报刊、报人的共同体意识,不约而同地对黄色新闻予以批判,要求社会局严查,同时借助记者团体的官方刊物连续发文,指出黄色新闻没有登载的价值,有违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妨碍社会风化且涉嫌违法。他们倡议报界开展自清运动,鼓励报馆自我革新,以期通过同业约束的方式控制黄色新闻的蔓延。
早在黄陆案报道火热之时,就有不少报刊和报人表示不满和抗议,他们批评记者盲目跟风,报道失实,助长了该案例中不实谣言的滋生[29]。当时有小报批评《时报》与《时事新报》败坏社会风气,有失大报风范和引导之责。但《时报》对此却不以为然,表示自己“抱光明磊落态度,不屑与人争辩”[30],并称报道详实而迅速[31]。《时报》的做法和态度,令社会各界大失所望。有文章称,黄慧如离世已明,但《时报》“为纠正第一次之新闻起见,乃不惜多方引证”以证明她未死,证据却不足为信,实在是自贬身价,牺牲名誉[32]。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郭箴一也直斥上海新闻记者在黄陆案报道中对当事人隐私及名誉的侵犯,认为新闻记者“决不能只图迎合社会心理,以之公开披露,但上海之记者却不知‘私人秘密’之应当保守,对于新闻,反毫无隐讳之加以宣布”,以“无冠帝王之笔”,制造轰动新闻[33](P82)。广州报界将围绕黄陆案的报道作为业界失范的典型给予批判,有报纸指陈在该案报道中新闻记者为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把全副精神用在采访黄色新闻上”,社会深受“黄色新闻的流毒”[34]。
黄陆案的报道还引发新闻界对于社会新闻“黄色化”的检讨。《大罗宾汉》发文称,记者对此类事件连篇累牍,而对一切慈善和有助于社会世道的事却不甚注意,将报纸作为“无聊文字的战场”,简直是“小题大做”[35]。另有人指出,各大报热衷报道黄陆案,以及“一切不离于‘奸’‘淫’‘劫’‘争’的新闻”,所启迪的“乃是一些秽淫晦盗的智识”,所引领的“乃是一些为非作恶的思想”,有悖报界所负民众喉舌、启迪民智、引领思想的天职。对于这一问题,有人建议为防微杜渐,社会局最好进一步告知各报“禁止此类无益人群的社会新闻之刊载”[17]。虽然当时的报界同业对黄色新闻的泛滥有所警觉,但在实际上,“各人站在各人的立场,各报站在各报的立场,动辄因利害冲突,不能结合,各自为政”[36](P175)。大报与小报之间本来就时常处于矛盾状态,《时报》《时事新报》等因黄陆案报道引发社会不满时,小报也借机攻讦,对大报口诛笔伐。
新闻界行业组织在批判黄色新闻时也有所行动。影响较大的是成立于1927年的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1930年前其章程未明确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但其会刊《记者周报》对新闻道德风纪问题多有着墨。如《记者周报》在1930年连续多期发文论及黄陆案、黄色新闻和新闻记者的道德和责任问题,试图对报界越轨行为予以纠偏。一些新闻界人士如身处法国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的陈学昭发文指斥报界关于黄陆案很少有正当评价,呼吁记者记述新闻取材要真实,秉持“公平及客观的态度”[37]。身在日本的沈立群刊发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报界存在一种“显著的弱点”,即对秽亵不堪的新闻特别注意,“不是用大号字刊出,便记载得详尽无遗”,实在有伤社会风化,与其被动取缔,不如报馆自我革新[38]。时任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执行委员的《时事新报》编辑、《记者周报》主编之一周孝庵则阐释了登载新闻应具备的基本要点,一为具备新闻价值,二为法律所许,三为于社会风化无碍,四为道德所容[39]。他还提议报界应举行一次“清洁运动”,扫除“社会新闻中的强奸及有伤风化”部分[40]。有趣的是,周孝庵曾采访报道过黄陆案,他基于自身反思基础上的上述认知和建议,颇有警醒意义。但是,除了发文讨论、呼吁外,新闻界同业组织鲜见有针对黄色新闻的其他控制举措。
四、社会公众对黄色新闻的控制
黄陆案经报章大肆渲染,成为轰动全国的黄色新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渐成社会舆论。从公众舆论主体来看,可分为一般民众、文化精英和一般社会组织。一般民众参与者以女性最具代表性。1929年6月,《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称黄慧如的人格是“性的结合”[41],引起一名叫冯惠贞的女性的不满,致信该报抗议,认为报道“有辱女性”[42]。一位民众撰文提出,上海各大报放着国家大事不敢据事直书,“却去找那上海下流社会所干的奸、淫、偷、盗来充篇幅”,有负“监督政府”的天职[43]。还有读者一语戳穿报道的两面性,“一面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一面大登“强奸、吃醋、风流”等社会新闻[44]。可见,读者对黄色新闻是拒斥的、持批评态度的,要求报刊和记者负起应有职责和使命。从根本上说,没有读者报刊就无法生存,报道黄陆案最健者之《时报》,“报格日趋低落”,最终“不为社会所重视”[45](P179),为上述命题提供了绝好例证。
通常情况下,社会精英特别是知识文化精英占据道德高位,是社会道德的捍卫者,他们自然要抵制、抗议黄色新闻,并在舆论中扮演意见领袖角色。针对黄陆案的报道,鲁迅直斥个别沪上人“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他指出,“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但“害则甚大”[46](P419)。沪滨公学教师张世豪斥责记者在报道黄陆案时一味凭主观出发,“抹杀了客观的事实”[47]。上海中国公学教授兼教务长樊仲云撰文指出,上海报纸对于黄陆案的报道“延长至数月之久”,使黄慧如不堪重负,最终沦为黄色新闻的牺牲品。上海报纸的靠山“完全系封建的余孽和腐化的官僚”,记者的态度是“玩世的,享乐的,冷酷的,而毫无同情的态度之表现”。他还批评上海报纸“大报的小报化”“不顾堕其‘报格’,登载卑劣消息,以迎合次智识阶级的欢心”[48](P58-61)。世界语学者黄尊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批评报纸上刊载的黄色新闻“简直是年年月月,无日无之,而且时时都可以占足半版的篇幅”[49](P147)。
一般社会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在抵制黄色新闻报道方面表现突出。纷纭一时的黄陆案较早就引起了妇女组织的关注,并对报刊诋毁污蔑黄慧如的行为表示不满和抗议。1929年1月成立的妇女共鸣社,是当时活跃于上海、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妇女组织。其机关报《妇女共鸣》曾被称为“妇女界唯一之刊物”,是维护妇女权益的重要舆论阵地[50](P236)。该社发表专文强烈谴责黄色新闻记者的卑劣行径及对女性的污蔑,认为是新闻记者逼死的黄慧如。文章指斥黄陆最终悲剧的根源在于各报的渲染,尤其是有的报纸还妄造谣言以吸引读者注意,黄慧如之死并非社会经验浅薄所致,是新闻记者“徒从中推波助浪,必置黄慧如于死而后已”[51]。该社批评新闻界说,以往关于妇女团体的新闻“多摈而不录”,然而遇到马振华、黄慧如等新闻“必又盈篇累牍,载而又载,极尽宣传之能事”[52]。该社当时还计划向政府提出议案严令禁止书籍报章刊载“有伤风化之文字”,犯者“以刑事犯论”,应“设法止制之”,“处以严重之惩罚”[53]。
妇女共鸣社在当时为黄慧如发声,批评新闻报道的黄色化现象,要求严惩黄色新闻记者,并打算向政府当局提案,显示了社会组织所特有的影响力,实属难能可贵。但遗憾的是,就整体而言,针对黄陆案予以反击的妇女团体十分孱弱,未能构成对黄色新闻强有力的控制,这与当时妇女运动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有一定关系。
五、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黄色新闻的社会控制,政策法规方面虽然滞后、迟缓,执行时亦有差异性,且缺乏长效机制,但其属于硬性控制,效力是最强的。由于黄陆案的报道尚没有达到大多数政策法规规定的标准,其结果是虽有相关政策法规,但鲜有针对性的干预。同业控制、公众控制在本质上属于舆论控制,主要方式是公开发表意见,批评相关报刊和记者,效力虽不能立竿见影,但是代表了社会上对黄色新闻的基本态度和要求,一定程度上预示着黄色新闻路线并不可持续。其间,同业控制虽然在制造舆论方面表现突出,但因内部存在冲突,共同体认同感较低,新闻界团体呈现此起彼伏、乍分乍合的现象,或因经济支绌而瓦解,或因意见分歧而消灭,有的虽能勉强存在而仍是“毫无生气”,因而未能“收协作之效”,也未“负起促进新闻事业之使命”[54],行业组织没有起到规范作用,导致控制力大打折扣。其他的如妇女组织作为一般社会组织,并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压力集团参与黄色新闻的社会矫治。而能够投书报刊表达抗议的一般读者毕竟是少数,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不具备条件和能力,有的甚至本身就属于商业文化裹挟下的黄色新闻消费群体。
鲁迅曾批评说,中国的报纸“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55]。这也精辟地概括了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新闻界与公众的关系。对于掌握权力的政府来说,报纸是无权的、弱势的,但对于更弱的社会民众——哪怕是出身于大户人家的黄慧如——而言,报纸又是有权的、强势的。它可以摇笔即来,污蔑诽谤,肆无忌惮,对女性更甚。在黄色新闻报道过程中,有的为利舍义,极尽大肆渲染之能事;有的捕风捉影,污蔑侮辱当事人;有的触犯法律,有违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新闻界因此而面临严重的社会认同危机。
依据系统论观点,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媒介的越轨势必激活社会控制机制予以纠偏,新闻业的自律,公众的抗议以及政策法规的管制等,从不同维度以正式或非正式、强制或非强制的方式对其予以控制,迫使其回到正轨。针对黄色新闻泛滥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形成了硬控制(法律)与软控制(舆论)相结合的基本框架,对新闻业有一定震慑、警示、约束、惩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控制机制尚不完善,社会力量分疏涣散,团体组织参与度有限,内部矛盾重重,政策法规的具体执行有失公允,整体控制效力大受影响,陷入虽有控制却屡禁不绝的怪圈,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