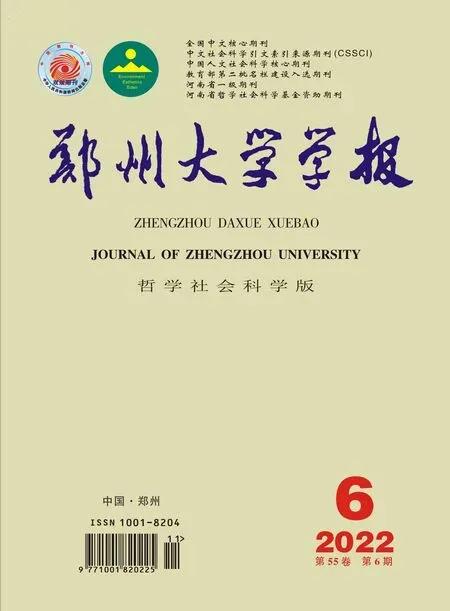虚实相生:“鸟工”“龙工”的文本阐释与文化认知
梁 奇 王佳钦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虞舜是古代著名的圣君、孝子,《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史记》《列女传》以及敦煌变文《舜子变》《孝子传》等典籍对其圣绩与孝行均有书写。为彰显其孝道,《孟子》增设了父母、弟弟的陷害与舜的逃生情节,汉至清代,虞舜罹陷与逃生的故事呈现出不同的阐释系统,这些阐释可分为四类:父亲与弟弟陷害,虞舜自逃;瞽瞍陷害,二妃助逃;“后母”主谋,神祇佑舜脱险;瞽瞍放生[1]。其中,“二妃助逃”的记载首见于《列女传》,它涉及“二妃”使用“鸟工”“龙工”助舜逃生,并为后世所继承而衍生出不同的文本系统。但这些典籍均未明确说明“鸟工”“龙工”所指,以致学界对其释义不一。鉴于此,拙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辨析相关文本及其阐释,详细考证“鸟工”“龙工”产生的历史渊源、神话基础与现实背景,以便更好地揭橥其文化意蕴与学术价值。
一、“鸟工”“龙工”的书写与阐释
《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所引《古列女传》记载“二妃”使用“鸟工”“龙工”助舜逃生,后人在此基础上展开书写与阐释。
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告二女。二女曰:“时唯其戕汝,时唯其焚汝,鹊如汝裳衣,鸟工往。”舜既治廪,戕旋阶,瞽叟焚廩,舜往飞。复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时亦唯其戕汝,时其掩汝。汝去裳衣,龙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从掩,舜潜出[2](P104)。
司马贞《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列女传》与上文相似:“二女教舜鸟工上廪……龙工入井。”[3](P34-35)它与洪氏所引当属同一文本系统。《古列女传》明确指出舜借“鸟工”飞离,脱“涂廪”之困,靠“龙工”潜出,解“浚井”之危,凸显了“鸟工”“龙工”在虞舜逃生时的重要作用,并被后世典籍所承继。《山海经·中次十二经》郭璞注曰:“二女灵达,鉴通无方,尚能鸟工龙裳救井廪之难……”[4](P158)《竹书纪年·有虞氏》沈约注、《宋书·符瑞上》均载:“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廪,自下焚之,舜服鸟工衣服飞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龙工衣自傍而出。”[5](P762)《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梁武帝《通史》、梁元帝《金楼子·后妃篇》、沈泰《盛明杂剧》卷三十均有“鸟工”“龙工”助舜之记载。然而,今本《列女传》则删去“鸟工”“龙工”,仅言“二妃”助舜脱险:“瞽叟焚廪,舜往飞出……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6](P1)二物的移除却消解了虞舜飞离、潜出的神秘性,弱化了故事的神话属性。
综上可知,《古列女传》将“鸟工”“龙工”作为虞舜逃生的必备工具,后世典籍或将“龙工”改为“龙裳”,或兼用“鸟工衣服”与“龙工衣”,其中已暗含“鸟工”“龙工”为衣物。然而,东汉至当下学者的阐释却出现不一致的义项,甚至相牴牾。
第一,“鸟工”为“习鸟飞之工”。详见萧道管《列女传集注》引曹大家语[7](P1-2)。
第二,“鸟工”指“如鸟张翅状”。明沈泰《盛明杂剧》卷三十“鸟工”下有“故他登廪如鸟张翅轻轻飞下,不得损伤”[8](P259)。沈氏对“鸟工”进行摹状性说明,认为舜如鸟展翅般飞离仓廪而未受损害。该说当对《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似鸟张翅而轻下,得不损伤”有所继承[3](P34),而《汉语大词典·鸟部》将“鸟工”释为“有如鸟飞的本领”[9](P1031),则与“如鸟张翅轻轻飞下”相似。
第三,“鸟工”指“头与身皆著毛”。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六引《宋书·符瑞上》舜“服鸟工衣飞去”,以证明王莽“头与身皆著毛”[10](P229)。沈氏认为“鸟工衣”指头与身所佩戴的羽毛,当继承了《山海经》的佩饰习俗及郭璞“佩其皮毛”之说。
第四,“鸟工”“龙工”分别指绘有鸟形与龙形彩纹的衣服。《佩文韵府》将“鸟工”“龙工”归入“衣部”,直言鸟工衣、龙工衣[11](P31)。袁珂认为“鸟工”“龙工”分别是绘有鸟形或龙形彩纹的衣服,舜穿上它们后便能化身大鸟飞出、变为游龙潜出[12](P262-264)。陈泳超将“鸟工”“龙工”当作能赋予舜飞、潜能力的衣物,认为舜“穿上‘鸟工’、‘龙工’,便有了‘鸟’与‘龙’的特殊本领,所以舜能‘飞出’、‘潜出’”[13](P220)。《汉语大词典·龙部》释“龙工(衣)”为“古代疏浚河流时穿着的工作服”[9](P1460),并引《列女传》《宋书》加以说明。
这些阐释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将“鸟工”“龙工”视为实体的衣物,如《山海经·中次十二经》郭注、《佩文韵府》《宋书》、袁珂《中国神话传说》、陈泳超《尧舜传说研究》《汉语大词典》等。其二,将其释为虚拟的能力或法器,如汉代曹大家、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汉语大词典·鸟部》、尚永亮《英雄·孝子·准弃子——虞舜被害故事的文化解读》等。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其物质构造,后者侧重于其实用功能。其中,郭璞的注释重在揭示《山海经》神怪与名物的神异性,“疏其壅闳(阂),辟其茀芜”[4](P6)。他认为“二女”是“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4](P157),故二女所用“鸟工龙裳”自然具有神性。沈钦韩认为鸟工衣是头、身皆著毛而具有飞行能力,已暗含鸟羽拥有巫术之力,从而使佩戴者具备非凡的飞行能力。袁珂、陈泳超、尚永亮等学者承续郭璞,从神话学视角研究《山海经》,或对“鸟工”“龙工”的功能进行界定,指出其为“衣服”与“神妙的法宝”[12](P262-264),或认为它们“已颇具可助人飞翔或潜游的神秘色彩”[14],均值得我们借鉴。然而,袁珂对于舜“化身大鸟飞出、变为游龙潜出”的阐说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12](P267),且仍未解决“鸟工”“龙工”的属性问题。司马贞、沈泰认为“鸟工”指“如鸟轻飞”,将“鸟工”视为一种比喻性的摹状,与神话相去甚远。《汉语大词典》仅强调“鸟工”如鸟一般飞行的能力,并未言明其为何物。将“龙工”理解为疏浚河流时所穿的工作服,承袭了古代的“龙裳”“龙工衣”之说,且用后世的服饰事象论证“龙工”所指,属于“以今证古”的阐释范式,与泰勒的“文化遗留物”之说不谋而合[15](P11)。但是,其中亦有不足:其一,忽略“鸟工”“龙工”的巫术特质而过于重实。其二,未能规避“以今证古”的缺憾,忽略民俗的变异性特征,以及空间差异对文化差异的影响等[16]。可见,史书、词典囿于编写体制(须典雅、正统),故缺少虚拟的神话色彩而偏重物态的描述。
事实上,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神话观,还是后来乃至当下其他学者的神话观,它们在承认虚幻特性的同时,更将神话视为现实生活的记录,强调神话的认识作用、记事功能与社会功能(1)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神圣的叙事:神话理论读本》、陈连山《论神圣叙事的概念》、王小盾《神话求原·序》等。。可见,神话具有虚实兼备的特征。而“鸟工”“龙工”是虞舜神话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唯有虚实兼顾方能较好地诠释其本质,也与神话虚实相间的特质相契合。其实,《古列女传》“鹊如汝裳衣,鸟工往”本身已含有穿戴“鸟工”之义。我们由“汝去裳衣,龙工往”可知“龙工”为脱去“裳衣”之后的行为,则“龙工”必为能穿戴之物。以此类推,“鸟工”应该与之相似。另外,后世文本常将“工”与“裳”互用、“鸟工(龙工)”与“衣(衣服)”连用,如郭璞注《山海经·中次十二经》将“龙工”作“龙裳”,《宋书·符瑞上》有舜“服鸟工衣服”“服龙工衣”,《金楼子·后妃篇》为“衣鸟工往”“衣龙工往”[17](P362)。其中,《金楼子》中的“衣”作动词,“鸟工”“龙工”自然为穿戴的对象。《宋书》中“鸟工”“衣服”连用,要么是“鸟工”修饰“衣服”的偏正关系,要么二者是并列关系,但无论哪种情况,“鸟工”均与衣物相关,指能穿戴的佩饰或衣物。可见,“鸟工”“龙工”皆为衣物,与袁珂“画着鸟形彩纹的衣服”“画着龙形彩纹的衣服”相符[12](P262-264),这属于“鸟工”“龙工”实的一面。需要指出的是,它们还应具有巫术性质,通过触染巫术将鸟善飞、龙善游的属性传递给虞舜,从而助舜成功逃离家人的陷害,此为其虚的一面。可见,它们具有虚实兼备的特征,兹可从先民衣鸟兽皮毛之习俗、“二女”及其后裔使鸟御龙的文献记载、“鸟工”“龙工”的巫术图像学原理以及古代“形名”传统等方面论证之。
二、“鸟工”“龙工”的民俗渊源与生成背景
神话既“反映了初民对事物的认识,也反映了因这种认识而产生的风俗习尚”[18]。就此而言,神话本身就是民俗事象,故而,我们可依据民俗事象与民俗活动考索、阐释“鸟工”“龙工”产生的渊源与生成背景。
(一)衣皮毛习俗与以羽通神为“鸟工”“龙工”产生的民俗源头
古代先民有衣鸟兽皮毛之习俗。《礼记·礼运》载上古先民在“未有麻丝”时“衣其羽皮”[19](P3066)。《王制》载北方狄人“衣羽毛,穴居”,孔颖达疏曰:“东北方多鸟,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19](P2897)《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子次于乾谿,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复陶”,杜预注为“秦所遗羽衣也”,孔颖达疏曰“冒雪服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御雨雪也”[20](P4481),此为用禽兽毛羽做成的御寒衣物[21](P1338)。《汉书·地理志》颜注保存了东北“鸟夷”服鸟衣之俗:“搏取鸟兽,食其肉而衣其皮也。居住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22](P1780)可见衣羽衣之俗在上古留存时间之久。这亦可从考古资料中得到验证,云南沧源岩画中有许多头插羽毛、身披羽饰的人物形象,这些岩画的创作时间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晚期[23](P72)。据说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24](P383),先民才以丝织品为衣服。
鸟类尾脂腺所分泌的油脂与其他分泌物具有防水、保暖的功效,早期先民将鸟兽毛皮视为“显著的遮蔽风雪功效的功能性服饰”[25](P11),御寒的实用目的明显。在满足御水、保暖等基本需求的前提下,人们才开始注重所衣鸟兽皮毛的审美价值与宗教价值,“衣必常暖,然后求丽”[26](P656)说明了羽衣由保暖到审美的转化。先民使用鸟兽羽毛遮风避雨、取暖护身而不知其中的科学道理,所以他们又将鸟兽羽毛作为通神的媒介。《周礼·地官》载“羽人”司掌征收毛皮,“以时征羽翮之政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27](P1613)。《天官》载“司裘”将征得的皮毛制成羽衣礼服,“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献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献功裘,以待颁赐”[27](P1470)。于是,鸟羽之服成为连通天地的津梁,具有礼制文化内涵。当实用、审美上升至礼制时,羽衣已富有宗教巫术的含义。如《原始思维》记载墨西哥的回乔尔人巫师佩戴鸟羽通神[28](P32)。《吕氏春秋·求人篇》载禹南至羽人之处为不死之乡[29](P292)。《山海经·海外南经》的羽民国“为人长头,身生羽”,郭璞注曰:“画似仙人也。”[4](P163)《楚辞·远游》将羽人与长生关联,“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曰:“因就众仙于明光也。……《山海经》言‘有羽民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洪兴祖认为“羽人,飞仙也”[2](P167),朱熹承继之,姜亮夫认为洪注说明“人之得道者能飞行自如,如鸟之有羽翼也”[30](P259)。事实上,古代有诸多佩戴鸟兽羽皮或器官以祛病禳灾、求福祈康的习俗,如《山海经》所记载的佩戴鸟兽羽皮或器官使人不畏、不聋、不眯、不厌、宜子孙。孙作云认为这是以鸟为图腾的鸟氏族自我庇护的方式[31](P606-607),巫术意蕴明显。它们与《吕氏春秋》《楚辞》中的羽人以及墨西哥巫师所佩戴的鸟羽,共同构设了羽衣、羽人的宗教意象,影响后世。
(二)“二女”及其后裔使鸟御龙的习俗是“鸟工”“龙工”产生的神话基础
《山海经·中次十二经》载“帝之二女”居住在洞庭之山,后世注疏对“帝”的解释有分歧,郭璞认为是“天帝”[4](P157),汪绂认为是“尧”,则“二女”为娥皇、女英,即《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32](P53)。袁珂调和郭、汪之说,认为“尧之二女即天帝之二女也,盖古神话中尧亦天帝也”[33](P176)。学界多遵从袁珂的说法,认为“二女”即“二妃”,指娥皇、女英。笔者以为,她们使鸟御龙之本领,当为“鸟工”“龙工”产生的神话基础。
首先,“二女”为使鸟御龙的神祇。《楚辞·九歌·湘君》载有湘君聚鱼鸟、驾飞龙的神往畅思,“君不行兮夷犹”“驾飞龙兮北征”“鸟次兮屋上”。王逸认为“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苞洞庭之波,方数百里,群鸟所集,鱼鳖所聚”[2](P61-65)。鸟兽是人们游戏的助手、工作的伙伴和通神的媒介,《山海经·海外西经》诸夭之野、《大荒西经》沃之野均有人鸟和鸣、百神群舞的人神同乐场面,可与湘君役使鸟兽相印证。《海外南经》的祝融、《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夏后启(开)、《海外西经》的蓐收、《海外东经》的句芒、《海内北经》的冰夷等神祇“乘龙”的记载,则与湘君“驾飞龙兮北征”相印证。可见,驾龙驭鸟的神祇尤为常见,“二女”即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其次,“二女”后裔能役使鸟兽。“二女”是帝舜系谱中的主要成员,她们的故事在虞舜神话中“占据着重要地位”[34]。《山海经》多处记载帝俊(舜),计有《大荒经》十处(《大荒东经》四处、《大荒南经》三处、《大荒西经》两处、《大荒北经》一处)、《海内经》五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有“日月夋生……帝夋乃为日月之行”[35],与《大荒经》“日月所处”的日月之神一致,“夋”当为“俊”。郭璞认为“‘俊’亦‘舜’字,假借音也”,郝懿行由“帝俊妻娥皇”进行反向推测,但又不敢完全肯定郭注[36](P328)。袁珂从三个方面补证郭注[33](P345)。于是,“帝俊(或俊、夋)”即“舜”得到学界的认可。舜与娥皇、女英的后裔役使鸟兽的记载多见诸《山海经》,如《大荒南经》载娥皇所生三身国“使四鸟”:“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4](P220)《大荒东经》载帝俊子中容国、黑齿国,及其孙白民国、司幽国“使四鸟”[4](P213-214)。《大荒东经》的蔿国亦使“四鸟”:“蔿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郭璞认为“蔿音口伪反”[4](P212),袁珂据此推判“蔿国或当作妫国。妫,水名,舜之居地也”[33](P294),“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3](P1575)。可见,“蔿国”应为“妫国”,他们为舜之后裔,亦能使唤鸟兽。古人认为“四鸟”乃“鸟兽通名”,“使四鸟”即驯服并通过乘、操、驾、珥、佩、戴等方式役使这些鸟兽,使之服务于己[36](P328)。可见,“二女”及其后裔皆有驯服役使鸟兽的能力,这当为“鸟工”“龙工”产生的神话基础。
(三)汉代羽衣、羽人为“鸟工”“龙工”形成的现实背景
汉代是追求长生不死、生命永恒及神仙信仰炽热的时代,这催生了现实生活和艺术品中羽衣、羽人的出现。其中,羽人多出现在雕塑、画像石(砖)、壁(帛)画等艺术中,它们为肩生双翼的仙人形象,是道家羽化升仙思想的产物。同时,羽人还以半人半鸟的图像形式出现在古代器物上,故被称为“羽人图”或“鸟人图”,该类图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猎壶”。到了汉代,人的成分增多,鸟的成分减少,便生成了头生羽的仙人图,它们常见于漆器、铜镜等器物之上[31](P561-582)。羽衣不仅在画像石中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亦有,如《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时的栾大与其他的使者均“衣羽衣”。颜师古注曰:“羽衣,以鸟羽为衣,取其神仙飞翔之意也。”[22](P1224)《后汉书·酷吏列传》中记载光武帝年间阳平令李章“带文剑,被羽衣,从士百余人到来”,惩治赵刚。李贤注曰:“辑鸟羽以为衣也,《前书》栾大为五利将军,服羽衣也。”[37](P2415)西汉天道将军栾大及其使者、东汉阳平令李章皆为穿羽衣之人,可见两汉时期穿羽衣之俗仍存,它们为“鸟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
综上可知,鸟羽兽皮经过“实用-审美-礼制-巫术”的演变历程。其中,衣鸟兽羽毛是“鸟工”生成的民俗源头,“二女”及其后裔使鸟御龙的习俗是“鸟工”产生的神话基础,汉代的羽人、羽衣为其现实背景。而龙则为幻想中的神异动物,它“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38](P245)。人们将其图像绘制到衣物上,借助其凶猛、奇异的特性而潜水入渊,巫术之义十分明显。可见,“鸟工”“龙工”的形成既有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又有宗教巫术因素,可谓是集真实与虚幻于一体。
三、“鸟工”“龙工”的图像认知与“形名”属性
鸟、龙分别赋予舜善飞、潜游的巫术特性,“鸟工”“龙工”为其巫术特质的物态呈现形式,这可从图像学与“形名”传统进行阐释。
(一)鸟、龙图像的驱邪求福之效能
先民通过佩戴鸟兽羽皮或器官而使自己获取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对于体格较为笨硕或迅猛不易控制的动物,现实生活中不能也无法靠近并佩戴其毛羽或器官。于是,古人就佩戴它们的画像以获取其威力,这在中外典籍中均有记载。例如,印第安、中非、罗安哥、巴西的波罗罗人重视肖像,认为“肖像能够占有原型的地位并占有它的属性”,“图像与被画的、和它相像的、被它代理了的存在物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也能赐福或降祸”[28](P43-46)。又如,传说大禹通过“铸鼎象物”而“使民知神奸”。上古先民将天狗的图像、鸓的图像佩在身上,挂在家门口或村落入口处作为御凶、避火、驱灾的咒符。时至今日,人们仍用雕有神祇图像的木刻、图片驱灾辟邪,图像的威力仍在彰显。
古人认为自己的肖像或动物的图像具有超常的威力,其原因有二:首先,交感巫术原理。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提出“交感巫术”,认为在曾经模仿或触染的情况下,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均能在心灵感应的原则下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而相互作用,以“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以太’把一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39](P27)。“鸟谓习飞鸟之巧,龙谓知水泉脉理”[40](P466),人们认为佩戴饰有鸟、龙图案的衣物,就能具备善飞或知晓水性的能力。其次,图像能产生视觉冲击力,具有先入为主的特质,被广泛应用于宗教仪式中。人们感知能力的获得,大多归功于五官,其中视觉占据重要地位。生理学研究表明,受到外界刺激时,人类的视觉神经细胞远比听觉神经细胞反应快[41],所以古代常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图像禳祸祈福、讽喻劝谏。绘有“鸟工”“龙工”图案的服饰利于沟通人神,虞舜借助它们能“感染”鸟、龙之威力,以达到飞廪、潜水而逃避灾难的目的。至于后世将鸟兽图像绘制于衣服上以表达不同的身份与地位,则由巫术转向了礼制文化。(2)如古代皇帝绣有龙形图案的龙袍、明清官服胸前或后背所织缀的绘有鸟兽图案的“补子”均属此类。它们既是对周代礼制的继承与发展,亦可看作是鸟工、龙工的孑遗。
(二)“鸟工”“龙工”的“形名”属性
早期先民给事物命名的方式有三种:以形命名(形名)、以声命名(声名)和以味命名(味名)[42]。其中,“鸟工”“龙工”属于形名的范畴,该方式主要通过描摹事物的体貌特征而定“名”,大致分为三类:其一,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进行笼统地描摹、命名,如羽民国、贯匈国、岐舌国、三首国、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一目国、大人国等。其二,描摹个体的局部体貌而形成摹态词,如委蛇、匍匐、凿齿、黄耇、台背、侏儒等。其三,依据个体的衣着佩饰及其图像而进行命名,如鸟工、龙工、大衣哥、草帽姐等。其中,第一类多用于早期族群部落的命名,第二类多“抓住人体某一特点,进行简单化、脸皮化的描绘”而形成一个固定的范式[43],第三类多依据外在的、附加的物件而命名。这些命名倚重外在的形貌特质。而早期先民只能对目见的人与事作外在的、表层的识别,认为事物的形貌往往代表了事物本身、本质(实),“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44](P114)。于是他们将事物的外在形貌作为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重要属性,即“名者,所以别同异”[26](P660)。这样,外在的“形”转化为通用的“名”,事物的名称则是形貌的体现,故而“形”的凸显遂成为中国早期思想史的重要特征[42]。反之,我们能以“形”观实(本质)、“以名举实”[26](P451)。因此,原本由“形”承载的“实”也被转移到“名”中,“名”成为连接“形”“实”之间的桥梁,通过事物的名称可以反推其形貌与本质。所以,我们可借“鸟工”“龙工”之“名”推测其绘制鸟、龙图像之“形”,窥见其巫术、法器之“实”。
“工”本为衣物,亦具有巫术性质。《说文解字·工部》:“工,巧饰也。……与巫同意。”[38](P100)《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与工同意。”[38](P100)工、巫互训,白川静认为“工”为咒具,“巫”像两手持其咒具之形[45](P505-507)。吉映澄亦从字形上寻求二者的关联,认为“巫工同意”“不仅仅只是同‘工’之本意,而是从字形扩展开来,借工之字形会巫之字义”[46]。可见,工、巫之义密切关联,“龙工”“鸟工”包含巫术意蕴。“鸟”“龙”为名、为形,而将衣物制成鸟形龙状自然是不合理的,只能在衣物上绘制鸟、龙图案,并以此命名为“鸟工”“龙工”。可见,“鸟工”“龙工”属于形名之范畴,它们体现了形、名、实的统一。
四、余论
理清“鸟工”“龙工”的释义,对于正确诠释“二妃助逃”乃至虞舜神话均有重要意义,亦能纠正当下工具书中相关义项的偏颇。
第一,纾解虞舜所面临的“人伦困局”。后世在阐释先前典籍时,亦会留有缺憾或不足。《尚书·尧典》概述父亲瞽瞍愚蠢固执、母亲刻薄荒谬与弟弟象傲慢骄横,但虞舜却能依靠美行孝德与他们和谐相处。《孟子》在宣扬虞舜圣主形象的同时,更注重其孝道的一面,通过极力宣传其孝行、孝迹,以期将舜当作孝治的典范[47]。为彰表虞舜的孝道,《孟子·万章下》增设“完廪、焚廪”“浚井、掩之”等情节,并将家庭成员的邪恶、凶残本性具体化[48](P5947),这表明《孟子》在诠释此事件时注重文本分析与自身视角的“视域融合”。然而,该诠释范式也留下了两大缺憾:一是未能指明“掩井”的主体与虞舜逃生的细节,即对施害者的参与度和受害者的逃生过程,尤其是后者语焉不详,这为后世留下充裕的阐释空间而致使异说纷呈。二是构设了虞舜的“人伦困局”。对于前者,笔者已有专文论析[1],此处重点分析《孟子》所构设的“人伦困局”。古人强调“敬父母之遗体,故跬步未敢忘其亲”[49](P79),用“三不”——不登高、不履危、不临深约束孝子的日常居处与行事。众所周知,“完廪”要登高,“浚井”则“临深”,它们已将舜陷于进退维谷之境,做则违礼,“危父母”而不孝(3)《孟子·离娄下》载“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此将“危父母”视为不孝之一。,不做则不顺从父母,亦是不孝(4)儒家将顺从父母纳入孝道的范畴,如《论语·为政》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里仁》载事父母“敬不违,劳而不怨”。。也就是说,《孟子》所构设的完廪与浚井情节,已使虞舜面临人伦困局——做与不做均为不孝,而“鸟工”“龙工”的植入则巧妙地纾解了这一困局,使舜依靠己力能飞下、潜出,摆脱窘境。
第二,赋予“二妃助逃”以神话色彩,促使该故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传承的延续性。《列女传》为彰表二妃的智德而弱化其神性,完成了从对她们的神性书写到智德颂扬的转变[1]。然而,智德颂扬偏重伦理说教,这一方面违背了虞舜逃生传说的神话特征,另一方面与世人的猎奇心理不符。而“鸟工”“龙工”的植入,则赋予“二妃助逃”文本系统以神话色彩,既能使其向神话归复,亦能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从而促使该故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传承的延续性。同时,“鸟工”“龙工”对后世典籍中虞舜逃生传说情节的生成,如敦煌变文《舜子变》帝释变作黄龙,“引舜通穴往东家井出”[50](P131-133)等,当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纠正词典中相关义项的偏颇。《汉语大词典·鸟部》将“鸟工”释为“有如鸟飞的本领”[9](P1031),《汉语大词典·龙部》将 “龙工(衣)”释为“古代疏浚河流时穿着的工作服”[9](P1460),并引《列女传》《宋书》加以说明。总体来看,《汉语大词典》的“鸟工”义项较为虚幻,“龙工”义项则过于现实,它们皆有一定的偏颇,均未能指出“鸟工”“龙工”的真正含义。而我们通过考证“鸟工”“龙工”,能兼顾神话的虚实相合之特质,从而纠正相关释义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