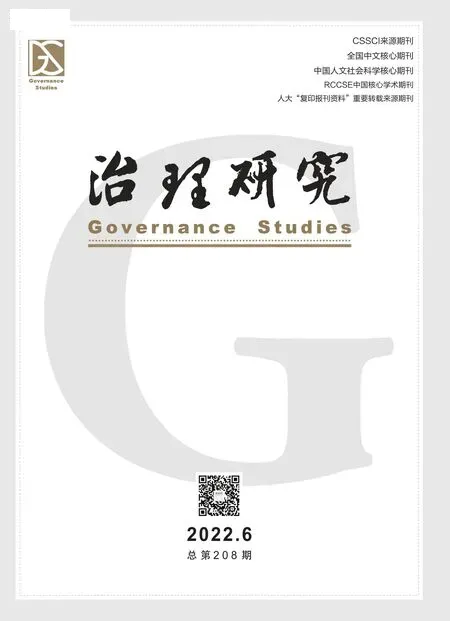重新理解贡献:共同富裕的一个伦理前提
□ 谭安奎
作为一个战略目标的共同富裕,体现的是一种政治、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具体内容固然没有,也不需要有绝对的明晰性,但确定无疑的是,它是普遍满足基本需要、摆脱绝对贫困之后的一个更高阶段。相对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共同富裕的理想不仅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还包括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而且这些提升是包容性的,它原则上要覆盖每一个人。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一个极具伦理吸引力,同时又可能包含诸多争议的理论主题。需要(need)一般都被认为具有客观性,因为它与主体的意向性无关。相应地,让每一个人满足基本需要、摆脱绝对贫困,就不应当成为道德争议的对象。因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所引起的痛苦应当优先解决,而且应当在不虑及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对生活水平进行人际比较,甚至也不必考量相关个人的责任或贡献的情况下予以克服。换言之,“我们对饥饿、贫困、苦难的关切,而不是对平等的关切,让我们赋予它们以优先性”。(1)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40.
然而,一旦超出这个层次,转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就会进入到聚讼纷纭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领域。在这个领域,除了从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权出发拒绝以整体之名推行“分配”正义或追求“社会”正义的主张,(2)关于从概念上对“分配”正义与“社会”正义的拒斥,可分别参见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4, pp.149-50;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种种争议或质疑往往可以聚焦到一个关键概念——贡献。在分配正义领域,我们似乎绕不开一个前提性的问题:谁,做出了什么贡献,从而应得何种回报?在这里,“应得”的含义是较为宽泛的,它既可以指一个人基于制度或规则可以期望获得的份额,也可以指一个人基于前制度的伦理特征而配得到的东西。如果每个人的贡献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贡献的差别不仅仅是多和少的问题,甚至可能是有和无的问题,那么,凭什么要推行共同富裕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是共同富裕的政治伦理前提之一。
一、生产性贡献的意义与局限
其实,即便是在与分配正义相关联的意义上,对贡献的强调或敏感都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当人们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强调贡献的时候,贡献的含义似乎又很快集中在特定的焦点上,那就是生产性贡献。这种贡献观念在起点上构成了现代社会推进公平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一个障碍。
(一)生产性贡献标准的凸显及其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挑战
分配正义的概念固然古已有之,但在古典时代,它所关注的焦点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政治职位,还有荣誉。在全社会范围内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使社会达到某种“正义的”状态,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久远的传统。严格说来,对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分配正义的系统性理论构造,其实是一个当代问题。在西方,古典政治理论着重关注的是严格的公民身份问题,而要拥有真正的公民身份,往往是以拥有财产为前提的。在西方古典的混合政体传统中,人们因其身份(自由民、贵族、平民等)或德性而配享特定的政治权力,甚至财富的多寡本身也可以构成人们在权力结构中占据相应位置的依据。在这里,财富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并未成为伦理上的焦点问题,更不是构想社会目标的核心要素。
走出身份等级社会之后,正义的含义则主要指向个人行为方面的规则,尤其是尊重他人自由和财产权,以及不违背契约以保持忠信之德,等等。用斯密的话来说,正义是很消极的一种美德,“一个仅仅不去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的人,确实只具有一丁点实际优点。然而,他却履行了特别称为正义的全部法规,并做到了地位同他相等的人们可能适当地强迫他去做,或者他们因为他不去做而可能给予惩罚的一切事情。我们经常可以通过静坐不动和无所事事的方法来遵守有关正义的全部法规”。(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0-101页。这其实正是梅因所谓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的一个结果。我们要问的是,这似乎是一种仅仅适用于民事、经济领域的正义观念,它能够涵盖我们对于正义的全部想象吗?难道政治共同体就不能更进一步,迈向某种形式的平等分配吗?
在个人主义的平等时代,如果试图超出上述消极的正义观而采取某种形式的平等分配,除了自由和财产权的约束,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最直接的挑战,就是被要求去澄清人们在财富生产过程中分别作出了何种贡献。也就是说,贡献,尤其是生产性贡献,将成为一个伦理焦点。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基础从身份转向契约之后,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原则主要也是从契约的角度展开的。诚然,似乎没有什么社会契约论以直白的方式强调订约方要作出生产性贡献。但正如森(Amartya Sen)所说,一种社会契约“在基本的意义上乃是一种关于相互获益之合作的设计”。(4)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38.这种相互获益,在最消极的意义上,当然就是安全、自由和互不伤害。如果要迈向更积极的方向,参与相互获益的合作就必须以作出生产性贡献的能力为前提。否则,我们如何能够确保这种合作是“相互”获益的呢?种种社会契约论往往是以隐晦的方式来表达生产性贡献的相关能力条件的,而这恰恰就隐含在它们对订约主体看似稀松平常的假定之中。在社会契约论中,订约方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能力正常的人,而且是正常的成年人。这意味着,能力超常或低于正常状态的人,包括处于婴幼、衰老阶段的人,似乎在契约论的基本框架中没有得到严肃对待。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因此敏锐地指出,契约理论没有为那些“在其生产性贡献方面与其他人明显不平等”的人留下空间。(5)Martha C.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3.我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许多能力低于正常水平的人,例如存在种种能力缺陷(disabilities)的人在何种意义上遭到了排斥。其实,基于同样的逻辑,那些能力超强的人接受这一合作体系的动力也是一个问题。
一旦把生产性贡献作为潜在的核心标准,再加上个人自由与私人财产权的刚性约束,平等分配或共同富裕的目标所面对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对社会经济平等诉求的一个长期流行的批判就是,它从根本上缺乏可靠的理由,而是基于某些情感的表达,例如忌妒。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社会早就开始以法律的形式去满足人们的社会经济要求,这就是韦伯所谓的“社会法”。而在韦伯看来,“社会法”要建立在“正义”或“人的尊严”这类“带有情感色彩的伦理假定”之上,因为它们声称的实质正义,偏离了形式上的合法律性这一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要求。(6)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II,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886. 中译本可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022-1023页。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虽然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已经被写进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该人权文件,以及它所倡导的那些权利,一直是国际上意识形态纷争的渊薮。美国就没有签署这一公约。相应地,究竟是否存在社会经济权利意义上的普遍人权,在哲学上也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状况与民事、政治权利方面的哲学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有人就此给出了一个判断:“社会经济人权仍然活在民事与政治人权的阴影下。”(7)Regina Kreide, “Neglected Injustice: Poverty as a Violation of Social Autonomy”,in Thomas Pogge ed., Freedom from Poverty as a Human 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8.那么,我们是该抛开“带有情感色彩的伦理假定”,还是放弃生产性贡献、互惠互利原则在政治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呢?这似乎成了一个让人左右为难的选择题。
(二)基于市场价值的生产性贡献测量:技术与伦理问题
在现实中,对人们生产性贡献的评价所依据的首先是市场价值,而且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市场价值是其应得的回报。对此,有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是技术性的,即市场价值作为一种尺度,是否能够真实可靠地衡量人们的生产性贡献?第二个是伦理上的,亦即,这种市场价值是做出生产性贡献的人所应得的吗?如果我们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们就会认为基于生产性贡献和市场价值的分配是正义的。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简要的分析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从技术上看,市场价值对生产性贡献的评价同时存在高估与低估的可能。我们不妨以现代社会最为重视的技术创新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因为它无疑是生产性贡献的“硬核”指标。纵观历史,技术创新一直都有,区别在于它们能否得到扩散和推广,从而转化为生产力。这一点受制于大量的非技术因素,包括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对统治精英获取财富的方式带来的冲击,以及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权力竞争的影响等。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足以证明,“仅靠具有技术创造力的人显然不足以构成经济进步的充分条件”。(8)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技术陷阱》,贺笑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版,第93页。此外,创新扩散的权威研究也表明,“创新的扩散本质就是人们对新事物主观评价的交互的社会历程。创新的意义会渐渐在社会发展历程的框架下体现出来”。(9)E. 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五版)》“前言”,唐兴通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IX。因此,我们无法单单从新技术与创新者自身出发来解释创新的社会经济价值。如果这样做,我们有可能高估了他们的贡献,因为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许多其他人(包括大量的前人)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可能低估了他们的贡献,因为在他们推出有重要价值的创新之时,甚至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其价值完全可能没有得到他人以及市场的认可。市场价值给出的评价,往往面向与最终产品直接关联的生产者,而且限于当下的、即时性的判断,这对于评判生产性贡献而言明显是不可靠的。
当然,从理论上讲,有人似乎还可以说,用市场认可的价值作为标准,这是生产性贡献的定义问题——就算某个人其实做了更多或更少,但它们与生产性贡献无关。但这就把我们带向了伦理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定义上就确定由市场价值来评定生产性贡献,这本身似乎无关伦理或正义。但生产性贡献作为一种现代观念的决定性意义恰恰在于,做出生产性贡献的人应当得到充分、恰当的回报,市场价值就是实现这一伦理目标的机制。换言之,是生产性贡献决定了市场价值。此时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循环:从定义上看,我们从市场价值中才能确定生产性贡献的大小;从伦理上看,恰恰是生产性贡献应当决定市场价值——但上文的分析表明,市场价值却总是偏离生产性贡献。这似乎可以说明,由市场价值所标示的生产性贡献在测量方面并不准确,而它的伦理意义也无法实现自我确证。(10)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生产性贡献甚少甚至完全没有伦理意义。参见Frank H. Knight, “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7, No. 4 (Aug., 1923), p.596.
二、从市场逻辑到社会想象:思考贡献与共同富裕问题的前置性框架
以上分析表明,即便是要强调生产性贡献,我们也不能把市场作为可靠的指示器,它需要超出市场与市场价值的考虑。至于在生产性贡献之外,还有无其他具有重要伦理意义的贡献并要求得到相应形式的承认和回报,那就更不能依靠市场体系本身来回答了。然而,从身份转向契约之后,市场的伦理正当性常常被视为自然的,与之相关的自发性想象也强化了市场逻辑的直觉性力量。因此,我们要提出市场体系之外的价值参照系,首先就要反思对于市场的自发性和自然性假设。
(一)市场的非自然性及其对社会的嵌入
对市场的自然性与自发性的反思,可以从历史和哲学两个维度展开。从历史的角度看,市场以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常常受到国家、政府所提供的动力的支持,这一过程包含着大量的集中组织和干预。贸易、市场的扩张与国家权力的相伴相随甚至互为因果,在经济史研究中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在此不需要详细讨论。但是,市场并不是自然或自发形成的,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这一点具有规范性的意涵。它至少意味着,即便选择了市场,对市场是否进行某种干预,对市场结果是否进行某种调节,在道德上也应该留有开放的空间。换言之,干预或调节与否,同样都需要辩护。内格尔(Thomas Nagel)在讨论市场结果的道德性质时提出,“在决定只坚持使得这一体制得以可能的那些权利时,国家做出了选择,而如果存在可行的其他选择,那么它就是选择了以牺牲较少生产能力者来奖赏较多生产能力者(及其后嗣)的安排。这不是说较少生产能力者被剥夺了他们劳动的部分价值,而是说他们被剥夺了他们在另一替代性安排之下本来能够拥有的东西。国家,因此还有其公民,应当对这一结果负责”。(11)Thomas Nagel,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00-101.内格尔的这个结论或许太强了一点,因为任何一种安排都会对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影响,但在什么意义上这里存在“牺牲”或“剥夺”,却不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相对温和也更可靠的结论应该是,对市场结果的调整并不必然是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而这就意味着,基于市场价值的生产性贡献并不必然是决定分配结果的唯一重要因素。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需要也不应该预设一种纯粹由市场或市场价值观来支配的社会安排。事实上,就连生产性贡献与市场价值之间的伦理关联性,也无法在市场体制之下确立起来。因此,要更好地讨论贡献与回报,以及相应的正义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更深的、背景性的框架,它应该是一个让市场与市场价值观受到约束的社会框架。用一个流行的概念来讲,市场、经济应该“嵌入”在社会之中。波兰尼(Karl Polanyi)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嵌入关系提供了或许是最具刺激性的对照说明。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经济都是浸没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但“一战”前约一个世纪自发调节市场的高歌猛进,试图把一切都商品化,它其实在塑造一种“市场社会”图景。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在这里,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因素对社会存续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结果。……这正是人们熟知的那个论断的意涵: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12)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58页。值得注意的是,波兰尼认为对“市场社会”的追求虽然带来了极大破坏,但它只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乌托邦。对市场社会的追求,实质上是一种让市场反噬社会的冲动,因为它不但试图让经济从社会中脱嵌,而且试图让整个社会系统依照市场和全面商品化的逻辑来运转。在波兰尼之后,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回溯到早期现代。他认为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契约论背后隐含着一种特殊的社会模式,即“占有性市场社会”。该社会模式不仅有产品市场,人的劳动力也成了商品,而不再是其人格的构成性部分;进而,市场关系影响和渗透到所有社会关系当中。(13)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48.
波兰尼对市场社会的批判,背后关联着一种悠久的经济(学)传统,那就是道德经济(学)。波兰尼本人也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道德经济学家之一。但道德经济学虽然源远流长,它却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理论范式,而只是一个松散的理论家族。它当然强调伦理对经济的根本性约束,有时候也特别突出对边缘群体生存处境及其行为逻辑的关注。但用波兰尼式的表达来说,道德经济学确实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那就是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想象为优先考虑,强调经济嵌入在社会之中,因此特别注重对社会的维护。有研究者指出,对20世纪的道德经济学家们来说,“道德沦亡的场面已经被对社会崩溃的恐惧所代替”。(14)蒂姆·罗根:《道德经济学家》,成广元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其实,把经济置于社会之中,而不是将其作为独立的(遑论统摄性的)领域,这本身就是道德经济学的隐性传统,只不过,市场社会的乌托邦追求给社会本身带来了空前危机,从而激发了批评者对“经济嵌入社会”的明确表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道德经济学事先预设了一个“社会”框架,但对于社会本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则因理论取向和时代而异。这是其作为一个松散理论家族而存在的根源所在。
(二)贡献与正义背后的前置性“社会”框架
上述讨论与本文所关注的贡献、共同富裕问题有何关联呢?如果有一种经济嵌入其中的先在的社会框架,那么,分配正义乃至共同富裕也好,对贡献的衡量也罢,至少其中部分的工作应该在市场机制之前就得以完成,因为它们是该社会框架本身的要求。换言之,相对于我们通常理解的分配正义,在道德经济学的视野中,正义问题的场域其实部分地应当被前置,而不是等待生产过程之后的市场评定,乃至市场评定之后的再调整。相应地,道德经济学的思维也就不是对生产性贡献及市场回报机制的直接认定。这种把正义问题前置的思路,与西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存在极为关键的区别,因为后者的主要思路,正是对收入进行事后的再调节而已。这种事后的调整,也就一直无法摆脱市场信条的强烈质疑。
前置性的思路意味着我们要从简单的再分配或调节性的资源配置,转向动态地维护一个社会框架本身。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本身成了我们责任的对象。这个说法当然会引起质疑,因为在现代语境下,我们讲权利和责任,其主体首先都是指向明确的个人。它还会引发担忧,因为把社会作为责任的对象,似乎是含糊不清的,因此会成为个人自由的对立面。但对风险的担忧并不总是构成我们拒绝一件事情的充分理由。事实上,优先考虑社会框架,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是我们日常思维的一部分。例如,当我们说“社会责任”的时候,我们当然不是指社会在承担责任,而是指人们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这一点在有的国家已经体现为法律实践。例如,埃尔斯特(Jon Elster)就曾提到过这种情况。(15)关于这种情况的讨论,参见Jon Elster, “Is There (or Should There Be) a Right to Work?” in Amy Gutmann ed.,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56.在有些国家,法律上明确规定公司有责任给残障人士配置一定比例的工作岗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一家公司没有给某一位特定的残疾人提供工作(即便这家公司确实也没有完成法律规定的比例),这位残疾人就可以起诉这家公司。但与此同时,公司可能因为没有完成指标而遭到国家处罚。任何一位残障人士都不能因此起诉这家公司,这说明,虽然公司承担着特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的对象却不是具体的个人。我们不能以残障人士享有工作的权利为由,支持特定的维权行为。那么,没有明确的权利主体,这种责任是对谁的责任呢?埃尔斯特转引社会理论家马歇尔(T. H. Marshall)曾经引用过的对于英国济贫法的一个评论来说明这个问题: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帮助穷人的责任是“对公众所负的责任,而非对穷人本身所负的责任”。(16)这是Ivor Jennings的评论,可参见T. H. Marshall, The Right to Welfare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Heinemann, 1981, p.84. 此外,David Lyons也曾分析指出,有时候,一些法律上被要求或被禁止的行为,作为责任或义务,它们并不是“负于”任何特殊个人的责任或义务,此时我们也不能从存在这类责任或义务这一事实出发推导出权利(参见David Lyons, “Rights, Claimants, and Beneficiarie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6, No. 3 [Jul., 1969], p.174)。在这里,责任对象就被认为是集体化的公众。如果我们将“公众”换为“社会”,其中的道理并无二致。
经济学家奈特(Frank H. Knight)在反思生产性贡献与市场价值的关系时曾提出一个重要洞见:“社会政策必须建立在社会理想的基础之上。一个组织化的系统必须依据某种社会标准来运转。”(17)Frank H. Knight, “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7, No. 4 (Aug., 1923), p.580.他认为,该标准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构成社会的个体的价值观有关,但却不能与之完全相同,因为它预设了某种程序,以此将种种个人利益组织起来,在它们之间进行权衡,并对它们之间的冲突做出裁断。因此,强调这种标准是“社会”标准,就在于它不能还原为个人的价值标准,或者还原为个人价值观的聚合——就像理想的市场机制那样,而是源于一种独立的社会想象。所谓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借用泰勒(Charles Taylor)的说法,它指的是“人们想象其社会存在的方式,人们如何待人接物,人们通常能满足的期望,以及支撑着这些期望的更深层的规范观念和形象”。(18)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8页。与社会理论不同,它具有大众性,是普通人想象周遭环境的方式,为广大人群所共享,同时具有不确定性,难以用清晰的学理形式来表达。在泰勒看来,“社会想象是使得共同实践成为可能的共同认识或理解,是对正当性广为共享的感受”。(19)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97页。当然,谈论大众性的社会想象,仅仅是在关注社会得以有效运转的观念基础,并不自然卸下了我们探究社会理论的智识负担。
我们重新强调社会标准和社会想象,源于对市场反噬社会的担忧。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社会想象并不必然排斥市场本身,它只是强调市场和经济应当嵌入在社会中。它真正要拒斥的,乃是市场逻辑及其潜在的生产性贡献标准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支配。换言之,强调社会想象的优先性,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思考经济和市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历史学家麦克法兰(Alan McFarlane)认为,现代社会的非常之处在于它坚持领域分立的原则:“现代世界的本质是,不存在一个定义性的基座(defining infrastructure),所有的事物各自分立,不可能长久维持一个中央。……在现代世界,生活的四大领域——政治、宗教、经济、亲属关系——之间永远保持着建设性的张力,因此这里有不息的斗争,却无任何一个领域可以胜出。”(20)艾伦·麦克法伦:《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9页。他还把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描述概括为“一种有分寸的宗教,一种有节制的家庭,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一种有界限的经济”,(21)艾伦·麦克法伦:《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并认为正是这种多元性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动力。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针对现代社会提出了行政系统(亦即强制性国家权力)、公共领域、经济系统所构成的三元结构,其中,各个领域有自己的整合原则,它们分别是行政管理权、社会团结和金钱。问题只在于这三种资源之间要获得某种平衡,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整合之需。(22)Jürgen Habermas, “Three Normative Models of Democracy”,in Seyla Benhabib ed.,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8.但是,如何从一种多元聚合式的社会想象提升为一种整全性的社会理论,对于西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正当化来说是一个明显的理论挑战,对于较之更加突出前置性社会理想的共同富裕目标而言,就更是政治伦理的奠基性工作了。
三、共同资产与社会再生产:契合共同富裕的贡献评价维度
不直接或间接以个人的生产性贡献为决定性依据来设想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而是提出一个前置性的社会理想,是否意味着本文开头提出的贡献问题完全被消解了呢?接下来我将表明,这种前置性的社会理想不是要否定贡献的意义,而是要我们扩展对贡献的理解,而且这种对贡献的新理解,才是与公平分配的共同富裕目标相契合的。
(一)寻求不可还原为个人生产性贡献的“社会”资产
要维护一种先在的社会理想,包括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我们就必须确认,确实存在一些真正的“社会”资产或共同资产(common asset),它们构成了从伦理上讲可以合理进行分配的资源。说它们是“社会资产”或共同资产,核心之处在于强调它们不可还原为个人的生产性贡献或其他个人行为,包括这类贡献或行为的聚合。事实上,这就是要解决拟分配的资源的来路问题,以回应诺齐克(Robert Nozick)式的持有正义观念的挑战:“按照获取和转让正义的原则,如果一个人对其持有物拥有资格,那么他的持有就是正义的。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物的总体(分布)就是正义的。”(23)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4, p.153.言下之意,只要每一个人的持有物都有正当的来路,就不存在什么可用于分配的“社会”资产。唯有回应了这一挑战,我们才能真正确立所谓的社会本位,虽然它是一种有限度的社会本位——就像前置性的社会想象不必排斥市场一样,社会本位的思路也不必主张所有的资源都不可还原为个人的生产性贡献,它只需要确认存在一些这样的资源就足够了。如果社会财富全部能够予以个体化地还原,那我们原则上就应该依照还原的结果来调整现有的财产分布,而不是去追求某种前置性的社会理想。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其中确有不可还原的部分,这样的社会理想就有了可能,因为它表明确实存在独立的社会共同资产。如果能确认存在这样的共同资产,我们也许会对个人贡献的表现形式,以及相应的回报形式形成新的认知。
在财产权以及财富分配的问题上,对于源头的终极追问是探寻私人财产权得以形成之前的状态。几乎所有探究私人财产权之基础的早期现代理论家,都觉得有必要回溯式地探讨原始共有(common ownership)或联合所有(joint ownership)的状态,以便为私人财产权的正当性给出某种解释。原始共有指的是最初的无主共有状态,万物还没有具体的所有者,它们是有待占有的。联合所有,则是一种有了所有者的状态,即万物为人类集体所有。(24)对原始共有的假定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观念史上很常见,包括格劳秀斯、普芬道夫、洛克等都曾涉及这一议题。但有当代学者指出,联合所有这一可能性被忽视了。对此所做的代表性阐述可参见G. 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83-84.在政治哲学史上,思想家们试图为从原始共有或联合所有到私人财产权的过渡提供历史和规范意义上的说明。但这种转变所需要的条件设置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否遭到了违背或不可避免要被违反,这些问题的答案往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笔糊涂账。这就是为什么私人财产权在现代西方虽然被极端重视,但将其作为自然权利的主张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证明。在思想史上,“作为不同于公民社会中的法律权利的私有财产,它的地位从中世纪直到革命时代都被认为是可疑的,在最好情形下,也是不确定的”。(25)彼得·甘西:《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时代》,陈高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相应地,从将私人财产权神圣化到允许法律来调节财产权,这其中的理论鸿沟也一直没有得到真正克服。
考虑到历史与经验维度上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试图论证对于具体外物的私人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这本身也许就是一种理性的自负。同样,试图从财产的实际分布状况中回溯式地厘清个人的生产性贡献,也几乎是不可能的。(26)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是“对具体外物的私人财产权”。但财产权还可以像生命、自由权一样被解释为一种主体性权利,也就是主体的一种道德能力。例如,有人这样解释洛克式的自然财产权:“我们并非生而对某项具体的物品拥有权利,而是生而有一种能力对特定的物品形成财产权。”(参见A. John Simmons, The Lockean Theory of Righ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72.)此时,作为自然权利的私人财产权,仅仅是指个人获得具体财产权的权利,它是一种二阶权利,而不是一阶的、实质的、针对具体外物的财产权。为了寻求一种公平分配或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可行的办法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无论特定时刻财产的分布状况如何,我们不是要去甄别个人此前的生产性贡献,而是要问此时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成果是否包含着不可还原为个人生产性贡献的部分?
(二)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历时性共同体及其共同资产
谈到这一问题,我们会自然地想起罗尔斯一个饱受争议的主张,即人们天赋才能的分布应该被视为共同资产。罗尔斯后来专门澄清,天赋即便在道德上具有任意性,但如果它们有所有权问题,这种所有权仍然是归属于个人的,“被视为共同资产的是天赋的分布,而不是我们的天赋本身”。(27)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Erin Kelly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5.即便如此,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如下批评仍然富有见地:就算个体并不应得其天赋才能,我们也不能推导出世界上的所有人可以集体拥有它们。要做出这样的推论,似乎还需要某个前提条件。在桑德尔看来,把天赋才能当作共同资产,事实上预设了人们一开始就构成了一个相互亏欠、彼此担责的共同体。他据此认为,自由主义的愿景“并非道德上自足的,而是寄生于一种它公开拒斥的共同体观念之中”。(28)Michael J. Sandel, Public Philosophy: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68-169.虽然这个批评也是建立在把天赋才能视为共同资产的误解之上的,但它仍然值得特别认真对待。因为这个批评的逻辑更能证明如下道理:个体之间如果没有某种先在的伦理关系,例如,如果他们仅仅是根据生产性贡献的标准联结在一起的群体,天赋才能在他们当中的分布状况虽然是偶然的,但同时也应该被视为中性的东西,并任其发挥作用,而不是像罗尔斯那样将其视为共同资产。这再次说明,要迈向某种平等主义的社会,共同体的想象,或者本文所说的社会想象,应该是优先的。
但仅仅有这个批评却是不够的。因为对同一个时间点上的人们而言,说他们之间是相互担责的共同体,因此天赋才能的分布应该作为共同资产,这并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相反,在相互受益的意义上,拥有超强能力和正常能力的人选择不与存在能力缺陷、难以做出生产性贡献的人合作,这至少是一个理性的取向。此时,仅仅强调他们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可能被质疑为一种道德绑架。而在同一时间点或时间段上对人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横向思考,这恰恰构成了现代契约论的一般思考方式。罗尔斯确实在此问题上有非常深刻的推进,因为他把社会视为一个世代相续的公平合作体系,从而把历时性的纵向维度纳入到契约论的框架之中了。但即便在这种框架中,人们的伦理推理却仍然是横向的,也就是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找到无时间性的(timeless)原则。真正的历时性思考仅仅在于假定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世代,但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因为契约关系其实并不在代际之间展开。严格说来,它也不可能在代际之间展开,因为代际的概念仅仅在家庭中是明确的,或者还可以在社会学上找到它的规定性,但代际关系在政治上却从来无从真正得到确认。因为政治社会中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口降生或离世,这一不断变动的特点就决定了,试图用代际关系模式来思考政治问题,最多也就只有隐喻的价值。
因此,真正的共同体或社会想象,需要把真实的历时性维度考虑进来。所谓的社会共同资产,其实不是特定时间点上人们天赋才能的分布及其生产成果,而是历史积累下来的财富和资源中不可还原为个人生产性贡献的部分。事实上,前文谈到技术创新与扩散及其带来的经济效应,它一方面表明市场价值不是生产性贡献的可靠指针,同时也表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财富创造,实实在在是一个“社会”过程。对于任何一个特定时间点上的人们而言,他们都面对一种“社会遗产”。有人之所以持续倡导无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Universal Basic Income),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为基本收入融资所征的税,并不是对今天的生产者凭空创造的东西所征的税,而是这些生产者为个人利益使用我们集体所有物的特权所付的使用费”。(29)菲利普·范·帕里斯、杨尼克·范德波特:《全民基本收入》,成福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3页。这里所说的集体所有物,当然包括自然资源之类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历时积累而形成的财富、观念、制度、互动模式等。按照这一理解,我们所挣得的收入,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我们自己能力或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社会礼物”或“社会资产”。无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也被倡导者认为是对这种社会礼物的平等化处理。就共同富裕的目标而言,这种历时积累而成的社会资产,就构成了可供正当地予以分配的物质基础。
(三)社会再生产的视角:超越贡献评价的生产性维度
所谓的“社会礼物”,借鉴自法国经济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关于“礼物”的研究。他认为,礼物是经济史分析的真正起点,它是理解原始经济形态的钥匙。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给予、接受、回报这三种义务,“生活贯穿着一条兼容了由于义务或利益、出自慷慨或希图、用作挑战或抵押的送礼、收礼和还礼的持续之流”。(30)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理由》,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60页,关于给予、接受、回报三项核心义务的说明,可参见该书第82-92页。莫斯特别强调,所幸现代人并没有完全变成“经济人”的样子,礼物所代表的互动模式仍然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地回归。对本文的论题而言,莫斯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两点至关重要的启发。其一,社会礼物的形成及其分配含义,是在历时性的社会过程(所谓“持续之流”)中形成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当下的、特定时间点上的生产、分配或交换问题。相应地,鉴于动机的混合性,以及这种赠礼、还礼的跨时间性与持续性特征,个人的生产性贡献在其中至少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其二,礼物呈现的是一种独特的交换体系,其内容并不仅仅是有用之物,各方的动机也不是出于单纯的效用计算,而是包含大量情感的、没有薪酬的工作。这再次表明,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不可还原为市场价值的贡献,而且在该体系中得到了承认。这就表明,“社会礼物”的概念为我们打开了更广阔的衡量贡献的视野。
有一种权威的评论认为,上述第二个问题,可能是《礼物》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政治启发。因为“承认存在一种无薪酬的社会劳动,并且这种劳动是个体对集体的馈赠,有利于消除社会救助中经常发生的慈善的诱惑”,而对于被助者而言,唯有“社会身份”才能还给他们尊严。(31)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理由》,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24页。承认他们拥有这里所说的社会身份,就是承认他们是作出了社会贡献的人——即便这些贡献是非生产性的。在此情况下,他们得到社会资源,就不是源于他人的施舍。如果说社会救助可以这样来理解的话,共同富裕的社会想象就更离不开这样的贡献观念了。相反,如果总是片面地强调生产性能力或贡献,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思路:成功者因其天赋、努力而应得其财富、地位,失败者也必须把自己的糟糕处境归咎于自身。结果,“在成功者中,优绩至上催生了狂妄自大;在失败者中,优绩至上带来了屈辱和怨恨。这些道德情感位于反对精英的民粹主义暴动的核心”。(32)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曾纪茂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12页。这样的怨恨和屈辱,不完全是基于生活水平、收入状况的社会比较所产生的对于不平等的心理反应,而是根源于其社会贡献和社会身份的被遮蔽。这种遮蔽是狭隘的市场价值观和优绩主义必然导致的结果。当今世界民粹主义所引发的社会撕裂,促使我们基于更宽的价值光谱来理解贡献,而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当然也要以这样的反思为前提。
到此为止,我们提到了不可还原为个人贡献的社会共同资产的概念,以及不可还原为生产性贡献的社会贡献的概念,它们提供了比市场价值或单纯的经济领域丰富得多的“社会”想象的基础。而且,我们把这些要素放在历时性的框架中来理解。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所关注的就远不仅仅是物质生产,以及个人的生产性贡献,而是社会本身的不断再生产。我们不妨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家务,以及在家庭中对婴幼儿的抚养,它们是典型的非生产性贡献,通常未获得市场价值的认可。但是,这些工作无疑是社会不断再生产的条件。这不仅表现在孩子的生养为社会再生产提供了人口基础,更重要的是,家庭教育还是儿童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渠道,因此是社会伦理关系不断再生产的重要依托。在此意义上,在家务和子女抚养方面承担的工作,理应在一个恰当的社会想象中获得足够的承认。一如前述,这种更多的承认,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问题,也是社会身份和尊严等价值层面的问题。
四、结语
本文试图论证表明,生产性贡献和市场价值标准有其自身内在的局限。无论是对于理解贡献本身,还是为了促进公平分配或共同富裕,我们都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想象作为前置性框架。这种前置性的社会想象,蕴含着我们对贡献的新理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贡献的主体不仅是个人,因为相当一部分社会进步,包括物质财富,是不可还原为个人行为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因而构成了社会的共同资产。这里的重点在于不可还原,而不是实践中没有以历史追溯的形式进行个体化的还原。其二,贡献的性质不仅有生产性的,而且还有非生产性的,或者说社会性的内容,它们最典型地体现在为持续的社会再生产而作出的诸多未获得市场价值认可的工作之中。
不可还原为个人贡献的社会共同资产为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提供了具有伦理正当性的、可供分配的物质前提。而贡献的性质或类型的多元性,则意味着一个社会应该对人们的工作有多种不同维度的承认和回报。这些多维度的承认和回报让我们可以摆脱单向度的经济标准,为人的发展、人的良善生活提供更丰富、更全面的要素,并让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获得社会承认与尊严。对贡献和回报的这种新理解,似乎更符合共同富裕的本义,也是共同富裕这一社会理想的真正吸引力之所在。我们倾向于用“common prosperity for everyone”来翻译“人民共同富裕”,或许也能从这里找到一个理由,因为“prosperity”虽然有较强的经济、物质含义,但同时也指向要素更宽广、价值更厚重意义上的福祉(well-being)。反过来说,本文的讨论也想表明,如果没有某种共同富裕的理想,我们将生活在以单向度的生产性贡献为主导的、不平等的、傲慢与屈辱相对抗的、不断撕裂的社会中,而这种糟糕的前景甚至已然在西方民粹主义、身份政治的风潮中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