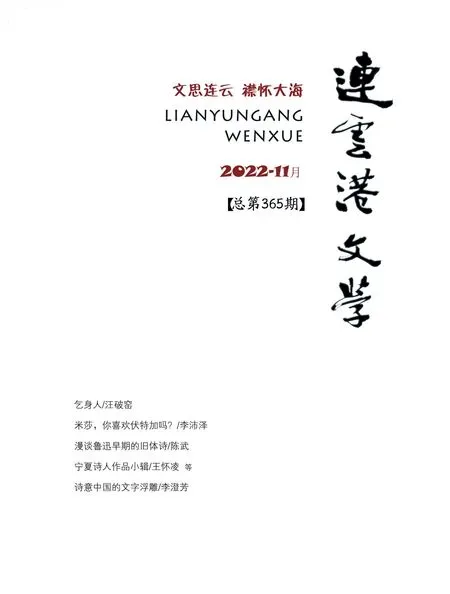莫问酒吧
顾拟
酒吧里流淌着酒和音乐。各种各样的酒色:红、黄、棕、深栗、灰青……以及呈不明色的液体,统统在透明的玻璃器皿里缓慢地流淌,抒情地流淌,又很快被按照某种固定的形状停顿,做潜伏状,凝滞不动。伴随着酒色,音乐也在流淌。音乐像绅士,像牧师,像良人;酒是浪子;音乐也像一服药,一味镇静剂,一双安抚之手让流浪的灵魂找到栖息之地。音乐和酒,一对灵魂的良人流浪在灯火辉煌的人间街头,相拥而泣:执子之手,此生契阔。
一般而言,酒吧会深陷于某段街巷深处。好比陷落于城市心脏或者纠缠于喉管的某个细小结节,于某段神经末梢突兀又隐秘,模糊又清晰,必须借助医学器械般精准的探知才能熟门熟路,才能摸得清来龙去脉。我事先查地图,又打电话问清具体方位,因此我比自己预料的提早半小时准确抵达:莫问酒吧。
有时候,我们就像一只只弱小到不能再弱小的动物,凭着一股近于虚无的力量,在密如蛛网的城市街巷中冲突,去往一个极易迷路、急需借助手机定位才能找到的地址。有时候,机器导航又会把你骗得晕头转向,于是你常常茫然无措地站立在十字路口,面对着城市永远修不完的马路旁堆积如山的障碍物和弥漫着尘土的人流,苦苦寻找因流浪太久急需宣泄的突破口,而这时候——酒吧这类场所也许可以准确地接纳你,卸下疲倦,让你经过一段漫长的跋涉后终于抵达——一个假想中的驿站。
莫问酒吧倚靠在街头的转角处。这名字听着有点范,依着旁边就是有名气的大酒店,所以连带似乎它也有着某种高档身份。酒吧很小,全名应该叫“莫问音乐酒吧”。有音乐指路,“小资”的身份就变得确凿无疑。骨子里仍是风尘的,媚俗的,所以大家还是习惯称它“莫问酒吧”。
情绪在音乐和酒的旋转中持续发酵,耳畔承载着各种液体在玻璃器皿中的碰撞,燃烧和倾诉,简洁而直接:
“莫问!莫问!一杯敬昨天,一杯敬明天。让我们活在当下!”
她看见我走进去,站起身来迎接。我以为她是侍者,本能地缩紧了感知的触角。可她放射出更多的热情,近似于张开双臂样想要拥抱我,于是我像一块坚冰被慢慢融化。彩色闪光灯下,照着她娇小玲珑的身材,一件紫色的休闲卫衣和及膝的棕色毛呢窄裙裹紧了身段,脚上蹬着一双平跟黑皮鞋。最惹眼的是,耳垂处两个状如扁平电视发射塔模型的耳坠正不停地晃动着,造型别致,仿佛两条活泼的鱼儿在游动。微笑和热情,也许对她来说是一种职业习惯,于我却是一份别样的温暖感受。
这个冬天,城市街头暧昧的霓虹闪烁着越来越浑浊的、貌似暖色调的城市表情,而寒意已悄然逼近人们的心脏。平素不习惯化妆的我,出门时穿了一件黑色的风衣外加一条酒红色薄呢围巾厚实地裹住了脖子。据精准的医疗器械说,我的脖子里长出了类似于结节的不明状物,这是近年医学上的常见病,多发症,对此医生们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或者等它长到一定程度,就动手术。好比干掉一个身份不明的敌人,我开始想象冰冷的手术刀划开皮肤时,“嘶嘶嘶”的喘息声如蛇信子在游弋和吞噬。不明状物貌似拥堵着我的神经和呼吸,可事实上我是无感的。白天,那个医术高超的主任医师说,别瞎说,连我们医生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得此病。难道和空气、水以及饮食有关?我问。应该说,和这些没有太大关系,不要太紧张,密切随访。字斟句酌。他说这些时面无表情,一边给我写病历书。他戴着厚厚度数的眼镜,且已过了退休年纪,也许他太疲乏了,以至于把眼睛凑得几乎趴在桌子上。看哪!他无奈地瞥一眼人群,后面黑压压排着队的患者们情绪复杂,脸上的表情更复杂,那些汹涌的情绪正被极力克制着,空气中充满着愤懑、委屈、忍耐和焦虑的力量,仿佛一条条可怜的鱼被搁浅在海滩,正无辜地翕动着呼吸的鼻翼。
当我走出医院时,又回头看了一眼高远的天空。
酒红色的围巾成了这个季节我脖子里的最爱。温暖绵厚地保护着神经和呼吸器官,给予我暂时的稳妥。我护紧围巾,按照她指示的方向走进酒吧。人声嘈杂,音乐喧闹。耳膜立刻被巨大的声浪重重冲击,无可懈怠。好像一条别着“温暖牌”标记的鱼,我快速地滑进汹涌的人群里。我开始流泪。肆无忌惮。脖子里的不明状物突然变得突兀而真实,此刻似乎在阻滞我的呼吸,但我还是奋力挣脱着这种蛮荒。我用力地游,随着涌动的波涛潜游,又探知到另外的无数条鱼,他们跟我一样有着各种疼痛,随波逐流又抵抗着生活固有的惯性和阻力,似乎每条鱼都游得气喘吁吁和小心翼翼,似乎每条鱼都竭尽全力地在深海里艰难地潜游,不放弃作千万次腾挪迂回、曲折前行的努力,最后试图找到一处足以立脚的小小礁石放稳人生的吉光片羽,以此作永远的栖息。迷失和暧昧,是酒吧的气氛。闪烁的灯光,隐约的人语。挣扎和呼喊,仿佛心中的向往:前进,前进!请指引我,朝着幽暗生活中的永恒光明,永无止境。
吧台旁有一块电子屏幕正滚动着炫目的音乐背景画面,伴着乐声,图片张张徐徐地摊开,又重重繁复地卷叠,卷叠又摊开,摊开又卷叠,海滩上的浪头一个个翻卷上来腾起一波波无穷无尽的泡沫,转眼间又消失了,海滩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然后继续重复之前的画面,无休无止。彩色泳衣的女人在沙滩上疯狂地扭动、尖叫、逐浪,烈焰红唇,像一尾尾彩色的鱼在摇晃、挑逗、喧哗、妩媚。这样的氛围,一切恰好。我的泪又开始拼命地流,目中无人。西北角落有个小舞台。暖色筒灯打在舞台上,一个清瘦的男孩坐在高脚凳上清唱,光柱正好泻到他的脸上,把他的眼睛照亮了。清冷而忧伤的曲风,类似李健的风格但比之少了些许清新,多了些落寞。听着这样的歌声,我渐渐从刚才的那个位置起身,走向离舞台最远的角落。
现在,我在一张长条黑皮圈椅里坐下来。犹如找到了停靠的礁石,温暖从皮椅的深处传导过来,我的整个身子陷于一种舒服的虚无感。喜欢这样的角落,喜欢这样给人安全感的地方,哪怕伤感也是舒服的。刚才的那个桌子一圈围着七八个人,两个男人外其余都是女人。高矮胖瘦,老少皆有。又胖又老的那个男人正和旁边的年轻女孩玩牌,兴致高涨,他们在玩那种类似于掷骰子的游戏,先用一个小盅猛烈摇晃然后朝桌上突然一扣,啪!迅速拿起小盅,谁的骰子点数大谁就赢。输的被罚酒,赢的拍手喊叫。女孩在笑,男人兴奋地附和着“嘿嘿嘿”的笑声显出像湿柴燃烧的困涩感,虚无以及短促。余下的兴致勃勃地观看,意犹未尽。看最年少的一个男人,顶多二十出头,脸型清瘦,他竟然殷勤地站起身示意我落座。我想拒绝但来不及,一时找不到措辞,坐下一分钟,却如坐针毡。立刻逃离。
逃离。爱丽丝·门罗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逃离》。生活时刻在发生逃离事件,书的封面印着这样一句话:逃离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就像看戏路上放松的脚步,就像午后窗边怅然的向往。
此时此刻我逃离的理由是什么?人跟人之间必须讲究气场,我和那个桌子之间明显气场不和,感觉缺氧般浑身难受呼吸困难所以只得逃离。而在生活中,更多的只是一次次逃离的闪念,那种念头无须预知,无从招架,亦往往遁形于刹那。或许我们早已被这些念头悄然逆转,或许这些念头早已将我们决绝遗忘。
当我成功逃离那个桌子,仍旧感受到从不远处传导过来的阵阵令人不安的悸动。若隐若现。传入耳朵中,有什么东西从心底流出。音乐?情绪?又像马路上堆积着障碍物和弥漫着尘土的阻滞,生活正在宣泄某种隐秘的痛感。
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对高脚玻璃杯、一瓶成色不错的红酒、水果瓜子盘碟。现在,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安全,身体呈现虚无的轻飘感以至于有点儿陶醉状,熏熏然。我忘了先前的窘迫,忘了脖子里的不明障碍物,想要跟着音乐像条鱼儿样畅快地游动,放声歌唱。可我的身体仍旧被阻滞在原地,发不出半点声音。台上换成一个女歌手,声音更加空灵。这是一首非常陌生的老歌,好像从没听过但又觉得如此耳熟能详。
一位三十出头的男人朝我这走来。他径直穿过人群,在我对面的高脚凳上落座,然后跟我交谈起来。我这时知道他就是老板。他说话很温柔,脸上有两颗很明显的酒窝,带着谦逊的微笑。他的脸色很白皙,但身材看上去很健壮的样子。他想和我随意聊点什么,也是为了生意,盼着我以后能常来。可我告诉他,我不会喝酒。我更不能把眼前关于脖子的窘困告诉他,软弱像坚硬的盔甲把自我层层地保护起来,不留一点被击溃的余地。于是,我的眼泪莫名地宣泄而出,如溃败决堤的海洋。
为什么不喝点,他说。我摇头,感觉自己像极了一条窒息的鱼。顿了顿,他又补充一句:过了十一点,所有的酒水可以随便畅饮。他晃了晃手中的玻璃杯,朝我轻柔地微笑。洁净的玻璃器皿在发光,猩红的液体被转成一个个好看的漩涡,魅惑极了。他的话惊了我一跳,于是,我与他深邃的目光有刹那的碰触。电光火闪。我像是被别人捕捉到生命中某一刻所有的困顿和疲倦,显得惊慌失措。我摆弄着空杯子,无所事事。仿若鱼儿在拼命呼吸,但我分明是一个从窒息的梦中攀爬起来的人。他遗憾地离去。而台上的歌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换了一对男女。一男一女。他们端起高脚酒杯给客人敬酒,说了什么。我好像都听不见。我被人潮的喧嚣抛弃在一片荒芜的海滩,努力辨认自己的方向。最终,我醒悟过来,情节已到尾声了,我跟着大家端起酒杯朝空中默念:
“莫问!莫问!一杯敬昨天,一杯敬明天。让我们活在当下!”
话音未落,音乐再次爆响。鼓手猛烈地挥击槌子,清脆的器皿发出尖锐的嚣叫声。猛烈地锤击着耳膜,鼓声像流水样倾淌。音乐和酒,相生相吸,如一对矛盾体又无比妥帖地结合在一起。把音乐比作大海,酒是孤独的旅人。孤独在深不可测的波涛巨浪里跳舞,一波又一波,直到浪头把灵魂吞噬,留下肉体的尸首晾晒在沙滩;把音乐比作雕塑家手中锐利的刻刀,酒就是一尊沉思的艺术品,裸露人性的成色。酒吧混合着酒和音乐,性感的、魅惑的、迷人的、令人窒息又让人沉沦的、幡然醒悟又惊恐万状的人们一起摇摆,幻化成一条条迷离的鱼。海面旋起一股股黑色的飓风和紫色的波涛,暗涌风暴,潮涨潮落。
酒和人性,关系微妙。比如左手和右手。是一对孪生兄弟,当它们沉默地绞扭在一起就成了无意识的类似整体,十个手指所指向的力是离散的又是聚合的,于是那种力就具有所向披靡的魔法和坚不可摧的意志,美妙地指引着人生。在走向成功的路途中,酒是胜利欢呼的泪滴,是天使洒下的甘霖挥洒着人性。
音乐和酒,陪衬的关系。比如左耳和右耳。是人的一个器官的正反面,当风呼啸而至,双耳同时作用就像一面鼓发出明亮而厚重的回声,呼风唤雨,所向披靡。这让我想起苏童的小说《哭泣的耳朵》,小小的主人公用手在自己的耳朵边使劲摩挲并且试图写下最后的人生体会。因为耳朵哭泣了,心不再感到压抑。当泪水从耳朵流出,记忆就变成明亮的事物,如同阳光里的一块暗斑或者瓦檐上长满青苔的时间胎记。
酒、音乐、人性。相离相合。生活和孤独的关系抑或又像脚和鞋子的关系?众所周知,鞋子的舒适程度只有脚知道,而脚在流血,脚被包裹在鞋子里,纵使脚在痛哭流血貌似没有理由反抗或者拒绝鞋子的恩惠,貌似脚被鞋子容纳了整改了,而鞋子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保护的桎梏。人性啊!酒泡出生活,生活被泡在酒中。绚烂奢靡的人性之花,那是孤独的脚磨出的生活之血泪。
我又想起了寒气森森的医疗器械。当医学专家拿着它们轻松地划开我的皮肉长驱直入,试图进入脖子深处鲁莽而巧妙地摘取那些不明状物,好比割掉生活的重重负累以及所有肮脏流经的斑痂——某个人生的病灶。
那么此刻,我需要一杯酒。
两个女孩走上台去跳舞。她们是艺校生,画着浓妆,随着节奏劲歌劲舞,纤细的腰身如细蜂剧烈地扭动,又似鱼儿在波涛里穿越着人生的惊喜疼痛。一袭红色的纱罗衣,染黄的头发披下来又猛烈地被甩动起来,那张小脸一忽儿出现一忽儿消失,动感十足;另一个披着黑色的纱罗衣,短发,劲酷热辣,惹得台下的人直愣愣盯着看。继而尖叫。中间正对着舞台的圆桌,那里围着一圈貌似搞艺术的人,男男女女,十六七岁或者二十七八岁,也有四十岁出头的老男人,穿着打扮很潮,说笑的尺度把握得准,眉宇间流露出暧昧不清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这年头动不动就有优越感爆棚的人,又剩下自卑到零的人,迷茫、伤感、歇斯底里。还有一类谓之佛系族,挎着写有英文字母的大布包怀抱一只肥硕的灰猫咪,独自慵懒地走过午后阳光灿烂的街头。或者一个人去浪迹天涯,仗剑四方,云淡风轻。生活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人生要么如此,要么那般。不管怎样,选择都是不完满的。除了眼前的苟且,心中的诗和远方,还有不明所以地躺着。这些话,成了近几年最通俗的抒情诗。
其实,我们都是孤独的人。一尾尾孤独的鱼,追逐着各自命运的河流,横冲直撞,又小心翼翼地改变着航向。各自命运的河流汇合成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人来人往。追逐的鱼,激浪的鱼,被时代潮流裹挟着朝前奔涌的鱼。风霜令我们容易迷失于远方的浪漫,然后触礁于生活的某一刻。于是,我们成了一尾尾困顿的鱼。迷茫的鱼。搁浅的鱼。水藻缠绕的人生需要花大力气拨开生活布下的迷障,而生活本身往往就是最好的参照物,让我们在止步不前的时候误以为已经远航千里。
邻桌有三个年轻人在喝酒。一个男的很帅,一个胖女孩穿红毛衣和黑皮裙,另外有一个女孩刚从那边走过来加入了,她穿白毛衣和黑裤子。黑皮裙女孩肤色白皙,红毛衣只有短短半截露出腰间雪白的肉,随着她青春大幅度的笑像翻滚的浪花跃动着。其实,她顶多二十岁。她在为青春的伤买醉。她还有资本为自己的青春买醉一回,不错。不知何时,她的手里又多了一个盅子,跟同伴玩起了和之前那桌一样的掷骰子游戏。简单的游戏规则,却让他们露出了儿童般天真的笑容,笑出了生活的想象性和譬喻性。眼看着一大扎啤酒很快被他们饮尽,红衣女孩输了,她站起身又去吧台新添了一大杯。他们越来越兴奋,阔声谈笑,青春迷茫的脸渐渐显得生动起来,继而暧昧模糊……
我开始感到某种深刻的不安。焦虑像窒息的鱼,窘得浑身不自在。为谁?为邻桌的青春买醉吗?一想到脖子里的不明状物有机可乘就再也无法停止我的痛苦思索,良知四散流亡顺着我的呼吸左冲右突。我仿佛又听到医疗器械尖锐的啸叫和哭泣,锋芒的寒光向着眼前生生扎来;我听到某些令人不安的碎裂声,刺耳声,呼啸着,奔突着;我感到某种坠落感像脚下深深的洞穴,要把一切吸进去。
我决意再进行一次逃离。人生需要作千百次逃离,在逃离的过程中寻找着貌似安全的着落点。
于是,我又看见先前迎接我的她。此刻,她坐在靠西南角落的桌子旁,正和两位女子谈话。从我这边的角度望过去,她如沐春风。仿佛正谈到某件事的高潮处,意犹未尽。我承认自己被那种愉悦的力量吸引,决定换到那边去。不知不觉,我已经迈开脚步朝她走去,仿佛受了一种神奇的力量驱使,心无旁骛。我像条鱼样游过去了,决绝而迅猛。
她起身,张开双臂做了个亲昵的动作。简直让我又有点受宠若惊的意思,站在渐渐暗下来的灯光下,这会儿,我还是很明显地捕捉到了——她眼角细碎的鱼尾纹生动地跳跃着,像一群群活泼的小鱼,一切都在告诉我这个女子的不同之处。她化着淡妆,表情恰到好处,以至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觉得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难道不是?你是这儿的侍者?我想问,可话到嘴边突然转了个弯,接着舌头直接把它送出:你是老板娘。我是老板。她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那种云淡风轻的笑意,从没离开过她——一个来自异乡的女子。原来,这间酒吧是她和男老板合伙的。言谈间,她的脸上带着几分自豪。接着,她示意我们继续聊,自己端着酒杯去别处招呼。
现在,另一侧坐着姐妹俩,和我隔着一张条桌的宽度。那位梳中发的姐姐化着精致的彩妆,圆脸庞,精神很足。姐姐用手拍拍旁边安静坐着的妹妹,向我介绍。原来还是90后,这么成熟,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朝她微笑。90 后妹妹穿黑色紧身针织衫,理短发,施粉黛,性感魅惑,正低头不停地摆弄手机,好像一直没注意旁人,非常自我。相比,姐姐的笑靥生动,坦诚率真。她们都是普通女工,到这座城市打拼已经好几年。姐姐问我住哪,我说住回观。她说她们住大龙港附近。我知道那是城市南端的一个老旧居民区。一头在城东南,一头在城西北,我们之间正好横亘着整座城市的遥远距离。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得知姐姐和女老板是闺蜜,一起打工认识。这下,我终于发现了她精致妆容背后的某种沧桑风尘。
我们等着女老板过来,想听她的故事。我看见不远处的她正在酒吧间游走,浑身上下熠熠闪光,洋溢着笑容,灯光下的她就像一条游动的鱼甩动着七彩的浪花。现在,我需要一种真实的存在感,在莫问酒吧这样的地方。撑起整座浩瀚无垠的虚幻之海,然后寻找生活给我的真实理由。
关于女老板的故事,她说到“缘分”一词。意思就是人和人之间都可以用缘分解释。“缘分”这个词好比深蓝色的浪头,唯美而魅惑。我好像看见她眼角的那些“鱼”,仿佛都要随着时间游走了。她说,同事邀她开火锅店,当时走投无路的她想不如放手一搏,然后真的赢了。从一家街边的小火锅店,到现在这个处于繁华地段的酒吧,她的生意越做越大。她继续说,我的故事长着呢。当年我揣着五百块从老家出来,想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开始一个月挣五百块,十个人合挤在一间出租屋里,经常吃泡面。第二份工作在一家料理店,月薪八百。好不容易攒点钱,同屋的女孩生病了,开颅术,几个老乡东凑西凑把积攒的钱都掏出来……
一般而言,女老板都是有故事的人。我从文学作品中读过那些故事,它们像酒味样妖娆艳丽,又呈现酒色样的幽深迷离。我想象中的酒吧女老板应该像故事中那样穿高档亮色套装,蹬黑色高跟鞋,浑身洒香水,散发雍容华贵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气质。而我眼前的她,年轻,不够妖娆却迷人,普通的紫色休闲服和及膝的棕色毛呢裙,平跟黑皮鞋。她的话语就像她的为人样亲切,我甚至很想把她比作一只紫色的鱼儿,美丽但不是城府森森的富贵态。
我听到的是关于一个外来妹如何在这座城市苦苦挣扎,从底层做起,一步步撑起一份事业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她在细细地述说,讲到一个动人的结尾:她有车有房,结婚育儿,老公是一位公务员。她在我面前特别强调她的老公是“本地人”,好比这三个字有着千钧力,充分诠释着她的成功人生。继而,她莞尔一笑,轻松吐出一个词:“缘分”,云淡风轻的脸上充满自信和傲骄。那一刻,我看见她化身一条迷人的鱼朝着大海深处游去。我沉浸在她的故事里,想象着那些美好的情节。我们都憧憬王子和灰姑娘的童话,其实生活里哪有这些,能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灰姑娘也不再是灰姑娘,因为她已换上靓丽的新装。
此时此刻,我感受到蓝色的波浪在周身涌动,一条童话中的美人鱼在大海深处优美地游弋。
这座城市该有多少莫问酒吧?莫问酒吧是城市喉管里的一个暗结,潜伏在城市身体里的一个暗色血块。有多少人间的故事在这里上演?有多少异乡人躲在深夜的莫问酒吧沉湎于一个个故事之中?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人生的故事。
酒吧里,谁也认不清谁。酒吧里,人群像鱼一样游来游去。人和人,就像鱼和鱼,倾听着彼此的故事,诉说着各自的心情。细碎的言语,波澜起伏的人生,遭遇和命运,不露声色的潜台词。随着漩涡摇晃的彩色灯光变成摇晃不定的浪花,内心的隧洞长出情感的山峰,撞击、迸裂、摩擦、凝聚,身体和身体向着各种不同的方向作自由式落体、上升、下坠、沿着抛物线滑落,而其中的某个环节又会出现弹跳和短暂的阻滞,某一刻又面目全非地黏连成一个圆球,或者集合成一排排图形,构成一组组无法想象的光怪陆离的意义。画,抑或歌。浑然天成,难分彼此,电光火色,山崩地裂。变幻的灯光,变幻的表情。涌动的人群,呆滞的人群,奋勇向前的人群。一群群搁浅窒息的鱼……大家在深海里游弋,暧昧地取暖,作最后一次深呼吸。
晃动的酒杯,幸福的微笑,骄傲的模样,所有流过的悲伤之泪化作汹涌的大海。他和她,以及更多的我们。城市收留各色酒样的灵魂,阔气豪爽地鞭笞,而疲累和窘迫的表情又被谁捕捉了?酒吧的某个角落,也许有个尚未成名的写作者不错时机地坐下来,一支笔就着摇摆不定的灯光和魔幻样不停变奏的鼓点,蘸着欲语还休的暧昧酒色,借着脖子里的暗色伤疤铺开内心的稿纸,写下蓝色的星辰大海……灯光骤暗,球形灯旋转,不停地旋转,五彩的光柱随之摇摆,酒吧像一朵黑色之花陷于漩涡,更似一条黑色的鱼在不停旋转。舞台上,女孩唱出一首歌,磁性深沉的声音述说真挚的沧桑和热情。她就是坐第一张桌玩牌的那个瘦弱的女孩,那个笑声很响的女孩,我忍不住惊叹那么纤细的身体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
人生是一片海。每条鱼都有自己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有各自的快乐和忧伤。每条鱼唱着不同的歌,一首首既孤单又温暖的歌。沃特艾文儿在《化身孤岛的鲸》里唱道:“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足够撑起海底那座琼楼,而在你到来之后,它显得如此清瘦。人心有时候就如同一座孤岛,期待有人可以靠近,又害怕给不了对方温暖的拥抱。”周深也唱过一首《化身孤岛的鲸》,歌中讲述了一条名叫Alice 的鲸鱼独自在深海旅行,从温暖的加州沿海到寒冷的阿拉斯加,从西比利亚的大西洋海域上万公里的风景线它总是一个人去经历着。也许,一条鱼很孤单,它想要找到同类吧?可是,它发射出的52Hz频率在深海之中总是得不到回应。终其一生,我们不过是想要找到另一条鱼——“知音”。我们是彼此失散的鱼,某一刻,如果另一条鱼能够感受到你的呼吸能够分享你的喜悦分担你的忧愁,这是多么美好的童话故事。
在你需要的时候,深夜的一条鱼也能朝你义无反顾地游过来。然而,那条鱼现在在哪?若你风尘仆仆,我亦等候千年。我的眼中有春花秋月,胜过你爱的山川河流;你的人生四季流年,最后我将是一条化身孤岛的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