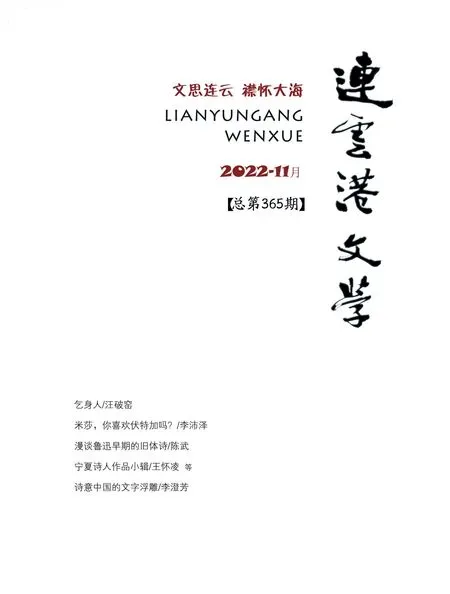乞身人
汪破窑
一
陈富兴兴致勃勃地扛着鱼竿出去,好像他扛的是一把枪,回来时却蔫不啦唧的了,两只塑料袋瘪瘪的,一看就知道打了败仗。那细细的鱼竿前两节没有收缩回去,欢快地晃动,像是在笑陈富兴。
姜蔓芬见他空手而回,有些意外,问道:“肥龙不让钓?”水库被肥龙承包后,来钓鱼的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一到节假日水库边停满了车,一个个戴顶耐克、LMB、INGPEI遮阳帽,黑色蛤蟆镜,像来了一群西部牛仔。陈富兴在姜蔓芬眼里不属于“有头有脸”的人,肥龙不让钓再正常不过了。
陈富兴脖子一梗,一根青筋窜了出来,像条蚯蚓在蠕动。他说:“他敢管老子,再怎么说老子还是他没出五服的叔!”
“那咋没钓着鱼呢?”姜蔓芬不解地问。
陈富兴眼一瞪,眼珠子恨不得要飞出来:“他只顾着赚钱,把水库上面的荔枝林给包出去了。”
肥龙从来没有消停过,总是想着法儿去捞钱,什么挣钱就干什么,把荔枝林包出去有什么了不得的。姜蔓芬怔住了,脸上充满了疑问,像在问,那跟你钓鱼有什么关系呢。
陈富兴解释说:“承包荔枝林的躲在里面养猪,猪粪直接排到水库里,臭死了,好多鱼都被猪粪薰死了。水面上漂着一层死鱼,这天气,一晒,更臭了。”
姜蔓芬像闻到了臭味,皱着眉头问:“肥龙不管?”
“管什么管,养鱼能挣几个钱,收养猪场的租金比养鱼来钱。再说鱼死的毕竟是少数,那些塘鲺、草鱼吃猪粪反而长得更快。”陈富兴有些惋惜地说:“只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水库,以前还有人划船、拍照、年轻人谈恋爱,现在好了,连鬼影都没有一个!”
“这个畜生!怎么不得猪瘟!”姜蔓芬骂道。
陈富兴没退下来前,到了周末会背着鱼竿出去,钓的鱼够老两口吃几天。虽说姜蔓芬的茶饭手艺好,变着花样弄,但是也害怕顿顿吃鱼,她见了鱼都反胃,只是陈富兴喜欢钓鱼,她也不好说什么。有一次陈富兴从水库回来,兴奋地告诉姜蔓芬,说看到有米把长的草鱼。那是肥龙下的种鱼,全靠着它们甩籽繁衍鱼苗。那些大家伙围着鱼钩吐泡儿,就是不吞饵,陈富兴急得在岸边直打转儿,恨不得直接跳进水里抓。
后来,陈富兴约陈三炮、陈二麻子、黑老鸦一起去水库找那几条草鱼。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坐在遮阳伞下悠闲地钓鱼,他们却是偷偷摸摸的。水库巡查员早就盯上他们了,一看是肥龙的叔,不好管,又怕他们打种鱼的主意。眼看着四月了,种鱼到了产卵排籽的时期,它们在水面活动更频繁了。那个巡查员歪戴着大檐帽,脚下一双脏兮兮的长筒胶鞋,像水里的鱼一样游弋着,警惕地盯着他们。他身上有一股浓烈的猪粪味,他一靠近,陈富兴就屏住呼吸。他们几个围着水库转,一直转,巡查员有些不耐烦了,索性不管了,仰身睡在躺椅上打盹儿。
他们终于在水库的另一则找到了那群草鱼。草鱼慢腾腾地游,露出了黑脊背。看见它们的位置这么近,几个人兴奋地睁大眼睛,双手紧紧地攥住甩竿。陈富兴与他们对视了一下,都是老钓友了,只需一个眼神就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陈富兴“打”字一出口,四根甩竿齐刷刷地飞了出去。那群鱼有十多条,最大的那条游在最前面,其他的草鱼紧紧地跟随在后面。陈富兴事先跟他们商量好了,就打那条头鱼,它没有几年活头了,其他的正值壮年不能打,它们正甩籽呢。鱼本来一条挨着一条,像一团黑色的云,鱼钩打过来,它们丢下那条头鱼迅速四处逃窜,隐入水中不见了踪影。
鱼打上来了。一米来长,估计三十来斤。几个人笑呵呵地盯着草鱼。陈富兴一看鱼鳞,心里暗叫“不好”,这条鱼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老,最多七八年的样子。陈富兴叹息一声,坐在地上抽烟。几个老哥们都看出来了,也跟着坐在地上。没有人说陈富兴眼光差,但这种沉默反倒让陈富兴更加难堪。
鱼平均分了,陈富兴要了鱼尾部分。他最喜欢吃鱼头,可他现在却害怕看见那条鱼的眼睛。姜蔓芬连做了几天的鱼。鱼很肥,鱼油漂了一层,做的汤喝起来鲜香可口。陈富兴吃完饭会抽上一根烟。姜蔓芬以为老头子沉浸在鱼的美味中,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饭菜能得到陈富兴的肯定让她很有成就感。后来,陈富兴亲手砸掉了那根甩竿。他砸甩竿时的样子很凶,姜蔓芬不知道原因,也不敢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砸。她心痛不已,那鱼竿上千块买的。
好长时间他都没有去水库了。黑老鸦来家里拉了他几次,陈三炮、陈二麻子也约了好几次,他才又拿起了钓竿。
叭!
陈富兴把渔竿扔在了地上。姜蔓芬看陈富兴并没有发火,脸上却流露出隐隐的忧虑,她不以为然地说:“钓不了就不钓,真是想钓了回我娘家去钓。”姜蔓芬是江西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来深圳打工,后来嫁给了陈富兴,是村里第一个外嫁过来的,陈富兴也成了村里唯一一个在家也要说普通话的人。姜蔓芬娘家有一个大鱼塘,陈富兴陪姜蔓芬回娘家时会过足钓鱼瘾。
“钓不了鱼是小事,我担心水库要毁在这小子手里。”
“毁就毁呗,与你何干,你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子,没有孙子让你带,就在家里享享清福,”姜蔓芬补充道,“你可有……不要多管闲事!”后面这句才是她想表达的,她想说陈富兴有前车之鉴,一时想不起这个词,说得很直接。一个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碍自己的事,管那闲事干嘛呢。
他沉默了,仿佛看见了一堆堆的猪粪,像堆在他面前,猪粪味浓烈得让人发呕。人老了,嗅觉却变得越来越敏锐,姜蔓芬骂他“狗鼻子”。他知道闻到猪粪味是不可能的,家距离水库很远,什么风也不可能把猪粪味刮到这里来,他暗自揣度。可是明明闻到猪粪味,这使他忐忑不安。
一晚无话。
陈富兴与姜蔓芬同睡一张床,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陈富兴辗转反侧,姜蔓芬用脚踢他,他才不再翻身。
第二天一早,陈富兴吃了早饭,背着双手出了门。姜蔓芬跟在后面“哎”了半天,陈富兴装作没听见,大步向前走去。
二
荔枝林的地早收为国有了,城市也禁止畜禽养殖。可人家肥龙就是有本事,把地租给外地人搞养猪场,硬是把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陈富兴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中到了执法队的大门口。陈富兴犹豫了,自己不能钓鱼就去举报,多少有公报私仇的成分。这些年在水库钓鱼,肥龙从来没有说过,给足了他面子。他开始往回走,又回头望了望。大院上面一杆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陈富兴心头一热,仿佛又回到半年前。
那时的他实名举报上级权力寻租,因证据不足而不予处分,领导照样当领导,而他在单位却干得不如意了,索性乞身告老。他一回来就被街道组织部长找去谈话了。组织部长不到四十岁,面相嫩,看起来像二十来岁的娃娃。陈富兴心里说,老子找人谈话时,你还穿着开裆裤,可是一说话,人家的水平就显现出来了。“陈老虽然告老还乡了,但是党性强、阅历深、威望高,回到家乡了还要发挥余热,一些难题单纯地讲大道理是不行的,您老的作用比法律法规还要管用。”部长讲了很多,陈富兴记不全,但句句听了很受用,也很受鼓舞。他当场表态要为家乡出一份力。他主动加入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动让他的“退休”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为这事姜蔓芬没少埋怨他。说归说,他还是老样子,戴着红袖章管一些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事。
执法队长不认识陈富兴,以为找他办事的,脸绷着。站在门口的保安连忙解释:“吕队,我没有拦住,他硬生生地闯进来了。”保安气喘吁吁,汗珠儿顺着脸往下淌也顾不上擦,呆呆地盯着吕队。吕队冲他挥挥手,他还想解释什么,看吕队根本不想听,只好蔫蔫地往大门口走去。
吕队看起来很忙,边和陈富兴说话,边处理桌上的文件,有的他粗粗浏览一遍,有的他看都不看就画了一个圈。吕队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很快,处理一份,又把目光投向下一份。陈富兴不说了,干坐着。吕队一副不苟言笑的神情,一边看文件,一边跟陈富兴说话,语调不急不缓。
“情况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
“哦,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吕队问,连头都没抬。
“没有了。就这些吧。”陈富兴想说点什么,又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吕队心不在焉的样子让他感到恼火,心里骂“一丘之貉”。
他缓缓地站起身来。有一些不舍,有一些无奈。
吕队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脸上露出了笑意,笔终于放下来了。吕队紧紧握住陈富兴的手,嘴里说着感谢的话。“您反映的情况我都记下了,您老放心,我们会处理的。”吕队说已经签下了军令状,非法养殖要年底实现清零。
谁知道呢。陈富全心里想,嘴上却说:“好好。”
吕队一直把陈富兴送到了大门外,这倒让陈富兴有些不好意思了。吕队再一次握住了陈富兴的手,叮嘱他一定保守秘密。陈富兴点头应着,心说难怪要送我,原来是怕我再向上反映,哼!你们这一套把戏我懂。我还怕你们不能保密呢,肥龙知道了还不晓得会怎样对付我呢。
陈富兴默默地往回走。他低着头,像一个丢失东西的人,正原路返回寻找,那全神贯注的劲头让路人纷纷为他让路,还差点儿撞上了电线杆。有一个司机冲他猛按喇叭,摇下车窗骂:“你瞎呀,路都不看,找死啊!”
陈富兴忙不迭地道歉。
回到家,姜蔓芬已坐在餐桌上等着了。菜冒着热气,看来刚做好没多久。
“怎么样?”姜蔓芬问道。
“什么怎么样?”陈富兴被问得有些莫名其妙,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我还不知道你吗?你肯定是找人了。”姜蔓芬边说边把盛满饭的碗递给他。
“找了。”陈富兴接过饭,气呼呼地说,“可人家不愿搭理我。”
“我早猜到了。”姜蔓芬扒了一口饭,嘴里鼓鼓的,嘟囔着说:“换成我我也不愿搭理你,这不是给人家找事嘛,指不定在背后骂你多事呢。”
“啊,啊嚏!”这时,陈富兴猛地打了一个喷嚏,幸好及时把脸扭到一边去,不然嘴里的那口饭就喷在了桌子上了。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他们肯定在骂你了。”
“让他们骂吧,人在做天在看,凡事凭良心。”
“良心?”姜蔓芬笑出了声,“现在谁还讲良心呀,良心值几个钱?”
陈富兴无力地叹息一声。
“你想想看,那么大的一块地,肥龙能包给别人喂猪,肯定上下打点了,人家肥龙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没人搭理你好,免得惹祸上身。”姜蔓芬门牙活动了,吃东西全靠后槽牙,一嘴的饭菜让她不敢把嘴张大。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发音含糊不清。陈富兴听清了她的意思。
吃了饭,突然下起雨。陈富兴又闻到猪粪味,是雨水冲刷出来的臭味,更浓,更臭。一群猪在雨中追逐,打滚,猪粪泡在雨水中冒泡泡。陈富兴眼里老是出现这样的画面,不知不觉中靠在床沿上睡着了。
他迷糊了一会儿,那些猪、猪粪、鱼,还有水库的水,一直出现在梦境里,一头猪冲着他哼,一下把他吓醒了。他醒过来四处找猪,却看见姜蔓芬四仰八叉地在床上睡得正香,拖拉机一般的呼噜声从嘴里鼻孔里呼啸而出。她的胸腔腹部随着呼噜声起起伏伏。四十多年前,她也是个大美女,岁月吞噬着她的容颜,他心生愧疚之感,年轻时他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一切都甩给她了。陈富兴觉得亏欠她太多了,原想着回来可以还还债,又养成了被她照顾的习惯,债未还成,反倒事事离不开她。
雨不知啥时候停了。院子里的那棵龙眼树被雨水压弯了腰,树叶贴在一起,黑压压的一团,雨水不时从上面滴下来,“啪”的一响,地上有雨水滴出的深坑。
三
投诉的事还是不要让人知道的好。那天陈富兴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竟跟黑老鸦说了。
陈富兴下棋老是心不在焉,这让黑老鸦有些生气,你这样敷衍我,也太不拿我当回事了。黑老鸦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推,气呼呼地说:“不下了,哪有你这个下法,把棋子往人家嘴里送!”
陈富兴发出一声叹息。
黑老鸦问:“富兴,你有心事?家里有啥事?”
陈富兴望着黑老鸦,嘴巴张了张,又开始收拾棋盘上凌乱的棋子。
黑老鸦看出陈富兴有话要说,又有些犹豫。他说:“怎么,不放心我,有啥话还不能跟我说?”
“不是不放心你,我是怕这事传出去不好。”
“还是不放心我。”
“有些事,你不知道好,免得连累了自己。”
黑老鸦一拍胸脯,说:“我这把年龄了,怕个毬!”陈富兴欲说又止的样子深深吊起了黑老鸦的胃口,黑老鸦保证:“你放心吧,你说了这事到我这里就打住了,就是打死也不会对外说一个字。”
话到这份儿上了,陈富兴只好把举报肥龙把国有土地外包给人办养猪场的事说了。黑老鸦明白了,反倒叮嘱陈富兴,“你要注意,可不能对人说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肥龙那畜生六亲不认,知道是你举报的,还不扒了你的皮!”
陈富兴有点后悔把这事告诉黑老鸦了。
黑老鸦向陈富兴保证会守口如瓶。
那天棋没有下尽兴。黑老鸦又说去水库钓鱼,陈富兴说姜蔓芬身体不舒服,拒绝了。黑老鸦笑他怕老婆。陈富兴有些窘迫,便说:“怕老婆就怕老婆。”陈富兴说得理直气壮,倒让黑老鸦没有话说了。黑老鸦笑了一下:“那你在家守着老婆吧,我去找陈三炮、二麻子去了。”
这段时间,陈富兴哪都没去,整天在家里猫着,像恒温动物进入了冬眠状态。他属于被动性冬眠,在家里照顾姜蔓芬。姜蔓芬也不知得了啥病,有气无力的,去医院检查,人家大夫说的玄乎,叫什么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陈富兴搞不明白人怎么跟植物扯上了关系。这世上有两个不讲理的地方,一个是医院,一个是殡仪馆,你得老老实实听人家的安排。药开了一大堆,一日一次的、两次的、三次的,饭前的、饭后的,整个屋都是药味,像走进了中药铺。
这天他正陪姜蔓芬看电视。姜蔓芬喝了药后,不是看电视就是睡觉,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来后又接着看。
有人敲院子大门,哐当哐当响,跟着传来一个似熟不熟的声音。陈富兴出来一看,竟是肥龙。他怔住了。虽说两家没出五服,平时很少来往。陈富兴在路上遇见过肥龙几次,肥龙坐在小车里面,摇下玻璃窗,主动停车下来搭话,满脸堆笑,客客气气地叫“叔”,显得很亲近。现在年不年节不节的,主动登门了,肯定有事儿。
肥龙上前一步,“啪”地给他跪下了。陈富兴不知道他唱的哪一出,赶紧把他往起拉,不解地问:“龙仔,你做咩嘢?”
肥龙不起来,“啪啪”自扇了几耳光,说:“叔,龙仔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您老多担待,也用不着往死里整侄儿呀。”
陈富兴彻底懵圈了,一时手足无措。
肥龙说:“叔,虽说我做人横,我从来没有在村子里横过吧?我有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您退休不退休我可是一个样儿待您,您去水库钓鱼我特意交代保安不要管,钓多少鱼都不收费。”
肥龙说的是事实。陈富兴连连点头。
肥龙说:“我把荔枝林包出去,这荔枝林是我们村里的吗?不是,早就收归国有了,我包出去也没有损坏村里的利益。”
陈富兴“噢”了一声,立刻明白了。他假装糊涂:“你包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肥龙从地上爬起来,拍拍手上的尘土,又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盯着陈富兴说:“说得好,跟您没有关系,那您为何要断我的财路!”
陈富兴说:“我什么时候断你财路了?”
肥龙说:“今儿黑老鸦去水库钓鱼,水库巡查员人有点‘轴’,不认识黑老鸦,硬是不给他钓,黑老鸦一急就说是你举报我侵占国有土地搞非法养殖。”
陈富兴想辩解一下,肥龙没给他机会,接着说:“水库巡查员给我打电话了,我不信,电话刚挂没多久,执法队就打来电话了,说是要整治非法养殖,要我一周内处理完毕,现在那几个养猪的不停地找我,要我赔偿他们的损失。”
陈富兴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了,索性倚老卖老,梗着脖子说:“就算是我举报的吧,你能咋的?”
肥龙没想到陈富兴这么爽快承认了,这倒让他没有想好该怎么收拾这个局面。这时姜蔓芬也出来了,指着肥龙骂:“你是不是傻呀,人家说你叔举报的就是你叔举报的?你有没有长脑子。黑老鸦是谁,他不就是一只到处瞎咋呼的老鸦嘛。他说是你叔举报的,我还说是他举报的呢。”
肥龙经姜蔓芬一骂,好像清醒过来,连声说:“对对对!这个黑老鸦,差点儿中了他的计。”肥龙连连给陈富兴和姜蔓芬道歉,气呼呼地走了。
陈富兴半天没回过味来。姜蔓芬吓坏了,好像病好了一大半,接着指着陈富兴骂:“你也傻,人家说了你就承认,这事儿打死也不能认!”
陈富兴频频点头。
四
期限已到,执法队要强制执法。终于传来了让陈富兴久等的消息。
陈富兴说过去看看。姜蔓芬不让:“上次把肥龙糊弄走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肥龙手段高,朋友多,一问,就能把这事给问清楚,你去,不是自投罗网!”
陈富兴说:“还是你说的那句话,打死也不认,他能把我怎么样!”
“那你也不能去,臭烘烘的有什么好看的。”
“我想看看养猪场能不能被清掉。”
“清掉?哪有那么容易,”姜蔓芬说,“顶多走个过场,这样的事儿还少吗,一大堆人过去,拍拍照,说遇上了暴力抗法,行动受阻,就不了了之。”
陈富兴心里痒痒的,还抱有另一种期望。这几年,他感觉氛围不一样了,干部作风转变了,敢于较真碰硬。但他对那个不苟言笑的吕队抱有成见,他想看一看执法队伍敢不敢啃“硬骨头”。陈富兴换上了白衬衣,像要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
荔枝林里浓烟滚滚,他以为失火了,一股浓烈的刺鼻味道,往他这边灌过来,风向却是相反的。水库边上有两只死猪,挨在一起。水面上漂了一层死鱼,白白的,颇为壮观,都是一拃多长的鱼,还有十几条大点儿的鱼,远一点的地方也有死鱼,三三两两的。不知是猪粪臭死的还是被人药死的。死猪死鱼全身胀鼓鼓的,死猪周边围着一大群鱼,正在贪婪地享受饕餮盛宴。死猪的臭味和死鱼的腥味交织在一起,周围弥漫着怪怪的浓重气味,令人头昏脑涨。陈富兴不知不觉恶心起来,死猪死鱼像在眼前。他连续干呕了几次,忙掩鼻疾走。
走近了,荔枝林里人声鼎沸,像菜市场做买卖。有人过来收购猪仔?再走近点。是人的吵闹声。这时,冷不丁地传来一声很凄厉的尖叫声,那声音来得突兀而又迅疾,穿透力极强,他心里一紧,不由得停下脚步向前张望。接着,传来了一个妇女痛不欲生的哭声。一个妇女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她正瘫软在地上,身边有几个孩子跟着在哭。
一群执法人员站成一排,有几个身上脏兮兮的男人手里拿着铁锹,不停地比画着。铁锹上糊有一层糠皮状的东西,那是用来搅拌猪食。一个男人看着眼熟,脚下正是那双长筒胶鞋,陈富兴想起他就是那个巡查水库的人。陈富兴看见了那个不苟言笑的吕队。他站在队伍的最前方,手拿一个大喇叭,在大声喊话。没有人听他说,人们堵在前方,那几辆轰轰作响的钩机动弹不得。行动受阻了。陈富兴早料到这个结果,下一步是拍照取证,然后人员撤离,这事就这样算了。
吕队大声说:“清场!将无关人员带离现场,阻碍执法的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陈富兴从鼻孔里“哼”了一下。
那几个妇女、孩子哭成一团。这场面让陈富兴心里不太好受。几名身着制服的女执法队员上前拉那几个妇女,不停地安抚。那几个妇女被劝离了现场,女队员们一直站在她们身边讲解着什么,还给几个孩子零食吃,孩子们一看见零食就止住了哭声。这时,十几名全副武装的执法队员并排而行,一步步向前推进。那几个拿铁锹的男人并不敢真往人身上砍,慢慢地向后退着。钩机跟着向前推进。突然一个人冲了进来,往钩机前方一站,钩机立马停下。
是肥龙。肥龙的出现让那些男人精神为之一振,他们立即情绪亢奋起来,又拿着铁锹往前冲。
肥龙站在钩机前方,钩机不能前进。吕队上前,肥龙根本不听他说。
肥龙站在钩机前面不停地打着电话,钩机还在轰轰作响,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打电话的时候,眼光四处踅摸,好像在找什么人。他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电话一连拔了好几个,打完电话他神情有些失落。他站在那里,那些养猪的人也没有退缩。一直这么僵持着。
陈富兴找到了浓烟的来处。荔枝林里的猪圈处有几口大灶,灶口冒着火,煮猪食的柴火是一个废弃的汽车轮胎,浓烟正是由它产生的,那股子浓烈刺鼻的怪味儿也是它滋生的。
“啪!”有人给了肥龙一记耳光。
众人惊骇。谁敢打肥龙!
肥龙被打傻了。是陈富兴。荔枝林静了下来。死一般的寂静。树叶不动,没有了一丝风。仿佛钩机停止了轰鸣,猪也停止了嚎叫。大家瞪大了眼睛,注视着他们。陈富兴与肥龙对峙,四目相对,无声无息。肥龙瞠目结舌,半天才说:“叔,您您……”他看陈富兴胸前别着一枚党徽,那光芒灼得肥龙眼睛眨了一下。
陈富兴二话不说,上前捏住了肥龙的耳朵,像一个屠夫拎一头小肥猪。肥龙疼得直咧嘴:“哎呀,叔,痛痛……”
陈富兴说:“你也知道痛,我就是要让你知道痛。”
肥龙说:“叔你再不松手,我可要……”
肥龙已把“您”换成了“你”,陈富兴没有听出来,他这时也顾不上这些细节了。“咋的,你还敢动手,别看你在外面混得人五人六的,在老子这里不好使,”陈富兴说,“政府的公务活动你也敢阻挡,你是不是又想进去了。”
肥龙半天才把陈富兴的手掰开。肥龙怒目圆睁,一只手不停地揉着红通通的耳朵,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时黑老鸦、陈三炮、陈二麻子几个人也过来了,他们几个紧紧地围绕在陈富兴身边。几个老一辈的人面对肥龙没有一丝怯意,一个个怒视着肥龙,反倒让肥龙不寒而栗,他眼睛里的火先灭下去一半,只剩一星半点儿的火光,最后硬是被他们几个给摁熄灭了。
陈富兴自觉自己行得端走得正,才不管你什么白道黑道。几个老哥们围在一起,把肥龙堵得动弹不得。吕队赶紧指挥钩机行动。搭建的猪棚被钩机砸倒,水泥地面被挖开,那些白花花的猪被撵进一个临时搭建的猪圈里。看到养猪场夷为平地,陈富兴心里爽快极了,像吃了一根冰淇淋。肥龙抱着头蹲在那里,接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全然不顾地面上的猪粪。
当天晚上电视里就播放了这则新闻。陈富兴盯着电视笑。姜蔓芬一看电视就明白陈富兴为何发笑。她跟着笑了,因为她好久没有看见陈富兴笑了。
五
院子里的那棵荔枝树愈发浓绿,陈富兴在树荫下驻足观看,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他伸出手把漏下的光点接住,手心一暖。荔枝树的花期已过,长出一串串小小的圆圆的荔枝。去年收成不是很好,今年必定丰收,这是果木的生长规律。荔枝吃多了上火,他打算等荔枝熟了,摘下来分给左邻右舍。
陈富兴背着双手,抬头望着那些小小的荔枝,一颗颗的荔枝仿佛正冲着他笑。
恍惚间觉得有人从身后向他走来,没有脚步声,像个幽灵。
“叔,看啥呢?”
不知什么时候,肥龙已站在了他的身后。他回过头一看,肥龙也学着他的样儿,把双手背在后面,昂首挺胸地看着荔枝树。
自打养猪场被清掉后,陈富兴听说派出所把肥龙“请”过去了,后来就没有听到肥龙的消息。姜蔓芬担忧地说,越是平静越是危险,这几天注点儿意,可不要出门挨了黑打。陈富兴嘴上说不在乎,其实也怕这小子犯浑。陈富兴做好了挨黑打的准备,但是肥龙就是不露面,陈富兴越着急,肥龙越是没有消息,肥龙去了哪儿呢?有人说当天派出所就把肥龙放了,肥龙坐着一辆黑色的奔驰走了。陈富兴提心吊胆地挨了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便不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现在肥龙上门了,那就不是挨黑打的事了,这不明摆着嘛,人家是明火执仗上门了。
肥龙冲陈富兴一笑。这一笑让陈富兴心里发毛,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这时他才发现肥龙背在身后的双手提着什么东西,不是棍子,也不是刀,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包装精美,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儿?
姜蔓芬从屋里出来了,她看见肥龙,一怔,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好。
肥龙把礼盒拿出来,“婶,我来看您老来了。”把礼盒往姜蔓芬手里塞。姜蔓芬木然地收下了,半晌才恢复神态,忙说:“龙仔,你屋里坐。”
肥龙连连拒绝:“不了不了,我找叔有事商量呢。”
姜蔓芬又开始紧张了。她最近看了不少港台的警匪片,知道黑道有很多种玩法,不知肥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肥龙一把握住陈富兴的手说:“那天多亏了叔给了我一耳光,把我给打清醒了,不然侄儿真进去了。”肥龙看陈富兴懵了,又说,“那天的执法行动有这么一项内容,就是要严厉打击暴力抗法行为,幸好叔打了我一巴掌。后来,派出所找我谈话了,说我把国有土地承包出去是非法侵占国家和集体利益。现在我已把租金,不,非法获取的利益,全部上交了,鉴于我的表现就不再追究我的责任了。这不,我又找了一份正经的营生,水库巡查员。”肥龙亮出了他的工作证。
“您老咋还不信了呢?我真是在看水库。”肥龙解释说:“因为我是水库边长大的,熟悉情况,所以水库才聘我为巡查员。”
陈富兴吃力地说:“我信!”
“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肥龙声音弱了一些,“水库太大了,我一个人看不过来,怕误了公家的事。我想请您老出山,当义务巡查员,没事时转一转,捞一下水里面的垃圾、漂浮物之类的,不知您老……”
陈富兴打断肥龙的话:“行!我还把黑老鸦、陈三炮、陈二麻子他们几个一起拉上。”
“那感情好!我先谢谢叔了。”肥龙冲着陈富兴连连作揖。
陈富兴手一挥,说:“谢啥,我们就当散步健身了。”
肥龙走后,陈富兴两口子还想沉浸在梦幻中。姜蔓芬望着陈富兴,想了半天才说:“世道真变了!”
陈富兴带着黑老鸦、陈三炮、陈二麻子沿着水库巡查,举着“党员志愿者巡查队”的旗帜格外醒目。转眼街道为他们授旗已有三年了,现在想来恍如昨日,他们的足迹也有“二万五里”,但陈富兴知道,他们的长征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刚刚开始。
放眼望去,水库三面环着山峦,周边林木葱郁,碧波无痕,远远望去犹如镶嵌在山峦之间的一块巨大而闪亮的翡翠玉坠。远方有一条亮眼的红色绸带在荔枝林中穿梭,这就是有名的网红打卡点“虹桥”,恰似串起玉坠的红飘带。再远点是欢乐田园的两千亩花海,各类花草漫山遍野,陈富兴仿佛看到了蝴蝶蜜蜂翩翩起舞,好一处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几个人贪婪地大口呼吸着这清新空气。
几只白鹭和野鸭在水面出没,水里的鲫鱼、草鱼老往上蹿。水库边还有一大片平整的草地,有人在此搭帐篷、打牌,有孩子们在草地上做游戏、放风筝……
陈富兴忍不住说:“真好!”
陈三炮跟着说:“真好!咋不像我们当年修的水库呢。”
陈富兴纠正道:“不是水库,是光明湖!”
陈三炮露出不解的神情,自言自语:“光明湖。”
陈富兴和黑老鸦、陈二麻子异口同声:
“光明湖!”
他们的声音震得一汪水面漾起了层层涟漪。两只白鹭展翅而起,飞向湖的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