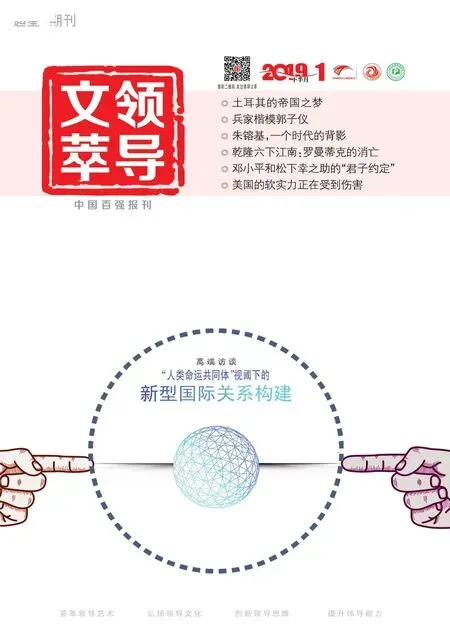烹饪的冲突:当厨房打仗的时候
[法]让-马克·阿尔贝/著 刘可有 刘惠杰/译
建立民族的菜式是饮食身份诸方面中的一个方面,饮食的疆界很脆弱,理论上的模式和烹饪的实际完全不相容,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人们一定都是关注菜品的味道怎么样,要花多少钱,而不是在吃上面一个劲儿想着国家利益。
“他者的厨艺”于是成了一种参照物,可以用来模仿,也可以尽量规避。
法国和英国的对立也反映在间接的烹饪对立上,18世纪以后,很多英国餐厅都拒绝把法国菜品写在自己的菜单上。法国宫廷烹饪无疑深刻地影响了英国贵族的饮食习惯,而所谓的“家庭烹饪”对法国影响实在的“反击”也不能忽视。1842年,雅克·阿拉贡出版《在巴黎用餐》,说到餐馆和大众餐厅,其言辞刻薄无以复加,但当提到法英餐厅的时候,却把法国菜和英国菜分开说,法国菜真的很好吃,英国菜实在难以下咽。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拿德国人的习惯开刀,说德国人的习惯过于“日耳曼化”,在吃饭上面表现得最厉害:偏爱油腻的菜式,菜量极大,还边吃边看书,这都是对匈牙利人生活的巨大伤害。奥地利的排犹情绪甚至蔓延到了烹饪空间,1872年,维也纳学生会建立了第一个日耳曼酒吧,禁止任何犹太学生和他们合用一张桌子,犹太学生也不能和日耳曼学生一起喝啤酒。
其他一些社团仿照维也纳学生会的样子,也有这样的歧视行为。“他者”的理论,也把食品和某个人群的道德(更多的时候是该人群的缺陷)联系在了一起。法国的“栗子文化”就很能说明问题。栗子本身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但是从18世纪以后,栗子渐渐地和种植者的懶惰连在了一起。科学家沙普塔勒说“栗子园不需要人照管”,1863年,噶斯帕兰在其著作《农业教程》中宣称:“仅仅依靠一棵树上的果子养活自己的人群,必定在生活中停滞不前。”类似的批评越来越多,有人抨击利穆赞地区农民所谓的闲散,又有人数落科西嘉的农民。1905年,让·洛兰措辞激烈地说:“栗子是科西嘉的小麦,这和科西嘉农民的穷酸与懒惰正好搭配。”噶斯帕兰比较爽快,干脆把栗子说成是蛊惑人心:“天上掉馅饼,果实从树上掉下来,上头掉着,下面拾着,这难道不是社会党人梦寐以求的黄金国吗?”他要传递的政治信息十分清楚:“栗子文化”可以滋生懒惰,保不准也会滋生反叛和动乱思想。
政治的危机是食品现象的极端化,那些被视作入侵者的人已经不是简单的对手了,而是要来摧毁我们文明的敌人。“他者”厨艺从此变成了战争文化的典型用词,纳入了爱国主义的范畴:吃了敌人的饭食,就有可能吸收敌人的优点和缺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禁止吃德国人的菜,如果实在躲不开、不吃就没得吃了,也要改了菜名再吃。这种“烹饪强奸”逼迫政府对已经变成寻常之物的消费品做出反应:如果不得不使用一些外国产品,就要完成一次派生词的革命。1918年,酸菜熟肉、8字形松饼加法兰克福小香肠从美国的商店和餐馆里消失了,变成了“自由酸菜”和“热狗”,汉堡包的名字也变成了“自由三明治”。大部分改了名字的食物在战争后都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唯有代替法兰克福小香肠的热狗例外。
战争中,交战双方经常指责对方是吃人野兽,这种说法并不鲜见,16世纪宗教战争时,几个城市被围困,天主教和新教也互相攻击对方是吃人野兽。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脱离这个窠臼,“吃人野兽”成为敌人的象征,“敌人”是一个和西方文明基本价值对立的野蛮人。当时的一些文章痛斥德国人禽兽不如,说在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德国占领区,德国人犯下了吃人的罪行,成为日耳曼人胃口牺牲品的儿童和妇女更加锁定了德国人的野蛮形象。
在德国,意大利厨艺从1920年“异国食品”的地位转化到了1930年的“可以接受”的地位,因为这两个国家地缘接近,而且这两个法西斯国家意识形态相同。但是,总体上说,这个时期大家不喜欢外国饭菜,《贝德克尔》导游手册里很注意避免提及做外国菜的餐厅,说到大城市的时候也是一样,当然也能看见一两处意大利招牌,比如在德累斯顿、维也纳或者柏林。1938年,在“德国首都”一章中,这本导游手册只有一次提到了一家中国餐馆和一家日本餐馆,一次也没有提到法国餐馆,而在柏林的法国餐馆其实相当多!至于俄国饭菜,整个德国只提供了一家俄国餐厅的地址……
有全球影响力的饭菜,是纯粹地方主义者的眼中钉。在汉堡包出现之前很久,法国饭菜就被说成是帝国主义了,法国饭菜阴险,它悄悄地但却很成功地控制了所有的“民族”饭菜。于是,反对法国成为新生的民族身份的催化剂:西班牙人穆罗要把烹饪的法语词汇变成西班牙语;匈牙利要建立自己的烹饪体系,摆脱法国的,尤其要摆脱德国的影响。
英国的情况差不多,尽管英国人承认在高级宴会上法国菜仍然是首选。如果不是把一款实在的菜品强行置于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之中,没有一个菜式是属于“民族的”。匈牙利饭菜就很能说明问题:匈牙利人不想否定英法菜式和匈牙利菜式的传承关系,但就是不能和捷克、德国有什么关系。这种对德国饭菜的“深恶痛绝”,是要建立匈牙利饭菜身份,同时促进在匈牙利生活的多个民族之间的融合。针对维也纳的“厨师手册”,匈牙利菜谱上列出的匈牙利菜有葱头烩牛肉、浓味蔬菜炖肉块、甜辣椒烩鸡和白菜包肉。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饭菜的国家主义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于“他者”厨艺的思考,每当关系到外来人口携入了某些烹饪传统时,就要对“他者”厨艺有一通激烈的说辞。19世纪,意大利人在洛林就有过这样的遭遇,那儿的人说意大利饭菜“粗制滥造、臭烘烘的”。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设第一家麦当劳餐厅的时候引起民众普遍忧虑,这些忧虑多有夸张和想象的成分,后来西方对“中国饭馆”也有同样的反应。个中原因都是一样的,“他者”厨艺让人害怕,尤其是当它把“声音和味道”掺和在一起的时候。拒绝向“民族饭菜”低头,其实是拒绝和全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包容需要通过食物来完成。在美国,对于那些坚守欧洲烹饪传统,对周围人不屑一顾的意大利人,各种批判像雨点一样砸过去,尽管他们非常想做出正宗的比萨。
不论是移民的厨艺还是外国的烹饪,“民族”问题的根源永远是担心代表身份的厨艺文化被瓦解和稀释,这种厨艺文化的表达方式有着民族主义性质,就是坚决反对“他者”的厨艺。反美主义是这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6月27日,有“美食家公推美食王子”之誉的古尔农斯基为《笑报》写了一篇文章,文中刻薄地挖苦美国的饭菜,虽然他本人从未去过美国:“入座以后,就是为了吃喝。实在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美国餐厅的可怕了,好像在电影上经常看到的画面一样,身体露了一多半儿的女孩儿玩着空中飞人,宾客们向周围的桌子上抛掷彩带,还有吃剩的香肠皮,不管卫不卫生……总之感觉不到自己是在吃饭!看到这样的情况,不禁对我们法国的餐厅和旅馆有了几分真诚的尊重,我们的地方还没有受到这些喧嚣的侵袭。好好过我们的日子吧!”《笑报》这一期特刊还有一段反犹的连环画,其中的内容对比不同人在餐桌上的表现,暗示“法国人”的形象和“犹太人”完全对立,犹太人自然是他者。《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也不客气,在写到美洲的时候,他对不知用什么原料制成的罐头嗤之以鼻——实际他是在不加掩饰地影射芝加哥投毒案件,国际新闻界对这个案件都有详尽的报道。
(摘自《权力的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