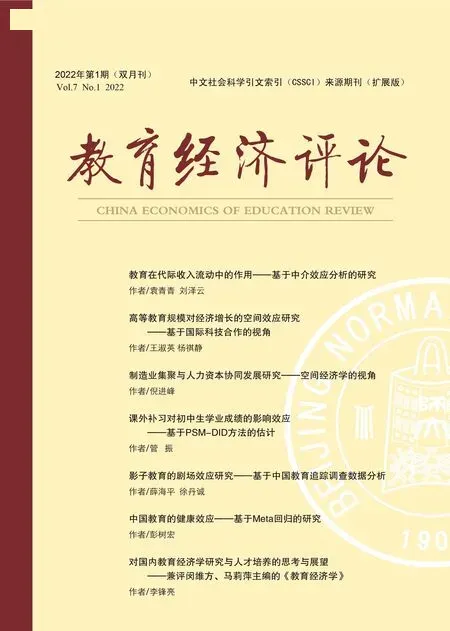对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思考与展望
——兼评闵维方、马莉萍主编的《教育经济学》
李锋亮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认为,1960年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在美国经济学年会所做的关于人力资本的演讲宣告着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Blaug,1976),而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或许可以被视为作为经济学分支之一的教育经济学的诞生(Blaug,1984)。在经过1960-1970年这一教育经济学的“黄金时代”(Blaug,1984)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理论、研究领域、分析框架已基本成型。而我国也随着改革开放,逐渐开始了教育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及相应的人才培养,相关的研究与著作也逐渐增多。
在笔者知识范围内,中国大陆第一本专门的、系统的关于教育经济学的专著是厉以宁于1984年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经济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收益率的迅速攀升,国内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相应人才培养的规模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关于教育经济学的教材进入了一个井喷的阶段——比如靳希斌199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 王玉昆1998年华文出版社版、范先佐199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林荣日200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版、张学敏2001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的《教育经济学》及其相关修订版。除此之外,由闵维方领衔翻译的、马丁·卡诺依(Martin Carnoy)编著的《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二版)》(以下简称卡书)也是一部有助于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里程碑式的专著。
之后,除了翻译国际上相关教材外,国内关于教育经济学新教材的出版似乎进入了一个平静期,接着在2010年左右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比如,范先佐201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经济学新编》、肖昊2010年武汉大学出版社版以及赖德胜201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的《教育经济学》。尽管笔者在各种场合经常听到有人呼吁要出版更多教育经济学的教材以更好促进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然而此后除了上述教材的再版与改版外,似乎再无重量级教育经济学教材的出版。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教育投资体制的不断完善、教育财政投入的逐年增加,各级各类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超过了4%,我国的教育事业进入了“后4%时代”,人们对教育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教育经济学研究队伍与学生规模越来越大,需要更多《教育经济学》的专门系统的教材。在这样的背景下,由闵维方和马莉萍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的《教育经济学》,对于广大国内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和学生而言,是一件值得重点关注与研讨的大事件。
笔者颇花费了时间对此书进行仔细研读,在研读过程中结合目前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现状,有以下四点思考。
思考一:如何更好地基于一个完整体系对教育经济学进行研究与讲述?
在卡书中,马丁·卡诺依将全书分成了八个部分,分别是:教育经济学的历史与现状;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收益;教育、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教育、收入分配和歧视;教育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评估;教育财政。
为什么马丁·卡诺依采取这样的一个顺序呢?笔者认为马丁·卡诺依在卡书的“教育经济学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导言中清楚地叙述了其中的逻辑。因为,教育经济学起源于人力资本理论,并且在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争论中进入了鼎盛时期。而人力资本理论的构成有两条主线,其一是讨论分析教育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为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带来的各种收益,比如更低的失业概率与更高的收入。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争论,也围绕着受教育年限与高收入、高就业概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行。因此,马丁·卡诺依认为“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存在于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之中”。这样,在让读者或者学习者了解 “教育经济学的历史与现状”后,就应该开始介绍“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而教育收益作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联系的重中之重,也就有必要紧随“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进行讲述了。其二是探讨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所以有必要在介绍完教育给个体带来的收益后,分析“教育、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这是宏观层次的“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而“教育、收入分配和歧视”是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公平问题,严格来讲这依然属于“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的范畴。
可见,卡书共八个部分,除第一个部分是导论性质外,第二至五部分都是围绕“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展开的。最后的三个部分是教育经济学独有的研究领域——教育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评估、教育财政,这三个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笔者非常认同卡书中关于教育经济学的模块构成与逻辑脉络,在自己的实际教学时亦是先突出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再分块讲述教育生产、在职培训与教育财政。
当刚翻开闵维方和马莉萍出版的《教育经济学》时(下文简称闵书),惊讶其内容的逻辑脉络,居然和卡书的布局有非常大的差异。闵书的第一部分“导论”先讲教育的经济学功能的思想脉络史,并且讨论了为何现代教育经济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个时间节点诞生,紧接着介绍教育经济学的分析研究对象、分析方法与研究范式。然而在第一部分“导论”的最后一章竟然是“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形成”,这让笔者一开始有些惊讶——为何是在导论部分的最后一章出现“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呢?
看完全书后,笔者有了自己的答案,闵书是将“教育是一种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作为主线贯穿教育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进而构建起全书的。这就不难理解在第二部分一开始即讲述“教育投资与生产”,因为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必然要有投资的属性、主体等等,教育就必然是一种生产过程。按照这一逻辑,第三部分是“教育成本与收益”就顺理成章了。闵书在第四部分才开始系统描述“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与之不同的是卡书在导论后马上就是“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这看似是闵书将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放在了相对靠后的位置,实质是因为教育经济学需要先让初学者系统地了解教育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教育的人力资本属性,然后一步步推演到第四部分的“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以及第五部分即闵书最后一部分的“教育与社会公平”。
所以卡书的内容构建是一个同心圆,“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作为核心是内圆,“教育生产”“培训”“教育财政”作为独立模块构成了外圆,而闵书是用一根“教育的人力资本属性”主线串起来,且后者更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各界对教育经济学的期待与定位——期望“科教兴国”与“知识改变命运”。就笔者看来,这是闵书最大的一个创新。
因此,国内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与人才培养应该还是对准教育的人力资本属性开展,应继续聚焦于教育的投资、教育的生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教育对个体收入增加的作用等重点领域,并且要敢于从理论上和实证上、从机制上和案例上,努力去揭示教育黑箱里面的真实细节。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教育经济学获得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当然,中国学人要获得理论上的突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思考二:如何在缺乏理论突破的情况下讲好教育经济学的故事?
正如Blaug(1984)所言,目前教育经济学的大多数理论与分析框架都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经济学再未有新的、有影响力的理论或者分析框架出现。这也是为何卡书的英文版是1995年出版的,到现在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在整体理论止步不前的情况下,相信很多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和学习者都多多少少会遭遇外界质疑和自我质疑——教育经济学的未来在哪里?笔者就曾多次遇到很多质疑,包括但不限于“这项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与应用,则这项研究的理论贡献何在?研究价值何在?”,“这项研究只是用旧的理论或分析框架分析一个新的对象,且并未得到与众不同的新发现,这项研究的理论贡献和研究价值何在?”,“这项研究所使用的实证模型是明瑟模型,该模型简单普通且使用极其广泛,这项研究似乎仅仅用不同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则研究贡献和价值何在?”,等等。
闵书虽然并没有正面回应,但第二章“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的很多内容让笔者看到了答案,尤其是第四节中的这句话是精髓:“一项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是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善于把自己观察到的感性现象进行理论抽象,用若干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建立起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框架,也就是把感性现象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笔者认为对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如果相关“理论”很多,而且缺乏若干个核心、主流的“理论”,这意味着这个学科内部本身是不统一的、不稳定的。而按照上述这个逻辑,教育经济学是一个较为统一和稳定的学科,主要理论包括人力资本理论、筛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且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了大部分学科内部人员的认可。
因此,教育经济学在缺乏理论突破的情况下,就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其一,用现有的成熟理论把现实生活中的教育相关现象进行“理论抽象”,完成感性对象的理论构建。其二,用实证研究不断拓展成熟理论的应用对象与边界,推动理论“攻城略地”,进而帮助理论的完善与构建。
上述两点都会对教育经济学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是闵书全书内容贯穿始终的两条思路,一方面通过在案例中引入理论来讲解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知识,另外一方面引导读者用做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视角来学习教育经济学相关理论与知识。这是笔者认为闵书作为一本教育经济学的教材最大的一个亮点。这样,初学者通过阅读此书不仅仅能够学习教育经济学的知识,还能“真刀真枪”开始进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让读者发现自己也可以用学科成熟的理论讲好属于自己的教育经济学故事。
思考三:如何更好发出中国声音、参与构建世界的教育经济学学科?
目前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国际学者构建完成的理论与分析框架进行的,对于世界教育经济学学科的贡献主要还是体现在理论的实践应用与实证检验上。这并非不重要,然而,相信有不少国内的教育经济学家期待能够“更上一层楼”。
对于此,笔者有一个欣喜的发现——除了用“教育的人力资本属性”主线贯穿全书以及重视通过研究来介绍理论、推广理论外,闵书将最后一个部分设定为“教育与社会公平”。在卡书中尽管有很多内容都提到了公平相关的议题,却只是散落在不同的部分与章节中,而闵书将其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进行讲述。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的教育及其政策已经到了需要突出公平的新发展阶段,需要花浓重的笔墨用教育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分析与教育公平相关的议题。因此,闵书最后一部分既描绘了我国新时代的特征,也试图用中国元素参与构建世界的教育经济学学科。而描绘我国新时代特征、构建世界教育经济学学科,是在“双一流”建设、《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背景下,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包括老师和学生)需要主动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思考四:国内教育经济学的初学者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创新获得突破?
在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前几年,国内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生在选题上应该不会遇到太多困难。因为,随便翻开卡书,都能找到一个当时属于国内空白的小题目。甚至无需专门去寻找国内空白的小题目,连大领域的研究都是缺乏的,比如,那个时候鲜有国内学者研究在职培训的经济学问题,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也寥寥无几。
而现在很难随意找到国内空白的小题目了,再加上整个世界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框架进入瓶颈期,这对于国内教育经济学的初学者,尤其是博士生不太友好。然而,笔者认为,还是有一些领域或者方向是值得研究的,且难度并不大。这也是笔者给闵书下一步改版提的建议。
其一,关于教育投资风险的研究需要专门介绍与论述。教育既然具有投资属性,则除了投资主体、成本和收益外,必然会有风险。然而闵书却没有专门介绍教育投资的风险。其实,教育投资的风险和教育投资的收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原理并不难以理解,而且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早在其1964年关于人力资本的著作中就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各种教育成本颇高,社会上还有“教育返贫”的论调,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教育投资风险进行学习与研究。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统计、计量软件的普及,目前对教育投资风险进行实证分析也并非难事。所以,笔者认为,国内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可以加大对教育投资风险的研究,相关教材也要加大力度对风险进行介绍与讲解。
其二,需要对不同子教育系统的经济学议题加以总结与提炼。教育包括很多不同的子系统,不同子系统肯定有不同的特点,必然带来不同的经济学规律。这是国内教育经济学学者,尤其是初学者可以发力的地方。比如,笔者刚刚拿到教职后也思考过如何选题,幸运地很快就选定远程教育进行专门的经济学分析。国内教育经济学的初学者可以锚定某个教育子系统或者环节进行系统深入地经济学分析,进而成为这个主题方面的资深专家。因此,教育经济学的教材也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习者关注教育子系统、各环节特有的经济学现象与规律。
总之,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需要对教育经济学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需要培养更多热爱、精通教育经济学的人才。笔者相信,闵书由于其体系与逻辑脉络的创新,由于其通过研究的视角推进教育经济学学习的亮点以及重视讲好中国新时代故事的使命感,一定会对众多国内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笔者呼吁需要更加重视教材相关的著作出版,尤其是目前国内还缺乏手册(Handbook)类型的书籍出版。手册和教材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并不求完整的体系与逻辑脉络,而是由若干个在某个主题有研究经验的学者根据主题撰写研究综述性质的章节,这些由不同主题构成的章节有对研究的分类、总结与展望,可以帮助初学者深入了解特定主题,有助于初学者选定适合自己的研究主题。比如,笔者之所以选择对远程教育经济学进行深入分析,就是在阅读了埃尔哈南·科恩(Elchanan Cohn)及其同事在杰兰特·约翰斯(Geraint Johnes)和吉尔·约翰斯(Jill Johnes)主编的《教育经济学国际手册》(TheInternationalHandbookontheEconomicsofEducation)中撰写的多产出成本方程后受到了启发。因为科恩(Elchanan Cohn)及其同事在该书中认为,随着美国大学远程教学方式的增加,非常有必要实证分析其中的成本与效率问题。
因此,笔者建议国内应该也有针对性地出版更多手册,可以分主题撰写手册,比如“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规模”“教育公平”“教育成本”等;也可以分研究方法撰写手册,比如定量分析、理论分析、案例分析、制度与政策分析等。
有了更多教材相关书籍的出版,中国的教育经济学高素质人才将源源不断、相关研究将蒸蒸日上。笔者怀着热切的期望,憧憬世界教育经济学学科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获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这些突破是由中国学者做出的,或者由中国学者参与的;即使中国学者没有参与理论上的突破,至少能用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框架讲好中国教育的故事,用中国故事去丰富世界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