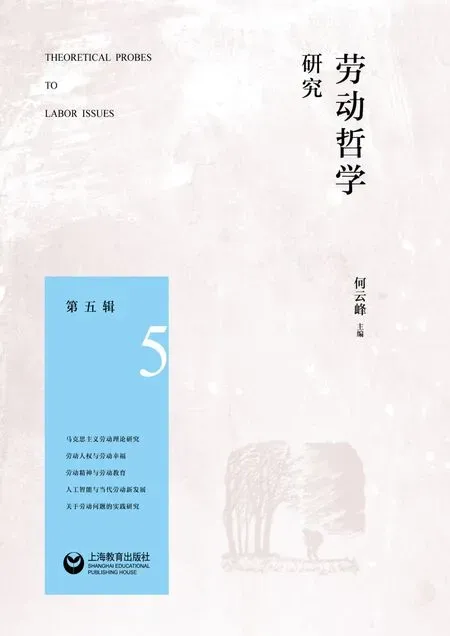从需要及其意识视域综论劳动教育及其具体形态①
刘 欣,潘二亮
人不是影只孤立的个体,而是充满需要的社会体,对于需要的渴求迫使人去寻觅能够满足需要的对象,但是人满足需要的方式不同于动物的直接方式,而是间接的方式——劳动。劳动作为一种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使得人的需要超越了动物的本能需要,并产生了劳动的意识即对象性的主体意识,历史即是这一需要及其对象性的主体意识满足和发展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本文即从这一视角谈一谈当前的劳动教育,我们以为,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目标即恢复“人作为人”的需要及其意识。在论述需要及其意识之前,有必要从逻辑在先的原则论述“劳动”。劳动作为一种活动,它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感性原则”与“对象性原则”,把握这两个原则,将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恢复“需要及其意识”为什么是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目标。
一、劳动:感性—对象性活动
世界一切万物皆在运动之中,动植物则皆在活动之中,而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其独特风格之所在,乃是其以劳动这一活动方式存世。人劳动之独特在于劳动是一种特殊的活动:感性—对象性活动。
(一)感性原则:对意识内在性原则的绝对超越
所谓感性原则,其指明了劳动的主体只能是活脱脱的每一个人,其之所以是一种原则感性,乃因为劳动感性不仅仅是个别的感性,而且是类(本质)的感性,它既是感性的又是超感性的,是作为超感性的感性。人们往往以为(意识)理性是对感性的提升和超越,其实(意识)理性是无所谓原则的,这正是黑格尔的理性(自我意识)劳动之失!理性(意识)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感性(需要),理性(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执行对感性(需要)的本质认识功能。这是因为劳动这种感性活动,本身除了具有生存论的功用之外,它还具有教化的潜能,即形成“劳动的意识”(理性)。我们知道,马克思高度肯定和赞扬了费尔巴哈的功绩,即重新确立了感性原则,但是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简单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528页。即是说费尔巴哈的感性仅仅是“直观的自然感性”,而不是马克思所指正的“活动的劳动感性”。“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马克思把感性原则牢牢地与劳动所直接勾连起来,而黑格尔的问题正是在于把劳动自我意识(理性)化了,“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而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是感性,并且是“感性的社会交往”。马克思从原则高度击穿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内在性的封闭原则,而第一次把感性作为原则性来看待并实现了对于费尔巴哈的根本性超越。马克思用一句话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这就是“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这也就是说,意识的深刻基础是人的生活,生活过程才是意识的绝对原则,因而,马克思的新感性原则实现了对意识内在性原则的绝对超越,第一次把意识建立在作为感性原则的劳动地基上。
(二)对象性原则:功能性主体的绝对必然性
我们说劳动创造人,其实这里的劳动是一种功能性主体,而非实体性的主体,“所谓功能性,是指劳动在显现与建构世界时的作用地位,它只是在功能作用意义下才是本体。功能性本体不同于传统实在宇宙本体论的本体”(7)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1页。。二者根本区别在于,功能性主体的创造是一种建筑学意义上的创造,即它是离不开对象的,也可以说劳动创世是以自然界或人化自然界为绝对必然性的。因此,劳动的对象性原则是指明了劳动作为功能性主体活动,它对于“他者”(自然界和社会界)依赖的绝对必然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的不可克服性,才使得劳动创造出作为对象性本质存在的现实的个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人在劳动中把自己的劳动的意识以作品的形式展现在自己的面前,同时原初对象也以人的方式不断敞开和发现自己的隐蔽的本质,从而成为现实的自然界。可以说“人及其劳动的使命便是唤醒自然潜能,使包括人在内的各个自然物的小环境汇合并不断发展为‘世界’。在‘世界’中,万物以协调配合与相互促进扶助的方式各尽其材性。在使万物各尽其材的同时,人也就尽其(实现)人性”(8)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第59页。。
因此,可以说,劳动的对象性原则是一种现实化的原则,离开这一原则,人和自然界都是在抽象意义即非对象性存在物的意义上言说的,“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1页。,也就是在意识内在性循环中申说的,这也就是黑格尔虽然看到了劳动对象化的哲学人类学价值,但是其对象化只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对象化,感性自然界在黑格尔那里不是在感性原则而是在理性原则下去言说的,因此它在根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妄,而马克思是在感性原则下使用对象性的。马克思第一次同时赋予劳动以感性原则和对象性原则,前者之确立使得他超越了黑格尔,后者之确立使得他超越了费尔巴哈,从而实现了双重超越,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具深刻性的变革。
二、需要及其意识的劳动生成
当前关于劳动教育的研究虽然很热,但是多停留在对于劳动教育教什么和怎么教的讨论,以至于五花八门,随意言之,可谓莫衷一是。而对于“劳动教育”是什么,大家却少有涉及,似乎不言自明。因此,旗帜鲜明地提出劳动教育是什么乃是当务之急。我们认为,劳动教育绝对不是“劳动”教育,把“劳动课”变成“劳技课”,这是对劳动教育非常粗浅,甚至是根本性的错误理解,劳动教育之核心仍在“教育”二字,而教育则是一种理论系统性的对象性的“成人”实践。通过上节对于“劳动”的原则性解读,我们认为,劳动教育的本质旨趣在于在理论层面上揭示并复活作为“感性需要及其意识”存在论基础——“劳动”,说白了,劳动教育就是要教明白为什么劳动创造了作为“需要体与意识体”双重存在的人本身。
(一)人的二重存在及其一元本体
我们常说,人之不同于动物在于人不仅有感官的可见的世界,而且人还有意识或精神世界,也就是说人是二重的存在体,而动物是一重的存在体,但对于这后一不可见的真实存在体是从哪里来的,却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我们以为,对于一个从事哲学事业的人来说,这无异于是对“人”的贬斥与侮辱。因此,为了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我们必须根究其来源于何处。我们以为,人之不同于动物,其根本上乃在于人对待世界方式之不同,这种不同方式不仅使得类动物式生存活动及其需要(比如吃喝拉撒睡)成了人的生命活动及其需要,而且也使得人在意识层面领悟了其生存活动的性质及其需要的意义,并进而产生了历史性的意识。这一方式就是“劳动”。正是劳动这个一元本体活动创造了人的二重性存在,即创造了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特征——需要及其需要的意识。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尝试解读这个创造了人的二重存在的一元本体劳动。
(二)作为需要满足方式的劳动
众所周知,一个生命体要持存下去,就要持续性地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满足生命所需,这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性存在的必然性自然法则,否则它的肉体就将承受饥饿的煎熬甚至面临消解的危险。然而,我们这里关注的重心不在于此,而在于人与动物持存生命体的方式之不同。为什么我们总是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是“人”,而不直接说是“动物”,虽然进化论已经科学地证明了人是从动物(猿)进化而来的,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直接与动物等同呢?这里人与动物存在什么断裂性的区别或者说人之优越性在哪呢?我们以为这一断裂性区别或优越性就在于人满足需要的方式即劳动,但劳动本身为人所独有的合法性并没有因此而确立,这需要具体展开分析,以做实这一劳动之为人满足需要的方式。
由第一节,我们已经知道劳动是一种独特的活动——感性—对象性活动。这里的对象性不仅仅是作为主观目的的对象性需要,而且是作为客观结果的或作品的对象性确证。也就是说,人经由劳动把头脑中观念的存在变成现实的作品,同时更为重要的一个层面,人也在对象性的作品中直观到自己的内在尺度,也就是说人满足需要并不是如动物那样只是吃掉对象了事,而是带有欣赏或美的态度或意向,这一种欣赏或美的态度或意向是对自身内在本质的关照、发现、确证。我们以为,劳动之为人所特有的活动方式,正是在于劳动具有节制欲望和把玩欣赏以对象性作品存在的“我”的本质特征,这个“我”由此不再是“我是我”的简单重复,而是有了实在的内容:“我即作品,作品即我。”
一个人有劳动能力还不行,他还必须踏踏实实地使这一能力由潜在状态变成实存状态,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虽然有劳动能力,但是若离开资本家出钱去购买其劳动力,那么他的劳动能力就无法现实地展现出来,就无法予以对象化,也即等同于“无”。正如我们有句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对于工人来说,没有资本家购买其劳动力的行为,他就将失业,甚至将导致生命的中断即死亡。反向来看,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离开工人活的劳动能力,他就将失去作为资本家的资格,而成为单纯的货币持有者,我们知道资本的唯一目标是为了获得持续的更多的剩余劳动,即以绝对延长劳动时间和以相对提高劳动强度的方式榨取更多由活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资本的绝对主体是活劳动,离开活劳动,资本就无法对象化自身,即增殖自身。因此,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绝对统一基础上的相对对立,它们之间的关系表明了现代性境遇中人存在方式的悖论性,即作为资本雇佣的劳动既创造出了“社会个人”出现的物质前提,同时也创造出了为生存而出卖肉体和灵魂的非人。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实质上满足了资本需要的劳动方式虽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相对于奴隶劳动而言是一种“自由劳动”,但对于作为“第一需要”的劳动,即自由劳动来说,则具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而共产主义革命所要达到的劳动状态,其实就是要使得“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以超越资本主导下的异化劳动现实,在这一层面,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对异化劳动现实的制度正义实施与安排,即以资本的社会所有制取代资本的私人所有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7页。,在这一原则下,每一个人的感性劳动本身成为每一个人的内在需要,那时劳动将完全是一种美的创造性活动。
(三)作为意识生成基础的劳动
人不仅通过劳动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即消费劳动产品,而且还在这一劳动产品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感受到了一种人之为人的成就感、尊严感、幸福感,因而劳动同时创造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意识。即使从现实层面来看,劳动的主导形式虽然仍是一种谋生的不得不的行为,但是通过劳动获得更多的货币工资依然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的基本尺度,人们也会以此作为自己成就感、尊严感、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劳动不仅产生了人的主体意识,而且产生了人关于历史的主体意识,可简称为“历史意识”。笔者以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就是自觉地以历史意识看待整个感性世界。感性世界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恩赐或奇迹,而是人类世世代代劳动的结果,是劳动历史展开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因此,历史就是人的劳动活动的过程,也就是人的自我生产的过程。历史并不是僵死的过去,历史始终是当下的活体,它为当前人的活动提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只有具备鲜明历史意识的人才能自觉、充分地利用先辈们所提供的一切历史条件,进行有使命感的创造。
既然历史就是人通过劳动而自我诞生的过程,那么劳动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以为,这仍然要根据劳动的对象性原则进行解释。劳动的对象性表明劳动要成为一种现实化的活动,它离不开实现对象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历史意识的产生是与劳动本身的原则特性紧密相关的,它植根于劳动对象性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这一社会历史条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本身就是世世代代劳动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劳动对象化的结果又作为当前劳动的前提条件而在场。我们以为,历史意识就产生自对于这一“前提与结果”的辩证认识,劳动的前提同时也是劳动的结果,劳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劳动的前提,所以马克思说,人既是历史的前提,也是历史的结果。由此而知,历史意识其实是一种当代的意识,只有活人才会思考人从哪儿来的问题,只有当人类需要谋求对于当前生活世界本质理解的时候,才需要也只能重思和反省走过的道路,向历史讨教,进一步具体地说,只有真正关切当代人的劳动状况的人,才能形成真正的历史意识。对于历史的重思和反省,无非是充分地认识劳动得以可能的对象性条件,进而充分占有这一条件,从而才能自觉地进行当代的劳动创造。
总之,劳动不仅是人满足需要的特殊方式,而且也是需要的意识产生的生存论根基。劳动教育就是要系统揭示劳动对于人满足其需要的深层的内在价值和重要意义,并复活人的劳动历史观:历史即是人通过劳动而自我诞生的过程。
三、劳动教育的具体形态:“劳动幸福权”的教育
在上一节中,我们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劳动教育之核心任务就是要明了为什么劳动创造了作为“需要体与意识体”双重存在的人本身。但是,这只是从哲学人类学的一般视角进行的解读,我们以为,劳动教育既要有哲学的终极价值的关照,也要有当前的可操作性,即可把它具体化,进而成为人人皆可接受的教育。我们以为,在当前,劳动教育在具体形态上是一种“劳动幸福权”的教育。
(一)何为劳动幸福权
劳动既然创造了作为“需要体与意识体”的现实的人,那么劳动就具有绝对、永恒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因此,劳动权是最根本的人权,维护和保障劳动权即是维护和保障人权。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鲜明的底色是劳动,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为劳动者伸张正义的学说,它有自己鲜明的劳动阶级属性和价值立场。因此,自然可以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劳动人权理论”。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所指和当代形态就是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基础是以下两个来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原初假设:(1)“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8页。;(2)“‘劳动的绝对自由’是劳动居民幸福的最好条件”(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1页。。“既然劳动创造人,因而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所以劳动对人来说就是展现人作为人的类本质的最高幸福获取过程。于是,劳动幸福就是人作为人的初始权利,具有不可转让性。否则,人就不成其为人了。”(14)何云峰:《劳动幸福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8页。由此自然可以知道,保障人们的劳动幸福权就具有了当然的正义性和天然的合法性,而“所谓劳动幸福,简单来说就是指人通过劳动使自己的类本质得到确证进而得到深层愉悦体验的过程”(15)何云峰:《劳动幸福论》,第17—18页。。劳动幸福不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状态,这种幸福是来自劳动的对象化生产,在这一生产中,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确证,人之为人的成就感、尊严感、幸福感油然而生。
但是既然劳动本身就是幸福的,为什么还要提劳动幸福权呢?我们认为,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活动,它的具体展开是需要各种条件的,特别是需要进行制度保障的,否则劳动幸福就只能在应然层面去谈,而无法落实于地。劳动幸福权的提出,一方面,指认了劳动幸福是最高形态的幸福,因为它与人之为人具有本质关联,保障和实现这种权利,就是使得人成为人。再没有比成为人的事业更重要和更崇高的了。另一方面,也是着眼于现实,从维权角度考虑,因为在现实中,劳动不幸福、侵害劳动的行为等还依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正因为这一存在的普遍性,我们才更要高举劳动幸福权的大旗,营造劳动幸福的氛围,为形成以劳动幸福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蓄力量。
(二)如何开展“劳动幸福权”教育
为了有效实现劳动幸福权教育理念,并应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机遇,笔者认为需从三个层面开展劳动幸福权的教育。
1.从资本层面——雇佣劳动教育
当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仅是个比较敏感的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而且更是每一个人不得不面对的生存问题,如何理解二者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和把握劳动如何创造人的当代形态和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劳资之间的对抗关系已经不存在,但是劳资之间的矛盾依然比较尖锐。因此,劳动幸福权的教育离不开雇佣劳动的教育,即离不开理性客观地认识作为资本雇佣的劳动的教育。
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或者从劳动与资本的绝对对立去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扬言驾驭、超越,甚至消灭资本,似乎资本是个邪恶的东西。其实,我们应当从人的具体存在方式去理解资本,资本表征了劳动创造人的当代样态,它相比于奴隶劳动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具有片面性,在资本雇佣的劳动形态下,劳动创造人其实创造的是经济人,劳动的价值只是经济价值,即赚钱,赚更多的钱,劳动仍没有脱离谋生的形态,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对货币物的依赖性上的。
在这一层面,劳动幸福权的教育就是要使得受教育者既看到这种劳动形态的历史合理性,也要以超越的视野看到这种劳动形态的非人性,从而以更大的勇气去为劳动幸福权的实现而不懈奋斗。
2.从价值层面——劳动价值教育
虽然劳动创造了一切财富,但是为什么那些辛勤劳动的人还是富不起来,反而那些不劳动者却越来越富呢?贫富差距及其分化的加剧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一味遮掩总不是解决的办法,我们必须直面这些问题:为什么劳动难以致富?为什么不劳动反而更幸福?出现这些吊诡事实和价值扭曲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必须对此给予充分、可信的解释,以从价值层面重建劳动创造价值的信念。我们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创造美好生活,这本没有问题,一个社会要形成凝聚力,就离不开这些正能量的信念,但是,我们不能为了单纯的凝聚力作用而忽视了最真实的现实,也许正视现实让人泄气,但是不正视现实却可能进一步使其恶化下去,从长远来看,这也不利于发挥正能量凝聚人心的作用。所以,劳动幸福权的教育离不开直面现实的维度——贫富差距及其分化。但要让受教育者看到现实并不是静止的,而应重建新的信心之城,即让劳动者相信劳动价值论,并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并无比珍惜不可转让和剥夺的劳动幸福权。
3.从法权层面——劳动法权教育
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劳动都是人和社会存在、发展、繁荣的源泉,因而劳动不仅具有永恒的必然性,而且具有永恒的正义性,由此,保障劳动及其幸福权本身也就具有了正义性,而这种正义要得到切实维护和保障,必须在法权层面以法的形式保障劳动幸福权不受侵害和剥夺。劳动法权教育不仅是关于法的普及教育,而且是关于法的根基的认识教育:法及其正义性所系在于劳动及其天然正义性,同时劳动法权教育能够有效地在思想意识层面消解资本法权及其意识形态的强势地位,笔者认为,这是劳动法权教育当前最重要的使命。
总之,要切实保障和实现劳动幸福权,首先必须从实现劳动幸福权教育的突破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