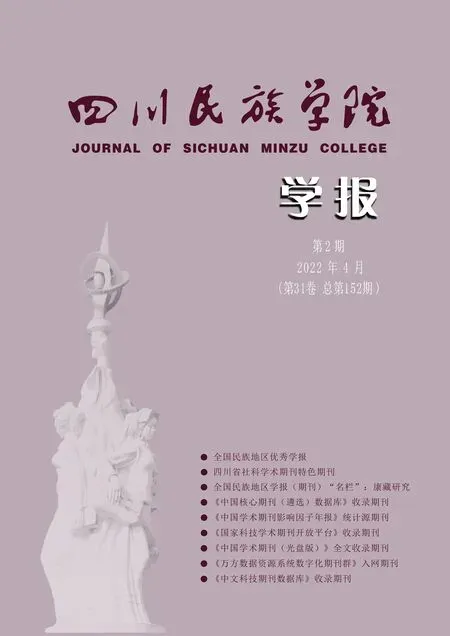鱼通历史进程考
郭建勋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近十多年来,民族走廊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费孝通将走廊地带民族文化接触的历史与现状调查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研究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1]同时,费孝通似乎还有更大的期待,即通过民族走廊的研究,以扎实的民族志成果向世界表明:实现不同社会和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目标,是如何成为可能的。(1)费孝通在《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中,强调“文化自觉”“和而不同”在构建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学科基础,以及如何应对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文明冲突等问题上的作用。费孝通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遗产,也是他对百年来人类学在认识世界方面诸多努力的总结。他说,我们既要打牢人类学的学科基础,也要为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作贡献。他在《文化自觉与和而不同》中提出,对于“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交流模式的探讨,各国的人类学家尽可以见仁见智,提出不同的研究办法。上述内容分别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若要在走廊地带的多民族互动与文化接触的中观层面,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等理念,也离不开大量微观层面的调查研究。在今之四川康定东部大渡河峡谷的沟壑之间,分布着用其语言命名的“贵琼人”(gu33tcha55)。这群自称gu33tcha55的人,在当地汉语方言里又称为鱼通人,(2)按照语言学家的分析,贵琼语的分布区域,曾包括泸定的岚安乡,可能还包括天全的西北部分地区。“贵琼”一词除了语言学界外,多数人并不熟悉,本文使用鱼通及鱼通人的概念。现居住在康定的姑咱镇、时济乡、鱼通乡和麦崩乡,当地称这一区域为下鱼通,(3)今天姑咱镇所辖的瓦斯沟一线各村,不再属于下鱼通范围。康定的三合、金汤和捧塔则称为上鱼通。自元代后,鱼通一词就频繁出现在汉文史籍中。据考证,鱼通曾经是折多山以东广大地区的统称。[2]208贵琼语与大渡河下游的尔苏语,雅砻江上游的尔龚语、扎巴语,中游的木雅语、纳木义语, 金沙江中游的史兴语、普米语,是语言学家拟构语言树的重要语料,[3]也是费孝通所称的藏彝走廊地带“围棋子”式文化现象的生动体现。在这里,我们既可看到早期南北向的多民族迁徙流动的痕迹,也可以看到东西向汉藏文化交流、交往和交融过程。
一、鱼通地望
古之鱼通较今之鱼通的地域可能宽广得多。方积曾著有《鱼通塞外杂诗》六首,所写皆是康藏高原景色。(4)方积(1761—1814),字有堂,今安徽省定远县人。诗作一:“平沙漠漠草芊芊。落日牛羊万幕烟。亦有参差楼观影,大都邻着白云边。”诗作二:“平芜初长马初肥,大小传呼晓合围。羌女能歌羌妇舞,夜深灯火载熊归。”因为当时将折多山内称为鱼通,而折多山以西自然就被视为塞外了。也有人写道,“渔通者,古国名也。距蜀省会之西南千里。附近有城曰打箭炉,即今西藏出入咽喉……过泸定桥一站,地名瓦斯沟,为渔通口,径山皆产金矿……渔通娃拾之亦知货售,故吴楚客旅于此处,专收细金。约有数十字号……再一站,始抵炉城。”[4]傅嵩炑认为,“鱼通,古地名也。打箭炉一带,皆称为鱼通,嗣各土司区分部落,另更地名,惟一小部落之名仍称旧,有一土司焉。地居明正咱里之北。宣统三年夏,同明正土司等遵部案改流,将地归并打箭炉管理,西康建省后,川康于折多山顶各界,打箭炉仍应归川。”[5]任乃强认为,(东部狭谷区与中央盆地区合建一县),惟此县治,不能不设于偏西之打箭炉,是为缺点。此部地方,古昔通称鱼通,清代称西炉,清末置打箭炉厅,后改康定府……如果分置,应改称此为鱼通县,即切今地,且存古名。[2]209今之鱼通土司属地有邛(土人读若昂)州之名,邛即鱼通,乃汉武时内附者,鱼通部落广大,今之明正、冷边、沈边、咱里皆在鱼通之内,[6]咱里土千户始祖阿交, 鱼通人, 明洪武二年投诚。(5)《泸定·档案县志》和《打箭炉厅志》均有记载。上述诸说如若不谬,古之鱼通,指折多山以东的区域,后来鱼通辖地慢慢缩小到今天的下鱼通地区。
20世纪30年代后,国内外形势使得康藏地区地位骤升,大批官员、学者、科考队员、游历者纷纷涌入,鱼通也被官员、媒体和文人“发现”并赋予“神秘”“独特”色彩。1930年,一位官员写道,鱼通为康定八区之一,其民语言风俗,都是自为风气,既不同于汉人,又不同于康民,简直等于另一民族了。[7]1934年,川康考察团的上海记者写道,鱼通虽全为熟夷居留地,然因道路险阻,即川康边区邻近各县居民,亦鲜有至者,中外学者,则更裹足不前。[8]
二、从异域到边地
古代鱼通较难考实其地望。石泰安(R·Stien)所述,从汉、隋、唐诸代以来的各断代史、还是古代敦煌写本和近代藏文文书中,都记载过沿汉藏边界地区散居的诸民族部落。[9]1石泰安引述塔菲尔(Tafel)的观点,高董(GOdong,SGo-LDong)是鱼通(离打箭炉不远)河(即金川)畔,位于罗米昌沟(Romi-Tchangou)(6)此处译为“鲁密章谷”可能更为妥当。“鲁密章谷”指的是今天四川省丹巴县境地内的区域,“鲁”在藏语中与“绒”同义,有农业的意义,而“密”(有的写为“米”),在嘉绒语中有“人”的意思,“鲁密”即是从事农业的人之意。在这一区域的人,因这一特点而被视为一个群体。明代的二十四村地,为天全六番宣慰司所辖的鱼通口外三十六种姓的鲁密区域。二十四村话接近藏语康方言。清时设有鲁密章谷土千户和土百户,属明正土司管辖。有意思的是,在鱼通南部边缘瓦斯沟对面的山间小村也叫章谷,从瓦斯沟西起直到丹巴境的山脉称为章谷梁子。藏语中章谷意为“群岩之首”,丹巴则意为“下部群岩之首”。和瓦斯沟之间土著部落的一个藏文名称。塔菲尔补充说,无论是汉人、西藏人,还是金川居民,他们对于该土著部落的语言都一窍不通,但与巴旺(Bawang)的藏语(7)据语言学家调查,巴旺话是“藏缅语族中的一个独立语言”,又称尔龚语。很相似。[9]70而鱼通在藏语中称为“Gotang”,汉语音译为“鄂通”,发音与“高董”接近。
如果塔菲尔的观点不谬,高董、鄂通及鱼通等族群的名称,似乎还有进一步阐释的意义。如许多藏文史籍记载,猴子与岩魔女结合后,生下一个小儿子,然后这个小儿子到有鸟群的树林的猴群里,与众母猴这伴,一年后繁衍到四百个与他类似的小儿。享用了观音加持的五谷、黄金和珍宝,变成人类的猴子越来越多,又因争夺谷物产生不和,人类就分成了四个部落,即塞(se)、穆(mu)、东(ldong)、冬(stong)四个族姓(8)格勒认为,骨系在汉籍里被译成了氏族、血统、人种或族系,等等。按此说法,这里的族姓也属于骨系的另一种译音。参见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22.。吐蕃之人大多是这四大族姓派生出来的。[10]石泰安认为,这些边缘部落是吐蕃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些部落还起到巨大的历史作用。
前文所引的“高董”部是有杂居背景的,高董是“土著部落的藏文名称”,是“舅氏”家族杂居而形成的在汉藏边界诸多董族人中的一类。现在藏族地区所说的“鄂通”即是石泰安文中论述的藏族早期之董族人,“鄂通”在康藏地区的地位似乎很高。正如石泰安讲到,西藏中部和西部的贵族家庭都竭力想与某一个“原始部族”发生联系,一般都与东北部的部族有着系谱沿革关系。
就上述有限的资料而言,鱼通也算历史悠久。属于东部集团的鱼通人似乎也有辉煌的家谱,有可以追溯的著名先祖。然而这个祖源传说,似乎有掩盖历史上藏东与吐蕃间的阶序,视康东为“边缘”的嫌疑。“所谓‘康’者是指边地而言,如同‘边地小国’被称作‘康吉结称’。”[11]另一种说法中,这些部落集团里,有的被卫藏视为“小弟”或“坏家族”,他们是被驱逐到边地。[9]29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吐蕃向东发展,一路东扩,占领今天的甘孜大部后,又奴役当地人并“为王前驱”,直向松州(四川松潘)进攻。在这个过程中,康藏高原的世居部族被吐蕃先用军事力量,尔后用藏传佛教等文化手段加以融合。[12]而六氏族的兄弟起源故事,也是这一重要文化手段之一。正如张云所言,为了确认吐蕃征服高原诸部这一事实,并对高原诸部融入吐蕃制造理论根据,在后世的藏文史书中出现了高原各部同一起源甚至是同一血缘亲族的说法,就是吐蕃人来自“六氏族”或者“六人种”的说法,其意义在于给通过武力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制造一种合法的理论根据,为吐蕃王朝在高原地区的一统伟业而张目。[13]后来,这种“起源传说”起到了培养群体感情,身份认同的作用。然而,兄弟故事长期存在于藏文史籍中,一般人无缘知晓神圣典籍中曾经的兄弟家在何处。兄弟传说倒为那些能够利用宗教经典的人,提供了攀附或想象其辉煌过去的依据。
三、从徼外到归流
从中原的角度看,在汉之前,大渡河流域乃至整个川西高原,史籍对其地望记载甚少。汉时开西南夷,始有模糊认识,唐时则为羁縻州治,元、明、清则由“听我驱调”的土司治理。清末的改土归流,最终完全将其纳入到一统的国家管理体系。
汉武帝时开发西南夷,中原王朝的力量也首度进入川西高原的徙、筰、冉駹,(9)“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并在其地设置郡县。(10)“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见《史记·西南夷列传》。而大渡河流域之鱼通,大致在筰域。所以称为筰者,按任乃强的说法,其地山高谷狭,水深而激,难架桥梁与设舟渡。其住民远在数千年前,已创绞篾为索,相对斜张于狭谷两岸,用木壳系皮条骑人,挟之滑翔以达对岸之法,即所谓筰。称其地“筰域”,称其人“筰人”。筰在两汉世,又分为若干部分。[14]196-197《后汉书》记载,筰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筰都县,元鼎六年,以为沈犁郡。至天汉四年,并蜀郡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15]沈犁郡的范围,曾包括了今康定、九龙、道孚、炉霍县境,因为当时的部落贪赏请所设,加上皆为牧部,人无定居,县不能立,后来又废去,并用旄牛都尉主治。“旄牛徼外”意味着,旄牛县是汉王朝在蜀郡西部实际控制的最后一个县,旄牛县以西,汉朝就无法控制。[16]115这表明汉王朝曾与徼外夷发生过相当程度的联系和交往。而沈犁郡及后设的汉嘉郡,成为蜀郡及“徼外夷”的重要的缓冲地带,由此而分为徼外与徼内进行管理。[16]117-118徼内夷即指青衣县所主的汉人,即汉朝直接控制的以夷人为主体的少数民族。
任乃强认为青衣县治,即今芦山县城,汉晋时县境,即今芦山、宝兴县境及康定之上下鱼通地区(康定县城以东之河谷地区),包有今天芦山河谷、宝兴河谷的全部,与大渡河谷的一段。[14]199而汉之旄牛县故城在今汉源县九襄镇(即汉原街)。[14]202任乃强还认为,在旄牛部以北,相当今大渡河上游鱼通、孔玉、金汤、大小金川一带,在汉代被称为“三襄、污衍”等部落,也是筰夷,但隔于青衣、冉駹、楼薄等部,极少与内地有交涉。[14]197《后汉书》载,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污衍种并兵三千余人反叛,攻蚕陵城,杀长吏。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蚕陵,杀长吏。今之鱼通,可能处于汉朝直接控制的青衣县境内。即便如此,鱼通地域因大山阻隔,远离青衣县城而为边缘地带,成为汉朝统治时徼内与徼外的模糊地带,因之也会与徼外夷部举事。
元代后,鱼通等大渡河流域诸地进入王朝的视野,其地望及名称较之前代来说,更加清晰。鱼通作为地理名称,可能来源于当时所居人群的自称,后被汉字转写进入史籍。再后来,当地人也接受了这一名称。经过外来力量,进而改写当地人的文化记忆。大渡河流域纳入元代的视野,与忽必烈南征大理有密切关系。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循大渡河南下,鱼通、长河西和岩州的土酋率先迎降。(11)见《元史·世祖一》卷四,以及任乃强、泽旺多吉《“朵甘思”考略》,载于《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42页。同时,元初宋军坚守四川,元军久攻不下,只能“斡腹入寇”,先取四川周围各部,迁迥包抄川中宋军。由于长河西、鱼通、岩州的率先迎降,加之该区域处于西连东接的重要战略地位,显然受到新兴的元朝重视。元朝希望该地区起到稳定本方,招抚西番诸部,加强控制。故沿边地方俱先于盆地内各地投元,其设治也较早。
而后,元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位,招降了“岩州诸蛮”,(12)参见《元史·列传第十六》中的相关记载。1265年,授雅州碉门安抚使保四虎符。公元1266年,元朝又在岩州等地招抚官吏军民。(13)参见《元史·志第十二》的相关记载。公元1267年,鱼通岩州等处达鲁花赤李福,招谕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14)参见《元史·本纪第六》的相关记载。公元1279年,碉门、鱼通及黎、雅诸处民户,不奉国法,议以兵戍其地。发新附军五百人、蒙古军一百人、汉军四百人,往镇戍之。[17]公元1298年,设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宣抚使司。(15)参见《元史·本纪第十九》的相关记载。元史记载,在鱼通等地先后设有如下机构: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鱼通路万户府、碉门鱼通等处管军守镇万户府、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
《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朝廷派遣礼部主事高惟善招抚长河西、鱼通、宁远诸处,“明年还朝,言:安边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坚,虽远而有功;恩威未备,虽近而无益。今鱼通、九枝疆土及岩州、杂道二长官司,东邻碉门、黎、雅,西接长河西。自唐时吐蕃强盛,宁远、安靖、岩州汉民,往往为彼驱入九枝、鱼通,防守汉边。元初设二万户府,仍与盘陀、仁阳置立寨栅,边民戍守。其后各枝率众攻仁阳等栅。及川蜀兵起,乘势侵陵雅、邛、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随碉门土酋归附。岩州、杂道二长官司自国朝设,迨今十有余年,官民仍旧不相统摄。盖无统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袭旧弊故也……且岩州、宁远等处,乃古之州治。苟拨兵戍守,就筑城堡,开垦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远者畏威而来归,西域无事则供我徭役,有事则使之先驱。抚之既久,则皆为我用。”[18]礼部主事高惟善曾言其便有六,一是可拓地四百余城,得番民二千余户,不仅保黎、雅,蜀将永无西顾忧。其二在岩州立市,通过商贸来牵制边地,并加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其三用长河西、伯思东、巴猎等八千户为外潘犄角,然后招徕远者,如其不来,八千户近为内应,远为向导。经蛮夷攻蛮夷。其四是在岩州设仓易马,利于茶马互市。其五在岩州设市,可倍收番民运茶之税,而鱼通、九枝蛮民所种水陆之田,递年无征。若令岁输租米,并令军士开垦大渡河两岸荒田,也可借给屯定官军。其六缮修开拓碉门(今天全)至岚安的道路,以便往来人马,巩固边防。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朝廷采纳高惟善的建议,在岩州设卫,修缮茶马官道,把雅州茶仓改设在岩州,在岩州茶马互市。这给岩州及鱼通带来了深刻影响,鱼通开始向屯军纳粮。(16)在《明史·列传第217》里,有详细论述。
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凉国公蓝玉击破西番蛮人遣指挥须胜回京献捷,并奏“岩州、杂道蛮人攻围大渡河千户所,亦被讨平。”[19]82-83后建昌酋月鲁帖木儿叛,长河西诸酋阴附之,失朝贡,太祖怒……礼官以帝意为文驰谕之。其酋惧,即遣使入贡谢罪。天子赦之,为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以其酋为宣慰使,自是修贡不绝。初,鱼通及宁远、长河西,本各为部,至是始合为一。
有明一代,鱼通及周边地区就被纳入到严格的朝贡体系之中,所贡方物多为马匹,朝廷曾数次制定相关规定。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三月申令: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头目剌麻番僧南合并乌思藏阐教王遣剌麻领卜车等,违例朝贡……及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每年亦量数放入。[20]661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四月申令:其长河西、董卜韩胡二处,一年一贡,或二年一贡,遣人不许过百。[20]688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九月,由于乌思藏、长河西及松潘、越巂三处地界相连,易于混淆,难以辨别。于是规定:其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朵干(甘)及董卜韩胡诸宣慰司,亦各给勘合六十道。其入贡道经四川,比号验放一如例。若该贡之年偶值道梗不通,后不许补贡。[20]759
清世祖定鼎燕京之前一年,即后金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天全六番,乌斯藏董卜、黎州、长河西、鱼通、宁远、泥溪、蛮彝、沈村、宁戎等土司,庄浪番僧,先后入贡,献前明敕印,请内附。[21]这表明鱼通等地在明代时乌斯藏管辖范围内,受制于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及其子孙管辖。
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七月,“天全六番、乌斯藏董卜、黎州、长河西、鱼通、宁远、泥溪、蛮彝、沈村、宁戎等土司各缴前朝敕印以降”。[19]18《清史稿》中也有“辛卯,天全六番、乌思藏等土司来降”的记述。[22]此材料与前引史料相似,(17)“……是为西藏通好之始。于是阐化王及河州弘化、显庆二寺僧,天全六番,乌斯藏董卜、黎州、长河西、鱼通、宁远、泥溪、蛮彝、沈村、宁戎等土司,庄浪番僧,先后入贡,献前明敕印,请内附矣。明年,世祖定鼎燕京,混一宇内。”(见《清史稿·列传第312》。)只是时间差了9年,但9年前是“献前明敕印请内附”,9年后是“缴前朝敕印以降”,其意义自然不同,这似乎意味着从此以后长河西及河东诸土司,由口外变为口内,与王朝联系进一步加强。当然,这有其特殊历史背景。明末统治康区的是青海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委派的第巴营官,营官势力极大, 土司俱向其俯首听命,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不甘受营官欺凌, 故清初, 清王朝势力刚到四川,就急去投诚, 希望依靠清朝的势力与营官抗衡。[23]这就是大渡河附近土司为何在清初由“内附”到“以降”的真正原因。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丹怎扎巴率十三锅庄投诚,经行介承袭其职,并颁换印信,印文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24]清初,长河西土司控告营官侵夺土地时, 清廷虽再三向第巴声明打箭炉原是内土司所辖之地,但除了派员会同勘明土司与营官所属地界外,未有行动。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明正长河西土官蛇蜡喳巴被喇嘛营官喋巴昌侧集烈打死,于是清政府才乘机派大军进讨, 诛昌侧集烈, 复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 乘胜招抚口外瞻对等五十余部, 一万二千余户,把和硕特势力驱逐到雅砻江以西。[19]168-179在西炉之役时,鱼通在进军的备用线路上,化林营参将李麟建议,清军除三路齐进之外,还可另拨兵,分三路进攻,则可以擒献渠魁。一路经由宁番,一路由鱼通,一路由宁越。[19]175可见当时的鱼通处于两军交锋之地。而西炉之役中,烹坝、冷竹关、大岗,均为战略要冲。而西炉之役最为艰苦的战役,就在大岗,即今天冷竹关和瓦斯沟背后山间台地,此处为今天鱼通的南部边界。
清嘉庆前,鱼通为穆坪董卜韩胡宣慰司所辖,这与明中叶后日益强悍的董卜韩胡极力扩张辖地有关。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朝廷曾宣谕,令其永息争竞之风,共享太平。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朝廷再次向其强调了各安本分,不要自生嫌疑,再起衅端,其子孙永享太平福。[19]587-588于是,清初,今之上下鱼通,尽为董卜韩胡所据。《雅州府志》记载的木坪土司西界连打箭炉,冷边土司北至岚州山岗与董卜交界。《四川通志》记载木坪土司西至鱼通蛇勒(舍赖、舍联)、章谷(瓦斯沟河口北岸台地, 今姑咱镇章谷村)交冷边土司界,冷边土司北至大冈(今姑咱镇大岗村,为瓦斯沟背后的山腰村落)交木坪土司界。嘉庆前,鱼通在木坪土司处认纳“夷赋”,木坪土司“夷赋”中,鱼通认纳之草粮五十石,每石折征银一两,共五十两,由木坪土司统解布政司。[24]427嘉庆年间,木坪宣慰使丹紫江初(甲凤翔)之两土妇争嫡,妻包氏率子甲天恩移居鱼通,然嫡庶之争在木坪与鱼通两地进行。道光五年(公元1825)包氏亡于鱼通,建有节孝坊。包氏之名分,仍用原封号“诚勤巴图鲁木坪宣慰使司”,而木坪本寨仍以当然嫡系承袭。甲天恩之子甲木参纳楚料理鱼通事务,竭力效忠清廷,在争嫡夺印案中,争得“鱼通长官司”的认可。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十一月,经川督鄂山请铸“鱼通长官司”钤记,十二月,因剿办四川清溪夷匪出力,赏长官司甲木参彭措、故宣慰土司甲木参多结(木坪土司)子甲木参龄花翎,表明清廷正式确立甲木参彭措为鱼通长官司长官。[25]至此,鱼通才有独立的土职封号,并世袭,与木坪宣慰使司并立。但鱼通与木坪争嫡夺印之争未了。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八月,都察院奏:“四川鱼通长官甲木参功布等,以夺袭吞业被诬激变”等情,遣抱告赴该衙门呈控,此案穆坪土司承袭宣慰使早已断结,何以该长官复以夺嫡具控。其逃犯喜力乐七力自戕一案,既非该长官谋害,何以坚参生朗多吉复行翻控诬陷,是否该土司恃强凌弱,抑或该长官扶嫌妄控,均应彻底根究。[26]总之,木坪与鱼通之间,关系时缓时急,矛盾一直存在,并时有冲突,鱼通民间尚有许多传说,表明木坪与鱼通之间的冲突。同时,在另一种划分体系中,鱼通土司又属于明清时谓之嘉绒十八土司之一,鱼通与嘉绒的语言不同,但因地域相连,文化交流频繁,相同之处甚多。[27]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0月,鱼通划归打箭炉厅专辖。宣统三年(1911年)6月,鱼通改土归流,上交缴印,土司制度虽废除,但鱼通土司势力依旧。民国时,土司甲安仁因握有武力,被任命为团总,康定土兵营营长。民国元年(1912年),甲安仁重赂镇抚府,要求恢复土司制度,被拒绝,又远奔北京请复旧制,也未得逞。清末民初,鱼通为康定县之东路,不久废路为区,鱼通为康定县之第七区。民国24年(1935年),鱼通设6个保。民国32年(1943年)康定县实施新县制,改区为乡,鱼通改称鱼通乡,仍辖6保,政权设置名称虽时有变更,但其统治仍是废土司甲安仁。
1951年7月,甲安仁困死在前溪菩萨山花石包岩洞中,显赫一时的末代鱼通土司,终结于20世纪中叶。1951年7月,撤原6保分设麦崩、前溪、舍联、时济4个乡。1952年6月,在麦崩建立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并建立麦崩、前溪、舍联、时济4个乡政府。1957年改区政府为区公所,乡政府为乡人民委员会。1959年8月,原麦崩纳脚五村归金汤管辖。
四、结语
透过鱼通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鱼通是早期民族交流、经济活动的通道,也是徼内与徼外、化内与化外、口内与口外,关内与关外的接触地区。历史上因时因事而来的各色人等,或沿大渡河谷早期民族南下北上通道,或循北部的明正、穆坪两土司世代联姻通好之路,或沿南部的碉门岩州的小路,飞越岭至泸定桥,过瓦斯沟之大路的茶马古道,辐凑而至。因而鱼通是汉家史官所谓的“夷番蛮羌”活动区域,也是西来之蕃人与东来的熟番或汉人的接触、流动和交往的区域。鱼通地望在史籍中由模糊到清晰,由异域到边地,体现了鱼通在制度、经济、文化和认同等方面逐渐与内地紧密整合在一起的历史必然性。如果忽视鱼通小区域与大社会之间的历史互动过程,而用一种固定和静态的眼光去审视和剖析今天鱼通人的来源,文化构成,或者截取历史,将其近代转变和国家化过程放置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或在政治经济学“中心——边缘”的权力格局中去思考,结论恐会失之公允。而要理解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怎样确认自己的身份,以及更高层次的族类和国家形象,鱼通从异域到边地,再到直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性,需要从更为长久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文化基础上去理解。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