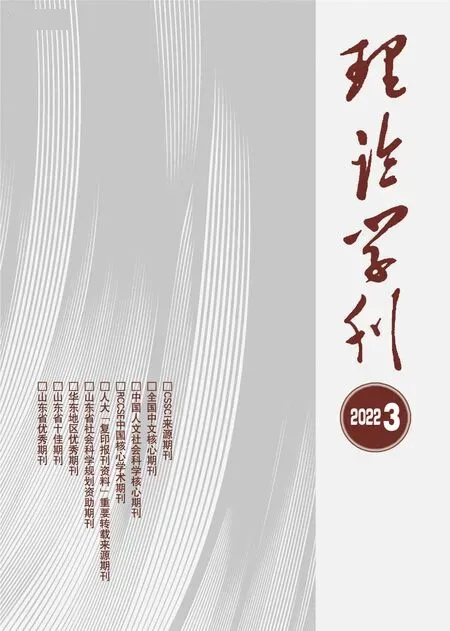南方史诗的文化资源供给与中华民族新史诗的书写
刘 洋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尽管新历史主义的思潮冲击了宏大叙事的权威性,源于对正史可能筛选的隐忧,元语境和元叙事讲述历史已然不能满足学人们的需求,寻求碎片化历史的延展和演绎似乎成为新的导向,但这种陌生化效应最终仍然指向重建新的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史诗性作品的书写榫合史诗性现象的生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民族新史诗是史诗性现象的生成,同时也是史诗性作品的书写,指向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宏大且严肃的叙事。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随处跃动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诗。”(3)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未来最好的把握,是开创更美好的未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史诗研究伴随“正风俗以正人心”的“述古俗,镜今俗”思路,历经“拿来主义—反思解构—本土重构—反哺世界”的发展轨辙(4)刘洋、肖远平:《南方史诗的文化精神》,《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27日。,见证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全过程,南方史诗所主张的安身立命、和谐共生、求真务实成为中华民族新史诗书写的重要文化元素。
一、南方史诗与中华民族新史诗的价值榫合
钟敬文先生认为,“史诗的价值不是历史的,而是文化的,每一个民族的史诗都有其特殊性”(5)钟敬文、巴莫曲布嫫:《南方史诗传统与中国史诗学建设——钟敬文先生访谈录(节选)》,《民族艺术》2002年第4期。。史诗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某一地区和某一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历史记忆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从史诗的产生到文本的解构,直至关注史诗叙述、抒情、意境构筑等各种审美情感的认知,我们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到整体、又重回个体的历程。劳里·航柯认为,“不同文化群体对同一史诗的认知存在极大差异,文化持有人不仅能够理解持有史诗的重复叙事,亦能够在这种特殊表述中获得认同,他者则难以感悟史诗精神”(6)[芬兰]劳里·航柯:《史诗与认同表达》,孟慧英译,《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劳里·航柯认为,“对外来的耳朵来说,这种冗长无味的、重复的叙事,都在特殊群体成员的记忆中通过他们对史诗特征和事件的认同达到崇高辉煌”。敖东白力格在梳理史诗学的发展历史时,将劳里·航柯的理论概括为史诗认同论,认为史诗认同论忽视了对活态口头史诗的经验探索,强调将社区听众的认同表达与史诗歌手表演相联系,对于研究口头史诗而言是非常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参见敖东白力格:《普通史诗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这种群体认知差异无疑是“文化的比较”的立论逻辑。具体来讲,同一史诗的变异性和不同史诗的差异性必然要求比较的研究,30多年前倡导的“文化的比较”已被学界广泛接受(7)杨兰:《贵州民俗研究70年: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在使用比较的方法时,应关注其最大的困扰是比较对象定义的不确定。因此,准确理解史诗表述、合理看待史诗文化与清晰凝练史诗价值,不仅需要回归族群生活场景与仪式场域,亦需要多维度感悟史诗想象建构的源流。
中国原本没有史诗的概念,亦少史诗的研究。近代以来,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实,传教士合儒、补儒、超儒和贬儒的文化输入,民族集团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文化精英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从厚古薄今到以今证古的摇摆,以及大规模接受西方话语体系以求救亡图存的时代风潮之下,史诗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难以绕开的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民族史诗得以大规模采录,北方史诗带和南方史诗群在“到民间去”的田野调查中确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史诗类型学不再取例西方学界的英雄史诗定义,形成了以叙事主题和口头程式为划分范畴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8)朝戈金:《朝向21世纪的中国史诗学》,《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10年第1期。。尽管历经文化自证与田野确证的南方史诗已然达成某些认知上的一致,但是学界引入的西方术语与跨学科视域的不协同、西方话语体系与本土文化传统的不一致、史诗研究者参与观察中他者视域与文化持有人自我审视本我视域的不契合、史诗研究中非此即彼的研究假设与史诗诵唱中亦此亦彼的生活实践的不匹配、史诗采录文本与史诗诵唱顺序的不吻合等等,致使符合中国话语的诠释体系建构仍面临诸多的难题。
进入20世纪以来,历经各种社会思潮的跌宕起伏,史诗研究作为西学研究的滥觞,已成为语言文字学、现当代文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难以回避的议题。中国学界不再讨论史诗的历史事实问题,而更多关注史诗的历史真实与当代价值。同时,西方文学批评家也并未停止对史诗的反思,他们或是以全知视角下的宏大叙事框定史诗,将叙述的诗等同于史诗(9)杨鸿烈在关于诗学研究流变轨辙的阐述中引用了文奇斯德的论述,其云:“诗人要是置身事外,把他己身以外的那经验的世界都表现出来,就是普通所谓的客观的方法,其结果就成为‘叙事的诗’或称‘史诗’。”详见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82页。,从而使史诗的边界得以扩大;或是将诗人置身物外的“客观的诗”(10)这里的所谓客观并非绝对意义的价值中立,而同样是充满作者情感的,这种考量显然偏重文人书面史诗。划分为叙述类和戏剧类,叙述类的诗也即“有音节的故事”和史诗(11)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或是统合史诗边界的讨论,但作更为细致的处理,将史诗逐项分解为民间口传史诗、文人书面史诗和准书面史诗(12)朝戈金:《朝向21世纪的中国史诗学》,《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10年第1期。;或是反思古典学的史诗视域,认为荷马样板是明显束缚,应打破传统的史诗边界(13)刘守华:《〈黑暗传〉:汉民族神话史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刘守华在讨论《黑暗传》时引用了劳里·航柯的论述,其云:“我希望希腊史诗刻板的模式,一种在现实行为里再也看不到的僵死的传统,不该继续统治学者的思想”。,不能再以希腊史诗为史诗的唯一标准。西方视域与中国观念交织互动,中国观念的树状知识网络亦在不断分化,不同的声音源于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受到欧美学说深刻启迪和影响,在早期研究乃至当前的一些研究中多有借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启发意义,但事实上忽略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质,与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学术导向不符,与客观公正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符(14)刘守华:《再论〈黑暗传〉——〈黑暗传〉与敦煌写本〈天地开辟已来帝王纪〉》,《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刘守华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是在欧美学说的启迪下建构起来的,其不足之处便是常以国外理论框架削足适履地诠释中国文化,从而将一些真正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对象列入不屑一顾的另类,形成文化误读。。具体来讲,理解南方史诗与中华民族新史诗的书写,不仅需要西方视域的启迪与示范,更应强调中国观念的表达与凝练。
二、从立足到立族:中华民族新史诗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力量
安身者当身有所宿,立命者当心有所归。人类的初级需求无非是生活有着落,身定而心安。南方史诗大多系统阐释了宇宙创生和人类起源,或源于浪漫的想象,或来自生活的经验,均可从诗性的语言中感受到早期人类生存立足之艰难。
(一)立足的生存需求
在进行南方史诗的比较研究时,可以有这样一种极为深刻的感受,即神人关系的调整使得诸神的混沌之力被分解,空间含混造成的神人世界的杂乱无章至此消解,神退出了人的生活世界而隐遁于人的精神世界,为人的社会秩序建构让渡空间,人类的生产和发展须依靠自身的劳动与创造。众多的史诗都将人类的起源与水紧密联系,水孕育生命是先民们最早期的体验和认知。原始人类多临水而居,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至农业时期,干旱和洪涝对当时的人们都是致命的灾难。在灾害面前,人类的力量十分弱小,无力抵抗成为当时的常态。不过即便力量悬殊,人类也在不停地寻找解决的办法。在长期的抗争中,人们将洪水与干旱等自然灾害融入了史诗内容中。但是在这些叙述中,人们将灾难的起因归结为人类的行为触犯了天神,比如因为浪费粮食、心地邪恶、不知礼义廉耻而遭到天神的惩罚,进而灾害发生。洪水或者干旱就成为了南方民族甚至是世界民族中最为普遍的内容,从洪水或干旱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被认为是天神的选择,也是人类生命力的象征。
洪水泛滥前,人类为天神所造,经历了洪水或者干旱之后,生存下来的人类一般都具有善良、正义、勇敢的特征,也即通过灾难筛选出来的人类与之前的人类有较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灾难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象征。人类从孕育到出生,在母体中经过了9个月的长养,逐渐具备人形,后经历分娩的挤压而终于落地成人。由此,人类的诞生必然要经历考验,只有通过考验才能继续存活。这对于人类认识自己、明确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了解人类发展史,均有重要意义。在洪水泛滥或干旱之前,人类与神的关系密切,历经洪水或干旱之后,神退出了人的世界,人开始依靠自己的能力生存和生活。因此也可以说,要实现人神分离,人类必须经受考验;通过了考验,人就从神的创造物转变为人自身,这个阶段也是人类从本能思维转向理性思考的重要时期。人类的童年时期都是在家长的庇护下生活,这与天神主导人类生活一样,而人一旦长大成人,他们就需要自己谋生,通过了成年礼仪考验的人才真正脱离了孩童状态。关于灾难的叙述是族群对自己所处群体的一种肯定,认为祖先的能力和品行得到了天神的认可,且经由天神的引导,祖辈才得以繁衍发展,形成今天的景象。相关叙述中祖先与天神的亲密关系凸显了这一群体的神圣性,同时期望后世的人们能够得到天神的更多庇佑和眷顾。在彝族史诗中就有相关的内容:洪水淹死了兄弟几人,其中最小的那一个在白发老人的帮助下得以存活,并与天女结婚,繁衍了各族祖先。类似的叙述还存在于侗族、傣族、苗族、畲族等的史诗之中。经历了灾难后的人类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依然秉承善良、坚毅、勤劳的品格,比如在壮族史诗《莫一大王》中,莫一帮助族人修路平地、围河造湖、布雨救苗;在苗族史诗《亚鲁王》中,亚鲁带领族人御敌迁徙、制盐炼铁、耕种养殖;在彝族史诗《梅葛》中,人类依靠自身力量制造工具、养蚕纺丝,通过劳动获取生产生活所需;在傈僳族史诗《古战歌》中,英雄木必扒率领傈僳人开辟怒江河谷;在傣族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中,人类为了生存,种田地、捕动物、制造瓷器和铜器。南方史诗传递的是战天斗地实现丰衣足食的历史记忆。史诗中的人物重视生产技艺的提高、强调生产技能的传承、向往生活水平的提升,他们认识到,只有自身强大,才能获得长足发展的能力。
(二)立族的时代需求
南方史诗70多年的研究轨辙伴随了本土文化遗产话语体系和理论建构的始终,取例西方但又被赋予了中国观念的史诗延续了五四以来知识界寻求一种能够提升和强化民族精神并为现代民族国家所认同的宏大叙事,南方史诗因此不仅呈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样态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价值阐释。回溯历史,公元前5世纪,世界范围的诸种文明进入轴心时代,创造性思维集体迸发,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贤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以孔子删定“六经”计算,至今已历大约2500年,中华文化在数度革新中得到传承弘扬。直至近代,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走向何方”和“中国文化走向何方”成为时代议题。晚清革命派作家肯定民间文学价值,采用民间歌谣、弹词体等形式创作了《猛回头》《精卫石》等文学作品,尝试宏大叙事,鼓吹社会风潮。彼时,“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的文化弱势心态广泛存在,中国学者迫切需要证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以回应时代诉求和民族觉醒,中国有无史诗的论辩遂成为文化自证的重要一环,舶来术语“史诗”在本土适应中与史诗性、诗史、叙事诗等概念相互交织,边界难以划定,资料匮乏和理论薄弱导致史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沿着古希腊史诗、印度史诗、北方史诗和南方史诗的梯次递减,且厚古薄今成为常态。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老舍先生将《格萨尔》定性为史诗,一举打破了“中国没有史诗”的西方话语,中国话语的史诗研究方才得以进入本土话语建构,由此,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亦被赞为史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家们的史诗情结和宏大叙事理想成为常态,诸如强调“史诗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印记”,“同史诗一样,……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总是联系着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15)胡良桂:《史诗与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2期。。史诗的范畴在实践中被泛化了,在大众语境中,“史诗性”通常被直接用“史诗”替代,史诗性现象、史诗性作品被广泛接受,这应该是史诗研究与实践落地的范型。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使命。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它在危难中敢为人先,在发展中敢闯敢试,在实践中实事求是,将最宝贵的资源放在最需要的地方,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百年辉煌发展史,展现了中华民族新史诗的伟大力量,书写了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壮丽篇章,创设了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力量底色。
三、从依赖到共生:中华民族新史诗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大致经历了“依赖—利用—共生”三个阶段。“依赖”源于人类力量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弱小且有限,必须依靠自然获取生产生活物资,又恐惧于某些自然现象所带来的震撼力,从而产生敬畏甚至崇拜。“利用”是指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取用于自然,这种取用如果不加节制,可能会超过自然的承受能力,从而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共生”强调“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16)《荀子·天论》。,将人视作自然存在物,认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不仅回答了人类在宇宙中为自身定位的问题,也指出任何个体和群体都不能忽视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人类需要在不同群体间实现资源的公平配置,建立更加合理的生态秩序。
(一)以神为主的自然创生
对宇宙本源的追溯是与人类社会的阐释和发展相伴始终的。陈连山在讨论宇宙起源时认为,对宇宙的追溯始于原始人时期,因为原始人相信事物诞生的同时,其本质业已确定,宇宙起源是任何民族思维萌发和思考本源时都不能避开的话题,任何神话体系必然包括宇宙起源(17)陈连山:《宇宙起源》,《前线》2017年第1期。。关于起源问题的探讨,中国哲学界原本将其理论起点框定在有文本记载的原始五行说和阴阳说,而早于这之前的哲学思想则处于空白。伴随口头文学的采录,带有感性色彩的早期哲学形态渐露其面,各民族中阐述原始先民关于宇宙本源思想的创世史诗成为探寻中国哲学的源头。严格说来,每一部史诗中都包含着原始先民的经验累积,他们在与自然抗争和相处的过程中,惊讶于自然的力量与造物主的神奇,进而产生了对自然的依赖感和敬畏感。人类自诞生伊始,便通过劳动获取生产生活资料并改善生活,但由于力量的局限,人们的创造能力并不强,创制的物品也并不丰富。待人类的创造力与创制物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他们才会开始思考世界万物是如何产生的,于是出现了化生、生育等对万物的想象。人类从自然中孕生,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从自然中获取新知,也从自然中获得生存资料,于是就对自然油然生发出强烈的依赖感。
南方史诗讲述了人与自然的同源关系。在以神为主的化生中,包括了巨人化生、神人化生、动物化生三种结构模式。人与自然均系同源,命脉相连。“化生”一词有转化新生之意,史诗中通常是以天神、神人或者动植物的躯体化生万物,无论是巨人化生、神人化生还是动物化生,它们在阐释宇宙起源和万物产生的时候,必定是与人的身体相关联。在古老的彝族文献《宇宙人文论》中,彝族先哲就将万物的来源归到一位披着金甲的老人身上,其云: “(老人)拄着金拐杖,站立于宇宙之中,默念了三句箴言,一查宇宙北方的金坑,顿时泛起大水,从四方漫到中央,水的根源从此产生啦。老人侧身转向宇宙的东方,查到整整齐齐的大森林,折下树枝到处撒,四方和中央都长起大树,树木的根生从此就有啦。又往南方挖个金坑,坑里出现白龙,青雾漫成火烟,红岩伸出火焰,火根也就产生啦。”(18)《宇宙人文论》,罗国义、陈英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在人类进化的历史过程中,人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还未能将自己与自然分开,人类不断探索和发现自然,在自然中获取生存发展的资料,在捕食狩猎中熟悉了动物的身体构造,加之人类和动物死亡之后,肉体腐化归于泥土,而泥土中再生出别的物种,于是人们将死亡看作是一种再生的形式,动物化生、神人化生和巨人化生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观察死亡与再生后的想象。维柯便认为人类“对未知事物,都是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19)[美]维柯:《新科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9页。。大多数的创世史诗都认为远古时期天地混沌不分、一片漆黑,没有日月雷电,不分东西南北,后来神人用自己身上的污垢或者骨肉做成天地之间的梁柱和其他自然物。这些描述生动地反映了南方民族“灵魂不死”的观念:天神和巨人在开辟天地的过程中不幸死去,于是尸体化生为世间万物。这种创生观和演化观是原始先民关于世界的普遍本质或宇宙本源问题的最早认识,它与哲学本体论的思考是一致的(20)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化生的想象源起于各族先民对万物由来的追寻。原始先民对万物的由来抱有强烈的兴趣,他们通过自我想象建构出万物由来的解释体系,其中以巨人身体或动物身体化生万物最为普遍,比如哈尼族有天王叫龙牛化生万物的叙述、普米族有杀马鹿化生万物的叙述、彝族有老虎化生万物的叙述、怒族有杀虾蟆造万物的叙述等。
史诗中的化生叙事源自对万物起源的解释,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形上求索。同时,化生也反映出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需要类型化处置混沌世界,并以此回应对世界的自我认知。这种类型化处置需要长时期的探索和更新,这种探索和更新的过程也是秩序确立的过程。叶舒宪在研究实体化生时便认为,万物起源伴随着原始生物的肢解,“一个原始巨人或生物的肢解和毁灭带来了宇宙万物的诞生。原始整体的分解导致丰富多彩的世界,其数字抽象模式为从一到多”(21)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页。。类型化处置混沌世界,抑或以化生切割混沌,可见混沌的切割绝非是无序的,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呈现,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认为的,人的身体自然而然的是空间的核心,“空间是围绕着人的身体而组成的,可以向前向后、向右向左、向上向下延伸”(22)[美]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1卷,吴晓群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于是先民们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按照形态、功能的相似性,将各器官与宇宙万物相对应,如眼睛与天上的日月相对应、四肢与支撑天地的撑天柱相对应、身体毛发与花草树木相对应、血液与奔腾的江河湖海相对应,这些对应因此具有一种天然的关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对应是人类对“天—人—时空”的一种系统的超验性的解释和经验性的复证。人类身体的各部分与自然之间的对应,自然成为化生的内层逻辑,并在时空系统中得到反复验证,这样,史诗的真实性、神圣性与合理性混糅为一体,成为文化持有人认识宇宙、理解宇宙、建构宇宙的底色,也成为文化持有人认识事物、理解事物和建构事物的基础。人们对开天辟地的思考是想象宇宙和认识宇宙的第一道门槛,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意识到了人体与地形空间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23)[英]埃蒙德·利奇:《文化与交流》,郭凡、邹和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世界秩序得到了建立,神与神、人与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明晰,不过这些关系界限都是人的主观行为,是人类自己对自然的一种切断。
在德昂族民间创世神话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中,人从自然中来,由茶叶化身而成。在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中,人诞生于石头,与德昂族史诗一样,亦认可人源于自然的观点。彝族支系阿细人的史诗《阿细的先基》认为泥孕万物,人与万物同源。苗族史诗《古歌》称蝴蝶妈妈生下人祖姜央、雷公、蛇等,亦说明了人类与自然的同源关系。生命的延续离不开自然,限于认知和抽象能力,南方史诗中的生态观念是先民对客观世界的直观感受和感性认识,它需要借助可触、可及、可感的具象材料方能完成表述,这些内容在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的同时,在年复一年的述说中实现了对后世的训诫,也实现了生活经验的累积与文化的传递。
(二)以人为主的英雄创生
在南方史诗中,天神创造宇宙且具有无限神力,这种神力可以创造一切、主导一切。在傣族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中,天地是天神英叭用身上的泥垢创造出来的;在彝族史诗《梅葛》中,天地是神人用蜘蛛网和蕨菜根创造出来的。毛南族史诗《创世歌》则讲述了天地乃神人法术的创造物,其云:“混沌刚刚开天辟地,未曾有我们世界,混沌下来到地面,修整天下做得到,他的法术很高强,摇得天地动,手向山上指,石头就垒成山头,泥巴就拢成田垌,水就积满池塘,火就燃烧成堆”(24)《中国民间创世史诗集成·广西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551页。。壮族史诗《创世歌》称颂道:经过混沌、汉王、天王等三代人族的繁衍,遭遇洪水泛滥的盘和古两位神繁衍了人类,“盘就成了娘子,古就成了郎君”,他们“结亲三年半,落得只生个磨石仔,砍成三百六十片,给乌鸦拿去野外撒,给鸟拿去四面分,三早七天后,就沿旧路去看,头颅变成个县官,嘴巴变成个皇帝,身躯变成了壮人,肠肚变成了瑶人,颈脖变成了毛南人”(25)《中国民间创世史诗集成·广西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551页。。在侗族史诗《嘎茫莽道时嘉》中,天和地均是天神萨天巴所生,“萨天巴生地取名叫‘嫡滴’,萨天巴生天取名叫‘乌闷’,地是摇篮为母题,又生诸神在上苍”(26)杨保愿:《嘎茫莽道时嘉》,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尽管都是讲神人创生,但是在这些史诗中,神人是力量和智慧的代表,寄托了人们对征服强大自然的一种幻想。
事实上,史诗对于天神创造型的宇宙起源的叙述,表明了原始先民历经自然崇拜转向天神崇拜和英雄崇拜的过程。神灵与英雄是人类对自我的一种期许,期望自我能够拥有超凡的力量主宰自然。在英雄崇拜阶段,人们崇拜的对象从完全神转向了半人半神。在多神崇拜体系中,各路神灵分管的领域不同,具有的能力也不同,比如山神能守护山林、雨神能播洒甘霖。职能分工的神灵体系实质上被赋予了人类社会中管理者的职能,可以说,这些半人半神的英雄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出现了分化。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多是循环往复和形式多样的,故而神便是多种多样的,这样就有了多神崇拜。当这些神名统统汇集在本氏族的主神——创世英雄身上,那么这个英雄便具有了多种神通,便成了一尊超级大神,即超人。所以,英雄崇拜与多神崇拜是紧密相连的,可以把多神视作英雄诸功能或能力的分化,两者实质上是互补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英雄或是多神,其产生的关键都不再是人类对自然力、对死亡、对睡眠之类的异样心理,而是与险恶的自然环境搏斗的人类活动全过程。人们在这些活动中不仅意识到自己的主动性,而且尤其希冀自身力量无限扩大,从而能在人与自然力的博弈中成为强者。英雄崇拜与多神崇拜反映出人已完成了从向自然力祈福到增强自身力量的转变。史诗中的开天辟地洋溢着勇于开创天地和群体协作的精神,充满了对神化了的劳动能手的颂扬,并对后来社会的发展长期产生积极的影响,诸如布洛陀、槃瓠、木布帕、英叭等都成为各自民族的精神象征。开天辟地的内容反映出先民已然具有类比的思维能力,他们将自然、动物与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并根据这种原始思维的逻辑,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神、人、动植物之间可以互相变形,这正是化生万物的思想根源。
还应当注意的是,在史诗的叙述中,创世一旦完成,也就代表着创世神的隐退或者消失,新的神灵系统随之出现。创世神的消失或者隐退实质上与人类框定自然为何之后的忧虑相关。创世神化作宇宙秩序的载体,其行动很有可能会带来秩序的再度混乱,甚至是回归到混沌状态。具体来讲,无论是时间的划分还是空间的稳定,时空的有序与确定的秩序仍有可能受到混沌力量或其他力量的影响,创世史诗中的洪水灭世便是混沌复归的一种叙述——被构建的世界秩序再度遭到破坏,世界复归于混沌之初的茫茫之水的状态。
(三)与自然共生的互利模式
张岱年认为:“天是人伦道德之本原,人伦道德原出于天。在今日观之,在天为根本的,自意义言,亦是在人为根本的,因人为自然中之一物。”(2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97页。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天与人的关系,是人类在宇宙中为自身定位的问题。天人一体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人生存于自然,也必将与自然共享共存共生。两者既是物质关系,也是一种道德关系,人类的活动是作用于自然的,因此,如何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乃是人们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各民族的天人一体观主要在万物起源的观念中有所表现。在史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的是同源关系,天神创造了万物,包括植物、动物、天地、人类,所以人与自然是同源关系,彼此命脉相连。生命的延续不能离开自然,这是人们在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料的实践经验,也是人们生态伦理观念形成的基础。基于自然孕育生命的认识,人们明白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这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也有所体现,例如人们会选择靠山临水的地方和有平坦田地的地方,这都是人们依据自身生存生活所需而设置的约定,不乏科学合理的因素。
史诗从很大程度上说,是对人与自然原初秩序的阐释。自然界中的具体的实物,除了具有客观的物质外形而外,还是人类的想象物,是物象与心象的重合。当史诗运用其特殊的符号和图示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这些蕴含在史诗中的片段表述和零散的逻辑法则,随着对史诗秩序的理解和整体的把握,会不自觉地转化为人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模式,并要求人们将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唇齿相依也体现在互帮互助上。在苗族史诗《金银歌》中,人类为了造日月,到处寻找金银,哪知金银躲在了深潭里,各种动物都来帮助人类运出金银——“螃蟹咬金银的根,低处两棵咬断了;还有两棵长得太高,是谁帮他咬?打鱼郎鸟帮他咬。他俩是一个妈妈生的,还是两个妈妈生的?他俩是一个妈妈生的,所以才一同挖开了金银”(28)马学良、今旦:《金银歌》,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74—75页。。在另一篇苗族史诗《古歌》中,螃蟹帮助拉出金银,遇见龙王吓得丢了魂,是榜布的父亲作法招回了螃蟹的魂。这些叙述体现了人类与动植物命运一体的思想,是史诗所展现的一种万物一体的共生关系,也是共同体的生态价值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市场经济和工业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好,如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须持续向自然索取,但正是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即便与发达国家存有发展差距,我们国家仍然选择与自然共生。这是史诗性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85页。自然生态是事关全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面对全球环境治理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行动,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上,用原初智慧为共生开启了保障。贵州从江自古以来便利用稻鱼鸭系统发展循环经济,使生态得到保护,人民也富裕了起来。石光银在毛乌素沙漠植下了100余里的绿色长城,创造了特有的治沙+致富模式,带领群众过上了富裕的生活。退耕还林、防沙治沙、蓝色海洋计划、碳达峰、碳中和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中华民族在自然生态关系中所作出的努力。
四、从共鸣到共识:中华民族新史诗为文明互鉴注入中国精神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30)屈原:《九歌》。南方史诗中的英雄重视发展生产,崇尚和平安宁,从不主动挑起战争,但是一旦敌人来犯,他们必定挺身而出、毫不退让。中国有许多开创崇高事业的英雄人物在民间崇拜中升格为地域神或职业神,诸如黔中屯堡的汪公、潮汕地区的龙尾爷,以及百工神中的鲁班神、杜康神,等等。这些英雄多被归为伟大的祖先一类,他们参与创造和发明生产生活资料、建立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在一些史诗中,英雄被视为氏族部落的首领、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阿巴白构率领百姓逃脱魔兵追杀、寻找水草丰厚的地方安营扎寨,并最终战胜戈人,为族群寻得可以安居乐业之地繁衍生息。在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中,数十代英雄的铜鼓王誓死捍卫作为族群希望和象征的铜鼓,在立族的征程中抛洒热血,成就了后世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些英雄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令人感佩。
(一)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共鸣
南方史诗不仅呈现了先祖们的生活轨辙,亦是传统与现代链接的媒介。民族精神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被本民族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民族心理、气质、品格的综合体。
在民族精神框定的场域中,文化生境、文化累积和群体存在共同建构了民族精神,培育了文化共同体。这些文化共同体的外在特征和心理素质构成了民族精神的表象世界。民族精神并非是一种固定的意识,而是变化的、动态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得益于礼仪的、伦理道德的聚合力,这些都在史诗中得到了变形的折射和朦胧的暗示,至今仍显示出独具的特色和顽强的生命力。在壮族史诗《莫一大王》中,莫一为了帮助乡亲,不惜广种竹子、培植神鞭,用神鞭将山石赶到海里,从而使众乡亲从此不再翻山越岭去种植。在史诗中,莫一是能够沟通神人的英雄,具有御靴飞行的神力。高尔基曾说:“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神并非一种抽象的概念,一种幻想的东西,而是一种用某种劳动工具武装着的十分现实的人物。神是某种手艺的能手,是人们的教师和同事。”(31)《高尔基论文学》,林焕平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所以在史诗中,神人、英雄就显得与众不同。既然是英雄或者神人,他们在史诗的叙述中所从事的工作必然就与史诗故事的脉络主线相契合,如射日射月、智斗妖魔、移山填海、操纵风雨等,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人民谋幸福。他们为了实现理想,敢于战斗、不惜牺牲,可以说与民族精神紧密嵌合,深刻影响了诸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模式,进而影响了诸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形态。“在古代中国的社会意识里,值得崇拜的不是‘力’,而是‘力’所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道德性质”(32)孙正国:《非遗保护的文化力量》,《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25日。。南方史诗作为中国精神的原始象征,也为道德色彩所浸染,史诗中关于人与自然道德的系统讲述,导致了人的精神的实用倾向、经验化以及创造性。当然,实用化不等于庸俗化,注重应用价值的实用倾向不等于实用主义。它既不排斥原始崇拜的知识,也不排斥科学的因素,而是使崇拜内容实用化、科学的知识应用化。
支配着中国历史的根本精神是对德的尊崇,因此,活跃在这种崇德气氛中的是一些富于道德色彩、对文明历史和人民生活有重大贡献的史诗英雄。例如,在苗族史诗《亚鲁王》中,亚鲁遵循长幼观念,不愿与兄长发生矛盾,在兄长挑起纷争时,他选择带领部族离乡迁徙。在彝族史诗《支格阿鲁》中,为了救出母亲,支格阿鲁经受了重重考验;为了帮助百姓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他完成了修天补地、除风降雾、制服妖魔等一系列壮举。史诗传承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忆、谱系的把脉和生活的向往,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当下史诗辐射区域的人们,仍然传承着传统道德观念,在尊老爱幼、长幼有序、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氛围中践行史诗精神。史诗的活形态决定了史诗文本、传承群体、仪式场域及文化符号等均能立体、生动、活态地还原史诗本真。史诗展演不仅是先祖生活轨迹的反映,亦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媒介。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它集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为一体,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与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南方史诗中的顽强坚韧、忠贞不渝、自强不息、务实平等等精神,历经锤炼和洗涤,为新时代民族精神的锻造提供了丰厚滋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洽的南方史诗精神在当下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未来仍然能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二)理性到实践的精神共识
在庆祝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贾芝先生发表了“史诗在中国”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将中国56个民族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的发掘和研究成就作了生动的介绍,从而将中国史诗推向了世界舞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33)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在南方史诗的语境中,祖先、神、英雄彼此并无明显的界限,祖先既可以是神,也可以是族群的英雄,所以南方民族的图腾崇拜和祖先神崇拜也即英雄崇拜(34)何光渝、何昕:《原初智慧的年轮:西南少数族群原始宗教信仰与神话的文化阐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3页。。伴随人类意识的产生,神和英雄一直是生活实践中最有影响和意义的现象之一(35)胡志毅:《神话与仪式:戏剧的原型阐释》,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无论是在神的时代还是英雄的时代,人类的力量都非常弱小,神和英雄被认为是特定时空中历史的开创者;同时,史诗中的神和英雄往往将自己献上历史的祭坛,以换取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他们又往往以受难者的形象受到先民的崇敬,从而成为荣格所说的“理想的集体表象”(36)[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他们多被归为伟大的祖先一类,是始祖神;在一些史诗中又被视为氏族部落的首领,以及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这些人自然会被视为英雄。以射日月母题为例,南方史诗中有许多生动的英雄形象,诸如彝族的支格阿鲁、瑶族的密洛陀、苗族的亚鲁王、壮族的布洛陀、布依族的布杰公、水族的牙巫、布朗族的顾米亚等等。
英雄崇拜的盛行是原始社会向部落、部族、部族联盟和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反映。在部落时期,祖先崇拜只在小范围内产生影响,而当部落中的祖先崇拜与史诗英雄之间建立起关系,祖先崇拜演化为英雄崇拜之后,其影响范围就变大了,成为了更大群体中的精神力量。古老的神性英雄让位给了人性英雄。英雄虽死,但能重生,他们被附会为具有神力的人物在群众中传播,成为凡人的榜样,更多人希望通过模仿英雄的行为,让自己也成为英雄。与此同时,各体作品中也塑造出更多具有神力的英雄,英雄于是而有了超越族际的性能,加进了某些“公共”的属性,具有了更为宽广的活动空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深化,英雄越来越成为提升社会凝聚力的一种精神性需要。
新时代,各行各业数不清的英雄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披肝沥胆、抛洒热血。比如张桂梅,这位被无数学子称为张妈妈的人,用她的生命践行着先烈们的遗志。她将江姐视作自己一生的榜样,带着她坚定的信仰和对党对国家的忠贞,在华坪女子高中通过燃烧自己的生命点燃了1800多名学子的希望。比如钟南山,2003年非典肆虐,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治危重病患,奔赴疫区指导抗击非典,为战胜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初,新冠肺炎暴发,耄耋之年的钟南山毅然“逆行”直奔武汉,为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被誉为“生命卫士”。饥饿曾是中华民族最深痛的记忆,袁隆平亲历过这段悲惨的历史,所以他时刻不敢忘怀,坚定地扛起了对家国和民族的责任,誓以稻米填满天下粮仓,为彻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和全球饥饿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南方史诗的文化精神,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和世界文明的演进轨辙中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五、结语
章太炎曾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37)《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重视实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在生产的重复与四季的轮回中,中华民族对于恒常和变易的体会更为深刻。变易是常态,恒常才更为久远。所以,史诗并非是到现实世界之外寻找心理慰藉,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生命的存在和生活的幸福,强调通过自身的能动性拼搏和创造。在当下,英雄们用信念和热血传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务实理想,不断书写着中华民族新史诗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