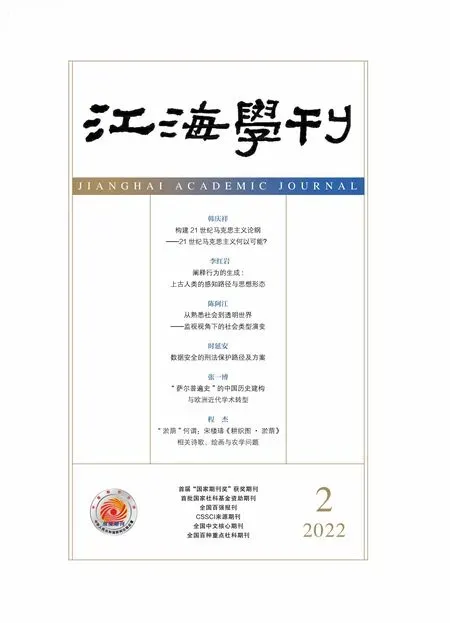在历史与艺术之间*
——胡适与王国维词学离合考论
彭建楠
胡适与王国维同被奉为导引20世纪词学新变的关键人物,两人治词的渊源承递与同异比较,至今仍是一个引人遐思的话题,但其中尚有被误解之处,也有未被充分注意之处。在诸如后人抱有莫大兴味的南北宋词高下论,意境说、境界说比类等话题上,胡适与王国维并未有深度切磋,两人的词学之合,反倒是基于历史态度与实证方法的默契。而当20世纪30年代《词选》《人间词话》被热议时,胡适却指出与王国维在历史与艺术之间最终选择的不同。胡适的刻意疏离,不仅给出了寻绎他与王国维词学离合的线索,更指向了词学行进方向的分野。本文拟对胡适与王国维的词学因缘做全面梳理,考察王国维与胡适的词学离合及后续的学术史回响,或也能引起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二省思。
从“词的起原”出发:胡适与王国维之合
胡适《词选》的批评观点与《人间词话》有“出人意外之如许相同处”,(1)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3期。但胡适、王国维在词学批评上的交流并不密切,这点由胡适在王国维生前竟未见过《人间词话》便可见一斑。胡、王之间唯一一番有案可查的词学讨论,是围绕“词的起原”展开的。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共同关注,提示了我们考察两人词学的另一角度。
先回溯这番讨论的因由始末。1924年,胡适因编纂《词选》而计划写作关于“词的历史”的长序,先作成《词的起原》一节,并将初稿呈送王国维指正,(2)胡适《词的起原》:“初稿写成后,曾送呈王静庵先生(国维),请他指正。”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563页。又按胡适:《一九二四年的年谱》(载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23—192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词的起原》作成于1924年。又按刘烜、陈杏珍辑注:《胡适致王国维书信十三封》(《文献》1983年第1期),其中五、六、七封论《教坊记》成书时间及《忆江南》《杨柳枝》《天仙子》《菩萨蛮》等调的创制时间,落款日期分别为1924年10月10日、10月21日、12月9日,综合看来,胡适写成初稿并呈送王国维应在1924年10月,而两人的讨论则持续到当年12月。胡适与王国维遂书信往复,各执己见。胡适把词的起源定在中唐时期,即胡夷里巷之曲流行之时。词的起源与音乐繁荣有关,是学术史公认的看法,胡适的创见在于强调民间的主导作用:“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词,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文人是守旧的,他们仍旧作五七言诗。而乐工歌妓只要乐歌好唱好听,遂有长短句之作。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一班人都是和倡伎往来的;他们嫌倡家的歌词不雅……于是也依样改作长短句的新词。”(3)胡适:《词的起原》,《胡适文集》第4卷,第560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民间乐工歌妓的艺术实践,也就不会勾起文人的兴趣,更不会有文人竞相填词的盛况。
胡适虽言只是“疑心”,但他对这一推演是极为看重的,因为这是他建构“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三段论,并在此历史框架下进行词学批评的原点,因此希望得到王国维的支持和确证。但不想王国维在回信中提出了两点商榷之处。第一,胡适不认可朱熹的泛声填实字说,“嫌他说的太机械”,(4)胡适:《词的起原》,《胡适文集》第4卷,第558页。并举出词调里仍有泛声的证据来反驳。按胡适的猜想,何处填实字,何处添泛声,都是乐工歌女自由调配,而非要把泛声全部填实。王国维虽然肯定胡适的看法,但认为胡适的猜测只是为朱熹之说“下一种注解”,(5)胡适:《词的起原》,《胡适文集》第4卷,第561页。二说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承衍关系。第二,胡适认定词起源于中唐,但王国维指出《教坊记》已收部分词调曲,而《教坊记》作者崔令钦为盛唐时人,因此从音乐的角度言,词之起源应前推到盛唐时期。
胡适对第一点并未有异议,但并不认同盛唐说,遂又针对王国维的举证作了一番推理和证伪,他依据《乐府杂录》《杜阳杂编》等佐证《教坊记》所收《天仙子》《倾杯乐》《菩萨蛮》《望江南》《杨柳枝》等曲都是中唐后新制,由此推测崔令钦生平记载可能有误;而即便崔令钦是盛唐人,《教坊记》很可能经后人补缀,因此《教坊记》所收未必都是盛唐旧有曲调。王国维再次回信:“如谓教坊旧有《望江南》曲调,至李卫公而始依此调作词;旧有《菩萨蛮》曲调,至宣宗时始为其词,此说似非不可通,与尊说亦无抵牾。”(6)胡适:《词的起原》,《胡适文集》第4卷,第562页。或许因为缺乏文献证据,王国维绕开了崔令钦生平与《教坊记》成书时间的问题,但坚持至少《菩萨蛮》《望江南》两调是盛唐教坊旧曲,因为《乐府杂录》《杜阳杂编》只是记载了两调被制成曲子词的情况,而制曲与制成曲子词的时间未必同步,乐调的创制流行稍早于乐工文人的填词活动,也是符合情理的。不过王国维也指出盛唐说与中唐说并无抵牾,可见王国维对胡适依调填词起于中唐民间的假设,大抵是同意的。
胡适对这次讨论的结果十分满意,欣然宣称“王先生承认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以后”。(7)胡适:《词的起原》,《胡适文集》第4卷,第562页。在胡适意中,中唐说已全然驳倒了盛唐说。但王国维恐怕并未放弃盛唐说,再则他举《教坊记》之例的本意也并非是反驳胡适。在王国维看来,词体是合曲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所以词调音乐何时兴衍十分关键,因此不能只关注依调填词发生的时间节点,盛唐说与中唐说结合,再加上胡适对民间创作现场的还原,才能更加完整地解释“词的起原”问题。显然胡适没有深彻地理解王国维的用心,他的结论也有些自说自话。但这番讨论仍反映出胡适与王国维相通的词学研究理路,即以考察词的历史作为进入词学批评的前提。
王国维在词的历史研究上曾投入相当的精力,这点由他对词调音乐文献的熟稔便可知。1908年王国维在撰写《人间词话》之际,辑成《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王国维对词体兴衍的考索,也体现在了附注中。按王国维辑本韩偓《香奁词》注:“唐人诗、词尚未分界,故《调笑》《三台》《忆江南》诸调皆入诗集,不独《竹枝》《柳枝》《浪淘沙》诸词本系七言绝句也。”(8)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该注还提到,韩偓词《忆眠时》未脱五言诗体,又刘长卿曾仿韩偓六言诗(“春楼处子”三首)作填《谪仙怨》曲,也可证诗格词格混同的情形。但在韩偓集中,《金陵》长短句交错,“尤纯乎词格”,(9)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250页。又可见词格独立的趋向。王国维言唐中叶后诗成“羔雁之具”,并由此论诗词升降,(10)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91页。与词格、诗格逐渐分界的历史时期正相对应。从历史考证到进入批评实践,王国维治词的脉络是分明可辨的。胡适以《词的起原》一文向王国维请教,恐怕能勾起王国维早年的记忆,胡适的中唐说与民间起原论,也能帮助王国维丰富早年的看法。
综上,王国维与胡适一前一后介入词学,不约而同地把研究“词的历史”当成词学批评之前的预环节。即便有具体意见上的分歧,但他们在这一研究阶段行进的方向是一致的。较为遗憾的是,1925年,胡适未及作更完整深细的词史书写,待“见解更老到一点”,(11)胡适:《〈词选〉自序》,《胡适文集》第4卷,第547页。便因中英庚款事宜而出访英国,后又游历欧美诸国,只在1926年旅行途中匆匆完成了《词选》的编选,“词的历史”研究也只是完成了起源部分。王国维1927年自沉昆明湖,胡适自此再没有和王国维纵深讨论词学的机会。但两人短暂的词学交流中所折射出的历史态度的一致,不应被学术史忽略。五四之后,伴随西方文学史方法论的大量输入,国内学者最初多有拿来主义的心理,如陈钟凡比照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勾勒中国文学演进的线索,(12)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文哲学报》1922年第1期。就是对西学的直接移用。而胡适和王国维深入本国文学史内部还原词体兴衍的轨迹,的确能为后继者们提供可循实以行的路径。
辑佚与实证:胡适与王国维的隐微联结
除了历史态度的相合,王国维与胡适在方法论上也有相当的默契,不妨从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说起。赵万里1925年至清华担任王国维的助教,日常协助检阅书籍并处理清华研究院购书事宜,因此“向静安先生学得了目录学”。(13)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转引自刘波:《赵万里先生年谱》,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9页。在1927年即王国维自沉当年的秋天,赵万里着手搜辑宋金元佚词。王国维曾辑佚唐五代词,赵万里将稽考文献的眼光下沿到宋金元,即绍继先师学术之意。1931年《校辑宋金元人词》编成出版之际,赵万里特请胡适题序。胡适欣然应允,符合他一贯的提携后辈的作风,而赵万里作为王国维晚年门生兼助手的身份,恐怕也引起了胡适的注意。胡适的题序,绝非泛泛而论,而是由表及里,直指其方法内核。
衡估辑佚价值的高低,辑考文献范围的广狭是最直观的标准。赵万里在辑词时大量引用原为清宫秘藏的《永乐大典》及各种珍本,这自然是前人不可企及的成绩,夏承焘就赞服其中诸多词集据《永乐大典》及稀见明钞本辑录,为“各家汇刻词所未收”。(14)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吴战垒等编:《夏承焘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胡适虽然也肯定赵万里发现的史料,不过并没有对此大书特书,而是把重点落在检讨赵万里的辑佚条例上。赵万里最核心的条例是辨伪,因此详举出处,“使人可以覆检原书”,“从原书的可靠程度上判断所引文字的真伪”,可疑的词则列为附录。(15)胡适:《校辑宋金元人词序》,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胡适还比较了王鹏运与赵万里辑佚李清照词的区别,以前者贵在求多,所谓“吉光片羽,虽界在疑似,亦足珍也”,(16)王鹏运辑:《漱玉词补遗》,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页。而后者贵在存真,不以数量多寡为标尺。
胡适以王鹏运对比赵万里,暗含对新旧学者治词高下的评判,而赵万里本人也有这份自信。赵万里不满王鹏运辑李清照词“真赝杂出”,“且于《古今词统》《历代诗馀》所引,亦深信不疑,又不注所出,读之令人如坠云里雾中”,(17)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第289—290页。因此拟定严格体例,每录一词,将所据文献一一注明,由此还解决了王鹏运留下的疑问。如《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王鹏运辑本注云“此首亦疑有伪似,借前临江仙调模拟为之者”,(18)王鹏运辑:《漱玉词》,《四印斋所刻词》,第257页。但据何本所录,为何疑有伪似,又是何人拟作?王鹏运并没有说明。赵万里则发现《梅苑》卷九引作曾子宣妻即魏夫人词,但《乐府雅词》下魏夫人词不收。加之《草堂诗余》附李清照序,言其酷爱欧公之句,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则《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为李清照自作的可信度较大。(19)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第301页。即便他人有异见,也须拿出新证据来反驳,而不似王鹏运仅凭直觉下断语。赵万里在自序中称宋元词集校刊“以长沙《百家词》始,至余此编乃告一段落”,(20)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第8页。既指辑佚使宋金元词的网罗编次趋于完备,也指一扫前人通病,为后人提供据实可信之本。
胡适在序言中也引用赵万里此语,以之为“很平实的估计”,(21)胡适:《校辑宋金元人词序》,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第9页。这不仅是对赵万里的表彰,更是在强调实证方法之于国学进步的关键意义。在胡适看来,西洋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的进步,归功于审定史料方法的严密,“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22)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言》,《胡适文集》第6卷,第175页。国人研究词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以实证方法审定史料是最关键的一步。赵万里辑宋金元人词的实证方法,即可视为词学向现代进步的表征。
胡适对赵万里辑词方法的关注,或是因为透过赵万里,看到了王国维的身影。赵万里的辑词条例,也确与王国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王国维辑唐五代词时,已显现出不同于时俗的实证态度。1906年王国维初入京城,与吴昌绶结识,吴昌绶与朱祖谋、缪荃孙等彼时都热衷于词集珍本的搜访与校勘,王国维藏书量和财力自然不及专门家,吴昌绶遂建议王国维“专搜五代唐宋元人词之遗佚者。凡有集者不采,见于《花间》《尊前》《草堂》《凤林书院》诸选者亦不采”,以“惠广异闻”。(23)吴昌绶致王国维信函,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往来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王国维采纳了吴昌绶的提议,并从标志词之起原的唐五代词着手,但他辑词实与吴昌绶异趣。
吴昌绶所言的辑佚,就是搜寻常见别集、总集不载的,散见于说部诸书、戏曲、碑刻、书画的词作。辑佚者将这些世人不经见的词作汇编,大可新人耳目,但这些词作是否可信,是难以确证的。王国维辑词并不拘于文献来源的常见或稀见,他首先考究的是所辑词作的真伪。如其辑温庭筠词,求得钱塘丁氏善本《金奁集》,该集卷首题“金奁集”,次行题“温飞卿庭筠”。该本混入韦庄、张泌、欧阳炯之词共64首,其余83首按书题似可归为温庭筠作,属于吴昌绶所谓“惠广异闻”者,但王国维疑“八十三阕尽属飞卿否?尚待校勘”,(24)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240页。没有轻易全采。又如《渔父》词二首,据传是李煜题画词,见彭元瑞《五代史注》引《翰府名谈》。但王国维对这条逸闻性质的材料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虽然辑录了《渔父》词,也注明“笔意凡近,疑非后主作也”。(25)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218页。当然,王国维辑佚的范围有限,且仅在案语中考述文献,还较为随意,赵万里则凝定成“注出处”的体例,实证方法得到了彻底的落实。
王国维的据实还体现在对异文的标注,注异文是校勘常例,但由于对词体赏心娱情的文体定位,历来校钞词集者每遇异文,多凭一己好恶裁断,这些做法自然会遮蔽文学史真相。王国维辑词纯以客观态度胪列异文,他辑南唐二主词以知圣道斋《南词》本为底本,该本与毛晋钞本、侯文灿刻本同出南宋初年辑本,王国维以为“半从真迹编录,尤为可据”,(26)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215页。但每首的异文仍在校勘记中注出。如李璟《浣溪沙》,《宣和书画谱》本“韶光”作“容光”;“鸡塞远”作“清漏永”;“多少泪珠无限恨”作“簌簌泪珠多少恨”。《尊前》《花庵》《草堂》三本“无限恨”均作“何限恨”。李煜《破阵子》,《容斋随笔》本“垂泪对宫娥”作“挥泪对宫娥”。(27)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219、222页。鸡塞远较清漏永,意境缥缈悠远,无限恨较何恨恨,更添悲情的力量,垂泪也较挥泪添了一份忧戚和隐忍。尽管如此,文献的优劣与历史价值不能混为一谈,异文的标注仍是必要的。
赵万里注异文的体例也与王国维一脉相承,且直接注于词句后,更易比勘。胡适也提及了这一点,强调不能“抹煞一个孤本的独异”。(28)胡适:《校辑宋金元人词序》,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第11页。他举宋祁《好事近》为例,通行本作“睡起玉屏风,吹去乱红犹落。天气骤生轻暖,衬沉香帷箔”,《阳春白雪》本作“睡起玉屏空,莺去乱红犹落。天气骤生轻暖,衬沉香罗薄”。从文义上看来,《阳春白雪》本远胜于各本,空、莺、罗薄,更能衬出佳人的空寂幽怨。不过存此异文,不是因其韵致更胜一筹,而是因《阳春白雪》本与诸本皆不同,所异四字极可能为选家擅改,故有作历史研究的价值。
综上,赵万里刊《校辑宋金元人词》,既是对王国维治词的接续,也符合胡适把实证方法应用于词的历史研究的期待。这部辑佚类词总集在胡适与王国维之间建立了隐微的联结,印证了二人治词方法的契合。不过,胡适并没有在这篇序言中提及王国维,不可不谓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虽然在胡适为赵万里作序的1931年,王国维早已谢世,而他本人搁置词学研究也有数年时间,但词学毕竟是胡适从事国故整理的重要部分,胡适也不可能淡忘他和王国维往复研讨词之起源的记忆。胡适不愿提及,恐怕和20世纪30年代后学界热衷于二人词学批评观念的比类有关,而出于文人负气,胡适并不想主动卷入“被比较”的局面中。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局外人的比勘,让身为局内人的胡适认识到与王国维之间的终极分歧。
词学批评的动观范式与静观范式
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人间词话》作为大师遗著倏然受到追捧,而同年胡适《词选》出版,迅速成为风靡国内中高等学校的读物,两人的词学成果几乎是同时为人瞩目。但时人没有细绎两人的治词理路与方法,比较的焦点落在两人“对词之见解”(29)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3期。上,如欣赏五代北宋词而贬抑南宋词,以李煜、苏轼为天才而批评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崇尚浅近自然而反对用典和套语,《词选》意境说与《人间词话》境界说的重合等。由于王国维与胡适学术界中坚的地位,这些相通的见解“莫不有极大之影响”。(30)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3期。其时文学史著如胡云翼《中国词史略》,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等都引述或化用两书中的“片言只字”,(31)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3期。俨然把两书奉为新的论词纲领。
但胡适对此却不以为然。1936年,任访秋热切地将《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一文请呈胡适指点,不想胡适在回信中开门见山地说“静庵先生的见解与我的不很相同”,因王国维的看法是“艺术的”,而他的看法是“历史的”。(32)胡适致任维焜(访秋)信,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9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82页。胡适的表态虽然极为鲜明,不过这封信应是信笔写就,仓促成文,胡适对历史与艺术之别没做任何解释,便话锋一转,着力区别意境与境界的意涵。但他又强分作者与作品的主客关系,言“意境”由作者主体决定,“境界”就作品本身而言,仅指真实的内容,显然未经深思熟虑,也带有负气的意味。其实,意境和境界的意涵原本相通。从语境看,王国维论词也频繁使用“意境”范畴,他论元曲更以“意境”代“境界”。从释义看,胡适言意境指作家“对于某种感情或某种景物作怎样的观察”;(33)胡适致任维焜(访秋)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9册,第83页。王国维也说大家观物言情,必“所见者真,所知者深”,(34)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77页。故能自成境界,当代已有学者指出两人的阐释“固没有多大的区别”。(35)参见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81页。著者认为“胡适之意境说与王国维之境界说的区别并非一侧重主体一侧重本体之差别,也非历史的与艺术的不同”。若今人因循胡适思路,继续作意境与境界的名理辨析,则必然转相迷误。只有透过两人关于词境的批评实践来推究,才能有更明确的发现。而两人既然都把体认词境作为批评的中心,那么要理解历史与艺术的所指,探明胡适与王国维的终极分歧,自然也须由此着眼。
先看胡适。胡适对任访秋说,词体自花间而至东坡,意境终不能“高超”。(36)胡适致任维焜(访秋)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9册,第84页。花间与东坡,恰好串联起胡适知名的词史三段论。胡适于词史的第一阶段即“歌者的词”,虽然大书特书词体的民间起源,但对词的意境并不满意。在进入词史第二阶段,即“诗人的词”书写后,胡适才寻觅到最理想的词境,即东坡词之谈禅说理,论史论人,如天风海雨般壮阔无极。“诗人的词”的另一代表是辛弃疾,胡适在小传中极力渲染辛弃疾才气之高与生平的峥嵘奇伟。综合来看,广博的学问、超逸的人格及豪情才气、壮阔的生命历程等等都是成就词境的必要条件。至词史第三阶段即“词匠的词”,则“是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37)胡适选注,刘石导读:《词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5页。意境因此完全丧失。
胡适论词境,与词史观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他所建立的词史三阶段的轴线,实际上勾勒了词境从浅显局促到充实广阔,再到衰落的过程。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相比,闺阁的精秀物象和绮怨思情过于细弱,流连儿女情长不及发抒平生襟抱,低徊倾吐愁怨又不及纵论历史、人生、学问的壮阔洒落。但第一、二阶段又远胜于第三阶段的无意境。胡适由动观词境而勾勒词的历史,也是他提炼文学史规律,从而“整统一切材料”(38)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第3卷,第15页。的步骤之一。胡适在编成《词选》后编写《白话文学史》,即超越具体文体属类,对历代文学之境作通观式的考察。他言建安文人受民歌影响初作乐府歌辞,“只能用诗来表达简单的情感与简单的思想”,而不能表现“稍稍复杂的意境”。(39)胡适撰、骆玉明导读:《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盛唐乐府新词繁荣,是因为“高才的文人运用他们的天才……加入他们个人的思想和意境”。(40)胡适撰、骆玉明导读:《白话文学史》,第157页。综合来看,各文体在发展初期,意境虽然真实但较为简单,只有当文体所能涵容和表现的思想和情感趋于广大,理想的文学之境才会诞生,且具备真实、复杂、高远的共同特征。而当文人摄于模仿传统,则文学沦为“文匠诗匠的文学”,(41)胡适撰、骆玉明导读:《白话文学史》,第80页。意境自然丧失殆尽。胡适推重“诗人的词”,贬抑“词匠的词”,无疑印证了他对文学之境嬗变的历史判断。
王国维也动观词境的历史变化,《人间词话》言冯延巳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又北宋风流,渡江遂绝,都可与胡适词境观对参。但寻绎《人间词话》的写作逻辑,王国维并没有胡适如此强烈的整统历史的目的性,他更抱持一种静观的批评态度,如《人间词话》“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42)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63页。一则,王国维专注体认不同境界的独一价值,而非如胡适对词境的演变规律作历史判断。较之考量境之小大,其实王国维更注重发掘少数豪杰之士才能营构的深境。王国维言:“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43)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682页。可见词境大小仅是外象,其内质的深浅更为重要。意境深浅系于观我、观物的深刻程度。王国维曾比较秦观与晏几道之词境:“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44)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683页。所谓意境之异,可与刘熙载“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45)刘熙载:《艺概》,薛正兴校点:《刘熙载文集》,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页。之论对参。因常人不经意之物而动心,是为幽趣。秦观观我观物,深入精神生命的幽独之境,自然较晏几道发抒常人共有的痴情更有深致。
观物观我相互错综,深入至极,便能触及一直横亘在王国维心中的“宇宙人生之问题”。(46)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125页。在王国维看来,诗人抑或说文学家的天职,就是“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发明表示“宇宙人生之真理”。(47)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133页。王国维流连于唐五代北宋词史,也是因为这一时期,有诸多王国维意中能承担此天职的大词人,如李白、冯延巳、李煜,王国维评三人词“意境两浑”。(48)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683页。按《人间词话》词例,(49)参见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85、522、505页。李白“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指向历史,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指向人生,冯延巳“和泪试严妆”,则寓指个体面对历史与人生的心志姿态,王国维对三词意境的体认,与他本身对悲剧命运的感察及在人生困境中的抉择也正相契合。分析至此,可知王国维治词的初衷和旨归,正是在文学史中找寻理想中的深境,并由静观而获得对个体精神生命、及至宇宙人生问题独特而深彻的感受。
要言之,胡适与王国维词学批评之别,并不在意境、境界范畴意涵的不同,实由两人在批评中,观照词体、词境的动静视角与终极目的而决定。如果说动观为西学影响下生成的范式,那么静观范式的建立则源出本国传统,更具体来说,导源于庄子虚静以知物的思维方式。徐复观分析庄子知物说:“因为是在静的精神状态下知物,所以知物而不为物所扰动。知物而不为物所扰动的情形,正如镜之照物,‘不将不迎’,这恰是说明直觉直观的情景。其所以能‘不将不迎’,一是不把物安放在时空的关系中去加以处理。因为若果如此,便是知识追求因果的活动。”(50)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四卷:中国艺术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追问词史的源流与因果,虽然是必要的知识活动,但显然是“把物安放在时空的关系中加以处理”,王国维凝神于五代北宋大家之作,则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判断,是以“静的精神状态”进行的,虽然会影响词史研究的客观和准确性,但静观范式的建立,实现了虚静艺术精神在文艺批评实践中的现代转换,也提供了由文艺批评实践上通庄子虚静之心的路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才在现代被真正激活。
历史与艺术:近代词学的两个维度
历史与艺术分野,指向了词学研究的两个维度,而两个维度之间也存在微妙的张力:强调词体历史的、过去的性质,对艺术维度的研究也是一种隐在的否定。胡适对于艺术与美的永恒性抱有明确的疑问,甚至言“那种所谓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学是一种僵死了的残骸,不值得我们的迷恋”。(51)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文集》第1卷,第120页。这种彻底扬弃历史的姿态,也能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52)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文集》第2卷,第27页。提供支撑。
在新旧文化急速更替的大势中,把文学视为“历史”更合于主流,甚至是承学朱祖谋的龙榆生,也暗中改换了师生授受、习为倚声的传统,取历史态度与实证方法,提出“词学”为“文学史家之所有事”,治词者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研习填词门径,而是“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53)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张晖主编:《龙榆生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页。由此词学也正式成为以词的历史研究为中心的、史学色彩鲜明的学科。
但彻底革新“词学”学术意涵的龙榆生,也有一层隐在焦虑。词学被归入文学史之一部,进而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注脚,词体所以兴衍的天人际会,及此天人际会所成就的词体的美学内蕴,则被淹没在浩瀚的文学史潮流中。研究词的历史是为必要,但词体的存续是否必要,则成了一种疑问。如胡云翼言:“词体并不是一种有多大意义和价值的文体,它的生命早已在几百年前完结,成为文学史上的陈物了。”(54)胡云翼:《词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95页。胡云翼的发言虽然较为决绝,其实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新派历史家的观感。在此背景下,龙榆生虽言词学因进入现代学术序列而有“复兴之望”,但也意识到其“将绝之忧”。(55)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龙榆生全集》第3册,第474页。
对比龙榆生的学理困境,王国维以静观范式介入词学批评,由对词境的体认而作纯粹的美学思辨,其实能消解历史维度的焦虑。只是静观范式也有逻辑分析未称周密的局限。缪钺继踵王国维,将静观范式的载体由词话转为更加系统的批评论述,完成了对词体之独特内质与永恒价值的分层次探讨。
缪钺认为词体与普泛意义上的诗体之别,“不仅在外形之句调韵律,而尤在内质之情味意境”。(56)缪钺:《论词》,《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词境营构又赖于词人情思。所谓词人情思,不同于常人皆可粗感之的喜怒哀乐,甚至不同于诗之所咏,是“人生情思之精英”中“尤细美”者。(57)缪钺:《论李易安词》,《诗词散论》,第54页。缪钺又把词境的外象归结为“隐”。(58)缪钺:《论词》,《诗词散论》,第48页。盖因词人情思深邃至极,取物造境,与常人的感知意会有所悬隔,相较诗体的比兴寄托,俨然无踪迹可寻。缪钺举冯延巳《蝶恋花》(几日行云何处去)为例,该词表面写闺中思怨,王国维解为忧世之作,只是冯延巳对世运命途的冥然感知,读者只能若有所得,不能沾滞求之。故缪钺言:“若论‘寄兴深微’,在中国文学体制中,殆以词为极则。”(59)缪钺:《论词》,《诗词散论》,第48页。缪钺也由此确认了词体的永恒价值:“词体之所以能发生,能成立,则因其恰能与自然之一种境界,人心之一种情感相应合而表达之。此种境界,此种情感,永存天壤,则词即永久有人欣赏,有人试作。”(60)缪钺:《论词》,《诗词散论》,第51页。由人心的永恒而推论词境、词体的永恒,不失为一种对抗历史维度的词体价值消解的答案:词体虽然为过去的文学,但在艺术维度中,只要仍有素心人生此细美情思,仍有赏心人能感词体深美之境,则词体便可存续,不会因新文学体裁之兴而走向彻底的灭亡。
静观范式与动观范式,历史维度与艺术维度也能实现有机结合。叶嘉莹在文学史研究中,即强调引入静观范式,在艺术的维度唤起对中国文学生命感的省思:“作品之真正生命的获致,则仍在于作者之心与外物相交接时,所产生的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所以如果不能探触到诗歌中真正生命之所在,不能分辨其‘境界’之有无深浅……这样当然无法成为一位优秀的说诗人。”(61)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批评家不应只如历史家作冷峻的知识判断,更应具备兴发感动,心物相接的能力,在静观中感受并传递文学之境的生命感,则所谓“旧”文学的生命力不因时而废,国人也能觅得心灵的永恒栖所,这或许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所在。
——评陈水云教授新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