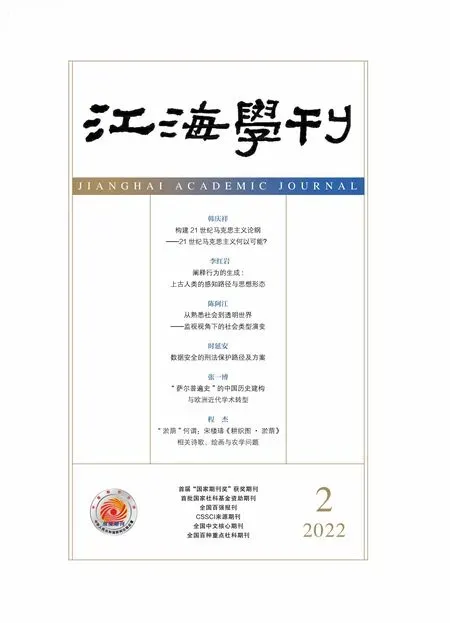海登·怀特“实践的过去”:概念、内涵及观照*
金嵌雯
无论在中西方,历史学之用都是一个重要话题,它根本涉及历史探究的自律性和价值问题。在西方,受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一些史家尝试为历史学打造一个科学的身份,他们隐匿地试图消除历史结论中的价值判断,悬置历史学之用的问题。(1)“休谟法则”或许能够为这种达成科学性的隐含设想提供哲学上的证明。休谟认为,科学和道德在逻辑上有着不同的基础,科学无力解决道德的问题,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而不能回答“怎么样”,我们始终无法从“是”推出“应该”。参见[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9—510页。但这种设想无论在实际操作还是学理层面,都受到了一定的质疑。在实际操作层面,明显的,面对如世界大战、大屠杀这类关乎人类存在的重大事件,史家不试图从中获得历史教益的做法是不明智且不尽职的。普通读者阅读历史作品不仅为了获得历史信息,还为了获得历史教益。在学理层面,这种倾向亦受到反思。尼采(Friederich Nietzsche)在19世纪末曾发出疑问,人们一味沉溺于历史事实的做法,是否会使自身变成一尊没有任何生机和活力的知识塑像,历史学是否也将因此失去对生活的价值。(2)[德]尼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240页。而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为代表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则使相关思考变得复杂。在《元史学》(Metahistory, 1973)中,怀特借助结构分析论证了历史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史家主观的审美偏好和伦理选择,(3)[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这一将历史知识相对化的论断实际削弱了历史学的科学性特征,突显了其审美和价值面向。由此,怀特破坏了客观主义史家上述有关历史学之用观点的前提,用一种引发史家担忧的方式,曲折地将历史学之用的问题示于明面。2000年后,通过“实践的过去”(the practical past)概念,怀特直接触及这一议题。国内学界对海登·怀特这位史学理论家并不陌生,但对其晚年思想的理解,仍有较大推进的空间。(4)国内有关海登·怀特“实践的过去”思想的研究,除译文《论实用的过去》(张文涛译,《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外,鲜有专门讨论此概念的著作或论文。相较国内冷清的局面,国外的关注度较大。2016年,国际历史理论网络(INTH)在巴西召开了“实践的过去:论历史对生活的利与弊”国际会议,“实践的过去”是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此外,一些学者近来也专门讨论和批评了这一概念,代表性文章有Jonas Ahlskog, “Michael Oakeshott and Hayden White on the Practical and the Historical Past”, Rethinking History, Vol.20, No.3, 2016, pp.1-20; Hans Kellner, “The Practical Turn”,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11, No.2, 2017, pp.221-228; Verónica Tozzi, “A Pragmatist View on Two Accounts of the Nature of Our ‘Connection’ with the Past: Hayden White and David Carr Thirty Years Later”, Rethinking History, Vol.22, No.1, 2018, pp.65-85; Chris Lorenz, “It Takes Three to Tango: History between the ‘Practical’ and the ‘Historical’ Past”,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Vol.65, No.1, 2014, pp.29-46。这些文章都启发了本文的写作。而“历史学之用”的议题,在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下,近年来也愈益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5)例如,2019年,西方史学理论重要期刊《历史哲学杂志》刊发了一组共7篇以“是否能从历史中获得教益(Learning Lessons from History-or Not?)”为主题的专栏文章(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13, No.2, 2019)。怀特作为20世纪下半叶在史学理论界重提这一问题的首倡者,其相关思想无疑值得讨论。本文即试图在“历史学之用”这一大的问题背景下,对怀特晚年提出的“实践的过去”概念加以剖析。
“实践的过去”概念来源及其含义
自20世纪60年代末转入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以来,怀特的思想对象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70年代对“转义”的讨论,到80年代以“形式的内容”为主题,再到90年代有关“现代主义写作”和“比喻实在论”的思考,直到2000年后,“实践的过去”成为其最后一部论文集的标题,并频繁出现在诸多文章中。对于如何贯穿这些不断变动的主题,怀特研究者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认为,“实践的过去”可以成为其全部史学思想的总结,它作为怀特生前最后阶段提出的理论,近乎“成功地整合了其作为历史理论家的50年职业生涯中提出的一系列关键思想”。(6)Herman Paul, 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Malden: Polity Press, 2011, p.144.同怀特所运用的大部分概念一样,“实践的过去”并非其“原创品”,它来自英国观念论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怀特成功地吸收了这一概念,将之融于自身的理论体系,用于说明特定的目的。因此我们先从奥克肖特处来熟悉这一概念。
在奥克肖特的论述中,“实践的过去”相对于“历史的过去”(the historical past),它们被用来指涉两种不同类型的“过去”。这并不意味针对现实世界中的同一个事件,有两种不同的实体性过去。过去无疑只有一个,但我们看待过去的不同经验模式决定了它有不同的意义。对观念论者奥克肖特而言,世界(包括过去)总是一个从不同经验模式中产生的单一融贯的观念世界或意义世界,历史事实只有在居于这一整体的观念世界中时才有意义。这意味着史学家的工作不是从一块白板开始的,在他开始收集材料之前,便已在头脑中拥有了一个在逻辑上为先的(大都是未经检验的)同质的观念系统或假设系统。只有在这个观念系统的基础上,史家才能理解出现在他面前的所有史料。(7)[英]迈克尔·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吴玉军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5—99页。“历史的”和“实践的”即是这样两类不同的经验模式或观念系统。
其中,“历史的”经验模式,奥克肖特视之为现代职业历史学用于理解过去的通行模式。在这种经验模式之下,史家出于对过去的纯粹兴趣而研究历史,其实践对象仅只与过去遗存——即过去发生之事的证据(甚至,当下的任何事物都可被视为过去幸存下来的残片)——相关。此时,过去被当作一个已逝的、“死的”范畴,“一个完整而纯净的世界”。(8)[英]迈克尔·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第105页。在史家眼中,这个世界掩藏在当下背后,它固定、完满、独立而有待发现。因此,史学家的任务是回返到这一纯粹的过去当中,对其中事件的变化、事件间的关系加以阐述。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独立于当下、“能够自己维持自己”的“历史的过去”并非独立于史家的阐释。由于这种过去本身是史家通过适当程序从现有证据中推论出来的,因此“历史的过去”仍然是当下的知识而非过去的知识。在这种意义上,它属于当下实在的一部分;并且,这一“历史的过去”区别于过去切实发生的事,在某种程度上,它只存在于史家笔下,且不是唯一的。
“实践的”经验模式是一种在范畴上与“历史的”经验模式全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它与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和行动密切相关。当人们用这种经验模式理解过去时,他将带着当下实践的关切:人们将根据自身当前的目的来判定过去的意义和价值,并用这种过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此时,人们或向过去汲取实践所需的灵感和生命力;或向它们咨询、提取有用的建议;或用它们来论证我们对当下和未来、对世界所抱有的实践信念的有效性;或用它们来表达自身倾向和自我理解,向别人解释自己的目的与行动。(9)[英]迈克尔·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第102—104页;迈克尔·欧克肖特:《论历史及其他论文》,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5页。较为典型的一种“实践的过去”即犹太教和基督教对过去的理解。相较希腊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尤其重视过去,但他们在乎的不是那些已死的、与当下全然不相关的过去,而是与自己的信仰和生活紧密相连的、自身族群和共同体的过去,只有这些过去对他们而言才有意义——摩西五经和福音书中的过去促使他们敬畏自己的当下世界,并使对上帝的信仰真切化。(10)参见[英]迈克尔·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第102—103页。因此,相较只存在于书本中的“历史的过去”,“实践的过去”通常伴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奥克肖特说,它是“活着的”,它的某些部分“和我们在一起,是一个我们将自己安置在其中的实际的或想象的祖先的过去,或更一般,是我们所属的社会”。由此,我们的回忆以及与我们现在某一偶然的身份、与我们当前的实践生活相关的种种来自过去的信息,如证书、文凭、契约、证明等,都可属这一“实践的过去”。(11)[英]迈克尔·欧克肖特:《论历史及其他论文》,第22页;类似于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说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
这两种理解过去的不同模式,为怀特所借鉴。同奥克肖特类似,他用“历史的过去”对应于“现代职业史家建立的那种过去”。(12)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The Practical Pas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9.用这种模式看待过去的史家,试图极力以严格非个人的、中立的态度探讨过去事件;他们遵照规范的史料考证和研究过程,在论述中很少运用归纳或类推法,其结果也不包含历史因果律。需要注意的是,怀特指出,在衡量这类过去时,我们仍然无法用符合的真理观来评判其真假。因为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行动者身处的时间、地点、感受、认知和设想中来书写过去行动者的当下,相反,史家总是站在后来的时间节点上来回溯过去的,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知事物的未来状态,这决定了他所能设想的历史图景是任何一位过去行动者都无法获得的。(13)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The Practical Past, pp.9-10.
“实践的过去”则紧密关联于现实世界。身处任何境况下,不管愿不愿意,人们“都会以之作为根据,从中获得信息、观念、模型、公式和策略,以解决所有实践问题——从个人事务到宏大的政治计划”。(14)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The Practical Past, p.9.小到最为琐碎的日常生活,如判断是否要以当前价格购入物品;大到做出关乎人生或共同体生存的关键抉择,如怎样对待正在发生的战争;人们都会求助于这类过去,来为现实中的行动提供依据。怀特倾向从康德的意义上理解“实践”,他认为,“实践的过去”所构成的知识试图帮助回答“我(我们)应当怎样做”这一伦理问题。它所叙述的内容定然是我(或我认同的团体),在当下境况中所认为最迫切需要探究的,它将我(或我认同的团体)与一种存在的当下(existential present)连接起来。正是在这种存在的当下之中,我寻求一个关涉“我应当怎样做”的判断和决定,而“实践的过去”正可以为其提供基础和来源。(15)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The Practical Past, pp.8, 10, 31, 76; Hayden White, “Politics, History, and the Practical Past”,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Vol.61, No.1, 2012, p.131.怀特指出,“历史的过去”可理解为纯粹理性构成的知识,“实践的过去”则是运用实践理性构成的知识,它与伦理意识、选择、决定和判断相关。(16)Hayden White, “Modernism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 Journal of Art Historiography, No. 15(December, 2016), p.15. 在康德哲学中,“实践的”即praktisch。鉴于怀特自己说明了他是从康德意义上来理解“practical”的,因此本文将practical译作“实践的”。国内一些学者将“practical”译作“实用的”,有一定道理,但易与“实用主义”(pragmatism)相混淆。尽管有学者认为美国人怀特思想中多少有实用主义的面相(见顾晓伟:《重塑海登·怀特——一个实用主义历史哲学的视角》,《江海学刊》2020年第4期;韦罗妮卡·托齐·汤普森:《位于现在的过去:怀特、奥尔巴赫与米德之间的人文主义联系》,《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但从文本上看,他几乎不曾引用实用主义者的经典著作。
承继奥克肖特的做法来区分这两类过去,意味着怀特肯定纯粹的历史研究和“为过去而研究过去”这种历史意识的自律性及正当性,也肯定历史实践效用的正当性。怀特承认,将这两类过去区分开来颇为有益,它能够帮助我们大体上划分职业史家研究的那类过去和日常生活(包括政治、宗教生活)中普通人、非专业人士及其他学科的实践者所试图从过去的经验空间中获得和寻找的东西。(17)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The Practical Past, p.15.怀特在此引用了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概念。这两类针对过去的探究毋庸置疑有着不同的原则。对职业史学来说,事实重于阐释;对以“实践”为出发点的历史探究来说,相较考察“事实是什么”的问题,它更意在探讨“什么将被允许看作特定‘历史’的事件”。(18)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The Practical Past, p.15.怀特举例说,前参议员奥巴马和希拉里在竞选美国总统时称,“我从没想过我们将目睹一位非裔美籍人士和一位女性参与竞选美国总统……这一历史篇章并非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这正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这里的“历史篇章”即属于“实践的过去”的范畴。(19)Hayden White, “Politics, History, and the Practical Past”, pp.129-130.此处,其重点不是强调事实的准确性,而在于通过将其践行之事在历史中定位,指明它们对未来的重要性和意义。不论如何,“历史的过去”和“实践的过去”作为两类不同的历史探究模式,其目的都是正当的。
然而,在对待这两类“过去”的态度和偏好上,怀特和奥克肖特不尽相同。对奥克肖特来说,这两类过去分属不同的知识范畴,是两类不同形式的、相互独立的推论知识,因而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但在怀特看来,这两种“过去”的划分更像是为史学(historiography)提供了两类假定的“理想类型”,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二者并非如此泾渭分明。职业史家也许会不假思索地接受“历史的过去”而拒绝“实践的过去”,但实际上,这类表面上的“历史的过去”式探究往往隐秘地包含了实践诉求,这些诉求只是被抑制,但从未被消除。这意味着,怀特在肯定这两类历史探究各自目的的正当性之后,又有意模糊它们之间的界限,强调它们共同存在于实际的历史研究中。相较“历史的过去”,怀特更青睐史学家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研究中的实践诉求。他的这种倾向可以说与其先前思想一脉相承。
“实践的过去”在怀特思想中的位置
2005年,在回答澳大利亚史学家登克·摩西(Dirk Moses)批评的文章中,怀特首次提及“实践的过去”与“历史的过去”的区分。同大部分批评者相似,摩西不满于怀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提观点的相对主义倾向。在这之前,怀特认为,任何历史文本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作者倾注其中的伦理和审美偏好,从理论上说,面对同一过去事件,史家可以自由地组织和阐释它们。在摩西的批评中,他虽然同意历史研究定然包含伦理要素,但他认为研究者有必要对其中的伦理要素加以规范。这要求史学家严格遵照种种研究准则来探究过去,以得出科学结论,进而解决由伦理要素引发的争端,寻求包容。(20)A. Dirk Moses, “Hayden White, Traumatic Nationalism, and the Public Role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44, No.3, 2005, pp.311-332.换句话说,摩西倡导通过强化专业的历史研究来规避历史伦理层面的争吵。怀特不同意摩西的做法,他认为摩西所青睐的这类“历史的过去”并不能解决现实争端。这种研究消除了未来主义的关切,它拒绝针对过去事件出当下的道德和审美判断,更不用说政治和社会的判断。这类研究还声称自己有权对其他形式的历史反思(如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和文学作品、诗歌、宗教、神话及普遍“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历史观加以评判,甚至将它们贬斥为“非科学的”。而这些其他形式的历史,恰恰有助于解决我们在面对多元化的历史阐释时所需应对的认识危机。
这些其他形式的历史,在怀特看来,正是“实践的”历史的典型形式。这些历史形式希望通过探讨过去来把握和批评当下状况。其中的一些历史哲学还鲜明地试图为正在被阶层差异、民族分裂和科学技术引发之创伤所撕裂的社会,指明未来的发展道路,而物理科学并无法为人类应对这些状况提供“解药”。(21)Hayden White, “The Public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Studies: A Reply to Dirk Moses”, History and Theory, Vol.44, No.3, 2005, pp.334-335.因此,怀特明确指出,历史学界需要这些实践的历史形式,因为职业史学守旧的科学性观念已无法帮助其处理当下历史意识面临的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一方面,史学家需确保针对过去之研究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史学家更要直面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人本身之存在性问题的巨大谜团。历史意识的这种分歧还说明了缘何当前历史研究会面临这样一种窘境:普通读者似乎正在丧失对职业史家作品的兴趣,但对于如人物传记、历史剧、博物馆、文化遗产和口述史等“实践式”历史,人们的兴趣却与日俱增。(22)Hayden White, “The Public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Studies: A Reply to Dirk Moses”, p.335.毋庸置疑,怀特在这里明确表达了他对“实践的过去”的青睐。他不赞成“历史的过去”纯粹提供过去信息的做法,鉴于它无力处理我们能够在过去中获知什么有关我们当下处境之知识的问题。(23)Hayden White, “The Public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Studies: A Reply to Dirk Moses”, pp.333-338.
在这次答复之后,怀特又陆续在其他场合重提这对区分,包括但不限于:(1) 在对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著作《记忆,历史,遗忘》的书评中,怀特十分赞赏利科的理论,他提及利科对历史性概念的延伸,似乎打破了奥克肖特对两类过去的区分。(24)Hayden White, “Guilty of History? The longue durée of Paul Ricorue”, in Robert Doran ed.,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57-2007,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32.(2)在对《新文学史》有关如何在全球化年代书写文学史这一专题的评论中,怀特提出,或许,我们的兴趣更应该在“文学的实践的过去”,而不是“文学的历史的过去”。后者意在探讨文学在过去曾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作为一种特定的规范形式是如何被终止的;而前者要求我们询问文学在我们时代的社会功能以及如品钦、伍尔夫、普鲁斯特这些作者笔下的文学形构“当下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或“作为历史的当下”(the present as history)的能力,这将有利于洞察我们自身时代的“历史性”本质(the nature of the “historicality”)。(25)Hayden White, “Commentary: ‘With no particular place to go’: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Age of the Global Picture”,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39, No.3, 2008, pp.743-744.(3)在专门介绍和讨论此对概念及其区分的两篇专题文章中,怀特强调,接受“实践的过去”(其在19世纪后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哲学的形式呈现)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历史写作与“虚构”、与对当下行动和未来道路的伦理关切,并不矛盾或脱离。(26)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Historein, Vol.10, 2010, pp.10-19; Hayden White, “Politics, History, and the Practical Past”, pp.127-133.前文后被收录在怀特生前最后一部论文集中,并被用作此部论文集的名称。(4)在怀特生前最后阶段对现代主义文化与历史感间关系的反思中,通过剖析多种现代主义式的历史性理解之后,怀特提醒说,即使将历史等同于过去,奥克肖特也表明可以有多种针对过去的思考模式,过去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可以作为伦理或审美反思的对象。(27)Hayden White, “Modernism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 pp.14-15.
从这些场合各不相同的零散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怀特有关“实践的过去”的四个基本主张:首先,怀特接纳奥克肖特对这两类过去的区分,这种区分有效地提醒我们存在着多种看待过去的方式。其次,相较历史的过去,怀特更青睐“实践的过去”,因为“实践的过去”能够为人们洞察和设想自身时代状况提供裨益。再次,实践式历史因其对当下存在境况的伦理关切,将必然有其想象性成分。最后,“实践的过去”与“历史的过去”共同包含于历史性概念之中,两者并非相互排斥。
我们知道,无论在《元史学》《话语的转义》(TropicsofDiscourse,1978)还是《形式的内容》(TheContentoftheForm,1987)中,怀特都意在揭示历史叙事内在的想象性,这种想象性指向史家在构想历史时引导其如此去理解的伦理、审美选择和由此为历史整体进程赋予的意义。广义上的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曾因这种想象性将历史叙事与神话等同起来。(28)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127-140.对“实践的过去”的探究表明,尽管在70年代运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但不同于结构主义者,怀特没有因历史叙事的想象性而否定史学家的全部认知工作。相反,在他看来,指向未来的历史想象将引导史家创造性地认知已无法被感知的过去实在,并且,他最终写就的历史叙事将影响和启发读者筹划当下。从这一层面看,“实践的过去”可以说为历史的想象性提供了合法性证明:当一种思想或设想对当下实践产生影响时,它便必定是真切的。
值得提出的是,虽然迟至新世纪后怀特才正式论及“实践的过去”,但他借由这一概念试图阐发的思想,却并非在提出之时刚刚形成。相反,类似的观点甚至构成了他写作《元史学》的前提。在发表于1966年的文章《历史的负担》中,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怀特对所谓“历史的过去”的批评。在这篇文章中,他深入剖析了当时西方人文学界的发展状况:在历史学界之外,包括文学界和科学界,学者们正越来越不满于19世纪确立起来的历史研究传统及其抱持的历史观。文学家和哲学家讽刺职业史家埋首于文献的“闺阁”之中,远离现实生活,对理论的疏离也使得他们抵制几乎任何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分析。而当历史学满足于自身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时,文学艺术和科学观念却已发生转变。它们共同关注于共时性结构,这种关注质疑了历史学作为自治和自证的思想方式的地位,并使得后者渐而失去了调停科学与艺术的功能。因而,更新历史研究,使之适应社会和知识群体的需求,或者说,“改造历史研究,使历史学家积极加入到把现在从历史的负担下解放出来的运动中去”,(29)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41; 中文译文见[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是史学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怀特写道:
对于任何一个敏感地认识到,我们的现在根本不同于全部过去情形的人来说,对过去的‘为其自身目的’的研究看起来只能是一种无谓的蓄意阻挠,即有意阻止人们去接近全然陌生和神秘的当下世界。……当代历史学家必须确立对过去研究的价值,不是为过去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提供观察现在的视角,以便帮助解决我们自己时代所特有的问题。(30)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p.41;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董立河译,第44页。
这里为过去自身目的的研究,可以说即“历史的过去”的前身。此处,怀特更为激进地(相较其晚年思想)批判了他称为“崇古主义者”或“文化上的嗜尸成癖者”的做法,呼吁让历史成为我们解决当下问题的“武库”而非“负担”。这篇文章成为后来怀特写作《元史学》的一个“引子”,(31)[波兰]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页。在这部庞大著作中,他时刻注意剖析19世纪史家作品与其现实关怀之间的联系。
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末,怀特已经洞察到历史与当下的不可分割性。在《何为历史系统?》中,怀特阐述说,不同于自然生物体系依照自然规律非人地做出反应,人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系统本身即是人类自主选择的结果。如3—8世纪的西欧文明,当时罗马文明的废弃和中世纪文明的建立,并非因为前者已像生物体死亡那样耗尽了它的“遗传潜能”,实际上,这种“遗传潜能”在拜占庭社会得到了延续。这一体系的出现是因为西欧人选择抛弃自己的罗马祖先,而代之赋予自己以犹太—基督教的文化血统。(32)Hayden White, “What Is a Historical System?”,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pp.131-132.同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行动者们,从彼得拉克到16世纪的诸多人物,都将古希腊罗马文明而非中世纪文明视作自身文化禀赋的“先人”,他们通过将之塑造进自己的历史文化系统中,来赋予古希腊罗马文明以新的意义和价值。(33)Hayden White, “Auerbach’s Literary History: Figural Causation and Modernist Historicism”,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89-90.不论是西欧中世纪文明,还是文艺复兴文化,都建立在对过去富有“效用”的文化理解上。这意味着,对任何一个历史和社会文化系统来说,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关系不是命定的(物理学上机械因果式的或生物学上遗传式的),而是可塑的。这一系统中的研究者如何处理过去,将影响他们如何设想未来,反过来,系统中的研究者如何设想未来,也将影响他们如何构想过去。这种观点实际上就重新定义了史学家的工作。传统认为,历史研究即要“发现”事件之间的联系,现在,怀特表明,历史研究还意味着“塑造”事件之间的联结,揭示历史在当下仍然可能存在的“后效”。这种历史研究的眼光,晚年怀特称之为“实践的”。
“实践的过去”的内涵及其观照
综上,虽然从表面上看,怀特借用了奥克肖特的概念,但他运用此概念的出发点和旨趣,不同于奥克肖特。在怀特的思想语境中,这一概念拥有特定的内涵和观照。
首先,这一概念的重提,表明了怀特在理论和实际层面对历史学之用的新思考。不同于奥克肖特认为史家可以分割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怀特认为,在实际情况中,这两者很难彼此排除,也不应彼此排除。西方史学发展史可以证明这一点。怀特指出,在西方历史学的发端处,即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时期,人们通常将历史写作看作神谕和先知预言的补充,认为它能够在公共事务及个人行为上为行动提供指导、准则和借鉴。(34)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The Practical Past, pp.10-12; Hayden White, “Politics, History, and the Practical Past”, p.131.直到19世纪,人们都更习惯将从属于修辞学的历史写作视为服务于实践活动(而非理论活动)的有效工具。(35)Hayden White, “Politics, History, and the Practical Past”, p.127.不可否认,19世纪历史学的专业化运动在改变历史学身份(与修辞学和美文相分离)的同时,也给予了历史学新的目标:将自身打造为一门能够提供各种真确事实,并帮助人们探明人类社会的科学。但即便如此,历史的实践功用仍然被保留下来。此时的历史学依旧担任着民族国家价值观之监护者的角色,它通过为社会传导爱国主义、民族美德,为国家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来获得自身作为人文学科的独特社会地位。(36)Hayden White, “Politics, History, and the Practical Past”, p.128.然而,随着历史学科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历史知识的个体性和特殊性愈发得到强调,为了防止将历史普遍化,陷入意识形态的歪曲和错误中,职业历史学家愈发切断历史意识与当下价值观之间的关联。(37)美国史家赫克斯特曾提到,史家远不是站在当下立场去看待过去事件的,当下时代的激情、预设、偏见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并不能影响他的视角,相反,史家对于过去事件的了解和熟悉将影响他如何看待当下。因为,史学家即生活于那个远离当下的、他所关切着的过去世界和时代。赫克斯特认为他正在另一个时空里享受着精神生活。J. H. Hexter, “The Historian and His Da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69, No.2, 1954, pp.219-233;[美]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杨豫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5页。“讽刺的是,历史学越加成功地转变为一门科学,它便越是客观主义、经验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它所生产的有关过去的知识就越不能给后代应对新的社会实在以效用。”(38)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The Practical Past, p.14.这意味着,西方的历史研究已越来越无法应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种种新问题。
毋庸置疑,在怀特看来,历史研究不应陷入这种困境。通过提出“实践的过去”,怀特试图在科学化历史走向极端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起历史理解与当下意识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在古典史学那里曾被认可,19世纪的史学大师们亦不曾放弃。此时,历史写作可以被视为某种由过去面向未来的投射,史家的每一次书写,都蕴含着他对当下的“证明”和对未来的设想。由此,借助引入实践理性,怀特对历史学之用做了新的思考。这种致用性,不是指依照过去事件来获得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它要更为抽象。怀特试图证明,历史应该并且有能力提供一些基础,以足够可能来为一个迫切的、关乎人类存在的判断或决策授权。与此同时,这种历史学的致用性也区别于“怎样都行”的极端相对主义观点。一方面,史家对历史的整体设想必然以过去实际发生事件的存留物为经验材料;另一方面,这种致用性以在伦理上负责为前提。因为就选择某种对当下具有意义的过去这一行动而言,它将迫使写史者承担起全部为面向人性的实现而理解和阐述过去的责任。
第二,“实践的过去”指向重新评估历史哲学、文学虚构写作在历史理解上的贡献。怀特提到,当职业史学愈加疏远当下意识时,另一些学科门类却延续了从实践性关切出发思考历史的路径,它们始终将历史作为其话语的最终指涉,尽管不像职业史学那样将严格遵照考证方法和研究规范放在首要位置。这些学科门类包括:从孔德、黑格尔、斯宾塞发展到斯宾格勒、汤因比、克罗齐等人的历史哲学(更具体地说,即思辨的历史哲学);从歌德、司汤达、巴尔扎克发展到狄更斯、福楼拜直至现代主义写作的文学现实主义。就前者而言,历史哲学家们通过对过去事件加以总结、综合和象征化,以给予零碎的过去实在一个整体进程,得到有关人类存在本质的一些普遍原则。尽管历史哲学曾被看作“神正论”、形而上学或神话的世俗形式,并因对事实的僭越而被职业史家排除出历史研究的合法领域,但“它的确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理解生命理应为何种终极目的而生活这样一个道德上的问题”,(39)[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第73页。它对历史和人类意义的探寻始终触动着人们的关切。就后者而言,在历史主义的驱动下,现实主义作家形成了自己看待现实及历史的独特方式。他们将社会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设想为过去事件和历史力量作用的结果与实现(fulfillment),进而,现实被构想为“作为历史的当下”。它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注重将时代的历史政治环境安排进日常生活的情节中,以塑造出人与环境、人与历史间的统一关系。巴尔扎克甚至将自己的工作看作就是在“写历史”,他试图在著作中展现历史镌刻在诸多普通人身上、反映在日常生活每一细枝末节上的深刻烙印,描绘出不同人物容貌、言谈、思想和装束中浸染的不同历史色调,并反思种种过去事件在人们理解现实、面对生存选择时所形成的复杂的心理世界。
接纳“实践的过去”,就意味着恢复上述历史哲学和文学虚构作品作为严肃历史思考的地位,这将使职业史学丧失仲裁这二者的权力。反过来,职业史学需要汲取上述两种历史形式的有益观念,以重新接纳它们的诗性视野和哲学式的自我反思。在实际历史研究领域,如记忆研究、口述历史、见证文学、叙事学、后人文主义和庶民研究等新兴历史课题中——它们被统称为“过去学”(pastology),怀特已敏锐地发现了一种存在式关切的回归。不同于纯粹研究“历史的过去”,这些课题关注于“历史的过去”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致力于探讨西方当下所呈现的多元社会是如何借由史学被谱系式地“烹制”出来的。(40)Hayden White, “Afterword”, The Practical Past, pp.98-99.这些研究明显地已不再对历史哲学和历史小说抱有敌意,相反,它们将这二者作为材料,或本身借鉴这两种形式来进行写作。
第三,对“实践的过去”的吁求突显了怀特思想中的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面向。20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于工人家庭的青年怀特阅读了大量二战后涌入美国的存在主义作品,如萨特、加缪、雅斯贝尔斯和马塞尔等人的著作。存在主义的思考方式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41)怀特曾坦言,存在主义是他青年时代用以看待人类状况的一种可能方式(另一种方式为马克思主义),见Keith Jenkins, “A Conversation with Hayden Whit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Vol.7, No.1, 1998, p.72.怀特与Erlend Rogne的访谈“The Aim of Interpretation Is to Create Perplexity in the Face of the Real: Hayden White in Conversation with Erlend Rogne”(History and Theory, Vol.48, No.1, 2009),Herman Paul的著作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和文章“Een beslissend moment van geschiedenis: Hayden White en de erfenis van het existentialisme”(Groniek, Vol.38, 2005)亦论及存在主义对怀特的影响。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存在主义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欧陆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它往往与人本主义亲密无间。如萨特这样的存在主义者,虽然认为在流逝时间中发生的诸多事情往往具有偶然性,没有计划、杂乱无章且无意义,但他强调人的自由能够使个体在面对混乱的过去和当下处境时,超越世界的无意义,自主选择和决定自身行为;同时,个体在当下的谋划也将决定他如何理解过去事件的意义。因此,存在主义者并不青睐经验式的历史研究,他们认为这种竭力去除主观影响,试图做到“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式历史,抹灭了历史理解本该体现的个体意志和创造性。在《历史的负担》中,怀特正是借由加缪和萨特的作品来说明客观主义式历史意识正遭遇的危机。同样,怀特晚年提出的“实践的过去”亦明显地带有存在主义色彩。史家探究这类过去的起点,不在给定的事实而在其当下的谋划;反过来,他在历史叙述中获得的历史意义也将对他或他所处共同体当下及未来的行为产生效用。
怀特思想与存在主义间的密切关联提醒我们重思他与结构主义间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末,结构主义以其“分解人”的观点取代意图“构成人”的存在主义,成为西方人文学界的思想主流。在《元史学》中,怀特亦采用了当时流行的结构分析方法,通过解剖话语模式来揭示历史文本中隐含的意义。然而,在这一结构性框架中,怀特独特地保留了史家的自由选择权。他提出,史家可以自由地选择某种话语模式,甚至,可以凭借自身的创造力,在不同的情节、论证方式和意识形态蕴含模式间进行无限组合,最终形成带有自己明显风格的、独具洞察力的历史创见。由此来看,对怀特来说,话语模式与其说是一个拥有规范性力量的“牢笼”,不如说是一种能够为想象所运用,帮助人类理解自身世界的有效工具,它通过生产意义,带领史家“逐渐接近有关世界的真理”。(42)Hayden White, “The Noble Savage Theme as Fetish”, Tropics of Discourse, p.177.从这一层面看,怀特应当被视为一名相信语言力量的人本主义者,而非留下一片物质荒漠,抹消人类主体的后现代主义者。
第四,“实践的过去”的提出暗示怀特已从历史的书写问题,转向思考我们与过去之间的关系这一带有本体论性质的问题;同时,这种思考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区别于《元史学》时期对历史文本做静态的结构性分析,在“实践的过去”中,怀特已明显地将史家写作视为一种带有意图的行动。由此,历史写作便不再仅仅聚焦于讨论事实的真确性,它还关涉“是否应当这样做”这一带有强烈伦理色彩的问题。而要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怀特指出,就需要接着问,“为了什么或谁,我应当这样做”。(43)Hayden White, “Truth and Circumstance: What (if Anything) Can Properly Be Said about the Holocaust?”,The Practical Past, p.31.因而,归根结底,这将转换为一个价值追求的问题,它将触及对人性及世界某种普遍性质的把握。
此外,对历史理解与当下意识间关系的探讨,突显了怀特试图超越经验主义历史观主客二分的立场。用安克斯密特(F. R. Ankersmit)的话来说,怀特的理论使我们意识到,“不是先有一个19世纪的文化本体,然后尝试界定其与过去的关系——不,正是通过界定这一关系,这一文化本体才成为存在……我们只有在试着界定自己与过去关系时,在通过书写历史‘书写自己’时才会碰到历史实在”。(44)[荷兰]F. R. 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的确,怀特的“实践的过去”概念以这样一种历史观为前提。这种历史观恰与经验主义的假定相反——在经验主义者看来,历史实在是一些留存于过去、不再现成的,或仍现成但对当前已无效用的事物。而怀特认为,历史虽然指涉过去之事,但它需在过去之事对当下之现实存在的积极或缺失的效用关联的基础上得以理解,也就是说,历史在当前仍具有后效。(45)这种历史观某种程度上也是海德格尔的,怀特在其晚年表现出对海德格尔历史理论的极大兴趣,见Hayden White, “The Aim of Interpretation is to Create Perplexity in the Face of the Real: Hayden White in Conversation with Erlend Rogne”, p.64; Hayden White, “Modernism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 pp.1-15.需要提及的是,这种非经验主义的历史观正在安克斯密特、鲁尼亚(Eelco Runia)那里转化为对历史之“在场”(present)的理解。而鲁尼亚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一种对实质的历史哲学的思考,也就是说,“去做那些对史学家来说绝对禁忌的事:去‘思辨’历史的某些机制(mechanism)”。(46)Eelco Runia & Marek Tamm, “The Past in Not a Foreign Country: A Conversation”, Rethinking History, Vol.23, No.3, 2019, p.409.
结 语
或许可以认为,海登·怀特“实践的过去”思想,是对20世纪西方科学化历史发展到极致后的一种“反弹”或“反应”,与其说它构成了一种系统性的理论论述,不如说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对改革职业历史写作和更新传统经验主义历史观的吁求。
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实践的过去”尚留有一些可探讨的话题,其中明显构成问题的,即如何理解“实践的过去”与“历史的过去”之间的关系。怀特虽然暗示,历史写作既包括实践的部分,也包括纯粹历史认知的部分,但他并没有明确思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芬兰史学理论家乔纳斯·阿尔斯科格(Jonas Ahlskog)在反思这一概念时指出,从根本上看,“实践的过去”仍然依赖于历史的理解模式,因为它需要“历史的过去”这一意识的“堡垒”筑造根基,以防止历史遭受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滥用,而这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往往漂浮在我们的实践理解中。(47)Jonas Ahlskog, “Michael Oakeshott and Hayden White on the Practical and the Historical Past”, Rethinking History, Vol.20, No.3, 2016, pp.9-10.换句话说,“实践的过去”需要“历史的过去”为其提供事实上的真确性基础,以保障其致用性,否则,一种认识论上的“失真”最终将损害致用性本身。阿尔斯科格的论证与怀特最终殊途同归,他指出,“历史的过去”与“实践的过去”并非两类相互排斥的理解模式,相反,它们相辅相成,促成了历史认识这一整体。
尽管怀特没有明确实践的部分在历史写作中应占何位置,但他对“实践的过去”的强调依然开拓了我们的历史观。他提醒史学研究者们走出经验主义的迷雾,重思历史的概念与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确不只是那些已逝的、固定的、过去的僵死事物,当我们说,我们生活在历史中时,便暗自肯定了历史对我们当下生活的效用。而这种效用,对当前正在经历加速变化和发展的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在变化中,我们似乎更需要寻找某些心灵的“原乡”,来为种种行动提供动力、意义和方向。而在宗教和形而上学已被部分祛魅的情况下,人们已很难再把自身命运托付给这两者,剩下的只有历史能给予我们一些启示。(48)怀特认为历史能够充当起原先宗教和形而上学在西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怀特似乎并不信任宗教,在与赫尔曼·保罗的对谈中,怀特明确否定了宗教的作用。他提到,一种更好地理解世界之偶然性的视角在于认识到人类自身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没有宗教的话,那么,留给我们的便只有历史。除了历史,我们还能去哪儿获得我们生活的方向呢?”Herman Paul, “Een Beslissend Moment Van Geschiedenis: Hayden White en De Erfenis Van Het Existentialisme”, p.590.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本主义历史观。
此外,如何处理历史问题,也的确是现今很多共同体面对发展需解决的困境。怀特曾思考到,对经历了20世纪种种难以言说、难以设想之事件和变化的社会来说,例如面对着法西斯主义、纳粹和通敌卖国者过去的西欧社会,面对着斯大林主义过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人们急需设想一种新的方式来将共同体的过去融于当下。(49)Hayden White, “Postmodernism and Textual Anxieties”, Nina Witoszek and Bo Strath, eds.,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Perspectives East and Wes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9, pp.27-28.这正从侧面说明了接纳“实践的过去”的必要性,它将有助于我们把沉重的历史负担变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值得提出的是,包括“实践的过去”在内的怀特晚年思想的确正在激励不同国度的历史学家们反思自身的历史。比如说,它出人意料地在南美国家历史学界受到重视并被接受。借助怀特的观点,阿根廷历史哲学家韦罗妮卡·托齐·汤普森(Verónica Tozzi Thompson)试图告诉学界:历史始终有其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对南美这样一个经历了种种变化并且不稳定的社会来说,历史远不能被抛弃。相反,社会需要从历史中找到自我的根基,史家需要为自身社会书写一种能够为当下行动提供启迪的不同的过去。同样的,中国史家亦肩负着这种面对复杂过去开创前路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