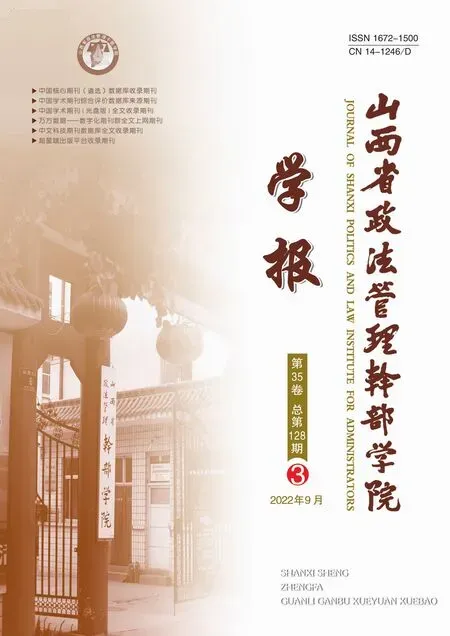抢劫财产性利益行为的司法认定
——以抢劫信用卡、抢劫欠条为例
刘丽娜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一般来说,财产性利益是指狭义财物以外的无形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利益的增加(获得债权)与消极利益的减少(减少或免除债务)。[1]对于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对象,理论和实践均有不同观点。但实践中以财产性利益为抢劫对象的判例已不少见,如抢劫信用卡案件、抢劫欠条案件等。由于对财产性利益的不同理解,导致此类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都存在争议。
一、实践问题的揭示和基本理论的澄清
(一)财产性利益作为抢劫对象的实践困惑
从涉及财产性利益为对象的判例中,反映出对财产性利益基本含义和特征的理解不明确。如刑事参考案例1185号[2]姚小林等抢劫案 。被告人姚小林与他人预谋,对被害人采用拘禁、殴打、搜身、持刀威胁等手段,劫得被害人张国某的黄金戒指1枚(价值4886元),劫得被害人张启某的黄金项链1根(价值13571元)、现金400元、工商银行卡1张。后被告人姚小林逼问被害人张启某说出工商银行卡的密码,指使被告人沈某和刘某从该卡内取出现金20000元,后又指使被告人杨某以转账方式转走该卡内资金50000元,后因被害人张启某报案,该50000元被银行冻结而未被取走。对此案法官评论到:“行为人劫取了信用卡甚至获取了密码均不等于行为人获取了信用卡上所记载的财物,被害人丧失对信用卡本身的控制也不意味已经丧失信用卡上所记载的财物。鉴于信用卡所具有的抽象财物与具体财物的双重属性,在抢劫信用卡类犯罪中,只有以行为人从信用卡中实际获取的财物数额,即信用卡所有人受到的实际损失为抢劫数额的认定标准,才能完整客观地体现抢劫信用卡的社会危害性”。[3]此评论即肯定信用卡具有抽象财物与具体财物的双重属性,又要求只有从信用卡中实际获取财物的数额,才能完整体现抢劫信用卡的社会危害性,实际是没有将信用卡视为债权的载体,一种财产性利益,否定了抢劫信用卡但不使用的行为可以构成抢劫罪。
但在习海珠案件中,[4]被告人习海珠为了迫使被害人彭某转让矿场,指使人采用组织本村老少到厂里拉电闸,阻拦货车等手段对彭某进行骚扰,彭某无奈,只能将矿场以390万转让给习某。习某支付了大部分费用,但仍欠75万。因彭某多次讨要,习某便指使人在某旅馆包间殴打被害人彭某,并强迫被害人彭某写下:“收到习某购买矿场所欠75万”的收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习海珠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本案中,法院以习海珠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说明量刑的依据是欠条所记载的数额75万,属于抢劫罪数额巨大情节。欠条无疑是证明债权存在的凭证,属于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行为对象。但是抢劫欠条是否等同于抢劫了同等数额的现金,如果二者相等那财产性利益就没有独立作为抢劫行为对象的必要。而且与前例相比,无论信用卡还是欠条都是财产性利益的载体,其中信用卡债权凭证的性质更明确,但没有判例认为抢劫了信用卡就是抢劫了信用卡里的现金,可见实践判例对抢劫财物还是抢劫财产性利益对象判断的困惑。
又如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1)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8刑终106号刑事裁定书。被告人常某等三人采取砍刀刀背拍、电警棍电击及其他恐吓的方式抢劫了被害人荆某、李某和王某现金共计21500元,后常某、许某、毋某某在荆某没有现金的情况下,迫使荆某写了一张10000元的欠条。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被告人所抢劫的财物中,其中有10000元系当场使用暴力, 强迫他人出具的欠条,被告人未实际得到10000元。对于该10000元欠条,被告人已经着手实行抢劫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抢劫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本案将欠条作为犯罪对象,又要求只有获得欠条记载的财物才是犯罪既遂。如果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行为对象,它就是独立于财物而存在的,将抢劫财产性利益行为都视为未遂形态,实际上否定了财产性利益作为抢劫行为对象独立存在的功能。
(二)基本理论的澄清
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财产犯罪对象。首先,实践中已存在大量侵害财产性利益的危害行为,其危害性与侵害财物犯罪相当。其次,通过刑法解释可以将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四章所使用的章名“侵犯财产罪”之财产解释为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再次,刑法规定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财产权,将财产犯罪侵害的对象分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与民法上物与债的二分制相契合,与民法对物权、债权保护相呼应,“财物价值”属于物权保护范围,“财产性利益”归于债权保护领域具有实践合理性。
当取财行为针对某种“物”而为时,该“物”中蕴含的价值可能具有两面性,即物本身的价值与物作为某种“利益”载体的价值,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面向,不能混为一谈,需要合理区分“财物价值”与“财产性利益”,以准确认定行为是针对财物的犯罪还是针对财产性利益的犯罪。[5]财产性利益可能以某种物为载体,但它不是物本身,如信用卡。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所谓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可见信用卡是一种债权凭证,抢劫信用卡是为了信用卡所记载的金钱价值。内容清楚记载债权债务关系的欠条也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载体。财产性利益是一种可期待利益,当债权变更或消失,财产性利益亦受到损害。抢劫债权利益是破坏原权利人对债权的占有和主张债权的权利,使债权持有人丧失可期待利益。虽然可期待利益不是现实财物,但侵害可期待利益就是对现实财产权利的紧迫威胁,用暴力手段威胁现实的财产权利,值得动用刑法保护。理清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是不同而独立的对象存在,才能分析清楚一行为构成犯罪是针对财物构成犯罪,还是针对财产性利益构成犯罪;是针对财物既遂、未遂,还是针对财产性利益既遂、未遂;针对财物的量刑数额如何计算,针对财产性利益的量刑又如何考量。
二、抢劫财产性利益行为的定性
信用卡、内容明确的欠条都是财产性利益的载体,抢劫信用卡、抢劫欠条的判例也不少见,尤其是抢劫信用卡的案件发案较多。
(一)抢劫信用卡行为的认定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六项规定:“抢劫信用卡后使用,消费的,其实际使用、消费的数额为抢劫数额;抢劫信用卡后未实际使用、消费的,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所抢信用卡数额巨大,但未实际使用、消费或实际使用、消费的数额未达到数额巨大的,不适用‘抢劫数额巨大’的法定刑”。但无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抢劫信用卡后使用的行为是以抢劫一罪定罪,还是抢劫罪与信用卡诈骗罪或盗窃罪数罪定罪,理论界始终存在不同观点。[6]而对抢劫信用卡后未使用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又如何量刑也难以统一认识。
对抢劫信用卡后使用的行为,有观点认为应当根据行为人当场使用还是离开现场后使用来决定构成抢劫一罪还是抢劫罪与信用卡诈骗罪数罪(如果在机器上使用也可以定盗窃罪)。[7]但无论是抢劫后使用定抢劫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数罪,还是抢劫后未使用也构成犯罪,都需要首先承认信用卡作为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的行为对象。“抢劫后未实际使用、消费的,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这一解释明确回答了抢劫信用卡不需要使用也构成抢劫罪,这同《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论处不同。《刑法》一百九十六条明确要求“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反推不使用则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但司法解释并未明确,抢劫信用卡未使用构成犯罪时抢劫的对象是什么。理论界不少学者认为是信用卡本身。持此观点有两个重要论据:一是抢劫罪不要求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所以卡片价值不足不是问题;二是认为信用卡属于具有主观价值的应予保护的财物。对此观点笔者不予认同。财产犯罪都具有逐利本质,可能极个别情形下犯罪人是为了毁坏信用卡,或抢劫后即毁坏。如果以毁坏为目的,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没有受到紧迫的威胁,也不必以犯罪论处。笔者赞同抢劫信用卡未使用构成犯罪是因为信用卡作为债权凭证、一种财产性利益被抢劫,债权人的财产就面临紧迫的失控风险,有刑法保护之必要。行为人以暴力、威胁手段侵害他人债权,其行为危险性明显高于盗窃、诈骗行为,值得动用刑罚处罚。所以抢劫信用卡而未使用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其行为对象是信用卡承载的财产性利益。
有观点认为抢劫信用卡而事后使用的行为应构成抢劫罪与信用卡诈骗罪数罪,此观点与司法解释规定的抢劫信用卡后使用、消费的,其实际使用、消费的数额为抢劫数额的解释看似矛盾,但对司法解释的“事后使用”可以有不同解释。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其一,从自然行为样态看,抢劫信用卡后使用的行为确实包括抢劫信用卡这一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和冒用信用卡的诈骗行为,两行为在危害程度上有较大差距。不同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从自然形态看造成财物损失的是信用卡诈骗行为,但盗窃和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危害性相当,以盗窃还是信用卡诈骗评价对行为人无明显不利。但抢劫与信用卡诈骗行为危害程度差距较大,将低度行为造成的财物损失视为高度行为造成的损失是对被告人的不利评价,应予禁止。
其二,抢劫罪虽归入财产犯罪,但其危害性不单体现为对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还体现为夺财手段的暴力性,对人身的现实危胁,所以抢劫罪法定刑明显高于其他财产犯罪。抢劫罪基本犯的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信用卡诈骗罪基本犯的法定刑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入罪数额高于诈骗罪、盗窃罪,所以抢劫罪的危害性不完全由抢劫数额决定。但在抢劫罪的加重犯规定中,则将抢劫数额巨大与持枪抢劫,入户抢劫等因情节严重而加重法定刑的情节加重犯并列。可见无论对抢劫犯的基本犯还是加重犯的认定,以数额为唯一标准都可能冲击罪刑均衡原则。更关键的是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抢劫数额巨大,参照各地认定盗窃罪数额巨大的标准执行”,进一步证实了以低度行为数额认定高度行为数额的不利后果。
其三,笔者认为,司法解释无权进行不利于行为人的法律拟制,如将低度行为侵害数额视为高度行为侵害数额。《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以盗窃论具有合理性是因为盗窃与诈骗的危害程度相当,所以将司法解释限制为抢劫后当场使用的数额视为抢劫数额是恰当的。因为抢劫后当场使用,由于被害人人身仍处于行为人控制下,此时被害人没有保护财产之可能性,此时转移使用的财物数额视为抢劫数额符合抢劫行为特征。而对事后使用的,即被害人已具有人身自由,有避免损失可能时的使用行为,以对信用卡这一财产性利益的抢劫和信用卡诈骗数罪并罚,则充分而合理地评价了行为人的危害行为。
(二)抢劫欠条行为的认定
抢劫欠条行为的判例也不少见,欠条能否成为债权凭证是有争论的。[8]从民事法律视角看,欠条就是表明特定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简约合同。对特定债权人而言,欠条当然是一种财产性利益,所以抢劫欠条行为往往也发生在特定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非特定人抢劫他人欠条的行为只能针对事后对欠条的使用行为以诈骗或敲诈等行为论处。而特定人抢劫欠条是为了消灭债权债务关系,此种侵害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意味着被害人的财产权利受到紧迫的、现实的威胁,同抢劫信用卡一样可以构成抢劫罪。当然,抢劫欠条是否意味抢劫了欠条所记载的现金?笔者认为,内容明确的欠条确实记载着债权债务关系,但占有欠条不意味必然消灭债务。一般而言法官不会仅根据欠条确定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还要有汇款凭证或人证,这些辅助证据都会帮助证明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失去欠条不意味失去欠条上的现金,失去欠条只能是财产权利受到紧迫的、现实的威胁,所以抢劫欠条的行为对象仍是财产性利益。
三、抢劫财产性利益行为的量刑
在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对象的前提下,对具体抢劫行为就要准确认定抢劫对象是具体财物还是物所承载的财产性利益,在此基础上才能准确量刑。
(一)对抢劫信用卡行为的量刑
笔者认为,抢劫信用卡事后使用的行为应构成抢劫罪与信用卡诈骗罪数罪(如果在机器上使用也可以定盗窃罪)。使用行为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当然以信用卡诈骗数额量刑,而抢劫信用卡行为其对象是财产性利益,笔者认为司法解释规定抢劫信用卡未使用的,以情节轻重论罪,是抢劫财产性利益的量刑根据。而所谓以情节轻重论罪,是指在抢劫犯基本法定刑内以情节轻重量刑。情节轻重可以考量抢劫的手段行为,信用卡记载的数额,主观恶性等,但是信用卡记载的数额不决定法定刑。对抢劫信用卡当场使用的,以抢劫罪一罪论处,当场使用的数额典型的是控制被害人当场取出金钱,也有控制被害人当场强令被害人转移卡内金钱的。姚小林抢劫案既有当场抢劫财物、信用卡的行为,又有事后使用信用卡行为,事后使用信用卡行为可以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对机器使用也可以是盗窃罪),其中5万因被害人及时报案而被及时冻结,构成信用卡诈骗的未遂,另外2万是既遂,因为被告人是两次使用信用卡,如果取出2万是在控制被害人时所为,那么这2万就应当认定为抢劫数额。
(二)对抢劫欠条行为的量刑
抢劫欠条的行为对象是财产性利益,应以情节论罪。欠条虽记载着债权债务关系,但一般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或消灭不会仅有欠条一项证据。抢劫欠条不等于抢劫了欠条记载的现金,但确实使欠条记载的财产权利受到紧迫、现实的威胁,所以欠条作为财产性利益,以抢劫手段侵害应当动用刑罚处罚。前述习海珠案例判处被告人11年有期徒刑,无疑是以欠条所记载的75万元作为量刑数额,按抢劫数额巨大的法定刑量刑的结果,是否合适有待商榷。如果承认欠条是财产性利益,分清抢劫财产性利益与抢劫财物之不同,类比抢劫信用卡未使用时以情节量刑,才能保持财产性利益作为抢劫对象时量刑的均衡性。当然欠条所记载的数额可以作为情节,在基本法定刑内考量。前述常某抢劫一案,常某强迫被害人写下1万元欠条,因为没得到1万而解释为未遂也不合法理。暴力强迫对方写下欠条,设定债权,抢劫的是财产性利益,对抢劫财产性利益而言已经既遂。如果将没取出现金就视为未遂,那还是以财物为抢劫对象视角下的逻辑分析,否定了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行为的独立对象。
总之,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行为对象,与财物作为抢劫行为对象不同。抢劫财物时数额是抢劫罪量刑的重要依据,但抢劫财产性利益时,应在抢劫罪基本法定刑内,考量情节轻重进行量刑。如果行为人不仅有抢劫财产性利益行为,还有其他对财物的侵害行为,可以依行为特征构成的犯罪与抢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