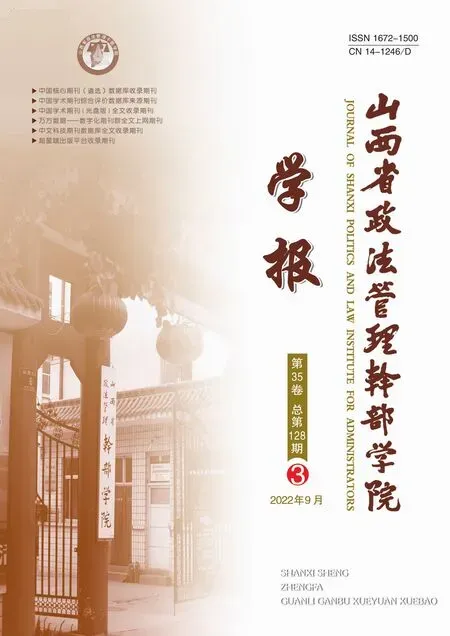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视域下环境法治完善进路
胡 锋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255049)
伴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生态女性主义思潮由此产生。“生态女性主义”这一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妇女权利解放的重要思潮蕴含着丰富的法哲学内涵,其以全新的视角推动了学界对于法学理论的反思与重构。[1]而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将法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围进行了深入拓展,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一种超越和创新,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其对于推动环境法治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是现代环境保护和现代环境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2]
一、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之理论阐释
深度剖析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之理论内涵,能够为现代环境法治的完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因此,笔者将从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三个维度,对其概念内涵进行系统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就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在认识论及方法论层面的独特性展开论述,以期为健全现代环境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指引。
(一)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Feminism)是19世纪以来兴起的为争取女性与男性具有平等权利的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潮。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由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精英群体等自由派发起,以争取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为中心。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新左派激进女性主义者提出,旨在从阶级、经济、文化等角度,谋求女性的全面解放和人格独立。第三阶段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女性主义者更加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探索建立女性的话语体系。[3]
生态女性主义是伴随着西方生态保护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形成的一种主动适应社会变革的思潮。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和生态灾难引起了女性主义者的强烈抗议,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应运而生。弗朗索瓦(Francois)在《女性主义·毁灭》(Feminism: Destruc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论证了女性正经受的压迫与自然正面临的破坏具有直接联系,倡导女性发起一场生态保护运动,促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席瓦(Siva)以女性与自然的结合为视角,探讨发展、性别与自然的问题,致力于寻求女性与自然的共同发展。波鲁乌德(Boru Uhde)把生态女性主义归结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探究统治女性和统治自然之间的联系,将环境保护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生态女性主义在我国的实践源自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女性主义者们和环保主义者们认真探索女性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理念运用到环境保护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当中。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其歌颂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倡导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是对于女性主义的一种超越。生态女性主义继承了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成果,是女性主义与环境伦理学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旨在探究“统治压迫妇女”与“盲目支配自然”之间的关系,批判传统的“父权制”世界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思维模式,试图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社会关系。[4]生态女性主义将性别与环境问题有机结合起来,秉承整体自然观和关怀伦理,将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看作一个整体,并主张人类应当给予自然基本的尊重与关怀。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倡导人与自然的平等,并维护和尊重其差异性,其环境正义思想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即环境性别正义、环境种族正义、环境代际正义和环境种际正义。首先,环境性别正义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诉求,其旨在通过消除差异和歧视,保证不同性别在生态权益的获取上处于平等地位。其次,环境种族正义是指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必须保证个人、种族、地区乃至国家之间的公正和平等。再次,环境代际正义是指环境和资源应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和使用。最后,环境种际正义是指要实现人与自然(或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公平,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应然关系。
(二)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的内涵
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法学领域的应用与表现,其以环境与性别双重视角作为切入点进行法学研究,同时吸纳生态伦理、女性主义和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内容。基于多重研究视角和对交叉理论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以其独特的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双重立场,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理念指引,深刻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倡导人类关注女性与自然的健康发展,实现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纵观历史发展进程,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是对于环境正义的演进,而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又影响、促进着环境保护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以全新的方式诠释着女性与环境、女性权益与绿色正义、女性权利与环境法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
(三)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的独特性
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以其独有的、不同于男性对自然和女性“野蛮侵略”与“暴力征服”的“融合之道”与“自然之道”,指引人类思考如何在法律上实现与自然的对话。采取和平、融合的方式,而非暴力征服的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1.认识论层面: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将人类利益作为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的标准,认为人类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即认为人是目的,是主体,而自然是客体。正因如此,人类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创造了经济收益,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生态女性主义一改西方传统观念中对女性与自然创造力的漠视,开辟了女性与自然相互联系研究的新视角,强调了女性选择与自然选择的同质性。正是因为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联,使得女性主体更适合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活动中去。生态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发展观。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是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一次超越,属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范畴,其思想渊源最初可以追溯到利奥波德提出的“和谐、稳定、美丽”三原则,罗尔斯顿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增加了“完整性、动态平衡”两个原则,之后奈斯又创造性地将“生态的可持续性”原则纳入其中。最终,生态整体主义经过三个阶段的演变与发展,于20世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5]生态整体主义不仅重视自然界生命个体的价值存在,还进一步强调生态系统整体的价值考量,承认并尊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价值。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作为个体处于自然界当中,只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实质上是一种生态整体观。[6]另外,道家生态思想亦认为人与万物都有其各自存在于自然界的价值和意义,在本质上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并且,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辩证统一的逻辑闭环,人类的行为应当在遵守自然秩序的基础之上进行,不然将自食恶果。
2.方法论层面:开创对“主客二分”认识论的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客二分”认识论将人类与自然分离开来,将一个整体世界分解成主体、客体两部分进行认识和研究,人为地将系统性、整体性的自然客观规律划分为“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两个相互对立的理论阵营,把自然界作为人类社会之外的一个独立部分进行区别对待。在“主客二分”认识论的指引下,人类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获取,过度透支自然,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有序运行和平衡。“主客二分”认识论为人类征服自然、忽略自然生态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发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诸多不和谐因素,人类虽获得了短期收益,但失去了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由此,生态女性主义开始反思传统理论学说存在的问题,重新审视和剖析以人类为中心的“主客二分”方法论,引导建立新的研究角度和发展理念。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理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类是构成整个生态系统的物种之一。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物种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所有生命形式应当按照其自然规律发展,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其二,人和自然之间所体现出的生态关系和性别关系具有内在的关联,自然孕育万物与女性繁衍后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似性。将父权社会的“性别歧视”与经济社会的“自然歧视”相互链接,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和历史联系,女性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二、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与环境法治的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对于推动环境法治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因此,从女性与环境、女性权益与环境正义以及女性权利与环境法治三个维度,对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与环境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展开系统论证,能够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善现代环境法治提供全新的法理视角。
(一)女性与环境
女性与环境的关系有着深刻而长远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女性在环境保护运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环境保护与女权运动的相互结合,催生了影响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与环境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女性是环境恶化的最主要受害者。全人类都是环境恶化的受害者,而对女性的影响尤为突出。环境恶化不仅导致女性经济上的贫困,更加影响着女性的身心健康。由于劳动分工与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女性在贫困人口中的占比远远高于男性,而受环境污染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贫困人口和底层民众。女性在面对环境退化时,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低于男性,许多女性处于“贫困—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当中。另外,环境污染对人类身体的损害不仅及于女性自身,还有可能通过怀孕、哺乳等行为影响到后代。第二,女性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女性由于其自身对周围事物的敏感性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脆弱性,最早掀开了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大幕。早期的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天然联系,认为女性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积极倡导女性参与到生态保护运动中去,对环境保护运动和女性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7]
(二)女性权益与环境正义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指出,公平的社会发展模式必须提高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者中女性的权益,赋予她们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女性是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的受害者,因此她们对于周边威胁生态环境的行为有着更为深刻的洞见和体会。生态女性主义在保障女性权益、关注环境正义等方面的影响意义重大。环境正义是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和前沿理论,[8]其概念最早起源于在美国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环境正义所解决的最核心问题是如何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合理分配有限的自然资源,即如何公平处理不同国家、地区、人群之间的生态资源分配问题。根据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可分为代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国内环境正义与国外环境正义。所谓“代内环境正义”包括国内环境正义和国外环境正义,是处理当代一定地域之内或者一定地域之外的资源分配正义问题。而“代际环境正义”则是解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资源分配问题,这要求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时不仅应当考虑到如何满足自身的现实需要,还应当站在造福子孙后代的立场上,为后代保留必要的生存和发展资源。[9]
(三)女性权利与环境法治
频繁爆发的环境危机引发了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深刻反思,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界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的理念在此背景下诞生。生态文明理念促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强调对于人类所处环境整体性利益的保护,反对对于自然资源的报复性、毁灭性的利用和对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的威胁与迫害。生态文明对法律的革新起到了推动作用,不仅是旧有部门法律制度的完善,还包括基于现实的环境危机而催生的环境法治的制度重构。环境法治要求对任何的种族、少数群体、个体权利都应当给予公平公正的尊重和维护,对于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权利的忽视甚至歧视,应当在环境法治的框架下予以纠正和完善。环境法治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还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引。在环境法治的维度里,理解公平正义的视角是多元的。在法治框架中,“男女平等”是一条基本原则,但这种平等并不等同于相等,即不是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实质上的平等。由于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导致女性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这与环境法治的本意甚至法治的理念都是相悖的。在社会认知层面,由于性别的差异,女性相较于男性所能占据和利用的社会资源及自然资源较少,而受环境恶化影响的程度却比男性大,其间权利义务的平衡需要靠法律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而非仅仅强调环境主体间表面上的平等。[10]
三、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视域下环境法治的完善进路
在厘清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的内涵及其独特性、明确其与环境法治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现代环境法治的完善应从宏观理念和微观制度两个层面进行综合制度设计,充分吸收生态女性法哲学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并将其运用到健全环境法律制度当中,使之更好地助力生态环境保护与现代环境法治的发展。
(一)理念层面:环境立法价值的确立
1.将环境正义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环境正义既有其生态哲学意义上的理论高度,又能体现对现实社会中具体问题的人文关怀。环境正义之所以与环境法的其他价值形态不同,是由于其原则的产生是独立的,不需要依赖于任何朴素的善的观念。而安全、秩序、利益、发展、民主等价值都可以由环境法的正义价值推演出来,即环境正义是环境法“价值中的价值”。其一,环境正义在道德观念上是优先于其他价值形态的,因为公平正义是人们内心最为朴素的价值观念。其二,在认识论上,环境正义也具有优先于其他价值形态的地位,因为环境正义是评价其他价值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正义已然成为了评价环境法律体系客观性、公正性、约束性的价值准则。因此,应将环境正义确立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形态。[11]
2.实现从关怀伦理到关怀价值的转化。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演变体现了人类对于环境伦理的认知与关切,而将环境正义作为环境法的终极目标和理想状态则能体现出人们对于环境价值的审视与关怀。环境正义应当作为人们界定环境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标准,在环境法律体系中融入“关怀”这一女性倾向化要素,并非是对于法律所要求之理性的挑战,而是对现有父权制统治模式及规制失灵的一种弥补和修正。强调关怀价值并不会导致环境法律体系的感性化色彩或者不稳定性,这只是对理性化环境法治的完善和升华,以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人对自然的人文关怀的双重目标。从“无害于环境”到“有益于环境”的目标转变,实现了从“关怀伦理”到“关怀价值”的转变过程,其间充分体现了环境正义的关怀价值。
(二)制度层面:环境法律制度的健全
1.转化国际环境法中的社会性别条款。国际环境保护对社会性别的关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关于女性参与环境保护运动的规定逐步确立在一些国际法律规范的条文当中。例如,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的序言中写道:“……妇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妇女有权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决策和执行”。再如,《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二十五条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第十四条都对妇女在自然资源利用方面的权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另外,在很多国际“软法”当中也存在社会性别条款。比如,1995年《北京宣言》规定,要保证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获取资源的权利。因此,应将国际环境法中原则性、纲领性的社会性别条款加以转化纳入国内立法体系,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机制。
2.保障女性有效行使环境保护决策权。基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环境立法,全面考量女性在环境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保障女性行使参与环境保护的决策权。其一,充分调动女性参与环境决策的积极性,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鼓励其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到环境治理和环境决策的过程中。例如,可适当调整环境治理及决策结构,增加女性的参与比例。其二,优化环境决策结构,设立专门机构进行过程性监督,保证决策程序的公平公正,实现女性参与环境决策的实质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发挥女性在环境治理及环境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其三,适当引入社会性别差异化的评价理念,从不同角度开展环境决策工作,在确保法律理性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丰富现代环境法治的内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