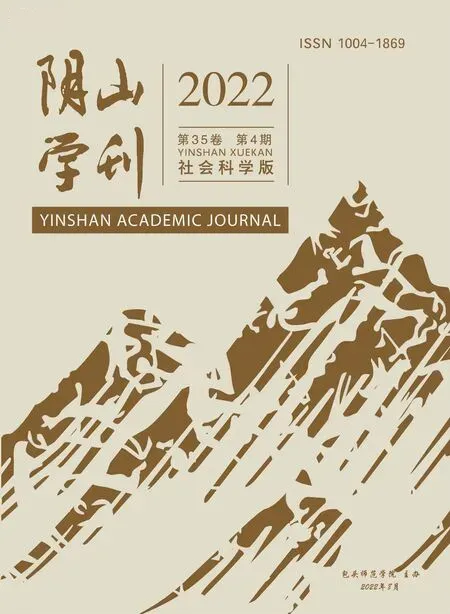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学语文古诗鉴赏教学
刘 思 宁,于 东 新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00)
中国古诗是中学语文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目前中学语文古代诗歌鉴赏教学却普遍存在着解读浅层化、语言形式化等突出问题。其实可以在古诗鉴赏教学中引进中国古代文论的资源,以之作为解决古诗鉴赏教学中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不平衡现象的理论工具。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1]如果能够在中学生“愤悱”之时,启发他们操持好古代文论这一利器,就可以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用,培养中学生诗歌鉴赏能力,提高中学语文古诗鉴赏教学的水平。本文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和诗画相通等三种理论,探究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学古诗鉴赏教学中的运用机制,并“窥斑见豹”,考察中国古代文论——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强大生命力,这不仅是文化自信的表现,更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生动明证。
一、知人论世:品读诗歌背后的人生况味
“知人论世”理论是由孟子在继承孔子文论基础上加以创新而提出的,始见于《孟子·万章下》:“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237孟子所谓“知人论世”,是为了尚友古人,本意是作为一种修身之道,但被后世转化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具有了文学理论的价值。在尝试解读一首古诗作品之前,首先需要让学生知晓“知人论世”的重要性。所谓“知人”,就是要邃晓作者本人,包括其性格气质、作品风格和审美取向等等;所谓“论世”,即考察作者创作时的社会世态,包括政治背景、文化环境,以及民俗风貌等等。作品往往既受创作主体主观情感的制约,又受到时代语境的影响,故“知人”与“论世”不可分割。清代学者章学诚有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速论其文也。”[3]“知人”与“论世”是同一个视角的两只眼睛,唯有左右开弓、双管齐下,才能对作品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与解读。
不妨以王维的《竹里馆》和柳宗元的《江雪》为例。在“知人论世”的理论指导之下,可以引导学生发现二诗都是被自然景物触动而有感而发的吟咏,都包含着隐逸的意蕴,但由于诗歌作者个人经历和生活的时代大相径庭,所以两首作品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也表达了完全不同的心境与情感。
首先,从时代来看,王维(701—761)和柳宗元(773—819)分别是唐代不同时期的诗人。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诗歌这一体裁诞生已久,历经了无数文人诗家的悉心打磨,到唐代已臻成熟,产生了清新明秀的山水田园诗和慷慨豪迈的边塞诗,但无论是描写青山绿水、塞北风光,还是抒发隐逸之趣、忧愤之思,盛唐时期的诗歌都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气韵,鲜有哀怨之词。王维便成长于此时,他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实力大大削弱,处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4]270的慌乱之中,大厦将倾,犹如百病缠身的病人,即便有振作之心,也是积重难返,回天乏力。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5],文人们面对家国动荡、民不聊生的现状,加上遭贬边地,辗转如飘蓬的际遇,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敏感,贬谪的人生经历同时也拓展了中唐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唐诗因而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柳宗元正是这一时期贬谪文学的代表作家。上述背景知识的把握,不仅是“知人论世”教学中的一部分,也有助于中学生积累必要的文学史、政治史方面的知识。
其次,王、柳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王维一生半官半隐,总体来看可以说是过着平静悠闲而从容自得的生活。他十五岁进京便得到王公贵族的赏识,二十一岁中进士,从政后也不忘修身养性、寻幽探胜,晚年无心仕途,直接隐居于水秀山明的蓝田辋川,吃斋念佛,澄性明心,如其本人所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6]《竹里馆》便作于此时。柳宗元生于安史之乱后,不仅无缘共创盛唐气象,并且从少年起就目睹社会动荡、官场腐败,还亲身经历过藩镇割据的战火,他因胸中的中兴之志而参与“永贞革新”,却因革新失败而被贬永州达十年之久(805—815年)。在荒远孤寒之地,过着被管制、被软禁的生活,思亲念友,失意落魄,他的忧郁、悲愤、愁苦常常折射于诗歌之中,《江雪》便创作于其被贬永州时期。
结合以上对两位诗人“人”与“世”的理解,再与学生一起品读这两首作品,就能够自然地将其中所建构的意境与蕴藏的情感融会贯通。王维的《竹里馆》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密竹、明月,说清幽也清幽,说萧瑟也萧瑟,而在诗人笔下的月夜幽林是如此澄明净澈,其间抚琴长啸的诗人也是安闲自得、尘虑皆空,这皆因一时清景恰好契合了诗家心中的恬淡幽静。结合之前所了解的盛唐诗风以及王维晚年长斋奉佛、寄情山水的人生追求,诗中所蕴含的宁静安闲、天人合一的况味便不言自明了。而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也写自然景象,却是飞鸟遁远、行人绝迹的一片枯败,读之觉寒气逼人,可由此联想到当时政治环境之严酷。接下来两句塑造了孤舟钓雪的渔翁形象,雪虐风饕的冷寂天地之中,只有这一叶微小的扁舟,是作者对自我形象的再创造,曲折地表达了自己虽然被贬后如孤舟蓑翁一般孤立无援,但他依然独钓江雪,保持着傲视风寒的勇气与信念,这正是贬谪之中的柳宗元遗世独立、峻洁孤高的人生追求与人生境界的象征。
由上述例证可知,“知人论世”理论确可作为解读中国古诗的一把钥匙,通过“知人”“论世”两个路径来解析诗歌,不仅能带领学生深入、细致地理解作品的情感和艺术境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带领学生走进古人的心灵世界,与之“交流”,感知他们的人格精神,接受中华优秀文化的陶冶。并且,值得注意的是,“知人论世”不仅是中国古诗鉴赏的利器,它实际上是可以作为一种通则性理论广泛运用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之中的,其理论价值是值得广大语文教师重视并深入挖掘的。
二、以意逆志:寻绎诗心合一的精神共鸣
《孟子·万章上》记录了一则孟子与弟子咸丘蒙的对话:“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词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7]311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之著名理论——“以意逆志”的出处。关于“意”的理解,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其中为后世所熟知的是朱熹的观点。朱熹认为:“当以己意赢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7]312即读诗不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诗之深层意味,而是读者用自己对诗意的理解推求出作者本意,也就是解诗的主要依据是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之意。关于“志”的理解,则有普遍共识。《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8]《礼记·乐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9]均说明了诗是“言志”的一种载体,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实用性、功利性等特点,基本可以将孟子所谓的“志”理解为通过文辞所表达的心志与思想感情。法国学者柏格森曾提出人的心理感受不能以抽象的语言来表达,想要接近它,形象和隐喻是最好的办法。“以意逆志”便是引导学生通过作品的文辞和形象的外在意义去探求作者之志,其最大的价值在于看到了文学作品是因为使用了一定的文学修饰手法而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而这种陌生化则使作品因审美主体的不同而拥有了解读的开放性。将“以意逆志”运用于中学古诗鉴赏教学的课堂,主要任务就是要使学生能够依据诗歌语言而又不仅限于语言,在以“作者之意”为旨归的基础之上结合以接受主体为中心的“读者之意”,在鉴赏这种“陌生化”的同时能够参透文辞之下的深意,并用自己的语言给予具象的表达。
在实际的诗歌阅读鉴赏过程中,不但要鼓励学生用“意”的思想去解读作品,而且还要培养学生具有用“意”的能力。李商隐的《锦瑟》是可以运用“以意逆志”理论进行解读的一个典例。关于此篇之主旨,历来说法纷纭。清代朱彝尊认为:“此悼亡诗也。”[10]而何焯则说:“此篇乃自伤之词,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11]另还有爱情诗、咏物诗等等说法。究其缘由,一方面是李商隐作此篇之“志”隐于文辞之下太深,主旨过于含蓄、隐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同读者的经历与处境有天壤之别,品评诗歌时的感受自然也就大不相同。这就使得学生鉴赏诗歌的过程中,需要在足够了解作者、品读文辞之后充分发挥“意”的作用,在思想上做到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才能够避免在解读时产生徒劳枉作之感。首联“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为诗篇之总起,晚年茕居,形影相吊,作者指责声声锦瑟“无端”,实为荡显心中泛起的层层波澜,在匆匆年华中不断浮沉,聚散别离,人世如烟,全部通过一个“思”字重现眼前。人同此心,心同此情,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但轻尘栖弱草、南柯一梦的缥缈无常,显隐断续的往事,一经驻足,就会现于眉头心上,人总是各有悲欢,于是每个少年心灵中的淡淡愁绪也不免交融于锦瑟之弦而与作者产生共鸣。颔联“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望帝春心、杜鹃啼血,愿望终究不能代替现实啊。再启发学生结合前文所说“知人论世”之方法,联系作者生平,义山多年科考不中,后虽如愿入仕从政,却常与妻儿相隔千里,一朝相拥不免恍惚若梦中。加之,卷入党争而朝不保夕,追求多年的政治理想最终沦为泡影,作者用此二典铭告世人,人生诸事何尝不是如此,烟火短暂,年华易逝。有言“心之官则思”[2]256,心灵认识的极致,是与所探求的对象合而为一。若能启发学生将自己的心志与情绪融入此时此刻此景,走进诗人的世界,就会感同身受,从而更深刻地把握诗歌的情志。颈联“沧海月明珠有泪,良田日暖玉生烟”,为宕开一笔,扩展了诗意诗境。“沧海珠泪”出自张华《博物志》:“南海水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12]“良玉生烟”一说出自干宝《搜神记》,书写的是爱而不得、化烟而逝的故事。诗歌到了这一层,就需要学生充分发挥审美想象力,海面浩瀚、明光月度与玉藏山岩、日暖生烟,良辰美景总如虹销雨霁,触手可及却又遥不可及。只有用主体之心灵去印证对象,形成心灵的“冥契”,在此前提下产生的“逆志”,才不会仅停留在诗歌构建出的形象表面,而是与作者之“意”深度契合,真正理解诗歌的内涵。尾联“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首尾呼应,遥接开端,仍“思”“此情”,却难“追”“华年”,因此一切都只能是“惘然”。事非经过,不知何难,作者尚且不能自喻,无法自明,读者更难确切道出其心声,诗读至此,不宜再引导学生像往常一样将《锦瑟》穿凿、狭窄为对一人一事的喟叹,而是可以尽情地用“我之境”去联想“他之境”,甚至可以做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13]。不过,虽说“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心何必不然”[14],但还是需要注意把握好此“读者之心”的“度”,做到“诗环其中”,将最终旨归锁定在“作者之意”,唯有如此,才能够避免“读者之情”无所依寄,泛滥无归。
需要指出的是,以读者之“意”探求作者之“志”只是解读“以意逆志”的角度之一,但将其运用于中学古诗鉴赏教学,对于目前诗歌鉴赏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分析上墨守成规、解读上千篇一律等问题来说,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能够有效地培养中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激发其创新能力。这种中国传统的“以意逆志”式文心追索与读者体验精神,不仅能为中学古诗鉴赏教学注入理性分析的血液,也赋予了学生——作为审美主体对美进行“再创造”的可能。
三、诗画相通:体悟气韵生动的意境之美
“诗画相通”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范畴的重要命题。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苏轼,其在《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言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5]自“诗画一律”论问世以来,诗画互位言说,逐渐成为了文艺批评的一种时尚。需要辨明的是,“诗画相通”不能片面理解为诗歌与绘画之间简单的相通,它是中国艺术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诗歌与绘画之间,存在着媒介的巨大差异,绘画是视觉的艺术,以“再现自然”为基调,是“有形”“无声”的艺术;而诗歌是想象的艺术,以“言志”为基调,是“有声”“无形”的艺术。简而言之:“画是‘见的艺术’,诗是‘感的艺术’。”[16]随着思想水平的提高与艺术的自觉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古代文人对于表现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在有限的艺术语言选择上,语言的叠加与媒介的交叉成为了扩展语言能指性的良好手段,于是便有了“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17]94,以及“人知诗之非色,画之非声,而不知造乎自得之妙者,有诗中之画焉,有画中之诗焉,声色不能拘也”[18]等说法,也就是说不受声与色界限的束缚才可达到“自得之妙”的境界。由此看来,“诗画相通”之美主要是由于诗歌与绘画通过在艺术特性上的相互吸取与借鉴而取得高于其艺术性质本身的欣赏效果与审美境界,这使诗歌被赋予了更加延展的空间性而具体可感,绘画也蕴含了更加绵长的时间性而耐人寻味。对欣赏效果的把握和对审美境界的提高也使得“诗画相通”这一理论可以完美适应并应用于中学语文古诗鉴赏教学。中学语文教材中很多诗歌篇目都可以运用“诗画相通”来做深度赏析,本文此处仅以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为例进行简要讨论。
《春江花月夜》一直是中学语文诗歌鉴赏教学的重点篇目,鉴赏的角度通常是情、景、理三个方面,即便分析情与景的交融、景与理的交织时涉及“诗画相通”的理论,也只是借此名称作一点套用而浮光掠影一笔带过。实际上,运用“诗画相通”理论对《春江花月夜》进行鉴赏,虽然不是全新的角度,却能够有崭新的发现。
首先,教学过程中需要带领学生解题,“春江花月夜”,由题目看来似乎是如“笔墨纸砚”“琴瑟琵琶”一般不分伯仲地描绘了“春”“江”“花”“月”“夜”五个意象,如此处理似乎也符合常理,但本诗最大的魅力正是在于张若虚做到了有取有舍、主次分明地统一了“春江花月夜”的意象群落。据《唐诗合解》统计:“题目五字,转环交错,各自生趣”,“‘春’字四见,‘江’字十二见,‘花’字只二见”,“‘夜’字亦只二见”,而“‘月’字十五见”,并用“天、空、霰、霜、云、楼、妆台、砧、鱼、雁、海雾等意象以为映”[4]49,从上述词汇出现频次的差异上,直观见出“月”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通读全诗可以发现,整首诗歌实际上以“月”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脉络,按照“月生”“月明”“月照”“月徘徊”“落月西斜”“斜月沉沉”“落月”的时间线索,一时有一时之景象,一幕有一幕之思考。在如此和谐自然的结构之中形成了一幅为月光笼罩之下各处景象彼此辉映、幽然朦胧的春江花夜图,故教学之重点便在于如何对这幅画面进行观与感。诗歌中对景象的描绘主要集中在前半部分,开篇四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19],诗人通过意象的选择与组合充分进行了视觉的延展,以海拓江,提高视点,江静波涌,动静相称,瞬间将一幅“海天相一色”“流波将月去”的宏大景观置于读者眼前,体现出诗人擅长摇曳情态的摹写之工。接下来诗人巧妙地以月之光华统一了江、海、花的大视野,又将整个广阔的景观“透明化”。“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月光同化了整个世界,不仅江水、江岸、天空是烟云渺渺,连花丛也是“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在月光的照耀下像水珠一般晶莹剔透,闪闪烁烁。所以,《春江花月夜》成功地将诗像画一般层层敷色渲染,实现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创造了一幅“有声画”。另外,在教学中还可以援引一些学者的观点,如王国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20]没有情感统一、不发生“质变”的意象群很难共同形成一个美的境界,《春江花月夜》不但完美体现了“诗是无形画”[17]93的艺术共通,并且通过画中之景,将“人何所从来,何所从去”的哲学叩问、将“人生短暂、宇宙无穷”的宇宙意识与哲学思考借助“月”这一意象表现出来,“江上之月”“江畔之人”,这一幅幅虚虚实实的画面,处处蕴含着诗人的诗语和哲思,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意蕴上的“画是有形诗”[17]93。
可见,使“诗画相通”理论不再作为陈词滥调的“面具”而用于深层解读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学生不仅能够感受到诗歌之美,并且能够理解美的内涵,读懂美的实质,去品味诗人所传达的语言之外的形与神,于表于里,内化于心。另外,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打开了学生作为欣赏者的眼光,跳出永远站在“文学本位”立场上的自我局囿,通过文学与其它艺术类型的沟通互联创造出新的解读角度,以期用更前沿、更新鲜的眼光鉴赏诗歌,感悟文学之美。
综上所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是异常丰富的,像“意境说”“思无邪”“滋味说”“神思论”“诗禅论”等等理论命题都有着丰富的课堂实践可能性。千百年来古圣先贤创造和发展了如此繁多、如此高妙的文学理论当然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在切实地践行对美的追求,包蕴着对美的创造。与西方文论相比,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在于体系自有,而不以体系的架构来呈现,系统性的意见潜存于吉光片羽的叙述之中,呈现出拈花微笑般的东方智慧。在西方话语一度占据强势地位的语境下,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弘扬是明智的选择,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将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学语文古诗鉴赏教学相融合,一方面能为诗歌鉴赏教学带来更多的建设性和启发性,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寻找切实可行的方向,这对于重新激发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树立中华文化的自信无疑是有益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