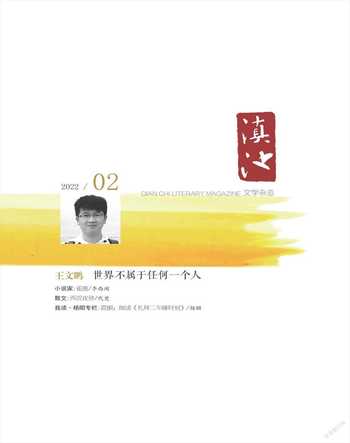劫后
〔越南〕曾广健
第十一郡是胡志明市其中一个郡,是全市最多华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坐落于堤岸区,这是劳动阶层比较多的一个郡。该郡有一个平泰公寓区。三十多年前,这里本是瑞义祠坟场。后来,政府就将该坟场拆迁改建为几栋公寓和一个规划区,住在这一区的人家大都是中高层的。
平泰公寓区一带有医院、学校、少儿宫等。最特色的是,每座公寓楼下,以及该区内一些街道或巷弄,都是琳琅满目的平民咖啡店。每天清早,附近的居民、外来的客人都在这里的咖啡店聊天和吃早餐,几乎都是长年的常客,大部分都是男子,中年和老年人较多。在晌午或下午时段,喝咖啡的人显然较少。
一个还没完成小学程度的十二岁女孩马佩珊,她黑漆的头发只用一条残旧的橡胶圈半扎成马尾发型,约二十公分长,看起来还挺可爱。可是,那张瓜子面上没有丝毫的血色,肤黑又瘦弱的个子,衣着不但又肮又有破洞,而且还有些异味。这套衣服显然是别人给的,因为有些宽大。
佩珊身上背着一个残旧的书包,里面有两套衣服和一张残破的薄被子。她右手拿着一叠彩票;左手手腕挂着一个里面装着几个汽水、矿泉水空瓶的塑胶袋。她从领兵升街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进了平泰区。这里一边是所小学,小学对着的是一个建好刚半年多的公园。但这时公园没有人,树木静静的,一动也不动。此时快到中午时分,阳光强烈,十分炎热,几乎都快把皮肤焯熟。这是胡志明市夏天的气候,所以,很多人外出时都要穿着防晒的衣服,尤其是妇女们,几乎个个从头到脚都包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
佩珊已汗冒满身,她路过公园向前走,来到一个刚建好不久第十一郡少儿宫,看见很多家长正在少儿宫外面等候接孩子放学。今天是周末,他们都送子弟到少儿宫参加课外兴趣班。片刻,各少儿纷纷从少儿宫涌出来,看见自己的父母或兄姐或工人,他们又说又笑,然后坐上机车就回家。
佩珊驻足观看多时,流出羡慕的眼神望着他们。心想,自己曾经也像这些孩子一样,但是好景不长,现在已沦落到只是一个孤儿,衣衫褴褛,四处漂泊街头去卖彩票、拾破旧和行乞。但佩珊没有埋怨也不再多想,她只知道在要继续去卖彩票,否则卖不完又要挨饿了。
此时已是中午,几家大小的平民饭店已开始卖午饭,附近咖啡店的服务员、一些客人或公司、单位的职员下班时都去这几家饭店吃午饭。此时,佩珊就走进这些饭店向食客兜售彩票:“叔叔帮我买张彩票”,“哥哥帮我买张彩票”,“姐姐帮我买张彩票”……
这时,饭菜的香味以及人人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令佩珊更感肚子叽里咕噜。今早的早餐,佩珊买了一条猪肉面包,她只吃了半条,还有半条留在中午才吃。可是现在虽然午饭当前,尽管肚子饿得难受,但她也不能及时吃上,因为她要趁着此时人多的时候,争取去兜售彩票。可是,食客都是劳动工人的,大部分人摇头不买,有的一眼也不看,只顾埋头吃着饭。佩珊在请人家买彩票的同时,若看见地上或桌上别人喝好的汽水瓶,她就拾起或问人家给,然后放在塑胶袋里。
这一区很多人兜售彩票,无论男女,从老到幼,有平常的、也有残疾的,大家都是靠卖彩票为生。因此,他们仿如蝴蝶,这个去了那个来,纷纷地在这一区的咖啡店穿梭兜售彩票。此时,佩珊挨过这个饭店,又到另一个饭店,大部分人都摇头不买。幸好,有一个中年男子在一个咖啡店与两个朋友喝咖啡和吃饭时,帮她买了五张彩票,她心里感到很高兴。
这时,有一位头发短短、满面风霜的五十多岁的女人,大家惯称她梅姨,穿着一件花纹的衬衫和一条到小腿的长裙,她送客户走出咖啡店时,无意中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卖彩票的小女孩在路上向自己这边走来,样子十分熟悉。于是便马上走上前看个究竟。果然,梅姨一眼就看出这个小女孩就是自己的侄女佩珊。
“佩珊,佩珊。”梅姨边走过去边喊着,喜悦中带着忧虑,因为她看见佩珊衣衫褴褛,皮黄骨瘦。
此时,佩珊顺着声音望过去,她用疑惑的眼神望了梅姨多时,显出似曾相识又陌生的样子。
“你是……?”
“我是你的大姑姐呀!”
佩珊显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买一个书包给你上学吗?”梅姨提起往事以勾起佩珊的回憶。
佩珊此时不停点头说:
“记得,现在记得了,这个书包我还背哩!”佩珊就把书包递给梅姨看,便说:
“我和大姑姐好几年没见面了!”
梅姨就摸摸书包,想不到侄女还留着这个自己当年奖励她读书考到第一名的书包,心里涌现暖暖的温情。
“你跟我来!”
于是,她就牵着佩珊仿佛没有肉的手掌往自己刚才喝咖啡的店里走。
“你母亲呢?”梅姨问。
“她已经死了!”佩珊脸色下沉。
“她是怎样死的?”梅姨感到晴天霹雳,难以置信停了下来,深深凝视着佩珊。
“妈妈是病死的!”佩珊鼻子酸酸的,双眼流出凄楚的眼泪。
“死了多久?”梅姨双眼抑住眼泪,与佩珊继续前走。
“都半年了!”佩珊心里一阵绞痛。
“现在你住在哪里? ”梅姨关心的问。
“我呀?四处为家,卖彩票、捡破旧和行乞为生!”
梅姨心里涌现一阵酸楚,追问:
“你哥哥呢?”
“不知道!”
梅姨听了叹了一口气。和佩珊走进了咖啡店。此时,咖啡店里有些客人在吃午饭和喝着饮料。梅姨带着佩珊在刚才与客人谈聊的位置坐下后,问佩珊吃饭没有,她摇摇头。
“你要吃什么菜?”梅姨问。
“我想吃咖喱香茅炒鸡和生鱼酸汤。”
梅姨中午时经常在外面打店的。于是,梅姨打电话,按佩珊点的菜叫了两份外卖午饭。
此时,咖啡店服务员端上一杯冰茶给佩珊,然后问她喝什么饮料?
“我喝可乐。” 佩珊不假思索就回答。“我最喜欢喝可乐,已好久没喝了!”
看见佩珊天真里藏着可怜兮兮的神情,梅姨心头一阵难过。
不久,当两盒饭送上时,梅姨付钱后,就把一盒饭盒打开,顺便把那包的咖喱香茅炒鸡倒在饭上,同时打开了一盒生鱼酸汤。此时,佩珊望着的饭菜已经垂涎,高兴的流出泪来。
“孩子,怎么哭呢?”梅姨不明白的问。
“好久了,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虽然我天天看见很多人吃,但我只能闻到它的香味,我朝夕希望可以吃到一顿好吃的饭,没想到我今天终于可以吃到了!”佩珊直率说出自己的际遇和期盼。
梅姨顿时心里不是滋味,咽着喉咙说:
“那现在好好吃吧!”
于是,佩珊就很自然、很开心地吃起饭来。这时,梅姨才打开自己盒饭来吃饭。佩珊边吃饭,久不久喝两口汤,偶尔也喝一口可乐,不时望着梅姨微笑。看见佩珊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梅姨为她的遭遇感到可怜。
片刻,佩珊吃完饭,把汤喝掉,梅姨微笑地问:
“吃饱了吗?”
“吃饱了,很久没有吃得这么饱,要是天天可以吃这么好吃的饭就好了!”佩珊再一次自然吐出心里话。接着,她匆匆把可乐喝完,拿过纸巾抹过嘴后,站起来说:
“大姑姐,谢谢您给我吃了一顿的好饭,现在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里呢?”梅姨脸色显出讶异!
“我要继续去卖彩票呀,要不争取时间,彩票就卖不完,明天我就没钱吃早餐了!”
是的,卖一张彩票只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但是佩珊每天只卖五十张,利润才五万元(越盾,下同),吃一盒饭起码都要二万五千元或是三万元不等,所以难以维持三餐。
“不要去卖了,跟大姑姐回家住好了,就可以天天吃到好吃的饭呀!”梅姨望着佩珊。
“真的吗?”佩珊天真的半信半疑。
“当然是真的呀!”梅姨抚摸着佩珊的头。
“太好了!太好了!”佩珊高兴的拍起手来。
梅姨吃过饭后,付了饮料钱后,就拖着佩珊的手走到店外,把自己的六十年代的汉达摩托车推到路边,坐上去后,用右脚打动机车后,就叫佩珊坐上车后面和抱紧自己的腰,就载着佩珊回家。
她们从十一郡路经第五郡,过了森举桥到了第八郡,赴一段路走上了二天堂桥,下桥右转就是范世显街,走约一百五十米,梅姨走到进了一条拥有二十间房子的巷子里。这条巷子还不到一百米长,有三米多宽,轿车可以进去。巷子里的房子高高低低,六成半只平房,其余是一两层高的房子,其中有三间房子有四五层高。每间房子的深处从十至十五米,三至四米宽不等。里面住着越南京族人和华人。华人占七成,其中潮州人占一半,其余是广东人。有很多家庭住在这里都有三四代百年以上之久了。
在一九七五年越南南方解放前,这条巷子全是华人居住。在九十年代初,已有几家移居外国,所以售给了京族人,故才有京族人居住。但是,大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十分安宁。巷子多是民宅,很多家门口都有种几盆花。其中有一半房子出租作为商店卖衣服、咖啡店、做文房或倉库等。
梅姨载着佩珊走进巷子将到尽头,便在右手边最后第二间的房子前停下,她打开了围栏的一扇门,走上两步把打开淡黄色的铁折门的两把锁,再用力推开两边门,便发出吱吱的声音。梅姨就把车子推进大厅,放在进口处之外的靠墙那边后,然后再走出去把铁围栏门关上,却没有把打开约一米大的大门关上。佩珊走进家里后,定定地环视大厅一眼。当梅姨把围栏门关上后,就拖着佩珊走进厨房。
开了灯,里有一个冰箱,一个旧式的碗柜,两个头的瓦斯炉,有条不紊的摆放着,厨房也挺干净的。在瓦斯炉上装有抽烟机,抽烟机旁边供奉的灶君爷。在瓦斯炉旁边有个洗碗盆,浴室和卫生间在一起,建在洗碗盆旁边。一张高高的食桌和几张塑胶凳子,放在隔着大厅和厨房那副墙的后面,桌上有个盆子放着几个玻璃杯。厨房里还有一个楼梯上楼,洗衣机放在楼梯下面。
此时,梅姨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冷藏的开水倒了一杯递给佩珊,然后再给自己到一杯喝。顷刻,梅姨就帮佩珊洗澡。这时,她惊见佩珊的手上、腿上有些新旧伤痕和瘀血,便问:
“这是什么?”
“被打的?”佩珊闷闷地回答。
“被谁打的?”梅姨感到心痛。
“很多比我大的孩子,他们欺负我,有的抢我的食物,有的抢我的彩票,我就反抗,与他们打起来!”佩珊脸色愤怒起来。
“现在还痛吗?”梅姨关心地问。
“还有些痛呢!”
洗好澡后,佩珊换上一套刚才回家路上,梅姨顺便载她去买的三套新衣服的其中一套。此时她心情乐滋滋的,没有了刚才愤怒的脸色。
梅姨就帮他在伤处搽药后,带她上了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休息。佩珊不忘顺便把那个书包带上楼去。
梅姨开灯、开冷气。佩珊走进去后,梅姨叫她上床睡觉,关门前说自己要下楼去做点儿事情。
当佩珊躺在一个陌生、有褥垫又舒服的床上。她回想两年多来,已没有躺在这样舒服的床上了。她辗转不能入睡,她望着天花板,中间有一个简单的花饰。这是一个粉红色的房子,在床前的墙上挂着一个四十吋的彩电,电视上有一盏灯饰。床的旁边有一个衣柜和一张办公桌,桌面有一台手提电脑、一个枱钟和摆着很多纸张。另一边的墙上有一部冷气。突然,她看到电视机旁边挂着一张照片。她下床走近仰头看,里面有大姑妈和父母、大哥和她。佩珊忘记什么时候拍的,她看见当时自己还很小的。而这张照片以前家里都有一张,但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佩珊注目多时,突然感到口渴,自然地就走下楼到厨房里倒水喝时,却见梅姨在厨房里切西瓜。
“起来了呀?过来这边吃西瓜。”梅姨一边说,一边把切好的西瓜拿到食桌上,边坐在椅子上。佩珊倒了一杯水,在食桌里坐下来,拿起一片西瓜吃,便说:
“我睡不着!”
“可能陌生的地方吧!”梅姨说。
佩珊点点头!
“哎,不知你大哥现在如何?不知他在哪里!”梅姨又想起又担心佩珊大哥纯义地感叹,双眼充满期望能够找到纯义。
“当年,大哥知道母亲把您给他的学费全部拿去赌博后,他十分生气,一怒之下就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了。”佩珊边吃西瓜边说:
“当时,我们都不知大哥跑到哪里去。而我们的出租房子很多东西,先后都被母亲一一卖光了,而债主经常上门寻找母亲,他们很凶恶,在屋外怒骂不停,时常把我吓坏。而母亲有时不知跑到哪里去,我天天待在家里不敢出门,一天只吃一顿晚饭,都是街坊给我吃的。”
佩珊簌簌地哭着说。
“那么,你们后来去了哪里?”梅姨边追问原因,边走到佩珊身边拍拍她的肩膀地安抚她。
这句话,勾起了佩珊的回忆……
有一天晚上,珊母不知从哪里回来,带着佩珊匆匆忙忙地离开出租屋前往西区车站乘搭客车深夜去了金瓯省(这是越南南部最后的一个省)。但是,付了车费和吃过饭后,钱都花光了。当晚,她们就睡在别人屋檐下。之后,她俩母女由于没有落脚的地方,所以四处流浪。有时睡在桥下、睡在街市的摊档或别人的屋檐下,又挨饿又受冷又被蚊子咬……
每天,她俩母女去行乞,餐饱餐饿。一个月后,她们母女有些钱各自去兜售彩票,生活虽十分艰苦,但可勉强过活。
有一天,债主的两个爪牙在路上碰到珊母,停下车来,一个凶巴巴地指着珊母怒骂欠钱还想逃跑,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有线眼,很难逃出他們的手掌。这时,佩珊十分害怕躲在珊母背后。其中一个打了个电话,然后说:
“大哥叫我们把她们母女带回去!”
于是,这两个样子凶恶的男子把她俩母女拉摩托车上,她们母女不敢反抗,载着她们去到一栋别墅里。那里守卫森严,有几个守卫和几条大狼狗看守。
当他们母女被载进别墅后,那几条狗吠个不停,令佩珊又吃惊起来,紧抱着母亲的腿。而珊母却没有半点畏怯,她想,既来之,则安之,反正逃不了。
于是,她们就跟着那两个男子走进了大厅,珊母就跟那两个男子上了楼,叫佩珊坐在厅里等。好半天,那两个男子就和珊母一起走下来,带着俩母女去了一个已联络好的地方租屋住。
这是一个出租屋的地方,约有十户人家,但房子十分简陋,都是劳动者租住的贫困窟。从这时开始,母女俩有了一个有瓦遮头的地方,虽然只有四平方米大,但总比以前餐风宿露好得多。
在安顿后,珊母带着女儿去附近的超市购买一些家具、日用品和衣服。两天后,珊母匆匆吃过晚饭后,就脂粉浓厚地打扮,穿着鲜艳露胸低背的衣服,全身香喷喷,背上一个玲珑的手提袋,就有一个男子来载珊母去哪里不知道。
珊母当时约四十来岁,虽然有了两个孩子,但她面貌仍那么俏丽,一头乌黑披肩的头发,身材苗条,一米六十五高,因此,当打扮后看起来就年轻了十岁一样。
于是,珊母每晚如是。当晚饭后就去打扮,之后就有人来接他离开出租屋,每晚至半夜三更或翌日清晨才回来。当珊母回到家里时,有时显得疲倦不堪,衣服不换,摊开席子倒在上面就睡着了。
佩珊每天早上就去卖彩票,早餐和中午都在外面吃,一直卖到日落前才回家。当她回家后,珊母已把饭煮熟,跟佩珊一起吃过晚饭后,她就匆匆忙忙去装扮,然后就跟人去了。
珊母天天如此。她回来睡至快到中午,醒来就去街市买菜回来煮饭。吃过午饭后,她又继续睡,到下午四点,她起来洗自己衣服,然后去烧饭,等佩珊回来吃。她很少跟街坊交谈,见面只是点头打个招呼就是了。
有时,佩珊卖完彩票回来,珊母已经出去了。每晚吃好饭,佩珊洗碗、打扫家务;她有时跑到隔壁看电视,有时就去睡觉。珊母也很少跟她说话。有两次,佩珊问她每晚去哪里,珊母只说去工作挣钱。珊母有时买些干粮、糖果、汽水或水果放在家给佩珊吃;也叫她去卖彩票时带在路上吃。
有时,珊母不用跟那些人出去时,她就带佩珊到附近去吃甜品,因为佩珊喜欢吃三色甜品。有时带她去娱乐场玩玩,但都是节衣缩食。生活尽管还欠缺很多,但总算比之前好过。然而,珊母满身还是累累的债务。
一年后,珊母的神态渐渐显得憔悴,身体开始觉得很疲惫,但晚上仍然去“工作”,早上睡觉,日日如是。有时候,她觉得疲倦也没有去买菜煮饭,母女只吃方便面而已。
后来,珊母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去西药房买药吃。但后来越吃越不见好转,感到子宫又疼痛,大便时有血,于是就去医院检查时,才知道患了末期子宫癌。这个病令珊母感到崩溃了,她想自己还年轻,要想再活几年,因为她还要见儿子,请他原谅,补偿给他,但不知他现在哪儿。而女儿佩珊还幼小,将来由谁来照顾她呢?至于说到大姑,她更不敢去见她……一连串的忧虑,她心里感到难受,令她病情加重。
由于没有钱在医院留医,储蓄到些许的钱都拿去买药吃光了。
她们住的出租房子附近有一间菩提精舍,里面主要供奉观音菩萨,香火鼎盛,住持是一位中年的尼姑,她在精舍开了一个西医慈善诊所,每周日下午为病困人家赠医施药。于是,佩珊就陪着母亲去看病。但后来,病情令珊母子宫好痛,不便走动。自从珊母发病那时候起,那几个来载她的男子也不见再出现了。
珊母的病情越加严重,佩珊也没有去卖彩票,待在家里来照顾母亲。她很害怕,哭了很多。
后来,珊母病入肤骨,导致不省人事。这时,得到房东和街坊的协助下,把她送进医院抢救,但珊母在医院的当天晚上就逝世了。还好,在街坊的协助下付了院费,同时得到菩提精舍施棺和代为处理珊母的丧后事。
当珊母的丧事办好后,有户小康之家的主人凤姑,她五十来岁,脸容慈善,散发出高贵典雅的气质,人人都叫她为凤姑。她是京族人,丈夫是当地人的潮裔商人。凤姑乐善好施,经常帮助别人和捐钱给菩提精舍的慈善诊所。在诊所时就知道珊母病情了,平时有送些食物予佩珊母女。
现在珊母去世了,只剩下佩珊孤零零一个。当办好丧事后,凤姑便问佩珊原来住在哪里?还有亲人吗?佩珊说原本住在胡志明市,有一位大哥和大姑姐,但现在不知他们在哪里了!凤姑问佩珊有什么打算,她说母亲临终前叮嘱她一定要回胡志明市找大哥或大姑姐投靠,但没有大哥的电话,大姑姐的地址和电话被弄掉了。
于是,凤姑给了佩珊一百万元,同时带她到车站搭车返回胡志明市找大哥。凤姑还给了佩珊的电话,叮嘱她如果找不到可以回来在她家工作。
当梅姨听了佩珊阐述,把头往后仰了一下,然后拭去眼角的泪水。梅姨明白珊母当时被逼是做什么工作了,但不好告诉佩珊。梅姨对珊母没有半句怨言,只为她的遭遇感到悲哀!
珊母命苦,她十七八岁嫁人,后来丈夫早逝;现在患了癌症也撒手人寰了,她才四十岁。为什么她们夫妇都英年早逝?而留下的两个孤儿,其中一个还不知下落。
想着想着,梅姨用沙哑的声音问:
“你母亲安葬在哪里?”
“灵灰放菩提精舍里供奉!”
梅姨点点头,用右手再拭去流出的眼泪。
抑郁在心里的话,佩珊今天才能倾述出来,心情轻松了许多。于是,佩珊咽了咽口水,继续说:
“当时,我返回胡志明市后,回到自己以前的出租屋时,屋主说大哥曾经回来过,但是说我们搬走了,他从此已没再出现。而我又不知您住在哪里,所以我就去卖彩票。但是彩票利润不够过活,所以没有租房子住。”佩珊继续阐述自己的遭遇:
“我每天一大清早就去卖彩票,中午只是简单充饥,然后继续卖彩票和拾破旧,晚上去一些路边的卖酒餐厅兜售彩票,九点左右就坐在路边等一些好心人来发饭吃。吃后,我有时睡在桥底下,或是睡在别人的屋檐下,或是街市里……”佩珊的神情显得十分可怜。
此时,梅姨泪已满面,把佩珊拥进怀里说:
“可怜了侄女,希望能早日找到你的大哥,大姑姐会在有生之年,代替你父亲把你们养大,给你们过一个好的日子!”
每晚吃过晚饭,梅姨洗碗后就去洗过澡,然后和佩珊一块儿看电视。可是,梅姨今晚与以往不一样,但当她洗澡后,却就换上一条深蓝色带有浅浅白色花纹的长裙,然后在左胸前别上两朵白花,给裙子添增高雅气质。梅姨再涂上淡薄的脂粉,当打扮起来时显得年轻和高雅。梅姨叫了一辆出租车到西贡去,她告诉佩珊去找纯义,叫佩珊留在家里看电视和先睡觉,不要等自己。
原来,梅姨月前曾去佩珊以前的出租屋给房东留下电话,托她如果有纯义的消息通知她。所以在数天前,那房东打电话告知梅姨她的儿子见到纯义在西贡的KingDom酒吧里面工作。当梅姨知道纯义的下落时,她喜出望外,所以趁着周末有节目表演的今晚,梅姨便去找纯义。
KingDom酒吧坐落在市中心的西贡的黎笋街。黎笋街一头对著是独立府(即旧总统府),另一头对着的是胡志明市动物园。这条街两旁,一边是著名的红教堂后面,一边是钻石商场。再往前走,就是法、美、英等国驻胡志明市的总领事馆;还有五星大酒店、商场、餐厅和几个政府机构等,都是上百年的别墅建筑。
那家酒吧就在法国领馆对面一条小街的街角里。当梅姨抵达后,那时才是九点,里面才三五个客人。梅姨就选了一个角落坐下,点了一杯饮料和一碟水果,不时东张西望,只见几个充满帅气的男女服务生走来走去,但没有一个是纯义的。酒吧里的音乐震耳锤心,但是,为了寻找纯义,虽然患有心脏病的梅姨还是强忍着难受,默默坐在音乐沸腾的环境里等候。
时间越来越晚,客人越来越多,红灯绿酒,大家觥杯交错。强烈的鼓乐,喧嚷的人群,音乐比初时更加激烈劲爆,灯光幽暗却闪耀令人炫目。对于喜欢夜生活、喜欢出入舞场、酒吧的人,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个非常热闹充满刺激的场所。但是,对于梅姨来说,只是一个深受折磨的地方。
当深夜十一点,六个高度一样、身材差不多的妖媚少女登上了酒吧中央的舞台上,她们就晃动着身子,好半天,就脱掉那薄薄的大外套,露出白皙光滑肌肤上,穿着黑色皮革的内衣和内裤,在闪烁迷离的灯光下跳动,令人入迷。她们随着音乐扭动着自己的腰肢和臀部,时快时慢,格外令人注目,挑逗的暧昧气氛弥漫着整个空间。台下的客人,男男女女疯狂地边挥手边喊叫,气氛越来越沸腾。
大半天后,音乐突然由快转向缓慢和神秘,闪烁的灯光也停止跳动。一盏大白灯照向一个房间里,六个穿着黑色长大皮衣和戴着墨镜、威风凛凛的俊男走上台去。
他们走上舞台后,就和那几个舞女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过了一会,那几个舞女就走下台回到房间里。此时,那六个俊男继续跳了片刻,跟着一个潇洒的动作把大衣脱掉,扔到舞台之外。原来,他们赤裸全身,只穿着一条三角黑色的内裤,晃动着身躯。他们个个身材魁梧,还露出六块结实的腹肌,十分性感,所有客人的眼睛都集中于他们身上,随着音乐快速的节奏和闪烁的灯光不停地挥手,同时呼应地喊起来,酒吧里的气氛顿时沸腾起来。
此时,在那一暗一明的灯光里,梅姨透过那个厚厚的老花镜看见台上其中一人好像是纯义,但不敢相信,她使尽眼力也不敢确认那个是纯义。
在舞动多时,这几个俊男很干脆抛开墨镜继续表演。此时,梅姨刚才看见那个舞男现在就确定是纯义了。她不堪目睹,心里抽搐难受,她为纯义感到羞耻,无法接受。她万万想不到,当年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侄儿,今天竟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
梅姨不忍再看下去,付了钱,便跑到酒吧外透透气,好让晚风吹走刚看到一切的阴影。好半天,梅姨再没有进去,只坐在门口等纯义下班。若有人出来,她都望望。快到凌晨两点,梅姨终于看见纯义出来了,就马上喊着他的名字:
“纯义、纯义!”
纯义顺着背后的声音回望过去,看见一个中年妇女。他对眼前这个女人依稀中感到仿佛熟悉但又陌生。于是便走过去一看,他顿时愣住了,不敢相信地眼前的女人竟是没见两年的大姑姐。于是,激动得喊了一声:
“大姑姐,您怎么会在此呀?”
声音中带着无限感触。
梅姨激动地笑中带泪一连串发问:
“你最近好吗?你怎么不来找我?你现在生活如何?你现在住在哪里?”
“当年我还在读书时,都是您来探望我们。我不知您住哪里,我又没有您的电话,不知怎样联络。”纯义流露着无奈的神态。然后继续说:
“现在我需要回家休息了,请大姑姐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我去您家再说清楚吧!”
于是,他们互相留了电话,梅姨叫纯义明早八点过去,佩珊都在家等他。
纯义点了点头表示答应。他目送梅姨坐上计程车离开后,才跟几个同事离去。
本来,纯义习惯和同事下班后去吃宵夜,但是今晚他不去。刚才,梅姨告诉他已找到佩珊,他感到惊喜,一个可怜的妹妹。但听到母亲死了,他心里冒起一层郁闷。毕竟,母亲是一个带他们兄妹来到这个世界的女人,也是一个毁掉他们一家幸福和前程的妇人。
今夜,纯义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一幕幕往事辗转到天亮。
翌日,对于纯义来说是半年以来最早起床的一天。因为他是晚间工作至深夜,所以一般都睡过晌午。他和三个男同事合租了一间公寓的房子住的。但是今天,在同事还在睡梦乡里,他一大早就起来梳洗后,就换上一件黄色的T恤,穿上白色的牛仔长裤和穿一对蓝白色的运动鞋,再戴上墨镜。他那俊俏的脸庞,魁梧的身材显得玉树临风,魅力洋溢,名副其实的阳光俊男。
当纯义下了楼,牵出摩托车,戴上安全帽骑上车后,就向目的地开去。好久的一段时间,他没有见到清早的阳光,所以他觉得今天阳光特别的美丽,路上的风景朝气蓬勃。从西贡去到堤岸区,大概20分车程。当纯义来到梅姨家的时候,正把摩托车放在门口锁好时,佩珊就马上从屋里跑出去抱住纯义,喊了一句动人心魄的“大哥哥!”
此时,纯义蹲下来,俩兄妹互相紧抱着。梅姨在家里看见他们兄妹这一幕,被他们感动得眼睛红了起来。
于是,纯义就抱着佩珊走进家里,坐下后,梅姨问吃不吃金边粿条?纯义点点头。于是,梅姨边走进厨房边打电话到巷口卖金边粿条的小店叫了三碗;同时端出三杯冰茶,分别放到每个人的前面。
梅姨此时打量着纯义,好一张俊俏的脸庞,不过比以前成熟了很多,满脸带有风霜,而且还有副健康的身材,青春年少,是多么美好呀!
这时,纯义先打开话题:
“当年,父亲死后再没有和大姑姐见面了!”
“是呀,都三年了。當你父亲去世后,我多次要见你们,你们母亲说你们要上课,要补习,要读其它科,没有安排到时间,所以一直都见不到你们。”梅姨说:
“但是,她有告诉我你们的学习情况。”
“我们也曾多次问母亲为什么不见大姑姐来玩,但母亲说您很忙。我们说打电话给您,她总是说改天吧,说您这个时候没空,那个时候您不在家等,不要打扰您!”纯义疑惑地说。
佩珊接着说:
“是呀!但是后来我们要搬家逃债,所以没有再提到这个问题,从此失去联络了!”
梅姨摇摇头,难以置信弟妇如此无情阻止姑侄联系。
此时,金边粿条送上。这是高棉族的特产食物,有鲜虾、猪干片、猪肉片、肉碎和鹌鹑蛋等,配着几样青菜一起吃。
他们三人就一边吃一边说话。
纯义望着佩珊问:
“妈妈是怎样死的?”
“她是病死的!”佩珊答。
“什么病?”
“子宫癌。”梅姨抢答,不想多说珊母的遭遇。
纯义听后,心里感到有点疼痛。
“其实,当我考上大学后,母亲有告诉我说您有给我钱交学费。那时我很高兴。可是母亲没有帮我交学费,她拿着那笔钱去赌博,当我知道后十分生气,痛心欲绝。”纯义望着梅姨十分激动地说:
“后来,母亲说她害了我不能读大学。但我劝她金盆洗手,不要再赌博了。我去工作养家,叫她也去帮人家做点杂役来过活!可是,她这边答应我,那头却继续赌,不知怎样弄到还欠了一笔大钱,当我知道后,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数日后,我回到出租屋房东说她们搬走了。那时我还没有电话,我还借朋友电话打给母亲不通,就这样失去了母亲和妹妹的消息,我不知如何是好!”
梅姨此时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望着纯义说:
“你的学费我给了你母亲后,两个月不见你母亲联系,于是就拨电话给她,但不打不通。于是,在一个周日我跑去找你们,但房东说你们两个月前已经搬走了。我深感奇怪,翌日便前往医药大学找你时,但是经过校方调查后,说你的确考进了该学校,却没有前来报名就读。”
其实,梅姨曾四次三番打电话给纯义的母亲都拨不通。梅姨感到十分失望,她很担心他们母子不知发生什么事。但是自己已尽力东翻西找,却不知他们的下落,只好嗟叹与默默地为他们祈福。
“当时,我只有拼命努力工作以安顿生活。但是,我也有时回到出租屋寻找母亲和妹妹,同时也打探大姑姐的消息,可是一直都没有联络到。从此我忙着工作,自力更生。在半年前,我就转到酒吧工作,收入比较好。现在,可以与大姑姐和妹妹重逢,我感到十分高兴!”
就在这个时候,佩珊说:
“妈妈临死之前嘱咐我若有见到你们后说几句话。”
“什么话?”梅姨和纯义不约而同地追问。
“她说对不起你们,请你们原谅她,她毁掉了我们兄妹的大好前途,若是来世有缘,她会双倍奉还今生欠下我们的一切!”
此时,梅姨和佩珊哭起来了;而纯义心里有一点抽搐又难过。
本来,纯义兄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的母亲叫冯美仙,外公早亡。她只有两姐妹,大姐已嫁到北部去,很少联系。当年,珊母十八岁就出嫁了,年底就生下了纯义。在两年后,珊母的母亲因病而撒手人寰。
纯义的父亲比妻子大六岁,他大学毕业后娶了纯义母亲。纯义的父亲中英越文相当好,于是就在平阳省一家台资公司工作,当主管兼翻译,薪资相当不错。两年后就生了佩珊,他们在第五郡一条巷子内租房子住。
妻子在家料理家务和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也挺悠闲的。他们家的街坊邻里,许多都有赌博的习惯。当无聊时,珊母就跟街坊玩起字花的赌博。
可是家门不幸,在纯义十七岁正读高中十二年级那年,有一天,他父亲陪总经理到生产车间检查产品时,不幸被一部卷铁机卷进双手至身躯。虽然及时制止,但失血过多,在送到医院路上就一命呜呼了。
一个晴天霹雳劈散了他们一家的幸福,他们痛心疾首。他们领到了灾难保险费和公司的补偿费,但始终家庭失去了生活支柱,家道中落。
纯义的父亲不幸英年早逝,当年才四十一岁,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儿女。纯义对母亲说要停学去工作来帮补家计,但其母亲不肯,叫他继续上学,读好高中才算,目前还有能力供他们兄妹读书。
纯义的父亲有位大姐梅姨,看见弟妇寡妇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肩起这头家是十分辛苦,而自己没有结婚,孤身一人,做保险经纪。于是,也经常有帮补他们的生活费。
由于纯义的母亲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当丈夫过身后,她做了接收字花赌博工作以赚取一些分红来养家。有一天,有一个人叫纯义母亲帮买个“八十五”号数字,包括买全组和头尾;而头尾两个数字都买很多钱,总共买起来的费用就三百多万。但是,一般人很少花这样一笔大钱去买的。于是,她起了贪念,收了别人的钱却不帮人家买,怎知当天下午就刚好开正“八十五”号,不但在头,在全组里也有两个“八十五”号。于是,她要赔偿,金额很高,丈夫的保险赔偿金也不够支付这笔中奖金额,于是就去借高利贷来赔偿给人家。
从此,纯义母亲继续帮人家收买字花,一边自己赌博,以博取中到钱可还给高利贷。所谓“十赌九输”,珊母一直想赌一赌以赢回一笔钱来还债,可是她没有横财运,总是输输赢赢,但输多赢少。
两年前,纯义他高中毕业后就考中了两间大学,他就选了胡志明市医药大学读医科。这是一间名校,学费很贵。珊母手上只有二百万元,还不到学费百分之十。于是,她就拿着这二百万元去赌一赌,希望中到一笔钱来给孩子交学费。可是,天与愿违,全部都输光。
珊母便去告诉大姑梅姨说纯义考中了两间大学,他纯义选了医药大学来读医科,学费要二千多万,但没有能力给他交学费。梅姨感到很开心,于是马上就拿了二千多万给珊母给纯义交学费。当有一笔钱在手时,珊母又想赌一赌,希望可以把这笔钱连本带利中回来,到时不但可以给孩子交学费,而且可以还清债务。
可是,一次、两次、三次……纯义的母亲始终把纯义的学费都給输光了;而纯义的大学梦就此破碎了。虽然珊母有向孩子解释理由,但纯义当时伤心欲绝,万念俱灰,一怒之下就离家出走跑掉了。
自从那次后,纯义一直埋怨母亲,更加痛恨赌博。其实,自古以来赌博已夺走了多少性命,摧毁多少家庭和幸福,但偏偏很多人却要沉迷下去,因此欠债累累。本来,纯义朋友介绍他到澳门赌场工作,容易挣钱;但是一想起又是赌博,非义之才,所以就拒绝不去了。
现在,面对母亲病亡,纯义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是否太过冲动?不知自己怨恨母亲选择离家出走是对或是错呢?纯义正在左思右想。
“你现在搬回来跟我和佩珊一起住吧!我还有一个空着的房间。”梅姨打断了纯义的沉思,充满殷盼地望着纯义说。
可是,纯义说自己已习惯在外面与朋友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他叫妹妹放心与大姑姐居住,他会时常回来看她们的,他会挣更多钱给妹妹继续上学的。
梅姨也尊重纯义的选择,毕竟他都已经长大了,但劝她不要在酒吧工作了,大姑姐的家随时打开门欢迎他回来。
“我要回去了!”纯义站起来说。
“你不留下来吃午饭吗?”梅姨温柔带笑望着纯义。
“不用了,我们舞蹈组今天要练习,今晚要演出。” 纯义一边说,一边走到门口向梅姨道谢后,便跟梅姨和佩珊说再见。
“重阳节快到,到时我们一起去拜祭母亲吧!” 纯义抛下这句话后,骑上车就离去了。
目送纯义离开后,梅姨心里暗忖:如果他们的父亲不是早逝,可能他们有一个幸福家庭。现在,这两位侄儿遭遇到凄惨的处境,难道这就是孽障?
算了,虽然自己已上年纪,但还可以卖保险赚钱,希望在有生之年,代替弟弟给他们兄妹一个补偿。
曾广健 1981年生长于越南胡志明市,祖籍广东清远。胡志明市华文文学会执委、越华写作者俱乐部秘书。 2011年出版新诗集《美的岁月》,2014年诗文集《青春起点》。2018年荣获“亚细安华文文学奖”;两次荣获胡志明市“青年笔锋奖”及其它国内外文学创作奖项。荣获“越南南部东区杰出青年”与连续3届“胡志明市杰出华人青年”等称号及其它表彰。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