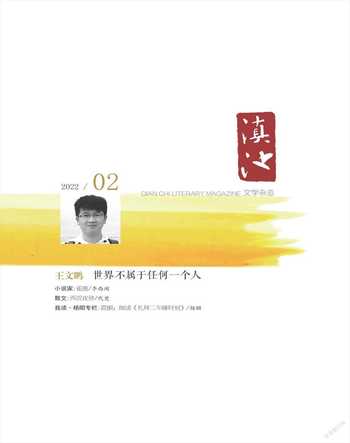龙笏(中)

赵焰 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异瞳》《彼岸》《无常》,中短篇小说集《与眼镜蛇同行》,历史传记《晚清民国四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晚清之后是民国》),文化散文集《思想徽州》《行走新安江》《千年徽州梦》《风掠过淮河长江》,电影随笔集《人性边缘的忧伤》,散文集《此生彼爱野狐禅》等30多种。
茶禅一味实是“空”
茶最初是药——神农尝百草,身边带的就是茶,吃了有毒的草,嚼几片茶叶,毒性就没有了。茶能去毒,也能去火、解乏、提神、强心、明目,这应该是中国人早就知道的。茶成为饮品,是魏晋之后的事,先在僧侣中时兴,再传入社會。它的兴起和发达,跟佛教文化的东传有关系。茶为什么为僧人所喜欢?因为僧人有时间和精力,可以细细把玩茶的味道。佛教重视直觉,僧人味觉敏锐,能分辨出茶的好坏。茶不仅可以提神,有助于僧人们修行,养精蓄锐集中精神,还在它的味道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空”——品茶,跟人开悟后对人生的感觉很相似。人在世界上,本质上是苦的,可是苦中有甘,苦尽甘来,甘苦交集中,有无限的空蒙和虚无感。意识到人生的悲苦,咂巴着人生的甘甜,此所谓觉悟有情,乃清风明月大境界——一如茶的芳香。
茶味,既是空,又非空,是一种最本真的味道,也是一种最旷远的味道。禅味,也有这样的意味,既处于最本真的状态,又处于最觉智的状态。都所谓戒生定、定生慧、慧生禅,这一个步骤,有简单呆板之感。人喝茶,可以一步到位,从茶直接悟到禅,找到相同的感觉。禅是人在最智慧,世界在最本真的状态下,交融而呈现的一种状态和感觉。茶禅一味,即是三昧。
茶不仅有佛学的通感,更有儒学的通感——茶的味道,即是端正、冲淡、静虚、温润,是不折不扣的饮中君子。
世界上第一部茶叶著作《茶经》,就是曾当过和尚的陆羽所著——陆羽对寺院生活不陌生,对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的生活也很熟悉。陆羽在《茶经》中提及了选茶、炙茶、碾末、取火、选水、煮茶、酌茶、传饮八个主要程序,还记载了三位僧人的茶事:第一个是单道开,东晋人,在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常以饮茶来解困驱眠;之二是北魏名僧法瑶,长年住在吴兴武康的一座小山寺中,严守戒律,仅以蔬菜入食,用膳时也只饮茶;其三是昙济道人,是位著名的高僧,避居于寿州附近的八公寺中。南朝宋国新安王刘子鸾与兄弟豫章王刘子尚来拜访,昙济道人以茶茗招待。子尚尝后,赞不绝口,说:“这真是甘露啊,怎么能称它为茶呢!”
这一句话有潜台词:原以为茶都是难喝的,没想到茶如此好喝。估计那个时候,茶主要限于药用、解渴、解酒、祭祀、养生;也有当汤喝的,加入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煮沸了喝,既咸又浓,至于用途,主要用来醒酒,或者解暑。
唐代画家阎立本,有长卷《萧翼赚兰亭图》,画的是唐太宗御史萧翼从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的弟子辩才手中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骗取到手的故事。画面右侧,是辩才和萧翼在谈话,左侧,则有一老一小在煮茶。画面上的情景,说明唐朝初年,已有喝茶之风了。
饮茶由僧人示范,慢慢推向社会,成为一种习俗,茶文化也随之蔓延开来。不过那时的茶,尚没有一个“道”,没有内在精神,喝茶就是喝茶,没有提升到美学和禅的层次。唐代白居易有诗:“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望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这是写的大碗茶,说明那时候对于多数人来说,喝茶与喝水区别不大,还是比较随意率性。
茶遇到宋,如鱼得水,故产生了茶道。宋朝国泰民安,崇尚理学,勤于思考,社会有静气,少浮躁,自然爱好喝茶。理学兴起,注重生命过程,也注重事物的过程。这样的理念,有助于茶道的产生,也有助于茶道的兴盛和发展。茶在宋朝发扬光大,还跟宋代皇帝有关。宋代的皇帝,个个有文化,个个爱好艺术,个个爱好喝茶。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皇帝爱喝茶,社会上自然茶风兴盛。宋代出瓷器也出茶,有很多瓷器,其实跟喝茶有关。
茶饮后来的发展,分三个阶段:煎茶、点茶和淹茶。唐朝之时,喝茶以煎茶为主。古法制茶,一般是将摘来的新鲜茶叶,放在蒸屉里蒸,随后放置石臼里用槌不断地击打,再将它们压入一个模具里,制成片茶、团茶或饼茶,随后在烤炉中烘干。待饮用时,将固形茶碾成碎末,放入釜中煮开,加入芝麻、黄豆、盐、香料等饮用。如此喝茶方式,跟现在草原民族吃马奶子茶之类差不多。唐代有胡风,如此喝茶方式,颇有胡风。
宋朝的饮茶是点茶,特点跟唐朝不一样了,不再加料,而是注重品尝茶叶本身的味道,是所谓注重“真味”。茶的做法区别不大,一般是蒸屉晒干或烤干,茶饮时一般将团茶饼茶碾成粉末置于碗中,注汤点饮,有分茶、斗茶等技趣性的品鉴游戏。茶上的泡沫被认为是精华所在,泡沫浓,茶就好。这一点,从现在的日本茶道中还可以看出。日本的抹茶,就是注重茶饮的泡沫的。
茶道,一般来说,产生于宋。喝茶的人多了,喝茶喝久了,便因喝茶产生一系列的程序、规范和要求。隐士的总体精神,是“人在山水间”;茶道的总体精神,则是“人在草木间”。人与草木,物我两忘;视茶为心,以人为茶。人若能修成植物,去心去火变成茶,是最高境界。如此状态下,自然有无数“玄学”。至于基本内容、基本精神,无非一个“闲”字——是放松,也是自由。闲时方知茶真味,人无闲心,不放松,不处于自由状态,嗅觉和味觉不能最大释放,就不能品出茶的滋味。“闲”同时也是静虚,与戒定慧有关,切合了中国茶道的真谛。说白了,茶道就是要求放下功利,自然而然,心在事物的过程当中。饮茶的过程即是这样,以水润茶,以茶润水,煮水、泡茶、啜茶等步骤,按部就班,一步一趋,做的极其细致认真。行为和心灵互相观照,以此自省:道在过程中,不在结果中。
明人陈继儒《岩栖幽事》中说:“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六七人曰施茶。”这是什么?这就是茶道。
茶道让生活艺术化,也让人生哲思化。宋朝茶道,与程朱理学要求类同,也是要求正心、诚意、修身。这一个“理”,既是儒,是道,也是禅。宋朝之所以在智力上有极大的开拓和上升,文化风格上有着整体的幽深和雅致,茶起着无形的作用——茶是机缘,是暗示,也是释放。茶让人愉快,茶道的意境,也让人受教——喝茶者可以从天青色的瓷杯、琥珀色的茶水,静谧而优雅的过程中,感觉孔子的温润、老子的旷达、释迦牟尼优雅的智慧,悟彻到生命的无限与广博。
什么是禅?只要细细地品尝茶的滋味就明白了,那种无法捕捉的空灵,难以表述的甘和苦,难以言喻的身心茶合一状态,就是禅。在现场情境的导引下,身、心、灵全面打开,全面融合在一起。这时候整体的感觉,是超越语言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语言和文字达不到的地方,禅和意境,已在那里微笑凝视了。
人,若能明白事物超越语言之上,若能明白语言的缺陷,竭力让思维和感觉抵达语言文字的边际。智慧也好,神通也好,必定随之产生。陶渊明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这个意思。
多说一句:音乐上的休止符,中国画的空白,数学上的零,哲学上的“无”……都是彼此的边界。人以边际为警醒,以手指月,便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茶与禅,是东方文化的“双生花”。它们一起生——茶饮诞生的年代,也是“禅”诞生的年代;也一起长——有茶即有禅,有禅即有茶,二者不可分。茶与禅在唐宋之后结合得很紧密,有很多关于茶的公案,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诙谐幽默、暗隐机锋、意味深长。《景德录》说及吃茶的地方竟有六七十处之多。《指月录》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处,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院主当下大悟。这便是大家熟知的“吃茶去”公案,赵州禅师三称“吃茶去”,是因为煎茶饮茶这等事,在僧人眼里却同佛性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吃茶即是修心,修心即是吃茶。
茶禅一体,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茶叶中含有咖啡碱,可以兴奋中枢神经,使肌肉的酸性物质得到中和,消除疲劳,提神益思,在生理上使人宁静、和谐,有助于出家人打坐念经,也可抑制性欲,避免出家人心思走偏。在精神层面上,茶道提倡的清雅、超脱、俭德、精行,合乎佛家淡泊的人生态度。茶虽然不能达到“空”,却有利于人“空”起来。
茶与禅,在更多时候,有镜花水月般的关系。禅能通神,茶也能通神。唐代名僧皎然在《饮茶歌》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这哪是喝茶,分明是悟道。
古时一些名山大岳中的寺院附近,常常辟有茶园,最初的茶人,大多是僧人。很多名茶的出现,都与佛门有关。西湖龙井茶,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天竺寺翻译佛经时,从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天台山带去的;四川雅安的蒙山茶,相传是西汉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直所栽,称为“仙茶”;庐山云雾茶,是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江苏洞庭山碧螺春茶,是北宋洞庭山水月院山僧所植,它还有一个名称,叫作“水月茶”。除此之外,武夷山天心观的大龙袍、徽州的松萝茶、云南大理的感通茶、浙江普陀山的佛茶、天台山的罗汉供茶、雁荡山的毛峰茶等,都产于寺院。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自然与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最初也由僧人种植;惠明茶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至于普陀佛茶,因产于普陀山,最初是僧侣献佛、待客用的,所以干脆以“佛”命名了。
和尚为什么会品茶?一是出家人心静,三昧自从静中来;二是出家人味觉少污染,比在家人敏銳得多。茶的玄妙,其实在细微。和尚能品出茶的三昧,自然能培植出好茶。
中国文化主“静”。静极了,好东西都出来了。由“静”而出的文化,余韵缭绕,有一番说不清道不明的美感和舒适感。中国的茶,有禅性,有诗性,有完美精神,好茶必须纯净,不沾一丝纤尘和油渍,清冷脱俗。与茶的平易、隽永、智慧与含蓄相比,葡萄酒过于高冷,咖啡过于浓烈,可可则冒着天真的傻气。
茶清淡冷隽,酒浓郁热烈。茶与酒相比,茶是渗入,酒是刺激:茶顺应人的感觉,调动人的感觉;酒是刺激人的感觉,迷乱人的感觉。茶与心灵有关,酒与情绪有关。茶,主要是用来谈心的;酒,主要是用来拥抱的。
茶还会产生通感——以茶来喻女人,也有意思:绿茶清新香甜,味同少女;黄茶半发酵,味醇浓郁,味同少妇;红茶全发酵,苦尽甘来,味同老妪。至于普洱,兼收并蓄,风吹雨打,杂树生花,实足江湖。喜欢普洱的人,一般都是老茶客,能从一盏茶中,品出江湖的深浅,人世的冷暖。
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都有玄学。玄学,也是双面性:好处在于有极强的通感,有艺术性,能捕捉细微的差别,领略不确定的精神,游离其中,玄美异常;弱在理性能力弱,逻辑能力差,经常扩大感觉,失之严谨,随意评判,故弄虚玄。
明之后,茶叶制作出现了“革命”:茶叶采摘后直接烘烤,随后泡发饮用,是谓淹茶。茶叶“革命”,其实是被动的——蒙古人统治九十七年,把中国传统文化搞得支离破碎,上气不接下气。茶的饮法,自然变化很大,元人喝茶,又回“胡风”:把茶叶跟牛奶混在一起,加入各种佐料一起煮。等到蒙古人逃往大漠,明朝人已不知宋人点茶的具体步骤——有学者注释宋代书籍,竟不知宋朝点茶用的茶筅的形状。于是明人饮茶“重打锣鼓重开台”——直接泡发饮用。明人于茶,不再是吃,是呷,以一种简单方便的方式延至现今。
茶,唐煎、宋点、明淹,即唐朝以煎茶为主,宋朝以点茶为主,明清之后,以淹泡为主。茶很神奇,煎也好,点也好,淹也好;不发酵也好,半发酵也好,全发酵也好……不管怎么糅弄,各有各的味道,都很好喝。茶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有魔性,怎么弄,都是一个“好”:采摘下来,立即用火烘烤,是为绿茶,好喝。放一段时间,待半发酵后再烤,为乌龙茶和黄茶,好喝。放较少时间,待全发酵后烤干,为红茶,好喝。把它揉成一团,压成团饼,或烤或不烤,随意放置,为普洱茶,好喝。做成砖块,跟牛奶在一起煮,为奶茶,同样也好喝。茶大多是用炭火烤出来的,可是揉一揉后,放在太阳下晒,这是古法白茶的做法,同样也好喝。
茶,只要品质好,或揉或酵或烤或晒,或青汤或黄汤或白汤或红汤,就没有不好喝的。
茶之事,茶之道,想想很怪,也觉得不怪。茶余味绵长,仿佛有启示。一部茶史,仿佛就是一部启示录。
说茶与禅,自然离不开日本。茶在唐宋之际传到日本,日本茶道沿袭的,是唐宋时期的寺院一脉。跟中国茶道的清静放松、自由自在不一样,日本茶道特别讲究精神敬修,主要精神是“四谛”:和、敬、清、寂。这些要求,与静虚大差不差,体现日本文化的清浅简洁之风,也更转向虚玄。日本受佛教影响,视角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万物有灵,视一切事物有生命,此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花也好,茶也好,植物也好,凡自然生长的东西,是有生命的;那些由人创造出来的物具也好,器皿也好,也都视为有生命的东西。茶道与其说是仪式,不如说是对生命的敬奉,所以格外郑重其事,也视若一场净心清魂的法事。生命本身是短暂的,也是不完美的,茶道试图表达的,就是生命在短暂和残缺中,所能达到的完美与和谐。
茶道的关键,还是互动,以物通人,以人通物,人物共同通神。静思、冥想与互通,都能激发人们的潜能,认识到事物的纯洁与和谐,最终体会“道”之所在。
日本文化,螺蛳壳里做道场,极度地敏感,极度地讲究,极度地精致,又极度地自恋和自怜。作家冈仓天心说,日本文化中,武士道精神,是“死的艺术”;茶道,是“生的艺术”。
冈仓天心的《茶书》,名义上是说茶,其实是一本无茶之书。意在人,不在茶。冈仓天心以茶喻人,评价人说: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难以体会人生中酸甜苦辣所蕴含的种种乐趣,会被说成是身上“没有茶水”。相反,如果一个人过于唯美,桀骜不驯,无视人间疾苦,只知沉溺于个人情感,我们则会指责他身上“茶水过多”。“茶”,在这里,是一种灵性的质地。
茶文化,基础是修身养性、节制欲望,特质是古典情怀,以物养心。咖啡文化,基础是商业关系、欲望实现,特质是以强刺激给现代生活补充能量。这些年,诸多茶馆败给了啡咖吧,其实是修身养性败给了现代商业;是虚无缥缈的玄学,败给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酒中不仅有乾坤
人类为什么要喝酒?人类存在于世,天生有无助感,有无力感,有孤独心。孤独要找安慰,要“打鸡血”。找来找去,找到了酒。酒可以让人血液加快,无所畏惧,气壮如牛。从生理学和医学角度讲,人类血液加快循环时,大脑会出现空白,凡大脑出现空白时,即成为愉悦。酒是这样,毒品也是这样。只不过毒品对人的神经系统伤害太大,所以要禁止。人死亡时,大脑空白,以此类推,死亡应该不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酒让人不再寂寞,输入快乐和自由,于是酒成为人们的好伙伴。
中国酒的历史很长,会种粮食的同时,就应该会生产酒了——粮食堆积发酵,产生了最初的酒。中国的酒,大多为粮食酒;西方的酒,大多是水果酒。中国的酒,不管是古代低度的米酒,还是元朝之后的高度酒,大部分由大米、高粱、绿豆等酿造,这符合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特点,也符合吃五谷杂粮成长的中国人的生理特点。
酒最初在中国出现的时候,人们视它为非凡之物。为什么?人类早期,认识世界的能力弱,总以为万物有灵,以为事物的变化必有神秘的力量。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酒,认为酒是粮食之魂,藏有鬼神,有魔幻作用,能左右人的行为,所以对酒高看一眼。
夏朝和商朝的最后一任国君都特别喜欢喝酒,最终两人都把国家(夏、商)给亡了。夏朝最后一个皇帝夏桀,文武双全、极有才华,但沉湎于美酒,还让人造了个超级大的池子装酒,称作“夜宫”,结果众叛亲离、夏朝灭亡。商朝是酒的黄金时代。商朝统治者,来自东部,生活相对比较富庶,时兴胡吃海喝。周之后,有成语“肉林酒池”,说的就是商朝人喝酒,就像喝池中的水一样。商朝最后一个皇帝纣王,天资聪颖、励精图治,中兴商朝,后来沉迷美酒、刚愎自负,最后自焚而死,商朝也因此灭亡。周朝吸取前朝灭亡教训,以道德为上,不准喝酒。商朝人祭礼,喜欢请神喝酒;周朝人祭礼,只请神吃饭。所以,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的礼器多为食器。
汉字中,凡是结构中带有酒坛子——“酉”或“酋”的字,多与酒有关。某些字的结构里即使没有酒坛,却也脱不了干系,儒家文化命根子的“礼(禮)”,也带有酒味:“礼”这一个字,就是从另一个带酒坛子的“醴”字引伸出来的——“醴”,就是米酒。古人讲究“酒以成礼”,祭祀时怎样用醴,盛在什么杯子里用,由谁斟酌,由谁敬献,都有严格的规定,这就叫作“献礼”。孔子出生于春秋时的鲁国,那一脉本是商朝的贵族,有讲究禮仪的传统,于是儒家就格外重视这个“礼”。
儒家重视酒的礼仪和规矩,道家呢,则注重弘扬酒的内在精神。酒有自由性一面,跟道家的主张相吻合。道家从一开始起,就跟酒有天然的贴近性。庄子悼念亡妻,一边敲打着瓦缶一边唱歌,从行为和内容看,应该是喝了酒的,喝了酒之后,认识更加透彻,对于生命,更有一种冷静和洒脱。庄周是一个热爱自由之人,宁愿做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自由乌龟,也不做昂头阔步受人束缚的千里马。这些主张,散发着饮酒的气息。春秋战国期间的中国文化,一直有真挚的自由倾向,是高蹈的,是尊贵的,充满着浓郁的酒香。
汉朝是畅饮的时代。汉朝成立后,虽然一开始也禁酒,可都是面子工程,喝得比谁都凶。身为宰相的曹参不仅自己一天到晚喝酒,还叫别人跟他一起天天喝酒。汉景帝在下令禁酒之后没多久,又下令让民众喝酒。《汉书·食货志》说:“有礼之会,无酒不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之后,跑去卖酒,生意大好。中山王去世之后,也要往墓室里放上万斤的酒,以备着阴间喝得快活。
三国魏晋,仍是酒的时代。最有名的,就是曹操《短歌行》所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凡稍有文化者,都是饮者。魏晋名士以为“酒正使人人自远”,意指酒让人远离世俗,超然物外,精神达到自由。又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是觉得不喝酒的话,精神必为世俗观念所束缚,得不到解放和自由。“竹林七贤”除了向秀之外,似乎个个能饮酒。阮籍最会“借酒遁”,当司马昭想和他联姻时,阮籍日日喝得酩酊大醉,让媒人“不得言而止”。他在《大人先生传》里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阮籍的玩世不恭,源于对当政者的失望和害怕,醉时的状态,永远比清醒着安全得多。
阮籍喜欢豪饮,嵇康喜欢小酌,一首《酒会诗》可以看出平日放情山水、饮酒弹琴的生活状态。阮咸最著名的便是“与猪共饮”,看来阮家子弟都放达任诞。山涛酒量最大,书中记载他能饮八斗,却没有人见他喝醉过。王戎为竹林七贤中最年轻的,因极吝啬,爱饮酒却不爱买酒。“竹林七贤”之中,嗜酒当属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让人拿着一把铲子跟在后面,对人说:我要喝死了,便把我埋掉。刘伶一辈子喜欢喝酒,著有《酒德颂》:“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一个牛皮,吹得够大,自我感觉够好。魏晋文人的“至人”境界,既是迷幻,又是佯狂,还有酒醉不醒的气息在里面。《世说新语》里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是大实话,是做人的境界,也是表演的境界。
与官人、商人、匠人、农人相比,文人与酒,发出的声响更大。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每张每页都散发着酒香——曹操爱酒;陶潜爱酒;李白是手不离盏的“酒仙”;杜甫“性豪业嗜酒”,酒量一般,酒风不错,被郭沫若誉之“酒豪”……唐朝豪气冲天的时代,诗文和酒,相互衬托,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这当中,李白以酒为题材的诗歌,写的最好,最有深情,最见性情。《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些,都堪称千古绝唱。
中国历史上酒量最大的人不得而知。武松虽然喝了十八碗,不过一夜成名的原因,不是喝了多少酒,而是打死了老虎。酒与文与历史的关系是:只有作诗作文同时又喝酒的人,才能千古留芳。
唐诗之后是宋词。宋词是唐诗的余韵,由兴致勃勃转到颓废悲伤,尽管余香若兰,不过脉息已近微弱。像是喝酒喝到尾声,从豪情转到悲哀;初衷是借酒消愁,孰料更添新愁。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是对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赞美。通俗的说法是:凡有酒水处,必有柳永词。宋朝饮酒,需有词曲美人相伴,有酒有词有美人,活色生香之中,有纸醉金迷的颓废和欢快。
酒真是个好东西:酒助欢乐,让人把酒言欢、不醉自醉,帮人渡过了漫长的古典时代。酒助审美,让人生出情怀,于盎然春色中看舍外烟柳,于萧瑟秋听渔舟唱晚。酒,造就了独特的迷离心境,让人于凭栏处极目苍天看群雁南飞,感叹大江东去人生无常……酒,带给人想象和自由,也带给人诗意和境界。
酒发酵了诗文,也发酵了相关文化,比如花样百出的酒令。酒令,也是社会的产物,雅致的酒令,让酒有了美好的引子,像是佛陀微笑时手中的那枝花朵。《红楼梦》中,一干聪明的小女子,不喝酒可爱,喝了酒更可爱,会说各式各样的酒令尤为可爱,连湘云的烂醉如泥,也妖憨如仙女一般。粗俗的酒令,诸如划拳什么的,仿佛酒的添加剂,让酒的度数更高,气氛更热烈,更欲罢不能。
文化的华章,文人的生活,因为有酒的助兴,变得更诗情画意。文不离酒,酒不离文,凡好诗好文,必有酒的影子。丰子恺就曾写道:“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中国文化人即使跟酒不钟情,也很少有排斥酒的。鲁迅不善饮,不过那首《自嘲》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却是在郁达夫做东的宴席上做成的。郁达夫呢,酒量不大,却极嗜酒,曾作诗“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读起来气势如虎。文人雅集,必定要有酒,酒能活血,更能助兴,可以让文字飞翔。酒不像茶,茶越喝越淡雅,喝到最后,把自己都化为一缕轻烟;酒则不一样,越喝越浓,浓到后来不分彼此,年岁不分,地域不分,阴阳不分,星月不分。
酒为什么受欢迎?因其有“真”。酒有真气,让人真实,诱发真情,也诱发真性。这是难能可贵的。人有追求“真善美”的愿望,也以追求到“真善美”为幸运。“真善美”当中,“真”是基础性的,也是最本质的,没有“真”,难见到美,更难见到善。塑料花美不美?第一眼看时,是挺美的;可一旦意料到花是假的,便觉得不美了。从酒中求“真”,虽是缘木求鱼,不过能求得一分是一分,得一分纯真,也是快乐。明清之后,中国“大一统”社会“明儒暗法”,双管齐下,“真”迹难觅。唯酒,才可以调动真实,听到几句真话,看到真实的行为——此种境地,实在不知是快乐还是悲哀?
酒带来了超越,即西方哲学自觉到的酒神精神。酒神精神是什么?就是杜绝平庸,呼唤与酒特质相似的激情、狂欢、进取、创造和斗志。人活于世,古板无趣是不对的,循规蹈矩也是不对的,需要现实之上的那一份激情来激活。酒神精神代表的激情,会导向创造和自由,拓展人类生存的空间。
尼采说:“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酒神精神,先以激情导向艺术,又由艺术通向美和自由。人类最潜在的力量,都包含某种沉醉的成分,需要以热情来消除审慎。酒神精神,不仅是前行和寻找,还是一种激发和暗示。有神酒精神,则风神俊朗,无酒神精神,则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以酒神精神连接艺术、美和自由,是酒的幸运。
中国文化,虽然也有酒神精神,不过大多时锦衣夜行,表现孱弱,只有在少数人身上厚积薄发。李白身上,是有酒神精神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苏东坡身上,也是有酒神精神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可是在此之外,还能看到酒神精神吗?酒神精神孱弱,是现实的严酷所决定的——现实凄冷严酷,想依靠酒的力量,根本不够。中国人喝酒,大多是当成麻醉剂喝了,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嵇康死后,阮籍活了下来,靠的是什么?就是酒。从《咏怀》诗中可以看出,酒成了阮籍生命中不可缺的东西,酒麻醉了灵魂,困苦就會少了很多。
中国知识人,不是没有情怀,只是缺乏浪漫。为什么?家国天下之价值追求下,心思重重,不堪重负,难得“为爱情为艺术”,难有普契尼般的咏叹。
酒神精神,是酒文化的上行;下行,则变成酒瓶精神、酒鬼精神。《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喝酒之后杀人放火,不是酒神精神,只是酒鬼精神。
西方精神文化多元,酒也多元,酒的味道也多元,相对丰富多彩,有包容性,也有宽容精神。葡萄酒,有无数种;果酒,有无数种;味道不一。中国文化相对固定单调,酒相对来说单调,酒的味道也单调,粮食酒的味道,万变不离其中。中国酒,从丰富性上,难比西方。西方的酒,不仅丰富多彩,酒的喝法也丰富多彩,可以将几种酒加在一起,可以冰饮,也可以热饮。就丰富性、复杂性、包容性而言,中国酒,比不上西方酒。
中国文化,自明清之后,总体下行。中国酒文化,也是如此。明清之后,中国酒文化,少形而上的精神,多世俗功利,酒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激情和斗志、创造和活力,反而给中国人带来的消沉、颓废、阴柔、讳忌和回避。明清之后,还有问天的诗句吗?好像没有了。酒还是能喝的,不过喝完之后,只能“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中国人不敢问天了,平时置身于礼教的低矮檐下,不敢发问;喝了酒之后,血脉贲张,仍不敢问不会问。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写《狂人日记》中,是饮了酒吗?文中的句子让人惊悚:“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样的句子,像是酒后恸哭,如屈原般问天。只是情绪更为阴郁,若呢喃低语,暗夜之中,像蛇信子一样咻咻吐出,很难传得很远。
中国的酒文化,文人锦衣昼行,官人素衣夜行,百姓糊涂迷醉,功能不在超越,只在安慰,在润滑,在世俗,在功利。中国人喝酒,喜欢以菜相伴,甚至喧宾夺主,菜压酒一头,没有丰富的菜,是不喝酒的。酒与菜的结合,让喝酒更多地回归到日常,浪漫和激情减少,功利和世俗增强,难荡涤出酒神精神。猜拳等酒场风俗出现,更让喝酒的主题发生变化——喝酒不再让人幽思和缅怀,而是让人耽于热闹和世俗:“一品当朝,两榜利呀,三星照呀,四季红呀,五魁首呀,六六顺呀,八仙寿呀,快得利呀,全福寿呀,喜相逢呀……”从酒令就可以看出,酒席上散发的,全是世俗精神。酒的气息不是轻盈而上,而是沉郁下行,渗透于腑脏及感官。酒神精神,也因此难以弘扬。中國酒文化,表面上文人搅动一池春水,骨子里与酒精粘在一起的,还是政治,是江湖,是鸿门宴,是煮酒论英雄,是杯酒释兵权,是心猿意马,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至于当代曾经的酒文化——酒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人情世故,带有越来越重的功利性——酒仙和酒神难觅,酒鬼和酒徒越来越多。官场是什么样子,酒场就是什么样子;社会是什么样子,酒场就是什么样子。酒场之中,充斥着虚伪和谎言——先是僵尸一般地排座次,随后逐次敬酒,一整场地谄媚、效忠、欺骗、浪费……一场酒喝下来,能把人累得个半死——好在现在少多了。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