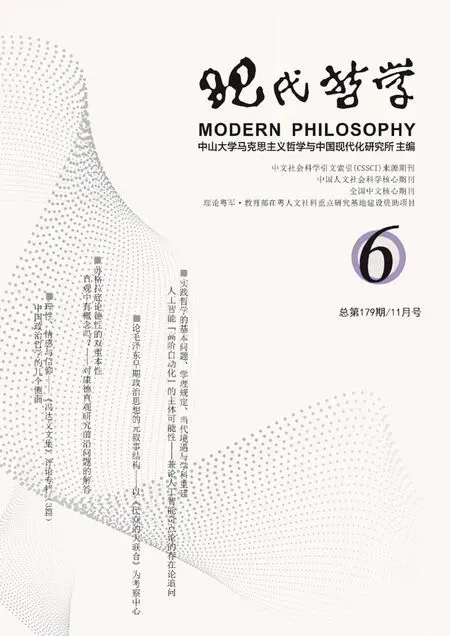汉娜·阿伦特的自由概念
——一种康德式解读
南 星
作为阿伦特(Hannah Arendt)政治哲学中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自由概念像一条红线,将阿伦特在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著作串联到一起:从她在成名作对极权主义的诊断开始,无论是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还是对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分析,乃至在她生命将尽结束时对人的精神生活进行全面刻画的尝试,自由概念在阿伦特的运思中总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阿伦特是否拥有一个融贯的自由理论?她关于自由的思想最重要的历史渊源是什么?这些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首先阐明阿伦特关于自由的两种构想,指出其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张力”;并尝试表明,我们如果注意到她的自由学说中的康德式要素,那么就不仅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张力,而且会对她在自由问题上独树一帜的见解有更深刻的领会。
一
尽管阿伦特几乎在她的全部作品中都谈到了自由,但她对这一概念最为集中的论述可以在一篇题为《自由与政治》的演讲稿中找到,她关于自由的两种构想都出现在这篇演讲稿中(1)这篇讲演稿是阿伦特为1958年5月22日的一场公开讲座准备的,原文为德文,经修改后发表于德文版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德文版发表后,阿伦特又对该文做了进一步修改,并以“何为自由?”为题将修改后的版本收录在英文版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中,该书的中译本就是根据此英文版翻译的。由于德文版和英文版之间有不少实质性的差别,笔者在论述中将同时参考两个版本。(Hannah Arendt, Zwischen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München: Piper, 1994, S. 201-226; [美]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在这场演讲一开始,阿伦特就断言说自由是政治行动的“意义”(2)See Hannah Arendt, Zwischen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S.201. 在英文版中,阿伦特将自由表述为政治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美]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139页。)。这一断言在这场演讲中被多次重复,可以说是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但由于自由概念的多义性,我们无法对这一断言的意义直接给出明确的解释,更无法说明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的讨论应当从澄清阿伦特对自由概念的理解开始。
在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历史中,人们常常在不同的自由概念之间做出区分,其中有两组区分意义最为重大。首先,正如阿伦特在讲座中所提到的,孟德斯鸠把哲学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区分开来(3)See Hannah Arendt, Zwischen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S.215. 密尔在其名著《论自由》的开篇处也做了类似区分。。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自由是意志的自由,它与人们在几个可能的选项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密切相关。与之相反,政治自由不涉及意志的形而上学,而主要与人或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关。其次,第二组区分位于政治自由内部,即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做出的著名区分。消极自由是免于由其他人,特别是由国家权力所施加的外在强制的自由。这种自由通常表现为某些权利,这些权利意味着在个人生活中有一些领域是他人或国家所不得侵入的。与之相反,积极自由是朝向特定目的的自由。虽然它有时也以某些权利的名义出现,但它实际上更多地指向某种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个人或群体得以去做或者实现他们所意愿的事情。积极自由是政治性的:一方面,这种能力可能受到国家的促进;另一方面,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积极自由的理想——自我规定或自主——只能由国家或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人来实现。大体上说,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的对比,可以看作是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笔下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的对比。消极自由的绝对优先性这一理念仅仅出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这一传统的出发点是现代的个体性意识;而积极自由则典范性地体现在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中(4)以上关于不同的自由概念之间的区分是十分粗略的,它们不应当被视为对孟德斯鸠、密尔、伯林、贡斯当等人思想的严格解释。笔者之所以提到这些思想家的名字,是因为笔者相信上述区分的基本方向的确是由这些思想家所指明的。。
几乎每一种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在由形而上学自由/政治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这两组概念构成的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那么,阿伦特的自由概念在这一框架中应当如何定位呢?按照一种标准的观点,阿伦特是“怀旧的政治哲学家,反现代性的理论家,对她而言,希腊的‘城邦’仍然保持为根本的政治经验”(5)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 x.。由于古希腊思想中几乎没有与现代观念中相同的意志概念,并且在希腊城邦中,政治自由首先意味着具有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能力或者说特权,因此阿伦特只对政治自由感兴趣,并且在此范围内只对积极自由感兴趣。
阿伦特自由理论的中心论题是,自由是一种“世间有形的实在”(9)[美]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141页;[美]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由此首先可以推出,内在自由和意志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10)[美]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139—140页。。内在自由指的是以爱彼克泰德为代表的斯多亚主义者宣扬的那种思想的自由。在斯多亚主义者看来,一个人只有对在他能力以外的事物毫无所求是才是自由的。但除了他自身的思想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处于一个人能力范围之内的。因此,斯多亚学派意义上的自由从原则上说就不能成为一个世间有形的实在,意志自由的情形也与此类似:与思想一样,意愿或者选择都不是某种能够显现在世界中、并为他人所经验到的东西。由于这两种意义上的自由都与阿伦特的核心论题相冲突,因此它们就被她排除在对自由的本真理解之外。

再次,通过将自由与行动等同起来,阿伦特对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展开了批判。上文提到,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是免于政治的自由,根据这种观点,“自由开始于政治终结之处”(14)同上,第141页。“自由主义尽管美其名曰自由,实际上也加入到把自由观念驱逐出政治领域的行列中了。”(同上,第147页。)。如果说政治是人们在它上面凭借自己的才艺而完成各种行动的最卓越舞台,那么自由主义的自由就恰恰是在远离这一舞台,从而直接与阿伦特的自由概念相抵触。在阿伦特看来,自由主义的自由实际上仅仅表示一种安全性,这种安全性被理解为某种私人的东西,人们可以像拥有一辆汽车一样拥有它。但是,私人的安全性在暴政面前是完全无所谓的,因为暴政恰好可以保证安全(15)Hannah Arendt, Zwischen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S. 202ff.。在极权主义的极端情况下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因此,极权统治的本质既不是削减或消除某些自由[权利],也不是根除人类内心中对自由的热爱。它仅仅在于通过暴力将人们如其所是的那样封锁在恐怖的铁链之中,而行动的空间——自由的现实性唯在于此——就这样消失了。(16)Hannah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 München: Piper, 1991, S. 714.
无论人们是否为这种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所说服,都应当注意到它只不过是从自由是世间实在这一核心论题所推论出的后果。问题在于,这个影响深远的论题是否只能从阿伦特对古代政治的偏爱出发来加以解释?抑或这一论题另有其内在的根据?人们完全可以设想,当阿伦特专注于自由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时,她错误地忽略或低估了自由的其他方面,因此她的自由观是不完整的。与之相反,笔者将尝试表明,阿伦特还有关于自由的另一种构想,把这两种构想联系在一起,阿伦特的核心论题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证成(尽管不是终极证成)。这另一种构想同样为阿伦特终身坚持,它就是能够开始(Anfangenkönnen)的自由。
能够开始的重要意义可以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诊断中最为明显地看出。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于决定论的世界观,在于对一切新的开始的可能性的否认。极权主义的追随者认为,有一个“巨大的、超越人性的自然或历史过程”(17)Ibid., S.710.,这一过程完全独立于个人意志,以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实现自身。尽管这一过程并不是由这些追随者们所开启的,但正是通过他们而实现甚至加速的;他们还认为,这一过程是一切人和物都要作为手段而为之服务的唯一的、最高的目的。根据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人们就可以理解以下观点:“与极权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讨论自由之所以毫无意义,是因为他们不仅对人类自由,即对人类行动的自由不感兴趣,反而认为这种自由对于自然或历史过程的解放是有害的。”(18)Ibid., S.711.因为在这里行动就意味着开始,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对正在进行的过程的中断。一个人哪怕仅仅在原则上能够中断这一过程,他就已经驳斥了该过程的所谓必然性,因此就不能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容忍。在极权统治下,这样的人仿佛是由这一过程本身自动处决的,而无需任何人或团体为之负责。
在阿伦特看来,人们在这里就发现了暴政与极权统治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对于暴政,进行统治的是暴君不受法律约束的意志,政治行动只有在与暴君的意志相抵触的情况下才会被禁止或压制,重新开始的可能性至少在原则上还不受影响;与之相反,在极权统治下,进行统治的是那些无人称的所谓自然或历史法则,因此这种统治本身与开始的可能性、即违反这些法则或中断这一过程的可能性已经不相容了,此时人类开始的能力被彻底破坏。这意味着人们不仅不能在政治上有所行动,甚至不能思考、意愿或制造,“因为显然所有这些活动都蕴涵着行动,从而也蕴涵着全部(包括政治)意义上的自由”(19)Hannah Arendt, Zwischen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S.204.。这些活动所蕴涵的自由指的无非就是能够开始,因为“就连制造也为世界增添了一个新的对象,就连纯粹的思维也总是会独自开启一个新的系列”(20)Ibid., S.223.。
那么,能够开始的自由与政治行动的自由之间是什么关系?前者看起来是后者的基础,因为它比后者要更加原初——行动自由依赖于能够开始的自由,反之则不然;也更加普遍——它不仅在行动中表现出来,而且在思维、意愿和制造中也表现出来。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最大的危险在于对这种自由的压制:“对人类未来而言,极权统治异乎寻常的危险主要并不在于它是暴政式的,从而无法容忍政治自由,而是在于它威胁要消灭一切形式的自发性,也就是说要消灭一切活动中行动和自由的要素。”(21)Ibid., S.223.
正在这时,也正是这些遗老遗小的一部分,他们是当时的浙江省议员,提出取消师范学生的官费,拿来增加他们自己的薪水,于是我们就和在杭各中学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包围省议会,把那部分主张加薪的省议员,痛打了一顿。
需要注意的是,政治行动的自由已经典范性地体现在古代的政治经验中,而能够开始的自由则是一个基督教的或现代的洞见。这一洞见的两个最重要的来源是奥古斯丁和康德。尽管奥古斯丁的名字通常和意志自由(liberum arbitrium)联系在一起,但阿伦特在他的《上帝之城》中发现了潜在的另一种自由概念,即开端(initium)的理念(22)关于奥古斯丁对阿伦特自由观的影响,参见王寅丽:《行动与自由意志:阿伦特的奥古斯丁论题》,《世界哲学》2014年第2期,第124—131页。。不过,学界一般认为阿伦特在这里不过是在“六经注我”,因为奥古斯丁本人并没有把开端和自由等同起来。而在康德那里,人们可以明确找到把自由理解为能够开始的说法。康德将先验自由或“先验意义上的自由”定义为“完全地开启一个状态,从而也开始其结果的一个系列的能力”(KrV A445/B473)(23)依学界惯例,引用《纯粹理性批判》时按照第一版(A)和第二版(B)的页码,引用其他康德著作时按照“科学院版”(Immanuel 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Berlin: de Gruyter, 1902-)的卷数和页码加以标注。本文对康德著作的引用采用以下简写:KrV指《纯粹理性批判》,KpV指《实践理性批判》,GMS指《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来自康德的引文均由笔者译出。,它也被称为自发性(Spontaneität)。尽管这一概念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自由意志,但阿伦特敏锐地注意到,康德的自发性并不“主要且完全是意志的现象”,而是同时是其他活动、尤其是思维和认识的基础(24)See Hannah Arendt, Zwischen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S. 220. 阿伦特在晚年出版的《精神生活:意志》中提出了“相对绝对的自发性”概念,借以修正康德过分形而上学的自发性概念。这一修正虽然十分重要,但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故在此不予讨论。(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Vol. 2: Willing, New York: Harcourt, p. 110.)。如果没有自发性就不可能有任何开端,一切都将按照严格的自然必然性发生,任何超出单纯反应的人类活动都是不可能的。
总之,尽管阿伦特在自由概念上无疑是一位“怀旧的政治哲学家”,但这只不过是她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已。她将古代积极的、参与式的自由和能够开始的自由这一基督教的或现代的洞见以一种极具原创性的方式联结在一起,最终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然而,她将这两种自由概念融为一体的尝试究竟是否成功?二者之间是否仍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些仍然是富有争议的问题。大多数解释者认为,在希腊的精英主义和现代的普遍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一张力也影响到那两种自由概念(25)尽管很多解释者都承认这一张力的存在,但关于如何准确刻画这一张力却有不同看法。Hauke Brunkhorst指出了阿伦特的思想“在政治的显现与前政治的潜伏之间从未完全解决的张力”。Seyla Benhabib认为,阿伦特持有“人类学普世主义”的立场,并宣称“在其道德和政治的普世主义……与其对希腊思想的哲学精神持续不断的依恋之间存在着两极对立的关系”。其他解释者则将张力定位在政治内部的两种模式,即政治中的民主制与精英统治之间。例如,Margaret Canovan认为,“如果说阿伦特在某些气氛下可以看成是卓越的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家,那么她也可以被解读为几乎和尼采一样强烈的精英主义者”。对此,本文不做详细讨论。(Hauke Brunkhorst, Hannah Arendt, München: C. H. Beck, 1999, SS. 135ff; 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pp.195, 198; Margaret Canovan, “The Contradictions of Hannah Arendt’s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Theory (6), 1978, pp. 5f.)。就所有人都有自发性而言,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从事政治或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似乎永远只是少数精英的任务。难道最终说来不是只有少数精英才有特权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他们的才艺吗?一直被人们视为民主制度理想的雅典民主制,难道不是以奴隶制的存在为代价才实现的吗?但笔者相信,由于前政治的自由可以类比康德的先验自由,因此如果我们进一步借助与康德自由理论结构上的类比,上文提到的张力就有望得到解决。在下一部分将表明,能够开始的自由和政治行动的自由实际上并不是两种相互竞争的自由概念,而是一个完整的自由概念的两个层面。
二
为了说明康德和阿伦特的自由概念之间结构上的平行关系,笔者首先必须简要概述康德的自由理论。该学说的基本结构是由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之间的区分所规定的(26)康德关于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论述相当复杂,在此笔者只能粗略勾画出对它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无法深入讨论任何解释上的细节问题。(See Henry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先验自由是从关于因果性和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语境中产生的概念,其含义在上文已做了解释,我们也可以将其刻画为原初的自由。与之相反,实践自由必须明确归于意志。它首先被否定地定义为“意动对于感性冲动的强制的独立性”(KrV A534/B562)。从这一否定的规定可以得出一种肯定的规定,即自由无非就是自主,亦即“意志成为自己的法则这一属性”(GMS 4:446f;KpV 5:33)。康德进一步宣称:“自由和无条件的实践法则……交互地指向对方。”(27)KpV, 5: 29. Henry Allison,将这一论题称作“交互性论题”,在学界引发了大量争论。(Henry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p. 201ff.)这里的“自由”毫无疑问指的是实践自由或自主。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一主张:实践自由或自主是通过并且仅仅通过道德法则来得到表达的;道德法则作为实践自由的表达,是其“认识理由”;实践自由作为道德法律的基础,是其“存在理由”(KpV 5:4)。
因此,康德的自由学说至少有三个层次:先验自由或自发性位于最高层次,与位于第二层次的实践自由或自主相比,它要更原初、更普遍,因为后者仅限于意志的立法,因而只是前者的一种特殊情况;道德法则位于它们之下的第三层次(28)邓晓芒也论述了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但本文对三个层次的划分以及对实践自由的理解均与邓晓芒不同。(邓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第2期,第24—30页。)。然而,人的理性只能洞见到第三层次,并且是通过将道德法则视为“理性事实”的方式而做到的(KpV 5:31)。实践自由的“客观实在性”——这是康德在批判哲学中经常使用的术语——是通过这个“事实”或对道德法则的意识而得到证明的。根据这三个层次的结构,我们可以补充说,由道德法则是实践自由的认识理由并且证明了其客观实在性这一事实可以立即得出,它同时是先验自由的认识理由,并且证明了后者的客观实在性。作为一种能力,先验自由或自发性首先将自身实现为实践自由或自主,而后又实现为道德法则或理性事实。因此,自由概念的这三个层次根本不是对自由的相互竞争的不同理解,而是作为潜能(dynamis)和现实(energeia)被整合进一个统一的自由概念中。
以上是对康德自由理论基本结构的简要概述。康德试图通过这一理论,在普遍决定论的背景下拯救自由。康德的自然观是决定论的,他将自然定义为“诸现象按照它们的实存、按照必然的规则、即按照法则的联系”(KrV A216/B263,黑体为引者所加)。因此,如果存在真正的自发性,那么它必须存在于另一个所谓“理智的”世界中。但是,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我们无法对这个世界有所认识,因此我们无法证明这个世界以及位于其中的先验自由的实在性,但也不能反驳它。它具有某种单纯可能之物的地位。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就像一个“事实”那样证明了实践自由、因而也证明了先验自由的客观实在性,只有通过这种意识,先验自由才不仅仅是某种单纯可能的东西,而是具有某种实在性。因此,严格说来,只有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才是现实的,而先验自由的实在性其实不应该被称为实在性,尽管它也不应当仅仅等同于可能性。它指的是一种能力,或者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是能够开始,这种能力会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实现自身。这样一来,康德就极具创造性地捍卫了作为一种能力的先验自由,并使之相容于自然的决定论。
如上文所述,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诊断与康德有相似的目标,即针对决定论而捍卫自由。但阿伦特关注的首要目标并不是自然的因果决定论,而是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来说不可或缺的历史决定论。为了对其进行反驳,必须证明人们有能力打破所谓的历史规律,这就意味着有能力从新开始。就像康德的自发性一样,这种能力本身无法被观察到;起初它单纯是可能的。它的“客观实在性”必须通过某种事实性的东西来加以证明。与康德听上去有些吊诡的“理性事实”相反,阿伦特总是把事实性的东西理解为具有“世间有形实在”的事件。尽管思维、意愿和制造也可算作此类事件,但政治行动无疑是所有活动中最突出的。只有在政治行动中,也就是说“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而不是在与自我的交往中”,一个人才能以原初的方式经验到自由和不自由,因此才能将自身确认为自由的存在者(29)[美]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141页。。正如对道德法则的意识证明了实践自由和先验自由的客观实在性,从而驳斥了普遍决定论;政治行动的自由也证明了作为能够开始的原初自由的客观实在性,从而反驳了历史决定论。
尽管阿伦特本人从未阐明其自由概念中的康德式结构,但当我们发现了这一点,就不仅消除了她的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张力,而且让她的自由理论的真正意图和内在逻辑变得比以往更容易理解。特别是现在我们能够解释,阿伦特为什么说自由是政治行动的“意义”。康德通过区分合法性与道德性,可以说将自主确立为道德行动的“意义”。一个行动如果仅仅符合道德法则,但不是出于该法则,即并不是出于意志的自主而做出的,那么这个行动诚然是合法的,但并不是道德的。在其中我们只能发现法则的僵死的文字,但这些文字并没有被法则的精神赋予任何意义(KpV 5:71, 152)。同样,如果没有自由精神的在场,一种政治行动即使是按照某些公认的规则完成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将政治行动视作政治的,即视作在人们之间进行的,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将它们理解为作为能够开始的自由能力的行使。自由构成真正的政治,并赋予其以灵魂。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还留下一个问题:阿伦特将自由理解为“有形实在”,这是否意味着她仅仅把握住了自由的一个方面,而不当地忽略了其他方面?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实在的自由在她完整的自由理论中有着重要的结构性地位,因此可以很好地得到证成。但这并不是终极的证成,因为即使人们假定自由作为一种能力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实现,也不能确定它的实在性会表现为何种形式。事实上,阿伦特的自由学说正是在这一点上偏离了康德。对康德来说,对道德法则的意识作为理性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客观实在性,但阿伦特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一种可以说是世界的事实。这一偏离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康德的理论是以其关于个人自主的思想为基础的,根据这一思想,每个人作为理性存在者都必须已经能够为自己立法。阿伦特认为这个想法站不住脚,因为它违反了复数性这一人类的基本条件(30)复数性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一样,都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为数不多的关键概念之一。阿伦特从希腊城邦的政治经验中汲取了这一观念,并通过对海德格尔学说的批判性继承,将其进一步发展成自己独特的世界性概念。可以说,利用世界或世界性的概念,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发展了她的“社会存在论”。Seyla Benhabib从海德格尔哲学出发对阿伦特的这一存在论进行了富有启发的阐释。(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pp. 51ff., 102ff.)。上文曾提到阿伦特将表演艺术设定为行动的原初模型,这说明对她而言行动的关键不在于“客观的”、非人性的真理,而是在于在公众面前展示自身并承认他人。在阿伦特看来,康德道德理论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没有考虑到行动的这一基本特征:
正是因为康德想把真理建立在实践理性之上,因此与一个单一真理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那种非人性就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清楚地涌现出来。尽管他不懈地强调人在认识领域中的局限性,但他似乎无法忍受下面的想法,即人在行动中也不能像上帝那样行事。(31)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New York: Harcourt, 1968, p. 27.
在阿伦特看来,康德对客观的道德真理的追求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导致了一种行动理论,该理论将主权的理念设定为人类行动的理想,从而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铺平了道路。主权与复数性是相对立的:后者要求“与他人共同行动的才艺”,而前者意味着“独立于其他所有人,并在必要时反对他们而贯彻自己的主张”(32)Hannah Arendt, Zwischen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S.213.。唯一客观的道德真理像主权者一样,会迫使人们如此这般的行事,而毫不顾及作为人类的基本境况的复数性。普遍的强制——不论是来自客观的自然或历史法则,还是来自客观的道德法则——都显然与人类自由不相容,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让自由在行动中得以展示或显现出来的可能性都在同等程度上被排除了。阿伦特因此写道:“在人类境况下,即在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复数的人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事实所规定的处境下,自由和主权毫无共同之处,以至于根本无法共存。”(33)[美]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156页;Hannah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 S. 714.
通过对主权观念的批判,阿伦特重新定义了政治行动的自由。在本文开篇处,我们界定了积极的政治自由的含义,即当一个人能够做他意愿的事情就是自由的。人们常常将阿伦特和这种自由观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阿伦特那里,这个想法对应的是主权而不是政治自由。真正的政治自由无非是能够开始的自由在政治的——对阿伦特而言,这总是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行动中的行使和实现。
阿伦特对康德式道德的批评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她的自由学说绝不能简单同化为一种康德式的理论(34)See Dana Villa,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61ff.。然而,阿伦特坚持认为政治行动的自由是作为能够开始的原初自由获得其实在性的唯一形式,这与康德的“交互性论题”同样富有争议性。究竟谁对自由的“实在性”的论述更有说服力?本文并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想要强调的首先是他们的自由学说在结构上的平行关系。由此,我们可以为阿伦特针对非道德主义这一常见指控做出辩护。乔治·卡特布(George Kateb)特别提出了这一指控:“阿伦特在她的希腊式思想中暗示,政治行动并不是为了实现正义或其他道德目的而存在的。政治行动的最高成就是生存性的,其重要性似乎比道德的重要性还要高。”(35)George Kateb, Hannah Arendt: Politics, Conscience, Evil, Totowa: Rowman and Allenheld, 1984, p. 31.阿伦特并不是政治思想中的道德主义者,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她并不打算像某些政治哲学家(如约翰·罗尔斯)那样,在一种预先存在的道德理论的基础上或以之为模型来构建起整个政治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阿伦特那里行动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即使阿伦特拒斥了康德关于个人自主的想法,但她与康德一样,始终保持为一切他律的道德理论的最坚定的反对者。他们之间的差异仅仅涉及自主的形式,而非这一理念本身,因为他们都认为我们的行动应当受到的约束不能从外部强加,都认为行动的肇始者无非就是自发性或完全从新开始的能力。在卡特布的指控中,道德是按照一种实在论的、他律的模型来理解的。从阿伦特的观点看,这种道德准则与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们鼓吹的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与非道德主义相反,阿伦特始终认为,真正的道德是可能的,但只能在政治行动中产生出来。笔者以《人的境况》中的一段优美引文来结束本文的论述:
这些道德法则是仅有的不来自外部,不诉诸某些据说是更高级的能力或超越行动本身范围的经验,却适用于行动的道德法则。它们直接产生于愿意以行动和言说的方式与他人一起生活的愿望,这样它们就像嵌入行动和言说能力的控制装置一样,开启了新的、无休止的进程。(36)[美]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