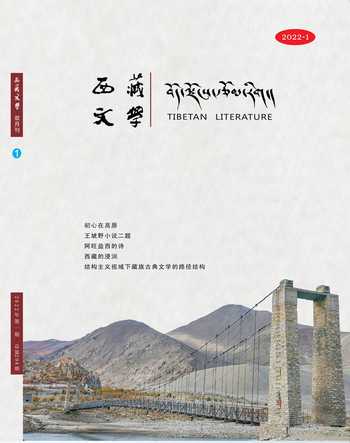抓着马尾爬山的那个女孩
旺珍
像往常一样,午餐后收拾完厨房,玛吉熬起甜茶,上好的斯里兰卡红茶在锅中与牦牛奶翻滚在一起,整个厨房弥漫着淡淡的茶香……拉萨夏日午后的艳阳很容易让人慵懒,此时来一杯甜茶是不错的选择。
滴铃铃……一阵铃声响起,玛吉拿起放在餐桌上的手机,电话里传出一个花季少女的声音,是她远在英国留学的女儿吾玛。
“阿妈啦,您在干吗?”吾玛边收拾东西边问道。玛吉说:“在做甜茶。”吾玛说:“我刚起床准备去上课。”
这时刚睡完午觉的拉姆掀开白底蓝纹的门帘踏了进来,玛吉赶紧凑近拉姆,给她看手机视频,电话那头的吾玛在喊:“嬷啦嬷啦!”拉姆双眼笑得眯成一条细缝,这时吾玛说:“哦,再不走我要迟到了,嬷啦拜拜。”拉姆正准备说点什么,视频已经挂断了。
“这孩子,我还没说一句就挂断了。”
玛吉放下电话,款款地拿出两个精致的瓷杯,一边斟着甜茶一边说:“她那边着急上课呢!晚上我再给她拨过去,您再跟她聊,现在很方便的。”
“现在的科技真是太厉害了,隔着千山万水却可以随时相见。”
“是啊,智能时代的科技把人类的好多幻想都变成了现实。”玛吉说。
点着头,拉姆伸出那双微微发颤写满岁月沧桑的手,小心地从餐桌上端起斟满甜茶的青花瓷杯,意味深长地说:“是啊,就像这杯甜茶!”拉姆不由得感慨起来……
“拉姆,还不快点跟上!”管家吼道。“隆司。”拉姆弓着腰吐了一下舌头说道。天蒙蒙亮就出发了,这会儿已经走了八个多小时,穿着那双露了脚趾头的松巴靴,小拉姆走在弯弯曲曲的野石榴丛的小道,望着眼前即将要翻越的这座山脊,小拉姆已经有些体力不支腿脚发软。
仰头望着骑马的两位领主开始爬坡了,小拉姆更慌张了,正午火辣的阳光,令她晕眩,上气不接下气,看着领主夫妇伴着铃铛声,骑在马背上穿行于蜿蜒的山坡上,小拉姆羡慕地看着领主的背影,幻想着自己是领主的孩子那该多好,她就可以骑马去拉萨,而不是白天黑夜地跟在领主的马后步行翻山越岭,累到嘴里有血腥味。突然一声:“快抓着我的马尾巴!”女领主有力的声音把拉姆一下子从恍惚中拉了回来,她立马抓住女领主的马尾巴,眼前这座海拔5100米的俗坡达拉是从山南老家到拉萨翻越的垭口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小小瘦弱的拉姆虚脱地基本上是被马拽上去的。
“那么小从山南老家徒步到拉萨,真是佩服您的毅力!”玛吉说。
“毅力是磨砺出来的。”
拉姆呡了一口甜茶继续说道:“1955年夏季,那年我10岁,谿卡领主前往拉萨乌拉差役,沿途需要随身佣人,就把我带上了。我们在路上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女领主对我不错,在翻越比较陡的山坡时会让我抓着她的马尾巴。”
“马不会踢您吗?”玛吉面露担忧地问道。
“不会,那匹马很温和。”
主仆一行四人起早贪黑地走,风餐露宿。管家选好有水源的地方露宿,小拉姆就会从附近搬来石头垒起三石灶,用捡来的干树枝点上火,之后她就双膝跪地鼓起腮帮吹个不停,生怕点不着火被管家怒骂一顿,劈里啪啦间干柴被点着后窜起火苗时小拉姆才会松口气,然后她就架锅熬茶。领主夫妇在管家的服侍下跳下马,盘腿坐在管家铺好的羊毛卡垫上,接过管家递过来的装好糌粑的木碗抓起糌粑吃,在噗噗的声音中吹过漂浮在上面的酥油喝起来。等领主吃饱喝足后,锅中剩下的茶渣里再放水熬煮,就是仆人喝的茶。
“那茶淡的呀!听母亲说起过,茶能解乏提神,很适合远足徒步时喝,我就在河边洗锅时捞起锅里的茶渣嚼起来,那味道涩涩的。”
看到母亲陷入苦涩回忆的情绪,玛吉赶紧起身给拉姆斟上热腾腾的甜茶,有意识地话题一转:“那次是您第一次来拉萨吧?当时很开心吧?”
“从小听老人讲,拉萨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是人间香巴拉,当时我的小脑袋里对拉萨充满了各种想象……”
玛吉微微点了一下头说:“是啊,拉萨作为藏传佛教圣地,如同穆斯林信众心中的麦加,是藏传佛教众生最向往的地方。”
当时从老家出发时,小拉姆是满载着兴奋和好奇出发的。从山南老家出发翻越了五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垭口,那双本来就露脚指头的松巴靴在小拉姆超负荷的步行中已经是破烂不堪。经过桑耶渡口,领主担心遇到强盗,就命令管家卸下马的铃铛,选择夜间悄悄出发。桑耶渡口附近有一大段沙丘路段,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只有轻微的沙沙声,一脚踩下去,塌陷在沙丘里,用力抽出来,鞋子里进满了沙子,小拉姆干脆就赤脚前行,她不敢掉队,因为听说这段经常有强盗出没。
“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恐惧包裹着我,脑海里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仿佛沙丘底下有一双魔爪,踩下去,就会被他掐住……那一夜走得好漫长!”
历经一路的艰难险阻,小拉姆出发时的兴奋渐渐被途中的劳累和恐惧取代。但,她牢牢记住临行前母亲嘱咐的话,做事要有始有终,要有给石头磨出窟窿的毅力。因此,不管多累,她都咬牙坚持着。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接近拉萨大桥时,走在最前面的管家兴奋地喊道:“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小拉姆隔着拉萨河望过去,看到远处,布达拉宫金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一刻他们都欢呼雀跃,每个人双手合十面向布达拉宫磕了三个头。
过桥时,骑在马上的谿卡夫人笑嘻嘻地说:“看,还没到拉萨城里呢,拉萨河大桥就那么热闹。”
“我看着大桥两边摆满的摊位,各种商品,有吃的、穿的、用的,五颜六色看得我眼花缭乱,应接不暇。长途的疲劳瞬间被兴奋蒸发了。”
看到母亲在说这段经历时,笑嘻嘻神采飞扬的样子还真有点返老还童的状态,玛吉的脑海里也不由自主地勾勒出1955年拉萨大桥的古朴与热闹,还有桥上面那个穿着破烂松巴靴兴奋不已的山南小女孩。
“咯咯咯咯”的笑声中拉姆前仰后翻着身子,继续说道:“你知道吗?当时过了拉萨大桥有歌声传来,感觉是天上飞来的,我好奇地往声音方向寻找聲音的出处,原来是一台支在树上的喇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喇叭,觉得好神奇。”
“哈哈。”玛吉也笑出了声,往下问道:“那年您在拉萨待了多久?”
“那一年我服侍领主在拉萨待了一个多月。”
“拉萨老城区里的甜茶馆是不是很热闹?”玛吉饶有兴致地问道。
“那一个月里管家和我服侍着谿卡老爷和谿卡太太朝拜了拉萨的各大寺院。当管家和老爷去噶厦政府办差事时,我就服侍谿卡太太探亲访友。那时我背着谿卡太太带给亲戚的氆氇,跟在谿卡太太后头穿梭在拉萨八廓街的扎廊里时,看见过甜茶馆,但从来没有进去过,都是门口匆匆一瞥。”
“听爸啦讲过,他小时候在拉萨娘惹夏私塾上课时,经常溜出来去甜茶馆,当时拉萨最出名的甜茶馆据说是绕色甜茶馆,因为在绕色甜茶馆能欣赏到拉萨民间的音乐演奏,甚至朗玛、堆谐歌舞表演。”
“是啊,你去世的爸啦酷爱民间音乐。就是他告诉我,40年代拉萨朗玛吉度最出名的歌女都来过绕色茶馆表演,像‘波若连巴’‘西米连巴’等。”
“40年代的拉萨甜茶馆真是别有洞天。80年代,拉萨甜茶馆里时不时有流浪艺人的身影,但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茶客都是男性,如果有女性踏入甜茶馆那可是要被男茶客起哄的。”玛吉回忆说。
拉萨喝甜茶的习俗由来已久,至少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据说最初是受最早到西藏的外国人喝下午茶习惯的影响,渐渐在西藏贵族、富商们家中兴起,后来逐步在民间流行,随后拉萨古城扎廊里陆续出现了甜茶馆。随时代变迁,拉萨的甜茶馆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魅力,依旧吸引着茶客们。
2000年,玛吉在美国盐湖城攻读硕士,寒假她专门飞到尼泊尔探望阔别已久的奶奶。当年奶奶离开拉萨时玛吉才10岁,奶奶是在爷爷病故后,去尼泊尔服侍在解放前就移居尼泊尔的双亲,之后就常住在尼泊尔。
加德满都的冬季犹如温暖和煦的春季,奶奶住在一栋二层带院子的花园房,院子里零星开着一些鲜花,玛吉进来时,奶奶缓慢地在院子里踱步,左手拨动念珠,口诵经文,玛吉三步并两步奔向奶奶轻轻唤了一声“嬷啦”,奶奶敞开怀抱,把她拥入怀中,奶奶看着玛吉說的第一句话就是:“像,真像你病故的爸啦。”
虽然客居异乡,但奶奶一直保持着小时候的饮食习惯,午后的甜茶是不能少的。当她看到80多岁的奶奶,一身考究的藏装,稀疏的银发用一枚小巧别致的咖色发卡盘着,淡淡的口红,用几种她喜欢的红茶品牌一起搭配着熬制甜茶,在午后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悠然地喝一杯甜茶,品一小块饼干,再好喝,也不会超过三小杯。如此不愿将就的讲究和自律,令玛吉对自己的这位出生于拉萨贵族家庭的奶奶印象深刻。
下午下班回到家,晚上7点,此时英国的格林威治时间是正午11点。玛吉摁下了微信视频,把手机递给了正在收看《新闻联播》的母亲,吾玛又出现了。拉姆接过手机,吾玛看到高兴的嬷啦把小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细缝,打趣地说:“嬷啦您看得见我吗?”
“看得见,看得见。”还没等拉姆接着说,吾玛说:“听到这个播音腔,我就能猜出来,您又在看《新闻联播》吧!”
“不看新闻怎么行?”拉姆说。
站在旁边的玛吉,赶紧凑近母亲,对视频里的女儿说:“当下疫情的发展,还有前不久的‘弗洛伊德’事件,嬷啦都一直关注呢!”
吾玛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个鬼脸,嘟起嘴唇拉近屏幕,亲了一下,说了声“拜拜”下线了。
“现在的孩子,只要自己肯学,除了母语、国语,还可以学各种外国的语言,真是幸福啊!我们是信奉因果的,不能忘记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来的。”拉姆语重心长地说。
玛吉感受到了母亲那颗朴实、真挚的感恩之心。她点了点头,起身给母亲斟了一杯甜茶。
1960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后废除了乌拉差役,拉姆以自由身从谿卡回到了家里。拉姆回家后的第一天上午,她起了个大早,可能是心情好吧,她感觉看什么都是那么美,远处耸立的雄日神山在新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安宁、洁净!头顶飞过的几只鸟雀的啾鸣,啁啾啁啾地仿佛在歌唱春天的到来,家门口地里的小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仿佛在冲着她微笑,拉姆呼吸着带有泥土味道的清新空气,开始在地里锄草。按照西藏民间说法,锄草是很苦的活,腰弯得像弓,腿立得像箭。拉姆虽然觉得腰弯久了会酸,但她不觉得苦,因为比起在谿卡当家奴时,这点体力活不算什么。
陷入回忆的拉姆说道:“就是在那天,在我锄草间隙,忽然有人向我招手,是两个男人,他们从远处走到我跟前,其中一位年轻点的用藏语说:‘这位是区委书记,我是他的翻译,今天我们是专门来通知你去西藏公学上学的。’我看了一下翻译旁边的书记,书记笑嘻嘻地说了些我当时听不懂的汉话,翻译马山说,‘书记说你是农奴出生,应该去,机会难得。’听到可以去读书,我真的很开心,但表达了感谢之后,我说:‘要问一下母亲。’”
父亲在拉姆5岁时就去世了,虽然她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但拉姆觉得母亲一个人把她们4个拉扯大特别辛苦。能上学当然令拉姆开心,但拉姆觉得离开家,母亲又会少一个帮手。晚上,拉姆把最小的弟弟哄睡后,看着苍老的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织着氆氇,她的内心非常纠结。母亲看到咬着嘴唇一声不吭站在一边的拉姆,慈祥地说:“我都听说了,你是不是还在犹豫去不去上学?去吧,你不是很羡慕来村里的有文化的工作人员嘛。”
“您上面不是有哥哥姐姐嘛?”玛吉问道。
“我从小心思就重,你姥爷过早去世,为了生计,有时你姥姥不得不翻山去别的村支差,哥哥姐姐都睡着了,但你姥姥不回来,我就会担心得睡不着。”
拉姆觉得生活像梦一样,六年前离开家乡第一次去拉萨还是作为家奴步行跟在领主的马后。六年后,拉姆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骑在了马上,脖子上戴着家人和村民们寄托着祝福吉祥的洁白哈达。那年拉姆16岁。临行前母亲眼里噙着泪仰头望着骑在马上即将出发的拉姆,哽咽地说:“我会为你祈祷的。”
玛吉若有所思地说:“1960年您去内地学习时好像正好是内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在学校吃得饱吗?那几年内地好多地方好像饿死了人!”
“是,那几年天灾人祸,自然灾害加上前苏联逼债,我们国家的确很困难,我记得当时在西藏公学开大会时校长号召大家:‘女的支援男的,肚子小的支援肚子大的。勤俭节约,响应党的号召,要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我们女生确实用行动去响应这个号召,会把自己饭菜的一半儿拨给自己支援的那个男生。后来才知道,当时三年自然灾害陕西也有饿死的人,但是我们在学校作为少数民族被照顾着,感受不到那么严重。”
玛吉自作聪明地说:“您和父亲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女生支持男生的号召下好上的吧?”
拉姆摇了摇头说:“和你爸啦认识是在1965年,我从西藏公学毕业后去西藏昌都左贡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三教。当时你爸啦以拉萨上层爱国人士贵族家庭的身份也来到了昌都左贡县参加三教。”
1965年夏季的一天晚上,西藏昌都左贡县政府后面空旷的草坝上放映了電影《上甘岭》,看完露天电影,拉姆和同寝室的姐妹拿着小板凳在回宿舍的路上,背后突然有人喊道:“拉姆啦!”拉姆打着电筒转过身,迎头而来的是丹增晋美,见到拉姆他笑嘻嘻地从衣兜里拿出一个用旧报纸包裹的东西交给了拉姆,然后说了声:“慢慢来。”就走了。回到寝室,拉姆拆开报纸,里面装了一个蜂花牌檀香皂,她拿起香皂闻了一闻,这时同寝室的姐妹们,都围观过来,冲她诡异地一笑,这时拉姆也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她满面通红,马上用两只手捂住脸。
“我们当时的三教工作,主要就是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语录,群众不懂汉文,主要推广的是藏文版毛主席语录。我们在西藏公学只是简单学了藏文30字母而已,几乎跟没学藏文差不多,为了工作需要急需学习藏文。当时你的爸啦自己编了一套藏文教材,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给我们教藏文。”
1966年昌都大部分地区闹旱灾,左贡县里庄稼都生虫,没有收成,农民拿圆根当粮食,灾情严重。驻扎当地的三教工作人员骑马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在缓缓前行的山路上,丹增晋美骑的那匹马突然仰头咆哮,把他摔了下来,因为一只脚还在马镫里所以还被拖了一段。看到这个情景,拉姆第一时间跳下马,追上丹增晋美的马,一把抓住缰绳。这时其他几个同事也赶过来扶起丹增晋美,大家围着丹增晋美你一句他一句关心地问道:“伤到哪里了?”丹增晋美一边拍着身上的灰尘,一边说:“没事没事。”当他看到拉姆在一边焦急地望着他,丹增晋美眼里冒着光微笑着说道:“只是腿部表皮擦伤而已。”看见丹增晋美笑了,拉姆也松了口气笑了起来。
丹增晋美送给拉姆的那块香皂,拉姆在昌都左贡县三教期间一直不舍得用,放在枕边,每晚睡前她都要闻一闻它的檀香味。一天,同寝室要好的一个姐妹对拉姆说:“我们可都是苦大仇深的农奴出身,你现在各方面表现都那么好,又是分团毛主席著作学习的积极分子,可不能跟丹增晋美啦好,他是拉萨贵族家庭出身,这样会影响你的大好前途。”但拉姆觉得找对象最主要的是要看人品,两情相悦是美好婚姻的感情基础。
后来昌都三教结束,拉姆响应当时国家的号召,选择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丹增晋美没有任何犹豫与拉姆一同去了那曲。
“真是充满奉献精神的一代。爸啦送您香皂,我觉得挺浪漫!关于甜茶的故事呢?”玛吉坏坏一笑问道。
拉姆微笑着摇摇头说:“我的甜茶故事里没有你猜测的浪漫爱情故事,它很简单,就是一杯甜茶,但对于我,那一杯甜茶非同寻常。”
1955年,10岁的小拉姆作为随身佣人跟随谿卡领主第一次来拉萨,她觉得拉萨好繁华,看什么都觉得很新鲜,但令她最难忘的是跟着领主夫妇参加的一次林卡。那次,在拉萨雄嘎林卡里,贵族老爷、夫人、少爷、小姐都是盛装出席,浑身珠光宝气。欢快的踢踏舞步,悠扬的青稞酒歌,此起彼伏,但小拉姆低着头,小心翼翼地站在女领主后头,听候使唤,不敢东张西望。作为受邀方的成员,领主夫妇跟前的矮桌上镶有金银的青稞酒木碗和白瓷茶碗边上给小拉姆也摆上了一个倒满了甜茶的小玻璃杯。小拉姆在那一次的林卡里喝上了人生的第一杯甜茶,吃到了一块印度进口点心。
“啊默默,那一杯甜茶,太好喝了!听说是印度炼乳熬制的。”
看到拉姆舔了舔嘴唇,玛吉微微一笑说:“难怪要勾起那么多往事,一杯寻常的甜茶,在那之前,对您来讲是遥不可及的。”
晚餐后收拾完厨房,天还亮着,玛吉搀扶着拉姆走出大门去散步。看着步履蹒跚、满头银发、布满刀刻般皱纹的脸上露出安详神态的母亲,玛吉的脑海中浮现起母亲年轻时的模样:一身蓝色的确良衣裤,梳着两个马尾辫搭在胸前,挺胸抬头,一张漂亮的鹅蛋脸精气神十足。恍惚中,玛吉看见了童年的自己,小手被母亲温暖地握着,一直在往前走,身后的路蜿蜒着伸向远方。
晚上,玛吉半躺在床上看着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手机震动了一下,她起身从窗边的书桌上拿起正在充电的手机,是她在外出差的先生发来的微信,说他明早9点的航班回拉萨,差不多中午到家。玛吉用微信回了一句:“我在家里做好甜茶等你!”
临睡前玛吉习惯性地撩开窗帘仰头一望,夜空中布满了星星……
责任编辑:索朗卓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