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会为你开窗透气
叶倾城

大张干什么都重。
呼吸重,喷过来像会打响鼻的马,气息里全是食物的味道,让人恶心;脚步重,从电梯下来几步路,走得地动山摇;说话重,动不动就“你怎么不死”;下手,更重……
所以,只要听见大张重重开门的声音,小寒就会下意识抖起来。
门被訇然推开,一声巨响,是大张把背包扔在地上。
他一眼就看见小寒,开口骂:“你死了呀?没看见我回来了?”
比语声还可怕的,是酒气。小寒一看就知道大张喝了不少酒。
是惯常的程序,小寒什么都没说,去架上把大张的拖鞋拿下来,蹲在他脚边,帮他换鞋。大张脱了鞋从来不放回原地,却又爱在嘴上讲整洁,一看到家里乱一点,就骂小寒:“你还是个大学生,连归置家都不会,你们大学学什么……”
大张自己没上过大学,有心结,所以特别爱把这事儿挂嘴上。小寒什么都不说。
她已经不记得第一次挨打是什么时候:先是热辣辣,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不是想哭,可能只是眼睛受了痛,眼泪便哗哗流下来。总是想尽办法遮掩那些红肿、那些破口,说是过敏、说是被蚊子咬、说是打羽毛球的时候去荆棘丛里找球划的,忽略听众的似笑非笑、急速闪过的怜悯。
红肿会渐渐变成青紫,然后变黄,就像笔迹久了会褪色一样,到最后,一切都会隐到皮肤下面。可是小寒疑心,那些颜色会沉积在深处,躲在内脏里,等到最不可忍的时候爆发。
小寒问自己:小寒,你怎么会混到这田地?
顿时,很多字都涌上来:稀里糊涂地恋爱、退学、与父母决裂、流产……
她摇摇头,却甩不掉这些字眼。
大张沉重地倒在沙发上,突然喊小寒:“你摸摸我头,是不是热?”
小寒几乎不敢碰他的身体,又不敢不去。其实光是靠近,都能感觉到大张火炉似的热,她的脚无意中碰到了大张的脚,是冷冰的。小寒想起自己在儿科病房轮转的日子,老护士长教年轻的规培医生们摸摸患儿的脚,是玉一样冰冷还是一团温热。小寒知道:大张在发烧。
但她不敢说。
大张从来分不清坏消息和告诉自己坏消息的人。
他只体检过一次,看到体检单上所有或高或低的指数,暴跳如雷,大骂医院,差点儿砸了人家分诊台的桌子。
最开始没看出大张是这样的人。
那时小寒在上医科生地狱般的大五,每天被各种医学名词压得透不过气来。有师兄约她去吃羊肉火锅,她想都不想就答应下来。羊肉极丰美,小寒吃得鼻子上溢汗,筷子都掉了两次,是身边的男生不声不响帮她捡,去厨房冲洗了递过来——那个男生就是大张。
到后来,小寒才知道大张不是“男生”,他初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一直混。是怎么跟小寒他们科主任认识的,大家说法不一,有人说某位药商是大张的叔叔,也有人说大张和主任的什么亲戚是战友,还有更下三路的,小寒开始不信,现在信不信也不重要了。大张嘴里没实话,他自己都说身份证年纪是假的,关于他到底是初中还是高中毕业,也是一会儿一个说法,有时候大张还说在军队上读了电大。
总之,当时小寒什么都不知道,大张就是一个高高瘦瘦、不怎么说话、总是皱着眉头的清俊少年。
那一天,大家一起玩一种叫“心慌慌”的纸牌游戏,小寒是好学生,没怎么参与过社会活动,第一次玩,一直输,不知被刮了多少次鼻子,鼻尖都红了。后来与大张打对家,出牌前,大张突然眼眉一挑,给她一个小小的暗示,她就再也没有输过了。
那天大家吵着要玩通宵,然而到了半夜,有人告辞,有人支持不住,七零八散睡得遍地都是。小寒也趴在桌上闭了眼。有人在她耳邊说:“会着凉的,来。”用力拉她,是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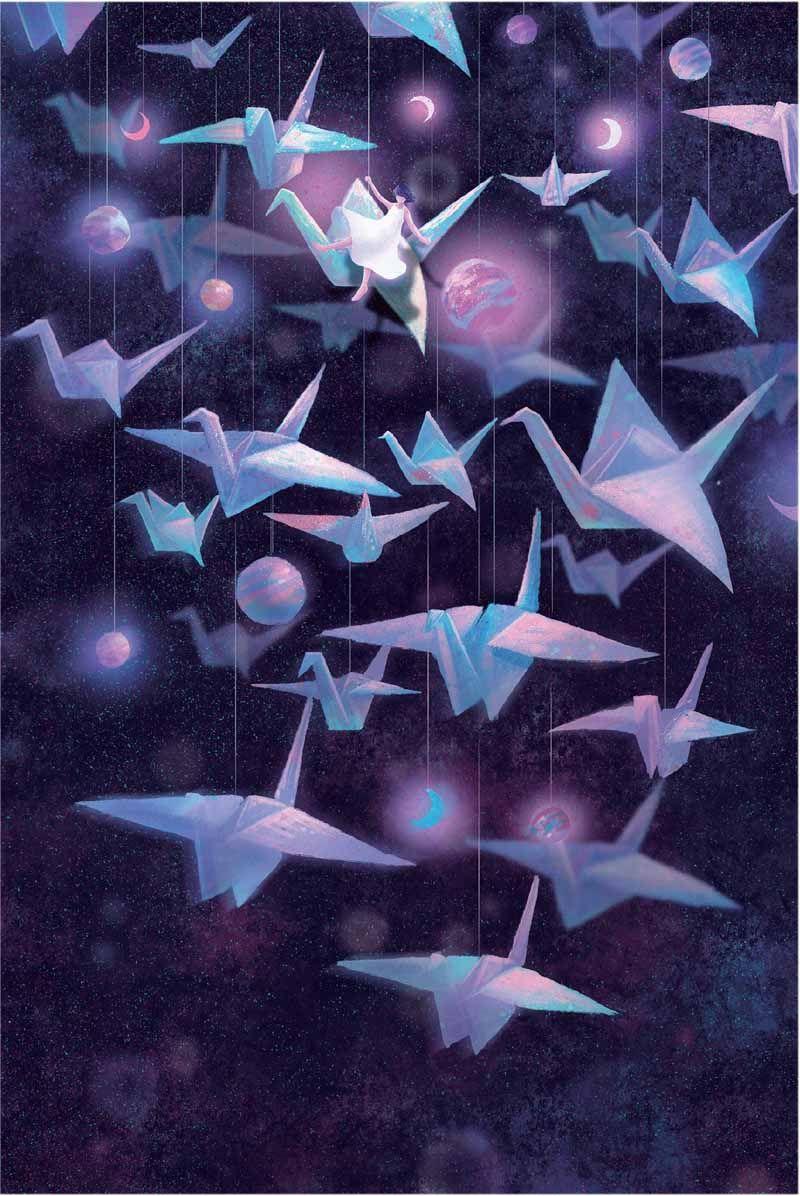
一拉开门,一股寒风迎面而来,小寒冷得直抖,睡意顿时消了。天寒地冻,月色却极清澈,照得操场如同雪野般澄明。医学院里空无一人,他们沿着跑道走了走,也没什么话说,经过学校里的驾校,大张说他就在这里学的车,小寒说还不会,大张立刻说“我教你”,拽起她就走。
小寒哪儿敢开呀,连司机位子都不敢上。大张便说:“我带你兜风吧。”一切都是新奇的,小寒上了副驾驶,大张把车窗摇开了,小寒一低头,看见月光下的车影上,自己突兀地露个头,竟然愣了神。
第二天,小寒在科室,突然收到外卖的奶茶。她不说:“发错了。”仔细看,留的是自己的电话。
正狐疑,忽然收到大张电话:“奶茶好喝吗?”
小寒心里一阵甜蜜。
最开始真的就是这样的。
大张是见多识广的、经验丰厚的,在小寒这样的雏儿面前,他是温文的得体的。
大张甚至主动告诉小寒,为了未来女朋友的身体健康,他注射了HPV疫苗。
过来好久,小寒跟朋友说起这件事,朋友冷冷问:他在哪里种的?我在美国种的,中国的HPV疫苗对男性开放了吗?
大张当然没出过国。
但那时,小寒已经怀孕了。
小寒当时一团乱麻,想到了很多可能性,大张向自己求婚怎么办,大张让自己打掉怎么办,万没想到的是,大张说:“我们私奔吧。”
大张烦她在医院里的各种班,早班、夜班、长白班、二十四小时班,妨碍他的时间。到现在,小寒也说不清大张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有时候会跟药商们混混,拿些钱回来;也有时会在一些卖仿制药的群里混混,替人买些印度进口药。大张是最不忙的人,所以他可以随时发情,而在他心目中,再没有比发情更重大的事了,发情时居然没人接招,大张就受不了啦。
那一天,他们从晚上开始吵,吵到第二天早上,天亮了,小寒必须去上班,她流着泪换衣服。就在她把毛衣举过头顶的时候,突然间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她压了下去,她跌倒在地。毛衣遮挡她的视线,她什么都看不见,奋力往上爬,大张用脚踩着她。她好容易从毛衣里挣脱出一点儿,却看见大张在窗边一信手,小寒的手机鸟一样飞了出去,那飞走的,是小寒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小寒一急,差点儿从窗口也跟着下去——他们是在23楼。
大张并不拦她,笑吟吟看她,甚至好整以暇抱住手臂,笑得鼻子都皱起来,像个孩子又像只猴子。他就是这样未开化的,又像野兽又像顽童的一个……动物。
而小寒目瞪口呆看着他,像第一次认识他。
小寒被“留”了一个星期,无论她怎么哀求,拿学业、父母、导师、报警……一件件跟他分析,大张就呵呵笑,她越说,他越视这件事为一个好玩的游戏。
洞中三日,世上便千年,何况七日。
说急了,大张脸一变,直接一耳光打在小寒脸上,用的还是手背。
戒指划破了她眼睛上面。最开始小寒不知道是血,她以为是自己瞎了,眼前一片流动的黑。
又或者,她下了地狱。
大张躺在床上,呼吸越来越重。
小寒不敢离开他,怕大张喊自己,而自己又没听见,那他就会暴怒,把手里的东西摔向自己。
大张有气无力地说:“我有点儿喘不过气。”
小寒说:“还是去医院吧,有发热门诊。”
大张惊叫:“现在疫情呢,一去就会被隔离,十四天。你就是要我被隔离,好出去找其他男人!!”
小寒尽量平静地劝:“不由得你想不想吧,手机有通信行程卡,只要发现你和阳性患者有过交集……”
大张说:“那我拔卡。”
小寒没碰过大张的手机,现在也是大张自己拔卡。
“你的手机,也拿来,别想背着我打电话给防疫中心……医院就想骗钱。”
小寒说:“我……陪你去医院。”
大张软弱地又恨恨地对小寒做了个踹的动作。
从昨天到今天,大张一直在发烧,连床都没下。天色再次逐渐暗下来,大张的呼噜声伴随着肺部的啰音,回荡在漆黑的屋子里。逐渐地,小寒心里燃起一团烈火,越烧越旺,热得她想立即逃出去。
大张再说话的时候,嘴唇都爆了皮,声音已经嘶哑了,“我……要……喝……酒,酒杀菌。”这是他经常挂嘴边上的。
“药……给我拿来。”他又说。
小寒还是心软了,转身去给他倒了半杯热水,“药和酒不能一起喝。”
大张连杯子带水砸在小寒头上,砸得她头失去知觉,连热水洒在脸上都感觉不到疼。过去的种种,在她脑海里回放:旷课的自己被开除了,成为笑柄的学生怎么还能在校园里待?失踪几天的女儿该怎么向母亲解释?
小寒只是哭。
也不是一直这么死心塌地的。父母上周还强行带走了小寒,她像被绑架一样送入熟人开的妇产医院。这样的爱反而激起她的恐惧与反抗:我不要,不要再被任何人关起来,我要逃!
但如今,小寒无处可逃。她是刚做过流产手术的女人,也许是遗留的药性令她脑子糊涂。
像做梦一样,小寒又回到了大张这里。
到底是怎么落到这一步的,小寒不打算再思考了,也思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酒瓶在身边炸开,碎了一地。大张喝完了大半瓶,还要。
小寒輕声说:“我出去买。”
她走向窗边:“我给你开个窗透气吧。”
窗外,是凌厉的冷空气,就像她和大张初遇那夜。
关上门,她一直紧紧地捏着钥匙。电梯来了,她没有进。突然间,她以一个决绝的姿势,把钥匙扔出了楼道的窗口,就像当年大张扔她的手机一样。手机里,其实有过很多她与大张的快乐照片,很多很多,但和坏掉的手机一起,扔在了垃圾筐里。
冷空气虽然刺骨,但清新。小寒迟缓地挪动脚步,一步,又一步。这双脚被禁锢了那么久,她以为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她有点儿一跛一跛,像不相信自己脚下是坚实的大地。
电梯又来了。但这一次,小寒决定用自己的双脚走出去。
要去哪里?先查个核酸吧。之后呢?还能重返校园吗?还能回家吗?还能回到正常生活吗?小寒都不知道,只是,她不会再回来了。
在漫长的黑暗中,小寒觉得仿佛走了几个世纪,直到天蒙亮时,她被出夜警归来的警察发现。小寒用尽最后的力气向对方嘶吼,自己可能发烧了,不要靠近。
上了疾控中心的车后,小寒向流调人员透露了大张的情况、住址。他会愤恨的吧,小寒想着,但她无所谓了。
也的确无妨。疾控人员和消防员破门而入时,大张已经来不及抢救了。他在酒醉中,咽下了大半板头孢药。小寒和他的手机卡,也被大张自己拔了不知道扔在哪,连个打电话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小寒在医院听到警察的通知,脑子里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要痛哭,还是要畅快淋漓地笑,压在心头上的大山,突然就碎成了无数粉末,轻飘飘飘上了天。医院也做了全面检查,小寒只是普通着凉,而大张一开始,也就是个普通肺炎。
出院的那天,小寒父母带来了一件红色的大衣,是保暖,是去晦气,也是新生。
这么多年来,小寒自己关上了自己的门,直到上天替她开了一扇窗透气,借着一丝生机,她重新回到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