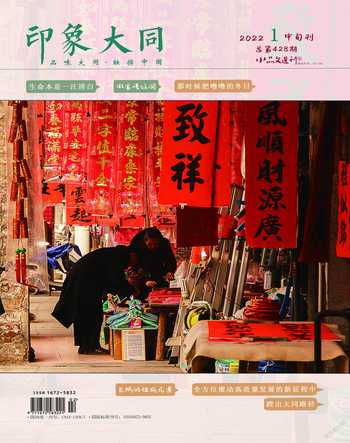生命本是一汪清白
许玮



一
终于,还是来了位于阳高县友宰镇境内的小龙门。与桑干之水对望的那一刻,历史云淡风轻。
对于纯粹的自然景观,我向来并无太大兴趣,总觉得单调,也有些单薄,若是添些历史的点缀,山水便有了厚度和底蕴,感受到的自然是另一番心境了。文人喜欢流连于山水,一方面是自身孤寂情怀的渲泄,另一方面也是为澎湃的诗兴寻一片安放,欲向天地万物倾吐胸中块垒,如此,大好山河间岂能少得了一两篇锦绣诗文!
小龙门对文人便有着这样的吸引。
“骇浪惊涛万马奔,居然气象是龙门。金鳞一跃云霞丽,石阙双开虎豹蹲。”这是清人黄文杰的四句诗,传神地写出了小龙门的动静之美,尤以“云霞丽、虎豹蹲”的画面对比,让这处景致在细腻中见粗犷,粗犷中透着细腻;再有,“两岸山摇还岳震,中流电掣更雷奔”这两句出自清人郭庭槐之口,同样写出了小龙门山势雄壮、水流湍急的气势,特别是借“雷奔”二字,摹写桑干河水,其急如雷电、如奔马之烈,怕不是今人能想见的了。
黄文杰和郭庭槐二位在诗坛并无大名,他们笔下的意境也算不得上乘,但却咏出了小龙门风光的殊胜,足见其在相对缺水的塞北,还是别有一番气象的。循着两位古人吟诵小龙门的诗作,脑海中随即展开对这处景观的遐想,真是有山有水呵。清雍正版《阳高县志》刊印有“小龙门图”,说此处曾建有一座“龙门桥”,为解铭等人修筑,“凿石中流,上为舆梁,下穿三洞。嘉靖间,巡府侯钺题曰‘小龙门’。”想来,小龙门在历史上曾有过石桥横跨,如长虹卧波,是别一种风貌啊。嘉靖年间,是大明中晚期,距现在已有五百年,解铭、侯钺何许人也,一时不得而知,但能在县志里留名,想必是于此地有过一番功绩吧。据说,那石桥毁于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倒是又多了几分悲怆。
山以形胜。小龙门并不嵯峨的山峦,在桑干河水的衬托下,生出几分耐看来,也颇有些雄浑。深褐色的岩石堆叠在天地间,本来就显得突兀,而一处处褶皱,如行如仰如卧,让山石显得挤挤挨挨,大有腾空跃动之势,再加上几处危崖峭立,似乎整个山体要向流淌着的桑干河倾覆而来。放眼望去,一处山体形如拱门,初见以为天造地设,大有桂林“象鼻山”的神韵,传说就是当年解铭等人修筑的龙门桥尚存之石洞。湍急的桑干水流到石洞附近,水势顿然平缓,河面如镜,汇成一汪清潭,香蒲和芦苇丛生,水天一色,景致极佳,成了历史上不少修行之人的绝好选择。
450年前的大明万历年间,一个叫“王继伦”的道士,踏破铁鞋四处寻觅修行的理想之地,最终与小龙门的山水相遇,便不愿离开了,决心在此修炼。王继伦来到小龙门之前,一定曾流连于不少地方的山水,那些山水各有各的神奇,有些或许还有大名气,但都没有留住他,他最后选择在小龙门驻足。在他看来,这里的山并不险峻,却在苍茫的天地间生出几分伟岸;水,亦无浩荡之势,可这条名“桑干”的河流,确为塞北数一数二的大河,那就在此留下吧。俢行之人,要有山水的陪伴,但自身心性的安宁最为要紧。王继伦或许面对小龙门这有形的山水发过感慨,说不定还有文字流于笔端,只是后人没有看见,消逝于历史深处的讯息,如眼前这流淌的桑干之水一样,既带走了天地间的精华,也无声地消殒着生命的气象。
在小龙门,王继伦带给后世不少关于修行、关于文人的漫想。
二
中国文人的真实心性,在山水而不在庙堂,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灿烂的诗词歌赋组成了横亘历史的华章,满溢文人的才情,也透出山水的精魂,因为唯有山水可以洗涤人的心性。这样说来,文人的天性里,多少有着山水气韵的填充,而且,文人的生命,真正安放之所不在官场。往前迈一步,是权力的诱惑;往后一步,在山水中可以看清内心的纯明。真正的文人,总会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于山水间独成风骨。
西晋的嵇康,一生不愿走向仕途,固然内心里有着对于官场的厌弃,但更有着和红尘之外的山水天然的亲近与默契——只有在山水的天然里,心性才是奔放且自由的,而像范仲淹那样在《岳阳楼记》里吟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真是少而又少。如此看来,走向山水需要的不仅是一种心胸的旷达,更要有一种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然而,文人总还是放不下官场的诱惑,自古以来文人缺乏的,正是对官场的勇于舍弃,尽管明白那是一份若即若离的浮华。够到了,可能一生榮耀;够不到,也许会摔得遍体鳞伤,但还是愿意“学而优则仕”。这一进一退,恐怕最见人性的复杂。
王继伦没有自诩为文人,也不慕混迹官场的浮华,他是一个道士,修行是根本,寻寻觅觅间,要的就是在山水中涤荡自己一路走来的风尘,来一场与时间意义上的生命和空间意义上的生命的对悟。小龙门成全了他的这个心愿。他在山水的喧响中,超然物外,或许他懂得时间意义上的生命,其实是一种可感知的岁月的绵延,而空间意义上的生命,则可作无限广阔的拓展。450年前,想必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小龙门有个修炼的道士叫“王继伦”,甚至连小龙门这个地方也未必有多少人知晓吧。几百年后,来此寻访山水胜迹的人,皆直奔桑干河畔,与清凉的河水亲近,无暇留意一个道士曾有的过往。毕竟,他算不得什么名人,也没有关于小龙门耳熟能详的诗文,但他抛却尘世繁华,潜心修炼,这份执着和坚韧,究竟令当代人啧舌,甚至望尘莫及。
我对道家文化没有研究,想来一定是极其高深而又玄妙。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不高深且玄妙的,这是中国人心性和智慧的提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不是简单地醉情于山水,而是要在山水中寻得修身养性的真谛。如今,能够弃绝红尘,一头钻进幽深的大山里修行的人很少了,因为这是对体力和意志力的极大考验,且不能不顾及世俗的目光。所以,面对小龙门有形的山水和无形的精神气场,我越发感到王继伦当年在此修炼的不易,尽管有山水为伴,却也要有常人无法轻易做到的舍弃与牺牲。
王继伦,多好听的一个名字,蕴含着古代名士的风流和雅韵。中国人把对生命的美好期许,寄寓在一个或简洁或复杂的名字里,却张扬出了生命的个性。《阳高县志》记载,王继伦是在大明万历年间于小龙门修行的,并在桑干河畔的山崖上开凿洞窟,后人又陆续建起了佛殿、玉皇阁、关帝庙等,伴着桑干河的柔波细浪,这些建筑在河两岸的山崖上凌空矗立。当王继伦打定主意要在此修行时,他时间意义上的生命似乎就此平淡无奇,而空间意义上的生命则开始拓展了。那时的王继伦,要把在小龙门修行作为一生的打算,但他究竟在此停驻了多少年,却没有见到史书里留下记载。
修行并非一味清苦,有时也充满了欢乐,因为这是对内心最大的坚守,而出家人要懂得守着本分,那便是不背离自己真实的内心,能做到这一点,才可得山水之真谛,否则,只是纯粹的娱情养性罢了。当年,与王继伦一同在小龙门修行的同道中人,有的或许比他年长,有的或许比他年轻,伴着桑干河水的涨落,他们一起焚香、听雨、抚琴,诵经、辩论、打坐,也一起静观白云苍狗,看桑干河上摆渡人的身影渐行渐远。余秋雨先生说,“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数百年前的王继伦,不就是活得自在且发出那般生命信号的人吗!
在历史的宏大长流里,每个人的生命都要寻一处安放。
三
大明万历朝,距今将有450年了,要还原一个道士的形象,着实不是易事。
王继伦当年在小龙门修行的情景已不可再现,他曾经凿下的石洞也多圮废,只剩下了一处名为“洪门寺”的寺院遗址,被列为六棱山的“十八景”之一,而且,曾经在此修行的还有他人——有道家,亦有佛家。从大明万历朝往前推五十年的嘉靖朝,据说一个法号“园晓”的僧人就在此修行。人事更迭,记忆湮灭,留下的只有遥想了。
对于王继伦这样一个平凡的道士,《阳高县志》寥寥几句记载,仅保留了历史的一脉线索,但也掀起了小龙门的时代微波。依着县志里有限的记载,450年后,我努力还原一个道士的形象,让他在我眼前隐隐幻化出来——一袭道袍、飒爽飘然,手捋髭须、凝神远望。对王继伦而言,家或许就在不远处,衣锦还乡是每个人最大的荣耀,但他选择了听从自己的内心,也一定承受过众人异样的目光。我不知道王继伦是何许人也,但他开始在小龙门修炼的那天起,肉体的生命和精神的生命,便永驻塞北的这片山水间了。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沉醉在山水中的王继伦,自不言悔。
明王朝到了万历年间,已有两百余年的统治,步履趋缓地行至王朝的末期。在经历了两百年的辉煌后,这个东方的大帝国,渐渐呈现出凋敝的迹象。一方面,大明的朝政腐败滋长,党争激烈,积弊丛生,一次次或大或小的变革,并没能让这个大国走出衰败的泥淖;另一方面,努尔哈赤领导的东北建州女真日渐强大,频频侵扰辽东,从大明王朝的一处肘腋之患,逐渐演变为心腹之患;再则,由于健康原因,万历皇帝朱翊钧近三十年不上朝,后半生嗜酒纵情、荒于政事,加重了王朝的衰朽。不过,在远离帝国统治中心的塞北小龙门,这个叫“王继伦”的道士,未必知晓这些,也不热衷于打听这些吧。帝国的运行与他无关,他只是一个寄情于山水的修炼之人,耳畔是桑干水日夜流淌的浩浩声响,香火日复一日,远处,有乡民在耕耘,骡马的嘶鸣和牛儿的哞叫,搅动着山野间的淳朴。
修行中的王继伦,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定力,但修行之余,走出石洞,和乡民们聊起天来,他则谈笑风生,显得无比亲和率真。每一次,他都会跨过石桥,走到正在忙碌的乡民们身旁,拉呱儿拉呱儿春种夏耘,偶尔还会帮忙一道犁地、播种,看着土里青苗的长势,便能想到秋天的收获。王继伦虽然静处修行,但凡俗的心性并非完全泯灭。既然小龙门是他和同伴的选择,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里也是他们的“家”,他能不关心这些吗!
得益于桑干河丰沛的滋润,得益于乡民们日复一日的辛劳,到了秋天,小龙门附近的庄稼收成还算不错。人们会在秋收时挑些菜蔬或粮食什么的送给王继伦,为他清苦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也带来了温暖。时间长了,鄉民们和这位仙风道骨的修行之人熟络起来,彼此不再拘谨,闲聊时直呼他王道士,所拉呱儿的也不止于耕作,或许还会询问他家在何处、俢行几载、缘何要选在小龙门,扯远了也会聊些关于世道的话题。
那个时候的桑干河,水可行船。船行河上,放眼望去,是一汪开阔的碧水,芦苇、香蒲,皆在水面上摇曳,风吹来,极其喧响,又极其静谧。王继伦或许会乘一叶小舟,往来于河的两岸,置办点日常所需,再邀些同道中人一起来小龙门,饮茶对悟、谈经论道,颇有几分惬意,更有几分潇洒。
450年后,桑干河水早已消瘦,但洪门寺及其它的遗址还在,并于陡峭的危崖间,隐隐站立着一个道士的形象。你能想见,王继伦面对斜阳时,会深情地俯瞰蜿蜒流淌的桑干河,余晖洒在水上,如金箔片片,他心头或许会猛地想起家来,想起曾经的父母兄姊之乐。塞北有炊烟的村庄,何处是自己的家啊!风吹过,他瘦薄的身影落在小龙门深褐色的山岩上,定格出一个永久的苦修形象。他,王继伦,不是西晋的嵇康,也不可比历代的名士,但小龙门这片景色殊胜的山水,却镌刻着他的名与姓——在山水中超凡脱俗,他已是小龙门最好的代言了。
生命,本就该是这样的清净和清白。
四
王继伦逝去几百年后,我和友人来到小龙门。时间改变了这里的一切,桑干河早不见当年的奔腾喧响了,但因为此处曾有道士苦修,让我觉得山水间依旧存留着他们的气息。
我们来时,恰逢初夏时节,桑干河两岸,一簇簇狼毒花开得正艳,花朵星星点点,白的如雪,粉的似霞,伴着桑干河上册田水库开闸注水的雷鸣声响,绽放出一份旷野的粗犷与柔情,也绽放着塞北大地生命的蓬勃。驻足桑干河畔,依稀之间,我感到了黄文杰笔下“骇浪惊涛万马奔,居然气象是龙门”的诗境,但却找不回王继伦当年在此修行的那份静谧了,只有他们开凿的石洞还挂在河边的崖壁上。
游人们一拨一拨到来,皆聚在小龙门的“象鼻山”下嬉水游玩,有的人攀到山崖上的石洞里一探究竟,似乎在寻找当年那些苦修者留下的生命的气息。我没有进那石洞,我知道当年的修行人已经不在了,那道袍、那白须、那面对桑干河水的深邃目光,都已消逝于历史深处,再也寻不见了。历史就在那里,踏访者无非是想重拾记忆而已,但能重拾的毕竟不多。想来,450年前的记忆已然模糊,留下的只是一份遐想——想那曾经在此停驻过的生命,于几百载的岁月长河中只是匆匆而过,有谁还留意洪门寺遗址前的石碑上刻着王继伦的名字!
在塞北为数众多的古代寺庙中,洪门寺没什么名声,只是桑干河畔的一处佛教遗迹而已,而碑刻上说它初创于隋朝,不免让人有些将信将疑。如今,洪门寺的佛殿在岁月的风霜中脱掉了漆皮,已斑驳不堪,倒是深褐色的火山岩依旧,远远望去,挤挤挨挨,如行如仰如卧。鹞鹰在山石间盘桓,如一个个黑色的精灵,从450年前王继伦生活的时代飞到当下,鸣叫声刺破苍穹,空旷而悠远,忽一个俯冲,倏然钻进了安在岩缝间的巢穴里,再无影踪,远处,河水淙淙,人影交错。
日升日落,王继伦当年一定和友人仰望着这些飞鸟而进出石洞吧,而且,他们一定采摘过艳丽的狼毒花,看花瓣在晚风中摇曳,看它们带着桑干河湿漉漉的水汽,年年谢了又开、开了又谢。一回头,象鼻状的石洞收纳着缕缕余晖,金光穿洞而过,照着桑干水,也照着王继伦,只是,他和山水早已物我两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