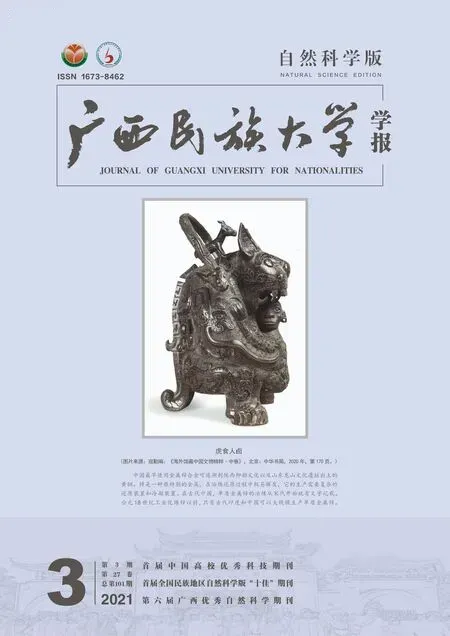陕西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研究*
长孙樱子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2)
0 引言
陕西省西南部汉中市下辖的城固县和洋县,自1955年以来,共出土了700余件商代青铜器,被称为城洋青铜器或汉中青铜器,[1-2]是商代重要的地方性铜器群之一。这些青铜器被集中发现于湑水和汉江两岸,未经科学发掘,基本都是单独出土,很少有伴出的其他遗物,[1]对于其年代、性质、功能和族属等问题多年来有较多的讨论。1998-1999年,汉中市城固县宝山遗址的科学发掘证实了这些铜器属于宝山文化遗存。[3]
汉中青铜器种类繁多,依据器形和功能可以分为四个大的类型:容器,兵器,弯形器、璋形器,面饰、铜泡。关于汉中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制作技术、铅同位素比值等,多年来已有较多的分析,[4-8]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其中弯形器和璋形器是最具本地特色的青铜器,面饰和铜泡也是个性突出的器物,兵器也颇有特点,学界对这些器物也有专门性的科技研究。[9-12]容器虽然是四类铜器中数量最少的,但是对判定整个汉中铜器群的年代、探析汉中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等情况具有重要作用。整体来看,汉中铜容器具有明显的商式风格,并显示出与郑州、安阳、盘龙城、新干、三星堆、湖南、关中等诸多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同时也不乏具有本地风格的青铜容器,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面貌。[1,13-14]另外,汉中青铜容器的制作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不乏制作规整、花纹精美者,但也有一些制作粗糙、纹饰不清者,显然不全是同一作坊所产。一件大型容器与一小件仪仗器或饰件在制作难度上不可等量齐观,在冶金史上代表的意义也不可相提并论,然而目前有关汉中青铜容器的科技研究较少,有必要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剖析。笔者在系统梳理已发表的有关汉中青铜容器的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归纳汉中容器的合金技术和铅同位素比值特征,并结合器物风格和制作水平对分析数据加以解读,以进一步探讨汉中青铜容器的来源,以及与其他地区商代青铜文化和青铜技术的交流等问题。
1 汉中商代青铜容器概况
容器几乎见于汉中所有铜器出土点,在城固县龙头、陈邸、莲花、吕村、五郎庙、湑水、宝山、苏村塔冢、苏村小冢、柳家寨,以及洋县马畅安冢、张村、县城北环路、张堡等地均有出土,加上零星征集者,至少有75件。其中以食器和酒器居多,还包括一些水器,具体器型有罍、尊、卣、簋、壶、盘、觚、鬲、爵、鼎、甗、瓿、斝、觥等,以及一些容器残块。这些容器的用途应与中原地区一致,作为礼器使用。赵丛苍统计后认为尊、罍、瓿三种器物数量相当,且年代较为集中,可能反映出一定的礼器组合格局。[1]根据汉中城固宝山遗址的地层堆积以及对青铜容器的类型学分析,考古学者们判断汉中青铜容器的年代跨度较大,上限为二里岗上层晚段,个别铜器的年代下限可达西周时期,[1,3,15]其中二里岗上层晚段至殷墟二期是汉中铜器群的主体年代,殷墟三期及以后的铜器很少。这些器物大多被采样分析,可以较好地反映出汉中商代容器的整体面貌。已发表的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数据见表1。

表1 汉中青铜容器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

续表1汉中青铜容器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
2 相关问题讨论
2.1 合金技术特征
由表1可知,汉中商代容器的合金技术以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同时兼具红铜、锡青铜和铅青铜等多种合金材质。图1是汉中青铜容器合金成分与年代分期关系图。如图1所示,二里岗上层晚段大部分容器为铜锡铅三元合金,且部分铜器的铅含量较高,超过10%。郑州[16]和盘龙城[17-18]铜器的成分分析表明,王都地区商代早期铜锡铅三元合金技术已较成熟,容器的合金配比较稳定,并有较高比例的高铅铅锡青铜。对比可知,大部分汉中二里岗时期铜器的合金技术与郑州和盘龙城相似,较特殊的是1975年在湑水发现的三件二里岗期的铜鬲,属于红铜材质。红铜熔点高,铸造过程中容易吸气造成砂眼等铸造缺陷,不适于制造大型容器。湑水铜鬲仍采用红铜技术,表明其冶金技术水平尚有一定的局限性。

图1 汉中青铜容器合金成分与年代分期关系图
汉中殷墟一期容器中,铅锡青铜所占的比例最高,还有一件红铜鼎,并出现了锡青铜。殷墟二期铜器继续以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锡青铜的数量显著增加,还出现了铅青铜。根据学者对殷墟出土铜器的分析,自殷墟一期起,容器中铅的含量开始下降,锡含量增多,至殷墟二期,铜锡二元合金占主导地位,锡含量普遍较高,[19]并出现了以妇好墓、M1004号王陵出土铜器为代表的高锡现象[20]。与殷墟铜器相比,汉中青铜容器的合金配比有相似的规律,自殷墟一期起,高铅器物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殷墟二期锡青铜所占的比例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高锡现象不甚明显。汉中殷墟三四期容器的数量很少,多数为铜锡铅三元合金,部分铅的含量较高,同时包含铅青铜和锡青铜,这也与殷墟出土同时代铜器的情况类似。
总的来看,汉中商代青铜容器的合金技术与商中心地区大体相似,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可能反映了铜器的不同来源。
2.2 铅同位素比值特征
图2是汉中青铜容器铅同位素比值与年代分期关系图。如图2所示,汉中青铜容器的铅同位素数据明显分为右上角的高放射成因铅(HRL)和左下角的普通铅(CL)两个部分。高放射成因铅容器有43件,占已分析总量的78%,且数据的变化范围较大,206Pb/204Pb的值在19.052~25.041;仅有9件容器为普通铅,占比16%,206Pb/204Pb值在17.241~18.707。龙头出土的1罍1觚以及马畅安冢出土的罍落在上述两个范围之间,与高放射成因铅已经十分接近。从图2来看,各时间段内均包含高放射成因铅和普通铅容器,其中二里岗上层晚段、殷墟一期和殷墟二期是大量使用高放射成因铅矿料的时间,也是汉中容器的主体年代。殷墟三期容器的数量很少,尚未进行过铅同位素分析。殷墟四期至西周的容器数量也不多,高放射成因铅铜器仍有出现。由此可见,以高放射成因铅铜器为主是汉中青铜容器铅同位素比值的主要特征。通过对郑州、殷墟、盘龙城、新干、三星堆等地出土铜器的分析可知,这种特殊的含高放射成因铅矿料是商代青铜生产使用的最主要的金属资源之一;含高放射成因铅的青铜器最早出现于郑州地区二里岗下层期,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二期大量出现,在王都地区出现的比例普遍在80%以上,在其他边缘地区也占大宗,至殷墟三期数量急剧下降,殷墟四期及以后很少发现(成都地区的金沙遗址除外)。[21]对比可知,汉中高放射成因铅容器的铅同位素组成与其他地区出土高放射成因铅铜器相同,[4,7-8]高放射成因铅矿料使用的时代规律也与其他地区相一致,这说明汉中容器所含高放射成因铅矿料与其他地区是同源的。

图2 汉中青铜容器铅同位素比值与年代分期关系图
汉中铜容器包含多种合金类型,其中铅青铜和铅锡青铜的铅同位素比值指征的是铅料来源,红铜指征的是铜料来源,锡青铜指征的应是铜料和锡料混合的结果。从图3来看,在高放射成因铅范围内,不同合金类型的铜器其铅同位素比值没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汉中铜器所用高放射成因铅矿料应同时包含了铜矿和铅矿。在普通铅范围内,铅锡青铜与红铜和锡青铜的数据有较明显的差别,可能来自不同的产地。有学者提出商代高放射成因铅矿料产自汉中附近的秦岭,[7]但笔者认为汉中铜器使用的高放射成因铅矿料,尤其是铅矿不大可能产自秦岭,关于这一点已进行过详细的论述[8]。

图3 汉中青铜容器铅同位素比值与合金成分关系图
2.3 青铜容器的来源
汉中青铜器中弯形器和璋形器最具本地特色,弯形器迄今未见于其他地区,而铜质的璋也仅见于汉中,年代均为商代晚期。与容器相比,这类器物制作粗糙,浇不足和砂眼等缺陷较多。分析显示,弯形器和璋形器的合金材质多样,以红铜材质为主,同时包含锑铜、镍砷铜等特殊合金类型,还有少量砷铜、锡青铜和铅青铜以及砷、锑、镍等特殊合金元素,应是冶炼了共生矿的结果,整体上合金化程度不高,反映出冶金生产技术的局限性。[8-9,11]虽然目前在汉中还未发现与冶铸生产直接相关的遗迹和遗物,但是由于弯形器和璋形器在器型和合金成分上的特殊性,被认为是汉中本地冶金生产的结果。[6,11]与之相比,容器具有显著的商文化风格,属于铜锡铅三元合金技术体系,不少器物制作精良,工艺高超,与弯形器和璋形器在青铜技术上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容器的年代上限要早于本土风格器物。因此,绝大多数汉中容器应是由外地输入的,而从其形制、纹饰、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至少可以辨别出几个不同的来源。
学者们普遍注意到汉中二里岗上层晚段容器,尤其是龙头铜器点出土容器的形制、纹饰与郑州、盘龙城出土同类器十分相似。[1,14,22]龙头容器的合金成分、铅同位素比值与郑州、盘龙城容器也非常接近,佐证了这些容器是从郑州或盘龙城直接传播而来。比较特殊的是四足鬲和三足壶,这两件器物造型特殊,仅见于汉中,其纹饰华丽,制作精美,显示出了高超的制作工艺水平。关于四足鬲的来源我们已有过专门的讨论,认为它是在郑州或盘龙城铸好后传入汉中的,只是目前在商中心地区还未发现同类器物,[23]三足壶也应是类似的情况。2004年在龙头铜器点发现的汉中唯一一件铜甗,束腰,圆腹,三尖足,三足外又套接三足,器体轻薄,形制与商文化铜甗完全不同。这件甗同样为铅锡青铜,但是其铅同位素比值为普通铅,与龙头其他早商铜器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来源也应不同。与龙头铜器相比,1975年在湑水发现的三件鬲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况。虽然其纹饰造型与盘龙城鬲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湑水鬲使用的是红铜材质,较疏松多孔,而盘龙城和郑州容器均未使用红铜。有学者认为湑水红铜鬲与本地冶铸传统联系不明显,而与关中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24]有两件红铜鬲的铅同位素比值与关中东部商代炼渣近似,佐证了相关看法[25]。
汉中殷墟一二期铜器中,鼎、觚、瓿、罍等器物的风格与安阳殷墟出土同类器物十分相似,尤其是苏村小冢出土方罍制作精美,与殷墟妇好墓出土方罍形制纹饰近乎完全一致,显然是从殷墟输入的。如前所述,这些容器的合金配比和铅同位素比值也与殷墟出土铜器相似,可见殷墟应是汉中晚商容器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比较特殊的是铜瓿1964CHWaT:1,器身比例不协调,腹部饰雷纹,制作粗糙,特别是高圈足上带大方镂孔的特征,不见于中原地区同类型器,可能为本地仿制。汉中晚商容器中也包含长江流域的文化因素,有代表性的是大口尊,与中原地区同类器显示出不同的风格。特别是苏村塔冢出土铜尊1963CHBSTT:1,夸张的大敞口和高圈足,尤其是肩上立鸟的做法与三星堆出土铜尊如出一辙。但也存在比较多的仿制品,例如尊1974CHBSTT:1、尊1974CHWT:1、尊YLZT:7所饰兽面纹不规范或无纹饰,制作粗糙,应是对长江流域大口尊的仿制。这些仿品也属铜锡铅三元合金技术体系,同样含高放射成因铅。汉中殷墟一二期仿制容器虽然在形制纹饰和铸造工艺上较粗劣,但是在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上并无明显区分,应是此时三元合金技术和高放射成因铅矿料已较普遍使用的缘故。汉中殷墟三四期容器大多与中原出土同类器相近,比较特殊的是罍1981YZHCT:1、簋YLZT:8,李朝远认为这些器物具有周文化因素,可能是受周原地区的影响,[15]但是这两件器物的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与殷墟铜器并无明显区别。
2.4 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汉中盆地位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江上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北越秦岭可达关中地区,向东顺汉水而下可至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向西南越大巴山即可进入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就是连接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处节点。正是因为汉中特殊的地理位置,当地先民可以触及郑州、安阳、盘龙城、三星堆、关中等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而有机会获取各地的青铜器,汉中青铜容器呈现出如此复杂的面貌也就不难理解。受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汉中在商代晚期也出现了本土青铜冶铸生产。
黄河、长江流域大量商代遗址出土铜器的分析数据和商文化边缘地区铸铜陶范的出土情况表明,除了商代青铜制品的流通,还应存在统一的金属资源分配体系。[8]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二期,高放射成因铅金属资源在王都和地方性铜器生产中均有大量使用,因此汉中青铜容器虽有多个不同的来源,但是在铅同位素比值上却具有相当的同一性。特别是汉中容器补铸处的用料也多为高放射成因铅,说明汉中先民可以获得高放射成因铅矿料,这是汉中参与商代金属资源分配和流通的结果。反过来,对金属资源和青铜技术的追求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中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3 结论
文章研究显示以下两点结论:
(1)汉中商代容器整体上为商式风格,合金技术属铜锡铅三元合金体系,与本土风格的弯形器、璋形器等区别明显,绝大多数应是从其他地方输入的。通过分析汉中商代容器的器型纹饰、铸造工艺和合金成分,可以看出有多个来源,郑州、安阳、盘龙城、三星堆、关中等地区都是可能的方向,商代晚期的仿制容器可能为汉中本地所产。
(2)无论是器物风格还是合金成分,汉中商代容器均以含高放射成因铅器物为主,与同时代黄河、长江流域诸遗址出土高放射成因铅铜器的矿料来源相同。本地青铜冶铸生产也使用了高放射成因铅矿料,应是汉中参与商代金属资源分配与流通的结果。汉中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那里的先民可以接触到诸多地区的文化,商代晚期本土冶铸业是在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对金属资源和青铜技术的追求也促进了汉中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