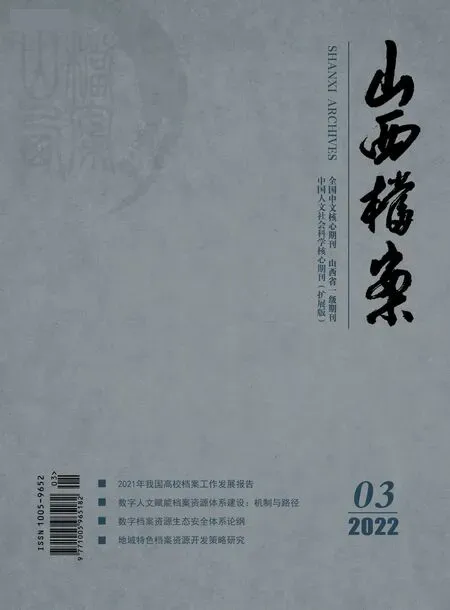党史学习教育背景下红色档案叙事研究—以百集微纪录《红色档案》为例*
朱琳 闫静,2
(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100;2.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1]、“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2]。“深入挖掘红色档案资源,建立‘四史’教育专题档案资料库”[3]亦是“十四五”时期档案资源开发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领导各机关、组织和个体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红色档案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奋斗足迹和历史记忆,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真实而鲜活的“教科书”,是讲述党史故事、传播党史文化的重要叙事资源和载体。叙事简单来说就是讲述故事,为讲好红色档案中的党史故事,发挥红色档案党史教育功能提供了新思路。
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指引下,档案学界积极开展红色档案服务党史教育的研究,其研究主题主要聚焦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在宏观层面上系统探讨红色档案服务党史教育的价值内涵、实现路径及问题策略;[4][5][6]二是在微观层面上,一方面,结合红色档案实践案例研究红色档案征集、保管、开发利用等管理活动,[7][8]另一方面,探索红色档案融入高校教育的方法路径[9][10][11]。整体而言,有关红色档案服务党史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多,且研究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而有关红色档案叙事的直接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涉及红色档案叙事优化策略[12]、红色档案典型叙事评述[13]、红色档案资源故事化组织路径[14]等主题,较少对红色档案叙事与党史教育进行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党史学习教育背景,以《红色档案——走进中央档案馆》(以下简称“《红色档案》”)为例探讨红色档案叙事,以期讲好档案中的党史故事,服务党史学习教育。
1 叙事、档案叙事与红色档案叙事
1.1 叙事
在英语语境中,“叙事”一词一般译为“Narrative”,与拉丁语narrativus和narrare有关联。在拉丁语中,narrativus意为“讲述一个故事”(telling a story),narrare的意思是“叙述、告知”(relate,tell)。[15]从构词法的角度看,叙事同时指涉讲述行为(叙)和所述对象(事)。[16]经典叙事学一般将叙事归纳为“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前者是内容层面,即内容或事件(行动、事故)的链条,外加所谓实存(人物、背景的各组件),后者是表达层面,即内容被传达的方式,包括叙事传达的结构和叙事在具体材料化中的媒介呈现。[17]因而,叙事是讲述行为(或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在后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叙事学由经典叙事学走向后经典叙事学阶段。在后经典叙事学阶段,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逐渐扩展,在关注故事和话语的同时,更加“注重作者生产语境、读者阐释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对于叙事的影响”[18]。因此,“叙事”一词的概念内涵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叙事成品, 而越来越倾向于一个过程,强调叙事形式与其阐释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19]在后经典叙事学下,叙事的概念范畴大大拓展,涵盖了符号现象、行为现象以及广义的文化现象,[20]呈现出泛叙事化特征,形成了各类跨学科叙事研究,如历史叙事、教育叙事、女性主义叙事、电影叙事、认知叙事、心理叙事等。伴随着叙事无处不在的“泛叙事观”倾向,档案叙事应运而生。
1.2 档案叙事与红色档案叙事
关于档案叙事这一概念,有学者基于“泛叙事观”的角度,认为档案叙事即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再现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21]也有学者强调档案叙事的目的性和导向性,将叙事视为一种行为过程,指出档案叙事是档案形成者出于特定目的,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对社会发展脉络进行选择与记录,再现特定时空中的事件,从而呈现给特定主体的过程。[22]以上学者都肯定了档案叙事是借助一定媒介再现或讲述特定时空的历史事件。正如上文所言,叙事既可以看作一种过程,也可以看作一种叙事行为的产物。尽管,在后现代语境下,学者对叙事的研究更多的强调叙事的建构性,将叙事看作一个建构的过程。但是,对于档案叙事若仅仅将其界定为一种再现历史的过程不免存在一些片面性。
基于以上理解,本文将档案叙事界定为:档案叙事是借助一定媒介记录和再现社会实践活动中特定事件的过程和成品。作为一种叙事过程,档案叙事被视为一个建构性的过程,叙事主体、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叙事媒体等共同作用于档案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成品,档案叙事的表现形态为小说、日记、影视、绘画等。因而,本文所言的红色档案叙事是指借助一定媒介记录和再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中特定事件的过程和成品。需要明确的是,红色档案叙事的内容并不完全等同于档案内容,受到权力、技术、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叙事的主体也不局限于档案形成者,而包括其外在的建构者和利用者等,如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内容的组织、档案利用者对档案内容的利用和阐释行为都是档案故事编码和解码过程的组成部分,影响叙事话语表达和内容呈现。
2 红色档案叙事对党史学习教育的意义
2.1 强化党史话语表达,建构党史话语体系
叙事具有话语建构性的特点,其最明显、最中心的一层含义就是“承担叙述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23]围绕党史学习教育这个议题,党史话语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和理论的具体叙述。红色档案叙事则是连接其党史和话语之间的桥梁,红色档案叙事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党史话语建构的过程。一是红色档案叙事视角或叙事元素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史话语表达的立场、态度和倾向。二是红色档案叙事结构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对红色档案元素进行排列、组合,建构党史话语表达的内在逻辑。三是红色档案叙事方式的选择影响党史讲述的效果。例如,文字叙事有助于阐释党的思想,图像叙事有助于刻画党的形象、还原党史发展场景,增强党史叙事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四是红色档案叙事媒体的选择影响党史话语传播的广度和效度。因此,行之有效的红色档案叙事策略有利于促进党史话表达内涵的丰富、形式的创新、逻辑的科学化和传播的有效性,营造良好的党史宣传教育空间,发挥党史文化育人的功能。
2.2 再现党的历史,坚定理想信念
档案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原始记录,具有与生俱来的叙事性特质,是一种最能还原历史原貌的叙事资源。红色档案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成长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记忆,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面对网络环境下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谬论,以红色档案为叙事文本讲述党史故事无疑是捍卫历史真相的有力武器。红色档案的独特叙事性既来源于红色档案本身,即红色档案是党史的真实记录;也来源于对红色档案的结构化重组,即以红色档案记载的党史人物、党史事件、党的理论等元素为基础,通过运用叙事手段和方法等全方位、深层次解读和建构党史,让党史“活”起来。发挥红色档案的叙事性,讲好党的故事,有利于向公众传递党史中蕴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公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24]深入了解历史发展趋势,从中汲取前行的经验、智慧和勇气。
2.3 打造文化精品,树立党史文化自信
红色档案是党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媒介,其所蕴含的党史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积淀,成为中华文化璀璨而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立足点和着力点。红色档案讲述党史的过程是一个文化创作的过程。红色档案叙事无论借助文本或图像等媒介,最终都以一定的物质形态呈现,如书籍、纪录片、影视剧、图画等。在党史学习教育的号召下,各地档案馆积极探索红色档案的多元叙事、多样表达,推出了大批优秀的文化作品,如北京市档案馆以红色档案为核心元素,融合多种媒体技术推出《北京红色档案》系列微视频[25],中山、珠海、江门三地档案部门联合出版《红色珠中江》革命历史读本[26],江苏省档案馆联合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摄制档案纪实类全媒体系列节目《红色珍档》[27]。这些文化成果都是对党史的浓缩和提炼,是党史学习教育的优质素材,既有利于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有利于向社会注入党史文化基因,以党史文化引领时代风尚,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体会党带领人民探索救国道路的艰辛、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党为人民服务的不懈坚守等,培育和深化公众对党史文化的认同感和信任感。
3 红色档案叙事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应用分析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中央档案馆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媒体中心推出百集微纪录《红色档案》。该纪录片立足于中央档案馆珍藏的大量红色档案,讲述红色档案背后的人物、故事,展现了百年党史的文化脉络和精神传承,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作为红色档案的典型叙事,《红色档案》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叙事媒体等方面的创新对于讲好党史故事、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借鉴经验。因此,本文以《红色档案》为研究案例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红色档案如何讲述党史故事。
3.1 叙事视角:以小见大,解读档案背后的故事
叙事视角是观察和讲述故事的角度和立场,影响故事的呈现以及受众对故事的感知。《红色档案》整体上从他者叙事的角度,由解说员解读红色档案,但是聚焦到红色档案内容的讲述,则选择从个体微观角度入手,将个体故事融入党的发展历程的宏大叙事,在保持叙事客观性的同时,注重情感的细腻表达。《红色档案》每集选择一份红色档案,从细微处着手,发掘关于青年革命者的凌云壮志、可歌可泣的革命爱情故事、红色名人的家风家训、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故事,向观众诠释和传达隐含在这些档案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如《红色档案》“家风明鉴”这一系列,以故事化形式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历史名人的文章、来往书信、电报等档案史料进行解读。不同于传统宣扬名人的伟大事迹,这些档案的解读着眼于名人生活细节,对子女的教导、对母亲的缅怀、与亲友的相处之道等内容,塑造了更加真实、饱满的红色名人的形象。其中,“子女眼中的毛泽东”这一集选取“毛泽东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这份档案,结合这份家书的内容和写作时间、人物等背景要素,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让观众体会到作为父亲的毛泽东对子女的爱护之心和谆谆教诲。这种微观叙事通过选取个性化、感性化的红色档案,对档案所记载历史的展开细节化描述,注重贴近日常生活,能够触动观众的情感共鸣,引起观众对家风家训的思考,于潜移默化中弘扬红色家风。
3.2 叙事结构:板块式叙事,多层次诠释主题
板块式叙事结构是“在同一主题下,将不同的人物与事件组合成不同的板块进行独立叙事建构,分别用不同的线索推动故事的展开,这些故事或板块之间没有直接的时空联系,而仅仅依靠内在逻辑进行隐性联系。”[28]《红色档案》主要采用了板块式叙事结构实现红色档案资源的梳理和整合,依据内容类别,设置了恰同学少年、信仰的召唤、一封家书、狱中纪、为有牺牲多壮志、革命的爱情等11个系列主题。每个主题下设置不同的故事单元,从不同人物、不同史料的角度阐释同一个主题。如“革命的爱情 ”这一主题,包含9个板块,各板块虽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叙事单元,但却共同诠释了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革命爱情观。又如,“信仰的召唤”这一主题则从农民、领袖、音乐家、法学家等不同社会角色的角度,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入党申请书、入党誓词、书信、文献等档案资料的叙述和揭示,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孜孜不倦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和坚持。这种板块式叙事结构不拘泥于单一故事情节和人物,而是跨越时空并置和呈现不同人物、故事,通过对相同主题红色档案叙事文本的整合和表达,以构建一个更具开放性和延展性的故事空间,增强叙事的立体感。
3.3 叙事方式:图像叙事,再现历史场景
叙事包括文本叙事和图像叙事,相较于文本叙事,图像叙事的最大特点就是可视化,“能够透过‘可视’来对客观对象进行相似性、生动性的描述或写真”。[29]图像叙事通过空间、氛围的营造,使历史事件和人物更加形象化、立体化,以增强受众对历史的代入感和体验感。《红色档案》结合红色档案的文本内容,穿插档案影像资料,并尝试利用“档案”结合各种器物进行拍摄,如“档案+常规道具”(如笔、台灯等生活用品)的组合,构建“档案产生时”的空间,这一空间既可以是虚拟空间的意向表达,也可以是具象化的仿真空间,并通过加入情绪元素,或结合投影(表现历史背景信息的画面)展开叙事。[30]譬如,“狱中纪”系列“囚室疾呼”这一集,以一册泛黄的案卷开篇,随着主持人的解说和影像的呈现,逐渐带领观众走进这份案卷。这是一份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在叙事过程中,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历史影像、1927年《晨报》等史料进一步完善、补充这份案卷所形成的背景信息,以铁窗、脚链、囚室、雷声等还原李大钊被囚禁的历史场景,渲染一种阴暗的气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燃烧的蜡烛,它象征着光明,也象征着李大钊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大无畏精神。通过模拟历史场景,运用对比、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再现红色档案故事有助于拓展故事想象空间,引人深思。
3.4 叙事媒体:多种媒体共进,多渠道并行
在传播媒体选择上,作为主办方的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整合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媒体平台,构建传播矩阵,推动《红色档案》传播的社会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展播《红色档案》,包括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央广网、微博、学校强国、B站等,以及国家档案局利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定时推送《红色档案》。据统计,该纪录片播出至半程时,央视新闻客户端阅读总量达1376万,央视新闻微博阅读总量达1.7亿,视频观看总量达6224万,#红色档案#话题阅读总量超过4亿,学习强国客户端的阅读总量达832万,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31]社会层面上,大量的个人、地方媒体账号在各类平台上转播《红色档案》,引起广泛的社会响应,如青岛档案、徐汇记忆、岐山档案等档案微信公众号。同时,在线下,重视加强《红色档案》在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群体中的传播。通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密切合作,推动《红色档案》融入高校思政课堂、团日活动,发挥党史对于青年学子教化作用。[32]广泛而多元的叙事媒体选择以及“红色档案+媒体+社会+高校”的运营模式,契合互联网时代用户多样化、多层次的媒体消费特点,使得《红色档案》的覆盖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大大增强,实现党史学习教育走向社会、深入群众。
4 党史学习教育背景下红色档案叙事启示
4.1 立足微观视角,挖掘红色档案中的党史元素
微观视角是相对于宏观视角而言的,是指将叙事视角范围聚焦个体或微观生活,注重细节化描述和感知。微观叙事具有直观、生动、简明的特点,能够对历史事件进行较为完整的陈述,这些特质使得微观叙事对历史教育的普及有重要的积极作用。[33]从微观层面入手,深层次挖掘红色档案中的党史元素,聚焦具体的人物个体、历史片段、实物等,有利于避免宏观叙事笼统、泛化现象,拓宽和深化党史文化内涵,构建全面完整的党史记忆,也有利于丰富党史教育素材。
其一,挖掘有关党史人物的档案材料。红色档案中记载了诸多党史人物事迹,为塑造和再现党史人物精神风貌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党史人物是党史的创造者,包括领袖、革命先驱、英雄模范、时代楷模等等。透过有关党史人物的档案(如日记、书信、回忆录、新闻报道、传记等)揭秘党史人物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思想品质、性格特质等,刻画丰满、鲜活的党史人物形象,有利于跨越历史的长河,实现公众与党史人物的对话,促进公众对党史人物的认识和理解。其二,挖掘特定历史片段的档案元素。以红色档案为核心要素,从百年党史中,选取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节点进行深入、具体的叙事,引导公众于细微之处理解宏大的历史进程。[34]如,“半条被子”这一集以一份报刊档案《当年赠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揭开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三位女红军将唯一的行军棉被留下一半送给村民御寒的一段往事。这件事情虽小,但却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人民情怀的真实写照,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的生动诠释。因此,讲好“半条被子”的故事,有助于在社会公众之间厚植爱国、爱党情怀,培育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其三,围绕纪念品、奖状、奖章、印章、老物件等具有时代印记的实物档案,结合档案文献资料以作补充、印证,拓展叙事的深度,增强叙事的直观性、亲和性和可信度。
4.2 多维度整合档案资源,深化党史教育主题
在基于红色档案讲述党史故事时,可以依据主题表达目的,借鉴板块式叙事结构,多维度呈现和讲述百年党史。与单一的线性叙事不同,板块式叙事更具张力,呈现出多层次、多事项、碎片化的特点。板块之间结构相对松散,但是却具有共同联系,即表达同一立意或主题,而板块内部则遵循一定的线性叙事原则呈现故事情节。[35]首先,确定叙事主题。在梳理党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按照历史名人、历史事件、历史节点、先进精神、革命地区等层次选择能够表达党史核心话语的叙事主题。如,《红色档案》是以红色档案所传达党的红色家风、革命信仰、执政理念、革命爱情观、革命人生观等为依据设置了11个叙事主题。其次,聚焦叙事主题特征,选择契合主题的红色档案素材多维度阐释主题。对每个主题的诠释主要是从多元主体的角度,将与之相关的档案,从实物到文本、影像,从人物到事件在到情节,使整个档案叙事更加连贯、流畅。[36]在板块式叙事结构下,碎片化的红色档案之间不再是孤立的、割裂的,而是经过系统化、条理化的整合,联结成一个叙事网络,共同诠释同一主题,有利于增强档案叙事的层次性和表达性,实现红色档案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功能的叠加和强化。
4.3 强化图像叙事,活化党史教育内容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图像叙事呈现出多媒体化、虚拟性、沉浸式的特点。图像叙事融合了图文声像等多种媒介符号,注重叙事的情境设定、场景渲染,进而触发受众情感体验,提升受众对于传达信息的感知度。这也为红色档案叙事效果的提升创造了契机。强化红色档案的图像叙事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图像方式形成红色档案,强调对客观历史的真实记录;二是以图像方式对红色档案进行描述、呈现,强调对红色档案所记录历史的建构和还原。这里主要探讨第二个层面,以图像化形式对红色档案进行描述和呈现能够将红色档案的党史教育功能和价值嵌入红色档案叙事过程之中,实现叙事过程和教育过程的有机统一。
具体而言,在讲述党史故事的过程中,挖掘红色档案中关于党的发展历程中的事件、时间、人物、故事、地点等元素,同时融入其他辅助叙事元素,包括技术、语言、文本、音乐、光影等,或是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或文化符号如勋章、画册、图腾等,以完善叙事情节。同时,依托数字技术,更加直观、精细地勾勒和再现历史场景,营造历史的氛围感、真实感。图像叙事的融入能够将红色档案所承载的有关党的精神理念、文化信仰、价值追求等抽象化的语意转化为具体的、可感知的符号,更容易建立公众与党史的情感连接,从而唤醒公众对党史文化记忆的认同,进而发挥党史对公众观念和行为的正向引导作用。
4.4 拓展传播空间,推进党史教育社会化
媒体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是影响红色档案叙事效果和党史教育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因此,红色档案叙事传播过程中应强化媒体运营理念,整合新闻类、社交类、视频类等不同类别的媒体资源,形成党史文化宣传教育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同时注重激活媒体平台活力,构筑公众与红色档案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借助平台的融媒体特性,实现“文字(叙述)+音频(情感传达)+图片、视频(视听呈现)”的有机融合,[37]丰富党史呈现形式,适应不同群体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如以短视频形式,再现党史故事,降低党史学习的门槛,以适应当下社会公众快速化、碎片化、个性化的知识需求,让公众在闲暇零碎的时间即可了解党史故事,进而不断扩大党史教育的受众范围。另一方面,借助平台的交互性特点,构建党史文化交流空间。《红色档案》在B站平台上播放,凭借B站的弹幕社交功能,极大地调动网友的积极性,引发网友的诸多讨论、点赞和转发。在信息交互中,调动公众学习党史的积极性,促进公众之间对于党史的交流探讨,以便丰富和拓展党史故事的解读视角和价值内涵,使党史教育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在线下,加强与高校、政府部门、社会单位等多方主体的联动、合作,推进红色档案融入课堂教育、团日活动、日常工作等,营造党史教育的文化氛围,发挥党史对于全社会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
5 结语
红色档案因其独特的形成背景和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成为党史教育独一无二的教育资源和载体。叙事建构起红色档案与党史的深层次联系。红色档案叙事为丰富党史教育内容、深化党史教育主题、创新党史教育形式、增强党史教育效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以红色档案为核心,立足于微观视角,多维度整合红色档案资源,借助图像化形式勾勒党史发展脉络,并依托多元叙事媒体,不断推进党史教育的纵深化、社会化,以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学党史、铭初心、担使命的时代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