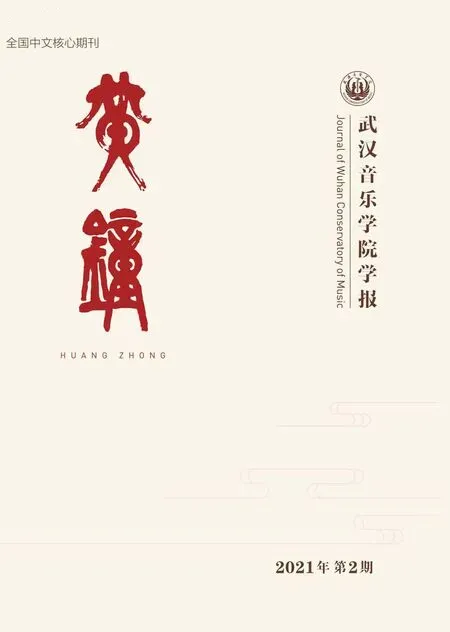论传统音乐曲牌的研究视角与模式选择
——兼论研究中需把握的三对关系
张天鹰
曲牌是中华民族传统音乐艺术的结晶,是中国独有的一种音乐现象。自古以来,对于曲牌的搜集、整理、研究从未停止,相关的历史文献与古代曲谱集有《碧鸡漫志》①[南宋]王灼:《碧鸡漫志》,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91—152页。《太和正音谱》②[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232页。《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③[清]周祥钰、邹金生等辑:《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刘崇德校译:《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柒)(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影印清乾隆十一年内府本。《御定曲谱》④[清]王奕清等:《御定曲谱》,北京:中国书店2018年版。等,其内容主要对曲牌的曲词与曲谱进行搜集、记录与审定。当下亦有大量学者对传统音乐曲牌进行研究,如冯光钰的《中国曲牌考》⑤冯光钰:《中国曲牌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袁静芳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研究》⑥袁静芳:《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武俊达的《曲牌【山坡羊】研究》⑦武俊达:《曲牌【山坡羊】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学丛刊》编辑部编:《音乐学丛刊》(第二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74—107页。、赵君的《【耍孩儿】曲牌研究》⑧赵君:《【耍孩儿】曲牌研究》,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吴志武的《〈新订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研究》⑨吴志武:《〈新订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7年版。等,主要涉及曲牌的历史谱本研究、乐目家族研究、音乐形态研究、音乐传播研究等多个方面。在曲牌音乐的研究方法上,亦有学者进行专题论述,如董维松《词七、曲三、辨程式——一种关于曲牌音乐分析方法的研究》⑩董维松:《词七、曲三、辨程式——一种关于曲牌音乐分析方法的研究》,《中国音乐》2009年第4期,第5—12页。、冯光钰《曲牌音乐研究要重视“论”与“证”的结合》⑪冯光钰:《曲牌音乐研究要重视“论”与“证”的结合》,《中国音乐》2004年第1期,第45—46页。、项阳《词牌、曲牌与文人、乐人之关系》⑫项阳:《词牌、曲牌与文人、乐人之关系》,《文艺研究》2012年第1期,第47—56页。、傅利民和张天鹰合撰的《传统音乐曲牌及其研究重点》⑬傅利民、张天鹰:《传统音乐曲牌及其研究重点》,《人民音乐》2020年第1期,第44—46页。等。除此之外,还有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⑭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孙玄龄《元散曲的音乐》⑮孙玄龄:《元散曲的音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郭威《曲子的发生学意义》⑯郭威:《曲子的发生学意义》,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9年版。等成果中也有部分关于曲牌的论述。
上述文献对传统音乐曲牌的研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在曲牌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模式上,目前还缺乏系统的归纳与论说。传统音乐曲牌具有深厚历史积淀,涵盖多种文化层次,类型丰富、形式多样,对于一个曲牌的考释或研究,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到位?要从几个方面或几种视角出发才算全面?在研究的过程中又需要重点把握哪些关系才能提纲挈领?这是研究曲牌音乐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基于此,笔者将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与构想,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论述,以期为传统音乐曲牌研究以及日后曲牌学的建立贡献微薄之力。
一、传统音乐曲牌的研究视角与模式选择
在对选定曲牌着手进行研究之前,研究者应当有清晰的头脑和思路,选择好视角与维度。综合当下学者对曲牌研究的个案成果,笔者认为,传统音乐曲牌可以有历史、形态、家族、乐种、区域、功能、思维七种基本研究视角,同时还存在不同视角组合的多种研究模式。
(一)传统音乐曲牌的研究视角
1.历史视角
历史是曲牌研究中无法回避的话题,也需要重点予以关注。对任何一个曲牌的研究,如果只关注当下的普查与分析而缺乏历史的回溯与审视,都是不全面的。曲牌的历史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层面,其一是文化背景的溯源,其二是历史谱系的梳理。文化背景的溯源旨在考察曲牌历史展开进程中所处的宫廷、文人、宗教、民间等文化层次,以进一步认知曲牌与古代政治、哲学、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相互关系。而曲牌历史谱系的梳理旨在探求曲牌音乐形态的动态衍化,以厘清曲牌音乐形态历史发展的源流体系。
袁静芳教授的《文化背景与音乐功能的演变——〈料峭〉乐目家族研究之一》⑰袁静芳:《文化背景与音乐功能的演变——〈料峭〉乐目家族研究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第36—44页。从曲名称谓、题材溯源、音乐功能演变三个方面,对《料峭》音乐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了考释;拙文《〈普庵咒〉音乐研究》⑱张天鹰、傅利民:《〈普庵咒〉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138—149页。在对刊有《普庵咒》的69 部古代曲谱进行分析与归类的基础之上,选取了7 部具有典型意义的曲谱进行比较。这两篇文章均是从历史视角出发对曲牌进行研究,前者重点关注曲牌历史文化背景的溯源,后者注重曲牌历史谱系的梳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注意将史料文献的考察与历史谱本音乐形态逆向推理予以结合、印证,共同把握曲牌历史的发展脉络。
2.形态视角
形态视角亦是曲牌研究中较为重要的视角,也是对曲牌进行剖析、归类、辨认的关键依据。从形态视角对曲牌进行研究,应当分为词之形态与曲之形态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字数、句数、句幅、句式、对仗、字调、用韵等;⑲此处分类借鉴董维松《词七、曲三、辨程式——一种关于曲牌音乐分析方法的研究》一文中对词之形态的分类,详见该文第6—7页。后者包括腔词关系(声乐曲牌)、旋律旋法、曲式结构、宫调体系等。
《昆曲曲牌【梁州第七】形态分析》⑳董维松:《昆曲曲牌【梁州第七】形态分析》,《中国音乐》2007年第4期,第31—39页。可谓从形态视角对曲牌进行研究的经典之作。该文首先从字数、句数、句法、分段等方面分析了昆曲曲牌【梁州第七】词之形态(词格),又运用了民族音乐形态学和程式性与非程式性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十首【梁州第七】曲谱的板数、字位、腔型、结构、特性音调等音乐形态。通过形态上的微观剖析,使读者更加透彻、深入地认知曲牌所蕴含的变化规律。
当有些曲牌既是声乐曲牌又是器乐曲牌,形态分析时又该如何把握两者关系?笔者认为,大部分器乐曲牌都是从声乐曲牌中移植过来,因此在进行形态分析时仍需要先从声乐曲牌入手,找寻声乐曲牌中词与曲的形态本质,再来观察器乐曲牌之变化。
3.家族视角
在中国传统音乐庞大的曲牌网系中,每一个曲牌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曲牌的复用性、可变性等特质使得每一个曲牌都同时存在于各个不同地域以及多种传统音乐形式,从而形成自身的家族系统。因此,曲牌研究过程只看个体不看整体,或以偏概全的做法都无法从曲牌研究的角度窥其全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袁静芳教授首次提到“乐目家族”㉑袁静芳先生认为:“乐目家族是指产生于一定典型环境(或典型题材)的社会背景条件之下,由相通(或主体部分相通)的音乐素材和曲体结构框架组成,在浩长的历史衍变过程中,所形成的流传于一定(或不同)地域、体现在某一(或多种)音乐品种并运用于某项(或多项)社会场合之中的若干乐曲——它们的主体或变体,均可划定在一个乐目家族之中。”参见袁静芳:《文化背景与音乐功能的演变——〈料峭〉乐目家族研究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第36页。,分别从文化背景与音乐功能的演变、模式分析与谱系家族梳理、宫调的特质类归与历史探索三个层面对《料峭》乐目家族做了系统地梳理。㉒该研究以论文形式发表,共有三篇,除了《文化背景与音乐功能的演变——〈料峭〉乐目家族研究之一》,还有《模式分析与谱系家族梳理——〈料峭〉乐目家族研究之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第3—17页)、《宫调的特质、归类与历史探索——〈料峭〉乐目家族研究之三》(《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67—72页)。截至2012 年,袁先生累计搜集、整理了129 份《料峭》乐目家族乐谱。㉓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238页。在曲牌的家族研究中,袁静芳先生的《〈料峭〉乐目家族系列研究》是真正能够做到贯通古今的穷尽式研究,其中所用“模式分析法”更是为后学树立了研究典范。惭愧的是,我辈学子中少有继承袁先生“乐目家族”研究之学者,当下仅见胡晓东、于澜《〈普庵咒〉乐目家族传承谱系梳理》㉔胡晓东、于澜:《〈普庵咒〉乐目家族传承谱系梳理》,《黄钟》2020年第1期,第77—87页。一文借用其概念与研究模式。在当下曲牌研究如火如荼形势下,笔者认为袁静芳先生的《〈料峭〉乐目家族系列研究》仍然是从事曲牌研究学子必读之经典文献。
4.乐种视角
曲牌在不同乐种㉕此处“乐种”是指广义上的中国传统音乐种类。之中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随乐种演奏形式、声腔特点、主奏乐器、乐队组合、演唱与演奏风格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乐种视角下研究曲牌不仅仅是对某一乐种之中单个曲牌的考察,而更多的是一种曲牌组合式的共性研究。基于此种情况,就需要考虑乐种赋予曲牌的个性色彩,选择具有代表性曲牌进行综合分析。
乐种视角下的曲牌研究不得不提到的是杨荫浏先生的《十番锣鼓》㉖杨荫浏:《十番锣鼓》,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杨先生这部著作重点对十番锣鼓所用曲牌和套曲进行了分析,其中涉及十番锣鼓曲牌的音乐形态、古今关系、一曲多用现象以及声乐与器乐的关系等多个方面。此类研究范例还有迟景荣的《京剧曲牌源流及应用》㉗迟景荣:《京剧曲牌源流及应用》,连载于《戏剧艺术》,1981年第2期,第22—34页;1981年第3期,第92—98页;1981年第4期,第82—385页;1982年第1期,第57—65页;1982年第2期,第78—89页;1982年第3期,第59—66页;1982年第4期,第76—83页;1983年第1期,第68—78页。、褚历的《西安鼓乐的曲式结构》㉘褚历:《西安鼓乐的曲式结构》,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等。
5.区域视角
曲牌在一定区域流传,亦会受到当地风俗、方言以及地方大型乐种的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而这又与区域文化交流以及同地域不同音乐体裁之间的相互借鉴具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一视角下,曲牌的研究更多地被赋予了音乐地理学、音乐传播学、音乐人类学等内涵。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流传于某一地域的各传统音乐戏曲剧种、说唱曲种、器乐乐种等形式之间会存在某种相通的共性特质,这些共性特征音乐表达的承载体,正是具有细胞意义的曲牌。
傅利民教授的《江西传统吹打乐的形态特质研究》㉙傅利民、傅聪:《江西传统吹打乐的形态特质研究》,《音乐探索》2019年第1期,第32—41页。是曲牌研究中区域视角研究的典型案例。傅教授认为,流传于江西省内的三星鼓、花钗锣鼓、公婆吹、十番等十几个吹打乐乐种曲牌,在音乐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文章从旋法特质、织体特质、结构特质三个方面,对江西传统吹打乐曲牌中蕴含的区域性风格特征在音乐形态上给予了剖析和解读。张伯瑜教授主编的《戏—乐音声——论戏曲音乐与器乐乐种之间的演变关系》㉚张伯瑜主编:《戏—乐音声——论戏曲音乐与器乐乐种之间的演变关系》,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同样具有曲牌区域研究视角的意义,著作通过对台湾北管音乐与北管戏、泉州南音与梨园戏、广东汉乐与广东汉剧等八个地方器乐乐种与同地域戏曲剧种的比较,探讨了戏曲与器乐之间在相互影响下形成的一致性特征,文中指出:“如果说,戏曲音乐和民间器乐在音乐上存在关联的话,曲牌上的关联是最典型的。”㉛张伯瑜主编:《戏—乐音声——论戏曲音乐与器乐乐种之间的演变关系》,第384页。区域视角也是曲牌的组合式研究,在共时性研究中更加聚焦于某一地域范围,这也是当下曲牌研究不可或缺的。
6.功能视角
曲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构成单位,具有“细胞”的意义,不同曲牌的变化与组合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缤纷多彩的世界。而传统音乐艺人在曲牌使用过程中,赋予了它不同的音乐功能。笔者认为,曲牌的音乐功能涵盖结构功能与社会功能两大层面。
何为曲牌的结构功能?民间艺人常常将不同曲牌连缀成套曲,作为套曲的组成部分,曲牌既要保持自身的独立结构,同时又要“被套曲结构”。㉜笔者认为此处的“结构”为动词。套曲的形成过程实质是多个曲牌相互结构的过程,曲牌作为套曲基本组成单位,既具有自身独立的曲式结构,同时又要与其他曲牌连缀共同构成更高一级的套曲曲式结构。每个曲牌在套曲中都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功能。在佛教京音乐中堂套曲“拍、身、尾”结构中,【垂丝钓】【山荆子】等曲牌作为套曲之序,通常在“拍”部;【金字经】【五声佛】【撼动山】三支曲牌经常连缀为【金五山】,构成套曲之“尾”;“身”部曲牌则常使用同一宫调进行连缀。尽管在套曲组合与使用过程中,每一支曲牌都发挥着自身的结构功能,但是在不同套曲、不同乐种之中,其结构功能又能随时转换。《中国民间器乐套曲结构研究》㉝袁静芳:《中国民间器乐套曲结构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10—17页。《昆曲音乐的曲牌联套结构特点》㉞褚历:《昆曲音乐的曲牌联套结构特点》,《戏曲艺术》1997年第4期,第43—48页。等成果均具有曲牌结构功能研究之意义。
曲牌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审美娱乐以及民俗为用等方面,如鲁西南鼓吹乐之中的【老梆台】【三炉香】【上天梯】等曲牌常用作丧事,【抬花轿】【普天乐】【拜花堂】等曲牌则用于喜事。曲牌在不同场合的使用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与此相关的研究与论述很多,在此不再列举。
7.思维视角
曲牌思维或曲牌性思维是中国传统音乐主要思维的构成,也是中国传统音乐区别于西方音乐创作理念的主要差异所在。正如乔建中先生所言:“如果有人问我,代表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理想是什么?我将会立刻回答:首先是曲牌。”㉟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曲牌思维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摇篮之中孕育而生,是我们祖先在音乐艺术领域的一种文化选择,也是探求曲牌产生、发展以及所处文化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当下,学界对于曲牌思维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成因、典型特质、表现方式等方面进行,如《曲牌论》㊱乔建中:《曲牌论》,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第313—326页。《论曲牌》㊲庄永平:《论曲牌》,叶长海主编:《曲学》第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曲牌:中国传统音乐传播的载体和特有音乐创作思维》㊳冯光钰:《曲牌:中国传统音乐传播的载体和特有音乐创作思维》,《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5页。等文都涉及曲牌思维的研究。整体而言,从思维视角对曲牌进行系统性研究和专门性论述的成果不多,当下仍有较大的推动空间。
上述七种研究视角是传统音乐曲牌研究的七种最基本视角,除此以外,曲牌的研究还可以有美学视角、传播视角、教育传承视角等。
(二)传统音乐曲牌研究模式选择
历史、形态、家族、乐种、区域、功能、思维七种视角分别对应曲牌研究的七个方面或七种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之间既有独立性又有整体型,形成了单视角与复合视角两种曲牌研究模式。
单视角研究可以从历史、形态、家族、乐种、区域、功能、思维中任选一种,此类研究一般重在深入而不在全面,把自身选择的视角领域以及想要解决的问题研究透彻即可。七种不同视角的交叉与综合即构成了复合视角的研究模式,复合视角既可以以一种视角为主,其他视角为辅,亦可以几种视角同时并举。但如果研究者拟要对一个曲牌进行全方位地纵横考释,那么这七种基本研究视角均需顾及,此类研究对于质量的要求较高、难度较大,需要研究者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也会更多。
单视角与复合视角可以选择对曲牌进行个案研究或组合式研究(见图1),曲牌的个案研究一般从历史、形态、家族三种视角之中选择,曲牌的组合式研究一般从乐种、区域、功能三种视角中选择。思维视角较为特殊,因为曲牌思维的研究需要在大量个案研究与组合式研究基础之上不断融入对曲牌所处文化背景的理解,这需要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不断积淀方可达到。

图1 传统音乐曲牌研究视角与模式选择图
无论是单视角的专题式研究,还是复合视角的综合性考察,两种研究模式都对揭示曲牌的样貌、内涵、规律具有积极的推动性意义。因此,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可以根据自身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目的、研究需要以及拟在研究中解决的问题,从上述两种模式和七种视角之中灵活地进行选择。
二、曲牌音乐研究中需把握的三对关系
冯光钰先生曾经提出曲牌的考释需要处理好“五对关系”㊴冯光钰先生在《曲牌考释:目的与方法》(《音乐探索》2007年第4期,第2—7页)一文中提出,曲牌的考释有“本体研究与关系研究”“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顺向梳理与逆向考察”“基础研究与考释研究”四对关系,继而又在其论著《中国曲牌考》中补充了“传播研究与接受研究”,共成五对关系。,这对后学进行曲牌的考释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下,随着曲牌研究成果的逐渐增多,对于曲牌相关研究方法还在不断地探索和推进,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几部最新成果的问世,㊵如板俊荣、张仲樵的《中国古代民间俗曲曲牌、曲词及曲谱考释》(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时俊静的《元曲曲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让我们在曲牌研究思路的整体性把握上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当下对于曲牌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仍未形成,在很多问题上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研究、讨论和汇总。笔者针对当下研究者在研究曲牌时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自身研究曲牌的体会,拟在冯先生“五对关系”基础之上再提出“形态与文化”㊶冯光钰先生“五对关系”中的“本体研究与关系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形态与文化”关系的意义,但是,冯先生在文中更多地强调曲牌音乐本体与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而并未在形态与文化关系上进行论述。“母体与子体”“乐谱与音响”三对关系予以补充。此三对关系亦是研究者在对曲牌进行全方位纵深考释之时所必须要考虑到的三个重要层面。
(一)形态与文化
在学界,关于文化与形态关系的讨论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只突出形态或文化的研究常被后人诟病为不全面:只突出形态是视野狭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突出文化是在音乐外围打转,没进入音乐本身;对形态和文化都关注但二者联系不紧密则被称为‘两张皮’”㊷褚历:《形态、文化、历史——音乐研究的三维模式及其多样组合》,《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32页。。曲牌本身所带有的唱词、旋律、旋法、音阶、调式、结构等形态特质是曲牌研究的重要着手点,而语言、宗教、风俗、社会风尚等文化特质亦是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在选择一首曲牌进行研究之时,应当如何把握形态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二者在研究中谁占据更大比重?
笔者认为,在进行一项研究之前首先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定位。曲牌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曲牌是一种人文、一种思维、一种形态、一部哲学、一个体系”㊸傅利民、张天鹰:《传统音乐曲牌及其研究重点》,《人民音乐》2020年第1期,第45页。,但是对于一位音乐学研究者来讲,曲牌首先是一部音乐作品,特殊性在于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衍化过程之中。考释一个曲牌,可能面临的是几十或上百个不同的变体版本,继而,在这些不同的变体版本中找到规律,再对其进行系统性地整理。基于此,形态的分析与研究必然成为曲牌研究的首要切入点。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曲牌除了是音乐作品之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研究曲牌音乐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研究背后的曲牌思维。思维必然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来表达,曲牌音乐的形态构成,就是曲牌思维表达的现实性存在。曲牌思维的重要特质“一曲多变”表现在每位艺人、每次演奏都不完全相同,“表面上看是一种随意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规律性的特殊表现,是一种有别于专业方式而为一般理论尚未认识清楚的特殊创造方式。那么要了解即兴还有其他传统音乐的一些特殊思维方式,就必须对这种思维表现的大量作品进行研究。”㊹杨善武:《拨开迷雾——厘清传统音乐研究的文化观念》,《交响》2019年第1期,第12页。
另一方面,曲牌研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于形态与文化关系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当下而言,我们对中国古代的曲牌曲谱集、当代集成卷本以及各乐谱谱本中最基础性的曲牌统计工作都尚未完成,形态的分析、对比、辨认、归类更是大量欠缺。文化的阐释固然重要,但眼下对于曲牌基础形态的研究才是当务之急。因此,笔者认为,当下对于传统音乐曲牌的研究应当是以形态研究为主、文化研究为辅,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共同把握其本质规律和整体样貌。
(二)母体与变体(又一体)
曲牌的母体与变体(又一体㊺《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御定曲谱》等古代乐谱文献中将同一曲牌的变体形式均称之为“又一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曲牌在同时期的横向传播与历史的纵向传承中会不断裂变产生变体,这与传统音乐不同体裁之间的音乐移植、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承时的变化以及艺人演唱或演奏时的即兴发挥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于曲牌母体与变体的研究,其实质是对同一曲牌族承关系的研究。在对收录曲牌的历史谱本、当代集成以及地方各乐种曲牌的演唱、演奏音响中对某一曲牌进行重点聚焦,其实很容易感受到其家族内各母体与变体之间的相似之处,而困难在于,谁是母体?谁是变体?
如果从乐种视角出发,对某一乐种使用的曲牌及其变体进行研究,相对来说会有较多的判断依据,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对艺人的访谈、声腔唱法、乐器演奏技法、传统乐学理论分析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㊻相关成果如荣蕙荞:《鲁西南鼓吹乐曲牌〈开门〉及其调名溯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81—90页;杨善武:《一个典型的乐曲系统——灵宝鼓吹乐“门面”曲研究》,《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4期,第10—25页。对不同乐种同一曲牌族承关系进行研究,其难度相对来说大了不少,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一种音乐传播历史的逆向追溯。曲牌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口传”,因此,某一曲牌的历史传播过程极少有文字史料可考,在文字史料欠缺的情况下,我们不可忽视地需要从音乐形态入手,结合实地的考察,才有可能接近历史史实。
笔者以为可以大致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判断:
1.谱本
载录曲牌历史谱本的抄录或刊印年份是判断所载曲牌年代的重要依据,另外,谱本中对于曲牌作品的相关记述可能会成为考证曲牌来源的线索。
2.牌名
曲牌在流传的过程中牌名经常会发生变化,如曲牌【普庵咒】有【大普庵咒】【小普庵咒】【乙字普庵咒】【普兰咒】等称谓,一般来讲,牌名保持正体的要比产生变化的更为原始。
3.形态
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曲牌的旋律、结构、宫调等音乐形态会有不同的表现特征,研究者可以依据相关材料的分析与佐证进行综合判断。
4.史料
文字史料较少不代表没有史料,某些地方志、人物传记及相关音乐著述中还是能发现曲牌流传和使用的蛛丝马迹。
5.口述
对民间艺人的口述采访亦能获取到曲牌族承脉络的部分信息。
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参照上述方法,但是,不能将它们作为判断曲牌历史族承关系的全部,毕竟谱本年代、艺人口述的真伪问题以及某些乐种曲牌在形态变化上的特殊性等因素随时都有可能会干扰研究者的判断。目前,学界对于传统音乐“一曲多变”的现象在乐学上也尚未形成清晰的认知,以李宏锋㊼李宏锋:《三首【脱布衫】曲牌音乐对比分析——兼及传统曲牌“原型—类型化”分析的方法论思考》,《中国音乐》2019年第4期,第104—138页。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也在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对曲牌进行形态分析,但是,对此现象仍缺乏理论性的认识和总结。因此,对于逆向考证必须十分谨慎,要有足够充实的材料,同时要对材料进行深入地分析,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
作为中国一种独特的音乐现象,曲牌对其母体与变体问题的探讨同样包含着形态与文化双重内涵,对“母体”的溯源既有形态,也涵盖文化。其实,对曲牌家族族承关系研究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搞清楚它究竟有多少层次的母体、变体,而是通过母体与变体的衍化过程把握曲牌历史纵向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继而在个性研究中认知曲牌发展变化的整体规律和文化内涵才是研究的应有之义。
(三)乐谱与音响
当下,有学者致力于曲牌曲谱的搜集与整理,以为研究某一曲牌只要集齐它所有版本的曲谱资料进行分析即可大功告成。事实上,曲牌不只是曲谱。曲牌由乐谱到音响的生成过程是传统音乐曲牌研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核心环节。对于民间艺人来讲,乐谱的主要功能是记录与备忘,就音乐研究者而言,隐藏在“死谱”背后的“活腔”,才是让乐谱文本趋于完整的关键。曲牌呈现的是直观的活态演绎,而不是冰冷的“白纸黑字”,从乐谱到韵谱再到实际的演奏或演唱,是曲牌音乐生成的基本过程,“原始谱字与呈现过程,才是中国文化的景深”㊽张振涛:《记谱与韵谱》,《音乐艺术》2017年第3期,第10页。。
谱系家族是曲牌传承与传播的历史发展过程,田野考察的实际音响是曲牌在当下的存在样态,将乐谱与音响对应,才能从现实中厘清曲牌的“源流系统”,从而真正把握曲牌的“古今关系”。正如黄翔鹏先生所云,“传统是一条河流”㊾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曲牌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核心构成元素,同样是一种动态的发展体系,在古今衔接过程中把握曲牌整体样貌,在真实田野环境中感受曲牌音响绽放,将曲牌研究与“人”对接,将“曲”之动态研究贯穿于传统音乐之“律”“调”“谱”“器”,才能体现曲牌研究的本质意义。
结 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传统音乐曲牌研究的历史、形态、家族、乐种、区域、功能、思维七大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视角组合的多种研究模式,同时探讨了传统音乐曲牌研究中需要把握的“形态与文化”“母体与变体”“乐谱与音响”三对关系。“词山曲海,千生万熟”[50][元]燕南芝庵:《唱论》,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第162 页。,虽然传统音乐曲牌研究是一项难度很大的综合性课题,但是,我国大量遗存的古代音乐历史文献、曲谱文献以及民间传承作品,为曲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传统音乐曲牌的价值不仅仅表现在自身蕴含的史学、乐学、美学等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为中国传统音乐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创作体系、表演体系的建设提供鲜活的例证。近年来,众多学者、研究团队、基金项目、尤其是高等院校音乐学子的学位论文选题都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传统音乐曲牌,曲牌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方法不断完善,相信在当代学者共同努力之下,定能最大限度地发掘这一蕴含巨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