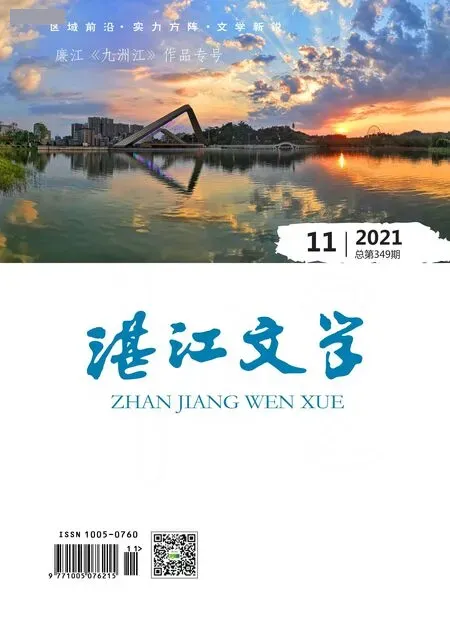自从您搬了“新”家(外一篇)
云 舟
自从您搬了“新”家,我的家里便冷清了不少。
那天清晨,一缕阳光把我唤醒,我匆忙拭去昨夜梦里遗落的泪珠,穿起衣服就往楼下跑。我忐忑不安地推开您的房门,您的床已经不在了,空荡荡的房间里每一粒灰尘都变得这样清晰,又格外碍眼。我像石雕立在门外,迟迟不忍离去。
自从您搬了“新”家,客厅里您的藤椅也已经不知去向,我倚在堂前的小黑板旁,看着黑板上模模糊糊还有您的手迹——“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苦读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我的思绪被拉得好远好远。
我记得您没搬“新”家前,家里总有一个老人,抱着一本书坐在藤椅前,身旁便是一本千页的大字典。这个老人就是您呀——我尊敬的祖父!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您时而仰头深思,低下头来是一番查阅字典,总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不明白的字词,您是这样一个读书做到一丝不苟,又总自嘲学识浅薄的人;您时而又欢喜若狂,大概是沉醉在文章里罢。每当看到好词好句您就欣欣然朗读,甚至还叫我过来跟前给我细细讲解。自然,年纪尚小的我听得一头雾水,您也没有失去耐心。
自从您搬了“新”家,您就把所有的文学读物兼上那本厚厚的读书笔记留给了我。后来我读上大学,偶尔回到家中,随手翻阅您的读书笔记,我好像渐渐明白那一个您教导过千百遍的词——“学海无涯”。曾经幼稚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您明明读了一辈子书,为什么还这样如饥似渴地阅读?只要有一本书,您就可以废寝忘食、不论昼夜,似乎稍稍一纵便会流失许多重要的东西。坚持了一辈子读书的您也终于熬不过时间的折磨,我越是长大,就越是看到您日渐衰老的身影。直到再也没有力气抱起一本书甚至是一张报纸,您才停止了您的阅读。我何必作践自己,非得等到你离去才想和你一起读书。
您不知道,您搬了“新”家后,家里再也没有人说我的字写得像鸡爪一般。我还没上学您就教我练字,我的字从一开始的歪歪扭扭变到现在还算工整,您都没有一次赞过我,总能让你找到应当批评指正的地方。那时我憋屈,觉得您鸡蛋里挑骨头,有时还和您杠上,后来我才发现您是对的。现在无论是硬笔还是软笔,每当我提起笔管,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的总是您慈祥而严厉的样子。我多么想您还在我身边指点一番。
您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不看卡通了,家里再也没人霸着电视机不让您看新闻联播了。我依然记得您那一声声无奈的叹息,您说我长不大,可您不知道我现在真的不想再长大,我还想跟着您逛街,赖着让您给我买吃的;还想坐在小黑板前搔首挠腮,让您不厌其烦地讲解算术;我还想再依偎着您听您朗读,听您讲关于学习的故事,哪怕同样的故事您已经说了十几年,哪怕我已经耳熟能详,我再也不会不耐烦,我只想静静地听。
可您还是搬了“新”家。那天中午,我只当你睡着了罢。父亲给您穿上了寿服,接着几个人把您抬上车,我不知道您往哪方去。后来,父亲抱回来骨灰缸。一晚上道士敲敲打打,众人抹着泪一声接着一声地喊:“爸,您回来吧”、“爷爷,您回来吧”……第二天,骨灰缸埋入早就准备好的墓穴中,盖上土。母亲咽呜着对我说:“爷爷搬了新家。”说着又回头对着新坟嘀咕:“爸,搬进‘新’家您不要怕,以后我们不能再服侍您了,您……”抽泣掩盖了一切。
自从您搬了“新”家,身边的人事都慢慢恢复,只是孙儿的思念愈发深切。
瞎忙活
“爸妈,你们别瞎忙活了,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
“坐不住啊!”
熟悉的对话在无数个家庭中辗转,“瞎忙活”成了子女的口头禅,也是老父母的“日常工作总结”。短短的子女深情的嗔怪,流露出子女对父母那浓浓的爱和怜惜,但这真的是“瞎忙活”吗?不这样就真的可以享清福吗?
其实,“瞎忙活”也许不是老人们想要的。人似乎总有忙不完的事,不管年轻还是老迈。小的时候,还来不及玩耍就悄然长大。青壮年时从不懂偷闲,工作结婚带孩子。那时活得像牛——无言无怨,唯有一边羡慕那些落得清闲的老人一边埋头苦干,期盼着有一天能够放下这劳累的一切去享清福。
可当真正白了头发模糊了双眼,又觉得闲了便空虚。闲了未必就是享清福,看着子女都在像自己年轻时一样为生活奔波,刚开始还庆幸清闲,久了便憋了一肚子话想倾诉,儿女在家的时间总仿佛不够用。再久点则见人就说,说得精彩也罢,可无非就是些生活琐事,对年轻人来说索然无味,于是老人们就被扣上“唠叨”的帽子。越是孤独越是想倾诉,越是倾诉越是“讨人厌”,后来自己终日无所事,坐在家中,面对着冷冷的墙壁,有老伴的还可以嗑上两句,独自一人一天下来说不上几句话,徒然生悲。就像无边无际的海面上的一座孤岛,看着来往的大小船只在身边掠过,偶尔有船只靠岸,却又匆匆离去,想挽留而留不住。忙的生活过得充实,用苦来把思念填满,用累来换得一夜安眠。就这样,老人们打着“老有所为”的旗号开始“瞎忙活”起来。尽管知道没必要,但依然乐此不疲,或多或少是对空虚的打发吧。
同时,“瞎忙活”仿佛也是对已过去而不可复来的生活的悼念。老人记忆总有一个特点:记远不记近。他们滔滔不绝地讨论几十年前的辉煌岁月,却记不清近些天的芝麻小事。老人枯瘦的双手曾忙碌地为工作和家庭,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孩子,辛苦但快乐,那大手牵着小手走过的时光倍感亲切和清晰,仿若就在昨天。现在小手长大了,老手却在风中寂寞着。曾那样健壮的老手啊,昔日“锄禾日当午”,如今就像新翻过的土地那般沟壑明显,想再抓起锄头往地里乱舞,又已然成为儿女口中的“瞎忙活”,忙碌了一辈子的老手“尴尬”得来回搓动,想说点什么,却又咽住,因为谁不知道那一番众所周知的大道理呢?有些时候就是想偶尔任性,但偏偏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便只得沉默点头。
不得不说,“瞎忙活”亦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爱的体现。老人,如枯黄的树叶,常怀“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心,即便哪天“零落成泥碾作尘”,也只当为子女留下最后的赠礼罢了,满足而无悔。老人,又如飞鸟的羽毛,托鸟上蓝天,哪一天残了,掉了,在空中划过谁也看不见的弧线,投身泥土里。也许还会自豪地仰头远望,“呵!那是我儿啊!”
一句“瞎忙活”出自内心的孝,却有意无意地打击老人们“任性”的要求,那就是陪伴。也许我们该多点了解老人们需要什么,也许我们在无意识地变成了父母老年里的过客。安东尼·罗宾有句话说:“你知道怎么去做,但就是不去做。”别再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为自己解脱了,多一丝陪伴,听听老人的唠叨,也许比一百句“瞎忙活”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