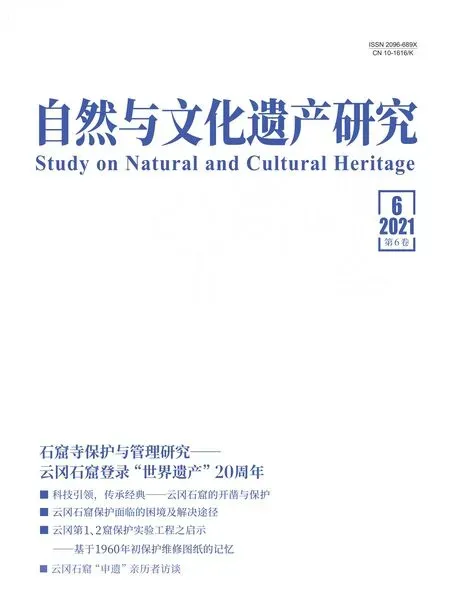云冈石窟“申遗”亲历者访谈
宋 瑞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2001年,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28处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的申报涉及多方主体力量的参与,不同的参与者基于自身的动机在世界遗产申报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将申报本身看作一个过程,能够更清楚地反映遗产研究过往所关心的主体关系、保护理念等一系列问题。为此,笔者采访了郭旃、黄继忠、孙辅智3位云冈石窟申遗工作的亲历者,借此反映这其中所包含的诸多理念和实践性问题。
核心理念与基本要求——郭旃访谈

郭旃(1948—):河南南阳人,历史学硕士,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世界遗产处处长、巡视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副主席。参与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ICOMOS/China)的创立,并曾任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在我国文物系统长期从事文物的保护、研究和管理工作;致力于我国世界遗产项目的申报评选和世界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曾参与ICOMOS《奈良真实性文件》《西安宣言》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献的研讨制定。在世界遗产工作和中外文化遗产交流合作方面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
宋瑞:郭旃老师您好!本次采访主要围绕云冈石窟申遗这段历史,请您谈谈在工作中的经验和思考。您曾说世界遗产有“三大支柱”,这3个“支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郭旃:“三大支柱”主要指世界遗产核心要素——全球突出普遍价值(OUV)——需要满足的3项基本要求:①符合世界文化遗产起码一条价值标准;②具备真实性和完整性,能够体现遗产的真实面貌、反映完整的历史信息;③有良好的保护管理,能够使遗产永续地保存。这3者是支撑起一个世界遗产OUV最重要的3条标准。在我国世界遗产事业发展之初,我们对这3条标准的认识和掌握也经历了熟悉和接轨的过程。而云冈石窟的申报正是在大家较早地认识到世界遗产的标杆性意义,并共同遵循三大核心标准的基础上实行的。
宋瑞: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标准共有6条,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考核遗产地申报的过程中,对遗产价值的认定也非常严格。所以在申遗文本的撰写中,我们往往很注重对这方面的阐述。您对这6条价值标准在云冈申遗工作中的运用是如何认识的?
郭旃:界定文化遗产价值的6条标准有:①人类创造性智慧的杰作;②一段时间内或文化期内在建筑、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中代表人类价值的重要转变;③反映一项独有或至少特别的现存或已消失的文化传统或文明;④描绘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时期的建筑物、建筑风格、科技组合或景观范例;⑤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特别是在其面临不可逆转的变迁时的传统人类居住或土地利用的突出范例;⑥直接或明显地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相关(该项标准一般不宜单独作为列入条件)。
一般来说,一处遗产只要单独满足第6条以外的任意一条,就可以认为它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标准,这对云冈石窟而言并不困难。但是,当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与同类遗产进行比较。云冈申遗时,莫高窟、大足石刻和龙门石窟都已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比较。最初大家总认为,比较就是要一较高下,在重要性和价值上压过其他遗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遗产地之间的比较,是通过总结各自的特点,在各自所属的时代、类别中找到自身的特殊性、代表性、专属意义与价值。石窟申报中,如:龙门石窟可能最突出盛唐时期的杰作,而大足石刻代表的可能主要是宋代及以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道德关系更密切的发展和繁盛阶段,具有突出的民间风格。云冈石窟的代表性就在于,它是北魏时期由统治阶级主持开凿的皇家石窟,代表了石窟艺术初传内地时,外来风格与本土风格的交融,这也是它最为突出的地位和价值之一。
宋瑞:除了价值标准,真实性与完整性也是必须具备的核心要求,而且这两个概念也被学界反复讨论。您在云冈申遗时对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怎样理解的?对比当时,现在的您又有了哪些新的想法呢?
郭旃:真实性和完整性之中,我们对真实性的讨论比较多。它的原文是“authenticity”,中文语境和儒文化圈中并没有完全与之对应的词。我们目前习惯把它翻译成“真实性”,但还有一些同行习惯使用“原真性”,这是日本传来的译法。我曾经也偏好“原真性”,但后来发现这个词在实际操作中会造成一些误解。比如,有一处重要古建筑修复的时候,一些学者认为“原真性”强调的是原来的真实性,也就是它最辉煌时期的样貌,因此修复应该排除后代的改建,将它“再现辉煌”。产生这种理解,是因为这种译法强调了“原本”的意思,但实际上“authenticity”的词义中并无“original”的含义,它强调的不是一时、一事的真实性,而是遗产从创造至今发展全过程的真实性,其中的任何变化都是历史全过程中留下的实物印记,这是对遗产“史实性”的准确诠释和尊重。现状中除非含有给遗产的安全带来明显、急迫的威胁和负面影响的因素,否则一般对其保存现状都不应该修改。所以,在认识云冈石窟时,我们认为它的真实性不仅包含北魏时期开凿的洞窟主体,也包含后代在窟前接建的木构建筑以及对窟内造像的重妆等,它所具备的是一个全过程的真实性。
而完整性的要求,就是指遗产能够完整地体现出它所代表的文化面貌,并能够确保遗产的可持续性。关于这一概念的理解近年来也有发展。以云冈石窟申遗为例,当时为了保障石窟周边景观的协调性,拆除了附近的大批村镇民房。有学者认为依照现在对完整性的认识来看,当时的民房有的时代已久,也见证一定的历史沿革,或许只需要改造,而无须全部拆迁。认为这些民房也是云冈石窟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是一种社会的选择和历史。
由此可见,我们对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的。
宋瑞:您提到了云冈周边的拆迁工程。我们知道当时为了申遗,政府投入大量精力对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改,拆迁是整改的一部分。您对云冈石窟当时的环境整改,包括后续的保护管理怎么评价?
郭旃:前面说到,保护与管理是世界遗产OUV的“三大支柱”之一,是可持续性的保障,也是评定一处遗产的重要考核项目,要求周边环境景观需要与遗产本身相协调。云冈石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峻,109国道从石窟门前通过,运煤的车辆频繁往来。附近的云冈镇和村庄无序扩张,很多房屋已经建到了石窟面前。这些房屋没有经过统一规划,参差不齐,与石窟本体严重不协调。不仅是云冈石窟,我们以前很多地方在公共卫生、环境景观上做得不尽如人意,有些景区的卫生和秩序比较混乱,大多欠缺对历史遗产周边环境景观的保护意识,没有做到让遗产与其周边环境相协调。
我们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在和世界遗产旗舰样板对接的过程中,克服存在的问题,改善遗产周边环境,做出了让国际同行都称赞不已和羡慕的成绩,树立了一个个成功的样板。比如,云冈石窟门前109国道的改道和周边村镇的整体搬迁。在当年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环境景观问题认识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难度这么高的环境整治工作,起了带头的典范作用,很了不起,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但是,在后续的工作中也会存在一些认识不清晰导致的问题。比如,今天云冈石窟的入口处建设了许多古埃及、古罗马风格的建筑,包括景区内建设的水上殿堂等,在业界争议比较大。前些年大同古城的开发保护,规划界和古建筑界也都有争议。我们认为:附加、新搞的建设需要慎重考虑它对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影响,而且需要保持环境景观协调的审美,以此来判定每一个主张和项目的合理性、可行性、必要性,做出合乎专业和法规的抉择。真正的保护是要把真实的遗迹遗物可持续地保留和展示,即便它是残砖断瓦,也是真实的历史证据,从审美和历史的角度也可以让人从中感受到古朴与沧桑。所以,世界遗产要求的“保护与管理”一项也正是为了给遗产地的长期保护、科学管理提出要求,使其具备的价值和真实性、完整性能够永续地保存下去。基于我们成功的经验和认识的不断进步,我想云冈石窟未来的保护与管理会越来越科学、合理。
宋瑞:是的。那么,您如何评价云冈石窟申遗成功的意义?
郭旃:一方面,云冈石窟的申遗是在中国世界遗产事业推广的较早期,对社会认识的深化和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是一个表率,给后来的工作带来了强大的鼓舞。比如,它对我们“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的申请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在文化传播的路线上,石窟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项代表性的遗存,云冈石窟艺术也是中外文化融合的产物。我们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后,有一位外国专家做过一个题目为“One Belt、One Road、One History”的演讲。而在这一文化线路之中,石窟是人类历史上和平交流重要、主要的实物见证。所以云冈石窟的申报在早期就为我们后来提出“一带一路”的愿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见证。此外,申报过程中我们对真实性与完整性的深入认识、对环境景观的深入改造等都具有值得汲取的经验。
另一方面,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常常是各国遗产地人民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广度、高度、深度出发,在对比研究中,对原本可能是与生俱来、习以为常,乃至司空见惯、视若平凡,甚至可能熟视无睹的身边家乡进行的重新感知和认识,也是全社会对发现、发掘遗产的独特意义与价值,并进一步加强科学保护和严谨管理的动员和推进。所以,申报过程本身就是值得支持和赞赏的事。即便申报一时不成功,这个过程也已经达成了认知的深化和推广,它的积极效益和影响也已经彰显。
价值认定与科学保护——黄继忠访谈

黄继忠(1965—):山西原平人,工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1988年起在云冈石窟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曾任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云冈石窟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2011年任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党组成员,现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丝绸之路文物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古遗址保护与加固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石质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ICOMOS-ISCS)专家委员、国家文物局砖石质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等职。主要从事岩土文物保护,先后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
宋瑞:黄老师您好!云冈石窟启动申遗工作的时候,您正在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工作。请问当时是如何决定要正式开始申遗的?
黄继忠:云冈决定启动申遗工作是从1999年开始的,当时大足石刻申遗成功给了我们很强的动力。之前云冈一直没有把申遗工作提上日程,是因为周边的环境比较差,周围全是煤矿、企业、村镇,污染非常严重,距离世界遗产的要求还很远。但是大足石刻的申遗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因此我们组成了一个考察队伍,在大同市文物局时任局长的带领下考察了大足石刻和当时正在申遗的龙门石窟。之后,我们向市政府汇报了两点内容:①云冈石窟申遗是完全可能的;②申遗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环境整治好、把文本写好。市里反复研究之后,正式决定启动申遗工作。
宋瑞:环境整治的工作主要是由市政府来承担,而申遗文本的写作则是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的职责。当时您也参加了文本的编写,这个过程中您有哪些思考呢?
黄继忠:之前的几家单位申遗时都邀请了外面的专家来帮忙编写文本,但云冈石窟申遗的时候,文本是由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自己的团队完成的。那时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部分都很年轻,以这一拨人为主来完成申遗文本的撰写,真的很不容易,需要比一般的专家学者们付出更多的心血。但是完成文本的过程促进了大家的研究、学习,极好地锻炼了我们的队伍,有几位大专毕业的成员后来都是以研究员的身份退休的。在文本编写的过程里,郭旃老师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从开始撰写到送审,再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郭旃老师帮我们审阅、修改了无数遍。
对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而言,撰写文本的过程让我们对云冈的价值进行了系统地梳理、深入地挖掘。当时我们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的6条价值标准,提炼出了云冈石窟的4条价值:①云冈石窟是世界伟大的古代雕刻艺术宝库之一;②云冈石窟对石窟艺术的变革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③云冈石窟是公元5世纪中国民族大融合的特殊见证,是早期佛教艺术大规模植根中国中原地区的杰出代表;④云冈石窟是世界佛教石窟艺术第二个繁荣期的最佳作品。这4条价值也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
宋瑞:这4条价值精准地概括了云冈石窟的独特性和珍贵性。这20年来围绕云冈进行的各项研究不断地发展,如果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云冈石窟的价值,您会有哪些新的想法?
黄继忠: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云冈石窟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上的价值十分突出,当时申遗文本中虽然提到这一点,但阐述不够深入。另外就是限于当时考古发掘资料的不足,我们只知道1992—1993年窟前遗迹的考古发现。后来在2010—2011年间,我们进行云冈防水保护工程之前又在石窟顶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在西区洞窟顶部发现了北魏的佛塔遗址、建筑遗址,推测是寺院建筑;在二区窟顶发现了北魏和辽代的佛塔,以及辽金时代的大型冶铁遗址等。也就是说,云冈不仅仅是佛教石窟,也是一个包含北魏、辽金寺院遗址、冶铁遗址、道路遗址乃至戍堡遗址在内的、内容更加丰富的遗址群,它的价值也应该更加多元。
宋瑞:为了申遗,大同市在云冈周边做了大量的环境整治工作。而石窟本体的科学维修保护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这也给后来的申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您怎么评价早年的修复工程?
黄继忠: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看到石窟岩体开裂、坍塌,洞窟岌岌可危。周总理就提出,要在3年时间内完成石窟的加固保护工程,“不管怎么样,云冈石窟艺术一定要保存下去”。所以,1974—1976年的3年间,国家投资160多万元,支援云冈石窟进行了“3年保护工程”。
“3年保护工程”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最重大的意义就是解决了云冈中央区大洞窟的稳定性问题。石窟最怕整体垮塌,垮塌之后就再无科学研究可言了,所以首先要让洞窟保留下来,然后才有条件做防风化、防渗水等进一步的工作。“3年保护工程”就是通过科学手段对石窟岩体和洞窟本身进行加固,从根本上解决了让石窟保存下来的问题。此外,它还给云冈培养了一支文物保护队伍。这支队伍在“3年保护工程”的过程中组建,之后逐渐成熟,一边完成云冈其他洞窟的加固保护,一边支援国内其他地方的文保工作,比如20世纪80年代支援了大足石刻、响堂山石窟等重要文物单位的保护工作。
我国石窟寺保护面对的第一大问题就是石窟的稳定性问题,不仅是云冈,其他石窟皆然。现在大型石窟的稳定性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很多中小型石窟还没有得以解决,所以目前的工作仍是抢救性和预防性保护并重。而云冈、乐山、敦煌等大型石窟或石刻的稳定性问题得到解决后,面临的就是解决其风化的问题。
1992—1997年,云冈再次进行了被称作“八五保护维修工程”的维修保护,国家、山西省政府、大同市人民政府总计投入1 000万元,主要针对石窟的风化问题做了基础性的工作,比如降低窟前地面、铺墁石条、修筑排水渠道、修建第7、8窟木结构窟檐等,并且对少部分洞窟继续进行加固。
我认为,历史的保护措施和手段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我们是前人的后人,也会成为后人的前人。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做的,就是用此时最科学、最合理的办法去保护遗迹遗物,同时给后人的保护措施留有余地。“3年保护工程”的修复中有些地方人为痕迹过重,但我觉得瑕不掩瑜。敦煌莫高窟当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给洞窟前面建设了保护性的外立面,人为痕迹重,和原始岩体有明显不同。但是如果没有当时那些不太完美的措施,现在很多洞窟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总体来说,“3年保护工程”为云冈的现在和未来都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值得肯定的地方更多。
宋瑞:我们知道,《世界遗产公约》对遗产的保护方式有着严格的要求,需要在保护过程中保持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这需要正确的理念来引导。您在主持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时,都秉持着哪些核心理念呢?
黄继忠:1992年,国家文物局联合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办了古迹遗址保护管理培训班,为期1个月。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培训班,盖蒂保护研究所的阿格纽先生、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主席沙利文女士、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院长、著名文保专家黄克忠先生这些顶级专家都曾为我们授过课。所以,我们从那时起就已经受到了先进文保理念的影响,比如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预性原则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也是国家文物局和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几方共同完成的,其中对中国已有的保护理念中合理的部分有所继承,也融入了国际上先进的理念,这在我刚开始从事工作时就对我有很大影响。我们在文保维修工程中,特别注重尽可能减少对文物的影响。在做一项工程的时候,所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都要考虑,在决定实施之前要反复斟酌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它的正面作用和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所以当时秉持的理念和国际上倡导的,以及现在国家仍然秉持的理念是比较接近的。
宋瑞:也正因为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坚持正确的理念,不断探索新的保护技术,才能让云冈石窟保存本来的面貌,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日益深入、云冈学也正在兴起、景区的参观展览正不断优化。您对未来的发展有哪些期待?
黄继忠:从云冈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在学科建设过程中,除了着眼于历史、艺术、宗教的研究之外,保护也是极端重要的。没有石窟稳定性问题的解决、没有石窟岩体的加固,现在一切研究都将不复存在。所以云冈学的建设一定要把文物保护、石窟保护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没有保护就没有后面的一切。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曾说,以前他总是从石窟和造像的学术研究角度去看云冈,现在他作为院长,从更全面的角度去看问题,才意识到石窟保护的迫切性,因为云冈的保护问题是如此的艰巨且复杂。我认为,现在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抢救信息、保护信息,因为石窟的客观现实就是今年不如去年、明年不如今年,我们的措施和手段只是延缓它的消亡,不可能让它一直存在下去。所以,通过摄影、测绘、三维建模、报告编写等多种方法来尽可能留存更多的信息是很重要的。
从云冈展览区来说,我感到很好的一点是:有博物馆来补充说明石窟考古的信息。现在院史馆也落成了,其中展示了20世纪初沙畹等外国人拍摄的老照片,以及云冈的同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一步步维修将它的面貌逐步改善的过程。只是不知道多少游客会去参观?我认为院史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在那里可以看到云冈修复前残破的状况,也能看到文保工作者们通过长期的努力取得的成果。现在观众们看到的是石窟比较完美的样子,而看不到它原来的惨状,所以展示修复过程是很必要的。一代代文保人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有了今天成为世界遗产的石窟。如果游客首先参观了院史馆,然后再去看石窟,就可以更加正确地认识到文物保护的艰辛和重要,有利于人们树立更加强烈而自觉的石窟保护意识。
政府协力与持续发展——孙辅智访谈

孙辅智(1945—):山西阳高人,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1964年9月参加工作。2000年2月任中共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2003年7月当选为大同市政协主席。
宋瑞:孙老师您好!您在任大同市市长的时候完成了云冈石窟申遗这项事业,请问大同市决定开启云冈石窟的申遗工作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孙辅智:长期以来,大同市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经济,在文化宣传方面并不重视,导致外界对云冈石窟缺乏了解。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市政府很早就对云冈申遗的提案有所考虑。当时大足石刻、龙门石窟的申遗工作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示范,因此,在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的持续推动下,大同市政府于1999年10月正式提出云冈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2月7日,我们邀请了郭旃先生来大同指导申遗工作,他提出了世界遗产评定的标准要求:第一是遗产的价值、历史底蕴的保护;第二是周边环境的保护。
宋瑞:当时云冈周边环境污染严重,村镇建筑影响石窟本体,政府主要采取了哪些政策来改善环境呢?
孙辅智:为了使云冈石窟的环境达到世界遗产的标准,大同市成立了整顿环境的领导组,我任组长,副市长解廷香任副组长,制订了详细的规划和目标,并逐项落实。1999年,云冈门前的109国道改线工程竣工,原来的公路也改造为云冈旅游专线。我们对附近的污染企业进行大力整治,并在旅游专线沿线进行大范围绿化,有力地改善了石窟区被煤尘污染的情况。工作中最困难的内容还是云冈镇的整体搬迁,沿线的拆迁任务非常艰巨,当时很多群众不愿意离开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我们坚持和群众沟通,宣传保护云冈石窟的意义,最终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可。云冈能够成功申遗,不仅要归功于相关工作人员的努力,更应该归功于当地搬迁群众的牺牲。整个拆迁改造工程前后投资了约1.5亿元,搬迁面积达到58 000 m2。后来,我们又投资3 000多万元完成了云冈引水和排水的整修工程。
2001年3月3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拉菲克·姆高博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来到云冈石窟考察。他来的那一天非常冷,气候恶劣,但他冒着严寒在石窟考察,由当时的副市长解廷香陪同参观。那时石窟周边的环境还没改造完,他留下的意见就是必须好好整治,还表达了要再来探访云冈的意愿。
宋瑞:虽然困难重重,但大同市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的改造,也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
孙辅智:是的,2001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主席团会议上,云冈的申报通过了初审;接下来,12月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将进行最终表决。当时我们满怀信心,我有幸作为遗产地的市长跟随中方团队一同参会。
那天是2001年12月13日,云冈排在下午的第4个项目,因为前2个项目遭到很大的非议,讨论超时,云冈可能会被推迟到明天的会议。大同市的同志们早已聚集在云冈石窟前等待结果,谁知一直等到了北京时间的半夜。所幸,云冈终于在当天上会了。拉菲克·姆高先生的助理尤戈博士作了云冈石窟各项情况的介绍,国际专家发言表示完全赞同,随后主席团举手表决,全票通过!全过程只用了7分钟。中方代表师淑云女士和我都在大会上表示了感谢。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我立即给家乡的同仁们报信,当时已经是北京时间12月14日凌晨0点25分了,大家仍然非常激动,热烈地庆祝了一番。
宋瑞:您亲眼见证了云冈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孙辅智:对世界遗产工作,我们原来没有认识得这么深刻。去了芬兰参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全世界都在关注这项给国家增光添彩的事业。中国国家文物局的郭旃同志和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的同志们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市政府做的只是辅助性的工作。后继的几任市长也很重视云冈石窟的保护,经过一代代的努力建设,云冈的面貌越来越好了,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宋瑞:您认为,云冈的申遗成功对大同市有哪些意义和影响?
孙辅智:趁着申遗成功的东风,云冈石窟的管理也进一步加强,能够以更新的观念、更科学的理念指导工作。我们也适时地提出了3个“加强”:加强保护;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加强科学管理、促进科学发展。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也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更先进的保护方式,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坚持建立科学完整的资料系统对云冈石窟开展考古研究。市里坚持以事业单位的改革为契机,以科学的管理模式提升云冈的管理水平。1998年,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就从原来的科级单位调整为正县(处)级,2006年正式成立了云冈石窟研究院。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5月视察云冈石窟,更是带来了飞跃性的进步。我们的研究力量加强了、专业性更强了,从前市政府没有主管文物工作的领导,现在也有了。
另外,云冈石窟申遗成功对旅游业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大同市寒冷天气多,每年适合旅游的时间很短,过去来大同旅游的人数不多,甚至许多大同人都鲜少来参观云冈石窟。现在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慕名来云冈石窟参观。旅游产业也对大同市内其他配套产业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申遗之前,旅游产业在全市GDP中的占比很小,而现在旅游业蓬勃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前大同的旅游收入可达到1年700亿元左右。当然,发展旅游是增加了收入,但文物保护则有一个承受能力的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如何协调这个矛盾,二者之间更重要的还是文物保护。
总体而言,云冈石窟越发展越好,我们为云冈,也为大同市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