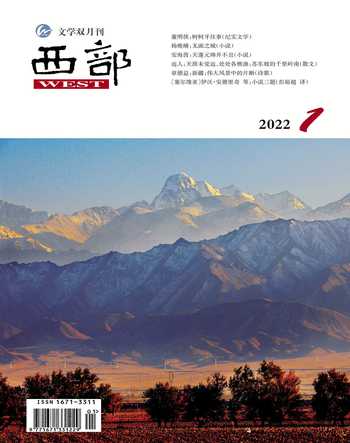慢动作的奔逃
何荣
屏幕右下方伸进一只话筒,“市民徐先生”出镜,画面饱和度太高,西装发黑,脸发红。您为什么要来广发家居城呢?镜头越过记者肩膀,对准徐先生:正好家里装修,听说建材市场开业,顺便来看看。
画面配字幕,黑体,白芯黑边,很正式,电影感强烈。张杰嘿嘿干笑,把进度条拉回一点。“市民徐先生”再次出镜,刚才那一遍像是彩排。
怎么又在看?有完没完啊?
哟,建功还挺帅。头一回上电视吧?
他笑得很哑,算是默认。手上力道不对,把一次性杯子捏扁了,啤酒漾了一身。张杰扯了纸巾帮他擦,他任他擦。采访那天建材市场的电焊味儿又回来了,他对自己说:不是。
不是头一回上电视。一九九八年中考,他是全县第一,县电视台来采访中考状元。那时也有一只话筒伸进镜头,他身后不是建材市场,而是灰扑扑的二中大门。在他被采访的同时,大门右边的传达室里,坐着四十一岁的父亲。
换衣服时,他把刚才在建材市场拿的一叠名片掏出来,抽出一张,展平。上面印着两个黑体字:周磊。
他认识一个周磊。他初中同学,家里是种大棚的。就是那种塑料大棚,种反季蔬菜,西红柿花点催红素,黄瓜花蘸膨大剂。一大早就要起来揭草席,太阳下山前再盖好,忙都忙死了,不会有人帮他出头。他跟张杰堵过周磊,敲不出几毛钱,就是过过痞子瘾。他们也没有存心难为他,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村的。不过周磊很硬,难搞得很。为了让他嘴上服个软,他带头扇过周磊几巴掌。那会儿是冬天,周磊耳朵上长了冻疮,挠破了,没几下就被扇烂了。他手心血淋淋的,很红很艳,看着腿软,赶紧去厕所洗了。早自习下课,他潜入医务室,偷了两颗土霉素,用纸包好,拿钢笔擀碎了。课间操结束,他叫上周磊,躲到实验楼后面的背风口。他打开纸包,撮点黄药粉朝周磊的伤口上撒,边撒边骂:怎么这么不经打?我要是下手再重点儿,早把你打死了!他估摸着,周磊他爸也会这么打他,说不定也这么给他上药。张杰经过,看看周磊,又看看他:哟,你俩这是干吗呢?他脸一热,头一昂:不小心打坏了,治一治不行啊!
后来他就没动过周磊。天热了,周磊的耳朵快好了,痒得很,被光一照,红通通的。血在皮下安静地流,没再跑出来吓他一跳。从头到尾,周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像一袋很沉的货。
爸爸,腰带又打死结了!
贝贝养得太金贵,在学校老被人扒裤子。王俐的对策是,把所有的松紧带裤子换成系带裤子。他叹口气,放下名片,蹲下身帮儿子解裤带。结太紧,他用牙咬,啊呜啊呜,头拱在贝贝肚子上,贝贝咯咯笑。你爸以前是扇人耳光的,怎么到了你就被人扒裤子了呢?他打算找个机会,偷偷教贝贝:谁扒你就扒回去!这句话是徐富贵当年教他的,挺管用。当年周磊他爸没教过他这个?那会儿他们个个都野得很,有个别不野的,不是机关干部子女,就是周磊这种老实头。贝贝的教育方式就是致敬那时候的干部子女。入园费六万,每天穿得干干净净,斜挎印着自己名字的订制小水壶,学了钢琴和画画。他儿子很文雅,完全没有野的必要。
爸!爸!你坐下!你坐下吃!
徐富贵不,徐富贵偏要蹲。他穿着儿子买的乔丹运动鞋,两脚一拧,背朝着他,埋头啃大饼。在苏州火车站里,徐富贵折叠起自己,喂着那只农民胃。
蹲式馬桶白装了,高龄老人卡白办了,业主老年群白加了,徐富贵还是要回老家。加湿器、扫地机器人、健身年卡、周五家庭日,市三好生长大了,变成市民徐先生,他一手打造的新式家庭快要孵出来了,却被徐富贵戳破一个洞。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徐富贵,腿坏了之后就在街心卖水果。水果摊旁边是猪肉铺,再远一点儿是供销社大楼,现在拆了,变成“易买得”超市。念初三时,每个晚上他总有卖不掉的“骷髅头”吃。长虫眼的、烂疤的,每只苹果都剜得七窍玲珑,像人头骨。徐富贵看着他吃,他吃给徐富贵看,嘎嘣嘎嘣,敲骨吸髓。
现在,徐富贵在他脚边蹲着,啃大饼给他看。大饼是一张脸皮,啃一点儿,少一点儿。视线移过来,底座是两只系带皮鞋,西装裤裤缝笔挺如柱,撑得自己高大又无情,他只好坐下。他发现徐富贵后脑勺很扁,奶奶那辈人都喜欢把小孩睡成扁头。徐富贵是老幺,开头那几年被正儿八经地宠过,有时候他会返祖一下,朝他讨要一点儿一去不复返的“扁头时刻”。
他给不了。王俐没来,贝贝也没来。当初是他一个人来车站接,现在也是他一个人送。永远是一对一,爹跟儿子,儿子跟爹。他们仿佛还卡在他上高中的时候,徐富贵踩着三轮车把他送到村口搭公交。钱够不够?不要舍不得吃,我供你们姐弟俩吃口饭总归供得起的。车来了,徐富贵止了步,夕阳跟着车跑。车窗斑驳,窗外的油菜花田里间种着梨树,黄的金黄,白的雪白。沂河大桥下有养鸭场,白鸭像废纸,麻鸭像泥巴。远处河坝上一排排小白杨,像篦子齿。过了个小收费站,县城就到了,两边的半环形欢迎牌硬搂你入怀。进了城,公交车就规矩多了,开始按站停靠、等红绿灯。车不直达他学校,最后二里路还得靠小三轮。不是徐富贵脚蹬的乡下三轮,而是烧燃油的城里三轮。去县中几块?三块。两块行吗?行,县中嘛,天之骄子哦。天之骄子现在要送老爹回乡下。这条线上的春夏秋冬,他看了三年,现在还给徐富贵。徐富贵进了站,成为人群的一部分,灰扑扑,黑乎乎。徐富贵不富也不贵,种了大半辈子地,泥土色打脚底爬了满身,渗进皮肉。他的朋友圈封面图是他姐拍的照片,他跟徐富贵还有贝贝坐在一个绿草坡上,三人长得很一致。风也被拍了下来,它是画面里的第四个人,负责逗祖孙三代笑出来。
胡丹的生活分为“打榧子前”跟“打榧子后”。
一九八四年冬,一个不相干的男人走过贤官医院妇产科门口,一眼看见了抱头蹲着的胡国栋。男人想:去年我女人小产那会儿,我也是这副[屣] [怂]样。
胡国栋到底是什么[屣] [怂]样呢?没人记得,没人能说。大家只知道他在手术单上签字时哭了。一个三十多岁的老爷们儿哭,医院马上传遍了。三个小时后,结婚六年的小学教师胡国栋终于得了个闺女,母女平安。
胡丹一直是个小顺民。两只中国特色的单眼皮,没有任何发型的男孩头。走在路上总是磕磕碰碰,总有人踩她脚、撞她肩膀,他人即路障。脾气太软,妈会骂她窝囊;太硬,妈会说反了你了。她感觉妈在用一个模子浇铸她,刮去毛边打磨光滑。假如一个家里爸像妈、妈像爸,那么胡丹一定会长成假小子。可是妈像爸的同时没有忘记自己是妈,把她的发式领口管得严严的。作为教师子女,她入学比别人早两年,上初中后,班里女同学纷纷绑起武装带(胸罩),她还不太讲究地穿着棉汗衫。某天妈买来一件化纤紧身小背心,偷偷塞给她:勒一勒就不会窜来窜去了。勒什么?窜什么?她半天才悟出来,妈想在胸罩跟棉汗衫之间给她找一个过渡点。之后小背心因为太紧被送给了八岁的小表妹,她觉得一向能干强悍的妈有那么点小失败。
直到一九九七年夏,打榧子让她逃出死循环。
一开始,榧子怎么也打不响。徐建功教她,把右手举高,拇指中指对捏,一搓。搓几回,指肚生疼,还是没声音,就泄了气。刚见第一面,他就把她眼里那点瑟缩给逮着了。他知道她爸是新调来的老师,她家肯定没人教她这些,于是他亲自上阵,教了她全套。
李玉换地方了,要带你去吗?
这次他没装聋,他像披上军大衣一样,披上了他爸的镇定。他像个领导,说行。
她领头,两人往耿圩庄的河坝上走,风吹斜了绿树,树冠在头顶合拢,树下是劲道的、清凉的绿空气。她走得挺快,他老掉队,隔一会儿,她就催一催。她不怪他,他要是急着赶着,那跟张杰他们就没两样了。他做跟屁虫还是头一回,以前都是人家跟着他。她脑后撇着两条小辫,她妈给她编的,下手紧,看着都觉得头皮扯得慌。他想学他姐那样,把手插进发根,帮她松一松,但她始终离他一臂开外。而且,她满头汗,他得忍受那湿漉漉的手感。拐了个大弯,再上土坡。哇,满满一坡白鹅。一层雪皮罩了地,下面几百只小红脚蠕动着,向南移。有几只跑得不匀,雪皮破了好几处,又飞快愈合。两人看呆了。
云移得慢,一摊灰影子在鹅群里爬,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灰影子越来越近,他俩眼前一暗,回过神来,开步走。
终于到了。她做了个“慢用”的手势,回头就走。他一把拉住她,两人并排伏在深草里,一点儿也不觉得硌。暑气蒸腾,身下的植物被压平,渗出汗气。
波光在远处,软极了,一漾一漾的,直送眼底。人影逆光,黑乎乎的,淋了水,又亮晶晶的。有一些凹跟凸,看不太清,有心朝前移,又挣不脱身下这块地。它黏着你,在哪儿趴下去,就得在哪儿待着,不然动静就太大了。他俩只要稍微一冒头,就能看见右边的运河闸口,过了闸口往北二里地,就能看见他爸跟她叔在田头歇脚,风在树顶,就是下不来,两人扇着破草帽。闸口往南是养猪场,他妈和她妈在里面拌饲料。现在,他俩在这儿趴着,啥也不用干,看就行了。有一阵儿,她发现他在看天,天那么好看?蓝的多,白的少,小蠓虫飞呀飞。她悄悄给了他一肘子。
李玉终于洗完澡,穿上衣服,走了。他还趴着,好像刚安了假腿。她站起来,眼睛眯着,像个小老太太。她得等他消化消化。绿树里藏着蝉鸣,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压着。
咋样?好看吗?
……就那样。
有那么一阵子,她觉得白忙活了。他教了她全套,她就是想回报他一下。他觉察到了,教她:你不能这么问。
那怎么问?
别问,这种事最好别问。
她点点头。
他们往回走,挠着蚊子包。白鹅早散了,土坡很普通。光线也不够了,那种喜气洋洋的亮没了。果然白忙活了,如果李玉排第一,那她也不是第二。她踩了点,贡献了情报,可他并不把她当成同党。
炊烟起了,这里一注,那里一注,像龙吸水。他看看她的籃底,松松几把猪草,这哪够?他叹口气,抖空了自己的,塞饱了她的。他预备好了一顿打,是他借他妈的手赏给自个儿的。小流氓!叫你看人家洗澡!下回还看不看了?
他妈常备一根油亮的藤条,拿来抽人腿肚子,挨一下能让人活蹦乱跳。一指宽的烙铁,一小寸一小寸,煎着皮肉。麻辣之后,钝痛凸起,一条条交错,打得人又红又胖,像个新生儿。想到一半,他发现她在把猪草往回塞。他凶起来,他不能让她弄乱了计划,夺了几回,她住了手。
晚饭前,他妈没回来。之后,一切都飞快,他们永远失去了那个下午里的慢。
主要是我们疏忽了,一开始以为就是中耳炎。等挂了专家号去看,已经晚了,化脓了。哎呀,小徐你不要客气嘛!……后来只能把听骨拿掉,这边耳朵就听不大清了,我们囡囡真是可怜……
可怜囡囡王俐掰开大闸蟹的壳,两排蟹眉毛整整齐齐,中间一汪金黄。她像在听别人的事,永远是一张厌食症样的死人脸,这张脸常年不见阳光,被私家车、空调房和机关办公室轮流捂成蚕白。两颊没血色,得用腮红补,薄薄搽两片,夹得脸更小。这种脸色的奥妙就在于,穿什么颜色都洋气,应酬时带着她,就相当于戴着欧米茄。上次他来吃饭,岳母讲的是王俐高中毕业后为了报志愿做近视手术的事。八十年代末的听骨手术,九十年代末的近视手术,听起来都很超前,这些手术会发生在自己家吗?光手术费就不是个小数目,只要死不了,徐富贵不会掏这个钱,也掏不出。他和姐姐似乎都知道自己没资格可怜,都结结实实长大了。
结婚后不久,他在观前街被一个穿紧身黑衬衫的人拦下,说是“发廊开业大酬宾,充一千送一千”。他没怎么推辞就跟着去了,“小海造型”在二楼,玻璃楼梯,台阶上贴着金光熠熠的防滑胶条,两边立着更多的紧身黑衬衫,他一走过就纷纷鞠躬。他不能再去“十元一位”的小理发店了,尽管他对一股烫发剂味儿的“小海造型”没什么好感。王俐一般都是和岳母去美容院,修个刘海就要六十八元。他得尽快习惯这些流程,早点把徐富贵味儿清干净,这味儿就像葱蒜,吃时香,吃完臭。徐富贵喜欢去公园看人打牌,那里有最老式的剃头摊子,一把椅子一块白布,五元一位。一地碎发,白多黑少,太刺眼。
后来,“小海造型”倒闭,他的两千块还没花完。店家好心发来短信,告诉他店面转到了十全街,改名叫“小海发廊”,余额可以继续使用。他按地址去找,在很远的地方停好车,发现发廊招牌上写着“十元一位”。他之前御用的首席名剪跑了,换成了怯生生的新人小马。小马口音重,听着耳熟,一问,巧了,两人是老乡,还是邻镇的。小马提起附近有家苍蝇馆子,老板老板娘都是他们村的,正宗老家味儿,小鱼干炒青椒,白面饼一卷,香不死你!聊得正起劲,小马手滑,给他脑袋上剃秃了。他手一挥,说直接剃圆寸得了。对不住啊哥,晚上有空不?我请你吃饭!两人加了微信,六小时后,脸对脸吹瓶。去他的大闸蟹!去他的鸡头米!去他的冬酿酒!他解了绑,挺快活,把老丈人送的表抹下,放进公文包内袋。他们点了不少菜,老板见是熟客,免费送十只锅贴。眼看小桌摆满了,换到里间的大桌。大桌又嫌空,干脆把老板也拉过来。
知道你忙!就三杯!我跟你说哦,你今天不要不给我面子。来,介绍一下,徐老板!哥,这是老李。
徐老板你好!以后多关照!
老板个屁,叫老乡就行。乖乖,你俩嘴还真甜。
他摸出一包软金砂,每人发两根。一根现抽,一根夹到耳后。店面不大,挺干净。老李说他以前在老家专门做婚宴,儿子在这边结了婚,他就在这边开了店。酒过三巡,老李讲他还有个女儿,怕计划生育送了人。小马说自己跟踪过前女友,划花了老板的福特汽车。他跟他们没那么熟,他不愿提王俐和岳父母,也不想讲徐富贵和贝贝,他选择供出周磊。
老李这里成了新据点。胡丹说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车不好停。张杰说你把车停佳福国际大厦,走过来就十分钟。走过来?凭什么?胡丹两脚一弓,撇了高跟鞋,一把拔了他的烟。张杰怔住不动,光用眼睛笑。半天,拿过烟盒,重新点一根。
你老公呢?又出差?
烟灰掉下一截,她才想起来吸一口。新做的血红色美甲亮晶晶的,好像还在往下滴血。他帮她开了一罐青岛啤酒,白沫子在拉环口漾,渐渐熄干净了,液面很静。
还是离了吧,你不怕他染了病传给你?
她直接掐了烟去洗手间,皮包留在椅子上,小小一只,也是血红色。他一只手搭上张杰的椅背,在他后脑勺弹一下:少说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心疼啦?我是为她好!你也不劝劝,看着她往火炕里跳!
行了行了,不聊這个。对了,建材市场那个周磊,是咱们那个初中同学吗?
怎么不是?他们办公室挂着合影呢,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人没大变化,就是胖了点。
他不是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吗?听说去常熟打工了。
反正人家现在混出来了。联系联系?
之前初中同学聚会,他就没来,说是联系上了,让加微信群,最后也没加。
这名片上不是有电话吗?打打看?
他瞪张杰,张杰没懂。他四下看看,凑近了小声说:我……以前扇过他耳光,你忘啦?
你扇过的多呢,我哪记得住!
他眼睛一横,一掌抡出去,手腕被张杰牢牢叉住。
来啊,干一架?你看看你,还念念不忘呢!约出来道歉嘛,光膀子背根小皮鞭请罪,让他抽你,抽舒服了为止!
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老李,结账!
三人拐进十全街,这一路全是小酒吧,一家挨着另一家,黄澄澄的,像是在黑里挖了洞。胡丹在前,他俩紧跟其后,空着手,吸着她的二手烟。路灯昏黄,腕表的表链极细,甩着水淋淋的弧线。高跟鞋是冷艳的漆皮黑,红底,前后交错,逗引出全身有规律的波动。晚风送来她的香水味,闻起来像夏天的河,让他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李玉后继有人。
他们走成一个松散的三角形。张杰老是往路边玉店的橱窗里瞄,他以为他想买玉,问他要不要进去看看,他说他在数标价牌上有几个零。笑骂又起,打闹的男人们关注着前面的动静,她一直没回头。他甚至想反超她,看看她是不是哭了。她的眼泪总是很多,在脸上冲出笔直的平行线。他从不帮她擦,似乎怕惊扰了两条线的走向。
等他回过神来,她已经蹲下了。老头跟前有个铁笼子,里面有一只虎皮猫,乡下最常见的那种。她从笼子缝里伸手进去,摸它的小鼻子。
自家老猫生的,就一只,独虎。老头开了笼子盖,把猫抱出来。她接过它,像抱小孩那样抱在胸前。这下坏了,红底高跟鞋完全失效。
干吗,你要买?
她抬头望望他,又望望张杰,没回答。小猫开始舔她的手指,舔得很细,她笑了。张杰摸出烟,自己点一根,扔过来一根。他俩眯着眼,并排站着抽。一辆货车要掉头,引起一阵混乱。他跟张杰避到巷口,正对一台空调排风机,火热的小风徐徐烤着小腿。她就在他们脚边,像徐富贵那样蹲着,小小一尊。
这猫多少钱?
三十。
三十!这不就是只土猫?送我我都不要!那边有个猫舍,给你买只好的!蓝眼睛的,外国种!
我不,我就要这只。
他眼疾手快地扫了付款码,老头抖开一只塑料袋,把猫装进去,捅了两个眼透气。她把它拎到与视线等高,笑出小虎牙。张杰摊手又耸肩,像个老外。
这种我见多了!明天他肯定再搞一只过来,还是自家老猫生的 ,还是独虎,你们信不信?
小猫在塑料袋里钻来钻去,尖利的爪子勾破了好几处。他们又折回去,把笼子也买了。猫回到原处,像他们刚看见它时那样。笼子有点沉,他抠着两边的把手,说我来拿吧。它叫得细声细气,像个婴儿。也许在张杰眼里,他和她和猫挺像一家三口,那又怎么样?张杰那张嘴打小就这样,早就习惯了。他们大声聊起被砍掉的小学,还唱了“小白人,小白棍,打扮打扮要出门”。十全街凭空消失,变成了老家的河坝。没整修的土坝,一下雨就烂成软泥,走上去东倒西歪,像是喝醉了。河坝两边的小白杨长得很密,又直又高。夏天的时候,白天蝉鸣,晚上蛙鸣。堵车的喇叭响成一片,也没能压过河坝的声音。猫什么也听不懂,显得很孤单。张杰抓着笼子原地转悠了几圈,给它起名叫“胡三十”。
她带着猫上了出租车,他们还没闹够。张杰说就咱俩了,要不要再续一场?他告饶说不了不了。酒吧太黑,一杯玉米汁就要三十,够再买一只猫了。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就能买到冰啤酒,坐在马路牙子上喝,吹着风,不美吗?美!一不留神,两人就干掉七八罐。张杰把易拉罐捏扁,朝他裆部一送。幸好他反应快,一把钳住暗器,易拉罐又扁了点。
哎哎!老实交代啊,你俩睡过几回?
有病啊你。
我说真的啊,你看看你,掏钱真积极!
就一包烟钱,你真的有病。
啧啧啧,装什么呀!谁不知道她当年喜欢你!
人家有老公,我有贝贝,醒醒吧你。
那她怎么跟我睡?
他唰一下站起来,张杰失去支撑,歪在一边。张杰还像初中时那么瘦,尖嘴猴腮,笑嘻嘻,软绵绵。他仰着脸看他,笑得更大了。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吃醋了。
他一言不发,夜班公交车在身边呼啸而过。梧桐遮了路灯光,大半张脸浸在阴影里,无法读取表情。
我可没逼她,她自愿的!大家都是成年人,老乡之间帮帮忙怎么啦?
有人经过,张杰住了口。在这无限长的寂静里,河坝再次出现,冬天树叶落尽,枝杈间零星几个喜鹊窝。雪太干,捏不成团。一地车辙印,结了冰碴。她跟不上他们,远远落在后面,一团胖乎乎的红。坝边的麦地里有许多奇特的小爪印,他们分头追,绕来绕去,最后都不知所踪。米厂家属区的澡堂永远冒着白烟,他们在男女浴室入口处分开,永远没机会看见彼此的赤裸。
他掏出手机准备打车,他只想一个人待着。张杰揸开五指,遮住屏幕:
怎么了?觉得我们很脏是不是?
我可没说。
你有资格说吗?好,你干净,那你当初怎么不娶她?
张杰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你别跟我说你只把她当妹妹!徐建功我告诉你,老子最烦你这种玩纯情的。还买猫!操,中学生才买猫。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是好人!好爸爸!好老公!好女婿!天之骄子!你知道她喜欢你,故意不睡,吊着她,对不对?
一拳下去,张杰的笑声变了调,听着像哭。他还想说些什么,他直接打断了话的后半截。黑暗里的人形靶子塌下去,一些黏糊糊的东西粘在手上。世界安静了。
他丢下他,独自趟过夜街。两岸的橱窗是黑色的镜面,左右倒影一路护送。他气走了徐富贵,打了张杰。至少,他还可以联系一下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