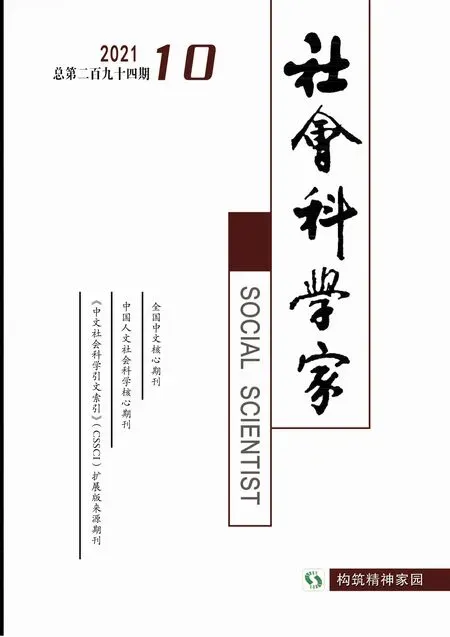中国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特征
——以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为例
鲍青青,钟 泓,谭燕瑜,王亚娟
(桂林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一、引言
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民与所处环境长期协作发展中形成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的知识和技术体系,以及独特的生态和文化景观的生态系统。它是一类特殊的遗产类型,是至今仍在使用、具有较强的生产与生态功能的农业生产系统[1],是农民生计保障和乡村发展的重要基础。文化景观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景观变化反映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对农业文化传承、农业功能拓展以及农业分布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景观仅限于美学价值分析,对遗产地景观的结构、功能和动态变化分析较少[2]。
农业遗产具有活态性、复合性和动态性等特点,采用“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保护原则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动态保护”是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实现“活态传承”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护措施,但是怎样在实施动态保护过程中处理“变与不变,变化程度”是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措施的关键[3]。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它是控制生物性状的本质,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呈现出来,具有物质性和信息性。文化景观基因是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不同传统聚落的景观和形态千变万化,实质是文化景观基因的差异。文化景观基因在文化的传播及复制过程中具有稳定性与灵活性,是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的DNA片段,只有抓住文化景观基因,才能有效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动态保护中,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景观基因理论已经在指导传统村落和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上做出了积极贡献。刘沛林等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提出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特征及旅游规划研究识别、传统村落文化基因识别以及非物质文化基因研究中[4-6]。王兴中等揭示了地域传统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研究[7]。翟洲燕运用地域文化遗传景观基因对古城和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进行了识别[8]。胡最等利用聚落景观基因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紫鹊界、上堡和联合梯田系统进行了文化景观特征识别[9]。以龙脊梯田为代表的稻作梯田农业系统是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地代表,研究稻作梯田农业系统的文化景观基因特征有利于科学评判农业文化遗产地蕴含的价值,对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推动产业兴旺、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二、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特征识别
(一)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概况
中国南方稻作梯田2018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包含福建尤溪联合梯田、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和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福建联合梯田位于尤溪县,自宋朝以来,联合村民使用木犁、锄头等工具开垦梯田,种植水稻,联合梯田通过山顶竹林截留、储存天然降水,再以溪流流入村庄和梯田,形成特有的“竹林-村庄-梯田-水流”山地农业体系。江西崇义客家梯田位于崇义县,始建于元朝,是一个非常“严密”“精致”“有序”的生态-经济-技术-社会复合大系统。从组成来看,是以“森林、竹林、村庄、梯田、水流”为主体组成的山地农业体系。湖南紫鹊界梯田位于新化县水车镇,起于先秦,盛于宋明,已有2000余年历史,最早为苗瑶祖先开创,是中国南方稻作文化和苗瑶山地渔猎文化交融糅合的历史遗存。
四大梯田都是中国南方典型的稻作梯田系统,在自然条件、农作物种植、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有共同的特点:一是梯田的相对高差较为接近,尤溪联合梯田为700m,龙脊梯田为880m,客家梯田为980m,紫鹊界梯田为836m[9],植被覆盖率高,梯田山上大都被竹林或竹林与阔叶林混杂的森林覆盖,涵养了梯田不可或缺的水源。二是田埂为“带子丘”和“青蛙一跳三块田”的碎田块,种植水稻,同时通过作物套种来获得充足的粮食。三是在地理环境上蕴含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紫鹊界地处孕育了苗、瑶等多个少数民族的大梅山地区腹地,形成了典型的“巫鬼文化”;龙脊地区居住着壮、瑶等多个民族,不同的民族呈现一种聚集而居的生存方式,各民族团结、和谐发展。上堡与联合地区都居住着大量的客家人,但上堡梯田是地处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客家社区”。
广西桂林龙胜龙脊梯田是国内较早开发旅游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之一,包括平安壮寨梯田、龙脊古壮寨梯田和金坑红瑶梯田三大部分,是目前旅游业发展最早最成熟的农业文化遗产地。龙脊梯田因山脉如龙的背脊而得名,是壮族和瑶族先民因势利导改造自然,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应用于山地的宝贵农业文化遗产,距今至少有2300多年的历史,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生产技术知识体系和确保系统稳定演进的村民治理方式,架构起了一种“上林下田、动态平衡”的梯田水土保持模式。
(二)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特征识别
1.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系统构成
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是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于一身的复合性遗产和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0],剖析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系统构成是识别其文化基因的前提。稻作梯田包含3个系统:一是稻作梯田生态系统。稻作梯田地理海拔高,生物多样性高,形成了“森林-村落-梯田-水系”的立体农业生态系统。二是稻作梯田生产系统。先民摸索和总结出适应山地种植的农产品品种、耕作模式、农具、水土资源管理等传统知识和技术等农业生产方式。三是稻作梯田生活系统。为适应山地自然环境及物质生产,人们在稻作梯田生产过程中衍生出传统习俗、宗教信仰、传统饮食及族群关系等梯田文化。
龙脊梯田系统及农业生产距今至少有230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生产技术知识体系和确保系统稳定演进的相关乡规民约,架构起了一种“上林下田、动态平衡”的梯田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模式。农业生态系统为稻作梯田生产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别具特色的地域少数民族文化,保存着以梯田农耕为代表的稻作文化,以“北壮”服饰为代表的服饰文化,以干栏式民居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碑刻和石板路为代表的石器文化,以铜鼓舞和弯歌为代表的歌舞文化,以寨老制度为代表的民族自治文化和以“龙脊四宝”为代表的饮食文化及各种节日风俗文化、宗教信仰文化等,它们与梯田一同构成了龙脊梯田独特而丰富的人文资源,是广西北部多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基于此,从稻作梯田生态系统、稻作梯田生产系统、稻作梯田生活系统三个视角可全面识别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基因特征。
2.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景观基因识别范畴及原则
识别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基因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典型性原则。拥有典型性的物质载体和景观,能反映农业生产或者自然环境,比如:稻作梯田独特的景观、耦耕劳作方式、吊脚楼建筑等。二是可复制性原则。农耕文化生产、生活方式表现出代际的可复制性,例如:耕作方式、语言、习俗、节庆的习得和传承。三是稳定性原则。农业生态系统表现出稳定性的特点,比如:稻作梯田立体生态系统是梯田农业生产生活的基础,梯田的森林涵养水源保证稻作梯田的水源灌溉。四是可变异性原则。随着外来文化的植入,稻作梯田文化因子会表征出可变异性,比如:居民的服饰变化、生计变化和生产生活变化[11]。因此从典型性、可复制性、稳定性和变异性四个方面识别稻作梯田农耕文化基因能全面把握文化基因的内涵。
3.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
构建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有助于深入分析与农业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要素的根本特征,进而界定最能表征农业文化遗产特色的文化景观基因[12]。在构建指标体系时遵守以下原则:一是全面性原则。农业文化遗产地是适应当地生态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形成的一种传统生产方式。因此,从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基因、生产基因和生活基因三个维度选择指标。二是典型性原则。指标遵循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识别的原则,同时要有能突出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农耕文化的特征,因此选取可以反映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特征的文化因子是构建指标体系的切入点。
依据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基因识别范畴和原则,将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划分为稻作生态基因、稻作生产基因和稻作生活基因3类,分别用稻作梯田生态环境特征、稻作梯田农耕特征和稻作梯田少数民族文化特征表征文化景观基因,选取了10个文化因子,构建了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基因识别指标体系(见图1)。

图1 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
4.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景观基因特征识别方法及过程
根据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的构成,综合运用特征解构法[13]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景观进行分层解构,从二维形态特征、三维形态特征、视觉与感知特征、空间结构特征四个角度解析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景观的形态特征[14]。从景观形态、结构特征及功能地位等文化特质诠释稻作农耕文化基因特征,并解释稻作梯田生态、生产及生活三者的关系,更好地为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保护提供理论指导和帮助,具体识别过程及方法(见图2)。

图2 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特征分析框架
本课题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进行第一手数据资料收集。课题组于2019年7月、2020年8月和11月三次共计12天对龙胜龙脊梯田的古壮寨、平安寨和大寨的村民、村干部、寨老和旅游经营业者进行深度访谈,共采访人员11名,录制访谈音频1600余分钟,同时,还对位于古壮寨的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进行了研究。综合访谈音频和博物馆的图片和文字信息,得到了龙脊梯田的村规民约、节庆习俗和族群关系等资料,对梯田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历程及变革有了深入的了解。
5.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景观基因特征识别结果
根据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特征的分析框架,从文化景观基因形态、文化景观基因结构特征和文化景观基因功能地位三个方面得出研究结果。
(1)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形态分析
按照农业文化遗产地景观类型[1],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属于典型的复合景观,从文化景观主体性层次来看,南方稻作梯田的景观形态由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的本底层、以农耕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层和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精神层共同构成稻作梯田聚落景观。龙脊稻作梯田农业生产以自然环境为基础,高山区为森林,低山区为梯田,村落坐落于中半山,便于稻田的深耕细作。龙脊村民修建了祭祀空间,通过各种祭祀活动规范人的行为,强化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同时呈现出人与自然互动过程表现出的多样性。
从空间景观形态上看,稻作梯田文化遗产地景观要素主要由山地自然景观、梯田文化景观、村落物质景观和村落非物质景观四大要素构成。山、水、森林、梯田、聚落依功能合理布局并组合形成自然和谐的景观,山、水、林、田是主要的自然生态元素,聚落、桥、亭、道路等是衍生出的民族物质文化元素,自上而下形成了“森林生态系统-梯田稻作系统-村寨聚落系统”的空间结构,形成了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龙脊壮族及瑶族先民选择稻作梯田农业为生计方式,在开挖梯田从事农业生产时,以神山和水源林的名义保护山顶的原始森林,在高山坑形盆地地貌上开垦的带状梯田,山间建有错落有致的村寨聚落,生态、生活和生产空间的布局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智慧。
(2)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结构特征分析
生态特征分析。南方稻作梯田山水林田寨格局构建体现了“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生态智慧。森林涵养、水利灌溉、耕作技艺是南方梯田稻作农耕系统的生命体系,南方稻作梯田生态智慧体现在对水源和土地的利用两个方面。水是田的命脉,“水”与“田”的关系是评判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15]。不同于平原的稻作灌溉方式,稻作梯田的灌溉方式自上而下,需要居民具有智慧和韧性[16],居民创造了独特的引水、分水和排水的梯田水利灌溉系统。
龙脊居民对于山体的利用充分考虑了自然条件,分为三段:山顶为森林,山腰建村寨,寨边及寨脚建梯田。山顶森林有利于水土保持、涵养水源,保证人畜用水和梯田灌溉。山腰气候温和,冬暖夏凉,适合居住。梯田分布于350-1100米,利于居民劳作,发展农业。森林-河流-村寨-梯田的布局结构实现了生态功能合理、自我调节能力强的养分循环,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复合农业特征。
生产特征分析。南方稻作梯田居民主要生计方式是稻作农业生产。稻作文化是龙脊文化的内核,也是当地民族文化的主体[17]。这一农业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壮族祖先的迁徙经历相关,受到壮族“那”文化生产的影响深远。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壮族和瑶族不断探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龙脊梯田农业生产技术知识体系和确保系统稳定演进的相关乡规民约。龙脊人民至今仍保留着一日三餐“饭稻羹鱼”的饮食传统习惯。喜食稻米、糯食,主要种植黏性糯谷类稻种,培育了同禾米、香糯、红糯、黑糯、青糯、白糯等龙脊特有的水稻品种。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祭祀祖先时糯食是当地不可缺少的代表性食物。由于梯田坡陡、田块狭小,便以人力代牛耕,龙脊地区保留着古老特色的耦耕耕作方式。遵循传统二十四节气的时令,形成了完备的二犁三耙的耕作技术体系、十二道农活(挖田、碎田、犁田、耙田、扶田基、播种、插秧、耘田、耘二道田、刷田坎、捉虫、收割)的种田方法、农耕用具、造田护田技术和农田灌溉系统,无不体现着梯田稻作的民族特色生产方式。龙脊的居住文化以壮族干栏建筑形式最为突出。干栏建筑一般分为三层,上层存放粮食及杂物,中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生存空间,既避免了人多地少、山地潮湿、猛兽侵害,也利于积累肥力、回还于稻田,保证了稻作农业生产生活的稳定。龙脊当地居民普遍具有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意识,逢年过节烧香供祭家族先祖,山林、田块、水潭、大树、凉亭等自然物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对其进行供奉守护,保留着壮族梯田农耕生产的烙印。龙脊梯田稻作文化已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与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北壮”服饰为代表的服饰文化,以壮族干栏式民居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碑刻和石板路为代表的壮寨石器文化,以铜鼓舞和弯歌为代表的歌舞文化,以寨老制度为代表的民族自治文化和以“龙脊四宝”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及节日风俗文化、宗教信仰文化等凸显了广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典型特征。
生活特征分析。稻作生活基因包含生活方式、村规民约和意识形态等要素。梯田生态环境、稻作文明及相关的文化习俗,塑造了壮族先民对大自然敬畏的天人观、豁达平和的人生观、恪守民约的道德观、勤俭务实的价值观,体现龙脊人民顺应自然、和谐共处、勤俭务实的族群特点。龙脊人赖以生存的梯田稻作的核心是水,分水与用水在当地被认为是众人利益均沾之事,为此巧妙设计“分水门”,形成了较为稳定、合理的分配灌溉使用方法,并记入“乡规民约”共同遵守维系。每年农闲时村寨中每家便自发派人集体修葺和维护水渠,世代传承很少会有用水纠纷。龙脊人在农忙时节或遇重大家庭活动时有换工的劳作互助习俗,守信、互助为换工的首要原则和契约,蕴含着梯田农耕社会务实互惠的社会秩序。“三鱼共首”是龙脊壮族地区的一个标志性图案,折射出族群之间守望相助的文化特质。
(3)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功能地位分析
人类与自然环境、社会之间不断调适,形成了人-地-文化的互相嵌套与循环共生关系。生产基因、生态基因与生活基因互利互哺、耦合均衡,共同促进了南方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支持功能。南方稻作梯田固有的多样性生物、森林植被、优质土壤、涵养水条件、山形地势等丰富的生态环境资源因子,满足了传统的糯稻生长所需的温度、水分、光照等自然条件,为把山岭开辟成梯田、依山建寨提供了依存环境和空间条件。山顶为林、山脚为河、山腰建寨、寨边造田的生态布局,形成了相互协调、相互平衡、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自然生态系统,为独具特色的梯田文化景观的产生提供了生态支持。龙脊壮族先民从河池、南丹一带迁徙而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壮族一直保持着“那生产”的族群习惯,这一族群习惯促使迁徙的龙脊先民恪守着稻作生产的本分,顺应自然、依山造田以达到自身的生理、行为和遗传的适应。生态环境因子为稻作生产提供了可能,同时壮族先民利用自身传统的稻作族群文化惯习改造、利用自然环境,创造了独特的梯田景观。
生计保障功能。以稻作为生产和生计方式使得稻作文化扩展到了高山地区,高山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又保障了先民原有的稻作生产活动,二者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并逐步衍生了独具特色的梯田生产系统和生计模式。龙脊的地理地貌使壮、瑶人民创造和发展了梯田空间格局,培育和保存了多种特色稻种,形成了相应的垦田护田、山林守护、水源分配、灌溉习俗、耕作方式等一套完整的农具文化、农业生产技术知识体系和耕作管理制度。农业生产因子又进一步稳固和保障了龙脊地区各族人民的生产持续和基本生计,从而使得龙脊梯田人民传统的生产生活得以延续。
村落治理功能。围绕着农业生产、农事活动、保护山林、水源的村规民约形成的生活基因调适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持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和生物多样化的保护,建构并维系着族群的人伦道德、行为观念、价值体系与社会秩序;同时也形成和维系了人与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合作互助关系,从而使梯田先民传统生计方式得到了保证,维护了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龙脊先民利用生态环境,发展梯田稻作农业生产,维持农业生计活动,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形成了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善待自然的理念与思想,演变、延伸出了以梯田稻作生活为核心的农耕文化生活空间,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饮食、居住、服饰、仪式、祭祀、礼仪、节日习俗和信仰等文化生态链。
三、结论和讨论
稻作梯田是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的一种类型,是我国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的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它蕴含着适应环境、改造环境、探索生产生活的智慧。把文化景观基因理论引入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特征分析,对正确理解遗产地“三生”空间结构和功能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基于文化景观基因的系统的内涵和构成界定了识别范畴及原则,并借鉴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方法,构建了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特征识别的分析框架;二是对南方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基因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深入解读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的特征,对于正确认识这一生产方式的文化、经济和生态都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有利于唤醒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促进乡村文化复兴。
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特征研究为未来深入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保护和传承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今后,在结合GIS等技术手段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农耕文化基因链的演变规律、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应用地理信息图谱方法,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信息数据库,识别遗产地文化传承的关键基因,绘制农业文化遗产地基因组图谱需要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拓展研究深度和广度。通过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景观基因的研究将有效促进人们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内涵和价值的认识,从而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