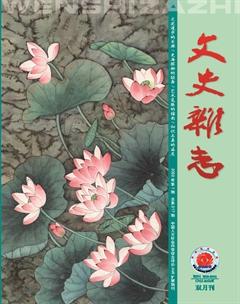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河南”称谓的移易迁变
王俊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南”相关称谓使用广泛,呈现指代不一、多元并存的格局。“河南”称谓移易迁变的内在逻辑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南”各有所属,随着乱世结束,侨立的河南郡之“河南”被历史所淘汰,黄河上游的“河南”伴随区域政权的兴衰沉浮而归于沉寂,新的大一统王朝置郡县,变羁縻之地为直接控制区的釜底抽薪之举,客观上保证了境内称谓在区分识别度上的唯一性,使得中下游的“河南”专名化,成为“河南”称谓的中心。
关键词:
“河南”;地域范围;移易迁变;多元并存
引言
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地名,演化内涵丰富的“河南”一词,为学界所重视。[1]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关于“河南”地域范围变迁的探讨和研究,在时段上相对集中在先秦秦汉、唐宋及以后时期,研究内容和重点多在政区沿革及“河南地”;概念方面,魏晋南北朝作为“河南”由地域称谓逐渐向政区名称转变的关键时期,成果单弱:崔建华意识到秦汉以后河南政区的核心始终在今洛阳、郑州一带,[1]然未予深究;卫丽对魏晋北朝的河南尹辖区做了考察;[2]朱叶俊界定北朝的河南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河南中西部地区;[3]王兴亚认为:“地名河南是一个多义词,既是地域名称,又是行政区划县、郡、府、路、道、省的名称”[4];且关注的视野常局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对“河南”称谓及地域范围的移易迁变缺乏动态考察,对其嬗变的内在逻辑缺乏深入探讨,对其同名异地的状况缺乏系统考察,仍有拾遗补缺的必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带“河南”二字的称谓有“河南”“河南国”“河南地”“河南宫”“河南尹”“河南郡”等,它们所指代的地域范围不一。笔者拟从西向东,分别对其进行逐一考察以厘清其间的联系与区别和移易变迁的动因。
一、吐谷浑部河南国之河南
吐谷浑部族是源自鲜卑慕容氏的分支:“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5],“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6]。吐谷浑之“河南”,因部族处黄河之南而得名,“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7]。南朝刘宋时:“陇西吐谷浑慕容延改封河南王”[8],这是文献记载得名之始。拾寅“又受刘义隆封爵,号河南王”[9]。萧齐时,高帝(萧道成)于建元元年(公元479年)五月“进河南王吐谷浑拾寅号骠骑大将军”[10],建元三年“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浑度易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11];武帝(萧赜)于永明八年(公元490年)八月“以河南王世子休留代为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12]。
吐谷浑王国在南朝话语体系中常被称为“河南国”或“河南”,不仅体现在南朝授予吐谷浑部族爵位名号上,还表现在吐谷浑部族向南朝遣使、朝贺、贡献方物等活动上。刘宋时,河南国多次遣使献方物,《宋书》对此有记载;“宋世遣武卫将军王世武使河南”[13]。萧齐时,“河南王吐谷浑拾寅奉表贡献”[14],萧道成即位改元后,“河南国遣使朝贺”[15]。萧梁时,“河南国献舞马”“而河南又献赤龙驹”,[16]“其世子又遣使献白龙驹于皇太子”[17]。从有关南朝与吐谷浑双方频繁互动的记录中,可知该国辖境在南北朝时常被称为河南国或河南。
浇河郡辖境曾被称作“河南地”。凉州及其周边地区受其地缘环境影响在南北朝时期成为各方军事斗争频仍、激烈的核心地区之一,浇河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地区。浇河初在吐谷浑境内,后分别为后凉、南凉所属,“降光乐都、湟河、浇河三郡”[18],“南凉秃发乌孤又以河南地为浇河郡”[19]。此“河南地”指的就是南凉所置的浇河郡辖境,而浇河城在今青海贵德县境,处黄河南岸。浇河郡辖境相当今青海省贵德、化隆一带。几经争夺,此河南地即浇河郡終又重新回到吐谷浑境内,“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浑阿豺为安西将军、浇河公,即此城也”[20]。此后,北魏与吐谷浑也曾争夺过该地,北魏曹安“昔为浇河戍将”,吐谷浑“拾寅部落大饥,屡寇浇河”。[21]

关于河南国之河南的地域范围,由于不同时期,其势力强弱起伏波动,导致其疆界盈缩不定,文献记载不一。从其得名原因可知该“河南”起初是指其所据有的今青海省黄河以南地区,即河湟谷地,后疆土虽然扩展,仍以“河南”为号。《宋书》对该国西境沙州的记载为:“其国西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为号”[22]。《梁书》:“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23]叠川在今甘肃迭部县东南,于阗在今新疆和田县西南,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通秦岭泛指今青海西倾山东北至洮水通向秦岭一带。《册府元龟》对吐谷浑部族控制区有描述:“吐谷浑晋时据有西零巴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都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其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24]《南齐书·河南传》介绍了河南国四个重要的核心地区及河南国的南界:“河南国在益州西北亘数千里,其南界龙涸城去成都千余里,(犬戎有田)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直川,皆子弟所治”[25]。由上所述可知,吐谷浑虽以“河南”为号,然随着其部族的发展壮大,其活动空间和控制区域也随之拓展,以致该“河南”地域范围方圆千余里,远远超出了使其得名的今青海省黄河以南地区。
慕容吐谷浑部族王国建立于公元313年,其灭亡于663年。“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26]。吐谷浑国祚绵延了300多年,南朝宋以后将其境称为河南国或河南,该河南称谓沿用至隋初,其后未见以“河南”称之。隋代,尚有封吐谷浑河南王事:吐谷浑寇凉州为隋所败,“上以其高宁王移兹裒素得众心,拜大将军,封河南王,以统降众”;“是岁,河南王移兹裒死,文帝令其弟树归袭统其众”。[27]
二、金城、陇西之河南
此“河南”是指今甘肃省黄河以南地区。东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前凉张骏“复收河南之地”[28],东晋咸和初“骏遂失河南之地”,“骏因长安乱,复收河南地”。[29]张骏所失和收复的河南地,即“金城治大河南,所属半在河北,自金城而南,东则陇西,西则狄道,皆为河南地”[30]。这个“河南地”也是后来乞伏部所据的河南地区。
十六国时期鲜卑乞伏部,乞伏乾归据有金城、陇西地区,于公元388年自称河南王。《晋书》《魏书》《十六国春秋》对此事均有记载。“乞伏国仁死,弟乾归嗣伪位,僭号河南王。”[31]“是岁,乞伏国仁死,弟乾归立,私署河南王。”[32]“仁薨,群寮以仁子公府幼稚,乃立乾归为将军、大单于、河南王。大赦,改四年为太初元年。”[33]以上几种说法,虽略有不同,但乞伏乾归称河南王的史实是清楚的。“以太元十九年,十二月,僭称秦王。”[34]东晋太元十九年即公元394年,这期间(公元388—394年)是河南国时期。名爵封号固然源于现实地理状况,但受不受封号,称什么王却颇有一番考究与取舍。鲜卑乞伏部称河南或秦,与其实力和当时的地缘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秦存在甚至强大时,称河南王,意在强调或确认割据一方的既有事实,以凸显其相对独立的地位。根据形势需要,乞伏乾归先后接受过苻登河南王及姚兴都督河南诸军事、河南王的封号,乞伏炽磐也袭称过河南王的名号。招降纳叛是拓展壮大部族的有效方式,“南羌独如率众七千降之”,“于是秦、涼、鲜卑、羌、胡多附乾归”。[35]秦衰亡之时则复称秦王,可能意在分享前秦的政治遗产,于灭前秦杨定及苻崇的次年,称秦王。虽然这个部族王国,史称西秦,但不可否认的是,称其为河南国或河南也是符合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历史事实的。鲜卑乞伏部立足于今甘肃黄河南部区域,其活动地域可谓处于“河南”周围;加之虽然持续时间不长,时有中断地接受河南王封号或自称河南王的名号,使之以河南国或河南代称其境,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印记。西秦崇尚佛教,译经活动盛行,“右一十四经合二十一卷,晋孝武世沙门圣坚于河南国为乞伏乾归译”[36],“西秦乞伏国仁世法坚于河南译太子慕魄经五纸”[37]等记载,可以表明西秦国境曾被称为河南国或河南的事实是存在的。因此,虽然“西秦”在后世的史书中使用得更多,以别于前后秦,但回到该时期来看,曾以“河南国”或“河南”作为称谓也应是事实。

而对于这个“河南”的地域范围,可参照乞伏部河南国即西秦国的疆域范围:“置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漒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十二郡,筑勇士城以居之。”[38]乞伏乾归平灭仇池杨定部后,“于是尽有陇西、巴西之地”[39]。“西秦兴盛时期,所辖面积从甘肃武威到天水、陇南以及青海东部,共十一州、三十郡、四十八县、一护军、一城。”[40]虽然,西秦的疆域变迁频仍、盈缩不一,但其核心疆土如苑川、陇西、南安等始终在黄河以南区域,称其为河南国或河南也可谓名副其实。
三、河南宫之河南
河南宫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登国六年所建行宫。大破匈奴刘卫辰部,“自河已南,诸部悉平”,“是岁,起河南宫”。[41]北魏皇帝多次巡幸此地。“遂建此宫于悦跋城(代来城)。位于今内蒙古尹金霍洛旗西北。”[42]河南宫所在“大约是今准格尔旗沙圪堵镇南5公里的石籽(子)湾古城”[43]。河南宫所在也是属于河套地区,即是秦汉“河南地”所在。
四、狭义的河南尹之河南
河南尹的辖区,主要在今洛阳、郑州一带,虽然南北朝时,政局变动频仍,不同时期,盈缩不同,辖地大小不一,但其核心区域基本稳定。《三国志·魏书》:“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44],此河南地当为河南尹地区,“辖境相当今河南黄河以南洛水、伊水下游,北汝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以北原阳县地”[45]。“武牢、成皋皆河南地也”,“每有克获,修武、温城、河南地也”。[46]此“河南地”即是洛阳周边的河南尹地区,是周、齐争夺的重点地区。
五、广义的黄河、淮河间的河南
广义的“河南”涵盖地域范围很广,泛指的核心区域在黄河中下游洛阳、虎牢、碻磝、滑台一线的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广大地区,但并不仅仅局限于黄河南岸。由侯景附梁时所上降表[47]可知其所控制的河南之地,北起黄河,南抵梁境,西起函谷,东至大海。“河南九州三十镇,一时俱下”,“寻即除洛怀等九州诸军事、河阳总管”。[48]由此可见,该“河南”不仅仅在黄河之南,而是地域甚大的广义河南地区。广义的河南地区,是典型的四战之地,是南北方反复争夺和交战的地区:“宋景平初,失河南地”[49],“会江南使还,称刘义隆欲犯河南,谓行人曰汝疾还告魏主,归我河南地即当罢兵”[50]。
六、侨立河南郡之河南
南北朝时,侨立州郡曾盛行一时。南朝失河南之地,相继侨立州郡,然治所迁徙变更频繁。东晋侨置河南郡,属雍州,寄治襄阳(今湖北襄阳市汉水南襄阳城),“侨立,始治襄阳,孝武大明中,分沔北为境”[51]。西魏时治所在安养县(今湖北襄阳市樊城北),隋开皇初废。南朝宋侨置,治所在河南侨县 (今河南新野县东北),北魏废。西魏大统中侨置,治所在大坞城 (今河南渑池县北十五里),其后治所迁徙频繁,北周大象中废。北河南郡,东晋及宋先后侨立,北魏废。“晋孝武太原十年立北河南郡,后省”,“明帝泰始末复立”,“寄治宛中”, 领新蔡、汝阴、苞信、上蔡、固始、缑氏、新安、洛阳八县。[52]《南齐书》雍州条下有河南郡:“河南、新城、棘阳、河阴”;北河南郡:“新蔡、汝阴、上蔡、缑氏、洛阳、新安、固始、苞信”。[53]
结语
在先秦秦汉与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时局变换频仍,政权兴灭无常,“河南”相关称谓在该时期依然被广泛使用,呈现指代不一,多元并存的格局,是“河南”称谓从同名异地走向专一化的关键过渡期。隋唐以后,“河南”称谓指代的地域范围虽有盈缩变迁,然逐步专一化是其趋势所在。多元的“河南”称谓在历史进程中逐步被淘汰,趋于专名化。溯本追源,方能弄清其所指地域范围移易迁变的历史逻辑。
黄河上游的河湟谷地和金城、陇西之地俱在黄河之南,是鲜卑乞伏部和吐谷浑活动的重要地区。虽然后来部族发展壮大后,其控制区远远超出其固有的河南之地;但随着控制区的扩大,新的“河南”所指的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化。在鲜卑乞伏部消亡之后,吐谷浑部曾接收了一些败亡政权的遗部:“慕璝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部落转盛”,“乞佛日连,窟略寒、张华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愍,愿并敕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54]河南王的名号被南朝用来册封鲜卑吐谷浑部,于是河南国也随之转移,“河南”这个称谓所指即从金城、陇西之河南转移到吐谷浑部河南国之河南。
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南”称谓,指代不一,多元并存:泛指黄淮间地区的广义“河南”;指代今洛阳、郑州一带的河南尹之狭义的“河南”;指河套朔方地区的“河南宫”之“河南”;鲜卑乞伏部所据的金城、陇西之“河南”;吐谷浑部河南国之“河南”以及迁徙不定的侨立河南郡之“河南”。虽然这些“河南”的全称有所不同,或是“河南国”,或是“河南地”,或是“河南宫”,或是“河南尹”、“河南郡”甚至是以“河南”代称,但是却能看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南”称谓的应用相当普遍。其在运用中并无严格的区分,这或许恰恰是因为根据语境和说话对象,不论是带政区通名的“河南”,还是以“河南地”代称的“河南”,甚至是最为至简的“河南”,皆不会存在混淆和误读的情况。总之,“河南”的内涵与外延为使用者所共知。
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变幻剧烈,政权兴亡无常,“河南”称谓所指的具体地域范围与时盈缩嬗变,各有所属,但几个“河南”的中心指代区域保持大体稳定。除了侨立的“河南”,其他“河南”处于黄河流域的几个得天独厚之地,也免不了受其地缘环境影响成为各方军事斗争频仍、激烈的核心地区。侨立的“河南”,既是南朝管理失去土地的南下民众的政区,是因时应变之举;也是对失地念念不忘的政治宣示,是乔迁士族与民众精神家园的显化。这从元嘉北伐對“河南地”矢志不渝的渴求上可以窥见失地情结的强烈。
相对于洛阳、郑州一带的狭义“河南”和黄淮间泛指的广义河南,侨立的河南郡之“河南”,随着魏晋南北朝这个400余年大乱世的结束,也被历史所淘汰。吐谷浑部河南国之“河南”、乞伏部金城—陇西之“河南”、河套地区之“河南宫”均处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界的地区,也是军事活动频发、政治势力角逐的前沿地区,历来被视为边缘地区。随着吐谷浑河南国、西秦及北魏这几个区域性政权的兴衰沉浮,其“河南”之名,也慢慢归于沉寂。由此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所指的地域范围逐步专名化,成为“河南”称谓的中心,其变化不过是在指代地域上盈缩而已。
特别是随着汉地新的大一统王朝的出现、新的统一的政治中心的形成,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足以击败上述游牧民族,使其割据一方成为泡影时,自会把以往处于农耕和游牧分界线附近的羁縻之地变成直接控制的辖区。隋炀帝时在击败吐谷浑后曾采用画地为牢、分而治之的政策,直接设置郡县:“伏云遁逃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55]隋炀帝之策可谓釜底抽薪之举,确实把握到了游牧民族的命门所在,也在客观上保证了境内称谓在区分识别度上的唯一性。这大概也是在此之后黄河上游“河南”称谓消失的原因之一。加之唐宋以后政治中心东移、经济重心南移,中原之“河南”越叫越响,西北之“河南”在慢慢淡出人们视野后逐渐鲜为人知。这大概就是“河南”称谓地域范围移易迁变的内在逻辑所在。
注释:
[1]崔建华:《先秦秦汉时期的“河南”地域称谓》,《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第2期。
[2]卫丽:《魏晋北朝河南尹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16页。
[3]朱叶俊:《两魏周齐河南之争》,南京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7页。
[4]王兴亚:《中原地域称谓的由来及其地域范围的嬗变》,《石家庄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七《四夷·西戎·吐谷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37页。
[6][7](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诸夷·西北诸戎》,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0页,第810页。
[8][22][51][52](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6页,第2373页,第1140页,第1143—1144页。
[9][21][32][41][50][54](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37页,第2238页,第22页,第24页,第2293页,第2235—2236页。
[10][11][13][14][25][49][53](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3页,第36页,第1026页,第33—34页,第1025—1027页,第278页,第283—284页。
[12][15](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3页,第110页。
[16][17][23][47](唐)姚思廉:《梁书》第475—476页,第811页,第810页,第834—835页。
[18](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二十六《秃发乌孤》,第3142页。
[19][38](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2页,第422页。
[20](北魏)酈道元著,谭属春、陈爱平点校《水经注》卷二《河水》,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3页。
[24](北宋)王钦若等筹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274页。
[2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吐谷浑》,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01页。
[27][55](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87—3188页,第3189页。
[28][29](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六《张轨·寔子骏》,第2234页,第2238页。
[30](唐)房玄龄等:《晋书斠注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24页上栏。
[3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孝武帝》,第237页。
[33](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之《西秦录·乞伏乾归》,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页。
[34](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十六《西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7页。
[35][39](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二十五《乞伏乾归》,第3116页,第3117页。
[36](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九,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130页下栏。
[37](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六,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478页上栏。
[40]张文玲、燕鸣:《建都榆中的西秦国》,政协榆中县委员会学习宣传文史资料委员会:《榆中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榆中纪事》,1990年,第8页。
[42]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页。
[43]鲍桐:《北魏北疆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的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
[44](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页。
[45]张舜徽主编《三国志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页。
[46](北周)庾信:《庾子山集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90、794页。
[48](唐)令狐德棻等:《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525页。
作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