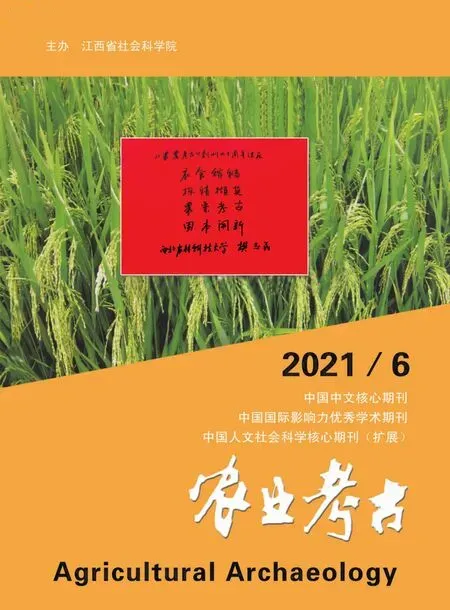明代军粮概论*
刘 佩
在中国古代,军粮长期作为士兵打仗时的必备物资。早在战国时代,秦军就已食用一种以粟米和小麦面粉制成的“锅盔”饼,这种饼厚实、便携且管饱,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充足的后勤补给。三国时,东吴广泛种植水稻,使大米成为主要军粮。唐宋以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麦稻各占军粮的半壁江山,粟米地位下降,不再是军粮主料。元朝是游牧民族政权,因此风干肉和奶制品成为军粮首选,其特点是迅捷、方便,能够快速补充热量。至明代,军粮品种增多,制作也已达到较高水平。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军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军屯、运输和仓储方面,而对军粮的具体生产过程和种类关注较少。故本文试从明代军粮的制作、军粮的发放标准以及将士墓中的军粮留存这三个方面,对明代军粮进行相关阐述。
一、明代军粮的制作
军粮为士兵行军打仗所用,因此便携和储存是制作军粮时首先考虑到的问题。明《武备志》载:“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炊,师不宿饱。况深入敌境,飞挽不通;袭师及敌,益资拟备。虽云困粮于敌,亦虞清野以待。”[1](卷九七,P3772-3773)军队作战时一般携带干粮,有利于保持战斗力与士气。下面具体分析明代制作军粮的原料和种类。
(一)军粮的原料
明代军粮使用大米作为主要原料。据《天工开物》所载:“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而犹系之谷者,从其朔也。”[2](卷上,P1)大米在日常所食中已占七成,且口感要好于小米,军士们亦逐渐抛弃小米,改食大米。不过,迫于人口压力,明代的粮食生产出现了重产量轻质量的局面。高质量的稻米口感虽好,但产量较低,“香稻一种,取其芳气以供贵人,收实甚少,滋益全无,不足尚也”[2](卷上,P2)。劣质但高产的水稻品种更能满足数量众多的士兵所需。
除水稻外,小麦也是明代军粮中的另一原料。宋时,江西抚州的百姓“厌贱麦饭,以为粗粝,既不肯吃,遂不肯种”[3](卷七八,P809)。随着品种的不断改进,宋以后,“南稻北麦”的粮食格局渐趋固定[4](P63),北方广种小麦。至明代,小麦逐渐成为军粮。用小麦制作的面饼易于保存,若不淘洗可储存数年,适合作为应急军粮,随身携带也较为方便。
此外,军粮内的副食品也是由多种原料制作而成。如豆豉、大酱等类,其以黄豆为原料,加入较多的盐后混合,捣碎晒干,这给将士提供了充足的盐分,以保持体力,从而避免无力作战。
(二)军粮的种类
原料充足,使明军制作的军粮种类也逐渐丰富。首先在主食方面,关于小麦的使用,《武备志》中载有:“取小麦面作蒸饼一枚,浸醋一升,曝干,以醋尽为度。食时每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1](卷九七,P3774)小麦做的蒸饼浸泡在醋中,增加了军粮的味道,晒干后便于携带,一人可食用50天,适合作战时的长途奔袭。抗倭名将戚继光在长期抗倭斗争中曾总结出一些军粮制作经验。他将小麦磨成粉,加上盐、碱、水,揉团搓成条状,压扁后烘制成圆形饼,并称之为“光饼”。这种饼直径约5厘米,厚约2厘米,饼中间留有一孔,以便士兵成串挂于脖上,随时可吃,较为方便。《闽杂记》中即有载:“今闽中各处皆有(光饼),大如番钱,中开一孔,可以绳贯。”[5](卷十,P155)因烘烤得法,光饼有着便于携带、存放时间长、富含营养的优点,即便在潮湿的南方三五天也不会坏,故深受广大官兵喜爱。民间也依据这种做法制作光饼。清人陆以湉的《冷庐杂识》记有:“吾浙市肆所售光饼,以戚少保继光兵间遗制得名。瑞安项雁湖文学霁以为宜避保之名,改称‘戚公饼’,作诗纪之。有云:‘孔类缗钱形,啖解连环结。携来肉串县,穿作鱼贯密。’”[6](卷一,P40)时至今日,光饼依然在福建沿海等地流行,且品种较多,颇为有名。
对于大米军粮的制作,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中亦有详细记载:“常日每一名,各将米二升炒黄包裹,一升研为细末,一升另包。麦面二升,一升用香油作煤,一升蒸熟。六合用好烧酒浸,晒干,再浸,以不入为度,晒研为面,另包。四合用盐醋晒浸,亦以不入为度,晒研为末,另包。行军之际,非被贼围困至紧,不许用。出兵随行忘带者,如失军器同。”[7](卷五,P53)戚继光要求部下出征时除辎重粮草外,还要携带四升炒米和炒面。大米炒熟后经过反复浸晒,能够长期保存;炒面所加香油、醋、盐等用于改善口味。军粮包裹好后写上本人姓名,人手必备。这里制作的军粮乃是应急军粮,并不是日常行军所食,非被敌围困的关键时刻不许打开食用。
其次,若战事突发或军情紧急,军士一般会将各种主食混合制成军粮。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率军北征蒙古,由于烧火不便,朱棣便准许“各军沿途炒面……每军关与小麦三斗”[8](卷一八八,P3824-3825)。炒面一般是士兵临时驻扎后所做军粮,他们将小麦、大麦、青稞等农作物磨成粉,加入盐,在铁锅中翻炒至金黄,然后边吃边装入包裹中,有时需要用水掺在一块,不然会被噎住。官方也会将营养丰富的炒面赏赐给将士。景泰四年(1453)正月“右都督杨俊奏:臣等统领官军八千赴宣府等处巡哨,乞敕兵部全关与军器、炒面赏赐”[8](卷二二五,P4902)。民间习得炒面之法,并加以改进。明人撰写的《养生类要》中记录了“开胃炒面歌”,配方是“二两白盐四两姜,五斤炒面二茴香”[9](P136)。若想调味,还可以“半斤杏仁和面炒”。
在南方,有一种制作复杂的吃食,称为“饵”,它是由粳稻米蒸熟后,舂制而成的圆、薄小块饼状食物。饵的品种众多,《酉阳杂俎》 记载:“餘幸罢、肛宰、餘寮,饵也。”[10](卷七,P41)最初是一种类似于干粮的食物。由于饵须用粳稻米制作,因此北方并无生产,南方由于宋以后稻米品种的丰富,百姓对干粮的需求减少,饵类也逐渐消失匿迹。然而,饵在军队中仍长期作为干粮,尤其是在南方将士眼中,它不可或缺。因为饵块一类食物既能很好地保持稻米的口感与筋道,又耐饥,且便于携带,十分适宜行军的需要。古人云:“饵,筋腱也”[11](卷三八,P1153),“饵之言坚洁若玉饵也”[12](P240)。明代,沐英在率军征云南的过程中将饵食带入云南。军士们戍守边疆,在此地建立军屯,他们也就把吃饵的习俗保留在了云南,并广为流传。据明代《云南图经志书》所述:“州中土人,凡遇时节往来,以白粳米炊为软饭,杵之为饼,折而捻之,若半月然,盛以瓦盘,致馈亲厚,以为礼之至重。”[13](P174)景泰时滇人已有互赠饵块的习俗。
最后,副食品在明代军粮中也很普遍。明代军粮中副食品的种类较多,这里仅列举数例加以阐述。明代军中会生产一种醋布,这种布“粗布一尺,以一升酽醋浸曝干,以醋尽为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1](卷九七,P3774)。有时还会和盐融合在一起,“盐三升,以水和入锅中,火烧之,即坚小不化,一人可食五十日,又宜于夏日远行”[1](卷九七,P3773-3774)。士兵外出打仗时会随身携带一片,吃饭时剪下一小片和主食一块煮熟,味道可口。
肉类在军中较少食用,除非因作战犒赏或军中无粮被迫杀畜充饥时才有机会享用。军队长途行进时,难免会遇到粮草不足的情况,“若班师在道,去境犹远,储贮乏绝,即须选择羸瘦牛马应卒,以充军食,庶全人力,不致为贼困逼”[1](卷九七,P3773)。粮绝时,先吃瘦弱的牛马,据估算“牛一头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马一头亦如之。驴一头食之,三十人可一日”[1](卷九七,P3774-3775)。军士们迫于无奈方才杀马吃肉,这时的战场情况已十分危急。亦有犒赏吃肉的时候。明成祖北征时,曾下令将光禄寺和尚膳监携带的米面、 腊味分赐给军中将士:永乐八年(1410),帝“说与总兵官清远侯王友、内官张泰、朱不花:但是尚膳监及光禄寺所有米面腊味枣子并一应物料,尽数给散与无粮军士食用,酒与沙糖盐酱椒不必给散”[14](卷八八,P1685)。此外,还下令“军中所有牛羊,不问是朝廷者、是官员军民人等者,尽数拘收,将作粮食,接济军士。但有隐匿私自宰杀不将入官者,治以重罪”[14](卷八八,P1685)。当然,这种军粮影响下的饮食习惯,也日益影响到当地百姓的饮食文化。宁夏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当地百姓的食物深受军事影响,他们爱吃的锅盔、炒面、手抓羊肉、烩菜等大多为军旅文化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军粮中用于药用的食品也日益增多。明军内有一种治疗疟疾的食方,“治疟疾初发用藿香正气散一二服、二三发后用鬼哭丹截之。黑豆四百九十粒,绿豆四百九十粒,雄黄二两五钱,信石二两,右为末,蒸饼为丸,如芡实大。每服一丸,冷水下,忌热饮食一日”[1](卷一四五,P5859),其中黑豆、绿豆等皆为行军常备副食,治疗军士疾病亦不在话下。
二、明代军粮的发放标准
明代卫所军士的口粮发放分为两部分:一是月粮,即按月发放固定粮食;二是行粮,主要在军兵外出执行任务时发放,其数额依照任务难度、距离的不同有所区别。月粮发放时间不固定,数额上大致分为“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15](卷八二,P2004)。同时发放的还有食盐,正常标准是“有家口者二斤,无者一斤”[15](卷八二,P2004)。然而,随着明朝国力下降、军队腐败之风盛行,军卒的口粮多有克扣。明人业春及有载,明初军队总额“国初置卫四百九十一,所二百一十一,以军计之约三百一十一余万”[16](卷三六六,P3955)。依据吴晗先生的研究: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军数超过120万,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后的军数达到了180万以上;成祖以后约有280万人左右[17](P101)。军员总数的庞大,使口粮发放严重不足。宣德十年(1435)中都留守司上奏:“近例,旗军月米一石止给六斗或四斗,余皆折钞。今怀远诸卫连年亢旱,缺食者多,请仍全支……暂从所请……后辽东、 江西诸卫亦有是请,皆暂从之。”[8](卷三,P63)月粮削减已成定局,折钞发放已是于事无补。
月粮无需做过多介绍,这里着重分析行粮的发放数量。明朝建立之初,沿用了两宋时期的口粮发放惯例,以每人50天的行军时间来分配军粮,并令军士提前携带3天口粮,保证供应充足。明军外出作战,起初多不带干粮,“今出征既不以车从,一切全不料理。在道,恣其抢掠居民;止营,任其侵渔地主。苟且若此,免于败亡幸矣,欲其成功得乎?故未及屯兵,先积粮草,欲积粮草,先觅道路,欲通道路,先卫车从。常使粮草多于人马,则早暮无忧。今脱粟无盐,尚且缺然不饱,而欲鼓其忠义之气,养其超投之勇,得乎?是故王政一无可苟,而行军尤不可苟”[18](卷八,P284),结果多数军卒在饥饿时或寄食旅店,或索取于民家,使明军作战常常陷于被动。受此教训,戚继光在浙江抗倭时,提出了“必队设火头,行锅负之以随军;身带干粮,赍裹备之以炊爨”[7](卷首,P4)的办法,解决了部队行军时的做饭问题。隆庆元年(1567),戚继光奉命前往蓟州任总兵官,加强本地防务和训练。其间,他创设辎重营,分设三营,后增至六营,“每营车八十辆,每辆载米二石五斗,棋炒三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载米三百石、棋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19](卷六,P342)。估算下来,“每车载米豆棋炒一十二石五斗,每营可供一万人马三日食。各于出门之日,再自带干粮二三日,计掳出入,日足用矣”[19](卷六,P342)。戚继光的辎重营,每次载重可供一万人马三日之食。每位士兵出征时另自带3天干粮,这样方可做到做到“师行常饱,而敌忾不销”[19](卷六,P342)。蓟州作为军事重镇,主要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因此辎重车仅供短途行军,不足大军50天所食,若遭入侵也不恋战,有利于保存实力,亦达到了防守的战略目的。
《实政录》中记有大军一日军粮所需:“行师以养力为先,养力以足食为要。大率每军一日用米一升,蒸饼十个,兵一万,日用米一百石,蒸饼银一百两。马一匹,日用草十斤,料豆三升,万匹用草十万斤、料豆三百石。”[18](卷八,P284)军粮耗费如此巨大,故前期借宿而食的行为并不得民心。此后,明代大规模屯田填补了军队日常所需,使军粮的原料补给充足,对百姓的掠夺亦有所减少。
三、明代的军粮随葬品
军士常年在外戍守边疆和征战沙场,所发军粮并不能满足他们的口味需求。一些将士牺牲后,家族为祈求其死后能够享用美食,便在墓葬中放入谷物。下面将分析随葬品中的军粮和盛放容器。
一是关于墓中存放粮食的容器。谷仓罐是存放随葬谷物的重要工具,在一些等级较高的将军墓中会有出土。明昭勇将军王俊之墓曾出土了6件谷仓罐,均为瓷制[20]。葬于南昌的明代昭勇将军戴贤夫妇的合葬墓中,出土了9件刷金谷仓[21],这些谷仓内并无存粮,但装饰华丽,展现出墓主人身份的不凡(见图1)。1988年,在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垅坪乡的明代百户张荃诰墓中,考古队出土了2件存谷器物,形状大小相同,口径大约8厘米,底径约9.2厘米(见图2)[22]。相较于将军墓,该武官的随葬粮具略显寒酸。
二是关于器具中存放的粮食。王俊之墓中的6个谷仓罐,有3个存有粮食,其中2个放有粟子、1个放有糜子[20],但皆已腐烂。张荃诰墓中的2个陶罐,其中1个存有稻谷,已无米粒,仅剩谷壳,保存较为完好。这些武官死后,其墓中存放着作战时的军粮主食,寄托了家人对他们死后依然足食的美好意愿。而有谷物随葬的墓,无论是否使用谷仓罐盛放粮食,墓主人身份都要较普通百姓高,目前尚无发现平民墓中有谷物随葬现象[23]。
四、结语
明代军粮承自宋代,但又有发展和创新。明朝改变了过去小米独占军队主食的局面,小麦和水稻的大规模种植给军粮制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军粮的副食品种增多,肉食虽不常吃但供给增加;将领们总结经验并设辎重车营,使外出作战时的准备更加充分;军粮对边疆地区的影响更大,一些边境市镇受其影响制作并食用军粮;军粮的药用价值也更加凸显;武官墓葬中的谷仓罐充当食罐、象征着军人的食物,谷仓罐亦成为身份象征的随葬品。
军队作战的紧迫性和隐蔽性决定了制作军粮时不易生火做饭。将士外出时多携带干粮,加之行军时机动性较强,因此很难吃上可口的食物。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改进后,明代军粮依然是我国古代简易食品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对明军的外出作战影响深远,亦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战局,故明代军粮的发展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