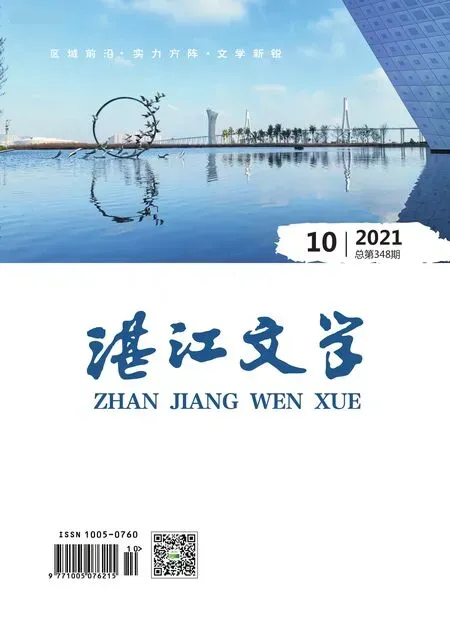手 帕
朱盈旭
手帕子,初遇在《红楼梦》。
少年时看电视剧《红楼梦》,大观园的女孩儿,个个有手帕,隔着屏都能感觉到它们轻柔薄滑,如一团软风。
红楼梦里女孩儿们的手帕子,素日里,或白笋般的指尖挑着,掩面低眉含羞笑;或玉手里拎着曳曳走,细腰处一点妩媚春风摇,她们是早春里的绿柳条;或红嫣淡绿地握在掌心里,恰使一颗女儿心,像被白月亮舔了一口的梨花瓣,水润润的凉软。
她们就是又美又软的手帕子。
手帕子,是爱情的香信物,大多是这样的身份。
手帕子,它的人间模样,跟扇子一样,是很私密的东西。
但比起扇子来,手帕不仅仅限于贵族女子,它很亲民,几乎所有的女子都有自己的手帕子,连宝玉的奶妈李奶奶都有。她的可能是用来擦鼻涕的吧。
还是喜爱《红楼梦》里的手帕。它关乎爱情。
小红和贾芸之间就有一方爱情的手帕:怡红院的丫头小红丢了手帕,急得小脸都红了,若是被登徒子捡了去,再胡言乱语,岂不是毁了女儿的清誉?若是这些浑话再被心心念念的芸哥儿听到了,那可是要了命了呀!哎,偏偏这手帕被喜相的月老送给了女孩心上的人,芸哥捡了小红的手帕!美少年贾芸对美貌可人的小红早已是郎有意,借机把自己的手帕还给了小红。
一来二去,一段姻缘就此形成。手帕充当了表情达意的爱情媒介。妙用!
“一方素帕寄心知,横也丝来竖也丝”。
红楼梦中随处可见手帕的影子。姑娘的,丫头的,夫人的,公子的,仆妇的,它们像一尾小狐狸,蹦蹦跳跳,和主人如影相随,探头探脑。
林妹妹的手帕一定是最多的,也是不离手的。“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某一日,晴雯撞见潇湘馆的丫头春纤晾了一栏杆的手帕呢!
林黛玉的手帕怜香惜玉,比宝玉还贴心。它和林姑娘一起不仅花气袭人知骤暖,也知世态凉呢!
手帕是林黛玉表达心情的小道具。嘴里咬着手帕的娇俏,手指绞扯着手帕的嗔恼,粉帕遮面假寐的妩媚,水绿帕子擦拭眼泪的梨花带雨.......
一颦一笑,千回百转,娇喘微微,闲花照水,弱柳扶风,一部红楼里,林黛玉明明白白是绛珠小仙,手帕就是她形影不离隐身的小白狐,古灵精怪,可心可意的贴心,善解人意的万种姿态。
宝黛爱情的见证和信物,就是两方旧手帕。
多少稀罕物,宝玉送给黛玉,反而被灵魂极清贵的黛玉斥之为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而宝玉被贾政痛打后,恐哭坏了疼坏了那个水晶人儿,派晴雯送过去两条旧丝绢手帕,晴丫头不解其意,担心黛玉恼了,宝玉却深知黛玉必知其意,果然,黛玉见了旧手帕,动容了,写下传世绝唱: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
红楼梦里的手帕,既有丝绸的圆润与薄凉,又有爱情的温婉细腻与幽香。红楼里的青春是热闹而奢华的,无边的香气从手帕里飘出来,在大观园里蛮夷着,那是绮罗香,体香,诗香和爱情味儿。最终呢,收足了女儿泪,到底也逃不过花落人亡的荒凉。
手帕,尤其在古代,那是每个人随身所带的小物件,也是文人雅士题诗作画的心情之物,更有那兰心蕙质、含情脉脉的小女子,在上面绣了红梅绣白荷,委婉含蓄地把自己的闺名隐示于帕,等到春风起,桃花开,柴扉被小扣时,走进翩翩美少年,崔护般讨水喝,女子故意把绣了花的手帕遗落在他眼前。美了姻缘。
因为手帕的万种风情,少年时做各种美梦,愿自己就是那带一股子清气,有几分清姿的唐宋女子,可以在青檐红窗的廊下绣花,在白绸缎的帕子上绣诗句,绣鸟鱼,绣绿的黄的红的梅,梅花月里出生的我,把绣了各个花色的梅手帕,送给那个白锦袍的如玉公子。
可我出生在没有半株梅花的穷村子。杏花倒是村里村外地开,不矜贵。我只能坐在杏花下做手帕,把娘的旧毛蓝头巾剪成一方方手帕,偷了堂姐做新嫁鞋的一团粉丝线,给每一块蓝手帕都绣上粉杏花。幻想着都城南庄桃花开,崔护般的少年打马讨水来,爱上一朵凉幽的小杏花。丫头身子小姐病。
春风一场,飘落在发间和肩头几片落花。我是贫瘠的小杏花,痴心妄想着奢华浪漫的爱情。灰姑娘的南瓜车,是乡下少年黑夜里明亮的童话。
我虽是深巷里的小杏花,可我不自怨自艾,也不孤傲清绝,却像一只乡间绿林里野生的小蜜蜂,勤谨努力地热爱那瘦瘠的少年光阴,饱饱地嘬花粉,酿花蜜,踏踏实实地欣悦,欢脱脱地丰实。
十四岁读书时,我得了一方手帕子。我们彼时叫它手绢。
其实,我得的这方手帕,无论料子还是做工,哪里抵得上大观园里手帕子万分之一的清贵!它们那一眼就能看出是绸缎子的料,水月亮一样的多情缱绻,小姐腰肢一样的又软又滑,握在掌心里,像汪着一团春水,幽香又薄凉。
而我的这个虽然叫手绢,听起来这名字似乎是端丽的大家闺秀,其实是小门小户的村姑,即便是素衣襟上给戴朵花,也掩不住手指粗糙且刺人。
它是班上那个唯一穿白衬衫的少年,某一日早读时,突兀地放到我面前的,这一定是蓄谋已久的,他彼时彼刻一定是鼓足了勇气,白净的脸红涨得如一块红帕子。那是一块涤纶加丝的白手帕,上面有一朵绿梅花,不是手工绣上去的,倒像是缝纫机粗针大麻线走上去的,皱巴巴的梅枝,像女子愁眉不展的脸。
彼时彼刻,班上女孩们的目光齐刷刷聚焦在手绢上,妒火欲燃。
我方方正正地叠起得来的手绢,把绿绿的梅花展在明面,女孩子的那点子小虚荣小傲娇,鬼使神差地让我把它放在脱漆旧课桌的显眼处。
果然,收拢够了足足的嫉恨!那群乡下女孩子把作业本不约而同撂向我,砸得我和手绢都衣衫不整、羞恼不堪。我是一截不懂爱情的青竹竿,又直又涩。只有小小的虚荣心在作怪。
彼时的我是收作业的语文课代表,在班里是有一点点可怜的小威力的,可是就因为那块手绢,好长一段日子,我都伶仃无力。
我的无辜和委屈是一颗熟透的红樱桃,弹指即破,流出了红浆汁,却是披着红外衣的苦涩。那天,也是早读课,我装着一副月白风清的幽淡样子,当众还回了那个白衣少年送给的手绢,并且冷心冷口,看着他热情的目光渐渐暗淡、羞惭、失望,整个人成了一块沸水里翻煮的手帕子。年少轻狂,伤了一颗白衬衫的心。
从此,班里那些大龄的初三女孩子们,看我时带刺的目光,都软和成了月白缎子的手帕子。我不再是她们的情敌。我原本就不是?我不敢口问心,有几次暗夜里闪过他星星般清澈的眼眸,遥遥地记起,再心疼着。
相思无用!永远失去了一方绿梅花的手帕子。少年的心,怅然若失,那年春天过早的霜意重重了。
时过小半生。想起少年时冷落过的那方手帕那个少年,禁不住心下怅然。柴米油盐重重叠叠的千山万水里,那方绿梅帕,也许早已被丢弃在风里,但愿它有个好去处。
也许是被他新婚的妇人,从他晾干的衣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团,狐疑、嫌弃、发恨地丢进浊气万重的垃圾房里?希望它有一个矫情地告别仪式:最好是夹在一本多年不动的泛黄古书里,或者是匆匆丢进花重鸟茂的春光里,无须忧伤,旧物初人和初情,都薄薄敛进手帕子一样轻软的白月光里了。
清气的少年,初开的情窦,花明月净初为人帕似的新奇,满心满眼,很清贵,很娇气,那块少年的手帕是雨前的杏花,唐诗里的杏花。
如今,那方绿梅花手帕,最好是被收进书架上,做了微微蒙尘的一部古书的一枚书签。经年后,翻出,两鬓微霜的中年男子唇边会有一缕老气凉幽的笑意:不荡漾,只慈和地想起那个青涩任性的少女。
翻古书,影影绰绰,那群甩着手帕的小丫头们一起浮出来,唱着“开辟鸿蒙,谁为情种.”一团欢喜一团悲戚地上演着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回头看,少年杏花树下做手帕,嫩嫩的情窦浮在雨气里,初洇开,彼时的故乡是一块古旧的黄手帕,从母亲粗糙的手里抽出来,柔柔铺开来,少年们在上面绣绵绵春雨缤纷下,不知朝暮;绣白白杏花碎碎开,未解人意;绣灰灰檐下读书郎,野心勃勃……
手帕,仿佛去了远古,纸巾是随身小新宠。那份优雅那些故事呢?它在我心里,细水长流,是香息袅袅的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