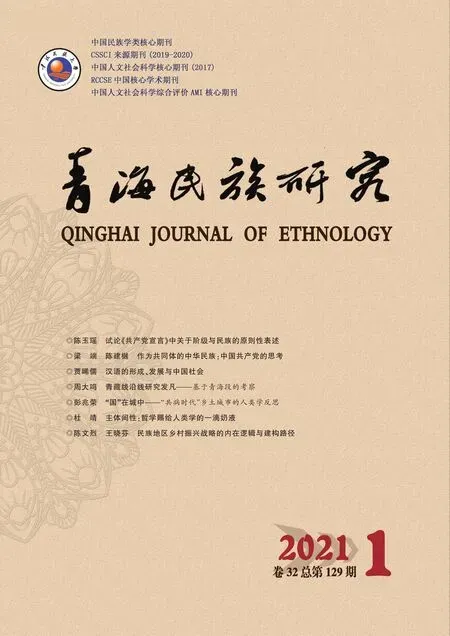试论《共产党宣言》 中关于阶级与民族的原则性表述
陈玉瑶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81)
阶级与民族是人类同时拥有的两种不同范畴的归属。 18 世纪以来,以阶级和民族为核心要义的两种意识形态都曾展示过各自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同程度地塑造并继续影响着今日世界政治格局。 在无产阶级寻求自身解放的历程中,对于阶级与民族的关系,《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出了明确的阐述:“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2]。
“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是《宣言》对阶级与民族优先级问题的一种基本立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则是《宣言》对无产阶级提出的行动纲领。 在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统治阶级、民族边界已经划定的先决条件下, 这一立场和纲领之间的关系是清晰明确的,不存在矛盾和张力。 然而在资本主义尚未战胜封建主义的地带, 资产阶级没能建立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边界待定。 在这种先决条件下,建立无产阶级民族国家与无产阶级联合之间就存在较大张力,“划清界限自立门户”(民族自决)的冲动与“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之间显得难以协调。 这是摆在马克思主义后继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对《宣言》立场正确性的检验。
对于阶级与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体系中阶级与民族的地位和关系问题, 国内外学者都进行过阐释解读和理论分析:陈玉屏教授曾探讨过经典作家如何看待民族与阶级的关系问题,并明确指出了阶级、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统率地位[3];王希恩研究员分析过阶级因素对民族问题的制约和影响[4]; 周竞红研究员结合经典作家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依次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阶级与民族的理论阐释,并就民族与阶级的当代意义给予了述评[5];国外学者中则有前民主德国的阿尔弗雷德·科津洛以及乌克兰的罗斯道尔斯基分别对“阶级与民族”“工人与祖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①这些研究成果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者应有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纵深,对国内民族理论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认识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但是中文“民族”的含义与经典作家笔下的“民族”并不始终完全对应,这种情况妨碍了我们深入而精准地研究相关问题。 因此,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法文版《共产党宣言》,结合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革命实践历程,对《宣言》关于阶级与民族的原则性表述,尝试作一阐释。
一、 无产阶级与民族:《宣言》对两者关系的明确
18 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国家,普遍建立了资产阶级主导的“民族国家”, 实现了封建特权阶级压迫下的资产阶级解放。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空背景,他们不可能对民族问题毫无感知。 相反,在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这股历史潮流初现时,他们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为了某个“民族”去建立“国家”,而是为了在“民族国家”的统一行政框架下建立“管理资本家事务的委员会”,以达到对内统一市场,对外划分市场边界的目的。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看到但并未在《宣言》中明确阐述的“资产阶级与民族”的关系。
既然“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手段与形式,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也要“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根本上也不是为了抽象的“民族”,而是借助这一形式, 实现无产阶级的独立和解放,推翻阶级压迫。 为此,《宣言》对“无产阶级”与“民族”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阐述。
《宣言》共有两处将无产阶级与民族放在同一框架下讨论。 第一处强调了阶级与民族在共产党人眼中的优先级问题,出现在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开头部分,谈论的是共产党人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中文版(即人民出版社2014 年单行本版,下同)原话是:“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6]
第二处也是在“无产者和共产党人”这一章,谈论的是“取消祖国”论和“取消民族”论之荒谬,中文版原话是:“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中文版为“民族的阶级”作了如下注释:“‘民族的阶级’在1888 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 ”[7]
将这两处与1983 年法国出版的由劳拉·拉法格翻译、恩格斯校对的法文版《宣言》做一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处关于阶级与民族优先级问题的原 话 是:“Dans les différentes luttes nationales des prolétaires, ils mettent en avant et font valoir les intérêts communs du prolétariat.” 这 句 话 的 前 半句——“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无产者”“不同”“民族”都是修饰“斗争”这个中心语的,这句话展示的场景实际上是“多个民族的无产者分别开展的针对本民族统治阶级的斗争”, 正是在多个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对于这种“民族斗争”的含义,《宣言》在第二处还有进一步说明。
第二处的法文原话及其相对应的中文意思是:“En outre, on accuse les communistes de vouloir abolir la patrie, la nationalité.”(有 人还责备共 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Les ouvriers n’ont pas de patrie. On ne peut leur ravir ce qu’ils n’ont pas. (工人没有祖国。 不可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Comme le prolétariat de chaque pays doit, en premier lieu, conquérir le pouvoir politique, s’ériger en classe ma resse de la nation, il est encore par là national lui-même, quoique nullement dans le sens bourgeois.(由于每个地方的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权,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但绝不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含义。 )”
如果着重关注法文版《宣言》中关涉“民族”的地方,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中文版和法文版在“民族的”(national) 这一形容词的使用上是一致的,但“民族”术语的使用却并不始终对应。 法文使用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读者普遍熟悉的“nation”,另一个则是不太熟悉的“nationalité”(即英文的“nationality”德文的“nationalität”)。
“nationalité”有多重含义,最初是指“民族特性”或“民族精神”,后来则“被实义化为具有相同种族或语言的群体本身,即‘族体’”[8],最后才演化出认知度较高的“国籍”含义。 “nationalité”成为“国籍”的前提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已然确立,但在《宣言》发表的时代(1848 年),意大利和德意志都尚未完成统一大业, 中东欧其他地区仍然处于帝国统治之下。所以“国籍”显然不是《宣言》想要表达的意思。
“nationalité”还可以所指代当时西欧大民族以外、尚未独立建国、具有语言文化同一性的中小规模的“民族”,比如匈牙利人、亚美尼亚人,甚至尚未统一建国的意大利人、波兰人等,其与“nation”的区别主要在于,“nationalité”规模小且没有建国,而“nation”往往规模较大且通常完成了资产阶级建国。 为了不造成概念混淆,笔者沿用民族学界已有的“族体”译法对译“nationalité”。 但是《宣言》在接下来反复使用“nation”“national”,所以文中谈到的取消“nationalité”应不是指取消“族体”。
因此,这里的“nationalité”很可能是就“性质”而言的,可以进一步解释为“民族的性质”或曰“民族性”。 中文版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民族”的译法并没有错,但是这里的“民族”似应进一步理解为“民族性”。 “nationalité”指“民族性”的这一推断还可以通过《宣言》接下来的论述加以佐证:如果说“工人没有祖国。 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是针对“取消祖国”论的反驳,那么“它本身还是民族的”(也就是具有民族性)应该就是对“取消民族性”的回应。 为什么“还是民族的”? 因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就上升为了民族的领导阶级。 可见,《宣言》 在驳斥这些指责时是逻辑严密而又深入浅出的:“工人没有祖国”,所以共产党人不可能“夺走”(ravir)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后,它本身还是民族的,所以“民族性”并没有因此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民族国家已成为主导国家形态的欧洲,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已日益获得国家的统治权,或者说资产阶级已成为‘民族’的领导阶级”[9],所以《宣言》更多以西欧情况为参照,多使用“nation”这一概念。“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是《宣言》的明确宣示,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实践主张,他们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然后再进行国际联合。 正如恩格斯在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中特意指出的,“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 ”[10]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在民族国家范畴内实现这一事实有清楚认识, 他才明确表示,无产阶级要反对资产阶级构成民族。 因此,“其革命视野远非否定民族,他协调了阶级与民族这两个概念,在各民族工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建立了清晰的联系。 ”[11]“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 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 ”②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空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战胜封建主义并开始快速发展的西欧,民族国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实现统治权的普遍形式。 然而此时的中东欧地区尚处于封建帝国统治之下,统治中东欧各国的四个封建专制帝国中, 除普鲁士外,其余三个帝国——奥地利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的资产阶级都没能建立起民族国家,且帝国境内族体众多,帝国统治者和资产阶级都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达到压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目的。在这种条件下,中东欧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不得不将“民族”与“族体”笼而统之地归纳为“民族问题”(question nationale),并在“无产阶级革命”框架下不断回应、阐发有关“民族问题”的各种立场、观点和主张。
二、 坚持“各族无产阶级自决”与反对“民族文化自治”:列宁的主张
早在1848 年,马克思就强调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要求欧洲工人政党要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战。[12]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无产阶级政党指出的这一外部主要敌人——沙俄帝国消失了。
然而,“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领导阶级”的这个国内目标却没能达成,西欧无产阶级在国内层面争取民族领导权的斗争普遍失败。 意大利和德意志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建立,在客观上强化了欧洲的反动力量,妨碍了无产阶级用革命方式建立以本阶级为领导的民族国家。 随着沙俄、奥地利、奥斯曼帝国的陨落,西欧强大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成了新的“反动势力的堡垒”。 资产阶级主张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即以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和“族体”为单位建立国家(“一族一国”)的观念占据优势,并向东欧地区散播。 于是,在中东欧社会主义者那里,笼而统之的“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以更为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了一起。
尽管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支持者和领导者,中东欧社会主义者与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意见却并不统一。 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围绕波兰独立产生的“无产阶级自决”与“民族自决”的优先级问题;第二是围绕奥地利国家组织形式产生的多族体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制度安排问题。
第一,在波兰独立问题上存在三种意见。 波兰社会党(P.S.P)的主张是“民族自决”优先,应“无条件”地承认民族独立。 实际上,在建党之初(1892~1893 年),该党就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而没有把争取自身独立的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 年)则认为波兰的社会党人不应当要求波兰独立,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才是最首要的任务。 “卢森堡正是出于波兰无产阶级的团结考虑, 才坚决反对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认为这一口号会被波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利用,从而不利于波兰人民群众的团结。 ”[13]
而列宁既反对完全无视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独立, 也反对完全无视民族诉求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于罗莎·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列宁认为她犯了“抽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14],他的《论民族自决权》(1914 年)一文尤其针对卢森堡的观点进行了阐发。
对于波兰社会党的要求,列宁也进行了专门阐述(1903 年),在“民族自决”与“无产阶级自决”的优先级问题上给出了如下意见:“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peoples or nations)的自决,而是促进每个民族(nationality)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 我们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nationality)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我们应当使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要求服从的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 这个条件正是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提法的区别之所在。 ”③可见在列宁那里,“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这一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尽管这里遭遇的是作为“族体”的“民族”。
第二,围绕多族体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制度安排问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与列宁的意见也不统一。 奥匈帝国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各自治党派(德意志党、捷克党、波兰党、罗塞尼亚党、意大利党及南斯拉夫党) 在1899 年大会上提出了以族体联邦的形式重新组建奥地利的方案。 根据该提案,“帝国要被分成‘根据族体划定范围,并以自治形式被管理的各个单元’。 这些单元的立法与行政附属于通过平等而直接的全民投票选举出的议院。 同一族体的所有自治地区将形成一个负责自身事务的联盟。 而政党自身将根据社会民主自治的联邦基础进行组织,每个社会民主组织都要涵盖一个族体。 ”[15]概括起来,就是要将奥匈帝国改造成以各族体所在地方为单位的“联邦制国家”。
但帝国的实际条件却表明该方案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各族体相互交迭分布,没有清晰可辨的界限。 于是, 奥托·鲍威尔 (Otto Bauer,1881~1938年)与卡尔·伦纳(Karl Renner,1870~1950 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超地域民族文化自治”(l’autonomie nationale culturelle extraterritoriale)方案。 在这种方案中,族体仅是一种文化共同体,各族体将分别成立社团性质的联合会并实行文化自治。[16]
鲍威尔与伦纳的“民族文化自治”论说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不小反响,考茨基(Karl Kaut sky,1854~1938 年)赞同这种主张,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也都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要求。“由于鲍尔(即鲍威尔——笔者)和伦纳的思想碰巧惹得列宁勃然大怒,文化自治的全部概念此后一直被共产党人拒绝作为一个信条。”[17]列宁为什么强烈反对“民族文化自治”方案? 因为他已经看到,“其他民族(波兰族、犹太族、乌克兰族、格鲁吉亚族等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在抬头,竭力用民族斗争或争取民族文化的斗争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伟大的世界性任务。 ”[18]在他看来,“民族文化自治”不仅对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建设产生负面影响,也威胁到了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统一,进而妨碍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完成。
于是,列宁在1913~1914 年间多次撰文(《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文化”自治》《论民族自决权》《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等)批评“民族文化自治”论。 他指出,在党内层面,“民族文化自治”的本质是“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19],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那样按民族划分党的组织结构,而应该实行实际上的统一;在未来的国家建设层面,“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鼓励各民族在教育事业 (乃至整个文化事业)上相互隔绝,是在分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妨碍各民族融为一体;[20]在无产阶级革命全局层面,“民族文化自治”论迎合了政治对手的宣传和意图:地主、神父和资产阶级通常都是在“民族文化”的幌子下,贯彻反对无产阶级的意图。[21]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根据奥匈帝国现实提出“多族体国家”这一构想,体现了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一族一国”论说的超越,具有一定创新意义;但是在多族体国家内部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却不利于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建设,也妨碍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统一。 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问题之关系的见解,也愈加凸显了他作为一位承前启后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修养。 遗憾的是,列宁的思想并没有在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得到坚持和贯彻。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中,证明了《宣言》中关于“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这一原则的正确性。
三、“外来民族”还是“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的实践选择
与中东欧的情况类似,19 世纪下半叶到20 世纪初这一阶段, 中国正处于封建帝国统治之下,这个封建的“中央帝国”同样显示着多族体(中文语境的习惯表述为“多民族”)的外貌特征;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已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 中国无产阶级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但中国共产党忠实贯彻了《宣言》的相关原则,正确协调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 就明确了少数民族问题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义,“1928 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作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问题的范围包括:‘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 ’‘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概念,突破了‘五族共和’的局限,明确了少数民族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 ”[22]
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包含着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解放,少数民族的解放也必然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宣言》相关原则的正确运用。 在这方面,仅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满洲之高丽人”(东北朝鲜族)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贯彻《宣言》原则的具体实践给予阐述。
东北朝鲜族是19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迁居中国的一个迁入民族,他们先后经历清政府、民国政府与日本殖民者的统治, 直到20 世纪初期还普遍被认为是“外来民族”。 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朝鲜农民是“外来民族”就无视或忽视其生存处境。 中共满洲省临时党委曾就本地区农民的被剥削情况专门给中央作过报告,其中就包括朝鲜农民问题:“满洲的最大地主是张作霖与杨宇霆、吴俊生等,其次就是乡村中的大地主, 他们的土地不是以亩计,而是以山沟计,农民也非常集中,普通的村落,在一千户以上,乡村中的地主,多有雇用工人在三百人以上。 贫农的成份除了山东、直隶去的难民外,就是朝鲜的难民。 由山东、直隶去的难民,多有单身无妻子,身上穿着一套衣,纯是一个无产阶级似的。 由朝鲜去的难民,多开垦水田种稻,待水田开垦后,中国地主即收回为己有。 ”[23]
东北地区党务工作报告不止一次地谈到过朝鲜农民在中国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在不同的报告中,对朝鲜人的称呼也不尽相同,有“朝人”“韩人”“高丽人”等等。 然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将其排拒在革命斗争之外。
阶级立场先于民族立场、 阶级立场重于民族立场,正是这种认识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注重联合、动员、团结朝鲜族农民,使之成为“中国的革命群众”:“朝鲜农民是我们反日的友军,是我们满洲革命的农民的一部分。 我们再不能旁观中国的军阀地主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去蹂躏朝鲜农民,我们当联合这部分可亲爱的革命群众,在斧头镰刀交叉的红旗下面,共同作反日运动,作土地革命运动,做谋夺取政权的斗争。 ”[24]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农民,是同样遭受中国封建地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摧残蹂躏的“无产阶级”,因而也是“中国的革命群众”。
“中国的革命群众” 意味着相同的社会身份、阶级归属和政治地位。 由此,才会产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凡朝鲜的农民在满洲与中国农民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和居住权,一律享有革命政权。 ”[25]
平等是联合的基础, 建立中朝民众的革命统一战线,正是在这种前提下被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中韩民众必须联合起来,以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强盗。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韩国地方富农、高利贷者的走狗作用, 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对于韩国农民的民族压迫,而坚决主张:在满洲的韩国少数民族有和中国民族完全平等的权利,主张少数民族有完全自决权。 但是中国共产党清楚指出: 少数民族自决权的完全实现,只有在中国革命完全成功以后。 ”[26]事实证明,1945 年光复以后,东北地区大部分朝鲜人根据自决权选择留下来加入中国,成为了当代中国的朝鲜族。 朝鲜族成为中华民族平等一员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同志在1957 年曾讲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27]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逻辑基础,正是在于共同的阶级归属。 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团结带领各族无产阶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用实际行动贯彻了“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这一原则, 证明和彰显了该原则的真理性和实践价值,为各民族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无产阶级从“受压迫者”成为“中国的革命群众”乃至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族人民正是在这一坚实的阶级基础上、在共同的革命、改革、建设进程中,逐步巩固了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也必然沿着这一历史逻辑继续向前推进。
综上所述,“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这一立场,是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列宁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实践的正确原则。 经历过中东欧社会主义者的争议、试错,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这一原则的真理性和实践价值愈加彰显。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宣言》是共产党人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的宣誓书,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初心”。在中国共产党建立100 周年之际,重温《宣言》的重要原则,回顾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实践,不仅具有隆重的纪念意义,也愈加凸显了《宣言》对当今时代的塑造作用和深远影响。
注释:
①参见【民主德国】阿尔弗雷德·科津洛《阶级与民族》,载陈玉瑶、朱伦编《民族与民族主义——苏联、俄罗斯、东欧学者的观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罗斯道尔斯基的 《工人与祖国——<共产党宣言>相关段落的笔记》(1965)一文的中译本可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dolsky/mia-chinese-roman-rosdolsky-1965.htm (最后浏览日期:2020 年6 月15 日)。
②这是1914 年列宁在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撰写《卡尔·马克思》这一词条时,对《宣言》中这一表述作出的简短阐释。 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95 页。
③本段中“民族”术语所对应的外文是参照列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献网站 (英文):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3/jul/15.htm (2017-12-23);中文引自列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列宁卷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37、3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