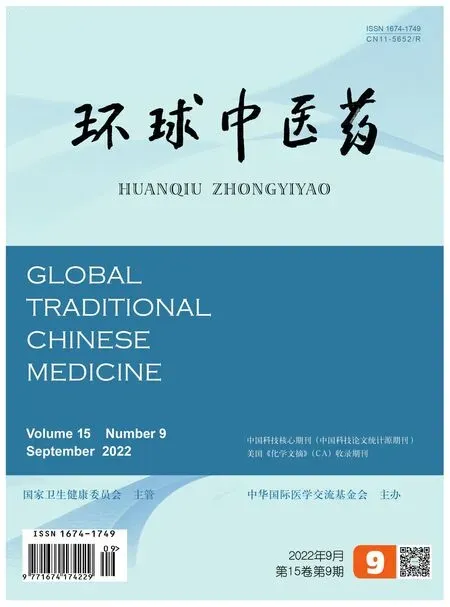从《金匮要略》虚劳病的证治探讨隔二隔三的治未病思路与方法
李福生 胡楠 胡嘉琦
《黄帝内经》首次提到治未病的概念:“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也对治未病的思想进行阐述:“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通过肝病应先实脾的治疗思路,揭示了治未病思想在疾病发展中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应用理念[1]。同时提出一个治疗肝病的办法:“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此治肝补脾之妙也”即利用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对肝、心、脾三脏共同治疗,来达到治疗肝病的目的。清·吴谦《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2]对《金匮要略》的这种治未病方法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上工不但知肝实必传脾虚之病……此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化生不病之理,隔二、隔三之治,故曰: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并首次对此法进行命名,提出“隔二、隔三之治”。即我生的脏谓之隔二,我克的脏为隔三。在治疗上,针对虚损的脏腑,进行“隔二、隔三之治”的思路,用的正是“此亢则害,承乃治,制则生化,化生不病之理”。
1 隔二隔三之法的概述
1.1 隔二隔三之法的各家观点
目前针对此理论研究的应用,争议主要还是在隔二隔三的脏腑选择上,多数学者认同蔡向红在《隔二隔三之治的方法》[3]中对于隔二隔三之脏的界定,即隔二脏为我所胜,隔三脏为我所不胜[4]。笔者认为这并非《医宗金鉴》之原意。《金匮要略》原文提到“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即肝病治肝的同时,应该助心火和益脾土。《医宗金鉴》中进一步解释其机理:“用焦苦入心……用甘入脾……使火生土,使土制水,水弱则火旺,火旺则治金,金被制则木不受邪,则肝病自愈也……隔二、隔三之治。”由此可见,木病,治心、土,实则是抑制肺金,使其不会压制木,让木病达到自愈的目的。心火为木所生,脾土被肝木克,在这一轮辨证中,以肝木为立极点来看,心火和脾土对于自己有生有克,但以五行相生为一个闭合圆环的话,治的心、脾两脏,正是肝木的隔二、隔三之脏。故笔者认为《医宗金鉴》对于病者隔二、隔三的界定,是病者生的脏是隔二,隔二者生的脏是隔三。以病脏看,隔二隔三者正是我生者和我克者。由此可见,《隔二隔三治的方法》与《医宗金鉴》中的我生者隔二、我克者隔三的界定不符。
1.2 隔二隔三之法只应用于虚证之中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提到:“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明确阐明此法为肝虚的条件下启用,当证机辨明为实证者则不再用。“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这句话说明了脏腑生克制化的原理,即进一步强调虚证用此法,而实证则用泻法,也可将此理论应用于其他脏腑虚损的治疗中。综上,隔二隔三之法只应用于虚证之中。董飞侠[5]认为《金匮要略》中的猪苓汤通过治疗肺金和脾土来泻水,采用的也是隔二隔三之法,笔者不认同这个观点。猪苓汤为水邪停聚,水热互结之证,病位属肾,病机属实。“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此处一个“攻”字,也可看出此证为实证并不满足隔二隔三应用之理论,所以猪苓汤中用泻法。猪苓、泽泻利水育阴、泻肾水,茯苓、滑石健脾利水通淋,阿胶润肺养阴清热,这其中涉及到肾、肺、脾三脏[6],且四味药都有利水作用,以肾之实证角度看,脾为肾所不胜,脾居中焦又为水液代谢之枢纽,故健脾利湿使得中焦水液正常运转。肺为肾之母,子病累母,水热蕴结产生相火,用阿胶滋润肺金,使金和水母子相生,气机运转,代谢水液。脾土和肺金并不是肾水隔二隔三关系。“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中的“余皆仿此”不是指隔二隔三之法,而是辨证加减按此方法行之,当小便不利出现渴证,应按实证“损有余”而处之,可投猪苓汤。
1.3 隔二隔三之法与治未病思想的关系
《医宗金鉴》对《金匮要略》中肝病治脾的病例进行详细阐述,提炼出“隔二、隔三之治”的理论,平衡脏腑的气血阴阳[6],来达到安未受邪之地和补虚损之脏的治疗目的。其利用五行制化的方法所体现出的治未病思想和《内经》《金匮》是一脉相承的。依笔者所见,隔二隔三理论可应用于《金匮要略》中很多地方,下面试用《金匮要略·虚劳病》篇中方证进行举隅。
2 用隔二、隔三之法阐释《金匮要略·虚劳病》
2.1 从肾水不足导致的“失精”进行隔二隔三干预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是治疗阴阳两虚,失精梦交之疾病[7],姜春华分析此方用药规律,认为其重用龙骨、牡蛎[8],意在发挥其敛阴涩精之功,甘草和白芍酸甘化阴,甘草和桂枝辛甘化阳,甘草亦可补脾,使气血生化有源,此为阴阳并补之法。笔者认为“夫失精家”是肾精亏失,导致的阴损及阳,并非是肾阴肾阳之实质损伤,而是一种肾精急且暂时的缺失状态,精亏则气窜,出现“少腹弦急,阴头寒”;肾藏精,肝肾同源,肝木又为肾水之隔二,母病及子,水病及木,肝失濡养,血亏必有营卫不和,故有“目眩、发落”之肝损证机表现;“男子失精,女子梦交”,精血俱亏,阴分不足,虚火内扰,心之阳气不能下潜归于肾水,导致心肾不交,火之于水,此为隔三。此“虚劳失精”之病因在于肾失精,母病及子,肝木失养导致升发太过,使心阳不得下潜,此证病机演变与隔二隔三理论契合,证机明确,为使土不趁水虚而埋,需栽木以固土,同时调火锻金以护木气,故仲景以助木益火之法进行调整。方中遣龙骨三两,主入肾经,取其收敛固涩肾精之用,《雷公炮制药性解》曰“肾主骨,宜龙骨独入之……故主精滑等症。”次入心、肝经,兼有镇静安神,平肝止眩之效;牡蛎与龙骨相须,增强收涩、平肝、安神之力。此一药组在本证机的隔二之治中,平肝制金以护水,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另有桂枝和芍药的一热一凉[9],调和营卫,在升降之中也是隔三法的妙用,此证机并无心火之虚损,所以只需桂枝配合生姜温煦心阳,使得心安本位,随龙骨牡蛎沉降之气下潜于肾水,为先安受邪之地,体现了治未病的理念;芍药凉润,滋肝阴,使肝气条达理顺,二者配伍,肝气得以升发,心阳得以下降,循环往复,平衡之道。另有甘草配伍芍药和桂枝分别取酸甘化阴、辛甘化阳之效,燮理阴阳,再伍大枣调和脏腑。诸药相合,不用补肾之品,却能调和阴阳平衡,其方法圆融,证机严谨。
2.2 建立中和,益水制火所体现的隔二隔三之法
小建中汤为治疗虚劳腹痛的名方,千百年来对于其“建中”之意众说纷纭,历代医家多认为“建中”乃“健脾”之意,刘宏岩[10]研究认为,参看药物组成及剂量,认为“健脾”或是“建立中气”等皆无依据及道理,更倾向“建中”于“建立中和”之意。脾胃为后天之本,为生命之大海,气血生化之根源,脾升胃降,鼓动其他脏腑的运行。“建中”其本质在于使气机中和,阴阳才能平衡。
笔者认为,脾土为中焦之本,为人体气机的枢纽,上承肺之清气,朝百脉散播水谷,下通肾之水道,借其阳气温煦运化,排湿利浊。“虚劳里急,腹中痛”脾胃虚弱,运化失常,导致营血匮乏之五脏失养。虚劳之气血不足,升清乏源,见“心悸”;脾不统血,导致血不归经见“衄血”;脾土生化乏源,运化失司乃至母病及子,津不上承,肺叶燥化见“咽干口燥”;虚劳失血导致相火虚扰见“手足烦热”和精关不固之“梦失精”等症状。小建中汤方中倍用芍药,《长沙药解》论其“善调心中烦悸,最消腹里满痛”,濡润脾阴,滋养脾络止痛缓急,配合炙甘草、大枣健脾和营,使脾土生化有源,恢复升清和统血功能;再用桂枝、生姜配合饴糖,润肺补虚以止咽干口燥[11],金之于土为隔二之脏,肺之清气与脾中水谷相合,使气血生化布散有源。此中的饴糖实为妙用,其不但可生津润金,和中缓急,又能养血以灭虚火,此为隔二之法;肾水为隔三之脏,但此方中没有补水之药,是因为补水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心火以护肺金,但症状中已有心悸和衄血等心虚表现,火已无力克金,所以可以不用补水。
2.3 肾气寓阴阳,阴阳并补的隔二隔三之法
《内经博议》有云 :“盖以肾之为气,主蛰伏,主归藏……体阴而用阳。人身之肾,其坚滑者水之体,其流动者火之用,得水火两具,而藏命门真火于至阴之中,坎之象也”。陶汉华[12]认为,肾气为肾之阴阳的总和,孤阴无阳无以下潜,孤阳无阴无以温煦,从“阳化气,阴成形”的角度看,肾中之血、精包括肾脏器质本体,都可称肾阴,肾之生理功能的活动即为肾阳。笔者认为,肾为人之根,肾之阴阳绝非孤立存在,肾阴与肝阴为伴,肝肾精血同源,相互资生;肾阳与心阳为伴,二者阳气升发,心为五脏之巅,心气宜升不宜降,心阳赖肾阳的温煦和鼓动。
肾气丸是仲景补肾的代表方,条文中提到“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的症状,此方证机同前二例的区别为:隔二隔三的脏腑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仅表现为肾阴阳亏损,肾络失养,膀胱气化不利的表现。但从五行制化角度来看,当肾水不足,肾阳无力上济心阳,或心阴不得下潜肾水,导致心肾之阴阳无法交合,出现水来克火,心气失衡的症状。若心力得助,能克制肺金,使肝木不被克制,就可解除后顾之忧;肝木又为水之子,水病及木,肝木升发条达之性依赖肾精的濡润和充养,肝木顺畅之时克制脾土,使肾水无忧。笔者认为,此方八味药的配伍可以佐证隔二隔三之法,同时也是治未病思想的高度体现。方中遣干地黄同入心、肝、肾三经,滋阴潜阳,填精生髓,养血滋肝,稳心凉润;取山茱萸入肝肾经,大补精血,壮元阳、固精髓、安小便[13];伍山药补虚羸,充五脏;此为三补,共奏补虚缓急之效。补水为补本虚,补木克土以保护水,为隔二之治;再伍桂枝、炮附子温心阳,壮火克金以保木,为隔三之治。泽泻入肾、膀胱利水育阴,牡丹皮入心、肝、肾,具有清心,条达木郁,行瘀血的作用,也可防止熟地和山茱萸补肝肾滋腻太过。茯苓入心、肾平心健脾利水,此为三泻,平衡五脏之阴阳。
2.4 借心脾以养肝魂治疗失眠体现的隔二隔三之法
酸枣仁汤治疗虚烦不眠,刘文龙[14]以“肝藏血,血舍魂”为理论根基进行深入探讨,肝体阴而用阳,肝木之条达升发全赖肝血的滋养,虽然造成失眠的五脏之间蕴含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但其本质是来源于肝。肝血亏虚日久,损伤心血加重失眠,所谓“母病及子,魂动神扰”; 肝木亢盛,易凌侮肺金,致易寤或频寤,所谓“木火刑金,魂魄难安”。袁成民[15]认为,阳中之阴的“肝魂”流入阴中之阳的“肺魄” 这一过程正与睡眠“阳入于阴”的生理过程相契合。
在笔者看来,酸枣仁汤主的虚烦不眠证,其病根在于肝藏血不足,肝气需肝血滋养以维持气机条达的属性,肝血亏损,母病及子,心气上升为顺,但心阴不敛,血虚生内热,虚火上炎,出现虚烦,阳不入阴,故目难瞑不得眠。在治疗上仲景立法以酸枣仁为君,取其“主筋骨虚寒,夜卧不宁,虚汗烦渴,安和五脏,大补心脾[16]”之效,从心肝脾经入手,宁心、健脾、养肝血,补肝之本虚,伍川芎调肝养血,为补本虚和隔二之治;用茯苓、甘草健脾制水以护心,为隔三之治。再加一味知母除烦兼缓诸药之热性。其实知母也另有妙用,在于其能走肺经泻金[17],以缓木之被金抑之弊。木升金降,各安其位,诸药和合,共奏除烦安神之效。
3 隔二隔三法应用于临床
3.1 心气虚弱,助隔二脾土和隔三肺金
患者,女,35岁,白领。2021年2月26日初诊。患者自春节前以来,出现心慌心悸,气短乏力,劳后加重,面色淡黄,饮食无味,自汗出。经查体心脏二级杂音,窦性心律不齐,心电图示:I°房室传导阻滞。血压120/80 mmHg,心率82次/分。曾服复方丹参片后稍有缓解,但劳累后又复发,且伴失眠。查脉象左寸部均沉细,右关部沉弱,双尺尚可。舌淡苔少。此为心气虚弱证。用补养心气,平调气机的治法,方选《医方考》之养心汤加减。方用柏子仁、酸枣仁、五味子、远志稳心敛汗,安神定志,用黄芪、党参补心肺之气,配合茯神、白术、炙甘草健脾益气,再伍当归补血活血,润养心阴与诸药之燥。稍佐少量白芍,一来配合当归养血柔肝,二来配合酸枣仁安肝魂,防止肝木失调,克伤脾胃。3月7日复诊,十剂后,诸证均减,左右部脉力上升,法同前,稍减量,再予七剂以巩固疗效。后随访,患者已无不适,嘱其来医院复查心电图及相关检查,结果正常。
按 患者劳累是诱因,加之工作操心劳神,导致心气不足,鼓动血液无力,故出现心慌心悸;汗为心之液,心气固摄无权,出现自汗;患者因春节来临,病情稍有迁延,患者平素体弱,心气虚弱累及脾土,母病及子,脾胃运化功能也随之减弱,出现面色淡黄,饮食无味的症状;心火之病同时又克伤肺金,出现气短乏力,劳后加重症状;心气虚甚,过用丹参活血,致心神失养,出现失眠症状。从病机演变来说,心火的隔二脾土,和隔三肺金都因为心气虚弱而有所累及,但正因脾土无法制水,肺金无法制木,故使该患五行能量场持续处于失衡状态,心气虚会逐步进展,如果不及时用生克制化之法进行干预,心气虚会变成心阳虚,并继续对其余脏腑产生影响。
3.2 肝血失荣,助隔二心火与隔三脾土
患者,男,42岁,2021年3月2日初诊,主诉右肩胛区酸痛、右手臂麻木,遇凉加重,纳差少食,睡眠不好,周身乏力,偶有胸闷气短。西医诊断为颈型颈椎病,中度脂肪肝,血脂异常症。查脉左寸关弦细,右关濡细,此为肝血失荣,血不养筋,风湿内侵之证。拟方先选用豨莶草、海风藤、桑枝、秦艽[18]以祛风除湿,通络止痛,祛除标实之邪;再伍生地黄、女贞子、当归、制首乌、白芍[19]以滋肝柔肝,养血和营;少佐黄芪、桂枝以充养心气,护助心阳,为隔二之治;以炙甘草、山药健脾补气,使正气充足,诸邪不生,护中土制水以救火,此为隔三之治。予7剂水煎服,7日后回访患者肩痛大减,诸证减轻,仍有纳差伴无力,嘱其遵前法再服5剂以巩固疗效。
按 因患者平素饮食不节,肝脏负荷大,长期处于过载状态,导致肝血消耗,营血空虚,于是风湿之邪趁虚而袭,发为关节肌肉疼痛;母病及子,心血暗耗,出现胸闷气短,睡眠差等症状;肝阴不足,肝木失于条达,木郁克土,影响了脾主运化功能,故出现纳差少食,周身乏力的症状。诸证相合,符合隔二隔三之法的应用范畴。
4 总结
隔二隔三之法提供了一种治未病的治疗角度,其对于疾病前期和疾病期的干预有确切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临证之时当司外揣内,确定虚实,不仅要找到病因,也要兼治疾病传变。实者需泻之,并查看所克之脏是否有虚象,虚者则用隔二隔三之法精确制导。如遇虚者,补虚的同时需顾护我生和我克者之气机,来达到阴阳平衡的状态。治未病思想就是把握疾病发展的前端[20],提前对疾病的走向进行干预,用生克制化的方法指导疾病诊疗过程。
笔者认为,此法尚需更多的进行阐发和应用,也是未来着力研究的方向,其他病症例如风寒暑湿燥火、气血湿痰郁等外因、内因等,也可以按照其各自的属性,结合五行的生克制化之理进行病机推演,提供更多的治疗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