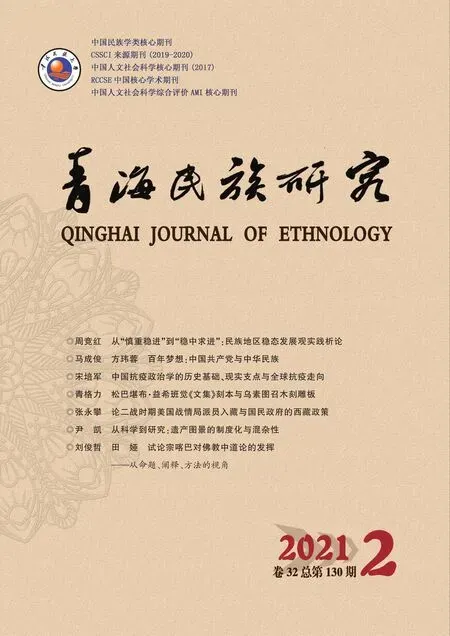论丰子恺佛学思想的民俗情怀
芦海英 孙 静
(江苏海洋大学,江苏 连云港 222005)
1948年丰子恺在厦门讲演《我与弘一法师》中将生活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这三层生活境界向我们展示了个体上下求索自我修炼的历程。自然,在这过程中处于顶端的佛教思想的形成,必是历经岁月打磨的结果。思想源于生活,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露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写道:“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丰子恺出生于具有独特民俗文化风情的江南水乡浙江嘉兴,正如印第安人谚语所说“创世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抔土,人们从杯里吸取生命的滋养”,他的思想中留存不可磨灭深入骨髓的地域民俗文化印记,他写道:“我们是浙江石门湾人,住在上海也只管说石门湾的土白。吃石门湾式的菜,度石门湾似的生活......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生 活!”[1]满含深情 的文字可看出民俗文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在丰子恺人生中占据的重要位置。根据“文化模式”理论,特定的习俗文化和思想方式构成一种特有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对人精神意识和生活行为的塑造力极大且不可避免[2]。不难看出,若想追寻丰子恺思想中独特佛学思想的源头必然要深探“上帝赐的那抔土”中孕育的传统文化的内蕴力量,一窥其中依托习俗的民俗文化模式对丰子恺佛学思想的影响。佛学思想在中国历史悠久,其传承演变进程复杂多样,流派思想层出不穷。欲探究丰子恺佛学思想的民俗文化渊源需要立足于对丰子恺佛学思想的全面了解和总体把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丰子恺佛学思想在中国佛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定位;二是丰子恺佛学思想的形成原因;三是丰子恺佛学思想的情感内涵。从三方面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观照丰子恺佛学思想的民俗情怀。
一
佛教思想自传入中国社会起,就凭借其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海纳百川的兼容性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渗透到各个领域中。近代中国风云变幻,在社会动荡、文化碰撞、生活困顿、道德失落和精神匮乏的情况下,佛学思想中国化过程中出现“救世型”和“救心式”两条道路分流[3]。救世型应用佛学以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为代表;丰子恺、夏丏尊、朱自清等作家为救心式的哲学佛学代表,二者之间存在继承发展的内在联系。救世型应用佛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以佛法求世法”[4]。例如章太炎的佛学主张,认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他以唯识为宗,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5],进而国民通过纯净的修炼拥有超人意义上的大人格,达到世道可变,国家可期的愿景。章太炎的主张是救世派重实用性的很好诠释。值得注意的是,丰子恺等白马湖作家所代表的救心式佛学并非是只唯心而将救世使命彻底丢弃,只是相比救世更强调佛学的救心功能。面对信仰缺失、精神匮乏的现实,他们选择以精神和情感的诉求为出发点,更重视佛教的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
佛教认为,苦海无涯,丰子恺的佛学思想形成离不开以苦为切入点,延伸出内因和外因两条线。内因包含丰子恺自身性格和其对“无常之恸”的体悟。丰子恺人生坎坷,使他对无常人生的痛感比常人更敏锐。7岁时他失去了疼爱他的祖母,9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一人苦苦支撑家庭,成人后亲人相继离世。在悲恸和失落中,他开始疑惑人生根本,以此为契机,佛教开始走入他的生活。内因以丰子恺主体性格为主导,他敏感善思,对万事万物有一种常人不能及的细腻体验,不论是一阵风吟还是一声蝉鸣都能让他联想到广袤的世界和个体的生命。“时间的状态都不明白,我不能安心做人!”在随笔《两个“?”》中丰子恺写出从小就一直困扰他的两个问题——时间和空间。无边的空间和绵绵的时间都让作者无法把握,“我不再问,只能让那粗大的‘?’照旧挂在我的眼前,直到它引导我入佛教的时候”。作者的求知欲和独特的哲理性思维方式最终将作者导向了佛教的世界。在解释李叔同出家原因时,丰子恺说“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如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这段话恰恰也体现了丰子恺自身建立佛教信仰的因由。欲探外因,必得置身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看亲友师父。五四时期,动荡变革,政治问题占据首要位置,多元文化交织碰撞,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在迷茫中满目荒芜。他们借助佛学构建精神家园,亲佛趋势胜于以往,丰子恺便是诸多五四现代作家中思想和行动都受佛学浸染的代表。丰子恺生于江南水乡,该地区经济发达、文化蓬勃,特别是传统文化土壤丰厚,幼年的丰子恺在丰富的民俗活动中就接触到许多佛教活动。他的父亲中过举人,丰子恺在父亲的熏染和系统的私塾教育中被儒学的仁学思想吸引,“仁者爱人”的朴素人道主义精神为他普度众生的佛家情怀奠定了基础。此后,在丰子恺佛学道路上,李叔同、夏丏尊和马一浮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李叔同起到了关键作用。丰子恺曾言“弘一法师是我学艺术的教师,又是我信宗教的导师”。弘一法师悲智俱足的人格魅力、无可比拟的艺术修养和严谨认真的人生态度为丰子恺才智的开启和开发做好了准备,使他终身受益。夏丏尊也是丰子恺浙江一师的教师,他多愁善感,《悼夏丏尊先生》有这样的表述:“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夏丏尊的慈悲情怀启发了丰子恺忧国忧民的爱世之心。母亲去世,让丰子恺跌入人生低谷,一度陷入颓唐。马一浮的鼓励和“无常便是常”的教诲使丰子恺有如醍醐灌顶一般,在得到极大启示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他的佛教信仰。
总体来说,丰子恺的佛学思想大概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无常之恸为出发点的缘起性空论。丰子恺在《无常之恸》一文中言:“无常之恸,大概是宗教启信的出发点吧。”丰子恺洞察无常为常的哲理,希望人们看清人世的真相,明白执着的事物皆为因缘流转而成,破除执念,抛弃私利,从而不为生活所惑,探寻真我。二是惠及众生(包含动物)的四无量心。佛家所说的“慈悲为怀”是慈悲喜舍这四种乐于利他心理状态的集合,即“四无量心。”慈无量是使众生得乐,悲无量是想使众生离苦,喜无量是见众生离苦而德喜,舍无量是平等对待一切,使众生远离一切苦乐[6]。四无量心尤重平等,既恩及禽兽又广及人世。三是信佛的目的在于悲智双运。谭桂林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中说:“用精神自我观照、嘲讽、警醒容易迷失于欲望和贪恋的肉体自我,这种处世态度与佛教推崇的悲智双运是比较接近的。所谓的悲,就是慈悲为怀,所谓的智就是灵知的心,就是对人生无常、万事皆空的洞明和彻悟。既不回避现实,又要超脱现实;既要体会人间的滋味又要勘破世间的幻象”。关于佛学思想指向,丰子恺明确表示是为了学习佛陀的慈悲与智慧以期完成人格和自我的修炼。四是戒杀护心的观点。佛家认为众生平等,都有与生俱来的佛性。丰子恺认为护生即护心,他说:“《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养成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说‘护生’就是‘护心’”。 丰子恺时而剪网出世,时而振臂入世,弘一法师的认真,夏丏尊的慈悲,马一浮的通脱,都能在他的佛学思想中捕捉到影子。
二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在《文化科学》中认为,人类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有着深厚人文历史底蕴的文化,往往无形中会形成巨大而潜在的心理积淀世代相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民俗文化经由漫长的历史沉淀,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成为某一特定时代和地区共有的生活方式,构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的人可以淡化或没有表层(文化)结构,却不能没有民俗文化存在的基本结构。”[7]深深扎根地域土壤的民俗文化作为个人内蕴文化潜在的基本结构是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的,反而会日渐沉淀,对人的思想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发生着影响,使人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丰子恺置身的民俗文化环境主要指其地域民俗文化环境。从丰子恺佛学思想的角度来看,民俗文化环境或大或小产生的影响分为两类,一种是丰子恺佛学思想成因的民俗诱因式影响;另一种是丰子恺佛学思想具体内涵的民俗映照式影响。
诱因式影响,是从佛学思想成因的更深处民俗源头发掘,沿着文化特质和文化氛围两个主要方向进行探究。首先就地域民俗文化环境来看,独树一帜的水乡文化培养了丰子恺对佛教思想的最直接的感性认识。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各地域文化凭借自身的文化特质屹立一方,竞相繁荣。江南水乡的通行解释是长江以南地区,以江浙等地为代表,其中包括丰子恺的出生地嘉兴。江南地区给人的文化印象大概就是戴望舒《雨巷》中那个撑着油纸伞彷徨在悠长雨巷中,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正如贾宝玉口中“水做的骨肉”一般。这水性蕴着诗意和绵绵无尽的情感,恬静而又温柔,既是天下之至柔又可驰骋天下之至坚,于柔美中带着一丝坚韧。丰子恺佛学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内因是其性格上多愁善感,灵敏敛韧,喜爱苦思冥想,这一点与其所处的地域民俗文化环境的文化特质相契合,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致有这方面的意味。
“吴越地区历来就有‘崇巫信鬼’的传统,其恪守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可说是与生俱来...因此持斋、烧香、念佛是很普遍的事情。”[8]这种世代相传的心理积淀,成为人类十分宝贵的遗传基因,因此丰子恺耳濡目染受到民俗文化的熏陶。散文《四轩柱》中详细描述了“谢菩萨”;《新年忆旧》中描写了人们在除夕夜半时,要进庙烧头香的过程;《放焰口》记载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之夜,为了超度亡灵,“普济孤魂”集资办佛事名曰“放焰口”[9]“放焰口”的重点是和尚做法事,潜隐着因果轮回之观念。 《清明》中指出清明又称寒食,石门湾一带当时有“清明大如年”的说法,清明扫墓是对祖先的追忆和崇敬“祭扫完毕后顺便到附近的三竺庵游玩”[10]。《元帅菩萨》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五月十四日,元帅菩萨迎神赛会的盛况,“让老百姓笃信不疑,由此可见当地宗教信仰活动的兴盛”[11]。在民间信仰活动中,人们期盼的是心灵有所寄托和生活的美好。字里行间,让我们享受着石门湾人敬畏天地神明的淳朴人性美。由此可见,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蕴藏着如潺潺溪水般的力量在骨子里流动,给予脑中思想一浪又一浪般的新鲜刺激。我们常说的文化环境影响归根究底是文化环境下的文化氛围的影响,文化环境是一种经长期历史积累客观存在的外在条件,而文化氛围则是这种环境下抽象的存在,有时似乎没有实在的形体,唯有依靠纯粹的本心体悟才能够进行感知。江浙地带丰富的民俗文化形式和内容给了丰子恺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广泛的思想基础,为以后佛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石。
如果说地域民俗文化环境是通过文化特质和文化氛围给予丰子恺的佛学思想塑造施加影响,那么家庭文化环境则在文化品格的形成、文化思想的培养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童年时期,以纯真之心看世界、体悟世界,这种依靠真切直观接触所累积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就如散落在记忆中的斑驳碎片,在脑海中积存形成映照,以待将来在某个特定时期被激活。
丰子恺的祖母可以算得上是丰子恺佛学思想启蒙的引路人。“二三岁上,祖母常带他一起去烧香。有一天午后,他睡着了,祖母便独自到西竺庵烧香去。可是他一醒来就找祖母,傍晚时分祖母背着黄布袋回来,被他撞见了,他一定要祖母重新带他去烧香,但那时候,寺庙的门已经关了。答应他第二天,他一定不依。最后,祖母只得再背上黄布袋,带着他去敲开寺庙的大门,重新烧香拜佛。”[12]祖母和母亲经常进行的烧香拜佛等基础佛教活动以及时常挂在嘴边的善良、慈悲等佛教观念为年幼的丰子恺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并不断渗入思想深处。丰子恺是家中的第一个儿子,在他出生之前家中已经有了六个姐姐,作为丰家烟火得以延续的希望,他自小就是沐浴着爱长大。祖母溺爱他,父母姑姑对他万般疼爱,姐姐们十分怜爱他,就连家中染坊的伙计们也十分喜欢他。在散文《新年怀旧》中,作者写母亲过年请自家染坊里的伙计吃年酒。上菜时一再叮嘱必须把鸡头向着空位,深怕不小心按照习俗辞退了谁。在这司空见惯的信仰民俗中,无形中就接受了母亲爱的教育,在爱中成长的他也让这种爱跟随了一生。“在母亲的保护之下获得了饱食暖衣之后,每天所企求的就是‘看’…现在我还可历历地回忆:玩具,花灯,吹大糖担……曾经给我的视觉以何等的慰藉,给我的心情以何等热烈的兴奋! ”[13]玩具与花灯属于民间工艺和民间美术的精神民俗,丰子恺当时认为的玩具就是印泥菩萨的模型和自己用红沙泥模型印塑的观世音像、文昌像、关帝像、宝塔、狗等等,既开启了他的艺术心门也使他以温柔之心和慈爱之怀去观世间万物,这种爱浸染着他的文化性格。在《取名》一文中述说了二月十二日是当地俗传的“花朝日”,又称百花生日,这一天,人们要祭花神,不经意间传达了众生平等的思想。这种温软和悲悯使他的佛学思想总是弥着化不开的浓浓温情,这种温情也渐渐上升到一种世间群体的高度,为丰子恺佛学思想阶梯攀爬提供了重要的内在因素。在许多普通佛事活动中母亲的放生施舍活动对丰子恺影响较大,丰子恺以佛教的四无量心去绘《护生画集》,历时之长久,画集总集之多,无一不向我们传达着他坚定的护生思想。民间这样一些平常的活动在丰子恺独特的体会和敏锐的思维中逐渐发展为丰富的内涵,将其仁者的大视野,大关怀放在其中。‘护生’的精髓也丰富为“亲和万物,热爱自然,尊重生命,构建人与世界之间和谐的审美关系,包括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诸方面关系属性的改变和完善,使生命的生存更加有序和谐。”[14]自然,地域民俗文化背景和家庭文化背景是无法完全割裂开的。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哪种文化环境或哪类影响都催动着丰子恺佛学精神向“善”的脚步。
仔细研究丰子恺的思想,不难发现,他是个十分推崇感情的人。丰子恺在《绘画之用》中说“人类倘然没了感情,世界将变成何等机械、冷酷而荒凉的生存竞争的战场!”丰子恺始终把情感放在一个最终目的和归属的位置,他本身看待世间万物时总是带着脉脉温情,正因如此,他的体悟中便多了些“情味”。有了情感才能产生悟性,基本上情感是这种独特沟通方式的先决条件。丰子恺人生三层楼的理论将宗教置于高地,那么与物质生活相比,精神世界的丰富才更为重要。回到丰子恺的佛学思想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丰子恺始终认为信佛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慈悲之心和智慧,他主张通过与佛陀的直接对话去学习慈悲和智慧,以期达到自我精神提升的目的。佛家很讲究“顿悟”的感觉,但无论是瞬间的顿悟还是长久的体悟,都是为了进行精神的不断修炼。那么,若想精神世界得到提升就必须不断思考不断体悟或顿悟,可产生悟性的前提是情感,由此可见这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况且对自幼开始就用自己情感探究这个世界的丰子恺来说,情感体悟的方式是精神修炼必备的前提。佛学思想作为他精神修炼的成果,民俗文化作为他艺术世界的本体,二者通过情感——艺术的表达方式相连接,这个纽带灵活且实用,为佛学思想和民俗文化进一步研究架起了一座桥。“艺术家将情感熔化、梳理,然后再表现于作品之中。 让人们发现和感悟艺术中蕴藏的情感,不仅是对艺术家情感的理解,也是与人类情感建立一种联系,以艺术为媒介达到情感上的共鸣”[15]。丰子恺的创作追随其一生,而表达思想情感民俗类题材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漫画都是他创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记录了他的生命轨迹,津津乐道于:石门湾是蚕丝之乡,“老少都穿丝绵”,甚至“乞丐身上也穿丝绵”;石门湾物产丰富,除了主食水稻外,还有菱角、桑树、枇杷等等,应有尽有,“四时蔬菜不绝,风味各殊。”[16]“夏天,门外刚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来了一担‘桐乡醉李’。喊一声‘开西瓜了’,忽然从楼上楼下引出许多兄弟姊妹。”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坐在太阳旁边吃冬舂米饭...”“傍晚,祖母穿了一件竹衣,坐在染坊店门口河岸上的栏杆边吃蟹酒。”[17]石门湾民居多为砖木结构,黛瓦粉墙。“客船是我们水乡一带地方特有的一种船”[18]。连日常生活中的叫卖声、打桩的号子声、小贩的招揽声在丰子恺看来都是“自然的音乐”[19]。这“关切人生”,“近于人情”[20]的创作,俞平伯称为:“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在丰子恺笔下,衣食住行、岁时乡土、民间杂谈乃至虫鱼鸟兽等无一不可入文且无一不饱含乡愁的可亲,乡土的温情。家乡特有的恬淡而又浓烈的文化氛围也使丰子恺的佛学思想蒙上了一层诗性的面纱,平添了几分禅味。“与民国佛教期刊中僧信作者比较明确的入世或出世立场有所不同,居士作家作品多见世间生活与出世间体验的对话、并置、转换与融合等,既有从佛教视角对现实生活的谛观审视,亦有从世间生活吸纳佛教智慧的意味”[21]。在丰子恺笔下充斥着大量让他难以忘怀的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当然,作者所观照的对象并非对象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而是这种生命气韵和人格精神所传达出的生命价值。在平凡却滋养了我们秉性的民俗中领悟对生命的态度,达到“物我一体”的人生境界,这才是丰子恺对“人间烟火气”——民俗文化“盎然兴致”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