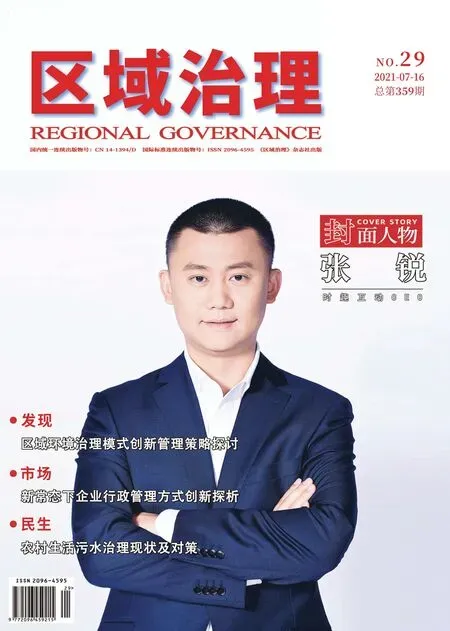商业方法可专利化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李想
一、商业方法概念以及与商业模式辨析
商业模式本质是管理者管理企业的重要工具,也是企业经营的核心。很多学者喜欢将商业模式和商业方法混为一谈,但是商业模式与商业方法在内涵上有本质区别。商业模式是经营者把自己依据市场信息做出的智力决策应用于企业经营之中,是对商业规律的总结,是一种思想活动,因此属于专利法中规定的不予以保护范畴。然而互联网背景之下的商业方法已经跳出智力活动的范畴。欧洲专利局将商业方法的定义为关系,这种关系是涉及人和社会与金融之间的,具体而言可以是产品分配的方法、服务方法等。传统意义上对商业方法的定义都是从将其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之内的角度,客观上商业方法被定义为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且能够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商业活动的基本准则,是人类智力劳动的成果[1]。
二、商业方法可专利化的原因
(一)商业方法的演进
我们现在所讲的商业方法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将商业活动中的规则方法记录下来,商业方法也在跟随着互联网发展而进步,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归纳,多是借助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处理系统有关的发明创造。法律通常具有滞后性的特点,为了紧跟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特征,近些年对待商业方法是否可专利化的问题上我们国家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立法工作者也开始认识到了商业方法于企业、于市场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国家从一开始的完全不承认商业方法的具备可专利性特征到多次修订《专利审查指南》,逐渐对含有技术特征的这一类商业方法进行承认,虽然商业方法的特征就是包含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但是同时它也有可以区别于其他商业方法所特有的技术特征,因此不应该被排除在专利法保护的范围之内。大数据时代的进步,互联网+模式等各种新型模式的出现,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方法具备了鲜明的技术特征,同时又密切结合了其本身的商业方法特征。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与技术特征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解决某一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并且能够获得相应的技术效果[2]。在实质性审查的进行过程中,通常将商业方法的方法特征和技术特征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新颖性以及创造性的审查。
(二)法律基础
2019年版的《专利审查指南》规定了包含技术特征的商业方法可以成为专利法保护的发明专利客体。进一步明确涉及到商业方法的专利申请中,不会因为该商业方法是应用于商业领域而不是传统的工业领域就不受到专利法的保护,对于判断该商业方法是否真正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则需要客观评判权利要求中是否包含技术特征。这其中对商业方法的保护最大的进步在于,一个权利要求同时包含商业方法和技术特征时,不仅整体受到专利法的承认,对其中包含的商业模式也可以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但是依据专利法规定,专利的客体必须由法律规定予以确认,也就是意味着专利权所保护的客体的增加、减少和变更都只能通过修改专利法来完成,与此同时我国《立法法》第80条也明确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据和授权之下,部门规章不能自行增加本部门的权力。然而我国目前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仅仅是通过修改了专利审查指南就将商业方法纳入了专利法保护的客体,这意味着专利行政机关也没有遵循专利客体法定这一原则,没有按照法定程序提出议案,某种意义上违背了立法法的规定。
(三)保护意义
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市场潜力的重要标准是他的商业方法运用是否发挥到最大效用,由于这种商业方法本身的易复制性、模仿性,非排他性的特点,创新者主体利益容易被他人免费分配。我们国家一再强调创新的重要性,我们对创新主体的利益不保护,又如何激励他们进行再创新,如何维护大数据时代下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传统专利法的利益分配原则本身也是为了鼓励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而生,我们制定专利法的价值目标就是将垄断权赋予专利权人,保证专利权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发明创造获得相应的激励,从而鼓励他们可以继续投入新的知识产品的创造,形成良性循环,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共同的知识财富,将商业方法纳入专利法保护的范畴本身也是对互联网模式下专利利益再分配的一个表现[3]。
三、我国目前对商业方法保护的不足
(一)专利审查周期过长
商业方法依托于互联网的模式决定了他可以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在商业方法为了满足用户需求,不断地更新的同时保护权利人的商业方法也十分困难,一边改进商业方法,与一边申请专利保护的商业方法做不到同步,由于专利在进行实质审查的过程十分漫长,要审查的内容对于商业方法专利来讲也过于繁杂,往往经过专利局最终审批下来,获取专利权的时候,下一代的商业方法也已经更新换代完毕,这样一来,商业方法申请专利的目的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保护商业方法的初衷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实质性审查过于严格
商业方法的创新大多数是以运营方式来表现的,这种技术方案的创新虽然是商业方法的载体,但是专利法中对于包含技术特征的技术方案要求十分严格,进行实质性审查过程中,多数商业方法通常会因为不具备“技术问题、技术手段、技术效果”技术三要素被驳回,但是在权利要求书的撰写过程中,对这些非技术特征的描述不可避免,毕竟这些才是多数商业方法的创新点所在[4]。
授予专利权时,对具有创造性的要求是应当与现有技术相比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一些对于现有发明创造做出的微小改进也可以适用实用新型予以保护,可见我们对发明创造的保护要求是相对合理的,但是在涉及商业方法的创造性审查中我们只能针对其技术特征判断是否具有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这样我们会忽略商业方法中主要的创新的非技术特征的部分,并且涉及到商业方法一些微小创新的问题上,往往会因为不具有创造性而被驳回,但是通常这种商业方法会为了用户更好的体验去做细微的改动,从而无法出现较大的技术性突破,这种情况下,这一类细微的商业方法创新就不符合发明专利的创造性审查标准,也不能获得保护。
(三)维权意识淡薄
商业方法的专利化保护不足在于这些中小型企业的专利保护意识十分淡薄,对商业方法专利进行有效的保护第一步不是国家制定如何完善的法律规范,而是权利人本身有明确的产权意识,发明人与企业要积极参与其中,否则,这一切也只是空谈。企业前期投入大量时间金钱成本研发商业方法,研究出这一技术方案之后申请专利,后期如何维护自己的专利权,以及每年的专利风险分析,这些都需要企业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运营部门,现实中,大部分企业将核心重任分配在财务以及业务上,对知识产权的维护不屑一顾,一旦遇到涉及专利侵权维权问题,则不堪一击。
四、解决措施与建议
(一)合理构建商业方法专利制度
商业方法的保护不仅关乎企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也不仅仅是体现在法律方面,它与国家利益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作为互联网较为发达的国家,商业方法的专利化保护是电子商务时代的重要走向,我们国家目前对商业方法的保护现状在专利法中没有详细规定,只是修改专利审查指南允许包含技术特征的商业方法成为专利法保护的客体,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专利客体的法定原则,专利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考虑通过修改专利法,增加专利法保护的客体,给商业方法的合理保护构建法律制度[5]。另外我们虽然多次修改专利审查指南,承认了具备技术特征的商业方法可以进行专利保护,但是对于具体商业方法中的技术手段如何实现仍不清晰,导致专利审查过程比较混乱,将来的专利审查指南还有许多细节完善。
(二)放宽实质审查标准
对商业方法专利不应一味地适用发明专利的审查时长,要因地制宜的制定符合商业方法专利的申请制度,从实质审查来看,对商业方法发明的技术方案审查标准适当降低,过分严格的要求商业方法专利像发明专利一样具技术三要素,必然会打击对商业方法专利的保护,我们依据商业方法专利快速、简便的特征对其适用恰当的审查标准予以保护,商业方法核心通常在于这种非技术特征,我们也应该适当借鉴美国、日本对商业方法的保护,将商业方法中非技术特征的创新点也予以认可[6]。
五、总结
纵观国外对于商业方法的保护模式,他们都经历了由一开始的限制保护到放开保护再到限制保护[6],我们国家目前对于商业方法的保护处于一种逐步放开的状态,但是对商业方法相关专利的相适应的具体审查标准以及专利法的规定尚不完善,诸多企业对待商业方法专利也不重视,国家或许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完善立法鼓励这些商业方法专利的权利人积极申请专利,保证创新不衰竭的同时促进社会进步,合理分配有关商业方法的利益,实现社会领域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