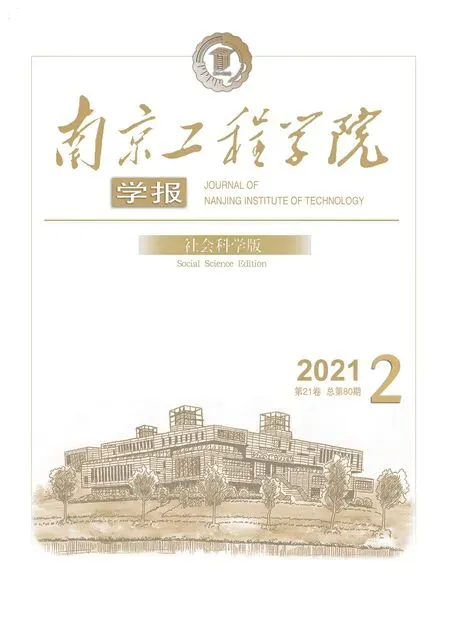藤田嗣治与常玉去国前后经历之对比分析
徐泳霞,袁 平,张燕飞
(南京工程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211167)
20世纪初的巴黎,艺术市场活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他们身为异乡人,在画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忧郁、漂泊感,带着强烈的抒情味和独特的乡愁,这种“表现”意味不同于当时欧洲的表现派,后人统称其为“巴黎画派”。在他们当中,除了犹太血统的莫迪利阿尼、夏加尔等之外,还有一些东方面孔,如来自日本的藤田嗣治和中国的常玉。
藤田嗣治(1886—1968),1913年来到巴黎,常玉(1901—1966),1921年到巴黎,两人此后与故国的联系都很少,几乎所有的艺术生涯都与巴黎相关。然而藤田生前是巴黎的宠儿,被认为是“二战前获得世界承认的唯一的日本画家”,也是后来所有想去欧美世界驰骋的日本艺术家的最大偶像,至今其生活和艺术仍为日本人津津乐道。常玉生前,对法国而言,只是一个不算出名的中国画家,是体制外的存在,对中国而言,除了两个朋友邵洵美和徐志摩在报纸上偶尔介绍外,在王震编写的《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中,与常玉相关的仅有一条[1]。1966年在贫困孤寂中去世后,他似乎遭到身体故乡和艺术故乡的双重抛弃,直到20世纪90年代,因台湾收藏家的关注,才渐渐重回人们的视野之中。
从表面看,藤田和常玉都是东方面孔,作品中都带有东方因素,都住在蒙帕纳斯,都曾有法国经纪人,都曾将作品送入作为重要现代艺术事件发生地的“秋季沙龙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生前身后出现巨大差异?学界一般都从他们作品的艺术风格进行对比。笔者认为,风起于青萍之末,两者的差异,早在他们去巴黎之前就已经产生,故本文将研究定位在他们前往巴黎的前后,从留学的基础、求学过程等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他们绘画背后的蛛丝马迹,希望能从其他角度寻找出原因。
一、留学之前,是否做了相应的准备
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成为日本政府乃至民众的狂热追求,不仅体现在政治体制上,也体现在文化教育上。1876年,工部美术学校诞生,开始推进西方式学院派美术教育,此后洋画洪流逐渐在日本泛滥;1889年冈仓天心创东京美术学校,赴法留学的黑田清辉自1893年起便在此执教,把印象派的外光画法引入日本,其时关于东西方画法孰优孰劣、在巩固日本美术的历史和吸收西洋美术的精华之间如何取舍等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连美国人E.F.芬诺洛萨(Earnest Fancisco Fenollosa)都参与辩论。
1907年,当21岁的藤田考入东京美术学院学习油画时,日本正处于美术现代化的新起点。藤岛武二、黑田清辉油画中呈现出的浪漫情调和装饰风格“标志着日本对西方油画的消化和民族油画的初步建立”[2]。藤田既看到日本的浮世绘燃烧起了包括莫奈、梵高在内的一批西方艺术大师们的热情,同时也领略到日本对西方的憧憬,对日本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间的碰撞融合有切身的体悟。此时他也开始学习法语,为去巴黎做初步的准备。
中国则是在戊戌维新后,“中学”“西学”的冲突才在上层社会中引起争论;至于西方的艺术学习,在1920年以前,只有一些零星的私人美术学校,如周湘1911年在上海创办的中西美术学校、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国立美术院”,此刻国人对油画的认知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及日本。
比藤田小15岁的常玉,出生于中国四川顺庆(今南充)的一个富裕纺织之家,1913年开始随父亲学习中国画,同时师从四川知名的书法家赵熙习字。中国历来有“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传统思想,估计那时常玉并不会以绘画作为他一生的职业追求,认为所谓练字练画与古文学习一样,不过是修身养性罢了。1918年—1919年他曾在日本进行短期观摩,书法作品还曾经刊载于日本的杂志,说明此期他关注的依然是与中日都有关联的传统书艺。他与油画相关的经历,根据其友人王季冈的回忆,是受到赴日归国时暂居上海那段时间的影响。当时因刘海粟提倡人体写生而沸沸扬扬的裸画风波尚未停歇,常玉由此想逃脱国内的保守之风。从这个风波看,中国人包括常玉在内对油画的认识尚处在非常粗浅的阶段。直到1929年,常玉认识了赞助商侯谢(Henri-Pierre Roche)之后,在他的鼓励下才开始使用油画原料进行创作。至于法语,常玉自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笔者并没有看到他在出国前有学习过法语的经历,然而通过他在20世纪30 年代写给经纪人法兰寇(Johan Franco)的信件中可看出,他的拼字和文法还不时出错,但对法国俚语的运用则比较熟练,这或许可以说明,常玉有关法语的学习可能是来自于巴黎实际生活的耳濡目染。
显然,在去巴黎之前,藤田所做的功课要比常玉扎实,这也为他迅速适应和融入巴黎的艺术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到法国时,藤田27岁,常玉20岁,在阅历、心智、对人生的把控上,藤田应该也更为老到。
二、初入巴黎,是否认知欧美美术世界规则
到了法国之后,藤田嗣治第一天便迫不及待地跑到蒙帕纳斯艺术家云集的圆顶咖啡屋,第二天又参观了毕加索的洗衣船画室,看到了卢梭和毕加索的画,心灵受到撼动。他说:“我至今为止在美术学校学过的画,实际上只有一两个人有限的画风。绘画应该是自由的。”他对自己在日本学校接受的古典技法和印象派技法的训练产生了怀疑,不久,他就与莫迪里阿尼混熟,并视后者为精神偶像,至死不渝。他一边研究这些巴黎画派的先驱者,一边到卢浮宫学习文艺复兴大师的人物塑造,同时决心用埋头创作来寻找创作的自由。从他1914年到1918年的画作可见,他开始尝试多种风格,既有立体派风格,也有表现派风格,甚至还有欧洲中世纪的圣像画风格;从题材上看,他不仅画现实中的人物,也画风景画,甚至也尝试宗教题材。他为自己的一点点进步和创新而欣喜,曾在一张巴黎城门的画幅背后写上“开心之作”[3]。
通过日本浮世绘在西方“成名”的经历,藤田隐约地意识到,正因为有了莫奈、梵高等大师的借鉴和演绎,浮世绘才得以进入西方艺术的脉络。作为一个异乡人,遵循西方艺术世界的游戏规则是第一要义,在此前提下,还得有与众不同的新花样。于是他试图将日本艺术的装饰性、大面积留白、墨线等特点引入油画创作。在巴黎浸淫、磨砺近10年的时间后,在20世纪20年代,他拿出了一系列裸女题材作品。他最具代表性的《五个裸妇》(1923年,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藏)画面尺幅达169厘米×200厘米,画中无论是地板、花布、人物造型无一不精准描绘,人物身上神秘莫测的乳白色肌肤和长长的墨线轮廓带有深深的东方韵味,而画中人物的冷漠、淡淡哀愁也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应该说,这时候他画中的日本风,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来借鉴日本艺术的,与马蒂斯的原始美洲风、毕加索画中对非洲木雕风格的借用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他看得更真切,技法用起来也更具日本味。正因如此,这件作品一经展出便大获成功,村上隆从藤田的成功中总结:“必须在欧美世界规则中构筑次文化”“不依循法则的作品在欧美只会是规则以外的‘物体’罢了”,必须“将日本独特的文化体系植入欧美美术史的脉络”[4]61-80。与此同时,藤田一反留学之初的西装革履和小分头打扮方式,对自己的形象做了刻意的设计:蘑菇头、圆框眼镜、圆领长袍、上嘴唇的一撮方形小胡子,特立独行,最大程度地让人记住他。这种树立个人样式的自觉并不逊于西方任何一位善于营销自己的现代派大师。巴黎的艺术圈和观众为他的技法和画面所折服,又能一眼认出他,他迅速成了艺术圈的宠儿。
比藤田晚八年到巴黎的常玉,从小在家接受私塾教育,没有进过任何的公立学校。初到巴黎,也没有进入公立学校,唯一出入的是私立大茅屋学院(La Grande Chaumiere)。关于常玉在大茅屋学画的过程,庞薰琹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用毛笔画速写,很多人认识他,他一来很多人围绕着他,……他专画全身女像,十分钟左右就可画好……我想他在巴黎十多年大概就是这样生活。”[5]与藤田一样,常玉也选择从裸女题材入手,他画出人物的各种动态,简练概括,后来也略用水彩表达。在巴黎的前十年,他画了近两千幅这样的速写,也曾引起一些关注。他也采用了自己擅长的东方方式,用毛笔勾勒人像轮廓,但与藤田对人物面部的精心刻画不同,常玉笔下的裸女是中国文人式的逸笔草草,脸上也没有细致的描绘。如果说藤田笔下的裸女眼睛直视观众,与提香、戈雅、马奈等大师所画的斜倚的女人一脉相承的话,那么常玉笔下的裸女目光则是闪躲的,不与观众交流的。因此,他的裸女,虽自有吸引人的因素,但由于没找到与西方艺术脉络的接触点,而让西方人捉摸不透。毕竟,对中国艺术的认知,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比如亚洲艺术的大收藏家Emily Guimet先生在“居美馆藏中国绘画展览”序言中写道,“中国艺术家就是印象派的画家,他对人物的要求就是动作,对风景则是空间”,以他频繁接触中国绘画的资历尚且只能如此简单定论,更遑论其他人了。
但常玉并不想抛弃他的中国风,在他以后的油画中似乎表现得更为强烈,一如费正清评价的那样:“甚至最洋化的中国人也不会丢弃其具有中国特点的意识,在海外居住反而会增强这种意识。”[6]在油画创作中,他用漆雕的色彩和手法,他用陶瓷上剔花的手法,他甚至还采用画像砖和中国壁画中榜题的形式写上“人约黄昏后”“北京马戏”等标题,这让西方人更加迷惑了。一位荷兰评论家的评价也许代表了普遍观感:“他以中国书法家般敏锐的手在厚厚的油彩中刮出了花篮或战马的线条,……但却看不出来他何以需要想仰赖油彩来完成他的创作意图。”[7]他后来在法国、荷兰、纽约举办的几次个展基本无人问津。吴冠中说:“常玉是巴黎花园里的东方盆景,巴黎的盆景真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卉都想在巴黎争奇斗艳。”以盆景类比,或许是对常玉并未能在巴黎花园里扎根的恰当隐喻。
三、能否跨越挫折是分歧点
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去留学,大部分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生活、学业、心理上的困惑与挫折。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挫折是留学生能否在异国他乡立稳足跟的关键。藤田嗣治到巴黎没多久,就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和法国的通信中断,家中的经济供给也随之中断,没法继续到学校学习,他便更多地流连于博物馆,参观临摹,与别的东方艺术家游学后回国发展不同,他立下宏愿:“我选择直接在画坛主场——欧洲,与大家竞争。”挫折反而增强了他的好胜心,他神秘的描绘乳白色肌肤的方式以及墨与油画颜料相融的技法都是在这一时间段解决的,藤田为此做了无数的实验,其中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常玉的长兄常俊民在家乡开设丝厂,获利颇丰,他比常玉大37岁,对幼弟非常宠爱,对其留学也是无条件支援,这让常玉在巴黎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到乡间旅行,演奏小提琴,打网球,在咖啡馆消磨时光,观察和速写周遭的人群。”[8]18他的大部分速写都完成于这一时期,他也想获得巴黎的承认,但他对待艺术的态度是贵族文人的“游于艺”式,并不指望靠它来养活自己。他选择留在巴黎,更多是因为向往这里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然而,“在欧美,艺术是人与人的战争。世界水平的胜负,原点要从个人欲望够大开始。”[4]65企图心不够大,仅凭浅尝辄止式的自娱自乐,在异乡出人头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常玉对很多东西的态度似乎都是这样,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曾经发明一种游戏。去过法国网球协会,但事后却无下文。”“我将他介绍给一位在杂志工作的朋友,以便做不定期的连载。这次也一样,后来也没下文。”[8]2841931年,当长兄去世、家里的供给断绝后,他就常常处于贫穷的边缘,绘画得不到期待中的重视,他变得消沉,最后对乒乓球、网球的兴趣更高于绘画,甚至不愿跟人谈绘画。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是阳光文化,他强大的辐射力使其国民具有大国意识和唯我独尊的心态,体现在常玉身上,是其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精简纯熟的毛笔线条和孤冷清高的意蕴;而日本的文化是月光文化,地处岛国带来的忧患意识使得国民不断吸纳和改造外来文明,体现在藤田身上,便是不懈努力以适应世界,即使在巴黎取得很大成功,终其一生,他在绘画的题材和技法上都不曾停止突破。
当然,将两人相提并论,并非苛求常玉,只想从中得些经验。与常玉和藤田嗣治同时在巴黎画坛寻求生机的,仅日本就有500人之多,真正在巴黎画派中成为翘楚的也就藤田一人。常玉作为民国初期的文人,选择现代艺术,选择在巴黎打拼,远比一般人开放开明,而他将自内而外渗透出的传统中国味与西方现代艺术对接的尝试,不但启发了后来者,最终也使得他自己被重新评价。
——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