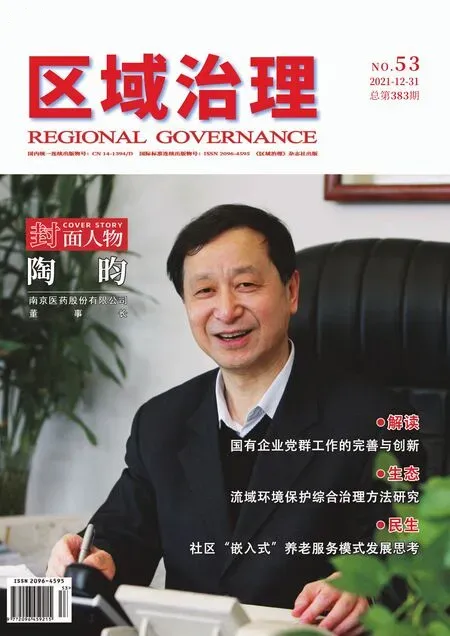家庭社会学视角下农村弱势老年养老困境研究
天津理工大学 王翎怡
一、问题提出
中国历来追求孝文化,小农经济下,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令男性获得了优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养儿防老的思想也因此根深蒂固,甚至在步入小康社会的今天依旧存在这种观念,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社会转型、人口老龄化、农村人口流动加快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空巢老人、留守老人数量与日俱增。有学者指出农村老人在生活困顿、赡养缺失、病痛难忍、精神孤寂等情况下可能会以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这种消极心理最有可能出现在失能弱势老年群体身上。在探讨如何应对日益加剧的农村老龄化进程时,一是要认识到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及其给养老照护带来的挑战,二是要关注弱势老年群体的情绪和心理调适。
本文认为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平逐渐提升的背景下,农村弱势老年群体的需求已从基本物质需求转变为精神或心理需求,相较于物质,他们更渴望得到更多的情感关怀,这种关怀的汲取渠道具有多样化,一般来自子女、配偶、兄弟姐妹或是邻里,这些社会关系都能为农村弱势老年提供一定的情感关怀服务。
二、弱势老年之痛:家庭养老的代际支持弱化与老年孤立处境
学界有关家庭养老的研究不乏少数,何为“家庭养老”?穆光宗将其解释为“由家庭成员来提供养老资源的养老方式和养老制度,是子女养老和在家养老的结合”。也有学者从养老内容上将家庭养老概括为以血缘为纽带,由家庭或家族成员对老人提供衣、食、住、行及送终等一系列生活安排的养老方式。不论是哪种定义,其实质都是家庭成员与老年人之间的代际责任关系的概括。本文认为,目前农村大部分家庭类型基本上已经从主干家庭或者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过渡,家庭类型的转化导致养老方式的变革。一般来讲,健康老年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日常生活基本不成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农村患有重疾、失能、失智和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养老问题,这群人才是农村养老照护的最主要的问题所在。分析农村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理解农村弱势老年的处境。
(一)代际照护
首先是子女之于父母的照护。通常有一定劳动能力、能进行自养的可称为健康老年。在农村,一般通过“逢年过节送礼”的形式提供物质支持,以常回家探望的形式提供精神慰藉,父母通过看护隔代子孙的方式回馈子女。健康的农村老人能在经济和生活上向子女提供帮助,因而代际互惠表现得比较明显。但当家中老人发生意外或情况特殊,比如患重疾或失能,如果膝下儿女较多,承担医药费和陪护照顾尚可,倘若独生子女或者无儿无女的家庭遭遇此等变故,这类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将会陷入艰难的局面。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首先是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中的作用较小,认为女儿一旦出嫁就不再属于家族成员,女儿在外嫁之后受夫家家庭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对原生家庭的贡献逐渐减少。其次是隔代子孙,通常情况下赡养和照顾老人由子女辈担当,极少情况下会落到孙系辈,但因父母外出务工等原因,隔代子孙不得不承担起赡养义务。总之,在直系家庭结构不完整、女儿偏多的情况下,农村弱势老年人的养老处境艰难。
(二)姻亲照护
以家庭为单位提及养老问题时会很自然地向子代的责任与义务上靠拢,但是构成家庭基本结构的除了代际直系血亲,还有姻亲关系,也就是配偶,儿、孙媳和女、孙女婿。从情感需求上来讲,老年人最需要的是来自配偶的照顾,双方健在的情况下是一种互助互惠的关系,尤其是在农村,有些体力活是女性老年人无法完成的,这里会体现出女性老年人对男性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依赖,农村女性老年人通常承担做家务和处理家庭琐事的任务。在照护老人的事务中,儿媳这一角色的争议很大,自古就有“婆媳矛盾”,儿媳照顾夫家双亲可以从两方面考虑:第一,农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搬离农村在城市居住,儿媳与夫家情感上愈加疏远。第二,小家庭运作的压力,比如无暇兼顾上班和照顾年幼的孩子。换言之,姻亲的照护地位甚至不低于血亲的子女,且配偶的地位难以取代,所以弱势老年的照护质量受姻亲关系影响颇深。
(三)手足照护
在亲属关系网络中,手足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因素,手足指的是兄弟姐妹,在农村,大多数兄弟姐妹居住的空间距离比较近,各自往返占用的时间和成本较小,联系情感也较为方便,因而手足在老年照护中起到一定作用。在老年人身体状况良好、自理能力强的条件下,手足之间的互惠是存在的,而当有一方身体出现问题不能劳作甚至不能自理时,手足能提供的照护的局限性就颇为显露出来,一是只能在家庭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提供有限的经济支持,二是以探望老人的方式居多,而对老人的照护偏少。
(四)地缘照护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像水的波纹一样逐一向外层推开的”。从“差序格局”的内涵来看,最贴近于血缘关系的是地缘关系,包括邻里之间的相互照应。河北省肥乡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就是基于地缘关系发展起来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一种,这种依托“外侍”的非专业照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照护功能不足的短板。但是,这种模式缺陷也较为明显,即这种模式在失能、失智和重疾等生活不能自理的农村弱势老年群体这里行不通,健康老人可以通过互助和邻里关怀进行养老,而弱势老年则需要更精细、更专业的照护,因此弱势老年只能被其排除在外。
总的来说,农村的弱势老年群体养老处境还是相当危险。依靠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是一种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和道德内涵,但不得不说,这种依靠传统伦理维系的家庭照护功能的弱化无疑又将养老照护推入新的困境之中。受家庭结构、亲属支持和地缘支撑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弱势老年群体缺乏良好的生活照料和护理,贫困家庭更是面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此外,除了分析养老服务供给侧的结构以外,还应关注老年主体的需求和心理。在长期生理残缺和不适并且得不到有效关怀下,老人既有可能会出现负面情绪甚至精神疾病,因而关注弱势老年群体的心理对解决养老困境必不可缺。
三、拯救弱势老年:融入与关怀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上某些特定成员遭到多元不公平对待,处于“边缘地带”即与主流社会和社会资源相隔离的弱势群体地位。老年人身心机能退化、收入微薄、消费节俭和生活自理能力弱,在这些方面与年轻人天差地别,老年人的需求满足和福祉程度远低于年轻群体,老年群体极有可能被其他年龄层排斥,正是由于年老后的“累积性剥夺”现象导致老年群体弱势地位的形成。在庞大的老年群体中,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是最需要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在乡土社会中“老而无用”的观念已然成型,尤其是失能失智等“生活累赘”,在生活的压迫之下,现实战胜了情感,亲情最终屈服于“无情”,弱势老年群体成为最容易被抛弃和被放弃的群体,弱势老年危机也因此赫然显现。
近些年,我国养老事业发展如火如荼,专业养老护理员、养老院以及日托服务等为失能老人提供了多样化的社会养老选择,为无数失能家庭带来了福音。然而,除了民办养老机构自身缺陷外,民办养老机构在农村的发展也是举步维艰。李伟通过对河南省的实地调查指出,目前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存在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积极性不高、行政审批繁琐、设施设备简陋、养老护理员难招以及管理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在养老资源供给方面,农村地区远不如城市,况且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拉大,中低等收入家庭根本无法负担起失能、失智老人的长期托养和专业护理费用,重疾老人甚至还会给普通农村家庭带来返贫危机。农村“未富先老”已成不争的事实,国家和社会一直将目光投注到农村养老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推广上,弱势老年的心理和养老需求长期备受冷落,农村家庭养老的地位也不受重视。然而,本文认为农村弱势老年的真正困境在于代际支持和养老需求得不到满足之间的矛盾。现阶段,老年人正逐渐与社会、家庭脱节,“回到家庭中”是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是立足于家庭、发展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是不二选择。
弱势老年人地再融入最需要的是家庭成员的配合。当家庭因照料老人的负担减轻之后,才能够将目光聚焦于照顾老人的精神需求和情绪变化,老人也能再次感受到亲情的关怀,心理得到调适的老年人需求更容易被满足,生活满意度较高的弱势老年更倾向于表现出积极的养老心态。因此,在着眼于经济保障的同时也要注重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生理和心理同时得到满足时养老难题才会迎刃而解。
四、结论
从农村老年人口变动情况来看,高龄、失能、慢性病、空巢和失独老人数量逐年增多,这部分老年群体处于弱势地位,更应该得到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老年人获取社会支持的路径一是通过国家制度性的社会保障措施,二是通过血缘照顾和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家庭是老年人获取情感支持的根本来源,家庭结构不合理、代际支持弱化往往会阻断情感的传递,在生理机能衰退并处于社会的边缘处境中,得不到亲情的关怀和慰藉,老年人极有可能滋生心理问题。在社会化养老的大趋势下,弥补家庭照护功能的不足同样对于缓和老龄化压力至关重要。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生育率持续走低,家庭养老的功能不断弱化,而农村社会养老发展还不够健全,且对农村弱势老年群体并不“友好”,农村弱势养老群体的养老仍然仰仗以土地为依托的家庭养老,而家庭养老处于弱化阶段,农村弱势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或如何让家庭养老“重获新生”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仅从经济层面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医养结合以及培养专业化护理人才是不足以解决当前农村弱势老年养老照护困境,因为社会养老自身缺陷无法满足农村弱势老年群体更为精细化的需求。因此还是得从农村弱势老年群体的家庭照护、从弱势老年的养老需求与代际支持之间的矛盾入手,关注被忽视的老年人心理调适和重担下的家庭功能弱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