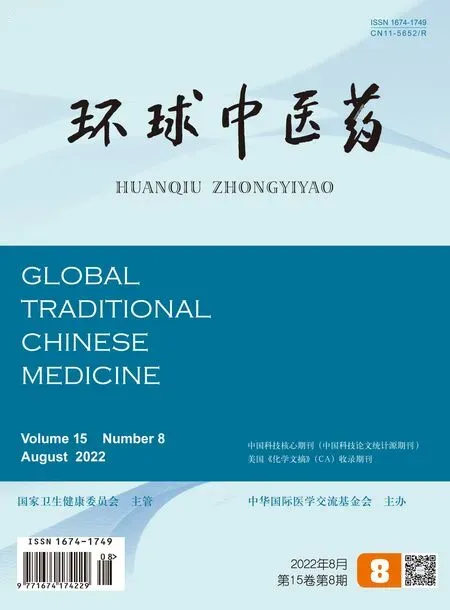陆廷珍《六因条辨》学术思想及特色探析
孙小梅 张津铖 程志强
陆廷珍(1821~1884年),字子贤,清代道光江苏崇明县人[1],其学术思想深受前贤影响,本于《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之说,遵“治病求本”“审证求因,审因论治”和王冰“得其机要则动小而功大,用浅而功深”之论,宗于《温热论》等之旨,借鉴吴鞠通《温病条辨》之名,诊余撰写《六因条辨》一书。《六因条辨》成书于清代道光时期,是陆氏考古贤之方书、审时人之病情而作的一部时病专书,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总列条辨180条,融汇伤寒、温病各家思想,以因为纲,以条为目,条分缕析,对春温、伤暑、秋燥和冬温等时邪进行阐发,可谓“简而明,约而赅”。但陆氏师古而不泥古,并不偏执一端,其以风、寒、暑、湿、燥、火六因为纲,对于时症的病机及其演变和诊治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陆氏《六因条辨》博采众长的学术观点不仅促进了后世论治温病时病的发展,亦对当今医者诊疗思路和临床思维的塑造有着深远意义。然而此书翻刻不多,更不及叶天士等温病四家所著影响深远,未能得到业内充分的重视和应用,但其中一些思想发挥也有诸家所不逮,兹就《六因条辨》一书探析陆廷珍的学术思想。
1 主张伤寒六经辨证与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相融合
1.1 伤寒与温病源流探析
“伤寒”病名首见于《素问·热论篇》,表广义伤寒,是外感热病的统称。“温病”一词首见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难经》将外感热病分为:热病、伤寒、中风、湿温、温病,此后“温病”隶属于广义伤寒。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一书中虽对伤寒与温病皆有论述,但总体重寒而轻温。到宋金元时期,刘河间主张“六气皆从火化”[2],提出外感热病初期应注重寒凉药物的使用,温病渐渐从伤寒体系中分立出来。明清时期温病学说则快速发展并渐趋成熟,吴有性《温疫论》开创寒温分论新局面,后温病四大家形成了理法方药较为完备的“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论治纲领[3]。陆氏在《六因条辨》中继承前贤学术思想,并阐释了“伤寒六经”和“卫气营血”的实质,临证主张寒温融合。
1.2 “伤寒六经”定病位
《伤寒论》三阴三阳证治各篇未明确“六经”或“经络”的概念,陆氏遵朱肱“六经”为“足之六经”的学术思想[4],主张用足之经络的生理病理及循行特点来阐述伤寒病证的发生、传变与转归机理,认为“伤寒六经”的辨证实质是用于伤寒病证的定位。如《六因条辨·春温条辨第一》言:“太阳经脉最长,由睛明穴,上额交巅络脑循项,挟脊抵腰入腘,行身之背,至足眼而终。”太阳病见证必“恶寒发热,头痛项强,腰痛足酸”。外感病症皆可据此定位归经,并分经用药。温邪时毒初起,可见颈间颌肿,主方荆防败毒散,但需辨明结在何经,以按经用药:其肿在颔下者,属阳明,以葛根、升麻为主;在耳下者,属少阳,以黄芩、柴胡为主;在颈项者,属太阳,以独活、羌活为主。可见陆氏深得仲圣和叶天士的六经辨证以及卫气营血辨证的精髓,其针对“伤寒六经”本质问题所进行的探讨,打开了后世医家研究伤寒的思路,如伤寒大家刘渡舟就对“经络说”非常认同,这推动了仲景学说的发展。
1.3 “卫气营血”辨病邪浅深
陆廷珍传承并发展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之说,言“卫气营血”辨证本质为病邪从表入里的过程,体现病邪之深浅。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侵袭人体,虽因病邪性质及个体体质不同而见症不同,但其传变顺序均为卫→气→营→血。如温邪袭卫,首见肺经病变,出现头痛身痛、无汗恶寒等卫表之症;邪气渐传入气,进而烦热口渴、舌黄脉洪,此时邪气留于气分;气分未解,邪传入营,热扰神明,可见“舌黄尖绛,昏谵脉洪”“神昏脉数,热已入营”;温邪深陷血分,邪热炽灼营血,迫血妄行,而耗血动血,出现神志异常、狂妄燥急、身出斑疹、脉搏急促之症,是热入营血之征。非独温邪,外感寒邪亦可按“卫气营血”传变。
2 主张以“寒温融合论”辨治外感疾病
古今医家论伤寒皆言“六经”辨治,论温病以“卫气营血”辨证居多,陆氏则主张伤寒六经辨证与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相融合,其言“凡温症,犹伤寒初起,亦先伤阳经,而后传变,然伤寒以六经见症为主,迨传变,而后更分营卫气血”,提出“寒温融合论”,认为“伤寒六经”能沟通脏腑及四肢百骸,脏腑功能及六经气化决定了各经病的症状特点,而循行于脏腑经络内外的“卫气营血”则可反映病邪传变之深浅。
陆氏认为春温病属六经中的阳明病,若在发热基础上又有轻度恶寒、夜卧不安,则是阳明经病,当辛凉解肌,予葛根汤;若不见恶寒,始见口干口渴、恶热、苔黄、脉见洪大,则是阳明气热,当辛寒清气,予白虎汤;若侵犯到营血分证,出现神志不清、狂妄谵语、舌绛苔黑、脉急数,则是阳明血热,当透热转气、凉血散血,予犀角地黄汤;若舌苔干燥老枯,则是阳明腑热,当急下清腑,予凉膈散。以上病证皆属阳明病,但因其病邪深浅不同而有经病腑病和卫气营血病证之分,此不仅适用于阳明病证,六经病都有如此规律,但因各经生理特点不同,故而各经中卫气营血各层次的发病机会有所差异。
再论伤寒“蓄血证”,属血分证,陆氏创新性地提出:“伤寒蓄血,六经皆有,不独膀胱与胸腹之间。”若三阳早期症状兼见鼻衄、吐血、肌衄、咳血等症,则提示邪气侵犯血分,在太阳者应开宣透表,切记勿因见血则妄使寒凉;在阳明者需两清气血,勿因少汗而妄发其汗;在少阳者宜清泻胆络,勿因出血而妄用滋腻。若兼见少腹硬痛、神志异常、谵语狂妄、小便正常而大便色黑,此乃蓄血证,三阳此证虽同为腑病,但病位略有不同,太阳蓄血在膀胱,治以桃仁承气汤,外解太阳、内破瘀血;阳明蓄血在冲脉,治以犀角地黄汤,清解阳明、活血化瘀;少阳蓄血在肝络,治以陶氏小柴胡汤加生地、归尾、桃仁、山楂、丹皮,清化少阳、破淤化滞。至热邪传入三阴,少阴心主血、太阴脾统血、厥阴肝藏血,热与血结聚难分,终致神昏难明、舌红绛,皆用犀角地黄汤加石菖莆、郁金治之;或大便色黑伴随腹痛,可予抵挡汤,两解瘀热。
六经本以阴阳分,卫气营血本以表里分,伤寒虽因其外感寒邪而更适用于六经辨证,但其传变过程亦需分清卫气营血之期;温病虽因温热邪气传变迅速而以卫气营血辨证为宜,但其亦可以症状定位病证之归经,这种“寒温融合观”在现代也被充分发展应用。
3 主张未病先治以截断邪气传变
《素问·四气调神论篇》“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及叶天士“先安未受邪之地”[5]的未病先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外感时病变化多端,陆氏传承并总结外感六淫的传变规律,临证时主张在治疗本位之病的同时,兼以祛除传变下游的邪气来截断疾病向里继续传变之势,达到早发现、早干预和早诊治的目的。
3.1 表邪化热当清气分以防深入阳明
以温邪为例,温病初期,无汗恶寒、头疼身痛,属太阳病,若兼见发热目赤、口渴脉浮数,即邪有从太阳传入阳明之征象,有卫分传气分之倾向,治以“热自内蒸,必兼清凉”,羌活乃太阳之表药,但陆氏注意到此病已有内传征兆,又以太阳之次为阳明,邪气在表,便弃羌活不用,以阳明之表药葛根治之,兼加薄荷、牛蒡子、桑叶以解表,又以黄芩、连翘等清里,陆氏以断太阳入阳明之路为治疗思路,避免出现邪传阳明,病情变剧而成或疹或斑等严重后果。至外感发汗后,微恶寒、头额痛、发热口渴、脉弦长,可知卫分之邪汗后已轻,但气分之热未清,温邪已在气分,形成卫气同病,卫轻气重的情况,故在卫用薄荷、葛根、牛蒡子、桑叶、枇杷叶开泄透表,在气用栀子、连翘、杏仁、瓜蒌皮清宣肺气,以双解卫分气分之邪,以防邪传阳明之腑,而为斑黄狂妄之重症。
3.2 气营两燔当凉血分以防耗血动血
陆氏认为病见烦热口渴、神昏谵语、舌绛苔黄、脉洪者,是阳明气热传营、气营两燔之证,在治疗时其不仅重视“透热转气”法的应用,认为需用泄气分热,清解心营之品,还强调要兼用凉血之品以防邪进一步内传血分。陆氏常加减化裁玉女煎为主方,以知母、石膏清气分热,菖蒲、连翘、竹叶清心营,加用玄参、生地以凉血,最后恐热灼津伤,用粳米、甘草、石斛以养胃阴,杜防痉厥等他变。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明确指出温病治疗急需“截断扭转”的观点[6],如今这种提前截断的思想已在一些皮肤病的诊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
3.3 由邪气传变到肿瘤转移发微
邪气在损伤正气的同时渐趋深入的特点并不仅仅局限于外感病证之中,这种明晰病邪传变规律并提早干预以防止疾病进展的诊疗思路极具深刻的临床意义。笔者团队参考陆氏等众多前贤之论,提出恶性肿瘤之“癌毒”传变亦可被截断,在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及肝癌等病时以“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理论为基石,认为肝脏及消化道肿瘤的患者极易出现脾虚证,即使病人暂未出现纳差、乏力和泄泻等脾虚症状,但治疗仍以健脾益气为核心,团队所化裁出的“调脾安肠方”现为中日友好医院院内制剂,方以党参、茯苓、薏米、山药和白扁豆等健脾益气类中药为主要药物,临床疗效确切。现代研究表明,健脾基础方四君子汤能够通过调节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来抑制结直肠癌发生肝脏转移[8]。
4 辨病为纲,辨证为目,提倡“辨病—辨证一体化”
中医的“病”指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机体出现正邪交争、阴阳失衡、功能失调的病理过程;“证”是对疾病过程中所处特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以及病势等所作的病理性概括[9]。陆氏遵张仲景所主“病下系证,证下列方,方随证出,随证治之”,确立了以病为纲、以证为目的“辨病—辨证一体化”诊疗体系,即将辨病和辨证相结合以充分认识和把握病机与证机,进而确立治则治法和遣方用药。
4.1 辨病为纲,指导遣方用药
临证中有许多疾病的致病因素十分相似,陆氏擅长通过综合分析四诊资料来对这些疾病进行准确地区分,进而把握疾病的共性和全貌,并以此指导遣方用药。如暑热为病,《金匮要略》中有“中暍”却无“中暑”,陆氏诟病后贤诸书将中暑、中暍、伤暑、中热、伤寒等混为一谈,这一局面直至张洁古提出“静而得之谓伤暑,动而得之谓中暑”[10]的观点后才有所变化,但仍未缕析“中”与“伤”的内含。陆氏认为寒有伤寒、中寒之分,暑亦有伤暑、中暑之分。酷夏之际,时人纳凉易被阴寒外袭,闭郁肌表,出现发热恶寒、头身疼痛、无汗、胸闷、恶心呕吐等症,此为“静而得之”的伤暑;暑热难耐,过食生冷,又房劳过度,导致肾阳亏虚,腠理疏松,外在受寒凉暑湿之气,内在伤生冷饮食,出现手足冰凉、胸腹憋闷疼痛、上吐下泻等症状,为“无论动静”的中暑;暑热当头,劳作于外,劳则耗气,元气耗伤,又被烈阳暴晒,出现意识丧失、昏倒在地等症状,则是“动而得之”的中热。盖暑症之来路有三,而治暑之立法非一:伤暑初起为邪袭卫表兼湿邪内蕴,治疗上,宜先汗解,选用香薷,辛温芳香,可解表散寒、解暑祛湿,有夏月麻黄之称,再加杏仁、薄荷、牛蒡子、连翘、大豆黄卷、通草等宣肺清暑利湿;中暑为暑秽直中入胃,以食盐、童便探吐,若吐后,症状有所缓解,用栀子豉汤加杏仁、厚朴、扁豆以和中化湿,若吐泻不止者,可予藿香正气散辟秽理气和中。此外,中热之人需至阴凉之地,并命人小便于其脐周,人即苏醒,醒后予洋参、麦冬、黄连、菖蒲、远志、黄连、竹叶等益气养阴、清暑开窍。
陆氏还将湿邪为病分为伤湿、中湿、风湿、湿温。伤湿则伤阳明之表,即肌肉四肢,故肢体必重,关节必痛,宣气为先;中湿则中太阴之内,即脾阴湿土,则胸腹必满,气机必滞,治以理脾;风湿即湿与风搏,而周身痛楚;湿温为湿与热合,湿热胶结,气机不畅,湿重则气机郁滞,故微热恶寒、身疼痛、胸脘痞闷、小便赤、舌白;湿轻则气机尚能运转,外似无苦,内似无扰,但见神疲乏力、嗜卧难起、脉弱无力等一派虚象,当知“误补之则湿遽化热而病反增剧,误消之则湿留正损而更觉难堪”。张丽萍等[11]指出妇科恶性肿瘤的致病因素往往纷繁复杂,传统的思维模式不能把握其主要矛盾特点,“辨病”的应用不仅能作为中西医沟通的桥梁,还能帮助现代中医明晰疾病固有的传变和演进规律。
4.2 辨证为目,指导加减化裁
同一疾病又可分为许多不同的证候,这是中医学的核心内涵所在,如今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现代医学的研究方向亦逐渐向疾病的进一步细化分型转变[12],这体现出中医学辨证思想的先进性。陆氏注重疾病的临床症状及舌脉的虚实之分,并以此指导方药的加减化裁。肠澼多发生于夏秋之际,腹痛、里急后重为主症,陆氏言腹痛、里急与后重三症皆有虚实之分。腹痛与里急之症,若便后症减,属实证,疏通为主;若便后不减,属虚证,固补为先;而后重之症治法上稍有不同,属实者,宜清泄,属虚者,宜温补。肠澼继续发展,可现闻谷欲呕之症,名“噤口”,最为险候,亦需分清虚实,提出“痢色清淡,口不甚渴,舌白脉软,身无大热,而食入呕恶,此属虚寒”,治疗上以辛开苦降、扶土抑木为治法,药用生姜、黄连、人参、甘草、乌梅、芍药,再以莲子反佐,使汤药入口而无格拒之变;“痢色浓秽,舌黄口渴,脉滑或数,发热痛甚,而闻谷欲呕,此属实热”,治疗上以苦寒攻下、和木畅土为治法,药用黄芩、黄连、白芍、秦皮、山楂、厚朴、大黄、芒硝,佐以车前子、茯苓前后分消,使积去热退而痢止。对于先贤之言——“暴崩暴痢,宜温宜补;久崩久痢,宜清宜通”,陆氏则不盲目遵从,他强调下痢一证,总体以疏通为法,但病有寒热虚实,须随证治之,若寒中有实,须温通兼顾,以附子大黄汤治之;热中有虚,须清补两全,以黄连阿胶汤治之;虚中有积,须通补兼施,以人参芍药汤治之;虚中有滞,须疏中带补,以景岳通解散治之。
辨舌方面强调辨舌之有“地”无“地”。舌苔为胃气熏蒸谷味之气上呈舌面而成,舌苔之有无直接反映胃气之盛衰;同时温病后期必见热邪煎灼机体津液,热退津复则预后较好,热盛津枯则疾病进展,舌象是热邪与津液的盛衰的体现[13]。舌色红绛焦黑,若无苔,是“无地之黑”,由热邪炽盛,灼津伤阴所致,主要矛盾在胃中津液枯涸,宜用复脉汤去生姜、肉桂以防助邪,加甘蔗、梨以助甘润,以扶正为主,旨在甘凉清润、滋养胃阴;若有黄苔甚至老苔,是“有地之黑”,瘀热内结肠腑所致,宜用大黄、元明粉、生首乌、鲜生地、鲜石斛、鲜稻根等味,以祛邪为主,旨在急下泄热而存阴。脉诊方面继承仲景以阴阳为纲的辨脉法[14],注重脉有“肉”无“肉”之分,即脉有力无力。尺泽脉轻取即得,若重按中实有肉,脉形脉势未变软减弱,推按筋骨而得见者名“伏脉”,此因病邪郁闭于内,脉行不畅,而致内伏,属实脉;若重按中空无肉而着筋骨,脉中无气者为“绝脉”,此为气血脱遏,脉中血枯,而致断绝。
4.3 “辨病—辨证一体化”,提高临证疗效
陆氏通过辨病以确定治法用方,如今青蒿素靶向“疟疾”一病的显著疗效即是例证[15],而辨证则以对主方加减配伍,症状的虚实缓急亦可指导组方遣药,其条分缕析,斟酌尽善的学术风格,堪为后学津梁。在现代中医临证中,“辨病—辨证一体化”模式俨然已成为提高临床疗效的利器,而当代医家不囿与此,还进一步发展了诸多之“辨”以充实此治疗模式,与现代医学疾病谱有机地结合,以实现精准治疗。吴旭基于现代医学研究成果,提出以“辨体—辨病—辨证—辨经—调神”之法论治儿童抽动障碍,临床获效显著[16];张丽萍等[11]将“辨证—辨症—辨病—辨机—辨人”结合运用于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收获良好反馈;周正华等[17]提出辨病—辨证相结合尤以微观辨病为要,其针对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提出的“以内辅外”理念能较好地防止疾病复发。值得注意的是,“辨病—辨证一体化”并不十分注重先后次序,对于现代医学诊断不明或诊断明确但疗效不着的疾病,反以辨证为纲,辨病为目常常更能获效。
“辨病—辨证一体化”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亦十分获效。笔者团队在病证结合论治基础上,又增加“抓主症”的方法论治肿瘤。“主症”与一般症状不同,指与肿瘤相关的、最令患者痛苦的症状或体征,如结直肠癌患者的腹泻便血、骨转移或肿瘤压迫引起的疼痛、肝转移的黄疸腹水和肺转移咳嗽咯血等实症或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低评分、体重下降等虚症。笔者团队根据四诊资料辨清主症特点和邪正关系,以确定证候立法“辨证”论治,再针对不同癌种酌情加入二三味抗肿瘤中药,如土茯苓、山慈菇、八月札、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等“辨病”论治。
5 重视肾精封藏,否认伏寒理论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及“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二句被看作是温病病因学说的源头,也是伏气温病的立论之本,凡后世有关伏邪之说,莫不引此为墙宇,加以论证。王叔和所注“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为伏气温病学说早期基本内容,即“伏寒化温”论[18]。后世王冰、杨上善等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论点,皆谓寒毒因冬主闭藏而伏于肾水,不即发病,待春日内伏寒毒随阳气外泄而见温病。陆廷珍对于“伏寒化温”论并不认同,其认为“冬伤于寒”,是指冬伤寒水之脏,为“冬不藏精”之互词,重点在于“藏精”二字,若人能于冬藏精,则于春不伤寒。
陆氏首先从《内经》原文角度诠释,“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出自《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的最后一段,此篇的中心思想是“天人相应”,通篇论述人的生命活动应顺应自然界的变化。《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亦言“冬三月,此为闭藏……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此以春起论,阐述人应顺四时之脏以藏精,五脏方能各司其气,交相递运,无偏无胜。而不明冬藏之理,妄动其阳,妄泻其阴,使阴阳亏虚而失和,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导致“四时之气,更伤五脏”,这是阴阳消长转化、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非寒邪伏于体内至春而发病。此外,四季相环,冬之封藏会影响来年春之升发,若冬藏肾本,阴阳得充,当春之升发来临时,真气充足,不至因升发之令而气散匮乏,此时卫气充盛,腠理毫毛开泄有常,纵使外邪来犯,亦不能内侵。
其次,陆廷珍在《六因条辨·春温辩论》中明晰其理论内涵,前人论“冬伤于寒”为冬天感受寒邪,寒邪潜伏于肾,待来年春季阳气升腾之时,随阳而出,发为温病,但陆氏提出寒邪是杀厉之气,是无形的六淫邪气,人既得之,当下即病,不可潜伏于肾,更何况肾是生命之本,藏精气而不泻,岂有容寒内伏而无他苦,直待春时始发之理,故“冬伤于寒”不应从邪气解,而应从正气解,指的是“冬伤寒水之脏”,是对“冬不藏精”的补充。因此,陆氏认为春温为病,是由于冬不藏精,肾不得藏,肾阴不足,阴阳失和,肾中少火,不得阴润,发为壮火,与春之温气,相互结合,此时又外感微寒引动内火,而见“春温”一病,实乃“肾精不藏之人,至春易病温,至夏易病热”之意。治法上,陆氏强调应辛凉清解,如此以轻宣之剂引邪外出;同时应预顾阴液,一来防止温邪伤阴,二来防止坎水更亏,壮火更盛;并大忌辛温升散,鼓动风阳,一来易使外邪内陷,二来更伤已虚之精,外邪更易侵犯人体,不利于疾病的痊愈。
笔者认为大多数医家以寒邪潜伏为论点提出“伏邪理论”,故治疗只能待来年春季见病之发与不发,才知此“伏寒”之有与没有,不合乎“治未病”的思想;而陆氏从正气来解释“春温”病机,指出其根本病因为肾精之不藏而非伏气温病,临证变被动为主动,在冬季就需重视患者阴精的充养,从根本上做到防治“春温”之疾,对后世“未病先防”及温病诊治有指导意义。
6 结语
陆廷珍以前贤学说为宗,以自身临证经验为旨,创作不拘泥于一家之言的著作《六因条辨》,书中主要论述外感时病的病因病机、治法治则以及用药思路,提倡“伤寒六经”辨证与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融合,为现代时病疫病的诊治提供新思路。擅长明察病邪传变规律以治未病,这种思想不仅在外感病中广泛应用,临床各科疾病皆可灵活发挥应用。主张辨病名以定方,辨症状之虚实以调加减,现代中医在此基础上与现代医学疾病谱相融合,进一步发展“病证结合”观,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对后世有争议的“春温”一证,陆氏提出“冬伤于寒”的本质在于“肾不藏精”,极大地发挥了《内经》之经旨,告诫人们应藏精于冬以防春易病温,临床治疗温病时亦格外注意顾护阴精。陆氏的学术思想及特色在《六因条辨》中各卷均有体现,本文不足窥其全貌,尚需结合临床及现代研究部进一步发掘其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