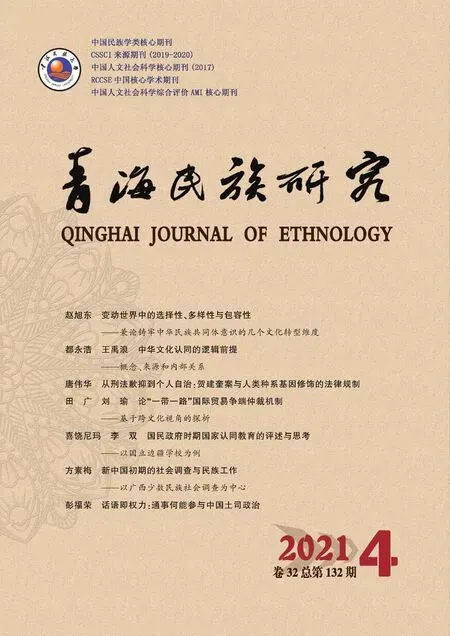论拉萨“藏回” /“甲卡切” (“兵安霸安惭”)群体族群认同与族群定位的历史嬗变
王 蓓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导言:从族群称呼透视认同与定位问题
拉萨 “藏回” 这一称呼,通常用来指称祖籍中国内地省份且由于已在拉萨定居若干代而成为拉萨世居居民的穆斯林群体。该族群兼具 “藏” 和 “回” 两种民族文化特征:一方面信仰伊斯兰教,遵从穆斯林共有的文化规范;另一方面以藏语为母语,大部分生活习惯已基本实现拉萨本地化。
尽管 “藏回” 的称呼比较简明清晰地概括了该族群 “藏、回杂糅” 的文化特征,但它作为一个被普遍使用和接受的称呼,并不是随着该族群的形成而出现的。最初,拉萨本地人将来自内地的穆斯林称为 “甲卡切”(“兵安霸安惭”),即为 “汉”(“兵”)和 “穆斯林”(“霸安惭”)这两个藏文词语的复合。也就是说,对同一个群体的称呼, 经历了从藏语语境中的“甲卡切” 到汉、藏双语语境中的 “藏回” 的改变,这一变化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而称呼的改变,作为社会实在的表征,正反映了在历史进程中这一群体的族群认同及其在拉萨社会族群结构中之定位所经历的微妙变化。
“族群认同” 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概念之一,概而言之,指的是 “个人运用种族、民族或宗教术语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并以此将自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1],通过个人对族群认同感的保持与维系, 族群才能成为一个具有社会行动力的行为主体。因此,族群认同主要是定义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联。与之相对应,“族群定位” 则标识作为整体的族群与处于同一社会中的其他族群的认同或排斥关系,它所确定的是某个特定族群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体系和族群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无论是族群认同还是族群定位,都包含了自我认同/定位,以及从他者角度进行的定义这内外两方面因素,而后者既指其他族群对该族群的界定,也应包括在跨族群关系中所产生的相对客观的规定性;除了自我和他者两方面因素之外,国家或地方政府权力由于相对于个体和群体而言的强势地位和统摄性,其赋予或规定对于族群认同与族群定位的形成也至关重要。
本文将主要以历史发展的纵线叙述为主轴,分四个时间阶段来分析拉萨 “藏回”/ “甲卡切” 群体族群认同与族群定位的嬗变,不过在进入历时性分析之前,有必要仅从这两个称呼的字面出发,简析在所指(signified)一致的情况下,能指(signifier)从 “甲卡切” 到 “藏回” 的变化可能开启哪些思考的方向。
能指的变化主要体现于三点。第一,最外在和明显的区别在于, 称呼由以藏语表达变为汉语表达。第二,作为群体最重要的核心特质的穆斯林身份标识始终保留在称呼中,无论是用 “卡切” (“霸安惭”)还是 “回” 来表示;而修饰词则从 “甲”(即 “汉”)变成了 “藏”。第三,尽管 “卡切” 与 “回” 都是对穆斯林群体的称呼, 但二者所指对象范围并不完全重合;而且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附着于词语之上的感情色彩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笔者在实地调研中所了解到的,在当前社会语境中,“卡切” 一词被认为含有微妙贬义而为被指称群体自身所不愿接受,同时随着对藏回群体 “回族” 身份的官方识别和认定,“回” 的族称已深入人心。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在于,汉语和藏语都是单个词汇具有巨大包容力的语言,随着时代变迁,无论是 “甲” (“兵”)或是 “汉”,“卡切” (“霸安惭”)或是 “回”,“颇”(“捶拜”)或是 “藏” 这样看似简单的单字都包容了诸如民族、地域、信仰、语言等等不同方面的意义,这就造成在不同主体、于不同时代、出于不同立场的理解中,“甲卡切” 或 “藏回” 的含义可能存在微妙而重要的区别。例如,“甲卡切” 可以被理解为 “汉族穆斯林”“来自汉地的伊斯兰教信徒”“汉地的回族人” 等;“藏回” 则可以被理解为 “藏化的回族人”“说藏语的回族人”“生活在西藏的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的藏族人”“西藏穆斯林”“藏族穆斯林”“既有藏族特征又有回族特征的人” 等。语义的不确定性和称呼的多义性、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理解共识形成的同时,也为自我与他者对 “藏回” 身份的阐释和再阐释开启了充分的空间;同样,对于研究者来说,模糊和差歧并不意味着混乱,反而可以成为思考该群体族群认同与族群定位复杂性的出发点。
本文行文中不追求术语保持一致,在论述前两个历史时期的情形时使用 “甲卡切” 一词,而论述后两个时期的情形时使用 “藏回” 的称呼。放弃形式统一性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一来希望尽量贴近不同时代人们所使用的主要指称,二来则为了凸显族群定位所经历的变化。另外,近年来一些学者倡导使用 “西藏世居穆斯林” 的说法,①该称呼考虑到了地域、谱系、宗教信仰等因素,并且规避了民族称谓这一易引发争议的麻烦问题,但它对于本文来说并不适用。本文之所以有意使用了更为啰嗦、不统一且字面意义较为模糊不明的称呼,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从研究对象范围来说,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祖籍中国内地的这部分 “西藏世居穆斯林”,而后者除此之外还包括了祖籍克什米尔等其他周边地区、被称为 “卡切” 的人群。第二,“西藏世居穆斯林” 描述的是经过历史的发展后形成的状态,而本研究主体部分在历史维度展开,重在追溯来自内地的穆斯林从外来移民成为 “世居” 的过程,因此,“西藏世居穆斯林” 与本文论述对象从时间角度讲存在一定的错位。第三,“西藏世居穆斯林” 的称谓近年来主要出现在一些学术文章和官方材料中,其使用范围有限,尚未被民间接受,而民间普遍使用的 “甲卡切” 和 “藏回” 称呼则可被视为本文所探讨的族群定位问题的一个显著表征。第四,“甲卡切” 和 “藏回” 的称呼虽然不精确,但其暧昧模糊之处恰恰反映了族群身份定位变动不定的特点。
一、清朝统治期间:“甲” 与 “卡切” 的复合
14世纪时,毗邻西藏西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完成了伊斯兰化,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经由阿里进入卫藏,逐渐在拉萨等城市形成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群体。“克什米尔” 这一地名在藏语中的发音为 “卡切”(“霸安惭”),西藏人便以地名指代人群,将来自该地的穆斯林亦成为 “卡切”;随后又将 “卡切” 称呼所涵盖的范围扩展到指称一切伊斯兰教信徒,包括来自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印度等诸地的穆斯林。根据流传于拉萨的民间口碑,17世纪中叶, 五世达赖喇嘛将拉萨西郊箭达岗一带的土地划拨给当时已常驻八廓街做生意的外籍穆斯林,并赋予其在商业贸易领域一定的特权。他们遂在拉萨社会中形成在血缘、宗教、文化等方面都不同于原住民的独特的卡切族群集团。
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在西藏驻兵,部分士兵在服役结束后不愿离开西藏,从而落户当地,其中包括不少回族士兵。另外,一些来自内地的回族商人也于清中叶之后在拉萨定居。这些回族男子大多来自四川、陕西、云南等省,②他们娶本地藏族妇女为妻,逐渐成为一个拥有一定人口数量、彼此具有高度认同感、显示出鲜明外在文化独特性的族群。当地藏人遵循称呼穆斯林为 “卡切” 的惯例,也将其囊括于 “卡切” 的称呼之下,同时为了将其与来自克什米尔等地的卡切相区别,又加上了这部分穆斯林的祖籍地汉地,即 “甲”(“兵”),从而形成 “甲卡切”(“兵安霸安惭”)这一复合型称谓。
卡切主要在位于八廓街东南绕赛巷的小清真寺做礼拜, 而甲卡切拥有位于河坝林的大清真寺,另外,卡切的墓地位于拉萨西郊的箭达岗,甲卡切的墓地在北郊夺底沟,两处也分别建有清真寺。遵循穆斯林围寺而居的传统,卡切和甲卡切分别聚居于八廓街附近与河坝林一带,因此当地人也以 “八廓街卡切” 和 “河坝林卡切” 分别称之。
有关甲卡切在这一阶段的历史以口碑流传为主,留下的文字材料很少,仅散见于当时清朝官员对在藏见闻的记录,以及零星碑刻中。根据现有材料,对于当时甲卡切的情况可获得几点比较明确的信息。第一,至清朝后期,在拉萨的 “甲卡切” 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族群集团,他们从其他留驻西藏的内地人中分离出来,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共同的墓地,因伊斯兰教信仰而彼此认同。第二,在当地人眼中,他们是来自内地的穆斯林,即卡切;同时,除了伊斯兰教信仰及与其相应的生活习惯之外,他们身上其他特征又是属于汉地的,作为来源地和重要文化特征的 “甲”(即 “汉”)的因素将他们与其他卡切明显区分开来。第三,随着在西藏生活日久,特别是通过与藏族妇女通婚,这一族群日渐藏化。
二、民国时期:藏化的 “汉回”
(一)内地记述者对甲卡切的族群定位
相较于清朝,民国时期有关拉萨甲卡切的记述要丰富许多:民国期间入藏的中央政府官员记录西藏见闻的书中都曾留下关于拉萨甲卡切的片言只语,如刘曼卿③的《康藏轺征》、黄慕松的《使藏纪程》、吴忠信的《入藏日记》、朱少逸的《拉萨见闻记》等,解放后问世的一些回忆、追述材料也不乏相关内容。尤为难能可贵的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内地的穆斯林刊物上曾刊发了几篇较为详细介绍拉萨甲卡切状况的文章:益吾的《西藏回民》一文于1946年发表于《月华》第16 卷第4—6 期;同年,内地回民马建业游历拉萨和印度,返回内地后向友人叙述亲眼所见的拉萨 “回民” 各方面情况,根据其见闻撰写的《穆斯林的旗帜飘扬在拉萨》(马瑛富撰)一文刊载于《清真铎报》1947年新二十三号,其缩编版《西藏拉萨的回民》(马建业撰)载于《回教青年月报》1947年回都第三号。通过这些材料,读者对于民国时期拉萨甲卡切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宗教实践、思想倾向等各方面情况可获得一定程度的了解。
根据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入藏的马建业的观察,当时甲卡切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习惯已然基本藏化:妇女完全着藏装,男子间或有穿汉式长袍,也依藏俗在腰间束带;饮食以乳酪、炒面(糌粑)为主,只偶食米面;住宅建筑及内部布置皆为藏式,形制多为方石为墙的双层楼房;行以骡马为交通工具,男女皆善骑。可见,处于特定的高原环境中并且在当时西藏与内地相对隔绝、交流困难的情况下,甲卡切完全放弃了祖辈在内地生活时的衣食住行习惯,转而采取与当地人相同的、更为适应高原自然条件和社会风俗的生活方式。意义更为重大的文化特征转变体现在语言方面,“除年老人能四川腔之国语外,其他如妇女子弟皆仅会一口流利之藏语”,[2]④究其原因,除了身处人人皆讲藏语的社会环境外,还由于男子多娶藏族女子,而子女在母亲抚养下自然以藏语为母语。
在 “边界说”“情景说” 等当代族群理论兴起之前,外在文化特征往往被作为族群定位的重要参考标识之一,显然此时的甲卡切群体已表现出十分明确的藏化特征, 然而民国时期的作者论及这一群体,赋予它的称呼中都并不包含 “藏” 的因素。他们一般按照当时内地普遍称呼穆斯林的习惯,将其称为 “回民”,同为伊斯兰信徒的作者也会使用 “教胞”(马瑛富、马建业)这一穆斯林之间相互认同的称呼,而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作者则将甲卡切定位为 “回胞”(吴忠信)、“汉人回回教徒”(刘曼卿)、“汉人” 中的 “回帮” 或 “回教商人”(朱少逸)等。这些称呼中的“汉” 是基于祖籍、血统而进行的族裔判别,而 “回”则是对其信仰的描述,并不含有民族意味。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内地伊斯兰教知识界不少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内地信仰伊斯兰教而生活习惯与当地汉人无异的穆斯林,应当称为 “回教徒”,民间俗称 “回民”,而不宜将其视为独立的民族 “回族”。此意见得到了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的正式确认,1941年, 行政院通令,“回人应称回教徒,不得再称回族”[3]。因此,这一时期 “回” 的含义基本等同于 “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如常见的 “缠回” 一词即指生活在以新疆为主的西北地区的维吾尔等各族穆斯林,而在述及西藏的外籍穆斯林时,当时的作者亦以 “克什米尔回民”[4]“印度回民”[5][6]称之,可见当时 “回” 的因素仅与宗教信仰相关,而与民族甚至国籍无涉。
尽管表现出藏化特征,但在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观察者特别是具有政府官员身份的作者看来,甲卡切就是居住在拉萨的汉回,本质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考究起来,产生这一认识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清末开始,以血统为种族、民族判断标准的近代西方理论传入中国,并作为 “科学” 为国人广泛接受,取代了中国自古以来以文化差别作为族群分野的传统观念,遵循血统论的理解,仅仅是甲卡切的祖先来自内地这一点,便足以决定其永恒的“汉回” 身份,至于外在文化特征等其他因素则是无关紧要的。其次,尤其对于吴忠信等政府官员来说,当时官方正统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民族观念根深蒂固,身负重大政治任务而入藏的他们也会将国府的政治考量自觉内化于心,诸如 “汉回同胞” 这样的称呼无疑具有强调西藏地方与中华民国之关联的意味,毕竟在当时国民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汉人与中国是对应的。再次,刘曼卿、黄慕松、朱少逸、吴忠信等人虽曾先后在拉萨停留过一段时日,但作为高层的国府代表, 他们的交际圈子实际上比较有限,特别是接触普通民众的机会并不很多。根据黄慕松和吴忠信的纪程、日记来看,他们在藏期间均只参观过一次清真寺,平时接触较多的仅是甲卡切中与西藏地方政府有联系的个别个体,如作为热振活佛和吴忠信间往来中介人的马宝轩。政府官员对甲卡切缺乏深入了解,限制了他们对其文化特征的认识。与之相对应,并无政府官员身份的马建业则留下了关于甲卡切生活习惯、文化特征较为详细的记述。最后,为了争取本群体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在地方族群格局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甲卡切通过其代表有意在国府官员面前呈现自身族群特征方面 “汉” 的因素,并着力强调本群体与祖国内地血脉相连,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予以详述。
(二)西藏地方政府对甲卡切的管理方式
无论其生活习惯和文化特征如何呈现出汉、藏、穆各种元素的杂糅,可以肯定的是,民国时期的甲卡切在整体上可以明显地与生活在拉萨的藏人、汉人以及外籍卡切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在以藏族为主体而多族群共存的拉萨社会中,甲卡切始终维持着自身与他族之间明确的族群边界;同时,尽管其祖辈籍贯 “有地域不同之分”[7],但甲卡切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很强,成员彼此间具有高度认同感。这一方面当然是出于同族同教的原生感情,以及成员个体在面临同样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时所必然产生的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作为当时当地拥有主导性权力的统治机构,西藏地方政府对甲卡切的管理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其族群认同。
作为拉萨的常住居民,甲卡切作为一个整体归属西藏地方政府的农业局,音译为索朗列空)管理。农业局是十三世达赖喇嘛 “新政” 后西藏地方政府所设立的部门, 职责包括登记人口,征收人头税;管理新开垦土地;登记非政府、寺庙、贵族属民的游民百姓;征收拉萨市内房屋税等。[8]拉萨的藏族百姓,除少数游民外,都属于 “本域属民”,即前文之政府属民)、世家贵族属民或寺庙属民,而甲卡切尽管是拉萨的常住居民,但并未被西藏地方政府归为上述三类属民之中,而是以整体的形式归属农业局管理,管理范围包括批准其领导者、收取赋税、处理牵涉该群体的重大纠纷、案件等。
农业局管理甲卡切的最基本方式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集团,以批准作为权力象征形式来为该群体自选的首领和自治组织赋予合法性,然后通过这一领导阶层实施间接管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对各个族群集团均以这种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的方式进行统治,如当时拉萨还生活着以前清驻藏官兵后裔为主的汉人形成的 “川帮”,也由农业局通过其保正来委派税收和差役,进行整体管理。[9]对于来自克什米尔等地的卡切,西藏地方也采取了类似的间接管理方式,但卡切并非农业局下属。在自行选出头领 “卡切奔布”之后,由达赖喇嘛亲自加以批准,再由他组织以自己为首的五人管理小组 “板吉”(ponj)⑤,负责清真寺以及卡切公共财产等的管理。[10]除了首领人选分别由达赖喇嘛和农业局批准之外,西藏地方政府对卡切和甲卡切实施的不同政策还体现在,前者享受贸易免税、免于支差等优惠待遇,而对后者,初时尚免除差役赋税等,后来则渐渐褫削了这些特权;[11][12]卡切出境往来经商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保护, 而甲卡切被限制不得出国;在两个群体间发生争执时,西藏地方政府从来都是袒护卡切而压制甲卡切。[13]这种不平等的待遇造成了两个群体在社会地位上的高下之别。总而言之,西藏地方政府对 “川帮” 等汉人、甲卡切、卡切等不同族群集团采取了保持其各自原有的群体性并分而治之的管理策略, 并且分别给予有差异的待遇, 该统治方式进一步凝聚了各族群内部的认同感,同时更加强化了其彼此之间的族群边界,如尽管甲卡切与卡切同为穆斯林,且双方成员间各种民间往来甚多,但西藏地方政府对于两个族群不同的管理方式和政策使二者间始终保持明晰的分野,而且也塑造了卡切比甲卡切更高的社会地位。
西藏地方政府主要以间接统治的方式整体管理甲卡切等族群意味着,这些族群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自治权利。在领导者的选择方面,由拉萨的甲卡切自行选出总乡约一名,保正两名,组成乡老组织,报农业局批准,乡老组织三年一换,[14]在这一过程中,农业局任命领导者的权力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在司法权方面,伊斯兰教法所要求的宗教精英对教民的司法裁判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尊重,由大清真寺的掌教和阿訇判决甲卡切内部的纠纷和案件,寺内设有监房和手铐、脚链、皮鞭等刑具,对违反法令的教民进行惩罚,只有严重到寺内无法处置的重大案件, 才交由农业局判决。[15]在税收征缴方面,乡老组织之下有八名管理人员,分管库、钱、房和尾,尾指的是屠户每宰杀一头牛,都须向西藏地方政府缴纳其牛皮和牛尾作为赋税,这些管理人员的设置,说明甲卡切拥有作为集体资产的动产和不动产,[16]尤其是管 “尾” 人员的设置,说明西藏地方政府将甲卡切作为一个整体并通过族群集团中的中间代理人来集中收税,而不是直接对甲卡切各家屠户分别征税。
专门设置管 “尾” 人员,也说明屠宰业对甲卡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生计方式, 而从事这项职业,也是西藏地方政府赋予甲卡切的一项特别权利。西藏地方政府规定,由河坝林的甲卡切专事宰杀和经营牛肉买卖,十三世达赖喇嘛还特许其中一户专门供应达赖的食用牛肉,另一户专供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食用的牛肉,并世代相传。[17]出于藏传佛教不杀生的戒律,藏族人民对于宰杀牲畜有所忌讳,而屠宰一直是各地回族人民从事的传统行当之一。西藏地方政府将源于文化传统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分工进行了制度化的安排,进而通过授予经营特许使甲卡切拥有了宰牛和买卖牛肉的行业垄断权,由此使生计方式和职业角色也固化为甲卡切的另一个族群标志性特征。
综上所述, 作为具有统摄性权力的外在力量,西藏地方政府对甲卡切的统治方式以及各方面的管理政策都对其族群独立性的保持以及族群认同的强化有所促进。
(三)甲卡切的族群生存策略
除了外部因素之外,甲卡切群体自身有意识地运用了若干策略,一方面强化内部族群认同,明确族群边界,增强群体凝聚力;另一方面则充分运用各种社会资源,争取使自身在本地族群结构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
甲卡切维持和强化族群认同的最基本方式是以伊斯兰教信仰凝聚认同,以穆斯林社群保持内部组织结构。具体说来,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注意。
第一,甲卡切的伊斯兰教信仰虔诚,谨守教法规定的穆斯林念、拜、斋、课、朝五功,伊斯兰教信仰是其区别于非穆斯林族群的最显著标识。
第二,甲卡切特别重视宗教节日和特殊时段对于增进信仰、团结集体的意义,“每年斋月所有回民皆就于清真寺,一方面锻炼团体生活,再一方面在他们终年辛苦,而获得这一个月的机会,以资修养而虔心向主礼拜把斋”;[18]每逢忠孝节、开斋节等传统节日,甲卡切均歇业休息以做庆贺,由于他们是拉萨零售行业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故每当此时,“三四天以内,拉萨市面均在停业状态中”[19]。
第三,自我组织化有力地使甲卡切团结为一个整体,掌教和阿訇依循伊斯兰教法在宗教和司法领域对信众进行管理, 乡老组织则负责民事管理,还有代表整个集体的类似于 “会” 的组织 “对外为宣传交涉等事项;对内扶持贫弱,帮助婚丧等事项”。[20]
第四,穆斯林传统上围寺而居,在内地城市中往往形成 “回坊” 这一特定的族群聚居区,甲卡切在拉萨延续了此居住格局,聚居于位于河坝林的大清真寺的东西南三面,[21]在地理上形成与其他族群居住区域相区隔的独立社区,对族群边界感的维持有重要作用。
第五, 甲卡切十分重视本族群后代的教育,内容以宗教教育为基本,兼顾世俗教育。1910年左右,清真寺的两位老阿訇在家中开办私塾,教授阿拉伯语、乌尔都语以及《古兰经》;几年后,大清真寺执事决定,在寺里集中办学,所有私塾学生都迁入寺中学习,主要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对学生入学年龄没有限制, 学校经费来源主要由清真寺承担;1931年, 清真寺又设立了一个半日读阿拉伯文、半日读藏文与汉文的半日学堂,将世俗教育纳入其子弟的教育规划中。[22]1939年,国民政府在拉萨创办国立拉萨小学,回民半日学堂和清真寺回民学校的学生都转入该小学,甲卡切由此成为国立拉萨小学的主要生源,学校因而专设回民班,开设阿文课程,在十年间毕业的12 位学生中,甲卡切占了80%。[23]甲卡切学校教育课程中的多种语言设计尤其值得注意,这是甲卡切结合回、藏、汉三种文化元素的特殊族群身份的一种表征:以教授阿文和《古兰经》为主的宗教教育保证了甲卡切族群核心特质的代代传承,而藏、汉文学习则分别适应现实需求和维系族源记忆。当然,学习汉文也不乏现实目的,正如在后文中将看到的,兼通汉藏语对于甲卡切个人在拉萨社会中谋求发展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因此,尽管困难重重,甲卡切的乡约马干臣还是设法专门从内地运回《平民千字》1—4 册,[24]和《幼学》《论语》《四字经》《平民千字》《增广全程》等汉文化开蒙读物一起作为甲卡切子弟的基本教材。[25]
第六,甲卡切普遍从事的生计行当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职业——族群对应性。除了前文提到的对宰牛和牛肉售卖行业的垄断之外,甲卡切还普遍从事小商品买卖、食品和糕点售卖、茶馆经营、种菜卖菜、磨面、裁缝等行当,其中诸如种菜、腌菜和磨不掺杂麸皮的 “汉地面” 等,由于甲卡切秉承从内地带来的独特技术,在拉萨没有竞争对手,因而成为甲卡切的专营生计并代代相传。[26]与其他族群的职业分野进一步明确了甲卡切的族群边界,某些特定职业成为其明显的外在身份标识之一,对若干行业的垄断以及世代传承则有助于强化族群内部的认同感;而在另一方面,职业的独特性对于甲卡切在拉萨社会中的立足也至关重要,通过在生计方式上与周边其他族群特别是藏族所从事的传统营生相互补充,甲卡切在当地的社会分工中承担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从而使自身成为内嵌于拉萨社会中的族群构成成分。
尽管时至民国时期,甲卡切以一个族群集团的形式在拉萨立足已稳,已然在当地族群结构中占有稳定的一席之地,但作为一个人口较少、文化并非主流的少数族群,甲卡切需要采取各种策略,发展和加强与各方面的社会联系,充分运用种种社会资源,为本族群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除了在本地经济生活和社会分工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之外,从现实角度讲,兼具汉、藏两种文化元素成为甲卡切最可利用的优势。通晓汉、藏双语,能够理解汉族和藏族各自的民族特性和心理特征,了解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双方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考量,这使甲卡切成为在汉藏两民族以及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进行沟通的最合适中介,而甲卡切也有意识地运用这一中间人身份,尽力与各方发展友好关系,以使自身在当地族群格局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
一些甲卡切凭借语言等能力供职于西藏地方政府,如官位五品的噶厦藏文秘书马和堂、热振活佛执政时担任其秘书的马宝轩等。在1934年国府致祭专使黄慕松入藏册封、致祭圆寂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1940年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期间,在西藏地方政府任职的甲卡切与国府高官接触密切。对于国府官员而言,这些甲卡切中间人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在官方层面上,他们正式代表西藏地方政要与国府使者进行沟通。如马宝轩不仅在吴忠信与热振会晤时担任翻译,[27]而且频繁拜访吴忠信,代表热振往来传递信息,⑥联络双方感情⑦;另一方面,在非官方层面上,由于来藏的国府官员对藏情相当隔膜,尤其是对于西藏地方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权力纠葛毫不知情,身处西藏地方政府体制之内的甲卡切便成为其重要的信息和情报来源。例如,黄慕松在拉萨期间,“回教马代表及马鹤堂两君”⑧在前去拜谒时,向其透露了 “僧官首领” 不赞成噶厦关于当时中央和西藏地方间关系的观点并主张恢复原有关系的重要信息[28];马宝轩则曾与吴忠信探讨热振的政治处境,[29]还曾向其通报英国代表警告威胁西藏地方政府的情况。[30]这些信息对于不熟悉藏情的入藏官员来说无疑是极为宝贵的,而通过向中央政府官员传递其急需的信息,甲卡切充分表达了对中央政府的善意,及其对于未来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趋好走向的期盼,这不仅是甲卡切因祖先来自祖国内地而油然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而且也是在当时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下,积极争取本族群发展空间的一种努力。
在整个民国时代,西藏地方政府时为亲英势力所左右,故而尽管甲卡切此时已然本地化而且其中的一些成员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但随着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就一些问题发生龃龉,甲卡切作为一个群体因其在血缘与文化上与内地存在的联系而不为西藏地方政府所信任,后者甚至针对甲卡切群体采取了某些带有明显敌视色彩的措施。如前所述,30年代初期,西藏地方政府已褫夺了在差役、赋税等方面原本予以甲卡切的一些特权,而且还派人对其进行监察。[31]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下达了禁止藏族贵族与甲卡切通婚的命令。[32]按照一位甲卡切老人的表述,“我们回回是倾向祖国的。因此,藏政府的亲英派们嫉恨我们,我们常常受他们的气。”[33]在这种对族群整体而言日趋恶劣的政治气候下,甲卡切在移民群体原本天然具有的不安全感之外,必定会产生更深的危机意识,这就促使他们更为积极地寻求外部支持,将有可能制衡西藏地方政府的其他权力体作为同盟。
除了供职于西藏地方政府的甲卡切通过提供信息以帮助中央政府入藏官员达成其使命,其他甲卡切也在与这些官员会面时屡屡表示极大敬意,并传达甲卡切心向中央之意。吴忠信前往拉萨大清真寺参观时,甲卡切的宗教首领坚请其不必脱履而入寺内,[34]这无疑是非比寻常的充分表示尊崇与善意之举;而在吴前往位于夺底沟的 “回回坟” 时,甲卡切特意在墓地的林卡中搭起帐篷设宴款待,“以示乡土之情”,[35]“回胞数十人” 在吴到来之前便 “肃候已久”,而且还向其表达了 “今日复见汉官入藏,不胜欣幸” 的激动心情。[36]甲卡切面对国府官员和内地来访者时表现出的热情、亲厚以及对心向中央之意的恳切表达往往给后者留下深刻印象, 使其得出“他们的爱国精神,不但高于西藏人,而且,高于内地人”[37]的言过其实的判断。不可否认,出于原生情感、祖籍纽带以及移民群体乌托邦式的怀乡心理,甲卡切确实怀有比较强烈的对祖国内地的依恋之情,政治立场也偏向于拥戴中央政府,比如在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拉萨后,甲卡切曾与国府在藏各机构人员、内地商人以及落户西藏的汉人一起欢宴,并在宴会后环绕大昭寺持火炬游行至半夜,以庆祝中国的胜利。[38]不过在承认原生情感作用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特定社会情境下理性的利益权衡和策略选择在甲卡切的行为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
因甲卡切在拉萨社会所处的特殊位势而决定的策略选择也体现在某些个体及其家庭的前途规划中。例如,任噶厦汉文秘书的马和堂,本人 “颇以文学见知于第十三辈达赖”[39],其子则被送入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由于在拉萨社会中,甲卡切从人口规模上讲是少数族群,从宗教文化上讲与当地社会的主流信仰相异,从族群整体的社会地位上讲处于社会阶梯上较低的层级,⑨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安全与前途考虑,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群体,充分利用其文化中介身份,与各方发展良好关系,谋求与各种势力建立利益同盟,并且注意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些都是必然采取的现实策略选择。
在社会族群关系中处于 “中间人” 位置,尽管常常因不可或缺的沟通中介作用而从中获益,策略运用恰当甚或能够左右逢源; 然而,“像此又像彼,非此又非彼” 的中间状态也相当尴尬,在社会动荡或族群关系紧张的特殊历史时期, 甚至是十分危险的。近代史上每值西藏发生藏汉对立事件之际,甲卡切往往成为暴力行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在1912年驱逐驻藏川军的 “壬子之变” 中,拉萨的 “接战最近为清真寺”[40],甲卡切及其清真寺也被藏军作为攻击目标,甲卡切自然与清军结为同盟,作战时 “其清真寺百姓均极奋勇”。[41]在解放军入藏前,西藏地方政府中有亲英派曾建议杀尽甲卡切, 由于在1949年 “驱汉事件” 中,拉萨的国民党驻藏官员等汉人已被遣返内地,孤立无援的甲卡切只有 “群集于清真寺等待死亡”[42],幸而极端的情况并未发生。每当西藏发生政治动荡,一部分暴乱分子发起针对汉人的暴力行动时,在当地族群结构中相对弱小的甲卡切反而往往成为最易受到攻击和伤害的群体,其文化特征中 “甲”(汉)的因素会在施暴者眼中得到放大,从而使他们成为转移矛盾和宣泄情绪的目标。类似的情形在1959年、1989年、2008年又多次复现。甲卡切具有多元文化特征,并且与利益有时对立的族群集团双方均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令他们在当地社会的族群格局中处于一个不稳定的位置,而族群定位的流动性一方面使其有可能因“中间人” 的身份而获益,另一方面,在社会结构中较为强势的两个族群发生矛盾时,在冲突方眼中,甲卡切身上与己相异的那些文化特征就会得到放大,他们不同于自己的利益和关切也会被突出强调,再加上其群体本身在人口规模和社会地位上的弱势,甲卡切便极易在这种情境下成为被排斥的对象,甚至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综上所述,在整个民国时期,拉萨社会中的甲卡切群体始终保持着独立而完整的族群认同,并通过坚守宗教信仰、建立内部组织、形成聚居社区、重视教育、从事特定职业等方式不断强化内部认同感,同时维持与其他族群之间的边界。西藏地方政府将甲卡切作为一个整体,采取了赋予其一定自治权利的间接统治方式,这种外部给定的统治政策同样使甲卡切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增强;而西藏地方政府给予不同族群集团有所差别的待遇则进一步固化了族群间的边界,同时也塑造了社会中诸族群的地位等级关系。
民国时期,西藏与内地彼此隔绝,甲卡切和内地汉族、回族的联系都极其有限;同时,他们作为少数族群长期生活在藏文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拉萨,现实生存环境以及与藏族女子的数代通婚关系决定了其在文化特征上较快的本地化速度。除了保持与伊斯兰教信仰相应的习俗之外, 时至20世纪40年代,甲卡切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以及日常语言方面与当地藏族已十分接近,“与土著无异”[43]。随着文化特征上的藏化趋势不断增强,甲卡切的自我身份认知以及社会大众对其族群定位也逐渐产生变化。薛文波在50年代初所作《拉萨回回》一诗中有 “三代以前仍‘甲米’,‘博巴’一名称于今”[44]之句,“甲米”“博巴” 分别为藏文 “汉人” “藏人” 两个词的音译。这说明,如果将 “卡切”/“回” 的因素暂且放在一边,仅在 “汉—藏” 二元结构中描摹甲卡切所处位置及其动态变化,则在20世纪上半叶,甲卡切的位移轨迹显然是从 “汉” 的一端向 “藏” 的一端单向移动, 以至于如果在当地社会中只存在“汉—藏” 或“甲米—博巴” 一种区分人群的方式的话,则甲卡切的自我及他者定位早先归属前者,而此时已可被涵盖于后者。不过,尽管甲卡切在拉萨社会族群结构中位移的方向是确定的,但这并未改变它在该结构中所处的 “介于之间”(inter—)的位置及其所暗含的不稳定状态。尽管困难重重,但甲卡切还是通过中央政府入藏官员建立与内地的政治联系,并在学校教育中尽量保持汉语等汉文化因素的存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既有出于原生情感和祖籍纽带的因素,也是甲卡切为了生存、发展以及在当地族群格局中争取更有利位置而做出的现实选择。
三、和平解放至今:从西藏的回族到拉萨市民中的 “藏族穆斯林”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当年秋,解放军进入拉萨,拉萨藏回热烈欢迎,许多人为解放军担任翻译,并积极协助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特别是在兴办学校方面助力良多。1952年8月成立拉萨小学时,回民学校正式改为拉萨小学分校,学生达170 人。[45]当时新近入藏的解放军干部在拉萨人地两生,许多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遭遇种种困难, 而藏回世居本地,对拉萨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尤其是与当地平民大众关系良好, 对于解放军各项事业的开展助力良多。例如随西北西藏工委进藏的回族干部薛文波曾记录过这样一件事, 当时拉萨各机关都在加紧建设,人力非常短缺,负责办理修造工程的干部一筹莫展,是一位藏回老琴师动员街头的乞丐流浪汉参加劳动,解决了燃眉之急。[46]在和平解放初期,拉萨藏回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在汉藏之间所起到的语言、文化及政治中间人的作用比在民国时期更为显著突出。
解放军进藏也使拉萨藏回的心态及自我认知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如薛文波所述,“此地回民有个错误的想法,认为解放军解放西藏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因为多年受到藏政府亲英派的压制,现在可出气了。现在解放军一视同仁, 回民便觉得失望了。”[47]这种心态正反映了族群定位中工具性的向度:在政治气候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中,藏回试图运用自己所具有的多重文化身份以及处于多种势力纽结点的社会位置,根据已反转的权力关系而对自身的族群定位进行修正,强调本族群与内地的情感联系及社会、文化纽带,以争取在新的族际关系与族群权力格局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并且希望因本族群曾在西藏地方政府统治下受压迫的地位与不公平遭遇而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偿,从而为本族群的进一步发展谋求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
1950年,国家开始展开民族识别工作,回、藏等民族作为早已确认的少数民族得到国家权力对其身份的正式赋予。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拉萨的藏回在自愿的基础上被认定为回族,包括嫁入的藏族妇女。族属的确定对藏回影响重大。从现实层面讲,民族识别的意义在于,通过人口普查、登记户口以及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使每个族群的民族身份固定化,这种民族身份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而且被赋予了官方认可的政治意义;因此,当藏回被认定为回族时,便意味着这一由国家权力赋予的民族身份至少在政治层面上消解了其多重文化身份所带来的可兼容性、多元性、杂糅性和暧昧性,也取消了其族群定位随着不同社会环境而变动的可移动性和可商讨性,在官方层面的资源分配中,从此藏回只能享有回族身份所对应的政策待遇。回族身份的认定对藏回的自我身份认知还产生了更为微妙却深远的影响。在全国民族识别过程中,除了九个具有一定族源独特性并具备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穆斯林族群被认定为独立的民族之外,我国其余穆斯林人口基本全部被归入回族。从此,“回” 的意义,从民国时期标识宗教信仰和文化特征的回教徒,转变成为回族这一附加有政治含义的民族身份。然而,以信仰伊斯兰教作为划定回族的主要标准带来了一系列理论与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诸如拉萨藏回这样的群体,除了宗教信仰一致之外,由于语言、风俗习惯、生活环境、心理特征等各个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很难与内地的回族群众之间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当 “回” 仅仅指宗教信仰时,其内涵单一、纯粹,由此带来的同为穆斯林的认同感也相对强烈和稳固;而当 “回” 的意义转变为民族之后,由于民族概念包含了共同地域、语言、文化特征、心理质素等多重因素和判断标准,反而使被统摄于回族这一范畴之下的各个族群间在以上诸方面的差异愈发凸显出来,生活在不同地方且语言、风俗、文化差异较大的回族群体间有时会在主观意识中形成彼此相异、无法合为一体的疏离感,从而造成官方民族身份认定与族群自我心理认同感觉之间的错位,这种错位对族群定位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尚在萌芽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发明显。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30年间,西藏与全国各地的情形类似,政治事件对社会其他领域的主导作用空前强大。拉萨的藏回与各族人民一起,经历了和平解放、叛乱与平叛、民主改革、中印交恶与边界冲突、“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共同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同为西藏人民的情感联系和彼此认同;同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也对藏回的身份定位、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在地方社会格局中的位置等问题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0年,紧随全国各地的步伐,西藏也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一时段的时代风潮与社会环境对拉萨藏回的族群认同形成巨大挑战,同时,也导致其族群定位发生了较大变化。
与此前的时代不同,挑战以及变化的诱因并非政治事件, 而主要来自两股势头迅猛的巨大浪潮:其一是社会整体现代化对于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社会结构的冲击,其二是从外省大量涌入西藏城镇的流动穆斯林人口所造成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政府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清真寺礼拜、圣地朝觐、宗教节日庆祝等伊斯兰教要求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现代化潮流也以压倒性的力量席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节奏大大加快, 城市生活方式愈来愈同质化,经济成功和物质追求成为主流价值,而传统价值观念被边缘化,等等。现代化对于诸如穆斯林这样以宗教信仰作为本质特征的群体来说冲击更大,比如,现代科学知识与宗教神学世界观和信仰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难于消解,现代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工作时间安排使中青年难以按时参加一天五次的清真寺礼拜,伊斯兰教法规定的宗教法权和现代国家统一的司法权无法兼容,穆斯林的内部组织化管理和对孩童的宗教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也是不合时宜的。
现代化之于藏回的影响显而易见。根据笔者对在大清真寺参加礼拜的穆斯林的观察,平时进行礼拜的藏回基本都是老年男子,在周五聚礼时偶尔可见中年或青年男子,但人数非常少。由于信仰伊斯兰教曾经是藏回的核心特质以及最主要的族群内部凝聚力所在,面对现代化和去宗教化对族群自我认同的冲击, 藏回采取了一些策略来抵消影响,维持族群认同。首先,利用传统节日演习特有的文化习俗,并借此联络感情、凝聚人心。开斋节、圣纪节和古尔邦节是全球穆斯林共庆的伊斯兰教三大节日,拉萨藏回对此也十分重视。庆祝三大节日时,除了依照每个节日的传统要求聚集在清真寺进行祈祷、听讲经等宗教活动以及在回族墓地游坟之外,藏回还会食用传统食品并身着盛装,特别是中青年女性一般也会戴上盖头,而现今在平日里,只偶尔可见老年藏回妇女日常戴盖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拉萨藏回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节日——抓饭节。根据介绍,抓饭节的起源是有一年大清真寺大殿维修扩建,工程结束时群众要求举办一个竣工典礼以示庆贺, 但当时恰逢藏族传统的萨嘎达瓦月,由于藏族习俗要求该月内不可杀生,于是藏回便不宰牲,而是到北郊的格格霞回族墓地举办了一个小型竣工典礼,以掺拌人参果、酥油的抓饭为餐。[48]后来每年八月中的一天,藏回男女老幼都会在格格霞墓地聚集,首先听教长讲经、集体赞圣,随后共进抓饭。之后各家藏回搭起帐篷过林卡,玩乐几日后回城。在当代社会中,藏回平日各自忙碌,在现代化城市中的居住格局也有所变化, 不再像旧时那样集中,族群成员间日常相互交流和联络感情的机会大大减少; 而抓饭节作为一个本族群独有的节日,通过一年一度的聚会,起到了传播传统文化、继承宗教知识、缅怀纪念先人、联络成员感情的多重作用,而这些作用对于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强化至关重要。其次,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藏回男女群众分别成立了 “穆日地” 和 “女友” 两个民间互助组织。[49]“穆日地” 在和平解放之前主要是负责为去世藏回举办殡葬事宜的自发组织,[50]在1966—1986年期间曾停办,后由一些热心公益的老年藏回重新组织起来,他们每月从退休金内拿出一些作为基金,用于操办孤寡老人的丧事,帮助贫穷、患病、无助的藏回,以及支付开斋节等集体活动的开支。[51][52]民间互助组织对于藏回保持族群归属感、促进内部团结、增强群体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藏回仍然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早期家庭教育中注重培养孩童的穆斯林传统美德,在清真寺内设立的学龄前儿童班则教授阿文、藏文、算术等课程,[53]这些早期教育有助于使下一代了解本族群的文化传统及相关知识,建立起对本族群的认同意识。
可见,在应对现代化冲击时,拉萨藏回所运用的保持族群认同诸种策略的要义在于保持和传承穆斯林传统这一族群文化的核心特质;而面对外来流动穆斯林涌入的影响,他们则主要采取了维持族群边界和强化群体间分野的策略,以求在拉萨数量日渐庞大的穆斯林人口中保持本族群的独立存在。
自古以来,穆斯林便以擅长经商和从事长途贸易而著称,世居拉萨的藏回,最初来源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内地省份的回族商人。改革开放解除了几十年来限制私人经济发展的种种桎梏,回族商人很快再次活跃起来。1985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取消了地区流动限制,并采取了薄税政策,大力鼓励人民外出经商。州领导先后五次进藏,为州内群众到西藏经商和谋取生计铺路。[54]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回族、撒拉族等西北穆斯林大量进藏经商和打工;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之后,更是人数激增。在藏的流动穆斯林人口具体数目难以统计,估计为几十万。他们多来自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临夏、广河、和政、康乐,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青海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等地,主要集中于西藏城市中,特别是拉萨。外来流动穆斯林在拉萨被称为汉回,而这恰恰与如今被称为 “藏回” 的群体此前的称呼 “甲卡切” 词义基本对等。也就是说,在与新近进藏的内地穆斯林的对比之下,已然本地化的曾经的 “汉回” 在现今被视为 “藏回”,或者说从前的 “甲卡切” (兵安霸安惭)如今成了 “颇卡切”(捶拜安霸安惭)。
虽然同为教胞,在宗教信仰上彼此认同,但是拉萨的几千藏回始终保持与人数规模远更庞大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社会距离产生的根源在于本地人与外来者的区分,作为世居居民,拉萨是藏回无可置疑的故乡,而流动穆斯林大多只是将拉萨作为谋求生计的工作地点,他们季节性在此暂居,很少有人计划长期定居。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本地人与异乡人间的社会分层差异和群体隔阂也必然体现于拉萨的藏回和外来流动回族之间。现代户籍管理制度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别。藏回在拉萨可以享受与本地市民身份相应的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权利,适用于本地的教育、就业、医疗等政策,而这些优惠的待遇或机会并不向外地户口持有者开放。在心理距离方面,由于长期在差异较大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并浸淫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两个群体的价值观、道德观相互间也产生了一定差别,彼此并不很认同。流动穆斯林主要来自我国西北穆斯林集中、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他们的信仰普遍较为虔诚,关于教义、教规的知识比较丰富,在他们看来,许多藏回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不足,一些做法不够符合教义规范;而拉萨藏回则认为,本地藏回 “很负责,懂多少遵守多少,很少有不良行为”,[55]相反外来回族受教育少、“素质较低”,而且良莠不齐,一些人的欺骗、使诈、小偷小摸等行为违反了穆斯林道德, 更有人从事违法的生意。再加上由于机会竞争而产生的本地人对外来者的敌视心理以及不同生活习惯、文化差异等带来的摩擦,在拉萨社会中普遍存在某种针对外来穆斯林的不满情绪,甚至从对个别人某些极端行为的怨气上升为对整个群体的污名化,这种大众情绪进一步加深了拉萨藏回与流动穆斯林之间的心理隔阂。
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外在体现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拉萨藏回与外来流动穆斯林两个群体之间交往较少。为了礼拜和做生意之便,有很大一部分流动穆斯林在河坝林一带租住本地藏回的房屋,不过笔者在采访中得知,平时双方除了生活中必要的接触之外,几乎没有更深入的交流。第二,两个群体普遍从事的职业有所区别。自从和平解放以来,藏回的职业选择逐渐发生变化。由于向来重视教育,从50年代起,藏回中便出现大量政府干部和从事科教文卫行业的知识分子,今天的藏回家庭普遍鼓励子女上大学,并且在毕业后倾向于在体制内择业。藏回传统上从事的一些职业则成为流动穆斯林的生计方式选择,比如牛羊屠宰和售卖曾经是被藏回垄断的行业,目前已基本全部由外来穆斯林经营。在商业领域,外来流动回族与内地商贸网络存在更密切的关系,拥有更为广阔的进货渠道,经营成本较低,经商开店更具竞争优势,因此,藏回基本也已退出商品零售行业,而选择将铺面租给流动穆斯林,自己收取租金。传统上藏回所从事的行业,基本只有餐馆和甜茶馆经营尚存。如今的藏回,与拉萨各族市民一样,以谋求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为职业选择取向,而流动回族则主要从事药材、皮毛和日常用品贸易以及餐饮、屠宰、客货运输、建材等行业。第三,两个群体在日常习俗、生活习惯上保持各自独立性,互不影响。与几个世纪之前藏回祖先落户的拉萨相比,今天开放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现代都市拉萨的社会氛围已大为不同, 外来人口在这里,无需像从前的移民那样一定要使用藏语和采用藏族的生活方式才能生存。因此,流动穆斯林往往只会说几句做生意时常用的简单藏语,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则仍然完整保持自身原有的生活习惯。相反,藏回除了清真饮食以外,其他生活习惯与本地藏族已无甚差别。
外来流动穆斯林大量进入拉萨,在拉萨原有的族群结构中增添了新的要素,在这一变化了的结构中,藏回的族群定位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如果说从前甲卡切族群定位的参照系主要由藏人、汉人和卡切组成,那么如今主要的参照对象则是拉萨的藏族以及以回族为主的外来流动穆斯林。
从拉萨藏回的主位视角来看,由于与外来流动穆斯林之间存在不小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他们会有意无意地通过一些外在表现或行为凸显“藏回” 与 “汉回” 的差异,强化穆斯林内部的族群分野。例如,根据笔者观察,藏回男性平时装束与其他拉萨市民无异,不像外来穆斯林那样头戴号帽,中老年男子一般戴有檐的藏帽,只有在礼拜之时才把藏帽挂在清真寺礼拜殿外,戴上随身携带的白色无檐号帽步入礼拜殿。再如,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藏回的起名方式与内地回族无异,都是兼起汉名(学名)和经名,并且在世俗场合使用汉名;不过从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藏回仅仅使用经名,而不使用汉名或者没有汉名。当今的藏回虽然接受 “藏回”这一称呼,但对其自有阐释。普遍来说,他们并不认为 “藏回” 的称呼是一个 以 “藏” 来 修饰 “回” 的 偏正结构词语,也就是说, “藏回” 并不意味着 “在西藏的回族” 或是 “藏化的回族”,而应被解释为 “西藏穆斯林” 或 “藏族里的穆斯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解中的“回” 有些类似于民国时期官方所定义的“回” 的内涵,即以 “回” 作为对宗教信仰而非民族的称呼。今天的许多藏回,尤其是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为藏族,而非回族。在户口登记、人口普查等实际操作中,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藏回将民族身份登记为藏族。拉萨藏回自我族群定位变化的原因是多重的: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其他文化特征的完全藏化是其自我定位为藏族的客观事实基础;在大量外来流动穆斯林人口涌入拉萨的社会情境下彰显自身文化特 征中 “藏” 的因 素,以 强 化 “藏回” 与 “汉回” 族群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在地方族群格局发生变化时的应激心理反应; 不同民族在高考、公务员考试录取等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中享受的政策存在差异, 则是藏回更换民族身份的现实动因。可见,藏回自我族群定位从 “回” 向 “藏” 的转 移是多层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一变化的后果之一表现在,藏回群体的官方统计人数与实际人口规模存在不小差异。由于藏回人口统计数字是根据户口登记为回族的人数得出,而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藏回已登记为藏族,因此尽管统计数字中的拉萨常住回族人口为3000 余人, 而藏回普遍认为本族群的人口为5000 左右。
拉萨藏回 “藏族穆斯林” 的族群自我定位也为其他拉萨市民特别是藏族民众所接受。许多藏族受访者表示,“藏回和我们没什么区别,只有名字不一样,再就是他们不吃猪肉。” 还有藏族受访者认为,如果仅从外貌和服装、语言等外在特征看,很难将拉萨藏回与本地藏族区分开来,二者间的外在差别远远小于拉萨本地藏族与从其他地区来拉萨的藏族群众的差别。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拉萨的藏族群众普遍推崇藏回所说的藏语,认为无论发音还是语言组织都堪称最标准、地道和典雅的拉萨藏语,特别是藏回对敬语的使用非常规范。
藏回族群定位的变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地方层面权力机关的认可。如前所述,尽管按照国家民族识别时的规定,藏回属于回族,然而在近年来的实际操作中,年轻一代许多人将民族身份登记为藏族,在藏回自我族群定位与当地社会中其他族群对其定位均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地方公安、民政等部门的变通做法相当于对既定变化的默认。另一个颇为有趣的例子是,拉萨藏回使用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上的文字出现了汉藏双语对民族表述不一致的现象:汉语的“民族” 一栏填写“回族”,而藏语 “脆安地罢邦”(即 “民族”)一栏则填写的是 “捶拜安地罢傍”(即 “藏族”);直到换发二代身份证,此现象才得以改变。[56]这一极其特殊的现象似乎表明,尽管国家为诸如藏回这样具有多元文化特征和复合心理认同的族群规定了单一、固定的民族身份,然而,不仅该族群的自我定位随着时代背景、政治气候、社会关系、族群结构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情境性的摇摆和转变,在地方社会的其他族群眼中,甚至于在地方层面的权力机关看来,其身份定位与官方的统一规定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可商榷空间,正如从“甲卡切” 到 “藏回” 的族群称呼所展现的那样。
注释:
①相关文章如马永龙:《西藏世居穆斯林及其文化变迁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②根据笔者对拉萨藏回的访谈,大多数人尽管对祖先事迹不甚了了,但基本都保存着祖先来自四川、陕西或云南省的记忆。在拉萨北郊夺底沟的格格霞回族墓地中,仍有若干清后期的墓碑留存,碑文标识了墓主身份和籍贯,如:“清逝者马公云麒之墓,嘉庆十二年九月初九,祖籍陕西秦州……,四川成都县落业……”;“先严脱中武,四川保宁浪中县,嘉庆四年二月廿八”;“清逝者马公成林,嘉庆十二年五月初十日,祖籍陕西固园人,落业军标右营”。
③刘曼卿为回族, 其先祖在清中叶随清廷使者入藏,并留居于拉萨,其家庭无疑是拉萨 “甲卡切” 群体的一份子。刘曼卿幼时生活在拉萨,9岁时与家人移居印度大吉岭,后定居北平。刘曼卿因藏语流利且关心涉藏事务而自请作为国府使者入藏,为当时官方沟通渠道不畅的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传递信息、沟通感情。刘曼卿到达拉萨时,本地一些甲卡切尚能认出她为 “刘家的姑娘”(刘曼卿《康藏轺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82页),可见从清中叶直至民国时期拉萨的甲卡切一直是一个成员间关系紧密、内聚性很强的群体。刘曼卿本人似乎并非伊斯兰教信徒,其书中述及某日入拉萨大清真寺听讲经,略记所听得教义并评论 “觉其说颇能自圆”(刘曼卿《康藏轺征》,第85页),言语间反映出她原本对伊斯兰教教义及相关知识较为陌生。
④此为1946年马建业的观察;1930年刘曼卿到达拉萨时,“行至清真寺一带,汉人回教徒多以四川土话相告,嗄刘家的姑娘呀,……”(刘曼卿《康藏轺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82页),可见相较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30年代初甲卡切使用汉语可能更为普遍, 据此或可推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藏地方与内地交往梗阻的这段时期的客观环境对甲卡切语言转变起到了加速作用,当然这一推测尚缺乏更多材料的支持。另外,即便在40年代后期,甲卡切也力图通过学校教育教授子弟汉语,一些精英也凭借汉、藏双语能力而得以供职于西藏地方政府,这些在后文中均有详述。
⑤“板吉” 意为 “五人”,一说为波斯语(陈波《拉萨穆斯林群体调查》,《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第89页),另一说源于印地语(David G. Atwill, “Boundaries of Belonging: Sino-Indian Relations and the 1960 Tibetan Muslim Incid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5, No. 3 (August) 2016: 602)。由于学识所限,笔者尚无力考证该词来源,姑且存此二说,以供识者考鉴。
⑥如商讨典礼中的礼仪问题(吴忠信:《入藏日记》,第262、265、266页)、转达和转询意见(吴忠信:《入藏日记》,第288、293页),等等。
⑦如安排宴会(吴忠信:《入藏日记》,第251页)、代表热振探望病中的吴忠信(吴忠信:《入藏日记》,第249页)、向吴忠信交送热振所赠之礼物(吴忠信:《入藏日记》,第271页),等等。
⑧“马鹤堂” 似为 “马和堂” 之讹。
⑨根据1951年随解放军到达拉萨的回族干部薛文波的描述,“在解放军进藏之前,在拉萨,除了藏人之外,其他族群的社会地位从高到低依次是是尼泊尔人、克什米尔人(卡切)、汉人、回族。” 见薛文波:《拉萨的克什米尔人》,《雪岭重泽》(卷二),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