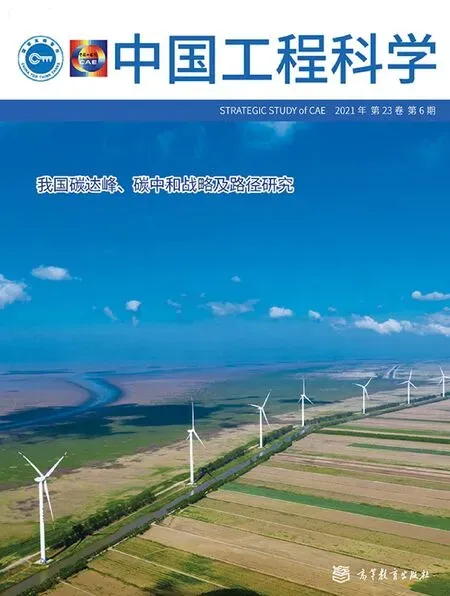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急支撑体系建设
李明穗,王卓然,武乐,蒋慧莉,杨俊涛,刘德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100730)
一、前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呼吸道病毒为主的新发突发传染病频繁暴发,如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2015年的寨卡疫情等。2019年末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的一次大考。
我国历经数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本形成了涵盖临床救治、病毒溯源、动物模型构建、药物疫苗和检测技术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多机构协作、多方力量整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急支撑体系。然而,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源头技术方面积累不足,生物安全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医疗器械的国产化率较低[2]。药物创新能力及产业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药物研发设备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医药研发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单个研发机构或企业承担难度较大 [3]。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药物疫苗研发能力、诊断试剂生产能力、防护装备储备能力、医疗器械供应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4]。与美国相比,我国数据资源中心、生物安全实验室等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和短板凸显[5]。为强化公共卫生体系的科技支撑,提升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的能力,我国需要着力破解公共卫生领域科技人才难题,不断探索完善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医学科学基础研究,探索疾病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机理研究,促进源头创新[6];摸清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对能力,从基础性生物实验技术、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防护设施、重要医疗救治和检测设备等方面找准“卡脖子”环节,确定科研主攻方向;重视研发快速反应技术平台和生物资源信息共享平台[7]。
二、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急支撑体系的建设现状
(一)科研基地平台布局逐步完善
截至2020年8月,我国已建成各类生物技术基地平台986家,包括生物医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74家(有5家属于多单位跨省共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31家、以企业为主体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1家、以医院为主体建设的各类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50家[8],针对常见多发病、重大慢性病、传染病预防控制与诊治、新药研究及中医药等方向进行了全面部署。建成亚洲最大的药物化合物库,优化建设国家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库等卫生健康领域的国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在COVID-19疫情中,依托传染病专项支持的“重大传染病应急处置检测技术平台”“传染病监测技术平台”,在5天内确认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为此次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分离出SARS-CoV-2毒株并拼接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得到WHO“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的高度评价。依托国家人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库,在全球率先建立COVID-19的小鼠、恒河猴、食蟹猴模型,被指定为国家疫苗药物评价平台;对首批8个疫苗中的7个进行评价,对上百种药物进行筛选和评价,为疫苗药物研发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大数据技术充分助力疫情监测和科研攻关
为开展COVID-19疫情防控监测,在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领导下,专门设立大数据专题组;科研攻关组成立信息化专班,综合全国确诊患者数、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外来流入人口、地理空间、遥感监测等由多个部委提供的数据,开展病毒溯源、传播链分析、疫情监测和风险评估[9]。为统一各地健康信息码,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出“防疫健康码”,累计申领近9亿人次,使用次数超过400亿人次[10]。
为促进科研攻关和成果共享,科学技术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中华医学会,建立防控COVID-19科研成果的专业性交流平台,集成共享COVID-19科研应急攻关项目的科研成果、研究论文、实验数据、临床病例、重要进展等[11]。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心及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术语集”,构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数据共享系统”,提供科学数据、研究文献、疫情报告、防疫指南、防护知识等信息服务。为促进SARS-CoV-2基因组数据共享应用,国家生物信息中心(CNCB)、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NGDC)及时开发并维护2019新型冠状病毒信息库(2019nCoVR),整合来自全球共享流感病毒数据库(GISAID)、美国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深圳(国家)基因库(CNGB)、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NMDC)、CNCB、NGDC等机构公开发布的SARS-CoV-2核苷酸和蛋白质序列数据等信息。NMDC建立了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与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NPRC)等单位联合建设“新型冠状病毒国家科技资源服务系统”,有力支撑了我国乃至全球冠状病毒数据汇集和共享分析[8]。
(三)公共卫生科技投入逐步加大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技术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于2009年启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重大研究计划共资助项目120余项,总经费达1.2亿元[12]。截至2020年,“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累计支持3000多个课题,中央财政投入达233亿元[13]。截至2018年,“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专项投入28 亿元,用于支持170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相关项目研究[14]。2020年,NSFC资助44个公共卫生领域项目立项,资助总金额为1795万元;陆续发布SARS-CoV-2相关的专项项目指南和长期计划(见表1),加强COVID-19方向的研究和应对力度[15~18]。

表1 NSFC发布的COVID-19相关专项指南情况
(四)科研成果应用有效转化
我国主动应对急性传染病、慢性重大疾病以及公共卫生、健康促进等健康需求,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艾滋病病毒核酸筛查试剂实现国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检测窗口期由28天缩短到11天;“血站核酸筛查”于2016年正式成为国家政策并覆盖全国。新型疫苗、免疫治疗等前沿技术研究进展显著。截至2019年7月,“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累计139个品种获得新药证书,其中1类新药44个[19]。截至2018年,累计超过280个通用名药物通过欧美通用名药物注册,29个专项支持品种在欧美发达国家获批上市,23个制剂品种以及4个疫苗产品通过WHO预认证[20]。基于Cortellis数据库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数据,2020年我国研发上市43种药物和疫苗产品,58项COVID-19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
(2)技术人员知识老化我国一些基层的兽医工作者,很多没有经过专业学校系统培训。而从畜牧专业学校毕业的人员,多数在县级和较大的乡镇工作,由于缺乏进修和技术更新,知识严重老化。目前,乡镇防疫技术力量薄弱,很难承担繁重的疫病防治工作任务,堵、防、检、控等综合措施的落实,缺乏应有的人员和技术支撑。
三、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急支撑体系建设存在的差距和短板
(一)公共卫生科技支撑原始创新能力有待增强
1.药物和疫苗研发能力
我国生物制药企业、科研院所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药物和疫苗研发能力逐步增强,然而在基础创新、中试及产业化、产品研发总量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基于Cortellis数据库,截至2021年9月,美国、欧盟、中国参与研发重大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SARS、流感、寨卡、埃博拉、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COVID-19)相关药物和疫苗的产品数分别为1102项、517项、437项;其中三方参与研发COVID-19病毒感染相关药物和疫苗的产品数分别为739项、365项、248项(见图1)。新药和疫苗研发资金需求大、研发周期长,如单项抗体药物研发经费需要2亿美元,在医药研发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甚至可达5亿美元,单个科研院所或生物制药企业独立承担的难度较大[3]。

图1 美国、欧盟、中国的药物疫苗产品参与研发数量(基于cortellis数据库,截至2021年9月)
2.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研发能力
高性能检测产品和医疗器械等防控产品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科技支撑,然而我国公共卫生相关的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仍较多依赖进口,原理性创新尤为不足。基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网站数据,近五年来我国研发重大传染病(见图2,包括COVID-19、流感、寨卡等)相关检测器械和病原诊断试剂的产品数为70项,美国对应为291项;2020年,我国COVID-19相关上市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的产品数为58项,美国对应为274项。由此可见,我国相关上市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的研发投入和产业规模仍需进一步扩大;涉及抗病毒药物、疫苗、抗体、器械设备等研发的交叉学科领域布局仍需完善,针对未知传染病的前瞻性、实用性探索研究有待加强。

图2 中国、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的检测器械和诊断试剂上市数量(2016—2020年)
(二)公共卫生科技资源基地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1.公共卫生资源平台建设
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亟需完善。国家生物医学数据存储、管理与共享平台,菌毒种、细胞株、实验动物、文献资源、人群队列等国家级高水平生物样本资源平台建设有待加强[21];生物医药技术和资源共享方面的国际依存度偏高,仍存在受制于人的情况。数据库、样本库、生物资源库等研究资源的汇交标准和共享机制有待健全,庞大的资源优势尚未转变为公共卫生科技产出优势[21]。
2.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
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缺乏合理布局,数量也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截至2020年,我国通过科学技术部建设审查的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有81家[5],真正投入使用的只有十多家;从地域上看集中分布在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从行业上看主要分布在海关、检验检疫、疾控中心等方面。美国几乎所有高水平大学医学院、医院都配备了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2011年美国即已建成1495 个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截至2017年12月,全球23个国家已建成和在建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共有54个,其中美国、英国、中国的数量分别为12个、5个、3个[22]。
(三)公共卫生科技应急支撑体系有待健全
1.公共卫生科技研究总体投入
我国公共卫生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医学方式列项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缺乏专门的医学科学基金,制约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支撑能力;公共卫生科研经费投入总量相较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有差距。2018财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统摄的生命科学领域经费总量达363亿美元[23],基于NIH RePORTER在公共卫生领域投入资金约181亿美元。基于NSFC的资助数据,2018年我国中央政府在生命科学领域投入研究经费约为130亿元,政府属科研机构支出研究经费约为2691.7亿元[24]。
2.国家级机构统筹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的能力
居于医学科技前沿的国家主要依托国家级医学研究机构,如NIH、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英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R)等,统筹分配国家医学健康领域的研究经费,引领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应急研究在内的国家医学科技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国家级医学研究机构的引领作用有待充分发挥。
3.公共卫生领域专业人才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关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在全国卫生人员中,疾控机构的卫生人员2009年的占比为2.53%,2020 年的占比为1.53%,呈持续下降趋势[25]。与此同时,我国从事疫苗、抗病毒药物、检测产品、医疗器械研发的专业人才相对匮乏,尤其是具备多学科知识基础、传染病流行理论和丰富国际视野及实践经验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四、强化我国突发公共卫生科技应急支撑体系的建议
(一)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效发挥科技支撑保障作用
强化基础医学研究能力。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以临床应用需求为牵引,开展新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毒溯源、传播途径、致病机理和危害致命性研究,建立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病原体组合筛查技术体系和预警溯源技术体系,全面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提升原创性医药产品和诊断器械的研发能力与响应速度。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部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药物和疫苗产品研发,加快推动疫苗的临床试验和上市使用,提高药物疫苗产品研发上市总量。加强高端医疗器械与检测试剂的研发能力、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提高关键原材料、高端医疗设备、检测试剂的国产化率。建立应急药物、疫苗、医疗器械产品储备制度,探索建立有效治疗药物、疫苗产品、医疗器械紧急使用授权管理制度。
强化高校、医疗机构、科技企业的紧密合作,建立高校、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围绕重大攻关任务的合作体系。为激发生物科技企业创新活力,建议相关部门联动给予政策倾斜,合理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企业应用基础医学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机制[26]。
(二)完善公共卫生科技资源基地平台建设,增强科技自主保障支撑能力
强化国家生物资源样本中心建设。加强菌毒种、细胞株、药用资源、实验动物、生物样本与人类遗传资源等国家级生物样本资源中心建设,成立大型队列项目和罕见病患者库,完善各类资源平台的汇交标准和共享机制,促进有限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
建设具有自我支撑能力的高质量数据管理和信息共享平台。借鉴NCBI、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PubMed)、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EBI)等机构的成功运行经验,建设国际一流的国家医学图书馆、本土化的全球生物医学文献检索系统和国家临床数据中心[21],推动实现生物医学、图书资料、科研文献、医学专利、临床试验数据等信息的高质量共享共用[7]。
完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国家级实验室布局。根据区域人口密度、病原检测和科研需求,合理增设区域化的固定式三级、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辅以小型移动式三级、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满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需求。强化公共卫生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行业引领作用。
(三)健全公共卫生支撑保障体系,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综合能力
加强公共卫生科技人才储备。改善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人才评价体系,打破唯论文和影响因子的评估方法。鼓励科研合作,淡化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身份认定。完善人才选拔聘用、培养储备和激励制度,多方吸引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建立国家和地方应急响应队伍,开展经常性应急防控演练。
充分发挥国家医学科学院的统筹引领作用。结合医学健康领域国家实验室建设,建立真正的国家医学科学院[21],借鉴NIH、INSERM、MRC等机构经验,充分发挥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医学科技创新的作用。面向居民生命健康,围绕医学科技创新重大战略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需求开展持续的科研攻关。整合优势科技资源和科研力量,统筹实施人口健康和生物安全领域科研布局,加强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卫生健康科技创新领域研究。
合理增加公共卫生领域科技投入。建议在现有五大科技计划(专项、基金)之外,成立专门的医学研究基金,独立管理卫生健康领域的科技资源布局[21]。持续稳定支持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