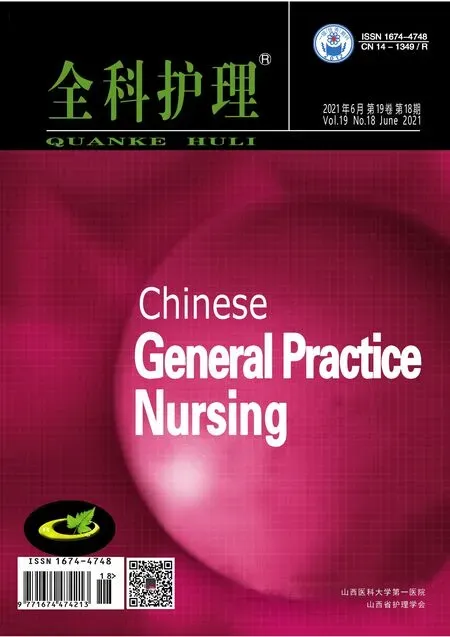女性癌症病人生育忧虑及其家庭功能的研究现状
杨亚宁,阮 真,胡艳梅
2018年全球癌症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癌症发病率及死亡率迅速增长,其中女性患乳腺癌、宫颈癌等的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1]。健康女性的生育力从30岁开始呈下降趋势,35岁以后明显下降,约41岁开始丧失,约50岁全部丧失[2],然而部分女性在确诊为癌症时其生育计划尚未完成,对于她们而言,癌症及其治疗对其生育能力及家庭成员生活质量都会造成严重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心理问题,从而使其生育忧虑和家庭功能问题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现对女性癌症病人生育忧虑及其家庭功能的研究现状、主要评估工具和护理干预措施进行综述,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女性癌症病人生育忧虑及家庭功能研究现状
1.1 生育忧虑研究现状 生育忧虑指个体对生殖及子女抚育方面的忧虑,包括对生殖能力、自身健康、子女健康及子女照护等方面的忧虑[3],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体对孕育及抚育子女方面的忧虑,这一方面的忧虑问题与病人癌症相比较,可能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压力且可以持续数年甚至是永远[4]。
首先,年龄是女性癌症病人生育忧虑的影响因素之一,年轻女性正处于生育的黄金阶段,担负着繁衍后代、抚育孩子及照顾家庭等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对抚育孩子存有强烈期盼,如果不能生育会对其带来巨大困扰,对其造成的心理冲击更为强烈,因此对自身的怀孕能力及子女健康的忧虑最为在意[5-7]。反之,子女数越多且年龄越长的女性癌症病人其面临的自我或家庭给予的生育压力越低,生育忧虑水平同时也越低[8-9]。
其次,家庭成员关系对女性癌症病人生育忧虑也有所影响,极端型家庭其成员之间或是过于疏远、缺乏情感联系,或是过于亲密致家庭角色区别不清,当面对女性成员被诊断为癌症时其家庭成员无法给予足够的家庭支持,较之平衡型及中间型家庭,极端型家庭成员的女性癌症病人的生育忧虑水平更高[10]。
此外,不同癌症类型对女性病人生育忧虑的影响也不同,妇科恶性肿瘤直接影响着女性的生育健康,对于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病人而言,其对自身的生育状况及儿女身体健康都更为担忧,生育忧虑水平较高,而非生殖系统肿瘤的女性病人,其生育忧虑水平相对较低[9-11]。
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女性癌症病人对生育忧虑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我国传统文化认为女性维系家庭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生育,女性有生育子女及传宗接代的任务,因此当有生育机会时便会努力尝试备孕[9-12]。
1.2 家庭功能研究现状 家庭功能是指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满足家庭成员各种需求的能力,体现于家庭成员间相互爱护支持、彼此间情感交流及共同承担生活事件、压力源[13]。
首先,女性罹患癌症后家庭成员关系的改变影响着其家庭功能,女性一般在家庭中承担抚育孩子的角色,在治疗过程中其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往往承担着一系列的心理压力,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要责任,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甚至是健康问题受到了一定冲击[14-15]。
其次,研究显示女性个体对家庭成员的依恋程度明显高于男性[16]。因此,当女性被诊断为癌症时,其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家庭亲密度增加,女性癌症病人对家庭成员的依恋及期待程度也相应增加,此时女性癌症病人需要其家庭具有较强的权利结构、角色分配或家庭规则弹性应变的能力,若其家庭适应性的变化无法满足到女性癌症病人的需求时,就会导致其对家庭成员及家庭适应性不满意程度的增高[11]。
病程治疗周期的长短对其家庭功能也有相应的影响,如宫颈癌的治疗周期较长,病人不仅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其家庭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心理及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家庭危机时有发生,家庭功能呈现恶化趋势[17]。
此外,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也影响着家庭功能的发挥,良好的家庭收入是维持良好家庭功能的保护性因素[15-17]。
1.3 两者关系 家庭是构成社会和人口生育的基本单位 ,是制约和影响人口生育行为的重要和关键因素[18]。家庭层次上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家庭成员个人生育意愿的综合,一般取决于家庭人口规模、权力结构、经济状况、成员关系及传统习惯等。
家庭功能对癌症病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9]。女性癌症病人的自身面貌、行为能力及角色转变都给本人及其家庭造成巨大心理压力,加重病人生育忧虑,而家庭功能状况是直接决定生育情况的因素之一,女性病人因癌症治疗等在家庭中的角色发生改变及家庭成员的一系列适应问题都将影响到女性病人,最终再回到生育问题,使得生育忧虑问题与家庭功能之间形成恶性循环[8]。
2 女性癌症病人生育忧虑及家庭功能评估工具
2.1 生育忧虑主要评估工具 我国当前对于女性癌症病人生育问题的相关研究较国外滞后,其中关于女性癌症病人生育忧虑的量性评估工具更为缺乏。因此,由Gorman等[19]研制的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Reproductive Concerns After Cancer scale,RCAC)成为目前评估女性癌症病人生育忧虑问题的主要工具。该量表共有6个维度,分别为怀孕能力、配偶知情、子女健康、自身健康、接受度及备孕,共18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代表病人生育忧虑程度越高,Cronbach′s α系数为0.78~0.88。该量表于2016年由我国乔婷婷等[20]进行了汉化,Cronbach′s α系数为0.72~0.86。
2.2 家庭功能主要评估工具 我国关于家庭功能相关理论的护理研究大多引自国外,评估工具多为国外学者研制且较少针对癌症病人。目前,针对癌症病人家庭功能评估工具主要采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及家庭功能评定量表等[15]。其中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mily Adaptation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 Ⅱ,FACES Ⅱ)的应用最为广泛[21]。该量表由Olson[22]编制而成,共有2个维度,分别为亲密度及适应性,共30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越好。该量表在大量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均体现出了良好的信效度[23]。
3 女性癌症病人生育忧虑及家庭功能护理干预措施
3.1 需求性信息支持 女性病人及家庭成员在面临癌症巨大威胁时会产生诸多需求,其中信息需求是重要部分。良好的信息支持对病人及家庭成员具有重要意义,如提供疾病、治疗及护理相关信息等。对病人及家庭成员进行长期、全面且系统的信息支持,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对疾病进行有效管理并适时提供生育信息的支持,提高家庭主要照顾者的照护质量、生活质量及家庭功能[24]。目前,我国癌症病人的信息支持多以病人住院期间为主,部分结合了微信平台、电话随访及健康手册等形式进行信息干预,未来仍需要进一步提升癌症病人信息支持水平[25]。
3.2 支持性心理干预 癌症对于女性病人而言是一个重大的精神刺激,不论何种治疗方式均会成为病人心理应激反应的压力源,同时对其主要照顾者也会产生多重压力。因此,健全的心理支持系统对女性病人及家庭成员正确认识疾病、积极采取措施保存生育力、缓解忧虑情绪、提高家庭支持程度和照护能力至关重要[26-27]。当前心理干预的主要手段有正念减压训练、认知行为治疗以及综合心理护理等,我国相关研究中多采用综合心理支持护理对病人进行相应干预,干预手段涉及放松疗法、情绪改善以及社区支持等[28]。
3.3 家庭护理干预 女性癌症病人对于治疗、康复、生育及家庭照护等方面的问题,均需要家庭成员的参与和支持[29]。家庭护理就是以家庭成员为服务对象,护士与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其中,确保病人及家庭成员的整体健康[30]。通过对病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家庭护理,病人及家属的心理健康及家庭功能等均得到了有效提高,并随着家庭功能的完善,病人的治疗依从性、生育忧虑问题也得到了相应改善[31-33]。然而家庭护理模式在我国尚未普遍开展,在部分经济发达和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城市发展相对较好,还需要更深入的探索及应用。
4 展望
我国癌症病人大多由其家庭成员担负照顾责任,而女性病人由于其在家庭中担负有生育抚养后代的责任,而在家庭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女性病人生育忧虑问题与其家庭功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作为护理人员,在面对女性癌症病人时首先要科学准确地评估其生育忧虑及家庭功能现状,才能有针对性对病人及家属进行干预支持,制定缓解病人生育忧虑及提高家庭功能的策略。虽然,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相关护理规范,但随着医疗进步及护理模式的不断发展,相关治疗及护理规范的制定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