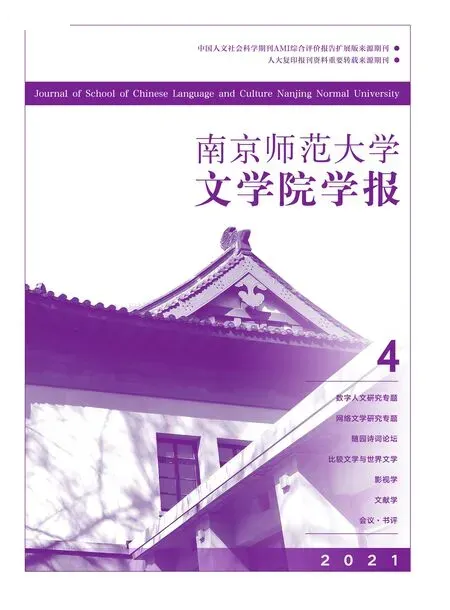现代性的忧思
——论杨德昌电影的人物图谱与教化思想
曹 桐 朱 洁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江苏 南京 210008;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4)
杨德昌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重要旗手,其极具现实批判性的创作视角和不拘一格的现代表现手法,开辟了台湾电影的新里程,并在华语电影史上立下了一座丰碑。杨德昌等台湾第二代导演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彼时的台湾影坛充斥着大量武打片和琼瑶言情片,缺少讲述台湾本土故事,展现社会现实的影片。“崛起的新一代导演们彻底摈弃了商业企图的逃避主义,努力地从日常生活细节或既有的文学传统中寻找素材,为当代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塑像。”[1](P166)
相较于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另一位领军人物侯孝贤对于乡土情怀的钟情,杨德昌更加执着于表现当代台湾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他的八部电影都聚焦于台北这座飞速发展的大都市,以知识分子式的批判精神对当代人的生活状态进行剖解,塑造了具有代表性的都市众生相,呈现出现代人异化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样貌。
从杨德昌电影的系列人物中,可进一步解读出作者的价值取向与道德立场。杨德昌所塑造的男性形象多以负面、虚弱的特质出现,即使正面人物亦总带着迷茫的彷徨感;而女性形象多以清醒、独立的姿态出现,即使反面人物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通过对性别权力的颠覆性构建,杨德昌表达了对传统主流价值的悖反,以及对新道德秩序的呼吁。在犀利的批判视角下,杨德昌电影也始终聚焦当代社会的教化与成长主题。在父亲这一形象的构建上,杨德昌电影中的父亲身份经历了缺失、缺损、重构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又可看出作者对传承与教化的态度从批判、怀疑直至憧憬与肯定的过程。杨德昌借助“永远的儿子”“崛起的母亲”人物图谱表达了对台湾历史与现状的反思,并通过对“理想的父亲”的构建表达了对现代人未来出路的期许。
一、 “永远的儿子”: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呈示
杨德昌电影中塑造的男性形象多被一种虚弱的无力感笼罩。对此,香港影评人纪陶认为:“杨德昌电影中的男性角色是‘永远的儿子’,即使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儿子,这些‘永远的儿子’也没有能力为自己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更无力为自己找到一个恰当的个人定位,从而获得幸福感”。[2](P38)纵览杨德昌的系列作品,我们大致可以将男性形象分为社会道德的“逆子”、随世沉浮的“庸子”和内心煎熬的“苦子”三种类型。
社会道德的“逆子”代表的是一批漠视社会道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男性。杨德昌往往选取中产阶级都市男性作为此类人群的代表,他们在生活中蝇营狗苟,以权利、金钱、性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驱动力,站在传统道德的反面,是现代人性异化的象征。例如《恐怖分子》中为了晋升不惜出卖好友的李立中;《独立时代》里在朋友面前两面三刀,在女人身边四处留情的Larry;《麻将》里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让纯情的少女卖淫的红鱼……他们每一个都在中产生活的追名逐利中逾越了道德和良知的底线。这一类人物的结局往往没有善终。婚变后李立中晋升的机会被他人顶替,落得人权两空;机关算尽的Larry失去了心爱的女人;“红鱼”精神崩溃,开枪杀人……从这些人物的结局可以看出杨德昌鲜明的道德叙事立场,但作者的审视态度,却自始至终带有一丝关怀与悲悯。这些看似反面的人物,亦具有十分详尽的人格世界和成长前史,他们的人生选择或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或是受到身边人的歪曲诱导。逆子的形象符号,象征着现代台湾乃至现代华人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之恶。在急剧发展的现代文明面前,被扭曲的儒家文化以及被漠视的传统道德,形成了当代人性的异化以及现代精神的困境。
随世沉浮的“庸子”相较于“逆子”,缺少了一定的“进攻性”,他们不再是社会恶行的始作俑者,而是在社会大流中随波逐流、无主见的庸人。他们或愚蠢,或偏执、懦弱,但又或多或少残存理想的善念和本心。《独立时代》中的阿king,出身富贵,任由家里为他安排一切,却仍真心渴望一份自主的爱情和事业;《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马,本性仗义豪爽,但在混沌迷惘的白色恐怖年代,迷失在少年们轻浮浪荡的风气之中。“庸子”们处在现代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中,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顺应本心的决心,半推半就地做着昧心逐利之事。就像《独立时代》中的小明所说:“我就喜欢跟别人一样,跟别人一样有什么不好?”大多时候他们并未察觉苟且有何不妥,但在内心深处又深知自己的无奈与懦弱,会在极度脆弱时暴露本心,直面内心的不甘。如《一一》中的阿弟,本是一个浮躁混世的油腻青年,可当他看到新生幼子时却无缘由地崩溃痛哭。这一情节充分展现出杨德昌给“庸子”们设定的深沉的内心世界——幼子无暇,在“庸子”面前呈现为映照自身的镜像,使他照见了自身的不堪,呈现出平日压抑着的懦弱与愧怍。在新生命面前“庸子”不得不直面自我,不得不反思下一代的出路,不得不对后代诞生在此世间感到不忍和忧思。这一类人物,是对台湾新兴中产阶级概貌的真实写照,代表着最广泛的普罗大众。他们并非失了良知,但却在时代浪潮中失了本心。对于这份平庸之恶,杨德昌寄托了最深切的怜悯与讽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内心煎熬的“苦子”,则是杨德昌塑造的最悲情的一类人物。他们纯真的良知和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无法与这混沌的世道和解。他们多是电影的男主角,是“永远的儿子”男性图谱的主体符号,也是杨德昌作者表达的直接寄托。他们不像“庸子”,可以在无意识的愚钝中荒度半生,“苦子”们的良知与理想恰恰太过清醒,不甘同流合污,却无它路,只能隐忍沉默。《海滩的一天》里的佳森,在严酷的家庭纪律下接受包办婚姻,放弃了青梅竹马的爱人,在残生中逐渐被人遗忘;《独立时代》中的小明,看不惯官场中的尔虞我诈,但又不愿跳脱安稳的生活;《麻将》里的纶纶,不愿与帮派中的其他人同流合污,但除此之外又无安身之处……在杨德昌的电影中,他们是最具道德自觉的男性形象,但又都缺少了传统男性叙事中果敢、无畏的英雄主义特征。“苦子们”体现出了男性力量的去势萎靡,以及男权主导的宏大叙事的消沉,承载了杨德昌电影对于现代性反思的精神核心。
杨德昌始终以手术刀般的犀利视角切开现实的侧面,从现实广度与历史纵深的双重维度,对于当代人性困境进行反思。在艺术表现上,他与录音指导杜笃之一起发展了照相写实主义,以精炼的视听元素,将生活中的场景、细节一一还原。都市的场面多以全景、远景调度,既给演员充分的自由表演空间,又囊括了大范围的城市景貌,时刻强调着城市与人的空间联系,凸出了人与社会环境的从属关系,喻示着个体在环境中被塑造的现实,使得现代众生态在空间的横向广度上被全景式呈现;人物塑造与故事的展开中,他又极力将台湾近现代发展历程以小见大地融入个体角色的人生轨迹中,通过展现历史对个体的影响,对现代性问题在时间上形成纵向的深度溯源。“永远的儿子”在三种类型的人物塑造中呈现了台湾当代人性的广泛困境,而要追溯当代人性格命运的历史年轮,则要结合台湾近现代历史进行审视。
历史和传承这两大范畴成了台湾新电影不同于其他地区电影新浪潮运动之处:法国、日本、香港等世界知名新浪潮电影运动大多试图隔断和过去的联系,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去呈现新电影的宣言。而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手们认为,现代人的种种疑惑都来自于过往的历史。这与近代台湾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经历了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国民党退守统治、内陆移民迁入、戒严令时期、西方地缘政治角色等多重特殊历史影响,台湾新浪潮代表们所呈现的台湾文化气候与历史记忆中,历史既决定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基因,又阻碍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步伐,以此造成了现代人性的彷徨。如侯孝贤的自传式四部曲《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和《童年往事》及随后的“历史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和《好男好女》,也很明显的涉及了对于历史的追问与纪录。台湾新电影运动如此关注“历史”和“传承”,或许是因为国民党对历史问题的种种查禁:一方面,为了了解现在,走向未来,人类必须明白过往;而另一方面,为了能够自立于世,人类必须有对价值观的传承。[2](P40)
在杨德昌电影里,男性的悲剧也多基于一定的历史决定论——人物的境遇与人格形成,多源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水土不服。《海边的一天》中给佳森带来悲剧的原生家庭,既带有强烈的传统宗族观念,又混合了日本残留在台湾的严谨刻板的礼教;《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最终制造血案的小四,成长于内陆移民家庭,混迹于白色恐怖时期的少年帮派,复杂混沌的成长背景给青春期蒙上了沉重的阴影;《独立时代》将儒家传统文化放置现代台北进行讨论,从一众男性群像身上,都能看到传统文化思想在都市法则中的迷失与变异。“永远的儿子”呈现了现代台湾男性的弱化形象,这一形象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代台湾社会的政治现状:既要服从古老的传统,又一度屈服于殖民统治,台湾人始终有一种需要依赖别人才得以立足的无力感。
二、“崛起的母亲”:主流价值的叛逆书写
通过对现代男性困境的塑造,杨德昌解构了男性所象征的主流叙事的整一性,喻指现代社会传统宏大意义的消解。而杨德昌电影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并非是父权制度下唯唯诺诺的依附品,大多是具有觉醒意识的独立女性,纵使是反面人物,也都展现出了强大的行动力与自我欲望。杨德昌所描绘的女性力量的崛起,恰恰是借性别不平等的破与立,展现对于现代性困局的反思与探索。作为男性作者的杨德昌,借“她者”寄托了对现代人理想精神状态的想象。
从杨德昌第一部短片作品《光阴的故事·指望》开始,他就开始聚焦女性人物的个体意识,希望能够通过女性的成长来反映社会现实。他曾经说过:“女性的敏感使得社会的变化在她们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从她们那个角度切入更容易看到社会变迁。”[3](P216)在第一部电影中,杨德昌便开始有意识地对女性欲望进行书写,借女性意识的觉醒,表达对传统主流价值的反思与叩问。《光阴的故事·指望》讲述了中学生小芬不仅面临着身体变化的焦虑,也同时经历着年轻英俊的大学生入住家中的风波,处在懵懂悸动的青春期里,小芬经历了一场苦涩的成长。影片用了大量直白的特写镜头表现小芬凝视大学生青春洋溢的身体,以此表现她内心的慌乱以及懵懂欲望的苏醒。不同于大多数男性导演将女性作为被凝视的个体,在《光阴的故事·指望》中,男性和女性“看与被看”的关系发生了置换。女性不再是被凝视者以及欲望的投射,而成为了欲望以及凝视的主体。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认为:“在性别不平等的世界里,看的快感变成两个方面:主动/男性和被动/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性凝视把他的幻想投射到具有类型化的女性影像上。在女性传统裸露角色中,女性既承担被看又承担被展示,外貌也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感和性感效果,这样她们就被说成是有着被看性的内涵。”[4](P102)性别凝视主体的转变,暗示了杨德昌电影中男女权力关系的颠覆,此类女性的主体凝视在《海滩的一天》《麻将》《独立时代》中均有呈现。从第一部电影开始,关于女性欲望与权力意识的表达,便成为了杨德昌“崛起的母亲”重要的精神内核。
“崛起的母亲”们大都敢于摆脱束缚,直面欲望,甚至向传统社会规范发起挑战。就像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样,杨德昌影片中的女性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并不是男性或者男权主义下的附属品,是拥有自我欲望的主体。[5](P54)《恐怖分子》里的小说家周淑芬终日忍受着和丈夫貌合神离的寡淡日子,事业也遇到瓶颈,而当她与旧情人重逢后,顺应欲望重燃爱火,自己的写作事业也随着心火重燃迎来高峰。如果说周淑芬作为欲望主体的觉醒,是对传统社会道德的背离,那《麻将》中的安琪则更是深谙权力与欲望规则的“恶之花”。安琪十分擅长利用自己的美貌在男性世界牟利,甚至能让自认老辣的“逆子”们栽跟头。片中名叫香港的少年是一个浪荡的花花公子,他擅长巧言令色欺骗纯情少女,使她们沦为自己手中的玩物。而在影片结尾,更为老辣的安琪也同样将香港的男色“物化”,在安琪的手段下,香港曾经犯下的恶行全部被施还到自己身上,沦为一群成年女性发泄欲望的工具。在《麻将》中,女性原本是香港等男性们的欲望投射,但通过叙事反转,女性从被凝视的客体成为凝视的权力主体,象征着杨德昌对于当代两性权力关系以及传统社会价值的重新审视。
杨德昌对于男女性别权力关系的颠覆性处理,一方面体现了他作为男性创作者对男性群体的审慎姿态以及对于异性凝视的美化与升华。另一方面,女性叙事的根本性意义,是基于一种反叛、解构的叙事出发点。电影中的女性视角应被理解为一种差异性的存在,这种特异的生存经验,长期以来被一种所谓“主流”“整一”的叙事所掩盖,不曾被发现和诉说。在男性占据言说者位置的社会里,男性是主流的同义词。主流叙事所反映的,就不只是男性的性别化的身体所感知的外部世界,更有与性别化的身体所处的权力位置相关的感知习惯。对这种差异性的经验拥有高度自觉,并以主体的姿态去呈现这种经验,使其成为所谓“主流”叙事之外的、与之相抗衡的陌异之声。[6]
“崛起的母亲”们所具有的反叛意味,亦背反了“母亲”一词所带有的养育属性。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并不承担着对于男性们教化的“养育”义务。她们的人物弧光以大破大立后的自我成长告终,并多采用开放式结局作为人物终点。如《海边的一天》中的佳莉选择遗忘丈夫,毅然远走;《独立时代》里的琪琪与爱情和事业勇敢了断;《一一》里的母亲选择放下妻子、女儿身份的找寻内心的宁静。独立的“母亲”们走出家庭、走出男性凝视、走出世俗的规范,但开放结局一方面给观众留以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又可能是对无解现实的留白。杨德昌表现的女性力量是相对于男性人物的虚弱、丑恶而成立的,是男性导演借“她者”视角对男性所象征的主流价值的批判工具。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刻意强化的博弈趋向。颠覆性的反叛精神在其特定的戏剧语境成立,但普适性与教化意义较为局限。杨德昌所树立的女性力量,更像是一种启蒙的符号,是作者抨击僵化传统的武器,是主观视角下孕育理想人性的“母体”。
三、 “理想的父亲”:完成传承和对教化的重构
杨德昌通过揭示现代人道德迷失、价值混乱的混沌图景,表达了对现代台湾中产阶级生存状态的审视和忧思。在批判的同时,他也在不断的反思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出路。《独立时代》的开头,杨德昌在字幕中引用了《论语·子路篇》中的一句话:“既富矣,又何加焉?”《论语》原文中,孔子答:“教之。”然而,杨德昌故意将这句回答在字幕中隐去。很显然这是他刻意留白,希望观众去发现的,也是他真切思考的核心问题——如何教化启蒙当代人?
成长与教化是杨德昌电影关注的重要母题,而比起成年人的成长,杨德昌对青少年的成长给予了更多的关切。在《海滩的一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恐怖分子》《麻将》以及《一一》中,青少年多被放置在了成年人构建的复杂、混沌的现实世界,自我本心与成长环境、社会规训之间不断发生碰撞。在这些苦涩的成长历程中,家庭与代际传承又是杨德昌的重点表现对象。杨德昌始终秉承对历史的反思,在他的镜头下,家庭成为台湾社会的缩影,而代际传承则是历史影响的缩影。卢梭在《理想国》中提出,“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首领就是父亲的影子,人民就是孩子的影子。”[7](P32)父亲在人类社会结构中不仅有养育、保护家庭成员的义务,而且作为外界权威的化身,也有着规训和教化家庭成员的责任。因此父亲的角色往往在艺术作品中成为“超越具像关于传统、秩序、权威的巨大象征符号”。在杨德昌的电影中,父亲的角色也经历了一个由缺失弱化到强化重构的过程。[8]
在杨德昌的首部作品《光阴的故事·指望》中,母亲抱怨联考失利的姐姐,“自从你们父亲过世,我早晚上班维持这个家……如果你不好好上补习班,既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爸爸。”这是父亲形象在影片中仅有的提及。而从小与母亲和姐姐一起生活的小芬,她的生命中一直缺少一个理想的男性形象,直到上门租房的大学生房客出现。当小芬表现出对于大学生房客的迷恋时,实际上是对缺失父爱的移情;在《恐怖分子》中,不良少女淑安的父亲形象也是缺失的。当淑安腿摔伤后,母亲回家拿起桌上的书本打骂她道,“你是没人要,没人教训是不是,有办法的话就跟你爸爸一样,死出去就不要再回来”,随后母亲将她关在家中养伤。在小芬和淑安的成长过程中都是由母亲扮演了父亲的角色,承担了惩戒和教化的责任。然而这样的规训多是无力且苍白的,且常带有独身母亲特有的哀怨、愤恨的负面情绪,在对后代的教化中只形成了相反的抵触力。在这些影片里,父亲教化的缺位,亦以其“不在场”形成了一种戏剧张力,使得“理想的父亲”形象像幽灵一样游荡在青少年的潜意识里,因为缺失从而渴求,因为渴求从而痛苦。
在杨德昌的其他早期影片中,父亲身份即使出现,也大多体现为古板的“庸子”或失德的“逆子”,他们身为人父的缺陷,也往往会在代际传递中得到延续。如《海滩的一天》中佳森的父亲是个保持着殖民时代日本传统生活的保守家长,古板守旧的观念也深刻影响了加森,让他放弃了更广阔的人生机遇,而选择继承家族小诊所,成为永远无法出头的诊所大夫;《麻将》中少年红鱼的父亲,是个事业成功但德性败坏的商人,耳濡目染的红鱼始终以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作为立身原则,他既看不起父亲,又自始至终沿着父亲的轨迹成长着。此类缺损的父权形象塑造,是杨德昌对台湾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当代社会弊病的反思与投射;此类代际关系的呈现,意在表现作者观点——当“永远的儿子”成为了父亲后,现代人的彷徨与无力感仍会代代传承。
早期的杨德昌电影所展现的僵化的家庭关系与反面的教化传承是沉重而绝望的。但在后续的创作中,杨德昌开始对父亲形象进行构建,逐步向着“理想的父亲”迈进。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开始,父权教化者开始以“苦子”的形象出现。主角小四的父亲是个有文化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当儿子在学校遭受不公对待时,他敢于为孩子出头,并教导小四坚持原则的正直态度,实现了父权对子女内心秩序与权威象征的构建。但父亲身为随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内陆移民,在“白色恐怖”年代,对于未来的人生也充满着焦虑和茫然。他被朋友陷害进警局接受监禁审讯,之后性情便判若两人,变得唯唯诺诺,也失去了过往的书生意气。退行回了虚弱的“苦子”,而父权偶像的坍塌也间接导致了小四生活信仰的崩塌,“理想的父亲”成为昙花一现。
在杨德昌最后一部影片《一一》中,导演真正完成了对于“理想的父亲”的形象构建。
该片于2000年问世,同年,杨德昌喜为人父。或许也是受此身份转变的影响,在《一一》中,杨德昌在一贯的现实批判里,融入了对于教育和传承的新思考,他不再带着审判的眼镜看世界,而换了一种更加柔和的表达手法。[2](P148)
在《一一》中,杨德昌明显流露出对下一代寄予的希望。主人公南峻是一个典型的“苦子”,家庭中的变故、事业上的违心、与初恋的重逢无一不让这个疲惫的中年男人倍感煎熬,可他对孩子却满怀体贴与关怀。小儿子洋洋最初困惑于“我看到的你又看不到。”父亲便教导他用相机拍下自己看到的世界,从此洋洋便一直执着地拍摄他人所看不到的景象——人们的后脑勺、空荡的楼道、校园的角落。“这就是他们说的前卫艺术耶”,愚蠢的学校老师对洋洋的照片大肆嘲笑,却无意中点出了洋洋行为的真谛,洋洋无意识的实践,却践行了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摄影机是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的眼睛。杨德昌所刻画的成人眼中的世界,是无法彼此共情的、充满矛盾和困惑的沼泽,但南峻对幼子的纯真的守护却隐隐透出了一道希望之光——纵使“苦子”们依然深溺苦海,但他们可以引导下一代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胸怀去接纳世界,毕竟,“我”看到的,和“你”看到的或许会不一样。《一一》在一众苦涩的现代群像中,传达了一抹淡淡的温情,树立了一份新的道德憧憬。
通过对父权教化意义的重构,杨德昌意在化解当代都市人的疏离与隔膜,重构关系中的真情与信任。在马丁·布伯的关系本体论哲学里,世界的本体由关系构成,分为“我与你”和“我与它”两种。当“我”作为主体带着目的和期待去与世界发生关系时,世界便会变成为“我”所用的客体,成为一种经验和利用关系,“我”就与他者构建了“我与它”的关系。而当“我”与“你”处在平等的,不失去彼此主体性特征,且全然相遇时,双方体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受,即形成了“我与你”的关系。马丁·布伯认为“我与它”的关系是人类世界依存的重要前提,人们会不断利用其他客体为自己服务,然而如果只拥有这一类关系,人们就会陷入迷茫和困境。“我与你”才是人性交往中真正的滋养关系。这看似是一组十分抽象的概念。运用杨德昌电影中的人物关系来理解,人与人之间多数处在“我与它”的关系中,个体立足于私欲和目的性,即使是最亲近的家人,也没有能全然的接纳对方,彼此的隔膜让他们无法拥有深度关系。人们都穿着自我的外壳相互碰撞,却无法让外壳下柔软的真我相互触及,那层壳就是“它”,柔软的核就是“你”。而当我们慢慢打开自我外壳的缝隙,让内在真我透出的光互相照见彼此时,即完成了“我”与“你”的相遇。这样的相遇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十分罕见,可为数不多的桥段都如平地惊雷般震颤人心。《独立时代》结局里,放下一切分手的恋人最终选择奔赴相拥、《一一》中两位孙辈对祖母跨越生死的自白,都表现出了个体全然相遇后超越自我的强烈共情性。
杨德昌以往的影片在主题教化功能上,多是通过对异化的现代价值体系的大破大立,以后现代的解构方式使观众从片中人物身上实现自我投射,从而获得对现代生活的警醒。而《一一》虽依然坚持对于现代价值的批判,但也首次平实地将影片回归到了爱与接纳这一经典主题。这或许却是杨德昌历经半生后返璞归真的内心写照。正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罗杰斯所说:“最好的爱,是深深的理解与接纳”。[9](P64)面对现代社会人伦关系与道德意识的滑坡,既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是个体的内在问题,影片回归到基础的家庭个体,从基本的亲情单位,让人们重新学会爱,然后以个体微薄的努力与温情,以全然包容的爱与关心让彼此的真实相互照见,融化冰冷的壁垒,滋养彼此的灵魂。洋洋的成长,既是杨德昌对于下一代的希望与祝愿,亦是对于当代成年人满怀憧憬的期许。《一一》的片名可有十分多意的解读,它有节拍的韵律美、有对中华文化返璞至简的内在隐喻,但更鲜明的含义,是呼应了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传统概念,生命周而复始,新的生命是被父辈的观念、行为一针一线编制而成。为了下一代,为了终结“永远的儿子”,现代社会需要“理想的父亲”。
《一一》既是杨德昌个人风格的集大成之作,又是一次大胆的创新,本应是他承上启下的新起点,可天妒英才,《一一》却成为了杨德昌留给世界的一份震撼人心的遗嘱。在他的电影中,在纷繁的现实世界里还有无数长不大的孩子仍活在自己的无力与迷茫中。杨德昌已永远地离开,但他留下的电影和期许依然会陪伴着长不大的孩子们继续寻找与世界和谐共处的方式,帮助“我”遇见“你”。
杨德昌电影聚焦台湾本土都市人群的生存状态,成为独特的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台北都市影像志。在本土化的地域影像的背后,他所展现的当代华人社会的人性症候,以及儒家文化在现代文明中下的发展瓶颈,又对现代中国人的整体生存状况有着鲜明的客观参照。
中国海峡两岸虽然受独特的历史政治影响,但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传统和相似的经济现代化步调。经济的飞速崛起、中华民族不断崛起的宏大叙事正在上演,而繁华与虚无并置的现代化城市况味也在不断放大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冷漠。杨德昌电影所呈现的中国都市困境与人性群像,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仍能形象对应,其作品超越时代的价值不言而喻,对于现代中国人的影像身份建构以及教化启蒙仍然具有重要意义。